相關專欄
書活網特推
★台灣國民戲劇:吳念真和綠光劇團的感動呈現 「人間條件」1+2+3+4+5+6全典藏,6集完整戲劇DVD&6集劇本書,全套合購原價4660元,圓神書活網獨家念真情價2665元!
內容簡介
吳念真累積多年、珍藏心底的體會與感動。
全台灣最會說故事的國民作家,暌違12年感人之作!
他寫的每個故事,都蘊藏了我們無法預知的生命能量與心靈啟發。
跟他一起回望人生種種,您將學會包容、豁達與感恩……
本書是吳念真導演經歷過人生的風風雨雨和最大低潮後,所完成的生命記事。
他用文字寫下心底最掛念的家人、日夜惦記的家鄉、一輩子搏真情的朋友,以及台灣各個角落裡最真實的感動。這些人和事,透過他真情摯意的筆,如此躍然的活在你我眼前,笑淚交織的同時,也無可取代的成為烙印在你我心底、這一個時代的美好縮影……
吳念真的真心話:
回憶是奇美的,因為有微笑的撫慰,也有淚水的滋潤。
生命裡某些當時充滿怨懟的曲折,在後來好像都成了一種能量和養分,因為若非這些曲折,好像就不會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見別人可能求之亦不得見的人與事;而這些人、那些事在經過時間的篩濾之後,幾乎都只剩下笑與淚與感動和溫暖,曾經的怨與恨與屈辱和不滿彷彿都已雲消霧散。
至於故事裡被我提及的所有人……我只能說:在人生的過程裡何其有幸與你們相遇,或輾轉知道你們的故事;記得你們、記得那些事,是因為在不知不覺中這一切都已成了生命的刻痕,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
只是……你們也還記得我嗎?
特別收錄 吳念真近年唯一小說創作<遺書>,寫下對胞弟離開人間的真情告白與不捨。
特別邀請 作家雷驤繪製插畫,看兩位大師以圖文激盪出的精采火花。
作者介紹 吳念真
全方位的創意人、電影人、廣告人、劇場人。
本名吳文欽。一九五二年出生於台北縣瑞芳鎮。一九七六年開始從事小說創作,曾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報小說獎,也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並著有多本暢銷經典作品,如《台灣念真情》系列等書。
一九八一年起,陸續寫了《戀戀風塵》《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無言的山丘》《客途秋恨》和《悲情城市》等七十五部電影劇本,曾獲五次金馬獎最佳劇本獎、兩次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改編父親故事而成的電影處女作《多桑》,獲頒義大利都靈影展最佳影片獎等獎項。
主持TVBS「台灣念真情」節目達三年,導演企畫及代言的廣告數十支。
二○○一年,舞台劇處女作《人間條件》獻給了綠光劇團,隔年又編導了《青春小鳥》。二○○六年,推出《人間條件2──她與她生命中的男人們》;二○○七年推出《人間條件3──台北上午零時》;二○○九年推出《人間條件4──一樣的月光》等系列作品,再次成功詮釋「國民戲劇」。
現任「吳念真企劃製作有限公司」董事長。
得獎紀錄
★2012 年
博客來華文文學Top5
蟬聯台北市圖年度借閱文學類冠軍
「一書一基隆」年度推薦
★2011年
博客來暢銷Top7,文學Top3,暢銷華文作家No.6
金石堂文學類Top3
台北市圖年度借閱文學類冠軍
入圍台北國際書展書展大獎。
代表參加2011首爾書展,法蘭克福書展。
高中職百校師長共推Top100
獲選台中之書。
高雄市「一城一書」Top10。
入圍新北市、宜蘭縣、花蓮縣「一城一書」決選書單。
入圍第10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
★誠品華文文學冠軍,博客來文學冠軍,金石堂文學冠軍
規格
ISBN:9789861333458
頁數:240,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789861333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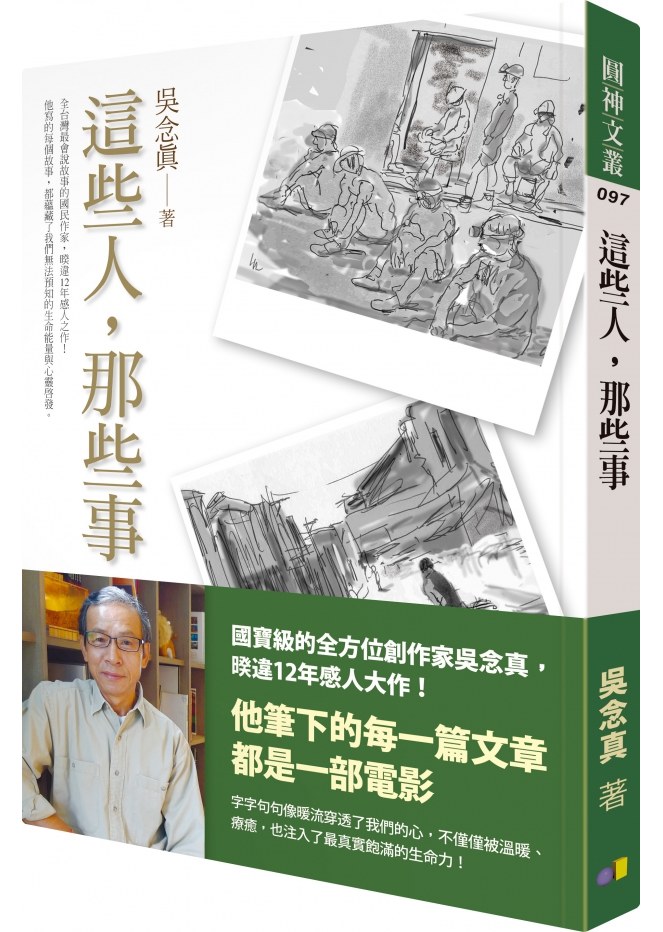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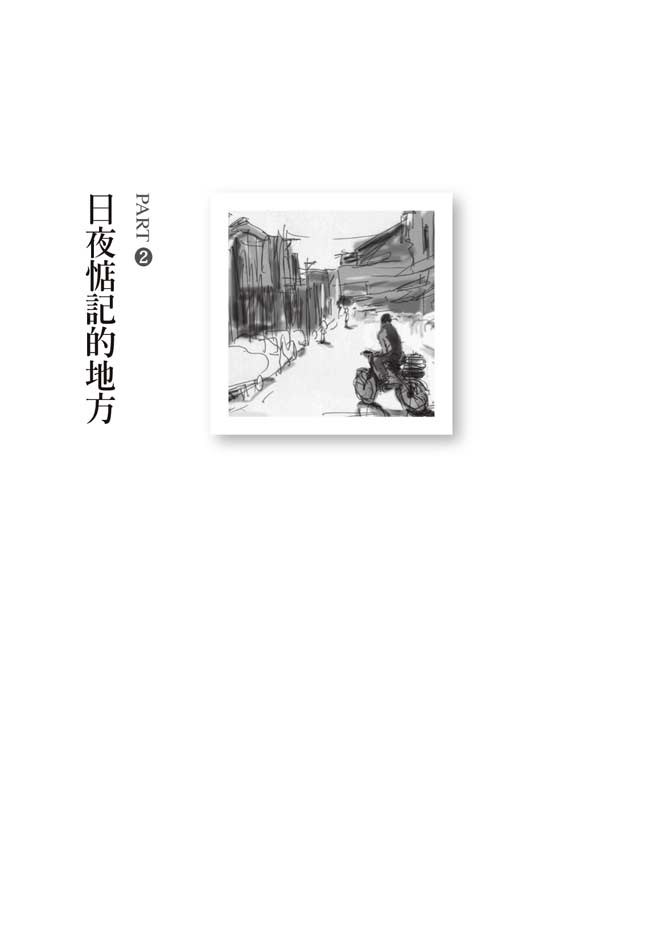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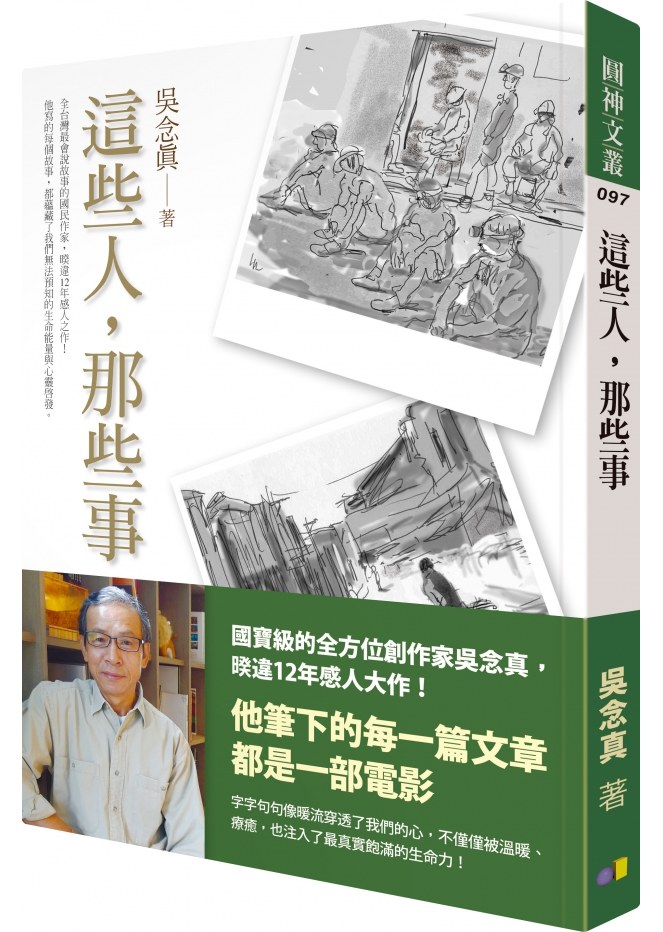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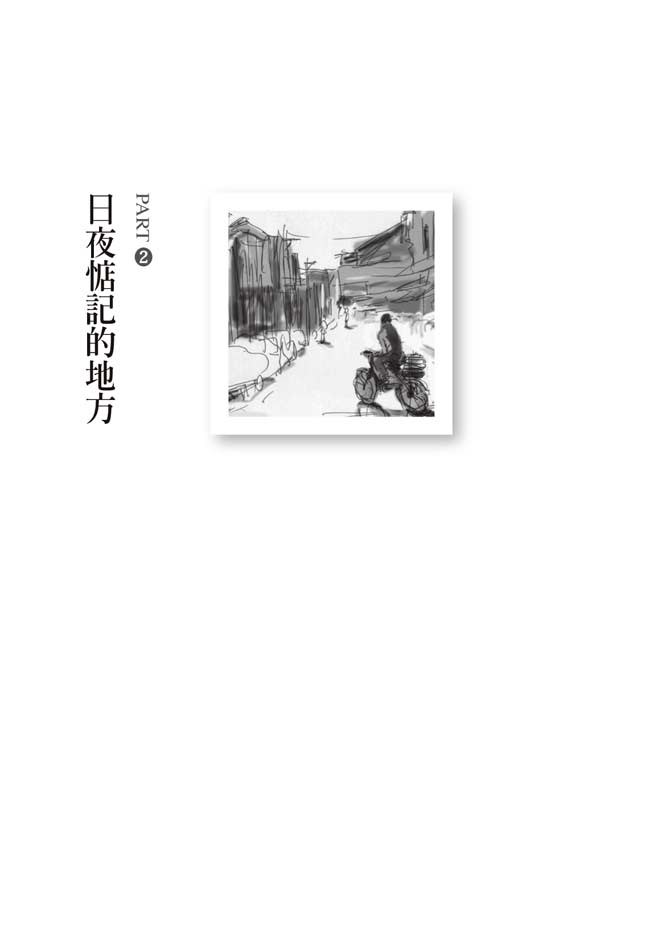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