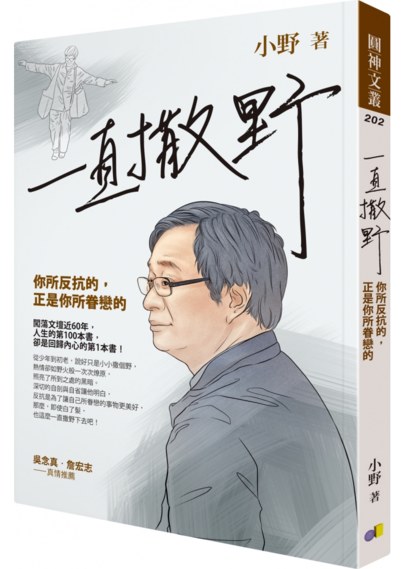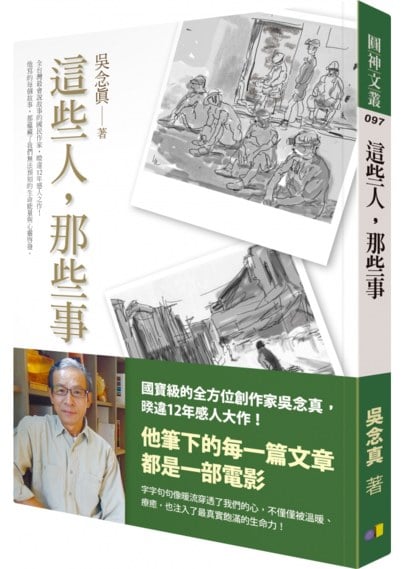「想改變什麼」的基因從沒變過/吳念真
野公「又」要出書了。 據說是「深具意義的第一百本」「以及……裡頭提到你很多次」,所以編輯說要寄書稿給我看,然後幫他「寫幾句你想講的話」。 她真的不知道這兩個老先生之間的恩怨情仇。
多年來兩個人只要提到彼此絕對沒有好話,許多朋友甚至以看到我們相互漏氣、抹黑、嘲諷為樂。 所以……如果為了他再度出書而特地講些歌功頌德、吹捧拍馬的話,老實說,我真做不到,而且也違背「固有傳統」,所以我還是選擇實話實說。
第一百本……對小野來說其實並沒什麼特殊意義,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有人跟我說:「小野實在了不起,勤寫不輟、著作等身!」當時我的回答是:「這倒是實話,因為他的確不高,而且蓄意把字體放大,讓書長得很厚!」
早年他有新書出版送給我的時候,都會用近似小學四年級水準的字體(而且迄今毫無長進)寫上:請念真指正。後來大概發現我根本不具任何指正的資格吧,所以通常就直接往我桌上一丟說:「不好意思,又出一本,哈哈哈!」
明眼人應該可以看出、聽出這語意和笑聲所傳達的驕傲和不屑吧?一如多年後的現在,他幾乎每天在臉書上 Po 四個孫子的照片以及當爺爺的他如何體貼、如何有創意的照顧的細節,然後在眾人面前故意問我:「兒子什麼時候結婚啊?」
記得有一次他又把新書丟在我桌上,剛好一個記者進我們的辦公室,用極誇張的聲音說:「哇!小野又出新書了欸!」然後在我發現她充滿仰慕、讚嘆的視線是從桌上的書直接移轉到小野身上,整個過程根本無視於我的存在的那個當下,我聽到自己的聲音說:「是啊,下筆有如腹瀉啊!這本妳拿走,別浪費錢去買了!」
之後的新書他就再也不曾給我了,而是送給我兒子。 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我覺得小孩還有希望,至於他爸爸……根本沒救了!」 所以……這第一百本,大概是多年來我唯一認真讀完的小野的大作。
為什麼要認真讀完?因為有一個記憶力超強、文章老是寫得落落長、說起我總沒好話的人寫了一本據說「多次提到我」的書……無論如何都有潛在性危機,讀完是必要的防衛性檢閱。
小野大概是我這輩子面對面最久的一個人,九年,比八年抗戰還多一年。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和他幾乎每天都在相看兩相厭的臨界點上,所以有一次漢中街一個專門賣黨外雜誌的老闆送了我一張日本AV女優的海報,我就把它貼在小野背後的牆上,沒想到將近三十年後的現在,那個叫「青木琴美」的女優的樣子和名字竟然是我在中央電影公司九年歲月裡少數鮮明的記憶。
不知道是隨著時間流逝記憶淡化,或是自己有意忘記和電影相關的人、事、物,那段和小野在真善美戲院大樓的同事生涯對我來說,一如現在偶爾走過西門町的感覺:如夢似真、似曾相識,如此而已。
於是……好吧,此刻好像必須為小野講句好話了--若非這本書裡某些片段的提醒,我好像早已忘記除了彼此鬥嘴、彼此窩囊彼此之外,在那段人生的黃金歲月裡我們好像還真的一起遇過某些精采的人、做過某些開心的事、面對過某些挫折,也一起驕傲地笑過、頹喪地哭過。 哦,不對,根據他的記載,我很愛哭,所以哭的應該只有我。
還有,若非這本書的提醒,我都忘了離開中影之後,小野其實還不死心地在形勢更險峻、鬥爭更複雜的幾個領域裡繼續拚鬥過,他那種「想改變什麼」的基因好像一直沒有被環境、挫折、年紀和體力改變過。 以及,若非這本書的提醒,我都不知道他未來竟然還有好多事想嘗試、想做。
有一個意志堅強、凡事打死不退而且還持續創作的朋友是壓力,而這個朋友如果還經常被人拿來跟自己做連結做比較……那根本就是一場悲劇。
四十年前一次小說創作比賽,他拿首獎,我拿第三。
三十年前他出書的數量已經比我這輩子能力所及的還要多。
他有兩個小孩,我只有一個。
此刻,他已經是四個孫子的爺爺,而我卻連兒媳婦都還沒有。
在人生向晚的這個時候,我只想跟他說:朋友,我輸了,不過心服口不服,未來至少還是要繼續贏你以口舌。
還有,這本書……寫得還真不錯。

小野〈序曲〉:老朋友的生日宴
這是我的第一百本書,我也即將跨過法律上可以享受某些優惠的「老人」的界線,不知道應該笑還是應該哭。總之,不管如何心不甘情不願,人生終於來到了這特別的一天。加上宣布要出版第一百本書,心情上喜悅多過尷尬和狼狽。
夏天我的老朋友吳念真獅子座的生日宴會才剛剛舉行,他自稱已經六十五歲了,我糾正他說應該是六十四歲,他還提醒我說臺灣人是連懷孕十個月都算進去,每當他提到「臺灣人」三個字時都很嚴肅,我只有閉嘴的份。他在生日宴上說了一段很長的話,比較有趣的是說他剛剛才從花蓮看醫生回來,頭部的幾根針還沒有拔掉,在火車上半睡半醒時聽到擠在四周的年輕人認出他來,也發現了他頭部的針,之後議論紛紛,結論是難怪他能源源不絕的創作,原來是靠這幾根針。之後他的話就轉為嚴肅,希望在場好朋友都能活久一點,好好為我們的後代子孫多做點事。因為我們很對不起下一代。
其實吳念真年輕時是個妙語如珠唱作俱佳的天生演講家,後來說起話來越來越多感觸和情緒,變得非常嚴肅,變得非常愛九十度鞠躬,臺下的群眾往往被他的真情感動得落淚。為了化解這樣的凝重氣氛,我就得被迫上臺講吳念真的糗事,要用力「踐踏」他、「消遣」他,以換取臺下的爆笑。我被迫演小丑角色真的很變態,對我而言也是非常艱難的任務。畢竟語言是很微妙的東西,直接讚美別人很容易,換個方式用罵人的口吻來表達讚美就高明些,直接糗別人又沒有踩到對方的地雷和痛處,還要讓對方由衷的發笑,更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尤其當吳念真的名聲如日中天時,作為他在二十多歲就熟識,後來又面對面上班八年的老朋友的任何一句不得體笑話,都可以被心理分析者解讀成酸味破表的嫉妒心作祟。
至今他還沒有因為我一次又一次的笑話和我翻臉,甚至在臺下笑得比別人更大聲。我深深懷疑他是用這種「毫不在乎」,默默的「懲罰」著我:「看你還有多少笑話?看你到底能講到幾歲?」是的,其實每次上臺時我也是這樣問自己。我甚至已經有了答案:那就是當我上臺再也說不出吳念真的笑話時,那就是我們彼此真的都非常非常老了,老到沒有心情和力氣說著往日的笑話了。或許就是因為聽了吳念真和我之間太多的笑話和故事,我們共同的朋友簡社長忽然很認真的向我提出了一本書的構想,他覺得我們在三十歲一起蹲在中央電影公司工作八年的故事非常有趣又很勵志,鐵定可以感動許多讀者:「年長的讀者可以回味那段飛揚的時光,年輕人可以從你們的故事中得到鼓舞。那段精采故事除了你和念真有臨場的經驗,根本沒有人可以寫。」
簡社長本身就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演講家,在這之前他也曾經企圖說服我把所有工作停下來好好寫本有時代背景的小說,他的結語很煽動:「你想想,全臺灣,除了你還有誰可以做這件事?你認真考慮考慮。這是作為一個臺灣作家的責任。」我承擔不起他的溢美和勉勵,口裡說好好好,心裡安慰自己說:「別相信他的話。他一定對很多作家這樣說,才逼出許多精采的好書。」也因為這樣,當他又轉而鼓勵我寫那段故事時不忍心推託,一咬牙,又讓自己回到遙遠遙遠的年代,試著換個角度來說那些老故事。我一邊痛苦的寫,一邊痛苦的想像著吳念真叼著菸,用嘲諷的口吻說:「天哪,這些故事我早就忘光光了,你怎麼老是忘不掉?你可能真是乏善可陳、江郎才盡,但是卻仍然下筆如腹瀉。你不要再寫了,你不會是我對手的,寫一百本不如我寫一本。」
所謂的「想像」,都是我從他過去曾經笑過我的話中重新排列組合而成,換言之,他的「惡毒」並不輸給我,我也耿耿於懷他笑過我的每句話。也許這才是我們的默契,我們得做點「不一樣」的事,藉著互相漏氣提醒對方,大家一起求進步一起加油。
--摘自小野第100本作品《一直撒野》,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戀的。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