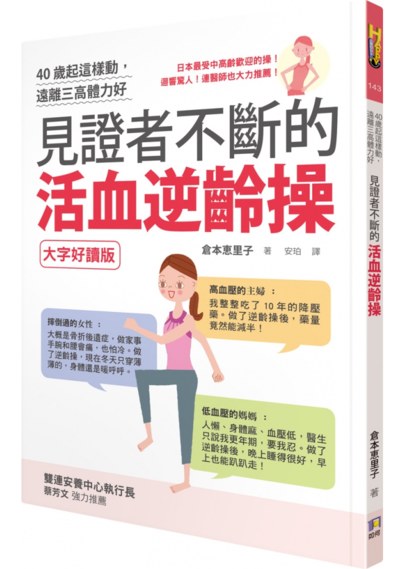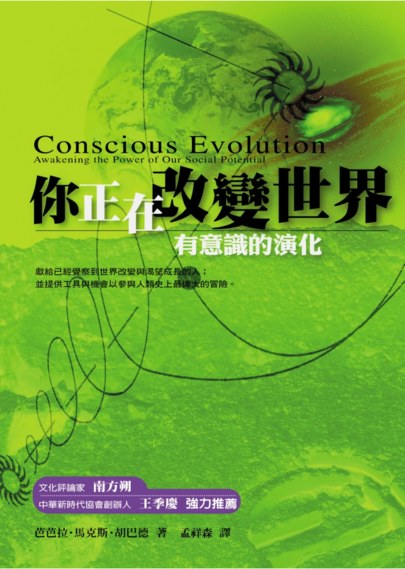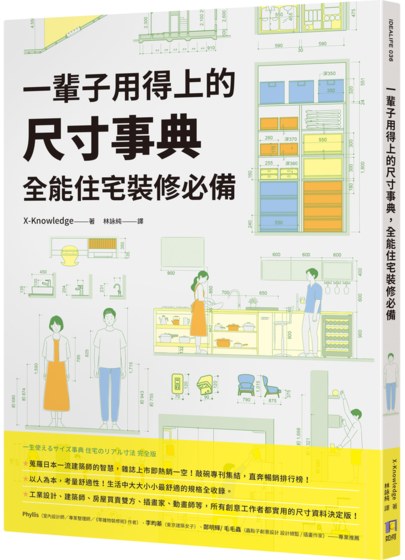2. 從此過著________的生活
◎生悶氣
有好一段時間,其他人對他們而言都是多餘的。在他們認識之前曾經長年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朋友,現在卻都遭到了他們的冷落。不過,罪惡感與重新燃起的好奇心終於逐漸占了上風。在實務上,這樣的轉變代表他們比較常與柯絲汀的朋友會面,原因是拉畢的朋友散布於世界各地。柯絲汀就讀亞伯丁大學時的死黨習於在星期五到拱門酒吧聚會。那家酒吧距離他們的住處相當遠,但供應的威士忌與精釀啤酒種類非常多,不過,在柯絲汀說服拉畢去參加那麼一場聚會的那一晚,他只點了一杯氣泡水。他因此不得不一再向別人提出解釋(總共五次):這不是因為他的宗教信仰,只是他當天剛好不想喝酒。
「夫妻耶,哇!」凱瑟琳讚嘆了一聲,口吻中帶著一絲譏嘲。她反對婚姻,最喜歡能夠證實她這項偏見的人。當然,「夫妻」一詞聽在拉畢和柯絲汀耳中也還顯得有點奇怪。他們提起這種頭銜的時候也同樣會刻意加重語氣,以開玩笑的語氣緩和這個詞彙所帶有的分量與不協調性,因為他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像是他們提到這個詞彙時所聯想到的對象,也就是比他們自己年紀大上許多、在社會上更有地位,生活也比他們悲慘得多的那種人。「克罕太太回來囉。」柯絲汀喜歡在回家的時候這麼喊一聲,戲耍著他們彼此都還難以相信的概念。
「欸,拉畢,你在哪裡上班?」莫瑞問道。他說起話來粗聲粗氣,蓄著一口落腮鬍,目前服務於石油產業,在大學時期曾經是柯絲汀的仰慕者。
「在一家都市設計事務所。」拉畢答道,突然覺得自己像個女孩子一樣。他在比較粗獷的男性面前有時候會有這種感覺。「我們設計市民空間,也從事空間規畫。」
「等一下,老兄,」莫瑞說:「我有聽沒有懂。」
「他是建築師,」柯絲汀幫他釐清:「他也設計過住宅和辦公室。等經濟復甦後,希望他可以接更多案子。」
「我懂了—在蕭條時期先屈身在大英帝國的這個黑暗角落,等機會來了再跳到鎂光燈下,打造出下一座吉薩金字塔,對不對?」
莫瑞的挖苦一點都不好笑,但他自己卻笑得很開懷。不過,拉畢感到不舒服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柯絲汀竟然也加入他的行列,手裡握著快要見底的酒杯,頭偏向她的大學同學,跟著他一起大笑,彷彿他真的說了什麼非常逗趣的話。
拉畢在回家的路上一語不發,然後聲稱自己累了,在她探詢的時候也只是以那句著名的「沒事」回答。他們回到仍有些油漆味的新家後,他就立刻走進裡頭擺著沙發床的書房,一把將門甩上。
「別這樣嘛!」她提高嗓門說道:「至少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他的回答卻是:「幹,別煩我。」有時候,恐懼會引發這種粗暴的言詞。
柯絲汀為自己沖了些茶,然後走進臥室裡,在心裡堅持告訴自己(其實不盡然誠實)她完全不曉得什麼事情讓自己的新婚夫婿如此生氣(不過他在拱門酒吧裡確實顯得格格不入)。
生悶氣這種行為表現當中其實混雜了兩種元素,一方面是強烈的憤怒,另一方面是一股同樣強烈的渴望,堅決不透露自己生氣的原因。生悶氣的人一方面迫切需要對方了解自己的心情,同時卻又執意不肯幫助對方做到這一點。要求生悶氣的人解釋自己的憤怒,這點本身就是一種侮辱:如果自己的伴侶還需要解釋才能了解,那麼對方就顯然沒有資格身為自己的伴侶。我們應該再接著指出:能夠成為別人生悶氣的對象其實是一大榮幸,因為這表示那個人對我們懷有足夠的敬重與信任,所以才會認為我們應該知道那個人沒有說出口的傷心處何在。這是愛情帶給我們的贈禮當中較為古怪的一件。
最後,她終於下床,到書房去敲了門。她母親總是說不吵隔夜架。她仍然在心裡對自己說著她不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親愛的,你表現得像兩歲小孩一樣。我和你是站在同一邊的啊,記得嗎?至少告訴我出了什麼問題嘛。」
在那間塞滿了建築書籍的狹小書房裡,那個大小孩在沙發床上翻了個身,只是一心想著自己絕不讓步。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毫不相干的念頭,覺得旁邊書架上一本書以銀箔印在書脊上的文字看起來很奇怪:MIES VAN DER ROHE(密斯.凡德羅)。
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狀況。在過去的戀情當中,他總是努力扮演漫不在乎的一方,但柯絲汀的開朗與堅毅卻導致他落入了相反的角色。這下子換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焦躁難眠了。她的朋友為什麼都不喜歡他?她到底在他們身上看見了什麼?她為什麼沒有插手幫他辯護?
生悶氣是向一種美麗而危險的理想致敬的行為,而且這種理想可以追溯到我們幼年初期:也就是一種承諾,承諾我們的需求不需經由言語表達即可受到理解。在母親的子宮裡,我們從來不必解釋。我們的每一項需求都受到了照顧。適當的撫慰總是就那樣單純出現。這種理想狀態在我們出生之後的起初幾年仍然持續存在。我們不必把自己的每一項要求都表達出來:那些體型高大而又善良的人自動會幫我們猜測。他們看穿我們的眼淚、我們口齒不清的呢喃、我們的茫然困惑:他們為我們口語表達能力的缺乏找出了原因。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感情關係裡,我們的伴侶一旦無法正確解讀我們的心思,即便是最口才便給的人也可能本能地不願提出明白的解釋。只有在無需言語的情況下準確感應心思內容,才會讓我們覺得我們的伴侶真的是值得信任的對象。只有在不必提出解釋的情況下,我們才會確信自己真正被了解。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終於再也無法忍受,而輕手輕腳地走進臥室,坐在她那一側的床上。他原本打算把她喚醒,但一看到她那張聰慧又和善的臉龐正在沉睡當中的模樣,他就改變了主意。她的嘴巴微微張開,他可以聽到她微乎其微的呼吸聲,她手臂上的細毛在窗外路燈的光芒映照下清楚可見。
第二天早晨涼爽而晴朗。柯絲汀比拉畢早起,為他們兩人準備了兩顆水煮蛋,還有一籃切得整整齊齊的吐司細條。她俯瞰樓下花園裡的垂柳,對這些可靠、樸實的平凡事物心懷感激。拉畢頂著一頭亂髮怯生生地走進廚房之後,他們先是沉默不語地吃著早餐,但最後終於互相微笑。午餐時間,他傳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她:「我有點瘋癲,請原諒我。」她雖然正等著要參加市政會議,卻還是立刻回覆了他:「你如果不瘋癲,生活就太無趣了。而且,也會太寂寞。」他們再也沒有提起他生的那場悶氣。
理想上,我們一旦成為別人生悶氣的對象,應當要能夠笑得出來,不過是以最溫柔的方式。我們理當能夠體認到那種動人的矛盾。生悶氣的人也許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擁有成人的職業,但那個人真正傳達出來的訊息卻是稚氣得令人動容:「在我的內心深處,我仍然是個嬰孩,而現在我需要你扮演我的父母。我需要你正確猜測出我真正的苦惱,就像別人在我嬰兒時期對待我的方式那樣,在我對於愛的觀念初步成形的時候。」
面對生悶氣的愛侶,我們能夠為他們提供的最大幫助,就是以關懷幼兒的方式對待他們耍脾氣的行為。我們總是習於認為別人把我們當成小孩是一種屈尊俯就的態度,但我們卻忘了這一點:有時候,別人如果能夠看穿我們成人的外表,而關注並且原諒我們內心那個失望、憤怒又無法以言語表達需求的孩子,其實是一種最大的榮幸。
4. 外遇
◎偷腥
拉畢獲邀到柏林的一場都市再生研討會發表有關公共空間的演說。他在倫敦轉機,並且在德國上空一連翻閱了好幾本雜誌。望出窗外,可以看見底下平坦而廣闊的普魯士,有些地方已經覆蓋上了十一月的初雪。
他和柯絲汀結婚至今已將近十三年了。
這場活動舉行於柏林東側的一座會議中心,旁邊鄰接著一家飯店。他的房間位於第二十層樓,看起來有如醫院般素淨而潔白,窗外可以眺望一條運河與一排排的田地。在這個白晝短暫的時節,他在天黑之後可以看見發電廠與一長排的電塔朝著波蘭邊界延伸而去。
在大廳舉行的歡迎派對上,他誰都不認識,只好假裝自己正在等待同事。回到房間之後,他隨即打電話回家。孩子們剛洗完澡。「我喜歡你不在的時候,」依瑟說:「馬麻都會讓我們看電影、吃披薩。」拉畢看著一架單引擎飛機盤旋在飯店停車場後方那片冰凍原野的上空。在依瑟說著話的同時,他可以聽到威廉唱歌的聲音,故意裝出一副對於那個拋下他的爸爸毫不在乎的模樣。透過電話,他們的聲音聽起來顯得年紀更小,他們要是知道他有多麼想念他們,一定會覺得很怪。
他一面吃著總匯三明治,一面看著新聞。透過那個新聞節目的播報,一系列的悲劇看起來都沒什麼兩樣,讓人看得意興闌珊。
第二天一早,他在浴室鏡子前面演練自己的演說。他的演說在十一點舉行於會議中心的大廳。他以滿腔的熱情和對這項主題的深入知識提出論點。倡導設計良好而能夠凝聚社群的公共空間是他的畢生志業。演說結束後,有不少人到台前向他表達恭賀。午餐時間,他和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同坐一桌。他已經有好一陣子不曾體驗過這麼國際化的氛圍了。一場對美國充滿敵意的談話正在進行著。一名在卡達工作的巴基斯坦人抨擊著美國的城市區劃法對迴轉半徑造成的影響;一名荷蘭人指控美國的菁英階層對於公眾福祉毫不在乎;一名芬蘭代表則是把美國民眾對於化石燃料的依賴比擬為老菸槍與鴉片的關係。
桌子末端坐著一名女子,斜傾著頭,臉上露出一道無可奈何的苦笑。
「我知道我在海外的時候最好不要為自己的國家辯護,」她終於插口指出:「當然,我也和你們一樣對美國充滿失望,可是我還是對自己的國家懷有深切的愛國心—就像是我如果有個酗酒成癮而且神經兮兮的阿姨,也一樣會在聽到別人在她背後說壞話的時候挺身為她辯護。」
蘿倫住在洛杉磯,服務於洛杉磯加州大學,目前正在研究外來移民對聖貝納迪諾山谷的影響。她有一頭及肩的褐色長髮和灰綠色的眼珠,年方三十一歲。拉畢盡力不盯著她看,她的美貌在他當下的處境對他可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在研討會再度開始之前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他決定到外面一片勉強算得上是花園的空地散散步。他的回程班機在第二天一早起飛,等他回到愛丁堡之後,將會有一項新計畫在他的辦公桌上等待著他。蘿倫那套合身的深色洋裝雖然很低調,但他卻記得衣服上的每一個細節。她戴在左手臂的那一串手鐲也一直浮現在他的腦海裡;他瞥見那串手鐲底下有個刺青,位於她的手腕內側—這是一項無意間的提醒,令他沮喪地意識到他們兩人之間的世代隔閡。
傍晚,在通往電梯的走廊上,他正看著幾份小冊子,結果她剛好走了過來。他尷尬地面露微笑,內心感到一陣難過:原因是他永遠不可能真正認識她,她的深層人格(可由她甩在肩上的那個紫色帆布袋看出徵象)永遠都不可能為他所熟悉,而且他終究只能夠過一次人生。不過,她卻宣稱自己肚子餓了,提議他和她一起到一樓商業中心隔壁的一家木牆酒吧去喝個茶。她早上在那裡吃過早餐,她又補充了一句。他們在壁爐旁的皮面長凳上坐了下來。蘿倫身後有一株白色蘭花。他們的談話主要都是由他提問,於是他也就零零碎碎地得知了一些關於她的事情:例如她住在威尼斯海灘區的公寓,先前曾在亞利桑那州的一所大學服務過,她的家人住在阿布奎基,她熱愛大衛.林區的電影,她參與了社區組織的工作,她信奉猶太教,喜歡誇大表現她對德國官員的恐懼,而這份恐懼也延伸到那個拘謹生硬的粗脖子酒保,看起來就是個很有喜感的人物,她稱那名酒保為艾希曼(注:納粹高官,被猶太人稱為納粹劊子手)。拉畢一會兒專心聽著她說話的內容,一會兒思索著她所代表的意義。她一方面是她自己,但同時也是他在過去十三年來所欣賞卻明白不能過於好奇的所有那些人。
她瞥眼看向酒保,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絕不可能把醋變成果醬,先生∼」她低聲唱著以柏林夜生活為背景故事的《酒店》劇中的歌曲,拉畢不禁為她的魅力所傾倒。他覺得自己彷彿又回到了十五歲,而她就是愛麗絲.索赫。
她在前一天搭機飛到法蘭克福,然後轉乘火車過來,她對他說。她覺得歐洲的火車非常適合沉思。拉畢想到現在家裡一定到了接近洗澡的時間。他要摧毀自己的人生是多麼容易的事情啊,只需把手往左移動十公分就行了。
「跟我說說你自己。」她說。這個嘛,他在倫敦念書,後來到了愛丁堡,工作雖然很忙碌,但他只要有機會就喜歡旅遊。沒錯,他確實不太喜歡那裡的陰鬱天氣,可是不要太在意天氣狀況也許是種有用的自律做法。省略掉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面向竟然容易得出乎他意料之外。「你今天做了什麼,把拔?」他可以聽到他的子女這麼問他。把拔在很多人前面發表了演說,然後看了看書之後就提早上床睡覺,以便明天可以搭第一班飛機回家看他最親愛的女兒和最特別的兒子—但這兩個孩子在當下最好不要存在。
「我沒有辦法面對那頓各國代表一起吃的晚餐。」她在七點的時候說,就在艾希曼剛過來詢問他們想不想要來杯雞尾酒之後。
於是,他們兩人一起走出酒吧。他的手微微顫抖著按下了電梯按鈕。他問她要到哪一層樓,然後在透明電梯往上升的時候站在她對面。霧氣遮蔽了戶外的景色。
中年引誘者的直率態度極少是出於自信或傲慢,反倒是一種焦急的絕望心理,產生自一種令人同情的知覺,亦即覺察到死亡的逐漸進逼。
她的房間在格局和擺設方面幾乎和他的一模一樣,但氛圍卻是出奇的不同。一件紫色洋裝掛在一面牆上,一本新博物館的目錄冊擺在電視旁邊,書桌上放著一部掀開的筆電,鏡子前面有兩張明信片,圖樣都是歌德的同一幅畫。她的手機插在飯店提供的床頭櫃音響上。她問他有沒有聽過一名歌手,然後在手機螢幕上點了幾下,開始播放她的專輯:伴奏很簡單,只有鋼琴和一些打擊樂器,聲音聽起來像是在一座寬廣的大教堂裡所錄製的。接著,一股強而有力的女聲開始唱起歌來,歌聲簡樸而動人,一會兒低沉得超乎尋常,一會兒又突然拔高,而顯得極為脆弱。「我特別喜歡這個部分。」她說,眼睛閉上了一會兒。他站在床尾,聽著那個歌手以愈來愈高的音調不斷重複「永遠」一詞,猶如一聲聲直接穿透他靈魂的呼喚。自從孩子出生以來,他就沒有再聽過這種音樂。在他受限的生活要求他保持堅決冷靜的情況下,讓自己受到這樣的情感激動並沒有任何好處。
他走到她身前,用雙手捧起她的臉龐,以自己的嘴唇印上了她的唇。她抱緊他,又閉上了眼睛。「我願把一切都給你……」音響中傳來的聲音唱著。
事情的經過和他以前的經驗差不多,也就是和一個新對象剛擦出火花之時的那種感受。他如果能夠把過往人生中的每一幕這種場景剪輯成一段影片,總長度可能不會超過半個小時,但這些場景在許多面向上卻都是他人生中最精華的時刻。
他覺得自己彷彿喚醒了內心他以為早已死去的部分。
那些自我懷疑到令人同情的男人構成了極大的危險,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吸引力缺乏自信,而必須不斷確認自己是否能夠獲得別人的接納。
她把燈光轉暗。雖然同樣是女人,卻有那麼多的細微差異:她的舌頭比較好奇,也比較急切;她在他貼近她的腹部之時弓起了背;她腿部的肌膚比較緊實,大腿的膚色比較深。現在有什麼能夠阻止他?這麼做大錯特錯的想法已經被他拋到了九霄雲外,就像鬧鐘吵不醒沉睡的人一樣。
完事之後,他們靜靜躺著,急促的呼吸逐漸緩和了下來。窗簾開著,在霧中可以看見那座燈光明亮的發電廠。
「你太太是什麼樣的人?」她面帶微笑地問。他沒辦法從她的語氣判斷她這麼問的用意,也不曉得該怎麼回答。他和柯絲汀所面對的挑戰感覺太過私密,不適合與別人分享,儘管他們現在又把一顆比較無辜的新衛星吸引到了他們的軌道當中。
「她……人很好。」他結結巴巴地說。蘿倫仍是那副莫測高深的神情,但沒有進一步追問。他撫摸著她的肩膀。牆外傳來一部電梯下降的聲音。他不能說自己在家裡感到煩悶,他不是不尊重他的太太,甚至也不是不再欲求她的肉體。不是,實際上的狀況其實比較詭異,而且也更令人說不出口。他所愛的女人經常顯得完全不需要愛,她是一位極為能幹又堅強的鬥士,以致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讓他呵護她。她沒有辦法和願意幫助她的人建立良好關係,而且她最自在的時候,似乎就是她對自己託付的對象感到失望的時候。他和蘿倫上床,似乎就只是因為他和他的太太近來連互相擁抱都做不到—而他內心深處對於此一現象深感受傷也深覺氣憤,儘管他並沒有多少正當理由這麼覺得。
極少有人外遇是因為對自己的配偶毫不在乎。一個人通常必須深深關心自己的伴侶,才會願意花費心力背叛對方。
「我覺得妳應該會喜歡她。」他終於又加了一句。
「我敢說我一定會的。」她語氣平和地回答。她在這時流露出了一股淘氣的神情。
他們叫了客房服務。她點了一份義大利麵,要加上檸檬和些微的帕馬森乾酪,她似乎習於對願意聆聽的人精確提出這類要求。在接受服務的情況下極易感到畏縮的拉畢,對於她那種理所當然的態度深感佩服。電話鈴響,她接了一通洛杉磯同事的來電,現在那裡的時間才接近中午而已。
比起上床本身,真正吸引他的其實是事後的那種親密感。這真是當前這個時代的古怪之處:要和一個人建立友誼,最容易的方法竟然是要求對方解下衣衫。
他們對彼此都熱情而體貼,兩人也不會有機會令對方失望。他們兩人都能夠表現出能幹、大方、可靠又率真的模樣,就和一般的陌生人一樣。他說的笑話會逗她發笑。他的口音相當迷人,她說。想到自己有多麼容易受到實際上不曉得他內心的對象所喜歡,不禁讓他感到一陣寂寞。
他們聊天聊到午夜,然後純潔地躺在床上的兩側沉沉睡去。到了早上,他們一起前往機場,在報到區喝了杯咖啡。
「保持連絡—如果可以的話。」她微微一笑。「你是少見的好人。」
他們緊緊相擁,表達了只有對彼此沒有進一步意圖的兩個人所能夠懷有的純粹情感。時間的欠缺是他們的一項特權,在缺乏時間的情況下,他們在彼此的眼中都能夠永遠保持著迷人的模樣。他覺得自己的眼眶裡湧上淚水,於是將目光轉向一幅由一名戰機飛行員代言的腕錶廣告,試圖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由於他們之間將會隔著一片海洋和一座大陸,因此他也就能夠盡情發洩自己對於親密相處的渴望。他們兩人都可以為了自己所渴望的親密而心痛,卻不至於遭受獲得這種親密性所可能帶來的後果。他們永遠不會互相怨憎,只有不可能擁有未來的愛侶,才能夠持續欣賞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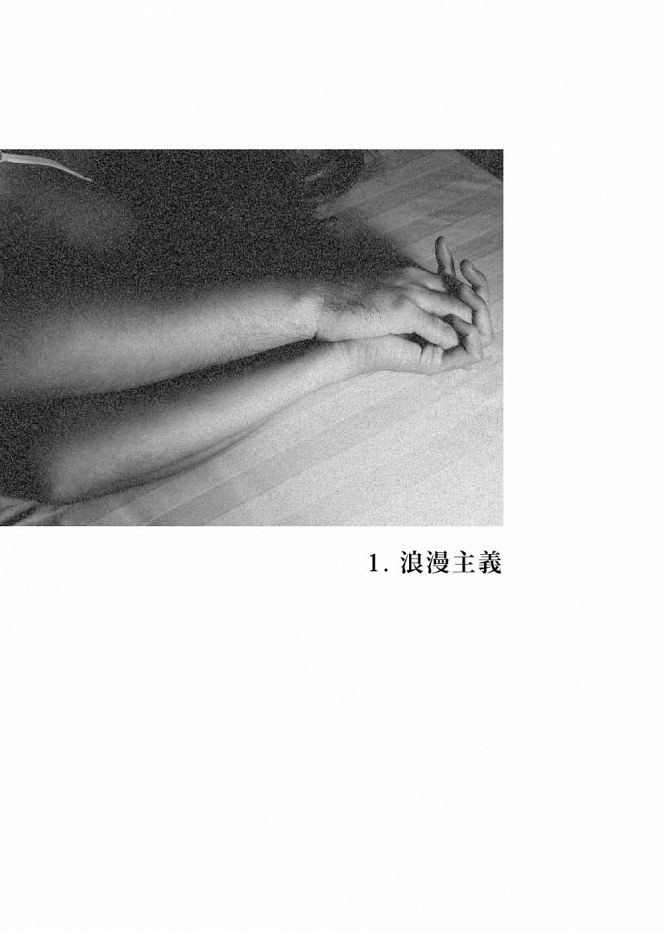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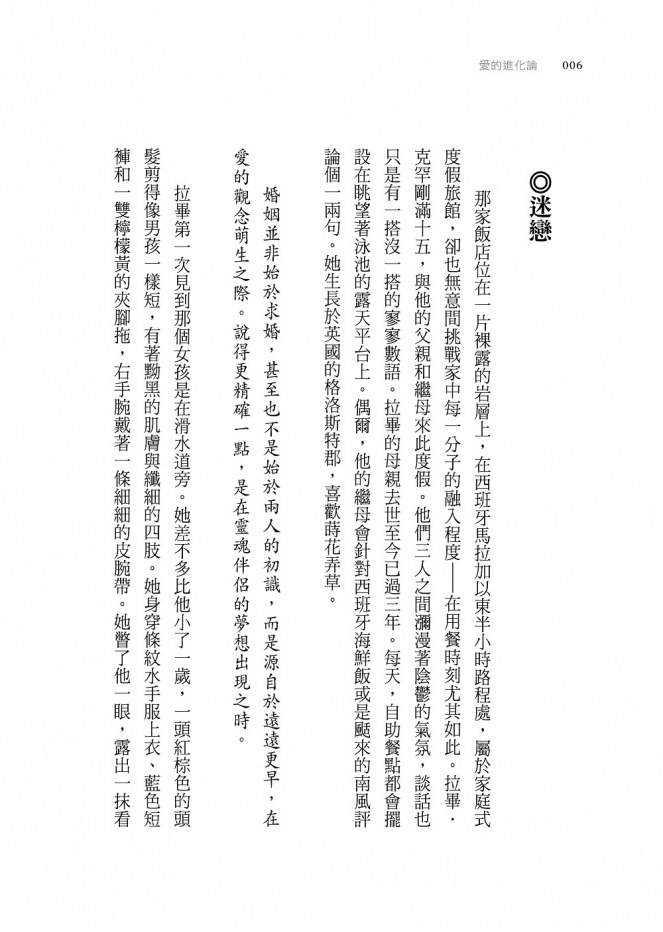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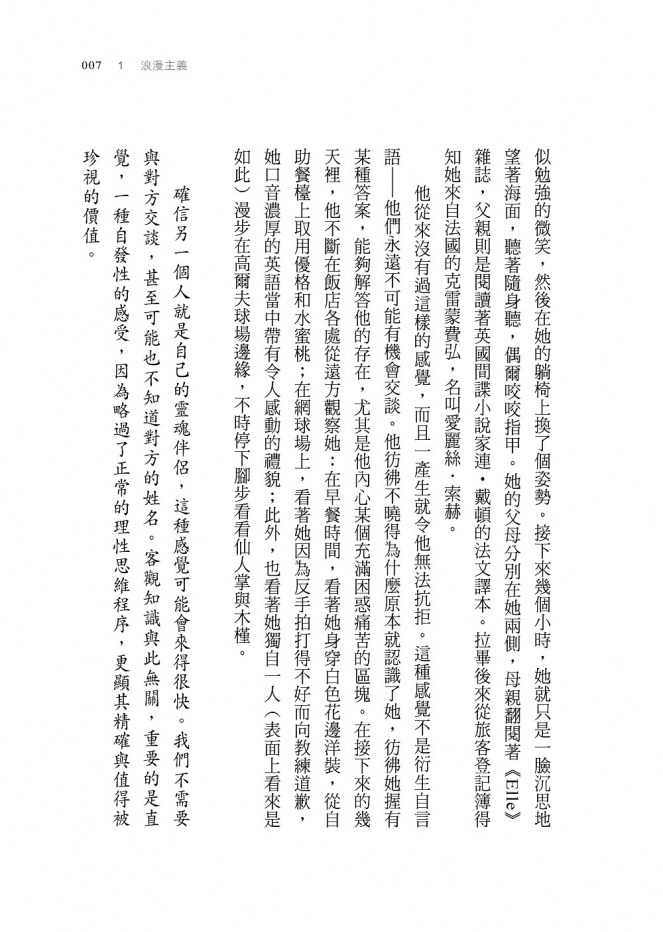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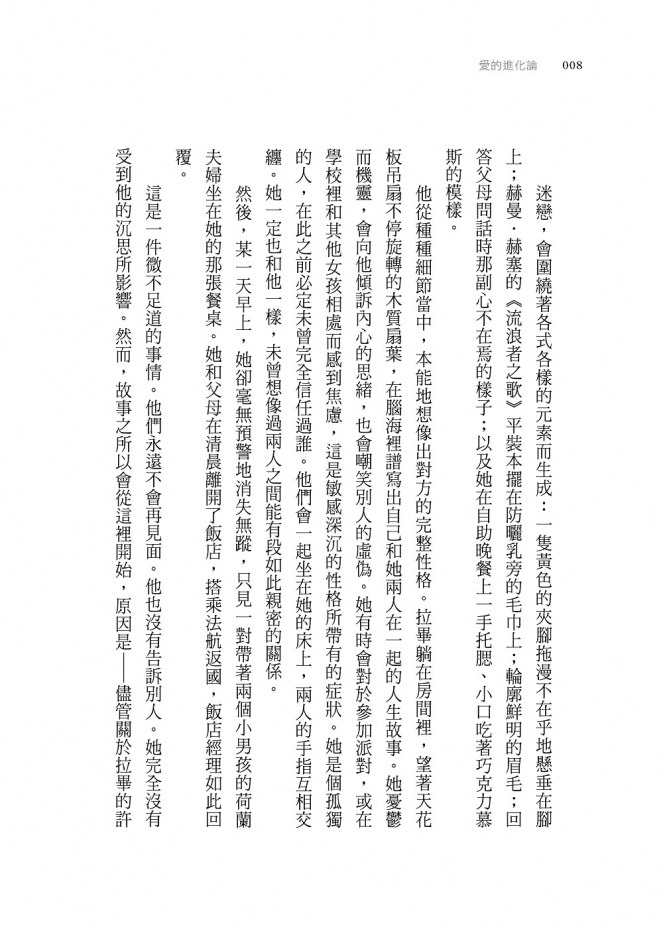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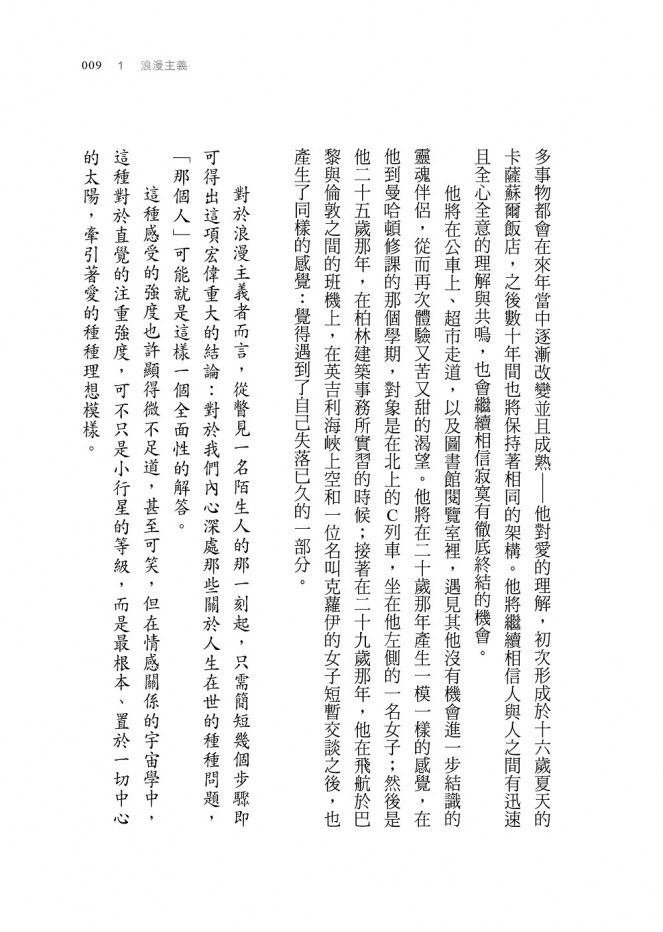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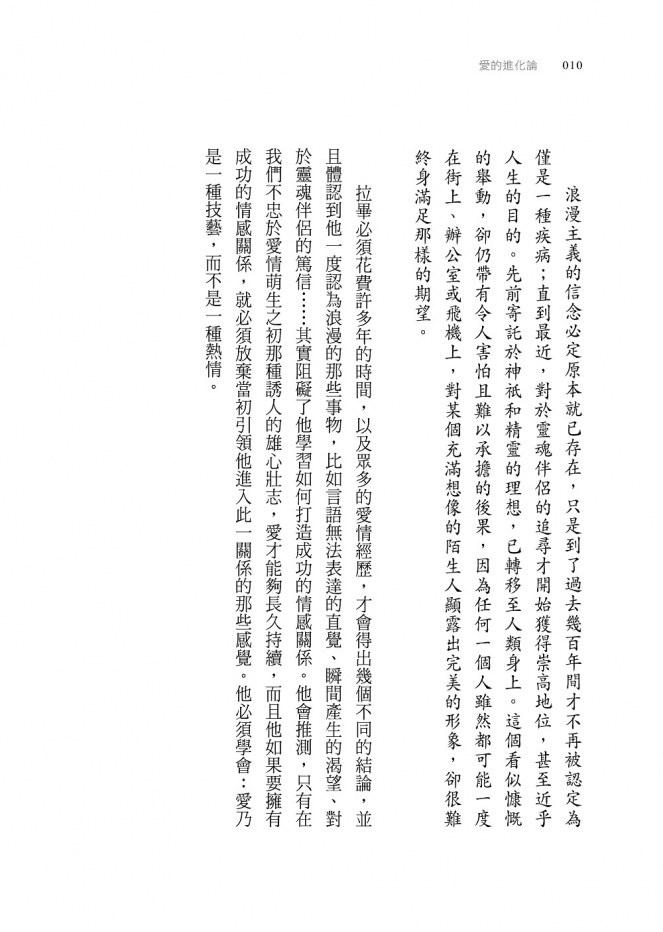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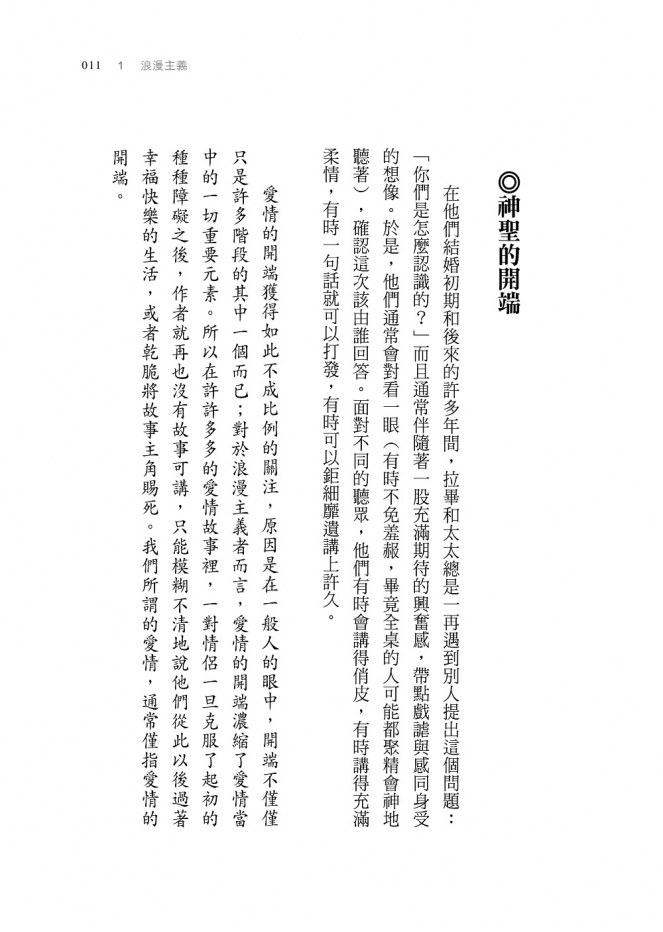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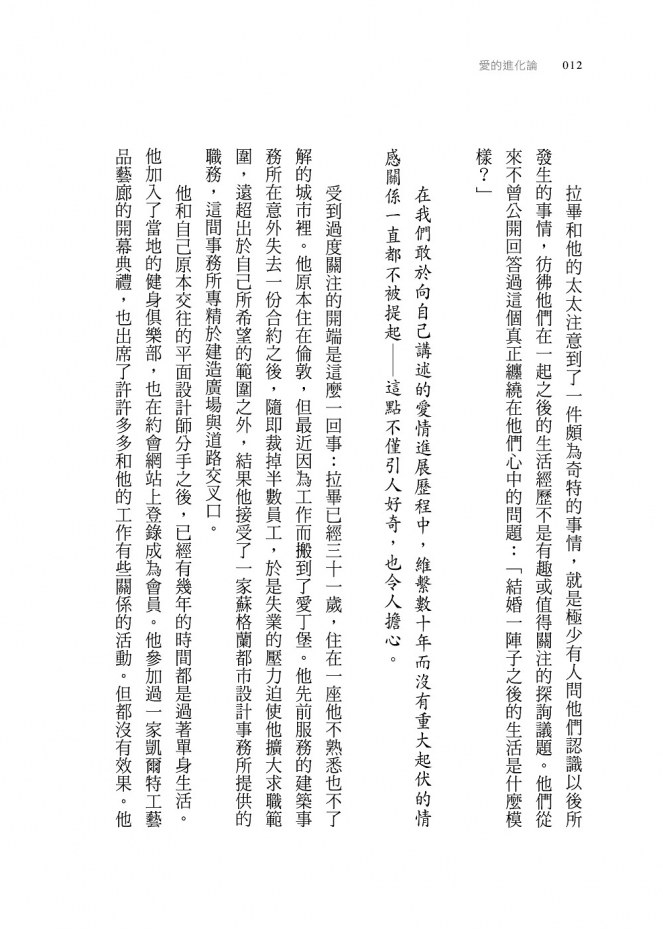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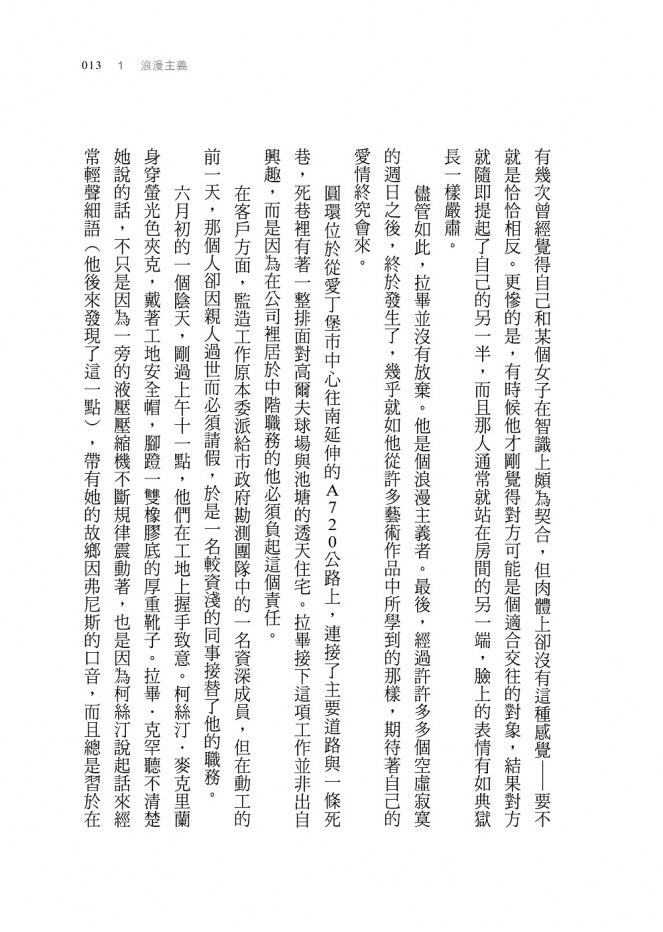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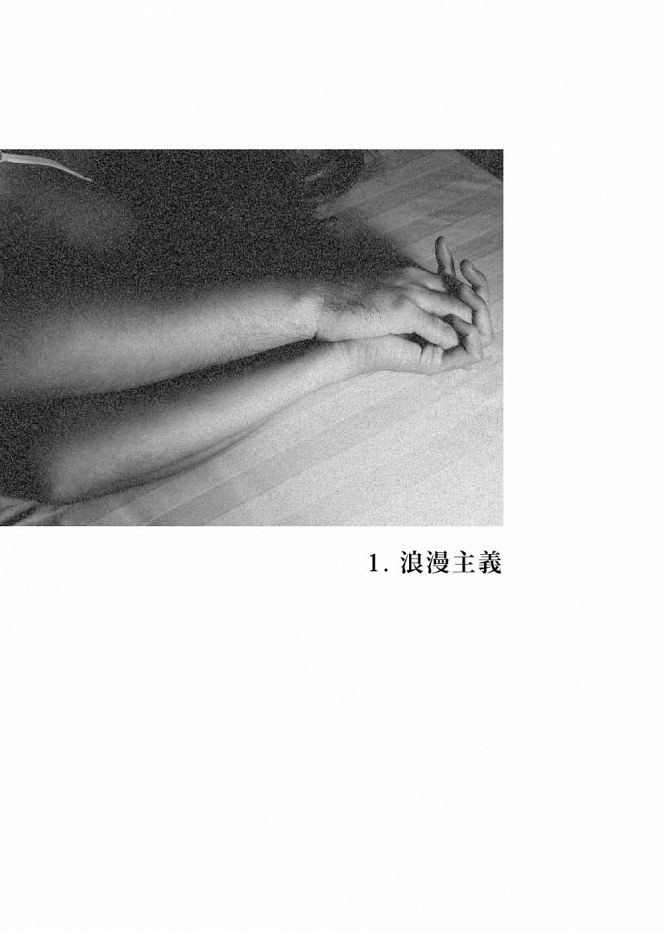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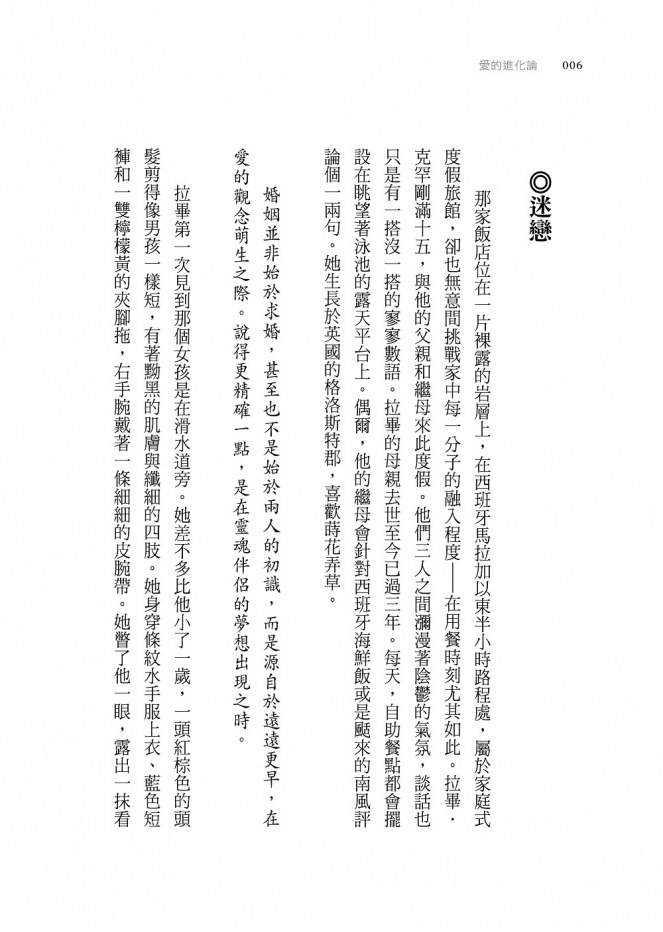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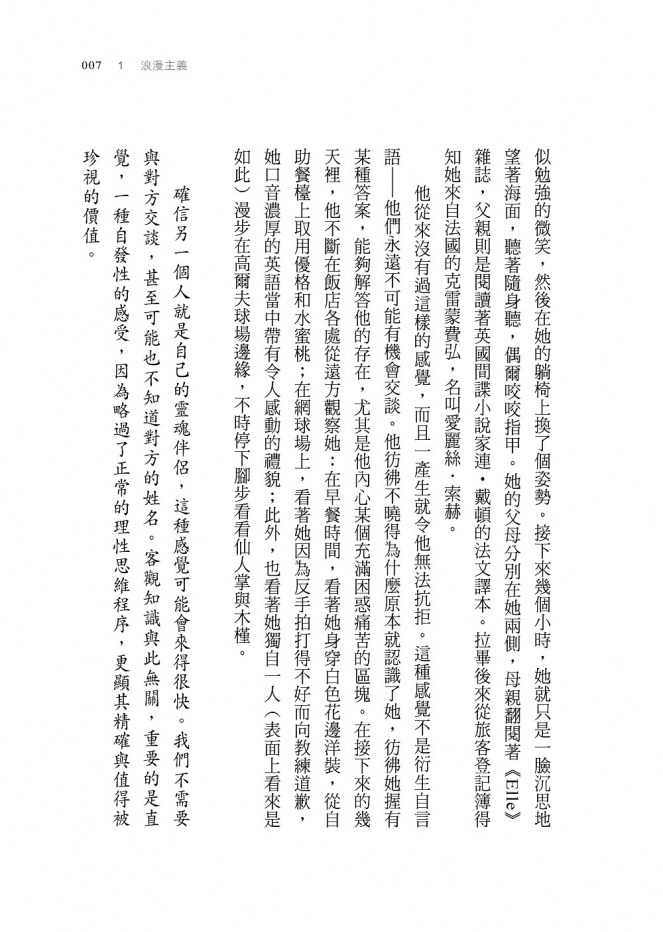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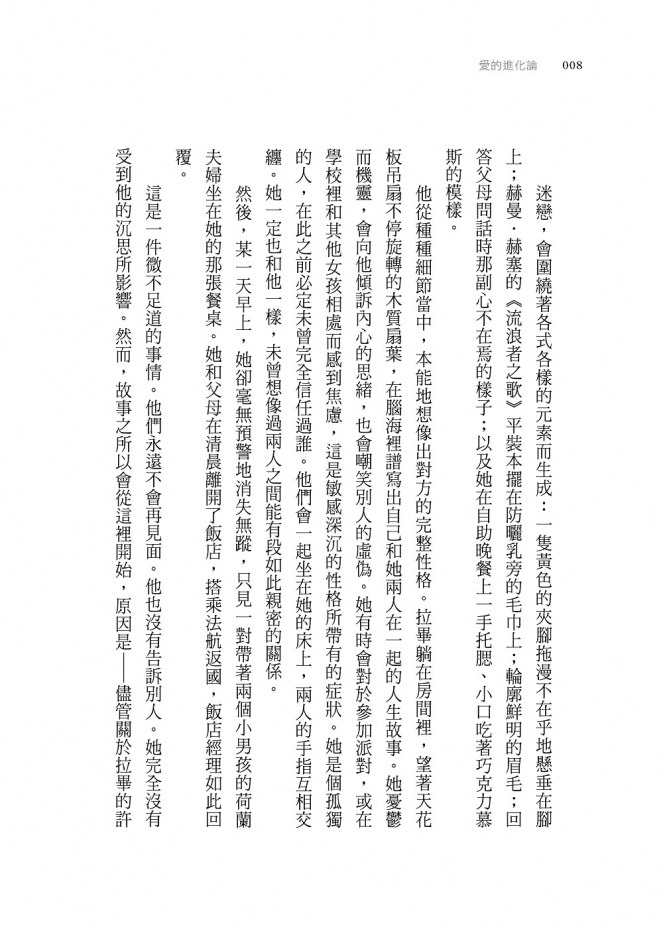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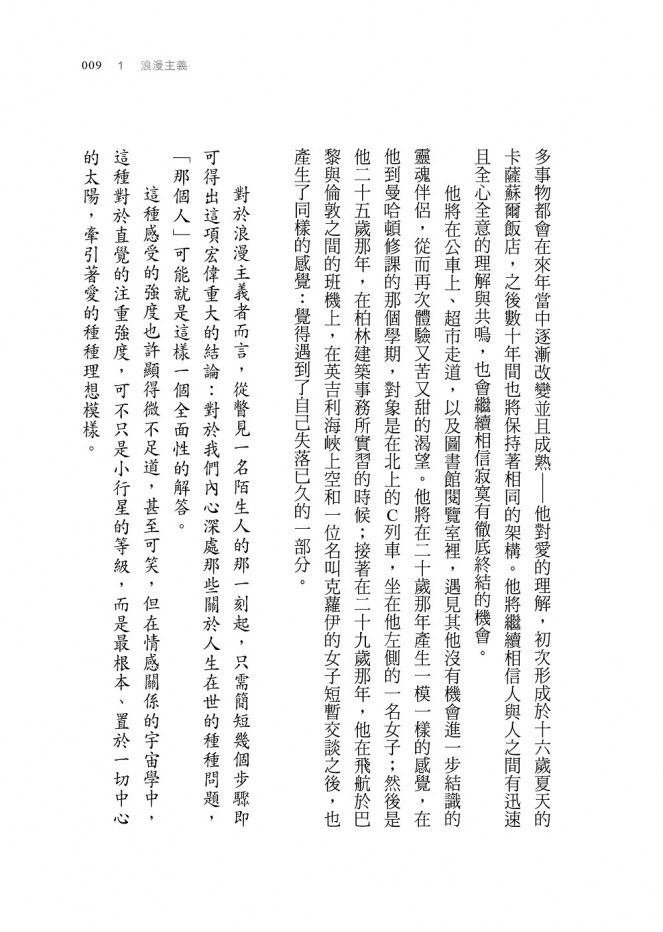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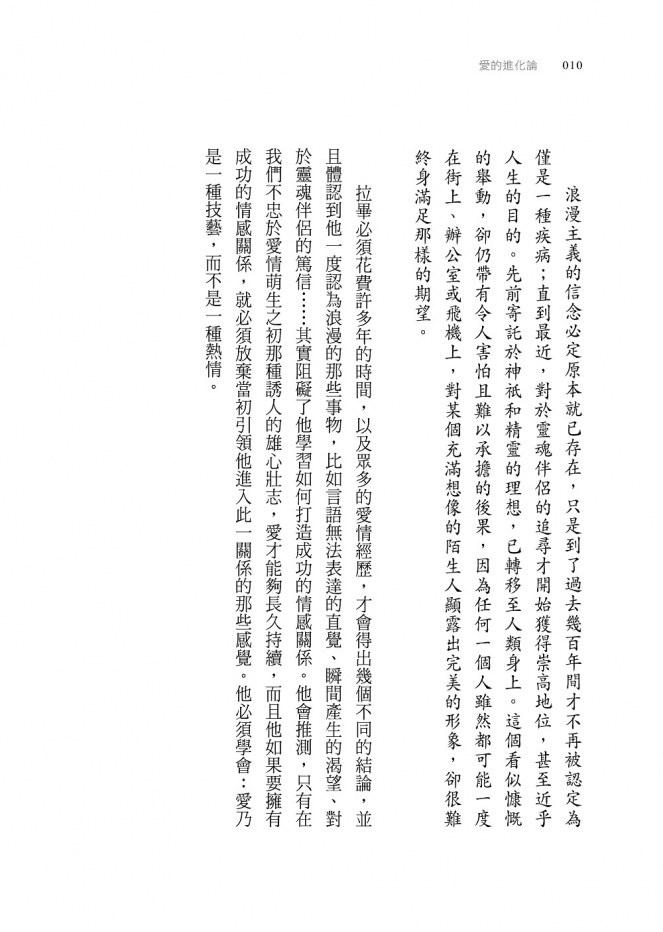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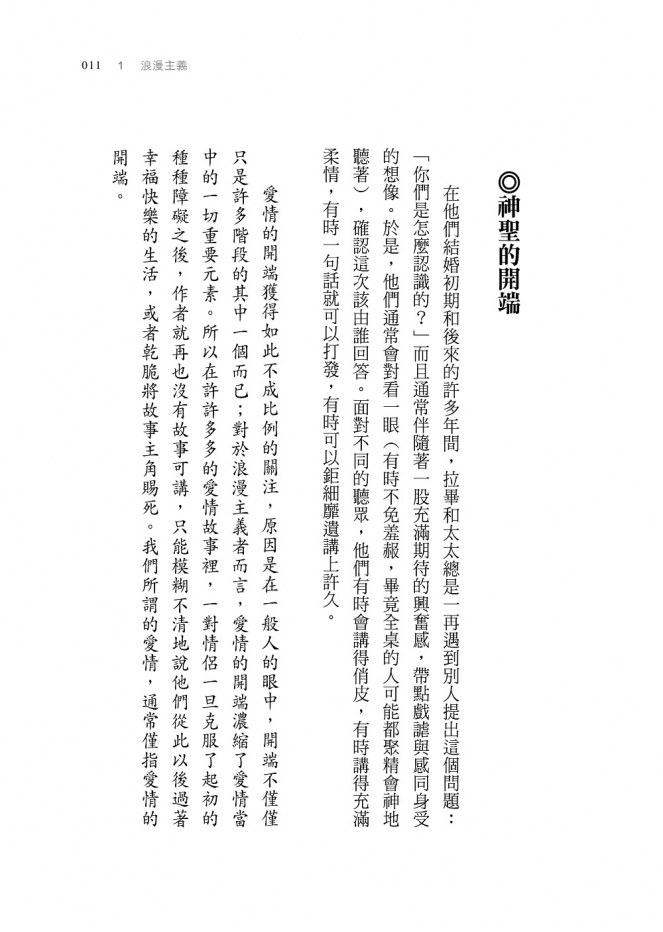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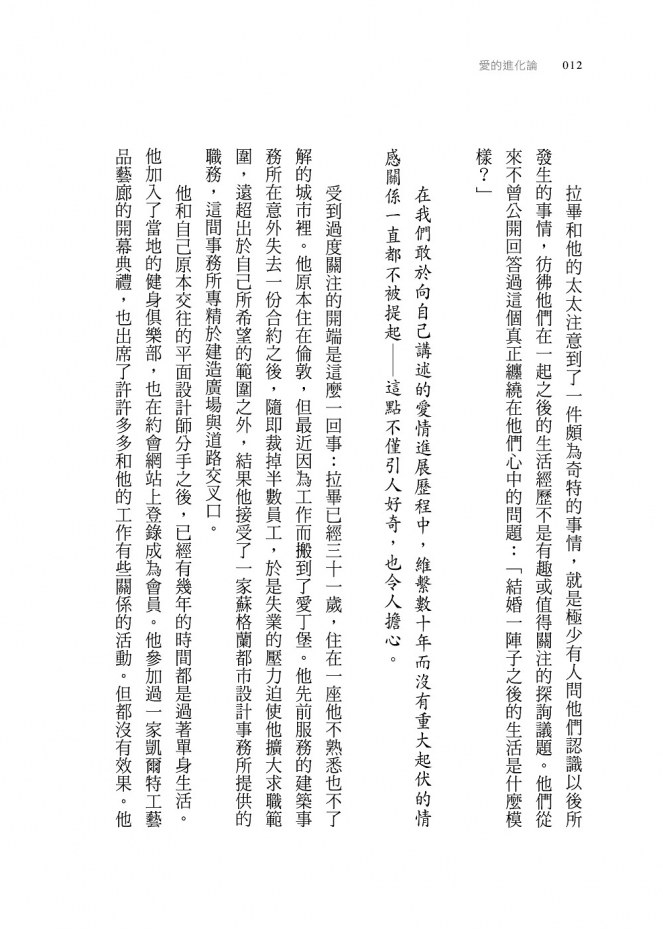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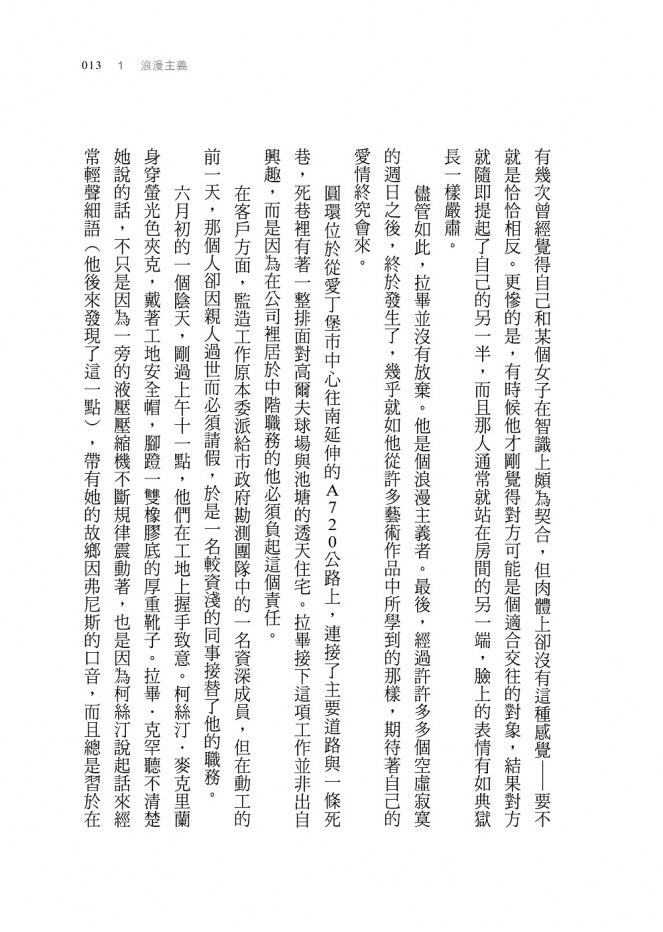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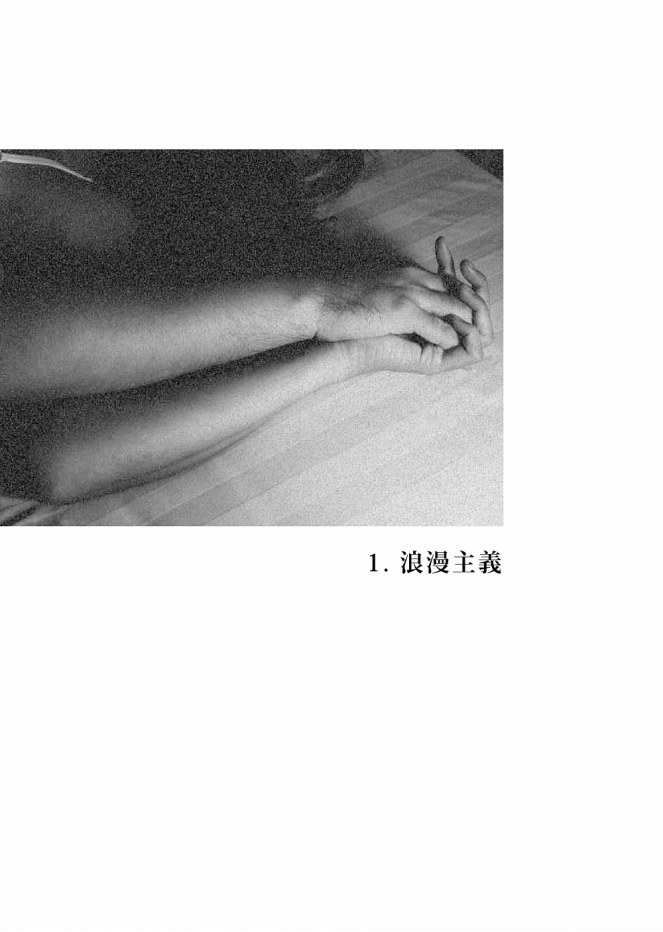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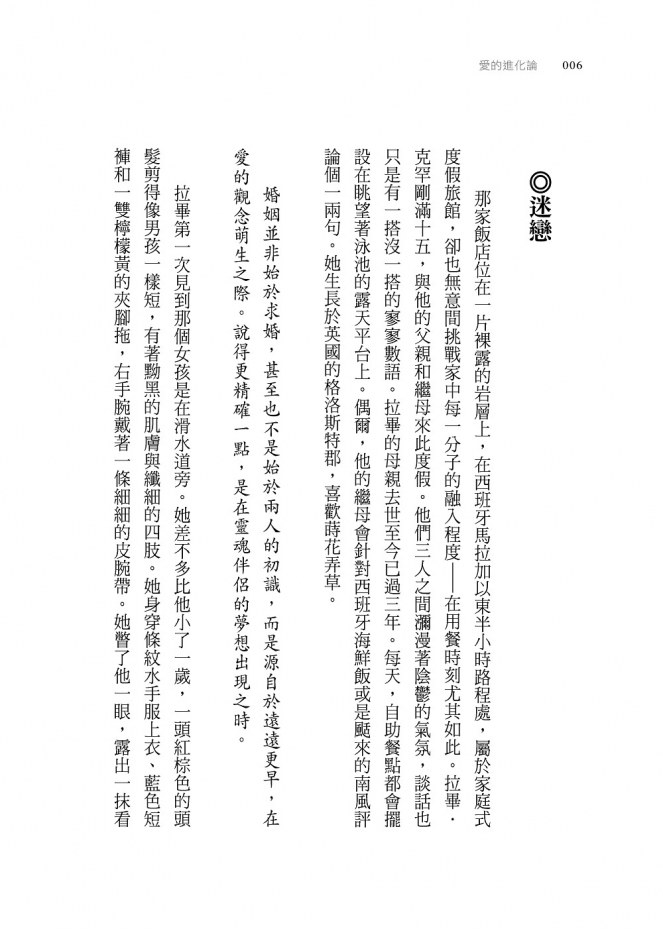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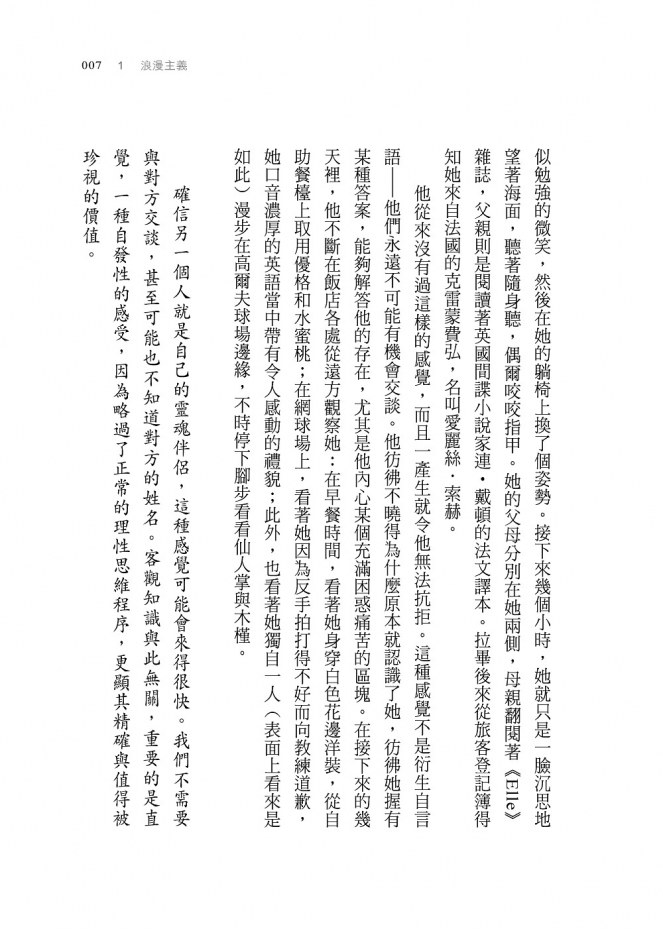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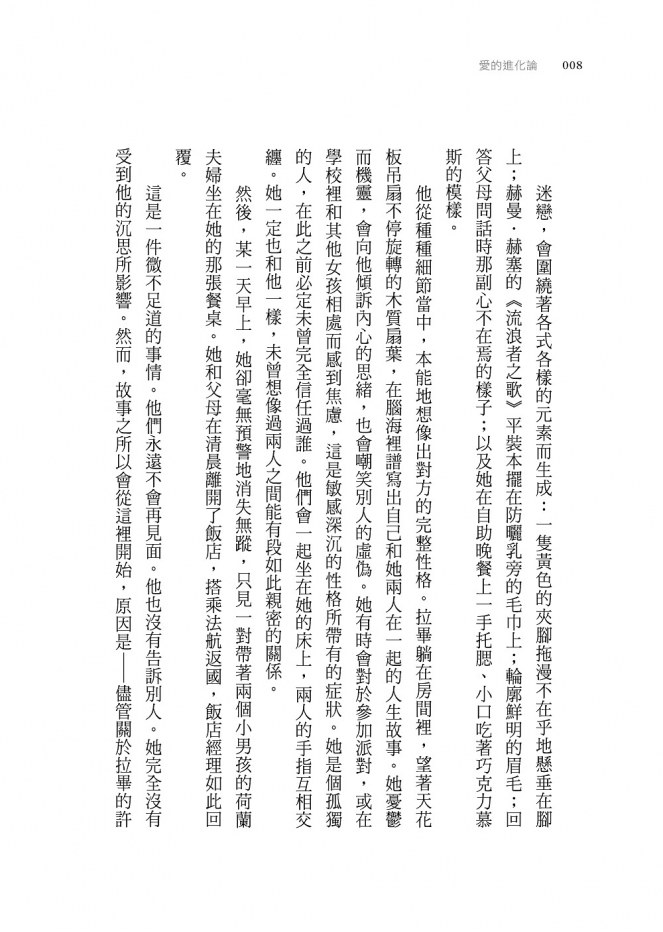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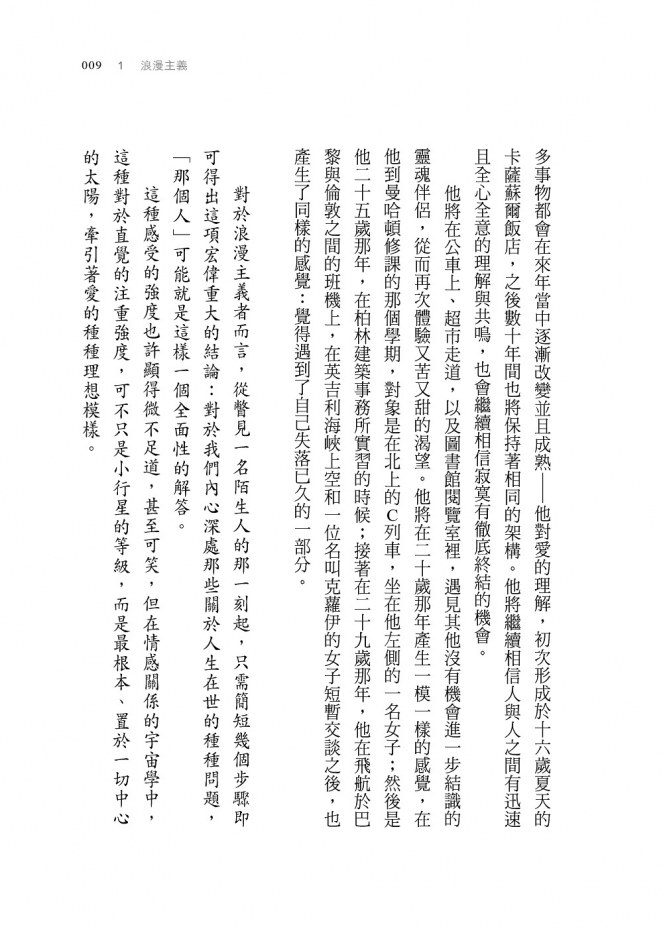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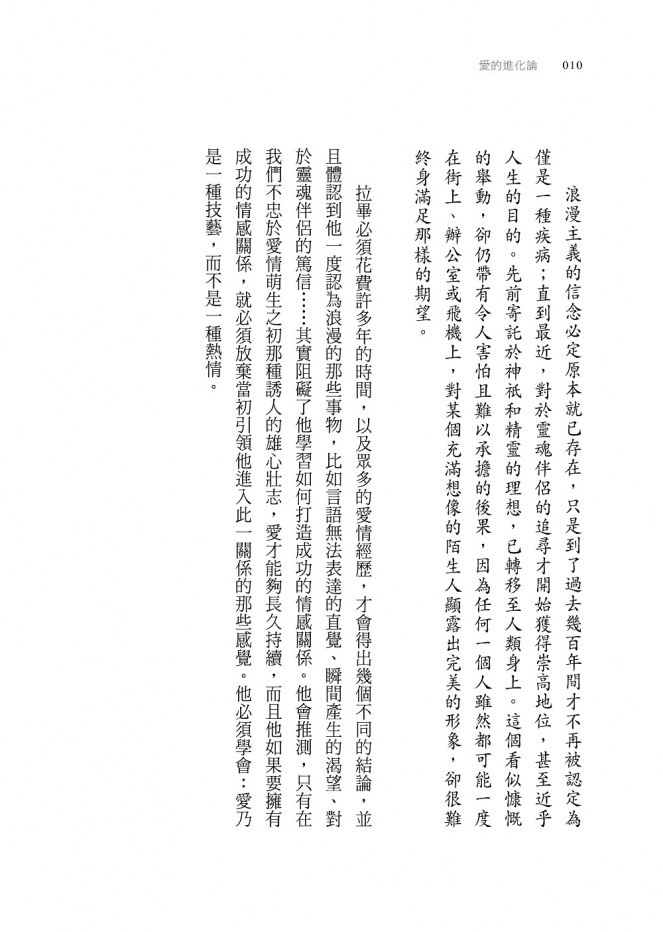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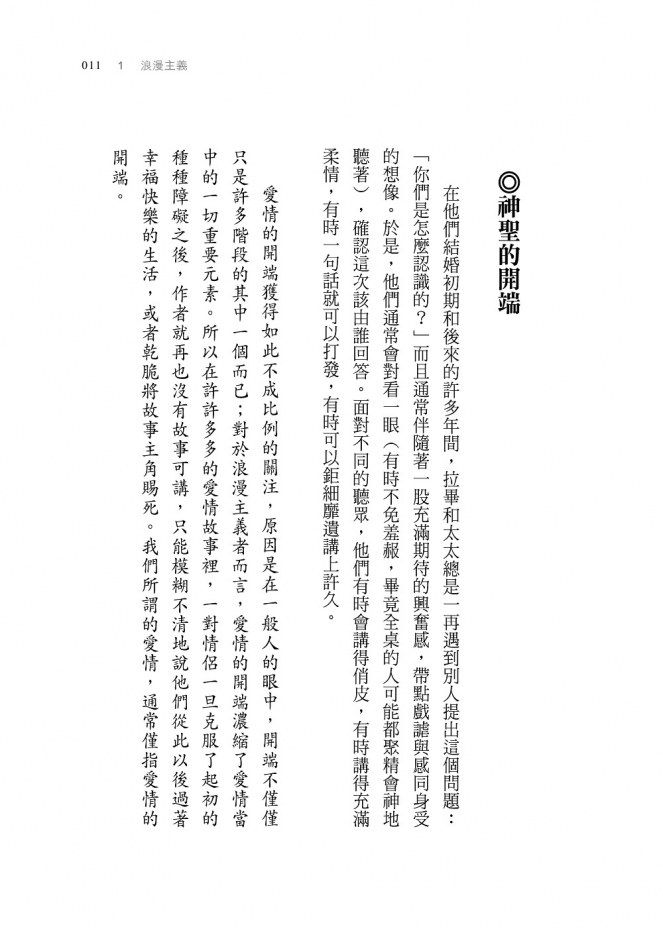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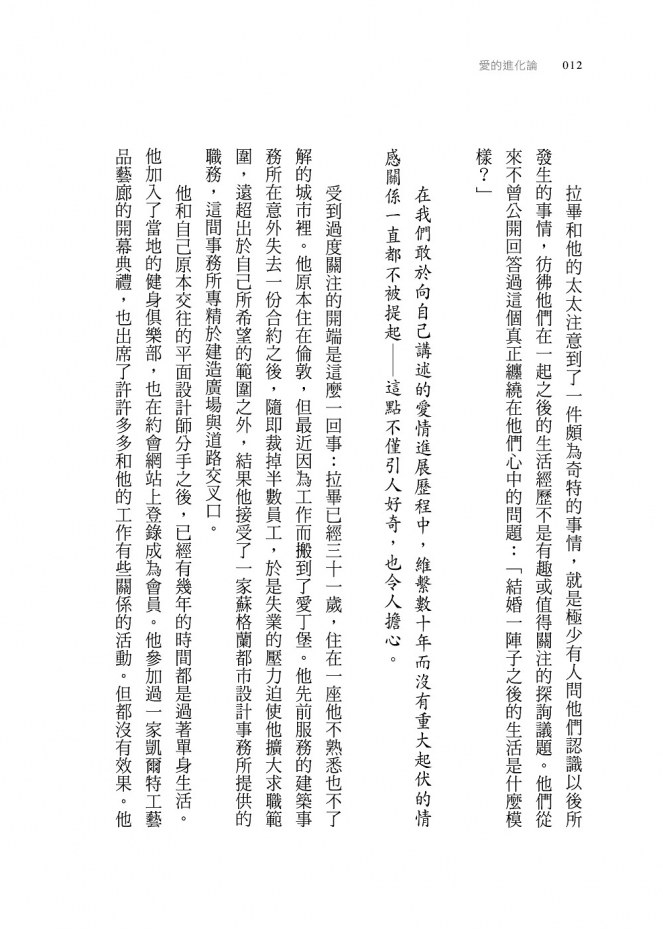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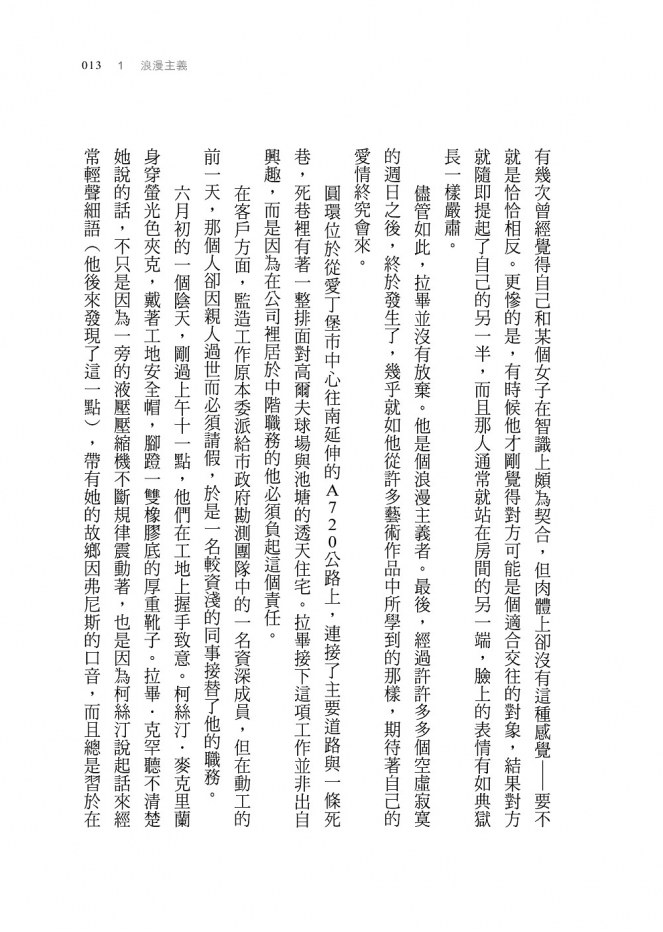

 英國最具特色的才子作家、哲學家、製作人。狄波頓寫愛情、聊旅遊、談建築、說文學,才氣橫溢,文章智趣兼備,不僅風靡英倫,全球各國更爭相出版他的作品,目前已有三十多國語言的譯本。創辦「生活建築」與「人生學校」,將有趣的哲學帶入日常,為生活增加更多元的面向。
英國最具特色的才子作家、哲學家、製作人。狄波頓寫愛情、聊旅遊、談建築、說文學,才氣橫溢,文章智趣兼備,不僅風靡英倫,全球各國更爭相出版他的作品,目前已有三十多國語言的譯本。創辦「生活建築」與「人生學校」,將有趣的哲學帶入日常,為生活增加更多元的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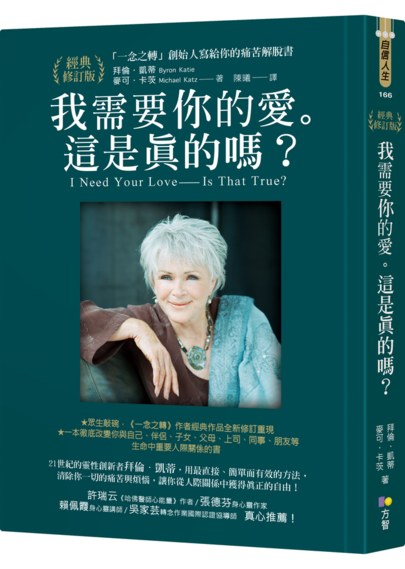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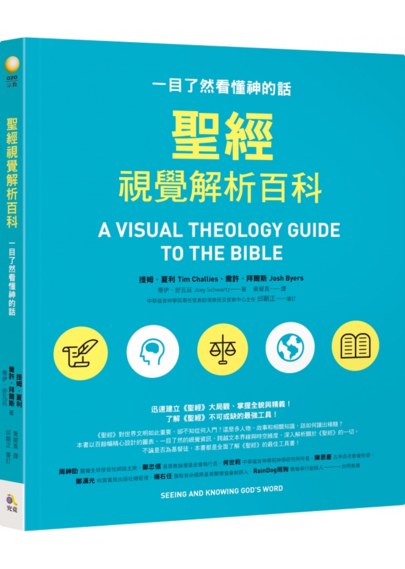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