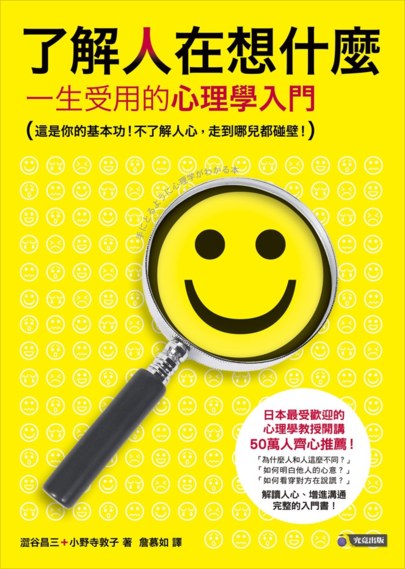油麻菜籽花
「同學!今天喝完早餐牛奶之後,我們這年級的學生要遠足到『舊眉村』那邊去撿共匪空飄傳單。」
新來的級任老師,長得像玩具牌子「尪仔飆」那個黑白無常,三角臉頂在一個瘦弱的身子上。他拿起手來指揮的樣子,又不免讓我想到爬在花叢間的螳螂,低斜著眼左看看、右看看。其實他人脾氣蠻好的,不像那個有鐮刀手的螳螂那樣會欺負小動物,因為是新來的級任老師,他的綽號也就在黑白郎君跟螳螂仔之間,讓班上的小朋友們一下子難以做好決定。
因為我是班長,小朋友們老喜歡看我做決定。大概是老鳥那種心情吧!幾天來我總覺得,這個不知道哪裡蹦出來的級任老師,活像是一隻菜鳥似的,還沒有我懂事。
「那就叫他『壁虎』吧!」
我很權威的跟班上的同學說。壁虎不是也有一個三角臉嗎?
「壁虎……壁虎。」
小朋友們都覆議著。
壁虎說完這話的時候,就轉身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大字「共匪的空飄傳單」,想是壁虎仔特別有心,把「共匪」兩個字特意的圈了起來。小小心靈哪分辨得岀大人們愛計較的世界,三不五時老師總愛在課堂裡面發表自己對時事的感想,一來是哪裡又戰爭了,二來是全民準備要反攻大陸了,三來是共匪正發起文化大革命什麼什麼的……
我突然想起阿嬤從我們家的油麻菜籽田裡撿回來的傳單樣的東西,我媽媽看了嚇得掉了半條魂,叫我趕快去跟阿嬤說……不管怎樣,千萬不要再帶掉在田裡面的這些傳單回來了。
阿嬤不識字,根本就不知道那傳單上寫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阿嬤只說……
「不知道哪裡吹來的這些東西,也不知道這些怪東西會有什麼害處。」
我們家漂亮美麗的油麻菜籽田,實在不應該有這樣的東西,像郵差遞來的信那樣,阿嬤要剛剛才認得幾個字的我為她翻譯一下,這上面寫的究竟是什麼碗糕?
「這個還有圖的,我是看有懂又像沒有懂,這個圖的意思就是說……戴帽子的是當兵的,那個穿背心的就是當工人的,啊那個拿抓耙子的八成是農人。啊看起來的意思就是說……這三個人是要把旁邊那個人打死就對了。」
阿嬤笑咪咪的這樣對我解釋。
我拿起那張粗粗的紙片左看右看,其實有好些字我都還不懂,我跟阿嬤說:
「老師說這是大陸那一邊的共匪,用那個氣球,很大很大的氣球,然後載過來飄到我們這邊的傳單啦!」
阿嬤跟我,你看我我看你的,都不能明白大陸究竟是在哪一邊?啊共匪又是誰?怎麼會有人姓「共」?名字取得那麼怪,還是土匪的「匪」呢!啊共匪是一夥人?還是一個公司?什麼樣的氣球可以帶這麼多的傳單掉到我們家美麗的油麻菜籽田裡?
我跟阿嬤說:
「我不要管了啦!我媽媽說這個東西不要再撿回來了,妳明天可不可以給我一包白糖,我要帶去加在早餐的牛奶裡面喝,我們學校那個聯合國牛奶,一點味道都沒有,難喝死了,我還比較喜歡喝豆漿呢!豆漿甜甜的。」
阿嬤說:
「念書還有這麼好康的,有牛奶喝喔!」
阿嬤笑咪咪的。
「我們老師說是聯合國送給我們的啊!」
「聯合國是啥咪果?」
我就知道阿嬤比我還沒學問,她再這樣下去,我簡直沒辦法跟她聊天了。
「聯合國是一個國家啦!妳不要再問了啦!阿嬤給我一包糖啦!我要加在聯合國牛奶裡面,我們學校的聯合國牛奶難喝死了。」
「去跟你媽要,去跟你媽要。」
「又沒有要過年做粿,哪來的白砂糖啊?我的阿嬤最不長進了,不念書不識字不要緊,連一包白砂糖都那麼不願意配合。」
「同學!千萬要記得,發現任何共匪傳單,一定要帶來交給老師,如果有家長偷偷的藏著傳單的,也要跟老師報告。」
我回去跟我阿嬤說:
「阿嬤妳不要再偷偷地把傳單塞在床底下了,老師說那是匪諜的行為。」
但「匪諜」又是什麼呢?
我把熱騰騰的牛奶放在我的桌子上,邊想著老師剛剛說的「偷偷藏著傳單的,就是匪諜的行為。」
匪諜是壞人的一種嗎?還是像布袋戲裡面的「真假仙」或是「黑白無常」?永遠都讓你猜不透他到底是東南派還是西北派的。我媽媽說:
「沒有要做粿,哪來的白砂糖?連黑糖都沒有呢!」
還笑咪咪的說:
「牛奶加鹽巴其實很好喝喔!」
早上來上學之前,我就爬到廚房的灶台上抓了一把粗鹽,用破報紙包著,抓在手裡一路奔跑到學校來,我超興奮的,今天終於可以不用喝沒有味道的聯合國牛奶了,聯合國怎麼那麼壞心!連牛奶都不給人家加糖,邊想著……我就把那一包粗鹽往奶杯裡倒去,旁邊的小朋友們偷偷的看著我,我覺得我太幸福了。
自從我發現一種含有薄荷味的「固齡玉」牙膏,在賽跑完可以拿來擦痠痛的肌肉,那種涼涼的感覺可以取代很貴的「擦勞滅」後,這是我今年的第二個大發現。我每天都在書包裡,拽著半條從家裡偷偷拿出來的「固齡玉擦勞滅」,在體育課結束以後,讓小朋友們分享。我們把牙膏塗在小腿肌肉上,那種涼涼的感覺真是……超幸福無比。聯合國牛奶加上鹽巴,我真是天底下最聰明的小孩。
油麻菜籽
油菜自古在大陸長江流域一帶即有栽種,因種子含油量高,栽種普遍,如同稻作與小麥。唯台灣中南部栽種用途多是翻入農田裡面當作綠肥。油菜開黃色小花,因大片栽種,美麗的黃色花海點綴了枯燥辛勞的農作生活。
綠繡眼
拳頭那樣大小的雜食鳥類,但偏好昆蟲,翠綠呈黃,聲音小巧細緻,不像麻雀那樣老是偷吃穀類,但牠喜歡吃水果,尤其是木瓜。我們叫牠「青笛仔」,是田間常見的留鳥。
「媽媽,我們前兩天那一條牙膏怎麼又用完了?怎麼又不見了?」那一整個夏天裡,我那個笨弟弟總是這樣子不住的問我的媽媽。
「是啊!說也奇怪內!黑人牙膏就可以用很久,怎麼換成這種固齡玉的,三天兩頭就用光了呢?」
我摸摸書包裡那一條今天早上偷來的固齡玉牙膏,一溜煙的就往學校裡跑,有了這個可以擦在腿上讓肌肉涼涼的牙膏,今年我鐵定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小孩。
壁虎老師跟在一班小學生的後面,遠遠的看起來,一定很像是趕鴨子到田裡覓食的農夫。圳溝的邊上站了幾顆很老很老的榕樹,榕樹下的土地公廟前,阿嬤跟幾個雇來的長工,遠遠的就跟我們招著手……
「老師老師,你是趕鴨子要去遠足嗎?還是美術課要寫生?」
快要中午了,幾個長工摘了斗笠坐在一邊納涼;土地廟前的供桌上,擺開阿嬤一早就忙著的料理,一定有炸番薯籤跟天婦羅,用薄薄的皮捲起來的雞捲條,兩面煎得焦黃焦黃的虱目魚,還有夢裡尋它千百回再也找不到的「大麵炒」。
「各位鄉親,啊如果有看到那個共匪的空飄傳單喔!就要麻煩你們叫小朋友拿到學校來,不要自己拿去看喔!千萬不要看喔!」
我心想那傳單上不就是白紙黑字,難不成看了會長針眼?壁虎老師也未免太小題大作了,我最喜歡農忙時候的田裡的野餐了,阿嬤張羅著幾個長工過來吃飯。
小土地公廟裡的土地公爺爺,長年燻著煙火的臉黑嗚嗚的,只能張著那大眼睛,看著阿嬤擺在祂供桌上的農夫野餐。神仙也有做不到的事,幾個長工說笑著,開始拿起碗筷吃了起來。土地公如果突然從祭壇上走下來,說要跟大伙兒混著吃,我想農夫長工們也分辨不出今夕是何夕了。
剛剛才插到田裡的秧苗整整齊齊的,整好隊伍的小朋友們也整整齊齊的、嘰嘰喳喳的走過油麻菜花田裡,驚動起了躲在田間覓食的綠繡眼。綠繡眼在藍藍的天裡生氣的飛舞著,我真希望每天都能走在這一望無際的澄黃裡。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幅偉大的畫作裡面的小配角,遠天的積雨雲慢慢的翻絞著,看起來像米老鼠,不一會兒又像大力水手,我遠遠的朝著土地公廟那邊,跟阿嬤招著手。
早上喝完了我的聯合國牛奶加鹽巴,覺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健康的小孩。在來的路上,偷偷的在我的小腿肚上,抹了抹涼涼的固齡玉擦勞滅,我猜想阿嬤一定有在家裡幫我留了一大碗的大麵炒等我回家吃,我肯定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小孩。
綠繡眼都可以在這一片的澄黃裡快樂的生活著。我拔了一根草,在嘴裡嚼著嚼著,我想我也可以每天都活在這片一望無際的澄黃裡。
「小朋友,注意看有沒有傳單喔!」壁虎老師在後面提醒著。
我想老師大概也很欣喜,可以在小學生上課的時候,有這麼奇怪的一個理由,可以趕著一堆小鴨子,跑到這一片一望無際的澄黃裡來。
遠天的積雨雲不斷的翻絞著,慢慢的變成漫天的氣球,我覺得自己像是一隻飛翔在一望無際的澄黃裡的綠繡眼。
山梔仔
圳溝旁的那一頭原本空著的幾分地,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山梔仔樹突然一起爆放了整園的花朵,山梔仔簡直像不受教的青少年一樣,滿園子的蒼白,讓你覺得刺目的蒼白,像一伙子不安份的青少年突然齊聲的尖叫了起來。
山梔仔花飄著濃郁的香,其實因為這樣的關係,就說在成長階段的山梔仔,你就不會特意發覺它的存在。老師說植物跟動物最大的不同,就是植物會把它的生殖器官大剌剌的暴露出來,招蜂引蝶的,硬是要你知道它該傳宗接代了。山梔仔就在清明時節裡沒命的開著花,沒命的洋溢著它的芬芳,也沒命的流淌著生命的汁液。
自從老茂他哥哥在一個深夜裡經過山梔仔園,被一個莫名的天外怪物嚇出病來之後,大人們就不准孩子放學時再從圳溝那一頭回來了。老茂說他哥哥在家裡躺了幾個禮拜,每天嘴巴裡總是說著些任誰也無法能懂的話,呢喃不清的。他那個做乩童的老子,在廟裡問了幾趟,說這孩子是被「豬哥神」附身了。小朋友們議論紛紛的說這是什麼太空時代了,還有這種天外怪物的神話。幾個帶種的還故意相約著放學的時候,要去山梔仔園裡面抓豬哥神。豬哥神終於在暑假的時候饒過了老茂他哥哥。
老茂他哥哥每天總是在黃昏的時候,在他們家的曬穀場裡繞著圈子,後來說的話倒是有幾分像人了,阿嬤說……豬哥神附身就是這個德性,時不時呢呢喃喃的還流著白白的口沫,又習慣性的在自己的臉上抹著,幾個孩子們過去逗著他,他就說:
「帶我去找白嘉莉。」
孩子們哇哈哈的齊聲的笑成一團,我阿嬤說:
「這個貓仔馬俊,今天說要白嘉莉,明天就要湯蘭花。你們這些孩子最好離他遠一點,我看這一生就要跟珠鳳送作堆了。」
孩子們齊聲歡笑了起來,心裡想阿嬤人真好,連珠鳳仔傳宗接代的事,似乎也是冥冥之中就決定了。
孩子們在暑假時,決定集結起來往山梔仔園裡把豬哥神翻找出來,先是三叔公說話了,三叔公說:
「你們這些死囝仔!都沒看見山梔仔園裡面跑來跑去的田鼠像貓那樣大。這麼大的田鼠,嚇得我們家那條土狗都不敢打園子裡穿過,你們這些死囝仔!你們知道這麼大的田鼠後面跟來的會是什麼嗎?就別提那豬哥神了,我猜那裡面一定有長得跟碗公一樣大的蛇。」
末了還用手在胸前比出一個大碗的姿勢。
叔公說完了,輕昧的笑了兩聲,留下一堆一臉狐疑的孩子。山梔仔花結實之後,本來是要拿來做一種黃色的染料用的。也許是收成的工作過於煩瑣,三叔公說是那一片園子的主人,賭輸錢跑路了,只得放任滿園的山梔仔不斷的開花結果,也從來沒有看見誰去整理它過。山梔仔花在一大片的水稻田裡,就變成一個怪異又神秘的地方。碗口這麼大的蛇,誰能想像那要有多長啊!幾個孩子能打得贏他嗎?更何況裡面還有豬哥神!
老茂說……我有一個辦法,我們叫死狗先進去看看,死狗如果被蛇吃掉了,我們大家就不要說就好了。我那個笨弟弟說:為什麼不叫你哥哥再進去一次呢?死狗那麼可憐,怎麼可以犧牲他呢!
「幹你娘啦!我哥哥才剛好,又要叫他進去,給我爸爸知道我會被捶死的。死狗反正也沒有豬哥神附身,我們給他五塊錢,騙他進去裡面給我們找……找……找……」
我弟弟就說:
「找蝦小啦!找白嘉莉啊……」
「幹你娘啦!白嘉莉怎麼會在裡面!」
老茂又說了,管他去死啦!他都秀逗成那樣男人女人都分不清楚,你管他去死!
「五元誰有五元!死狗!來來來……你來……」
暑假實在沒有什麼偉大的事,幾個小男生百無聊賴東敲敲西敲敲的成天裡不幹正經事。
死狗是我班上同學阿國的弟弟,也不曉得壞了那一根腦筋,從小就斜歪著眼、淌著口涎,從來也沒有入學上過一天課;大部分的時候,就只是跟著阿國的屁股後面到學校裡來。老師看這孩子可憐,會讓他坐在教室的角落邊上。他都是等著吃完便當,然後就不知道晃到哪裡去了,小小年紀超傳奇的,常常一晃就離開村子,三天五天都沒有訊息。聽阿國說,有一次死狗不見了之後,他爸爸還從隔壁縣的斗六把他領了回來。村子裡的孩子過了暑假,長毛的長毛、變聲的變聲,就像一園的山梔仔花一樣,齊聲的尖叫了起來,就只有阿國他弟弟死狗,還敢光著屁股在圳溝裡玩水。
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覺得死狗在我們這一伙孩子裡面,也不礙事。叫他做這個做那個,總也蠻聽話的,很可愛。可阿國老覺得他這個拖油瓶似的弟弟,越來越帶不出場。想起來也是,山梔仔花都說好要一起綻放尖叫,就只有我們的死狗,彷彿會一輩子斜眼歪嘴的流著口涎,不會成長也不會老去。
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堂,一堆野孩子就構築了一堆的天堂;自來只會呵呵呵笑著的死狗,從來也沒有用我們可以辨識的語言,告訴我們他的天堂裡是什麼,他天堂裡的樹是不是開花了。老茂幾次就笑著跟阿國說,我們帶他到山梔仔園裡,把他交給豬哥神,要不然就讓他給大蛇吃掉,這樣他就不會一天到晚都黏著你,不然到時候我們要去台北打拚時,怎麼可能一天到晚都帶著他呢?
就這麼辦,幾個不安分的少年就像山梔子花齊齊開放著一樣,就這麼辦。老茂去跟死狗說……
「圍著山梔子園子的那一圈泥溝裡,長了許多胳臂這麼粗的大鱔魚,你幫我下去摸摸看,抓到鱔魚的話,我用五塊錢跟你買,五塊錢喔!五塊錢可以吃很多的仙草冰。」
大熱天裡,誰受得了仙草冰的誘惑,孩子們或許有些不同意老茂的做法,但看看連他哥哥阿國都默許的樣子,大家也不再說話了。我自己就在暗地裡想,死狗只要一離開這個村子出差去了,就三五天的不回來,不是說還在隔壁縣的斗六都有人撿到他嗎?我想山梔子園裡的豬哥神,應該也拿他沒有辦法,以至於傳說中的大蛇呢,我肯定是三叔公掰出來的。我的三叔公老胡說八道,神經兮兮的。
要說豬哥神,我估計我三叔公被豬哥神附身得才厲害呢!頭先這兩三年裡,不知道是因為自己信心不足,還是聽了太多廣播裡的跌打損傷、壯陽藥的廣告什麼的,有一天,突然在我家的橋頭攔住我說:
「阿星,你偷偷的去把你們家的那個秤豬公的大磅秤,有沒有?就是大磅秤有一個秤砣,就是有一個大鐵塊那個秤砣,你偷偷的去幫三叔公拿來借用一下。」
我說:「叔公,你光要秤砣、不要磅秤,是要幹嘛?」
「小孩子,你不知道啦!你別問啦!」
「我要知道啊!萬一我阿公要秤豬公找不到要怎麼說?」
「哎呀!小孩子不好解釋啦!」
秤砣實在太重了,我求我弟弟用他的小三輪車,才勉強把那一只扛起來像豬公一樣重的秤砣,在一個夜裡,偷偷的載到三叔公家的園子裡。黑暗裡看見三叔公,早就用他家的秤砣練起功來了。
「壯陽的啦!壯陽的啦!」三叔公笑咪咪的這麼說。
「因為我的功力已經升級了,我自己這一顆五十斤的秤砣,早就不夠看了,現在是兩顆一百斤,按怎!你現在知道你三叔公的厲害了吧!」
大熱天,三叔公在黑暗裡穿著裙子也就算了,我跟我弟弟看呆了,三叔公把兩顆秤砣綁在一起,雙腳岔開,就把重的驚死人的秤砣綁在胯下,撐著站了起來。我跟我弟弟深怕三叔公一不小心會破功閃到腰,三叔公搖晃著手,臉上青筋一條一條的爆了出來,咬著牙蹦出幾個幹譙的字眼後,才吃力的說著……
「沒代誌啦!沒代誌啦!我果然已經升級了,小朋友不要亂來喔!三叔公有練過。」
原來這個就是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陰吊五百斤」,我的三叔公已經練到一百斤了,哪還需要八支磅秤的秤砣才會有五百斤。我在想這村子裡就我家跟三叔公,兩支磅秤大家借來借去的,再來三叔公的小雞雞,要用什麼吊呢?磚塊嗎?練這種功夫要幹嘛呢?我從來也沒明白。想來村子裡也只有養著那些去給人家配種的大豬公,三不五時的流豬哥涎,晃著自己的大雞雞過街。大豬哥為了面子,練練這功夫應該還有點用;我三叔公都兒孫滿堂了,怎麼這麼不成熟的,還在為自己的小雞雞擔憂,我坐上我弟弟的三輪車,往回家的路上時,心裡有一點憂慮的跟著我那傻呼呼的弟弟說……
「我覺得我們的三叔公,要不是就是豬哥神,要不也已經被豬哥神附身了。」
那一整個夏天,三天兩頭的,死狗總是用草繩拖著香腸般那麼大小的水蛇,走進教室裡來找老茂,一臉天真的拉著他以為是大鱔魚的水蛇,要來跟老茂換五塊錢,剛開始實在是有一點嚇人……
「要死了,那是水蛇不是鱔魚,幹你娘咧!水蛇跟鱔魚都分不清楚!」老茂急了。
班上的同學都笑成一團,阿國也因為他的弟弟,一整個夏天都有著新的遊戲,而放心不已,碗口般粗大的蛇一直都沒有出現,可以拿來換五塊錢的鱔魚,死狗一隻也沒有抓到過。我的三叔公閃到腰,在床上躺了兩個月,我跟我弟弟在一個夜裡騎著他的三輪車,去把我們家的秤砣給載了回來。
孩子們都有自己的天堂,一堆野孩子就構築了一堆的天堂,而那一園子的山梔子花,還是像不受教的青少年一樣,不時的開了滿園子的蒼白,也不時的尖叫著。隔年的春天,來了一批工人,推土機把那一園子的山梔子花全給摀平了。
「這下子豬哥神不知道要跑去哪裡了?」
我三叔公悻悻然的這麼說。好像因為村子裡少了這塊神秘的地方而唏噓不已。在那一整年裡,走過那片田時,總是感覺到風中依稀有著山梔子花的香……
梔子樹
常綠灌木,高三公尺,葉深綠具有光澤,繖形花序,花香淡雅呈白色,漸轉為乳黃色,是常見的庭園香花植物。果實俗稱山梔子,含有藏紅花素,常做為食物的黃色染料,自古就列為藥用,是外傷與解毒之良藥。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