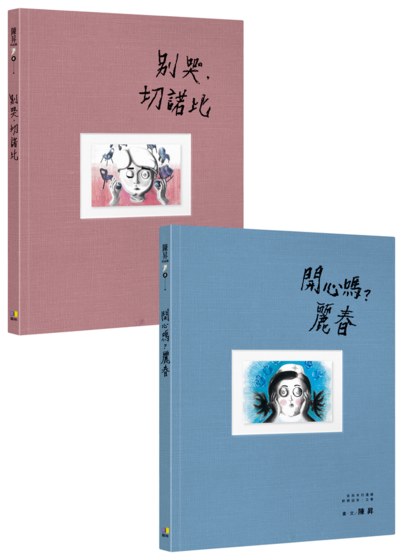女孩說︰「唱首歌給我聽吧!唱一首沒有顏色的歌給我聽吧!」
「歌都是有顏色的,歌都是無色的顏色。」
「這樣,我會很悲傷。」
「越悲傷的歌越是無色的,那我給妳唱一個影子的歌吧。」
卓瑪不要哭——時空錯位
沒有盡頭的國道公路,聽說盡頭的盡頭的是五千米高的可可西里,從路那頭飛馳而來的盡是滿車子泥濘,混身黑壓壓的大貨卡,拽著拖在車後的粗鏈條響著雷般的噪音,遠遠地讓人非要躲避不可。
倒淌河客運站裡停滿了這些亡命的傢伙,來自高原的漢子操著粗鄙的口音,跳下車來時身上都還冒著蒸騰的熱氣,七天七夜沒熄火過的引擎,一下子還不相信它已經又躲過一劫地來到了倒淌河。
倒淌河驛站裡的被褥從來沒有整齊地折疊過,客房的門斜掛在門檻上,漢子們跩開了門拉起被褥蒙頭就睡,被褥上映著千年來也不曾換洗的油光,一點也沒能掃了漢子們的興致,立馬就呼著轟隆隆的鼾聲睡去,可不?這可是從高原出發七天七夜後,唯一能讓鬆散的骨頭平放的機會,不多久永遠不會熄火的引擎又要發出怒吼催人上路,入了關此去又是幾千里的路,還有很多的七天七夜。
卓瑪在今天正午失去了她的孩子。剛剛才上學的孩子在倒淌河前迎上了高原的漢子,高原上下來的黑車子沒有人停歇下來,正午的草原上飄來了漫天的烏雲,夾在暴雨裡的閃雷追趕著一輛一輛從高原上下來的黑車子。
卓瑪跪坐在倒淌河邊上,張著發不出聲音的嘴。

他在驛站前看著,旁人忙著張羅把卓瑪的孩子送進站前的衛生所,剛剛才上學的孩子。
衛生所後遠遠的湖面上慢慢地結起了朵朵的烏雲,吹起一陣夾著焚燒野草味的冷風,站前的幡幟啪噠啪噠地被風扯著。
卓瑪跪坐在對面的倒淌河邊上,對著遠天的烏雲,張著發不出聲音的嘴。
他站在驛站前看著,好一陣子回不了神,他搭了一天一夜的長途車,顛簸得無法睡去,剛下了車就看見旁人忙著把卓瑪的孩子送進衛生所,任誰都不免要覺得這是不是含了點暗示性什麼的,他才下了車就遇上這樣的事。
長途貨卡一樣地來了去了,操著粗鄙口音的漢子,視若無睹地走過卓瑪忙著自己的事,驛站前人進人出的,送走了孩子,旁人也都散了去,他以為只有自己跟卓瑪是停格在路兩邊的人,他很想跟對面的卓瑪說:「卓瑪,妳不要哭。」
可是他沒有,他不知道這些來來去去的人怎麼了,烏雲慢慢地罩上小鎮,風越來越急地扯著人,感覺他跟卓瑪漸漸地淡出了這畫面……
他覺得應該找人說說話去,他覺得自己大半輩子沒跟人說過話了。
倒淌河蜿蜿蜒蜒地流向遠方的湖泊,湖泊在風裡起了伏流疊浪,湖邊的人們都在這個季節就準備向溫暖的南方遷徙而去,留下來的都是些無法遠行的老人跟等待著親人歸來的人。
湖邊的幡幟在風裡發出裂帛的聲音,草原上飄移過來的烏雲拖扯來了暴雨,物換星移,人們也不得不理解生命在這裡不過像草芥一般,而那是一個望不到盡頭的湖泊,那些千百年來堆積在湖裡的幡幟,層層疊疊地像尋覓不到彼此的屍塊,一切都會吞噬到湖泊裡,卓瑪的孩子在草原上睡了。
而一切都會吞噬到湖裡去,屍塊一樣的經文幡幟,老去了的卓瑪,睡去了的孩子,雲朵、暴雨、閃雷,時光、歲月,都吞噬去了吧。
連那不止的悲傷,也都吞噬去了吧。

他在夜裡給他的女人新發了一個短訊,跟她說去過倒淌河了,一點也不是她想像中的那個樣子,小地方就一來一往的國道公路,幾個修車廠、三兩家餐館驛站,湖邊的草原上倒淌河蜿蜒而過,不是尋死的藝術家會來過的地方。
「信是從這裡發出的沒錯啊,可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他在電話裡努力地對她解釋著,他怕女人是拿他窮開心了。他真能從地圖上找著這地方也真夠行了,不想還真為了要討女人喜歡,還得去找十年前從這裡發信的人。
就是死了,也早投胎去了。他真想對她那樣說,真不曉得在浪漫些什麼勁兒。
夜裡也沒什麼選擇地就在湖邊的驛站裡住了,跟路口僅有的攤子要了幾根羊肉串,雜貨店裡要了一兩白酒跟方便麵,繳了房錢領了鑰匙默默地回了房,挑了一個向湖面的房間,風景挺好的,雖說這個季節開始起風了,湖面總是沉鬱鬱的,就安慰自己說日子也不是每天都能是開心的,剛巧今天是這樣不高不低的心情就看著不開心的風景了。
屋裡的電視收訊很糟,洗澡自然是能免就免了。給自己倒了點白酒喝了,天空堆積起了雨雲,遠遠地從路的盡頭的盡頭,慢慢地往旅店這片草原飄移過來,彷彿是有人從天上倒了一大桶的墨汁,倒淌河的草原湖泊都漫進了雲雨裡,雲裡的閃雷在墨汁一樣的暗裡給大地切了一道道的傷口。
有點想找人說說這樣好看的風景,也想,這樣難以表述的心情就放在倒淌河旅店裡罷了。
.jpg)
起風了。草原上的人早早躲進了屋裡,他在想有什麼道理非得要一個人跑這麼遠的地方來,跟電話那頭那個女人沒完沒了地瞎耗了幾年,不該是屬於這個世代的典型了。
這年頭男人都是藝術家,女人都想開咖啡廳然後養一個藝術家,自己倒是反了,耗上了一個像是藝術家的女人,每天欲仙欲死的怎麼就是不死,自己是貧乏的人,夢想早在遇上這女人之前就已經讓狗給吃了,這樣想挺樂的,別人老把時光詩意的說成白雲流水什麼的,自己倒真覺得就是被隻瘋狗什麼的給吃了。
他知道這女人就也只是在跟自己瞎耗,說起來自己也就是個備胎,也或者再耗下去等到這女人投降委身了,可以報復性的不要她了,這樣想更樂了,沒道理到這遠地方來出趟差,還得幫人找十年前在這給人寫信的幽靈,怎麼想都難服氣。
窗外的風越來越急,他開始擔心起萬一天氣再壞高原上的路要封了,沒準十天半個月的都出不了倒淌河了。
現在的女人都怎麼了,很悶地睡了去。
起來的時候已經是大中午了,窗子外白晃晃的一片,還以為自己是死了上天堂了,急忙地起身,昨夜裡躺著也就睡著了,挺好。很久沒有這麼痛快地睡一回覺了。
昨夜裡狂風暴雨的今天倒是一片碧藍如冼,非要去湖邊走走,出了驛站大門路對面就一小雜貨鋪子跟修輪胎的店挨著,昨夜裡停了滿滿一廣場的大貨卡,卻一個也不在了,大概是趁著一早天氣好就又開上亡命的路上去了。
他在心裡面笑著自己,怎麼的昨天狂風暴雨裡驚惶失措見到的亡命貨卡,在這一早的大晴天想來也沒有什麼恐懼了,人在慌裡就會顯得多愁善感,暗夜裡特別顯得孤獨,所以要拒絕在夜裡去想念人了。
今天就不給她打電話了,天氣這麼好,也許應該找個亡命便車搭的,客運站的標示簡單得有點多餘地寫了,指向一望無際的草原那頭是傳說中的可可西里,他挨著標示牌在想,十年前她那個從這裡發出信的人,是否也就像現在的我那樣,搭上一輛頭也不回的便車,去了一個能永遠逃離她的地方。
他在客運站走了兩圈,封山的季節了,連個給人坐坐的椅凳子也收光了,他倒是不太憂慮回去的路,卻有點憂慮起萬一自己做了逃離她的決定時,是不是能有亡命的便車可以載上他奔向高原去。
奇怪的是昨夜一大廣場的人車,這樣好天氣,怎麼的一個人影也不見了,像是這裡人說好了把一整個倒淌河,在一個淒風苦雨的夜裡就扔給他憂心似的。都休息吃飯去了吧?他這樣猜的。
他在客運站裡發了一回兒呆,突然覺得有點混沌地想不起來,昨天小孩出事的時候,那個叫卓瑪的女人究竟是住在對面的哪戶人家,甚或覺得昨天是不是真有小孩撞上了黑車子這回事,可沒有了客運車回文明的地方,這事要在平常還挺嚇人的,可又不想白白地浪費了剛剛才興起的,要豁出去地搭個亡命便車逃離這一切的想法。
他走在街心感覺這路,怎麼就沒有車子會再經過的樣子,去了修輪胎的廠子那邊看了一下,門是掩上的,沒有打算做生意的樣子了。

過到這來之前就聽說了,到了嚴冬封了湖,這就都走了人,下到小鎮人多的地方去討生活,沒這麼巧都在昨夜裡走光了,這也逗,驛站裡不是還住了些黑汙汙的漢子跟自己麼,就是走人了,也沒道理不吆喝一聲。
他撥了電話給他女人,得跟她說說,妳這美妙的倒淌河小村子大白天有鬼的事。
沒想電話起先說的是電話不通,後來莫名其妙地說你撥的電話是空號,說了兩趟之後索性就沒了訊號。
真他媽見鬼了,徹底地後悔多事在就近出差時跑了這趟見鬼的倒淌河。
修車廠挨著雜貨鋪子,總算是有點人氣的樣子,他在門前探了探頭,屋子黑壓壓地散著點焚香唸佛的味道,大西北這邊人都這樣,生意居家佛堂都不分的,宗教感很重。
人要都跑了,恐怕連吃的都沒得混了,這才真有點著急了起來。
「有人嗎?請問……」適應著屋子裡面的黑,慢慢地晃了進去。
「有人嗎?請問這裡有人沒有……」
「……」暗裡有位婦人坐在櫃檯後面的爐灶邊上,爐子燉煮著一鍋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的湯汁,卻也不回話的,儘往灶裡邊添著柴火。
「有什麼事嗎?」婦人幽幽地別過頭來,他才發覺她是昨天失去了孩子的卓瑪,卻也不太肯定的,只覺得婦人卓瑪彷彿在一夜之間老去了許多,要不是她仍然穿著昨天一式的斜掛毛氈外套,跟那看過一眼永遠也無法忘記的憂傷眼神,他是不會認得的。
「不好意思,打擾了。」其實,更應該是他想為昨天的事,表達一點慰問的意思,只是非親非故的沒辨法起個頭,也就一陣子又僵住在爐灶的兩頭了。
爐子上的湯滾滾地啪啦啪啦響,有點蒙太奇的,依稀是昨天路兩沿停格的畫面,現在又慢慢地融進了現實。
突然覺得也沒有很著急想要知道,怎麼找到回去的車坐,只是一心地記掛著,該怎麼對昨天才失去孩子的母親說點什麼好。
「吃飯了嗎?」婦人好意地問。
「欸,不急。」沒想人家還先關懷起自己來了。
「回去只能是搭順風車了,這個季節湖都冰封了,沒有遊客不會有客運車了。」大概是看多了像自己一樣的冒失鬼,很流暢地跟他說了。
「……」沒想到怎麼回話地望著那灶裡的柴火看著。
「謝謝你了。」婦人抬起頭說,眼裡依然帶著那抹憂傷的眼神。
「是啊,就請妳……不要太傷心了……」好像也只能是這麼說了,也沒有覺得太奇怪地去想,人家怎麼會知道自己的心情。
「車晚些應該還是會有路過的,給點菸錢說說就能下到省城裡去。」好像交代完了事情,轉身又給灶裡添了點柴,佝僂著身子隱約在突起的煙霧裡,更融回去了現實些,彷彿一下子婦人又老了去,他慢慢地回過神來了。
「那就……請妳……不要太傷心了。」覺得該是離開的時候了,離開這個悲傷的婦人,離開這個悲傷的屋子,離開這個時空。
「那麼,再見……」說了就釋懷了。
彎過身子慢慢地迎向鋪子口的亮光走去時,門口也進來了一個老人家,喘著氣一樣佝僂著身子,吃力地走著。
「最後一個了,遊客都走光了。你是最後一個了。」他想昨天一下午還滿滿一屋子蒸騰的人來人往,車也擠滿了驛站的,這是在說什麼了?
老人家吃力地靠著灶邊,伸了伸腳,屋子裡漫著煙霧。
「人都走了!去山下去了,留下的都是等死的人,跟等著不知道死去的人會不會回來的人哪。」老人看看一旁的卓瑪,她在昨天失去了孩子,也在一夜之間老了。
「你問她什麼了?她不會說漢話的,她沒念書,她什麼都不曉得的,很久以前死了孩子就不說話了。」
他站在門外一片耀眼的光裡,怔怔地沒想到要再明白些什麼,他跟自己說,自己曉得就好了,自己是睡過頭了。
在這麼遙遠的地方,在這樣接近神明的路途上,他覺得自己已經離開了很久很久……似乎是卓瑪失去孩子那個時候那麼久了。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英文名叫Bobby Chen,生於臺灣彰化,是天生就很迷人的天蠍座。
英文名叫Bobby Chen,生於臺灣彰化,是天生就很迷人的天蠍座。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