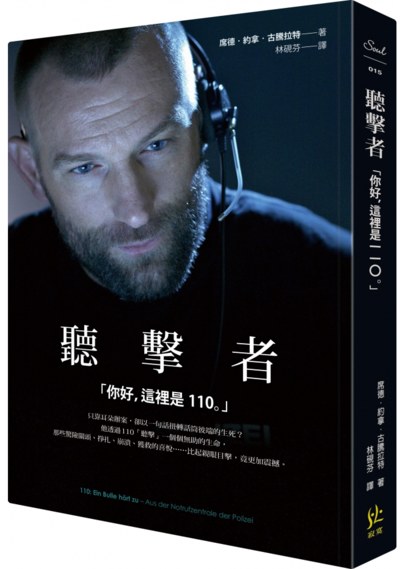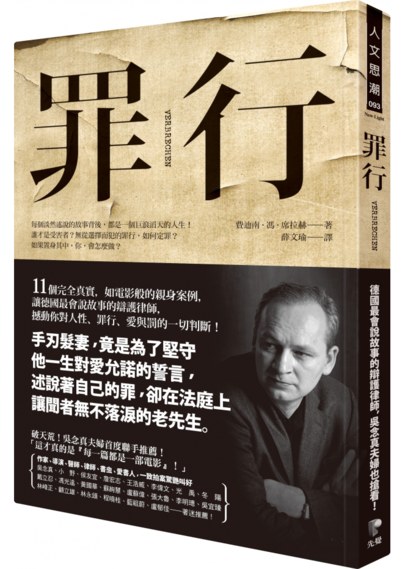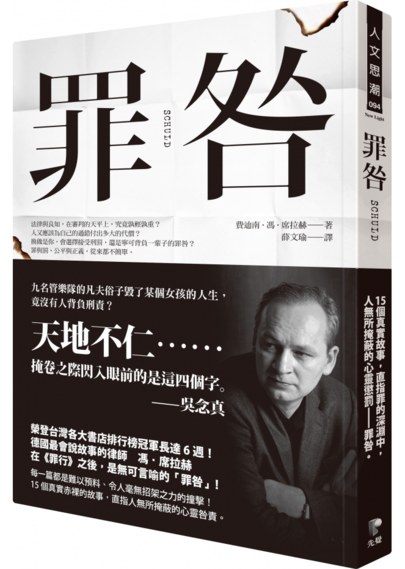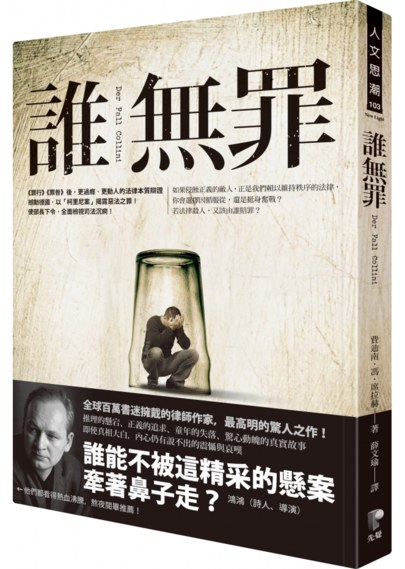每個人心中都有些說不出的秘密與痛苦,
即使過了好久,回想起來,依舊感到心疼;
當我們終於鼓起勇氣想說出來,
還需要一雙懂得聆聽的耳朵。
「本文作者史戴分.格羅茲是一位文學造詣非常深且經驗豐富的心理分析師,書中描述他跟診療個案之間的真誠交流,不斷沖刷我心中殘留對人的質疑。不知道是我個人的經驗與否,我相信這樣的關係應該是每個人心中都渴望擁有的心靈撫慰,換句話說,是人與人之間對「信任」渴望的一種滿足。因為這個世界上寂寞的人太多,我們更需要彼此的陪伴與聆聽。」──賴佩霞
同樣身為心理諮商師的蘇絢慧說:「我們都努力著聽懂當事人的生命故事中,難以被外人了解的生命邏輯。即使這生命邏輯的外在表現上是外人很難明白與認同的,甚至不認為是重要的,都有其重要的意義在其中。」
接下來就請您來讀讀,摘自書中〈愛,或被愛〉篇章中的這個故事:「回到家」,聽一位71歲老教授,說不出口的生命心事。
◆回到家
「我父親早已看穿我的內心,他卻不喜歡他所看到的。
但那個星期天下午的景象卻讓我幸福平靜,彷彿回到了家。」
我第一次見到詹姆士教授是在萬聖節早晨。我的小孩穿著睡衣跑來找我,說等會兒我到樓下工作的時候,他們要跟媽咪一起做巧克力蛋糕,還要用糖霜做成一個個的幽靈,放在蛋糕上當裝飾。
我走到樓下的診療室時,我太太收拾早餐的聲音,以及女兒彈出的鋼琴音符漸漸淡去,我順手關上身後的門。我打開燈,調整恆溫器,把報紙擺在候診室。再十分鐘就九點了。
詹姆士先前打電話來預約時,聲音聽起來並不會很焦慮。因此我猜想他不會提早過來,他比較屬於準時出現的客戶。我坐在椅子上,再次在筆記本上看了看他的名字和住家地址,之後我閉上了眼睛。我很難描述每次諮商前的心情:那是一種混合期望、好奇,以及一絲不安的感受。
九點剛過,門鈴響起。站在我家門前台階上的男子,比我從聲音中猜想的還要高壯。「請問是格羅茲醫師嗎?」
等他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定之後,我問他:「我可以幫你什麼嗎?」
他告訴我,他其實並不確定我幫得上忙,他甚至懷疑沒有人可以幫他了。接著,他開始向我敘述他的一切。詹姆士已經七十一歲,退休前在倫敦一間大型教學醫院當教授。他聲望很高,卻謙稱是因為自己講話慢條斯理,讓大家以為他很聰明。「我並沒有特別聰明。」
他也向我敘述他跟妻子依莎貝爾結褵四十四年的婚姻生活。妻子是家庭科醫師,跟他生了四個孩子:前面兩個是女兒,後面兩個是兒子。女兒都已經結婚也各自有孩子了,兩個兒子雖然還沒成家,但都有穩定的工作。「拉拔孩子長大是個漫長的過程,有時候也很辛苦,不過我的孩子沒讓我特別擔憂。」
他停頓了一會兒。「依莎貝爾跟我見過婚姻諮商師,諮商師認為我應該過來跟你談談。她說,你能夠幫我找到合適的諮商師。不過我不知道她是怎麼跟你說我的狀況的。」
我告訴他,諮商師認為最好由他自己來告訴我所有的事情。
我還來不及繼續說話,他追問了一句:「她有告訴你我是同性戀嗎?」
詹姆士說,故事其實很簡單:當他娶依莎貝爾的時候,他把自己的性向鎖進盒子裡。兩年前,他的父親過世之後,「我把盒子打開了。」他那時原本是到紐約探望女兒與她的家人,卻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家三溫暖。「我這輩子頭一次感覺自己的存在。」
他跟那個在三溫暖認識的男子僅維持短暫的關係,但之後,他還有過兩個男朋友。「我已經不年輕了,因此我還研究起『威而鋼』。不過,這不只是跟性有關,這一切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問他,他是不是想要告訴我,他以前從來沒有跟男性發生過性關係。
「沒錯。」他回答。他一直喜歡男性,很早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戀,也認為自己上了大學之後會遇見對的男人,一切水到渠成。可惜,這想像從沒成真。「有許多勇敢的人大方出櫃,承認自己是同志,但我不是那樣的人。」
他坐在椅子裡把身體往前傾了一些。他告訴我,他跟妻子一起念醫學院。「她那時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便是現在也一樣。」他們自醫學院畢業後就結婚了。這些年來,他曾試過好幾次,想跟依莎貝爾提起這個話題,但終究沒能說出口。
幾個月前,詹姆士坦白對妻子說他目前正在跟一個男人交往。當然,他妻子非常沮喪,但能體諒。在雙方同意見婚姻諮商師之前的幾個星期,兩人的生活簡直糟透了。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想留在跟依莎貝爾共同建立的生活裡,卻不知道該怎麼做。「這就是我來這裡見你的原因。」
有些時候,他認為他們應該賣掉現在的大房子,改買兩間小一點的房子:一間給依莎貝爾,一間給自己。如此一來,他們都能各自保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其他時候,他認為問題出在更根本的基礎上──親密感。「我有個很糟的感覺:我可以選擇跟男人在一起,但我很快發現自己也無法跟那個人太過親近。」
我問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告訴我,依莎貝爾擅長交際,他則不然。他真的不知道她這些年是怎麼容忍他的,在他們家甚至有句玩笑話:他只有在被麻醉的狀態下才能表現出最好的一面!「我是個笨拙的人,有些人喜歡這樣,但有些人不喜歡。我老是說些別人不會說的事情,那些每個人只會放在心裡,但不會說出來的話。」
儘管我沒有表現出來,但是我感覺到他知道我聽過他這方面的困擾了:他會說些別人不會說出來的事情,卻不說任何有關自己的部分。他是打算藉此讓別人尷尬,因此他就不需要尷尬了嗎?當我正在思考這個可能性,他問我:「心理治療能如何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回答他,我還不確定可以採取哪些方法來幫他。
詹姆士說,他很希望我們可以達成某些決定,然後他會照著做。此刻,他沒辦法決定該怎麼做。從來沒有人知道他也有困惑的時候,但他現在的處境確實難堪。離去或留下的決定在不同的時間看來,都是對的。他的孩子不知道他是同志,他也不希望讓他們知道。他不希望他們因此厭惡他,把他想成最糟糕的人。
我告訴詹姆士,我能明白他的心情,他不想做會後悔的事。
他點點頭。「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應該離開。我跟依莎貝爾在一起時,從來感覺不到百分之百的自己。」接著,他描述某個星期天下午他躺在男友懷裡的情形。「我們在房間裡聽音樂。當音樂播完,我靜止不動,他也就這樣抱著我。我們整個下午就躺在那裡,直到我想起身為止。我以前從來不知道可以有這種感覺。」
「而你不想放棄這種感覺。」
「一點也沒錯。我也不認為我能放棄。」
「為什麼要挑在這時候?」我問道。
詹姆士說他也不確定,或許是跟他和依莎貝爾有關吧。自從上了醫學院,他幾乎都在照顧別人。先是依莎貝爾的父母親,再來是他的。他們生病,需要照顧,各自因為乳癌、直腸癌、心臟病和胰臟癌而先後過世。他的大女兒有個非常糟糕的童年──她有閱讀障礙,跟老師處不好,會偷東西。但這些都過去了,父母過世了,孩子們現在也都很好。「也許這樣顯得我很自私,但我現在想體會有人愛我的感覺,而不是因為他們必須這麼做。」
我們彼此沉默了一會兒。
「我的父親過世之後,我感覺鬆了一口氣。聽起來很糟,但他真的很不可理喻。」儘管他父親生前是醫師也是議員,在地方上頗受敬重,但跟他一起生活的日子卻是痛苦不堪。他是個理想化的社會改革家,大家都認為他很了不起,但他實際上卻動不動就發怒。「雖然他發完脾氣就好了,但我內心裡仍然很害怕,甚至會發抖好一段時間。我們都能看出他的情緒火山即將爆發,卻沒有人能讓他平靜下來。」
更糟的是,他的父親完全不在乎他。「我記憶中的他,是個缺席父親,總在我上學前就出門去診所。彷彿我是個太沉重的負擔,他迫不及待想擺脫我。」
詹姆士敘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再度看見了他的回憶,那段他擁著男友的幸福時光,而他的男友也靜靜躺在他懷裡,享受被人無止盡地擁抱著。我問他,會不會因為被男人擁抱的幸福感,激發出正面力量,抵銷了父親給他的痛苦?
「我覺得父親早已看穿我的內心,卻不喜歡他所看到的景象。但那個星期天下午的景象卻讓我幸福平靜,彷彿回到了家。」
我們兩人又沉默了一會兒,後來他開口說道:「我猜,我的故事也不能算典型吧,上了年紀的老男人竟妄想逆轉人生,這種案例應該不多見,偏偏你眼前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攤了攤手,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活生生的例子。」
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安靜坐著,沒人出聲。我想著他一路走來的婚姻歷程,彷彿在看一連串的照片:他跟妻子在醫學院的日子、他們的婚禮、他們孩子陸續出生的樣子、父母親過世的樣子,以及他們一年又一年生活在一起的樣子。我看見生日派對和各種節日,年復一年地循環著。我想到詹姆士和他妻子還是醫學系學生的模樣,完全不知道未來有這麼多無可預見的事情。
接著,或許是樓上傳來的隱約聲響,也許是鋼琴的聲音或某些人聲,讓我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也想像著一連串的人生照片浮影--我們出生,我們死亡。橫亙在我們眼前等待的是什麼呢?
詹姆士嘆了一口氣,我問他在剛才的靜默中想些什麼。
「我在想,如果我的妻子可以接受現在的我,而且願意繼續和我一起生活,我想要留在她身邊,同時和我的男友往來。如果她能接受這一點,我想這就是我想要的。」
在這句話之後沒多久,我們結束了諮商。我把詹姆士轉介給我敬重的心理諮商師,他的診療室就在詹姆士的住家附近。自那以後,我就不曾再見過詹姆士,但不知為何,我總是忍不住回想起這次諮商。
兩年過後,我有一次坐在咖啡館裡等我的妻子。我瞧見別人遺留在桌子上的《泰晤士報》。在訃聞一欄中,我瞥見了詹姆士的名字和相片。上面詳載了他在職場上的傑出成就,以及學生和同事對他的稱頌之詞。這則訃聞最後寫著,他在家中平靜辭世前,他的妻子守在一旁,伴著他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這個故事來自《說不出的故事,最想被聽見》
讀另一則故事〈害怕失去的恐懼,讓我們更容易失去〉







.jpg)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