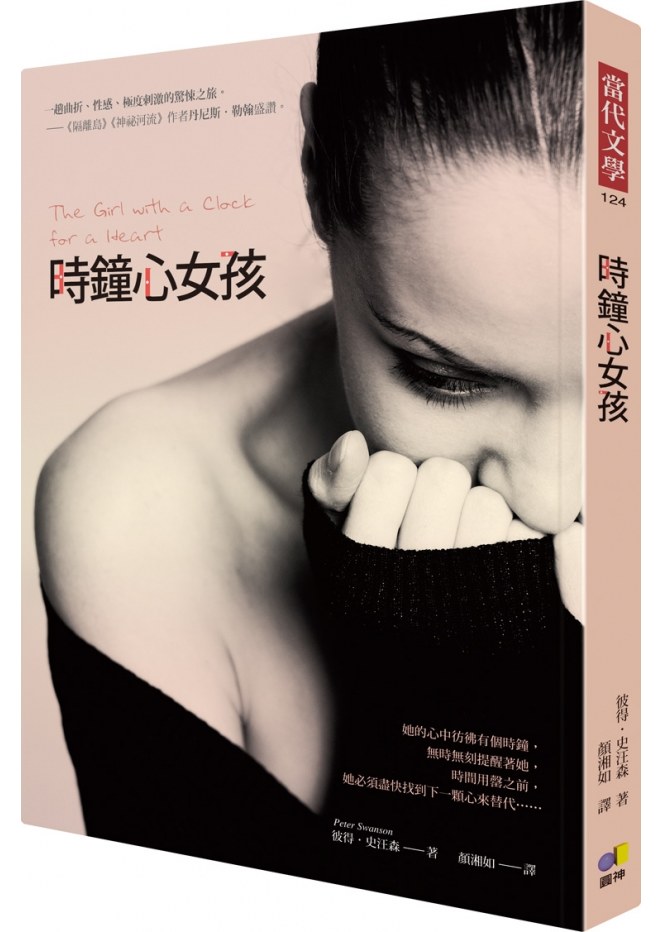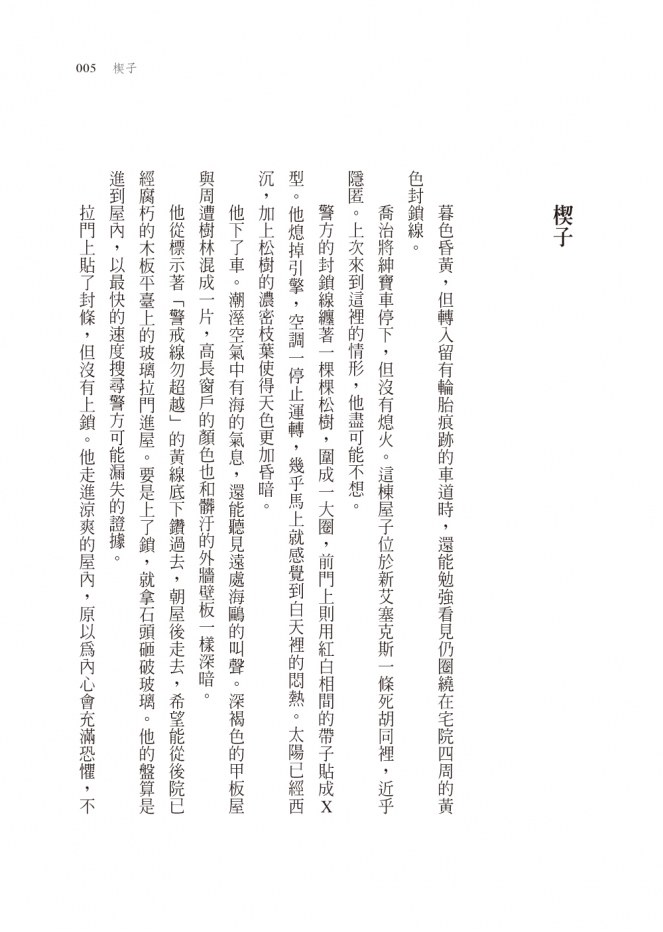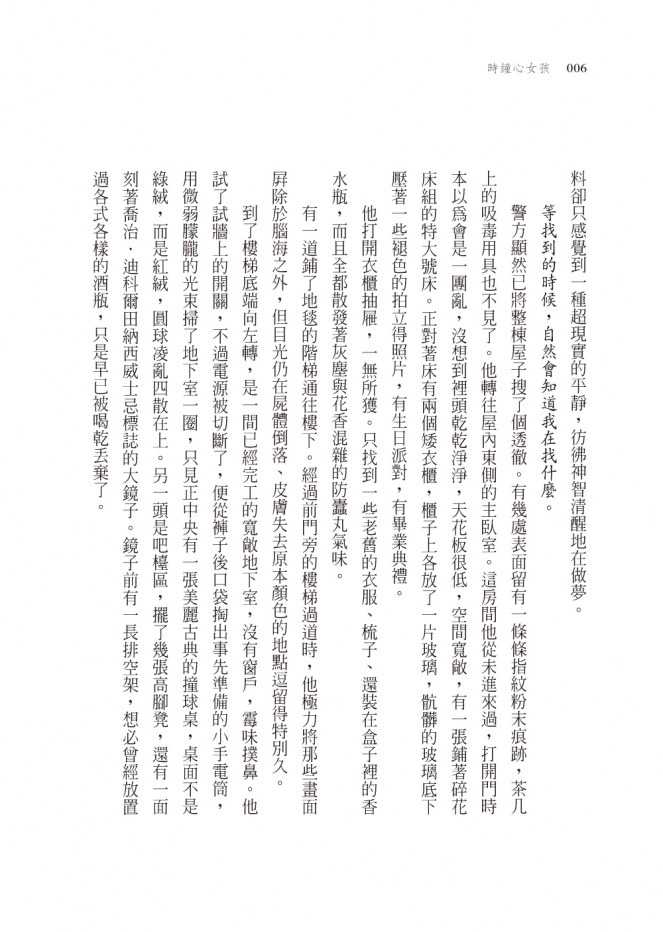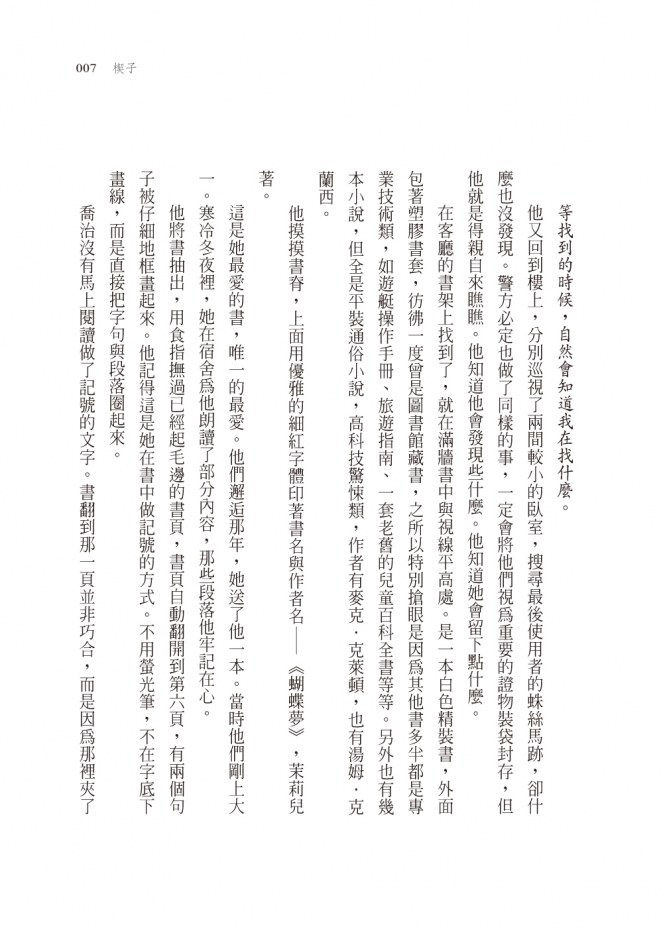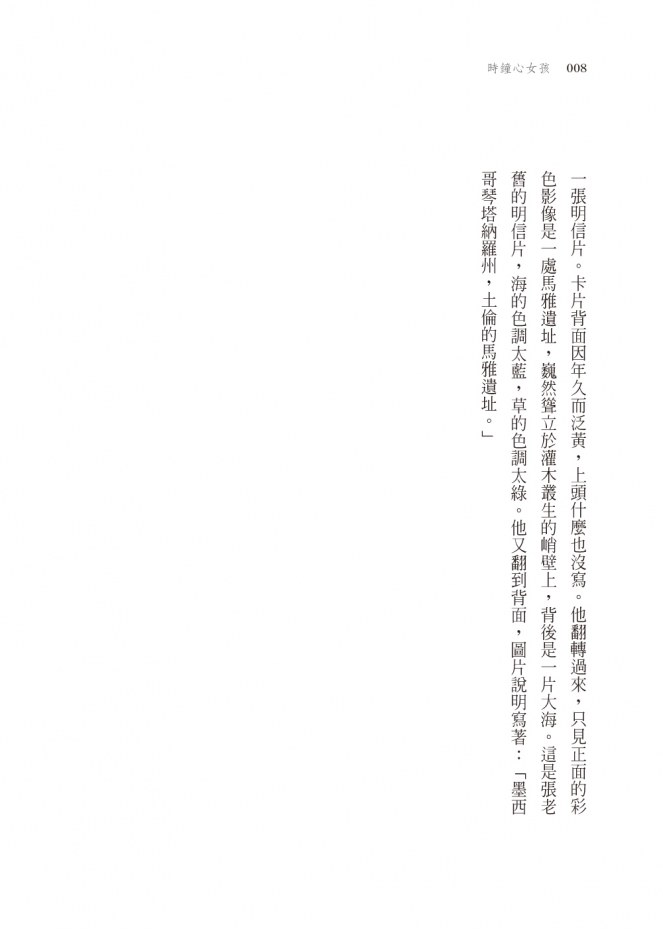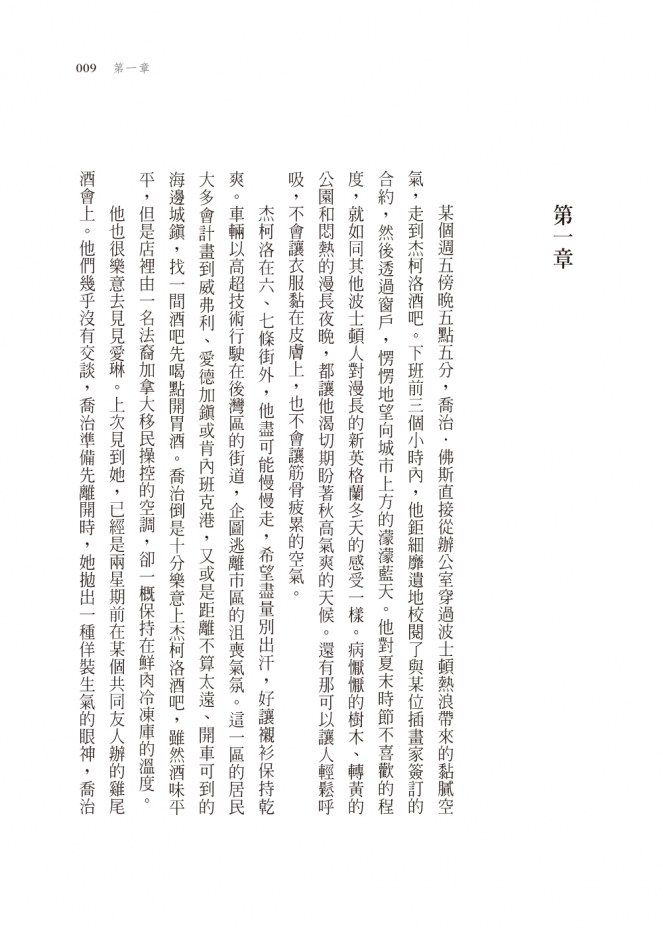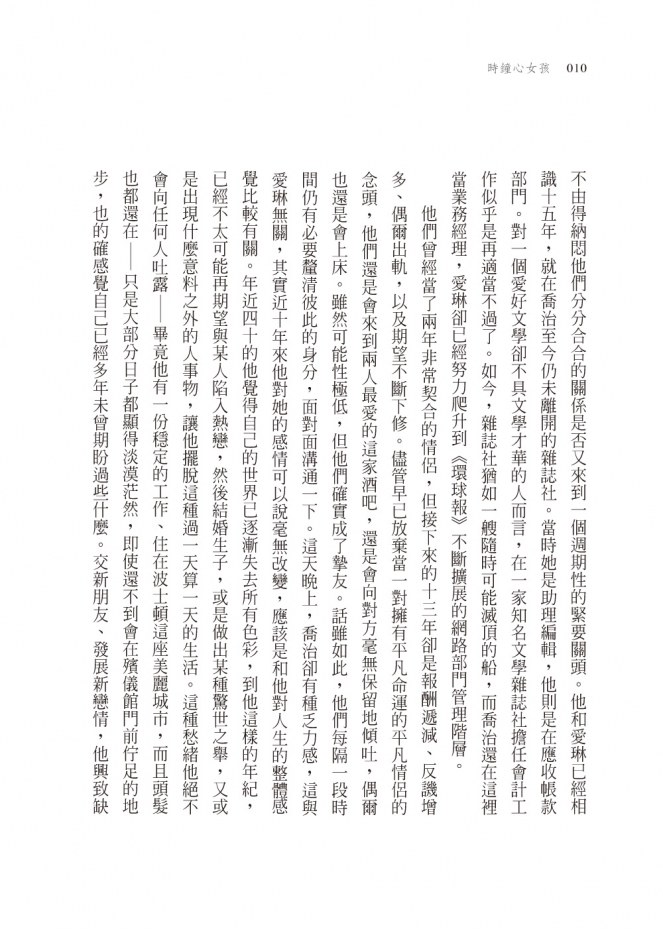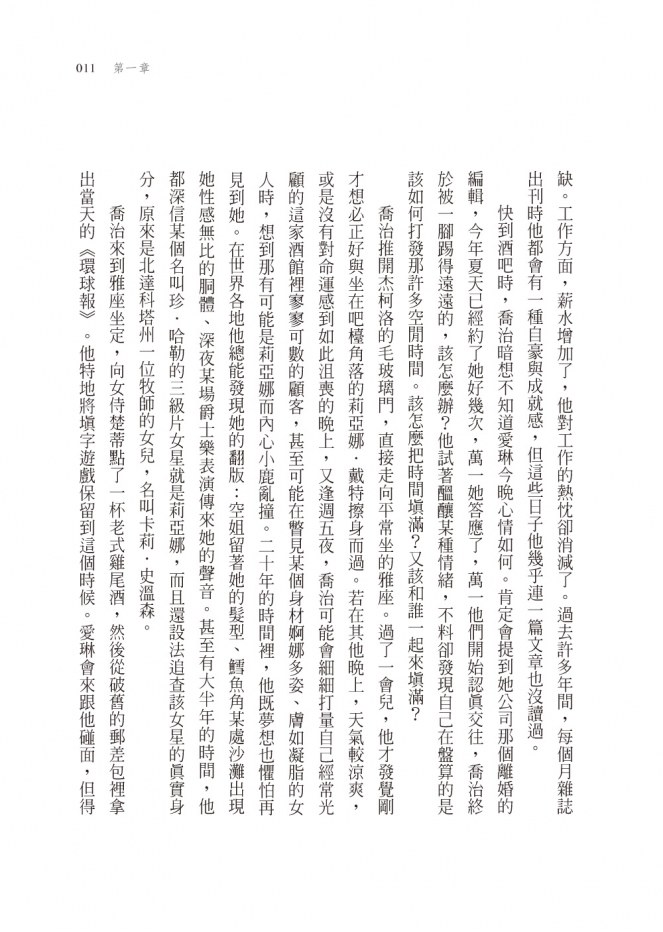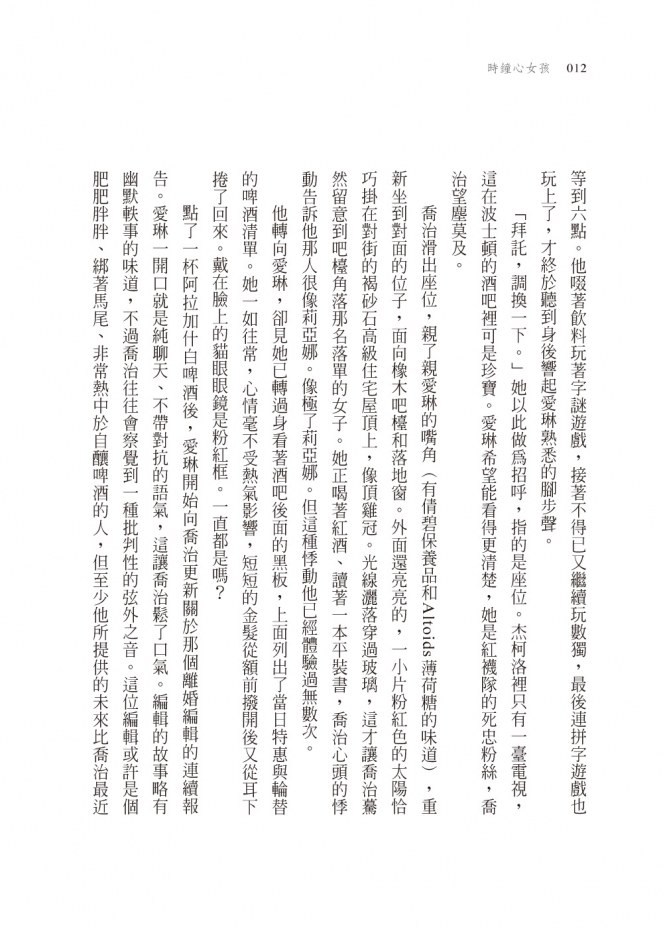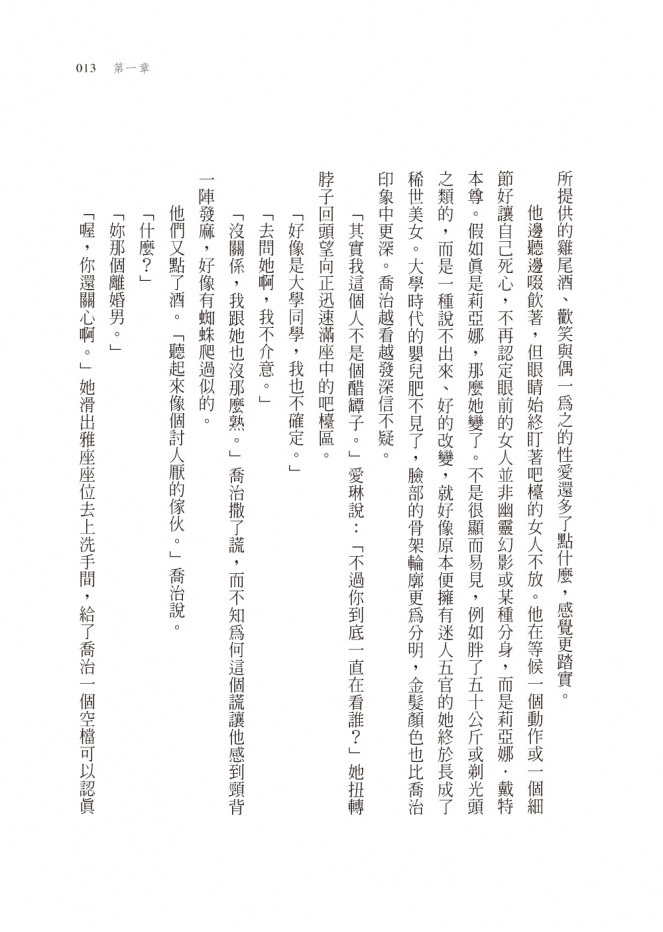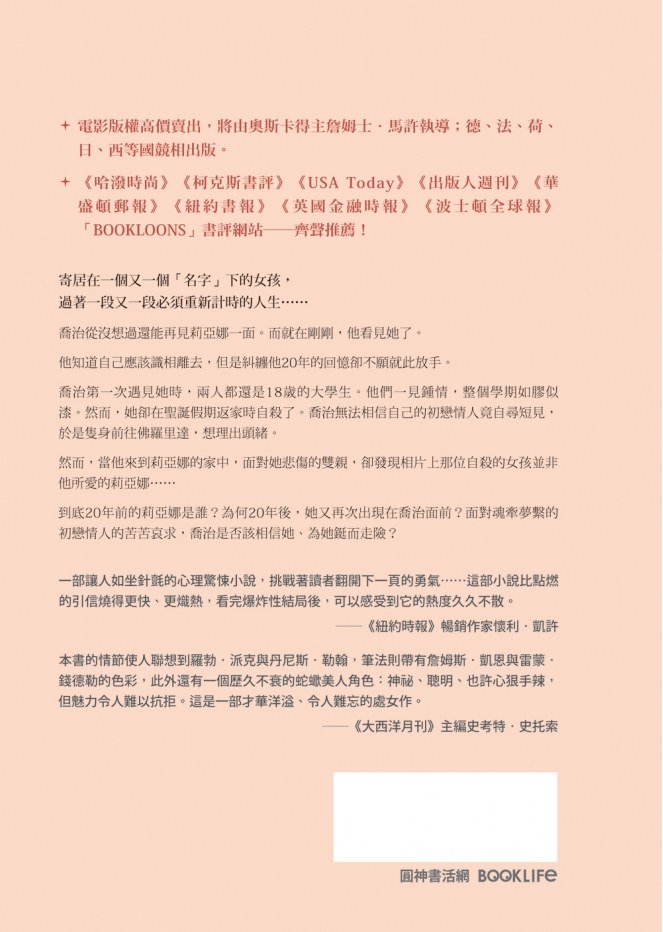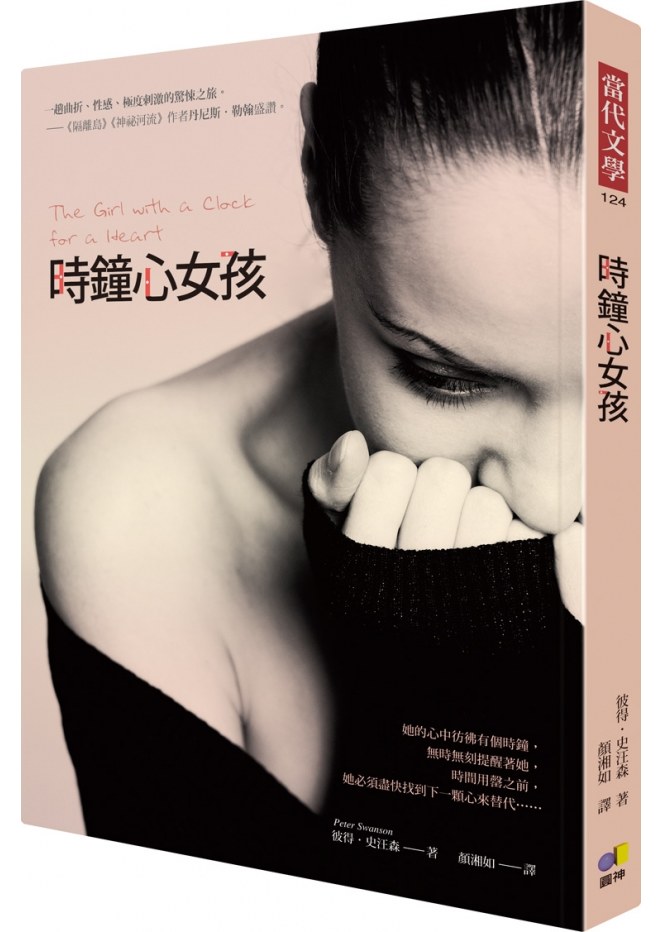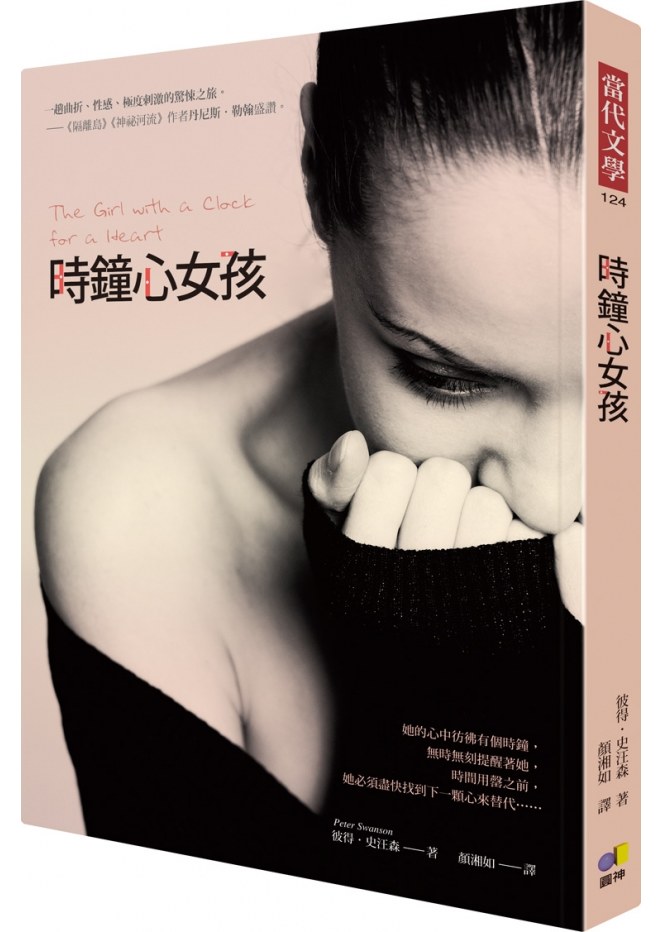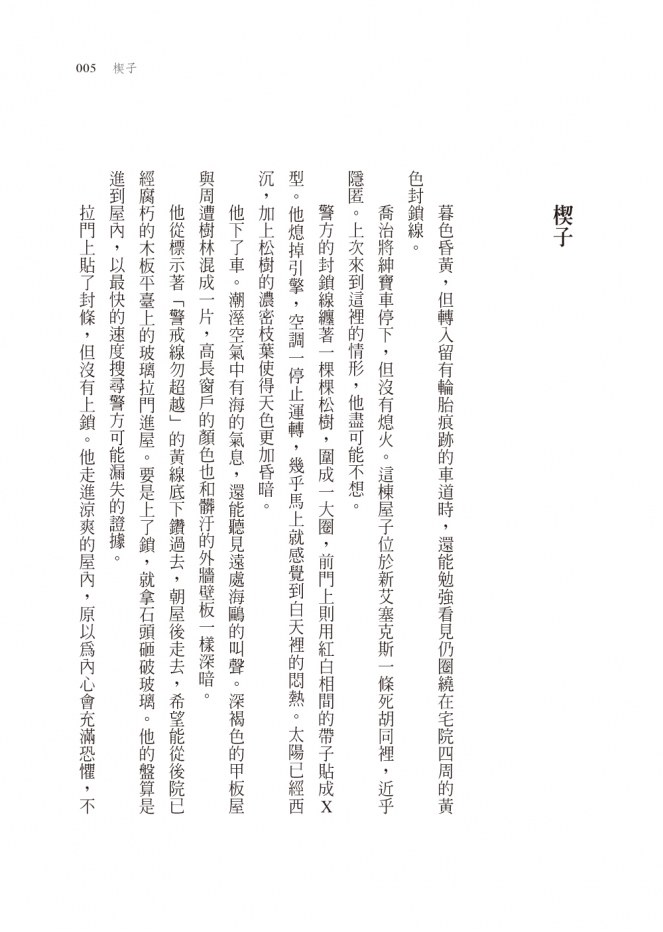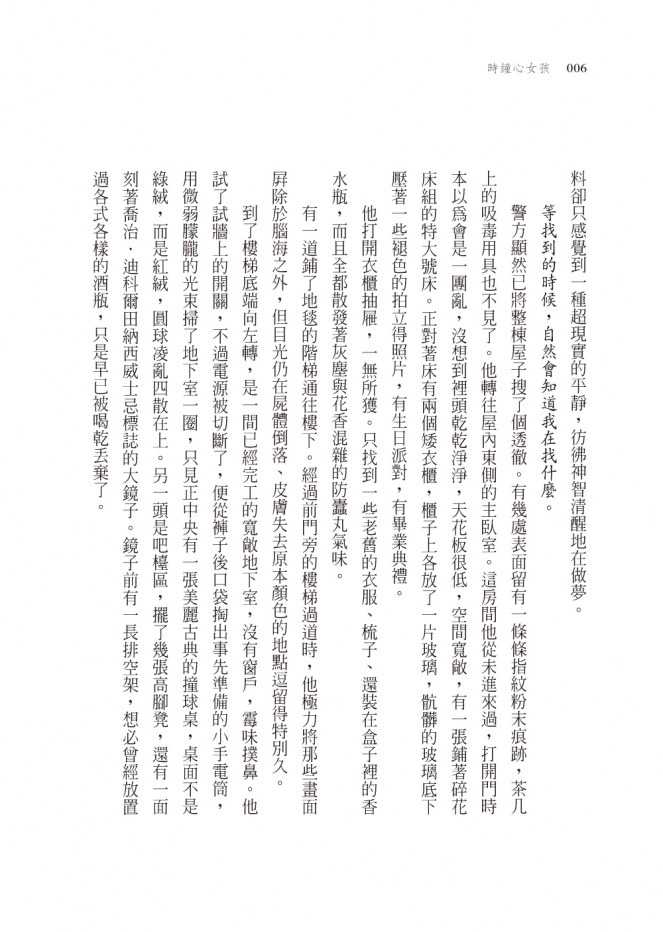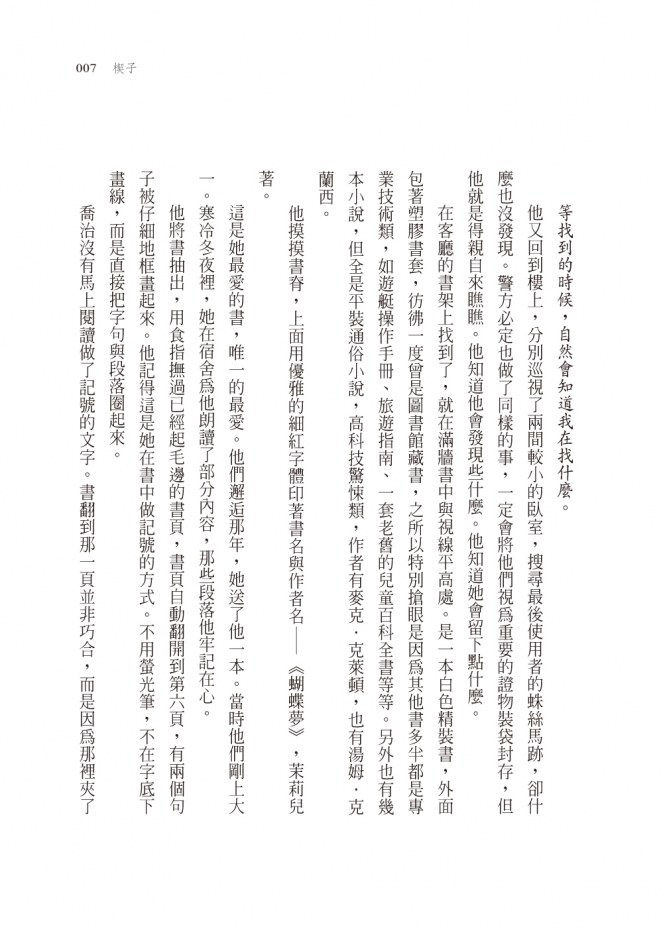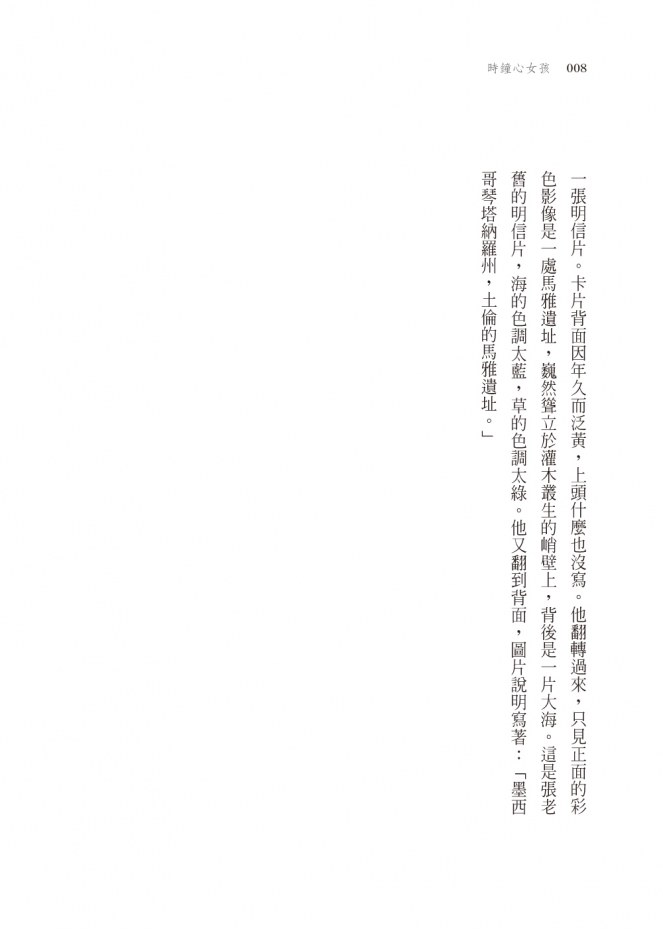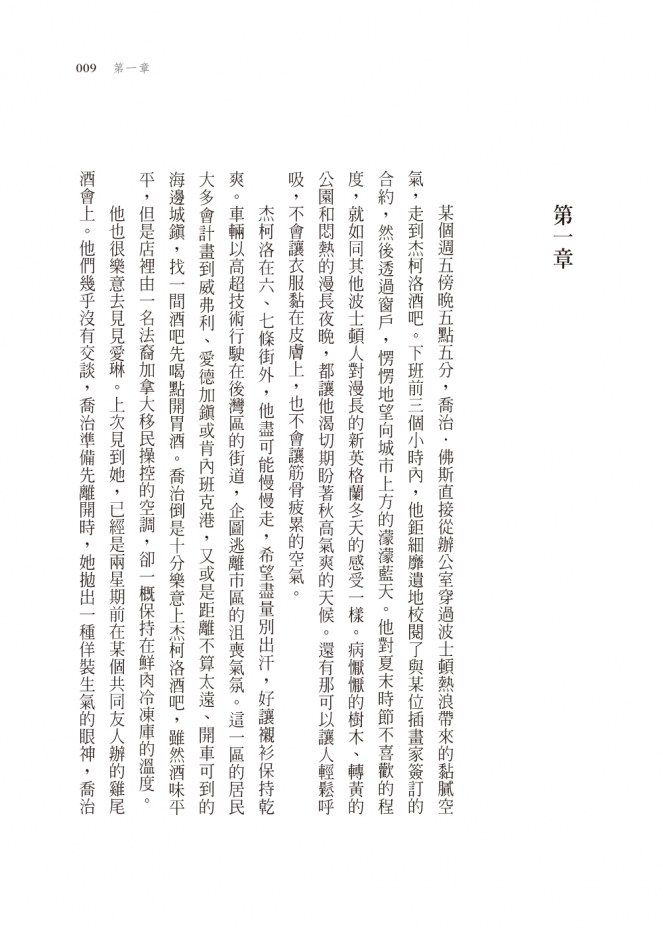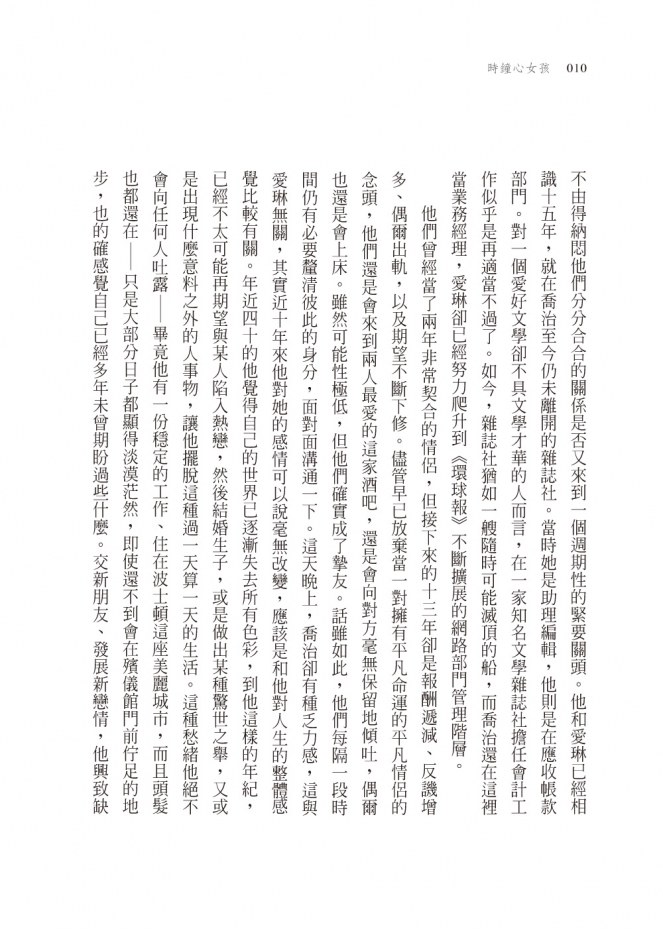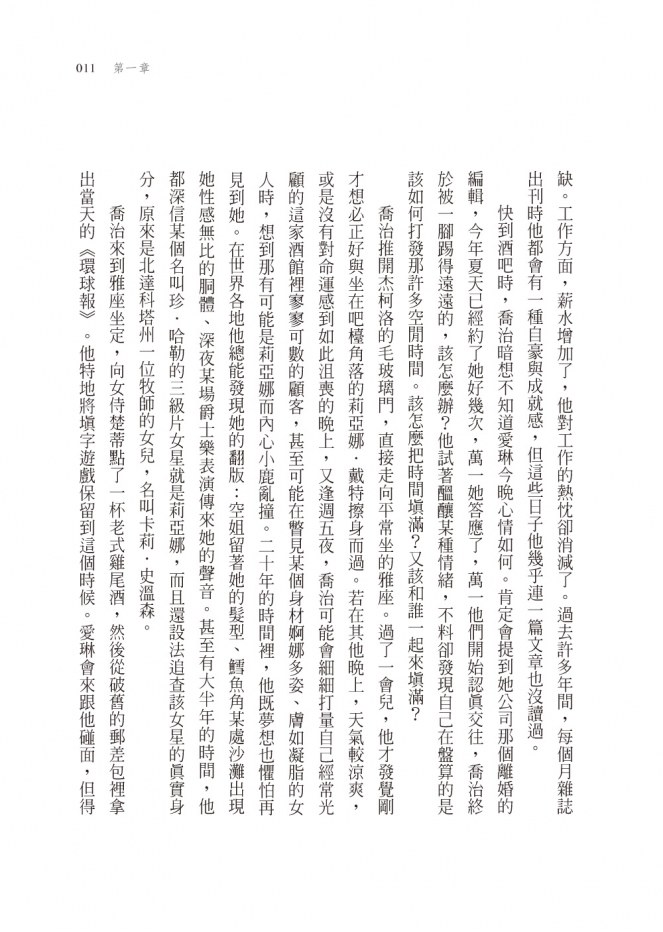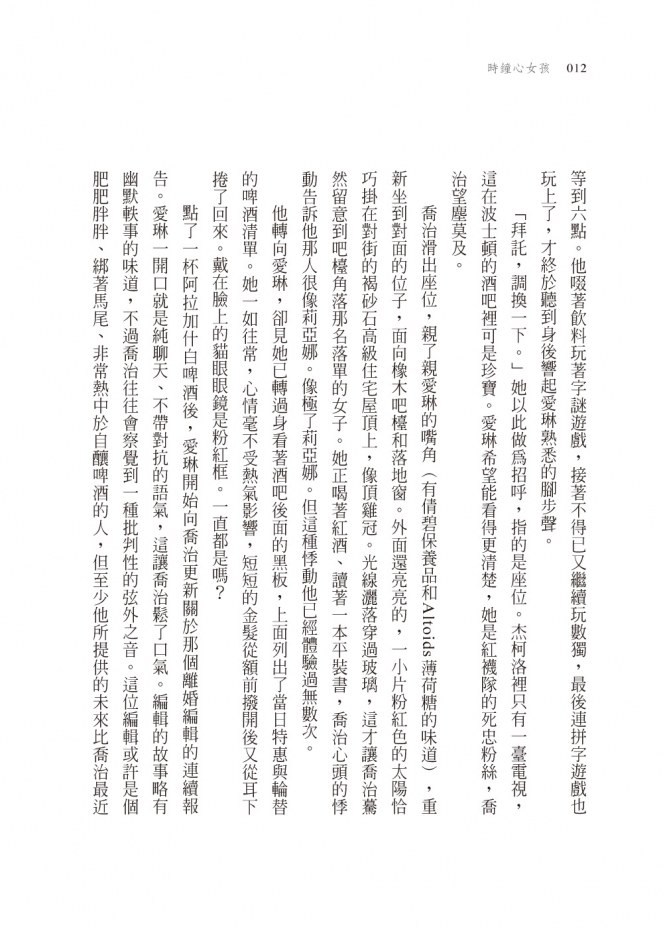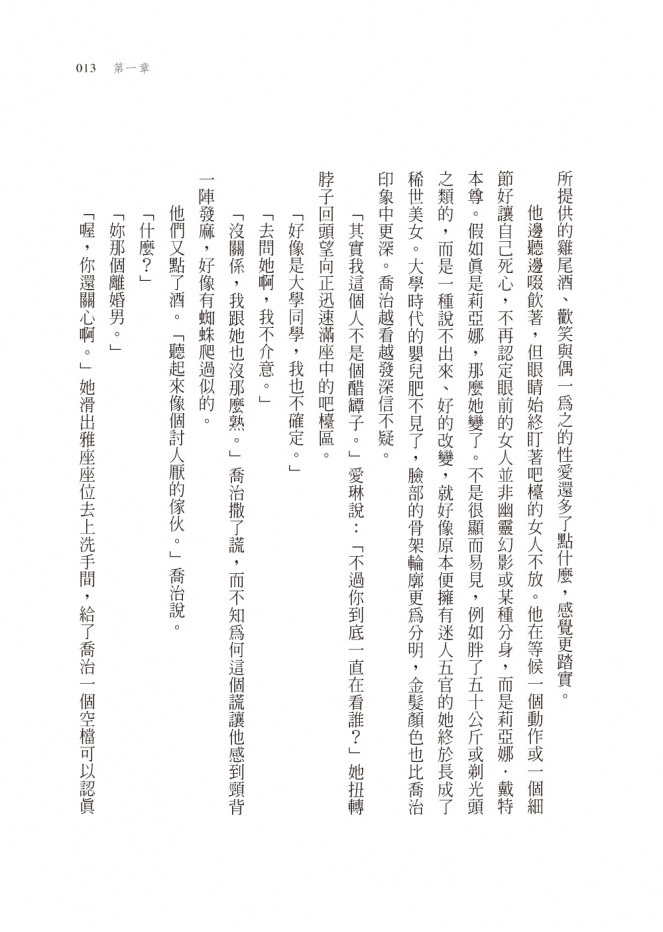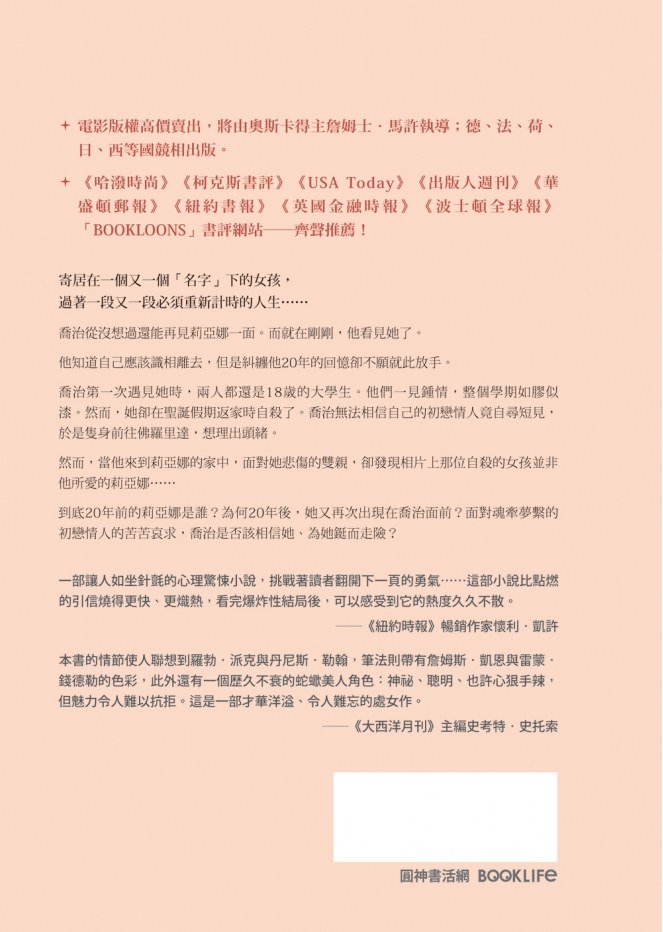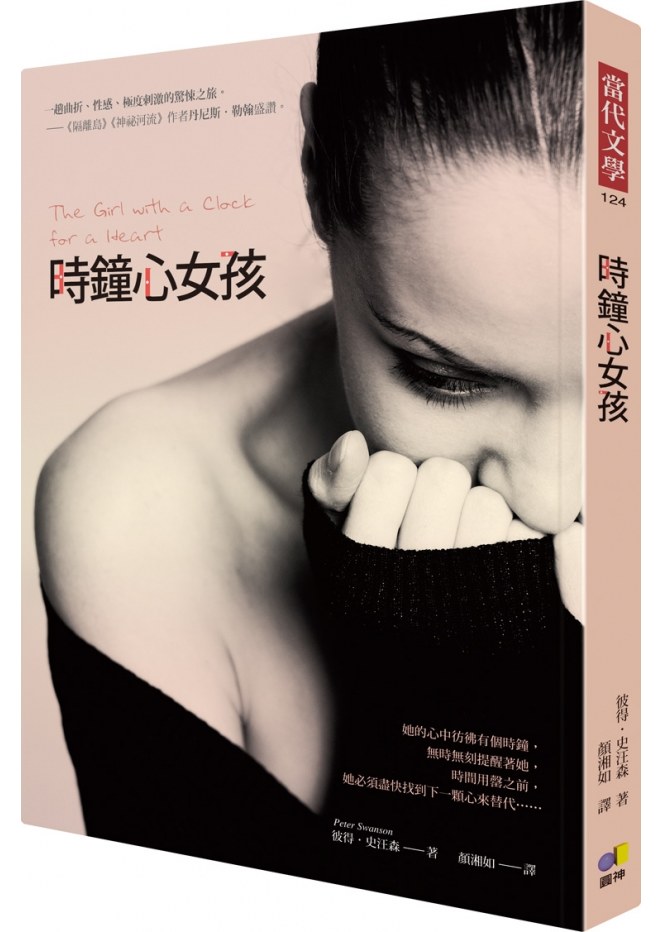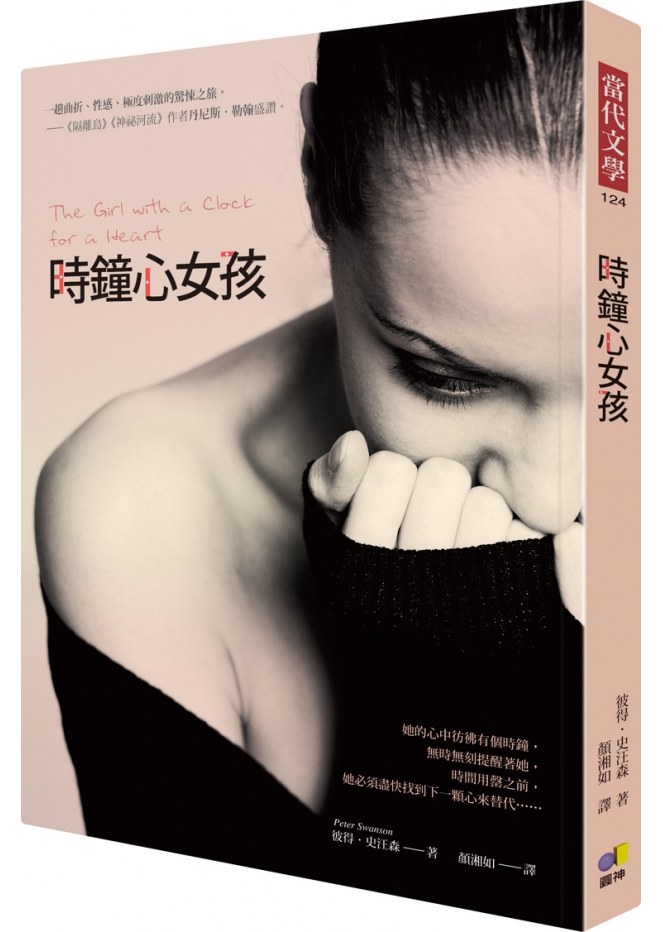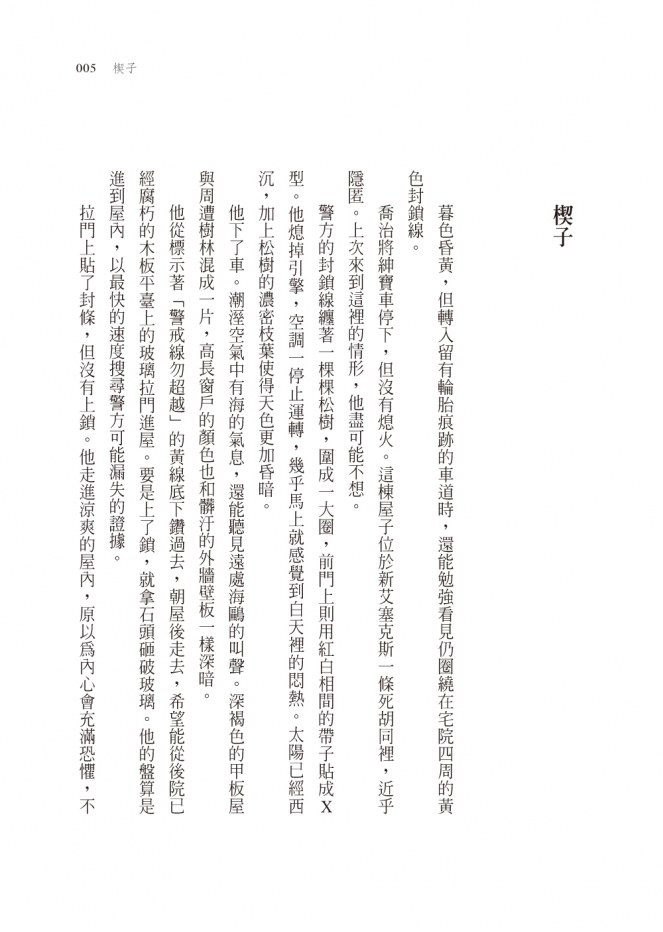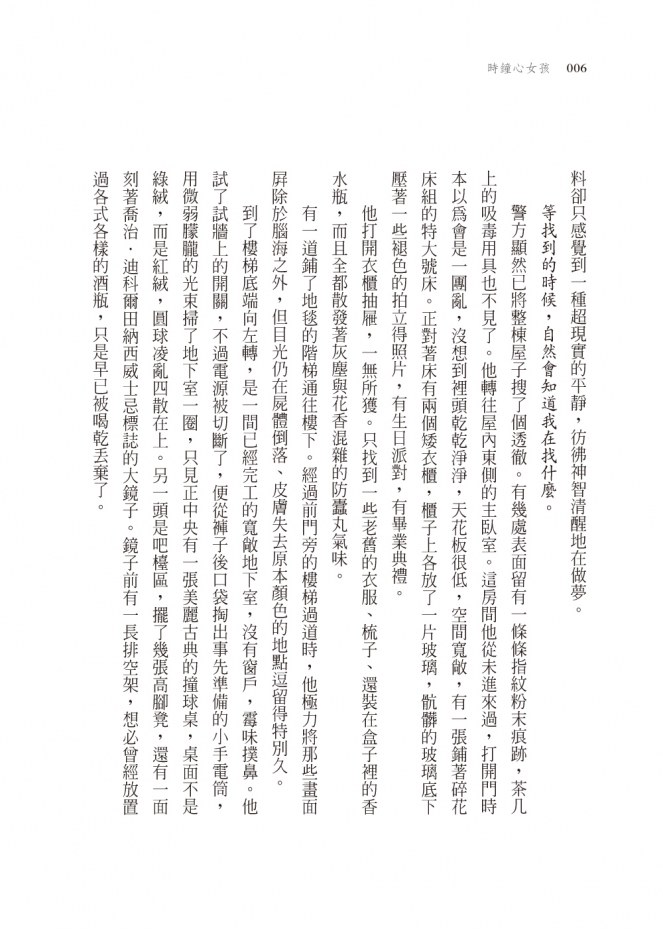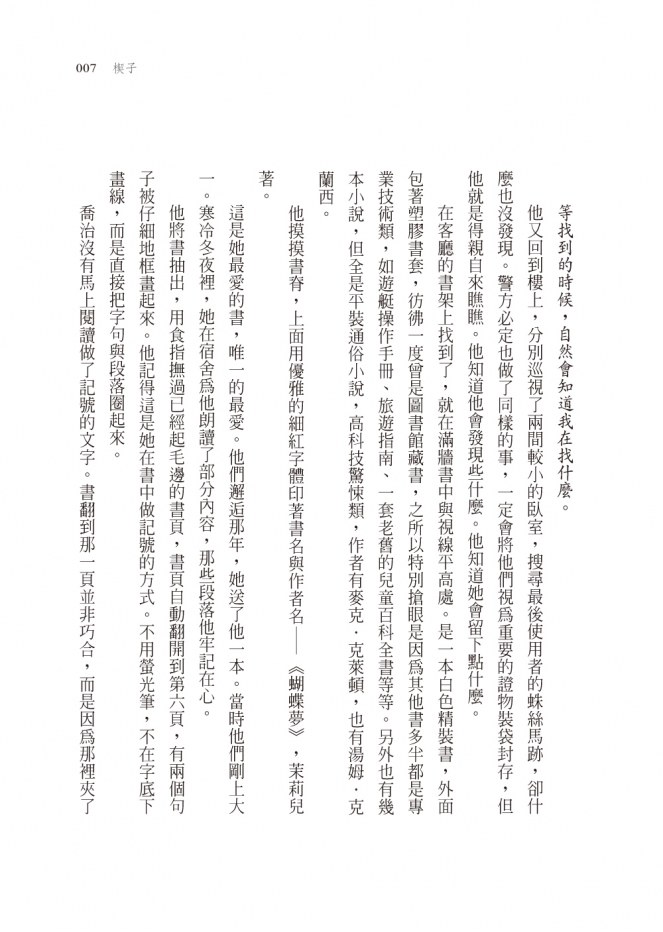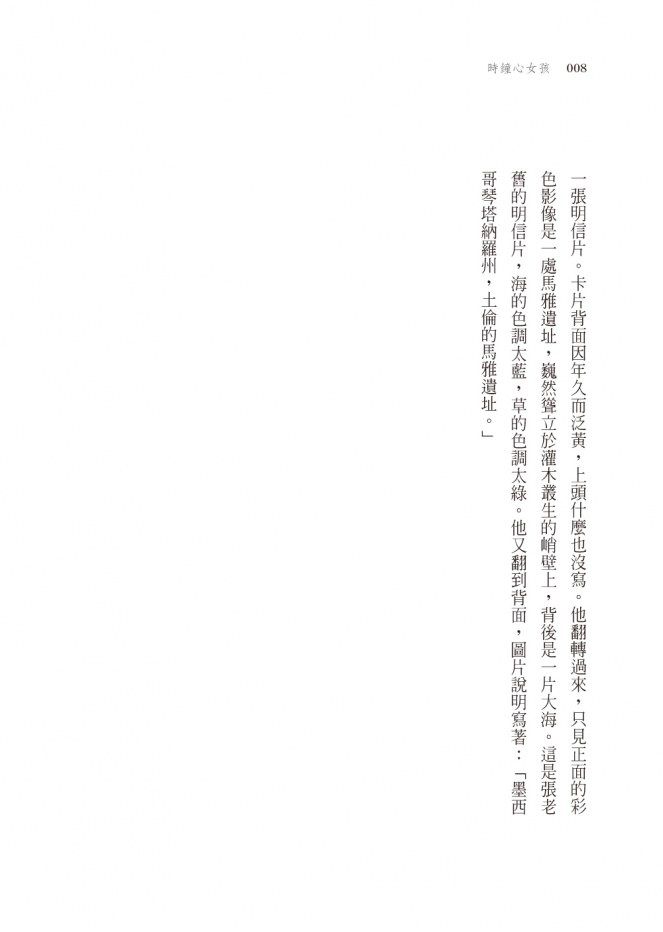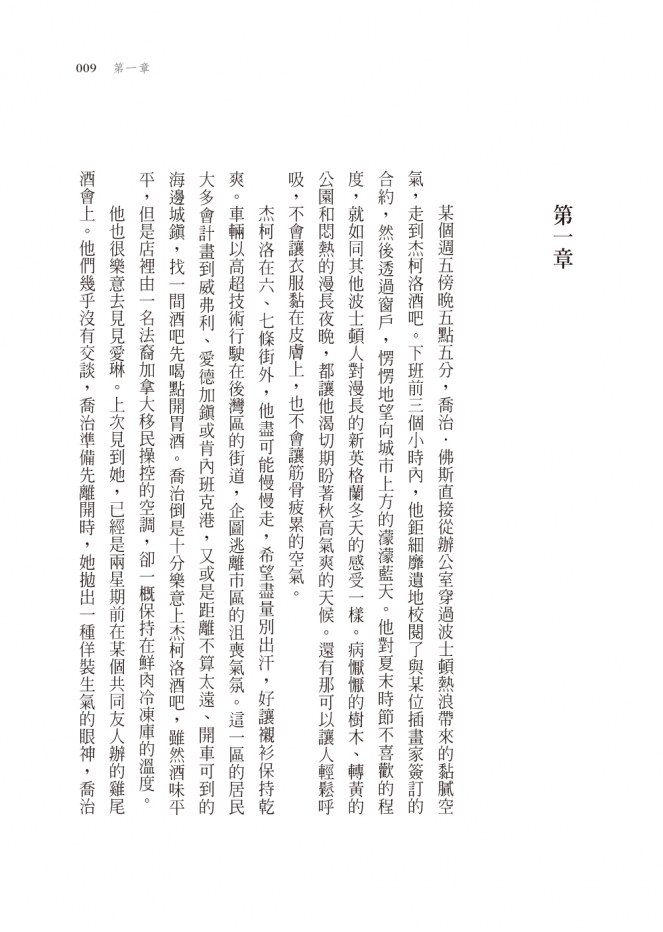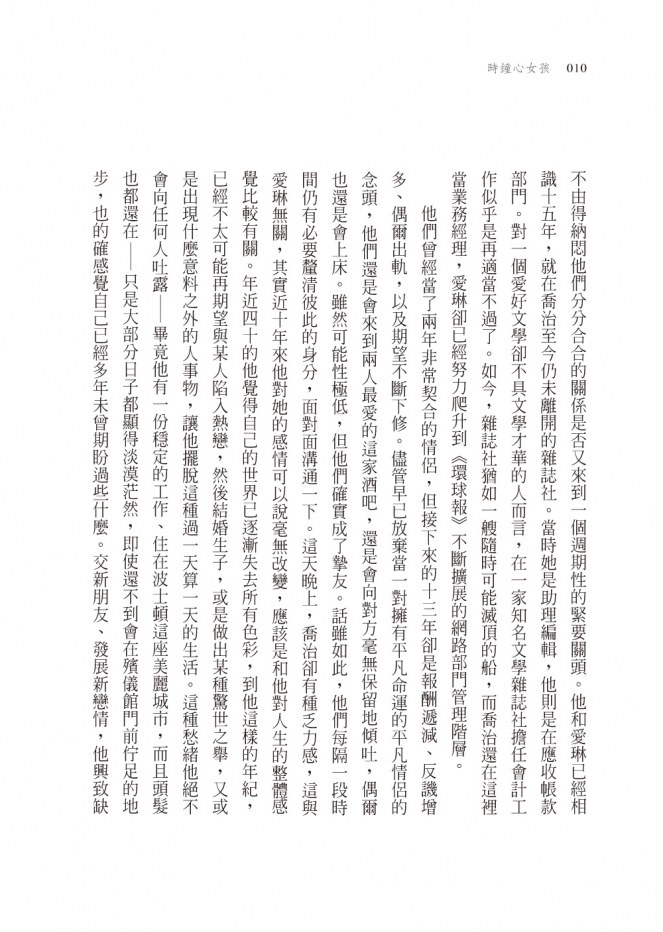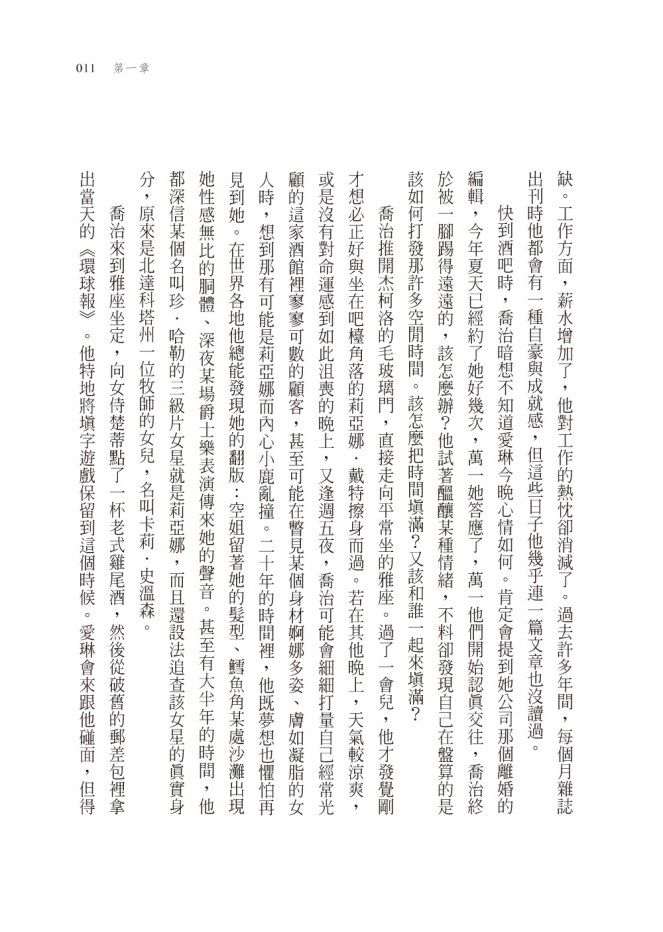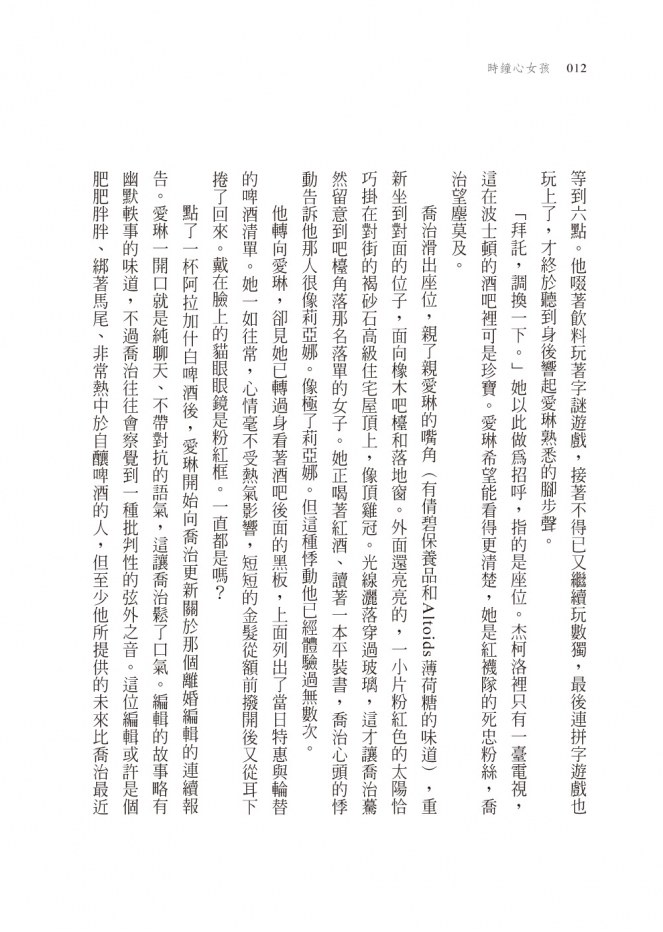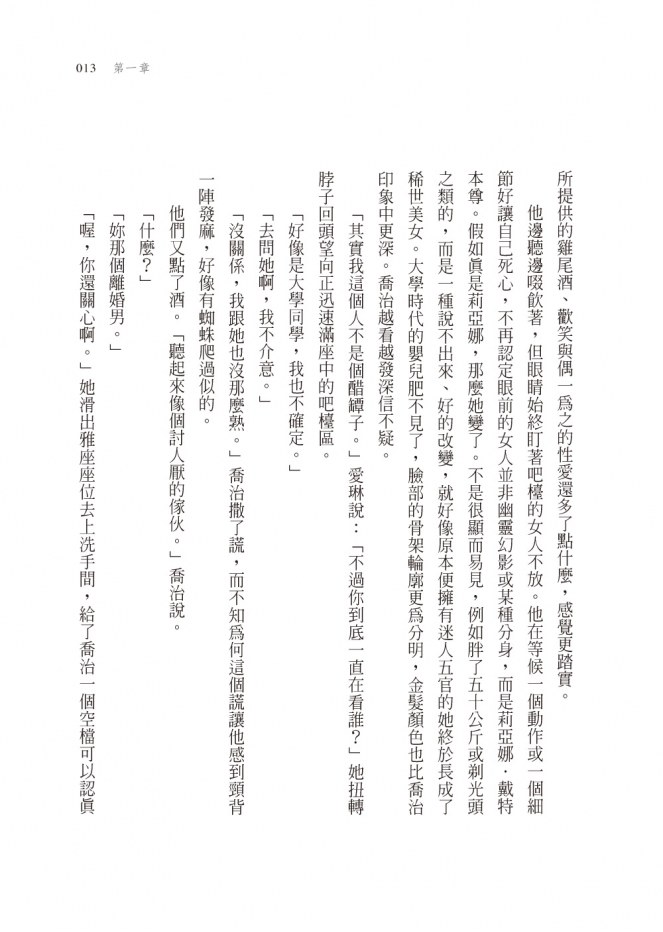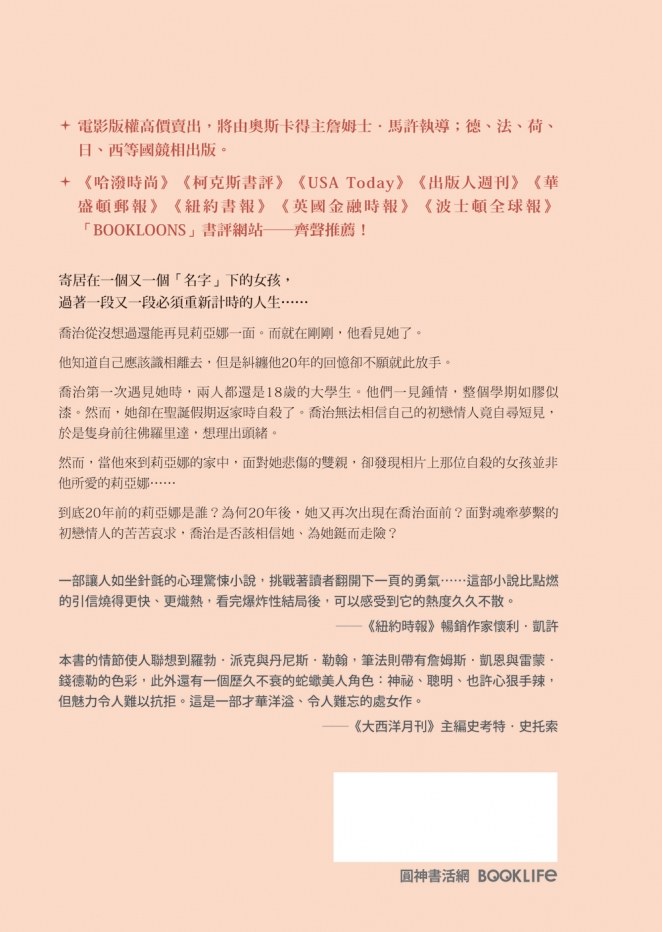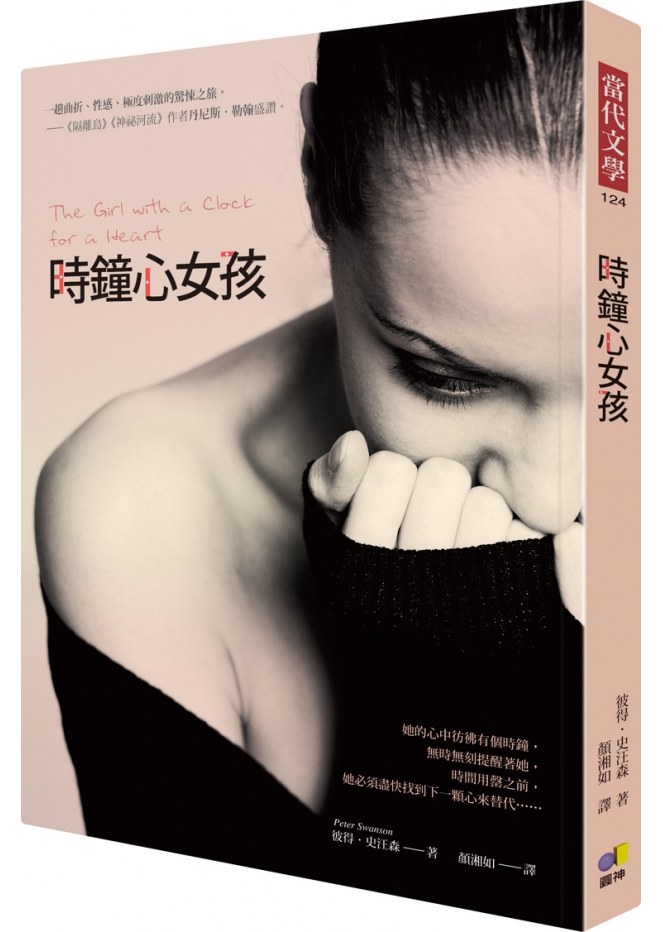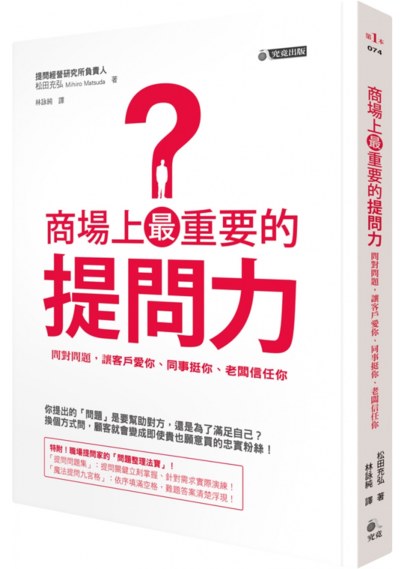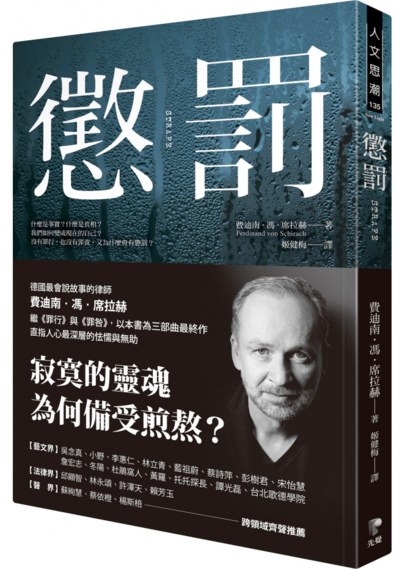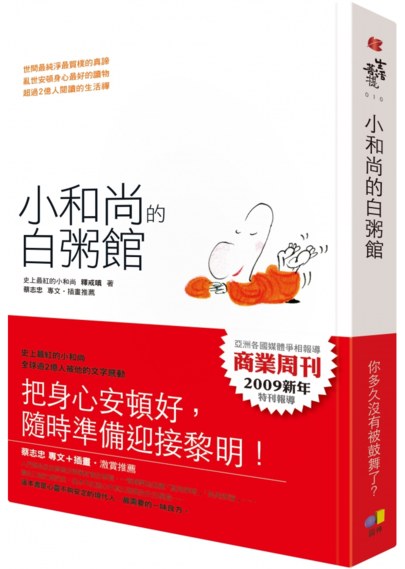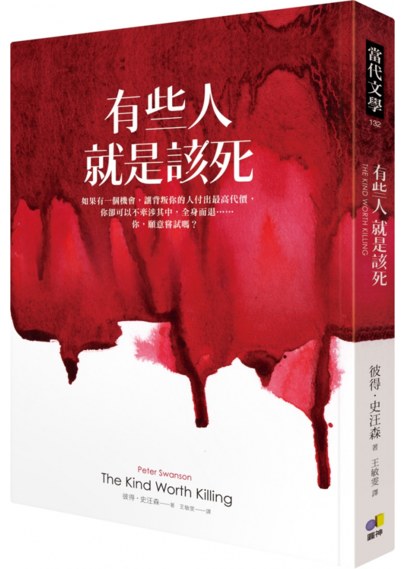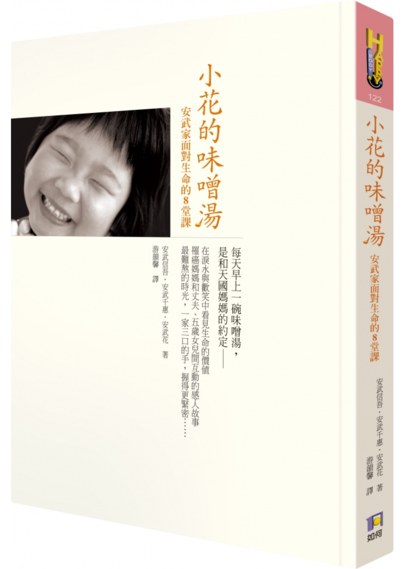楔子
暮色昏黃,但轉入留有輪胎痕跡的車道時,還能勉強看見仍圈繞在宅院四周的黃色封鎖線。
喬治將紳寶車停下,但沒有熄火。這棟屋子位於新艾塞克斯一條死胡同裡,近乎隱匿。上次來到這裡的情形,他盡可能不想。
警方的封鎖線纏著一棵棵松樹,圍成一大圈,前門上則用紅白相間的帶子貼成X型。他熄掉引擎,空調一停止運轉,幾乎馬上就感覺到白天裡的悶熱。太陽已經西沉,加上松樹的濃密枝葉使得天色更加昏暗。
他下了車。潮溼空氣中有海的氣息,還能聽見遠處海鷗的叫聲。深褐色的甲板屋與周遭樹林混成一片,高長窗戶的顏色也和髒汙的外牆壁板一樣深暗。
他從標示著「警戒線勿超越」的黃線底下鑽過去,朝屋後走去,希望能從後院已經腐朽的木板平臺上的玻璃拉門進屋。要是上了鎖,就拿石頭砸破玻璃。他的盤算是進到屋內,以最快的速度搜尋警方可能漏失的證據。
拉門上貼了封條,但沒有上鎖。他走進涼爽的屋內,原以為內心會充滿恐懼,不料卻只感覺到一種超現實的平靜,彷彿神智清醒地在做夢。
等找到的時候,自然會知道我在找什麼。
警方顯然已將整棟屋子搜了個透徹。有幾處表面留有一條條指紋粉末痕跡,茶几上的吸毒用具也不見了。他轉往屋內東側的主臥室。這房間他從未進來過,打開門時本以為會是一團亂,沒想到裡頭乾乾淨淨,天花板很低,空間寬敞,有一張鋪著碎花床組的特大號床。正對著床有兩個矮衣櫃,櫃子上各放了一片玻璃,骯髒的玻璃底下壓著一些褪色的拍立得照片,有生日派對,有畢業典禮。
他打開衣櫃抽屜,一無所獲。只找到一些老舊的衣服、梳子、還裝在盒子裡的香水瓶,而且全都散發著灰塵與花香混雜的防蠹丸氣味。
有一道鋪了地毯的階梯通往樓下。經過前門旁的樓梯過道時,他極力將那些畫面屏除於腦海之外,但目光仍在屍體倒落、皮膚失去原本顏色的地點逗留得特別久。
到了樓梯底端向左轉,是一間已經完工的寬敞地下室,沒有窗戶,霉味撲鼻。他試了試牆上的開關,不過電源被切斷了,便從褲子後口袋掏出事先準備的小手電筒,用微弱朦朧的光束掃了地下室一圈,只見正中央有一張美麗古典的撞球桌,桌面不是綠絨,而是紅絨,圓球凌亂四散在上。另一頭是吧檯區,擺了幾張高腳凳,還有一面刻著喬治.迪科爾田納西威士忌標誌的大鏡子。鏡子前有一長排空架,想必曾經放置過各式各樣的酒瓶,只是早已被喝乾丟棄了。
等找到的時候,自然會知道我在找什麼。
他又回到樓上,分別巡視了兩間較小的臥室,搜尋最後使用者的蛛絲馬跡,卻什麼也沒發現。警方必定也做了同樣的事,一定會將他們視為重要的證物裝袋封存,但他就是得親自來瞧瞧。他知道他會發現些什麼。他知道她會留下點什麼。
在客廳的書架上找到了,就在滿牆書中與視線平高處。是一本白色精裝書,外面包著塑膠書套,彷彿一度曾是圖書館藏書,之所以特別搶眼是因為其他書多半都是專業技術類,如遊艇操作手冊、旅遊指南、一套老舊的兒童百科全書等等。另外也有幾本小說,但全是平裝通俗小說,高科技驚悚類,作者有麥克.克萊頓,也有湯姆.克蘭西。
他摸摸書脊,上面用優雅的細紅字體印著書名與作者名—《蝴蝶夢》,茉莉兒著。
這是她最愛的書,唯一的最愛。他們邂逅那年,她送了他一本。當時他們剛上大一。寒冷冬夜裡,她在宿舍為他朗讀了部分內容,那些段落他牢記在心。
他將書抽出,用食指撫過已經起毛邊的書頁,書頁自動翻開到第六頁,有兩個句子被仔細地框畫起來。他記得這是她在書中做記號的方式。不用螢光筆,不在字底下畫線,而是直接把字句與段落圈起來。
喬治沒有馬上閱讀做了記號的文字。書翻到那一頁並非巧合,而是因為那裡夾了一張明信片。卡片背面因年久而泛黃,上頭什麼也沒寫。他翻轉過來,只見正面的彩色影像是一處馬雅遺址,巍然聳立於灌木叢生的峭壁上,背後是一片大海。這是張老舊的明信片,海的色調太藍,草的色調太綠。他又翻到背面,圖片說明寫著:「墨西哥琴塔納羅州,土倫的馬雅遺址。」
第一章
某個週五傍晚五點五分,喬治.佛斯直接從辦公室穿過波士頓熱浪帶來的黏膩空氣,走到杰柯洛酒吧。下班前三個小時內,他鉅細靡遺地校閱了與某位插畫家簽訂的合約,然後透過窗戶,愣愣地望向城市上方的濛濛藍天。他對夏末時節不喜歡的程度,就如同其他波士頓人對漫長的新英格蘭冬天的感受一樣。病懨懨的樹木、轉黃的公園和悶熱的漫長夜晚,都讓他渴切期盼著秋高氣爽的天候。還有那可以讓人輕鬆呼吸,不會讓衣服黏在皮膚上,也不會讓筋骨疲累的空氣。
杰柯洛在六、七條街外,他盡可能慢慢走,希望盡量別出汗,好讓襯衫保持乾爽。車輛以高超技術行駛在後灣區的街道,企圖逃離市區的沮喪氣氛。這一區的居民大多會計畫到威弗利、愛德加鎮或肯內班克港,又或是距離不算太遠、開車可到的海邊城鎮,找一間酒吧先喝點開胃酒。喬治倒是十分樂意上杰柯洛酒吧,雖然酒味平平,但是店裡由一名法裔加拿大移民操控的空調,卻一概保持在鮮肉冷凍庫的溫度。
他也很樂意去見見愛琳。上次見到她,已經是兩星期前在某個共同友人辦的雞尾酒會上。他們幾乎沒有交談,喬治準備先離開時,她拋出一種佯裝生氣的眼神,喬治不由得納悶他們分分合合的關係是否又來到一個週期性的緊要關頭。他和愛琳已經相識十五年,就在喬治至今仍未離開的雜誌社。當時她是助理編輯,他則是在應收帳款部門。對一個愛好文學卻不具文學才華的人而言,在一家知名文學雜誌社擔任會計工作似乎是再適當不過了。如今,雜誌社猶如一艘隨時可能滅頂的船,而喬治還在這裡當業務經理,愛琳卻已經努力爬升到《環球報》不斷擴展的網路部門管理階層。
他們曾經當了兩年非常契合的情侶,但接下來的十三年卻是報酬遞減、反譏增多、偶爾出軌,以及期望不斷下修。儘管早已放棄當一對擁有平凡命運的平凡情侶的念頭,他們還是會來到兩人最愛的這家酒吧,還是會向對方毫無保留地傾吐,偶爾也還是會上床。雖然可能性極低,但他們確實成了摯友。話雖如此,他們每隔一段時間仍有必要釐清彼此的身分,面對面溝通一下。這天晚上,喬治卻有種乏力感,這與愛琳無關,其實近十年來他對她的感情可以說毫無改變,應該是和他對人生的整體感覺比較有關。年近四十的他覺得自己的世界已逐漸失去所有色彩,到他這樣的年紀,已經不太可能再期望與某人陷入熱戀,然後結婚生子,或是做出某種驚世之舉,又或是出現什麼意料之外的人事物,讓他擺脫這種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這種愁緒他絕不會向任何人吐露—畢竟他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住在波士頓這座美麗城市,而且頭髮也都還在—只是大部分日子都顯得淡漠茫然,即使還不到會在殯儀館門前佇足的地步,也的確感覺自己已經多年未曾期盼過些什麼。交新朋友、發展新戀情,他興致缺缺。工作方面,薪水增加了,他對工作的熱忱卻消減了。過去許多年間,每個月雜誌出刊時他都會有一種自豪與成就感,但這些日子他幾乎連一篇文章也沒讀過。
快到酒吧時,喬治暗想不知道愛琳今晚心情如何。肯定會提到她公司那個離婚的編輯,今年夏天已經約了她好幾次,萬一她答應了,萬一他們開始認真交往,喬治終於被一腳踢得遠遠的,該怎麼辦?他試著醞釀某種情緒,不料卻發現自己在盤算的是該如何打發那許多空閒時間。該怎麼把時間填滿?又該和誰一起來填滿?
喬治推開杰柯洛的毛玻璃門,直接走向平常坐的雅座。過了一會兒,他才發覺剛才想必正好與坐在吧檯角落的莉亞娜.戴特擦身而過。若在其他晚上,天氣較涼爽,或是沒有對命運感到如此沮喪的晚上,又逢週五夜,喬治可能會細細打量自己經常光顧的這家酒館裡寥寥可數的顧客,甚至可能在瞥見某個身材婀娜多姿、膚如凝脂的女人時,想到那有可能是莉亞娜而內心小鹿亂撞。二十年的時間裡,他既夢想也懼怕再見到她。在世界各地他總能發現她的翻版:空姐留著她的髮型、鱈魚角某處沙灘出現她性感無比的胴體、深夜某場爵士樂表演傳來她的聲音。甚至有大半年的時間,他都深信某個名叫珍.哈勒的三級片女星就是莉亞娜,而且還設法追查該女星的真實身分,原來是北達科塔州一位牧師的女兒,名叫卡莉.史溫森。
喬治來到雅座坐定,向女侍楚蒂點了一杯老式雞尾酒,然後從破舊的郵差包裡拿出當天的《環球報》。他特地將填字遊戲保留到這個時候。愛琳會來跟他碰面,但得等到六點。他啜著飲料玩著字謎遊戲,接著不得已又繼續玩數獨,最後連拼字遊戲也玩上了,才終於聽到身後響起愛琳熟悉的腳步聲。
「拜託,調換一下。」她以此做為招呼,指的是座位。杰柯洛裡只有一臺電視,這在波士頓的酒吧裡可是珍寶。愛琳希望能看得更清楚,她是紅襪隊的死忠粉絲,喬治望塵莫及。
喬治滑出座位,親了親愛琳的嘴角(有倩碧保養品和 Altoids 薄荷糖的味道),重新坐到對面的位子,面向橡木吧檯和落地窗。外面還亮亮的,一小片粉紅色的太陽恰巧掛在對街的褐砂石高級住宅屋頂上,像頂雞冠。光線灑落穿過玻璃,這才讓喬治驀然留意到吧檯角落那名落單的女子。她正喝著紅酒、讀著一本平裝書,喬治心頭的悸動告訴他那人很像莉亞娜。像極了莉亞娜。但這種悸動他已經體驗過無數次。
他轉向愛琳,卻見她已轉過身看著酒吧後面的黑板,上面列出了當日特惠與輪替的啤酒清單。她一如往常,心情毫不受熱氣影響,短短的金髮從額前撥開後又從耳下捲了回來。戴在臉上的貓眼眼鏡是粉紅框。一直都是嗎?
點了一杯阿拉加什白啤酒後,愛琳開始向喬治更新關於那個離婚編輯的連續報告。愛琳一開口就是純聊天、不帶對抗的語氣,這讓喬治鬆了口氣。編輯的故事略有幽默軼事的味道,不過喬治往往會察覺到一種批判性的弦外之音。這位編輯或許是個肥肥胖胖、綁著馬尾、非常熱中於自釀啤酒的人,但至少他所提供的未來比喬治最近所提供的雞尾酒、歡笑與偶一為之的性愛還多了點什麼,感覺更踏實。
他邊聽邊啜飲著,但眼睛始終盯著吧檯的女人不放。他在等候一個動作或一個細節好讓自己死心,不再認定眼前的女人並非幽靈幻影或某種分身,而是莉亞娜.戴特本尊。假如真是莉亞娜,那麼她變了。不是很顯而易見,例如胖了五十公斤或剃光頭之類的,而是一種說不出來、好的改變,就好像原本便擁有迷人五官的她終於長成了稀世美女。大學時代的嬰兒肥不見了,臉部的骨架輪廓更為分明,金髮顏色也比喬治印象中更深。喬治越看越發深信不疑。
「其實我這個人不是個醋罈子。」愛琳說:「不過你到底一直在看誰?」她扭轉脖子回頭望向正迅速滿座中的吧檯區。
「好像是大學同學,我也不確定。」
「去問她啊,我不介意。」
「沒關係,我跟她也沒那麼熟。」喬治撒了謊,而不知為何這個謊讓他感到頸背一陣發麻,好像有蜘蛛爬過似的。
他們又點了酒。「聽起來像個討人厭的傢伙。」喬治說。
「什麼?」
「妳那個離婚男。」
「喔,你還關心啊。」她滑出雅座座位去上洗手間,給了喬治一個空檔可以認真直視遠在另一頭的莉亞娜。有一對正在脫下夾克、拉鬆領帶的年輕生意人已經將她半遮住,但他還是利用他們動作的空隙端詳她。她穿了一件有領子的白襯衫,頭髮比大學時代短一些,一邊披散在臉頰上,另一邊塞在耳後。沒有戴首飾,這卻是喬治對她保有的印象之一。她的頸項呈現一種令人想入非非的乳白色,胸骨處也閃現一抹斑駁殷紅。此時她已將書放下,偶爾往酒吧四下張望,像在找人。喬治等著她起身移動,總覺得在看到她走路的姿勢前無法確定。
彷彿與他有了心電感應一般,她滑下軟墊高腳凳,有一瞬間裙子全皺擠在大腿高處。當她雙腳一著地,起步朝喬治這邊走來,便再無疑問了。肯定是莉亞娜沒錯,打從進梅瑟大學第一年第一次見到她,至今已將近二十年。她走起路來臀部會緩緩地左搖右擺,頭昂揚著並往後仰,好像要越過某人的頭看什麼東西,所以絕對錯不了。喬治拿起菜單遮住臉,瞪著裡頭一堆毫無意義的字,胸腔裡心怦怦跳著。雖有冷氣,還是感覺手心開始冒汗。
莉亞娜從旁經過時,愛琳剛好滑坐回位子上。「是你的朋友耶,不想打個招呼嗎?」
「我還不確定是她。」喬治回答,不知道愛琳有沒有聽出他聲音中的生硬驚慌。
「有沒有時間再喝一杯?」愛琳問道,她已在洗手間裡補了口紅。
「當然有。」喬治說:「不過換個地方吧。趁天還沒全暗,可以散散步。」
愛琳向服務生招手時,喬治也準備掏出皮夾。「換我請了,記得吧。」愛琳說著從她那深不可測的皮包裡拿出一張信用卡。她付帳時,莉亞娜又再度走過。這回喬治可以凝視她的背影,那熟悉的走路姿態,發現她的身材也發育得更好了。喬治以為大學時代的她已經很完美,但認真說起來,現在的她更美:修長勻稱的雙腿加上異常玲瓏有致的曲線,這種身材只可能是與生俱來,靠運動也練不出來。她兩隻手臂內側膚如凝脂。
喬治曾無數次想像過這一刻,卻始終想像不到會有什麼結果。莉亞娜不只是很久以前令喬治心碎過的前女友,據喬治目前所知,她還是個通緝犯,這女人所犯的罪過與其說是少不更事的衝動,倒更像是希臘悲劇之類的罪行。她無疑已經殺害一人,而且很可能又殺了另一人。喬治感受到道德感與猶豫不決以同樣沉重的壓力壓在自己心上。
「走吧?」愛琳站起來,喬治也跟著起身,隨著她腳跟先著地的輕快步伐走過酒吧裡上了漆的木質地板。揚聲喇叭傳出妮娜.西蒙的〈罪人〉那急促而連續的節奏聲響。當他們大步邁出前門,依然悶熱的傍晚立刻以一堵沉滯、燠熱又潮溼的空氣牆迎接他們。
「再來要去哪?」愛琳問道。
喬治呆住了。「不知道,我好像只想回家。」
「好吧。」愛琳說,見喬治未動便又補上一句:「或者我們也可以就站在外頭這個雨林裡。」
「對不起,我忽然覺得不太舒服,我想我還是回家吧。」
「是因為酒吧那個女人嗎?」愛琳彎轉脖子回頭凝視前門的毛玻璃。「她該不會是那個叫什麼名字來著?就是梅瑟那個瘋女孩。」
「拜託,不是啦。」喬治撒謊。「我想今晚就到此為止吧。」
喬治步行回家。這時吹起一陣微風,在煙墩山的狹窄街道間颼颼響著。風不涼,但喬治還是敞開雙臂,可以感覺汗水從皮膚上蒸發。
回到公寓大樓前,喬治往門外階梯的第一階坐下來。只要穿過幾條街就能再回酒吧。可以去找她喝一杯,問問她為什麼回波士頓。他為了想見她等了那麼久,一再想像著這一刻,如今人真的出現了,他卻自覺有如恐怖電影裡的演員,手搭在穀倉門上,斧頭眼看就要劈頭砍下。他心裡害怕,近十年來這是他頭一次渴望有根菸。她來杰柯洛是為了找他嗎?如果是,又為什麼?
喬治相信,若換成其他夜晚,他也許可以回到家、餵飽諾拉後爬上床睡覺。可是這一個八月夜晚的沉重壓力感加上莉亞娜出現在他最常光顧的酒吧,就好像有什麼事即將發生,光是這樣就夠了。不管好壞,總之有事即將發生。
喬治坐了很久,久到開始相信她必定已經離開酒吧。一個人坐在那裡獨飲紅酒,又能待上多久?於是他決定走回去。要是她走了,就表示他們注定不會再見。要是她還在,就上前打個招呼。
走回酒吧的途中,風緊貼著背,感覺上力道更強也更溫熱。到了杰柯洛之後他毫不遲疑,直接大步跨進前門,就在這時候,仍坐在原來位子的莉亞娜剛好轉頭看見了他。他目不轉睛注視著她那雙因為認出故人而微微發亮的眼眸。她從來就不是一個舉措誇大的人。
「真的是妳。」他說。
「是我。你好,喬治。」她說話還是他記憶中的平板聲調,若無其事得好像當天稍早才見過面。
「我在那邊看見妳了。」喬治朝酒吧較深處偏了偏頭。「起先不確定是妳,妳變得有點不一樣,但後來從妳旁邊經過,就很確定了。我是走到半路又折回來的。」
「還好你折回來了。」她說這句話時,小心地將每個字區隔開來,而且每個字尾都帶有細微的氣聲。「其實我來這裡……來這酒吧……是想找你。我知道你住這附近。」
「喔。」
「幸好你先看見我了,不然真不知道我有沒有勇氣先跟你打招呼。我知道你對我有什麼感覺。」
「那妳比我還了解我自己。我不太知道自己對妳有什麼感覺。」
「我是說關於發生的事情。」自從他回到酒吧裡,她就沒有變換過姿勢,只是用一根手指附和著打擊樂的節奏輕敲木質吧檯。
「那個呀……」喬治似乎在記憶庫裡搜尋著她說的是哪件事。
「那個呀。」她把他的話重複了一遍,兩人都笑了。莉亞娜整個身子轉了過來,更明確而鄭重地面對喬治。「我應該要擔心嗎?」
「擔心?」
「公民逮捕?臉上被潑酒?」她那雙淺藍色眼睛邊緣生出細細的笑紋,這是以前沒有的。
「警察已經上路了,我只是在拖住妳。」喬治臉上始終帶著笑意,感覺卻很不自然。「開玩笑的。」他見莉亞娜沒有接話隨即說道。
「我知道。要不要坐一下?有時間喝一杯嗎?」
「其實……我待會和人有約。」謊話就這麼輕易地脫口而出。和她離得這麼近,又聞到她肌膚的味道,登時讓他腦袋昏沉,有一股近乎獸性的衝動想要逃跑。
「喔,那沒關係。」莉亞娜很快應道:「但我真的有點事想問你,想拜託你。」
「好。」
「可以找個地方碰面嗎?明天如何?」
「妳住在這裡嗎?」
「不是,我只是來……其實我是來找朋友的……事情有點複雜。我想跟你談談,當然了,你要是不願意我也能理解。本來就沒抱太大希望,而我也明白……」
「好吧。」喬治暗暗告訴自己晚一點也還能改變心意。
「『好吧』的意思是,你願意談?」
「當然,趁妳還在的時候就碰個面吧。我保證不會報警,只是想知道妳過得怎麼樣。」
「太謝謝你了,感激不盡。」她從鼻孔吸入一大口氣,胸部隨之鼓脹。喬治竟然聽見她硬挺的白襯衫摩擦肌膚的窸窣聲壓過了點唱機的樂聲。
「妳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
「上網找的,沒那麼難。」
「我想妳現在不叫莉亞娜吧?」
「有些人還這麼叫我,但不多。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叫我珍妮。」
「妳有手機嗎?我是不是晚一點再打給妳?」
「我沒手機,從來都沒有。能不能再到這裡見面?明天中午。」喬治留意到她敏銳地轉動眼珠子審視他的臉,試圖看穿他,又或者是在尋找熟悉與改變之處。喬治已然兩鬢花白,額頭上生出了皺紋,嘴角的紋路也加深了。不過身材仍保持得相當好,依舊顯得帥氣,略帶點卑微的那種。
「沒問題。」喬治說:「可以約在這裡,他們中午有營業。」
「你的口氣聽起來不像沒問題。」
「不是沒問題,但也不是有問題。」
「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我就不會開口了。」
「好。」喬治再次暗想,之後還可以改變心意,現在答應她只是延後決定罷了。稍後喬治心想,在他這輩子的某些時間點,他可能會直接跟莉亞娜說他們不應該再見面。他不需要司法正義,甚至也不真的需要確切了結,因此他認為自己不會驚動警方。她捲入的麻煩已是多年前的往事,從那之後便一直逃亡都已經夠慘的了,下半輩子卻還得繼續逃亡。她當然沒有手機,她當然想在公共場所,在位於波士頓鬧區某個十字路口的某家酒吧碰面,以便能隨時逃離。
「好,我可以來。」喬治說。
她微笑道:「我會來的,中午。」
「我也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