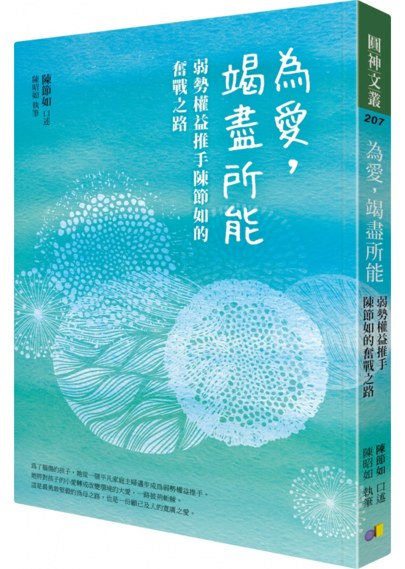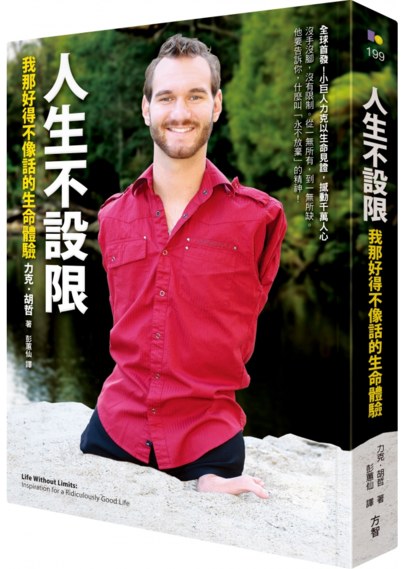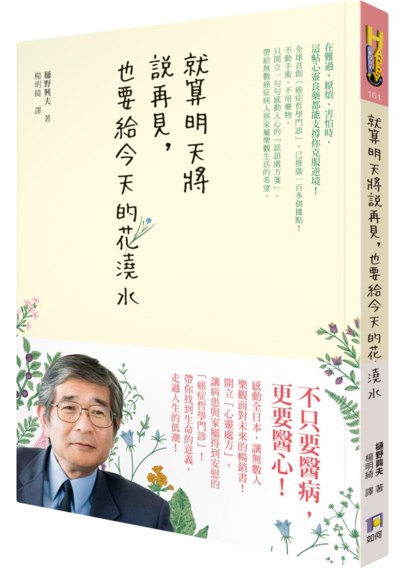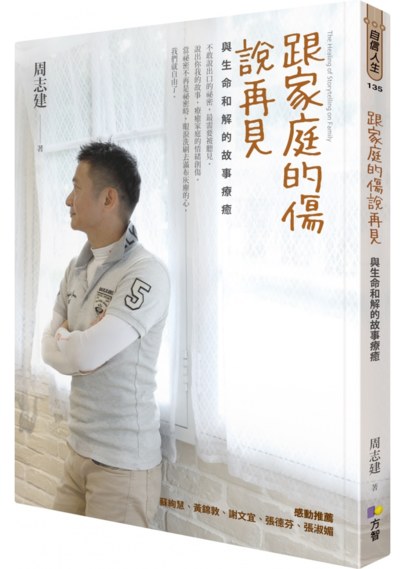一般父母擔憂孩子的學習成績,而她的孩子連上學都不是應有的權利,必須拚命爭取。
陳節如的孩子在幼年時因意外腦傷,造成智能障礙,她不知道是自己晚送了紅包,還是傷勢太過嚴重,從那天起,她的世界一夕轉變。所有母親對孩子的平凡期待,對她來說,都成為一輩子不可及的奢求……
她看見這些家庭們就這樣帶著哀傷,各自在艱困的環境中孤獨地行走,甚至成為一個個社會版上的悲劇。她決心成為那個改變!
不過,沒有任何改變只靠一個人就能成就。陳節如相信:面對問題的態度,決定了結果。
她堅決反對「要比小孩多活一天」的宿命論調,為弱勢權益奮戰30多年,現在70多歲的她說:
「我想在我離開的時候,不會有太多恐懼或哀傷,因為我知道,就算我不再了,孩子在眾人的關愛與越來越進步的制度下,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我的一生,已經足夠。」
.jpg)
我很喜歡走路,尤其是在城市的街道上亂走亂逛。
平時我工作很忙,沒什麼機會四處閒晃,所以只要有一點零碎時間,譬如會議與會議之間的空檔,我就會沿著街道隨意走走,看看附近新開了什麼店,裡頭賣什麼東西。
一個春末夏初的下午,某個離家不遠的會議提早結束,我沿著和平東路慢慢走回家。紅磚道兩旁的路樹正開得茂盛,走著走著,隔著不到二十公尺,發現昆霖和他爸爸走在我的前方,昆霖緊緊握著爸爸的手,緩緩向前移步。這是他們每天的例行活動。
他們走到銀行前面,再來是麵包店、畫廊、機車行,然後是排了長長人龍的蘿蔔絲餅店。我不確定他們的目的地,是要過馬路?走到前面的公車站?還是直接回家?我本來想走快一點好追上他們的腳步,但終究沒有這麼做。
看著他們父子的背影,一陣複雜的情緒湧上心頭。隔著二十公尺,就像是隔著四十年的驚心歲月……
已經四十年了。
那時昆霖才六個多月大,是個老是笑瞇瞇、胖嘟嘟的小娃娃,很得大家疼愛。就在我們仍沉醉在新生兒誕生的喜悅之際,剛學會翻身的他在爸爸上洗手間的二十秒,不知怎地從床上跌落下來。
我們急忙把他送到醫院急診室時,他已經開始翻白眼,連呼吸都有困難了。
….一切都太遲了。或許是傷勢太嚴重,或許是延誤了時間(那時候台灣還沒有MRI磁振造影的技術,如果有的話,昆霖就不會那麼慘了),昆霖大部分與腦相關的功能都受到嚴重的損傷。他變成重度智障,左手與左腳幾乎無法行動,視力差到只能見到光影,而且還有頑性癲癇,必須長期服藥。
我呆立在原地,腦筋一片空白。
我曾經阿Q 地想過,會不會是醫師弄錯了,昆霖還有恢復的希望?但我很快告訴自己,想這些有的沒的,一點用都沒有,既然事情發生了,就認了吧。哭天喊地、怨天尤人,這不是我的個性。
我了解,這輩子我永遠有個很深的遺憾,也清楚我的生活將永遠改變。但我也明白,時間會弭平所有的傷痛,讓我坦然接受一切。
昆霖是我的孩子,我會好好珍惜、照顧他一輩子。
這不是義務,是我心甘情願。
.jpg)
(昆霖沒有讀小學,經過一番爭取,直接上了國中。身心障礙孩子的遙遙迢迢升學路。)
.人跡罕至的那條路
台灣社會的劇烈變動似乎與我沒什麼關係。我關心的只有昆霖的健康,政治領域的事,完全不在我的視野裡。
直到某天報端上一則新聞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有個叫做「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社福團體,帶著智障者搬進台北市信義路五段楓橋新村的新家時,迎接他們的竟是「不歡迎,不妥協,回去吧!」「第一中心滾蛋」「反對第一中心非法入住」的海報。憤怒的住戶還把打算作為庇護工場的地下室加上大鎖,不讓工人進去裝修。
為何住戶有這麼強烈的反彈?根據報上的說法,他們認為智障者「有礙觀瞻」「有攻擊性,影響孩童的安全」,不希望這些孩子住進來,打攪他們原本平靜的生活。
那年昆霖剛滿八歲,是個乖巧的小孩,我很難想像竟然有人認為智障兒「有礙觀瞻」「有攻擊性」。但我更好奇的是,「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是什麼樣的單位?他們在做什麼?這些孩子的爸媽呢?他們是否跟我一樣,也有徬徨無助的時候,希望別人能拉自己一把?
市議員想居中協調,住戶毫不領情,堅持抗爭有理,還說:「我們不是沒有愛心,也不是不同情智障。可是同情歸同情,誰想跟一群不定時炸彈做鄰居啊?如果是你,你願不願意跟智障兒住在一起?你們同情一百個孩子,誰來同情我們一千五百位住戶啊?」
住戶的反應讓我的心都寒了。人性的殘忍,有時真是無遠弗屆。
我一直默默追蹤這則新聞,一連追了幾個月,直到那群孩子在員警的保護下,七上八下地住進了楓橋新村。日後沉重的家務讓我沒有太多時間思考這件事,「楓橋事件」便漸漸自記憶中淡出了。
如果日子就這樣平靜地過下去,我會覺得是種難得的幸福。然而人生就是這樣,總是一點一滴,不著痕跡地有了轉折,在不經意的地方累積下來,等發現的時候,人生的方向早已經轉了彎。
.改變一生的事
隔了幾年,我從報上得知有一群家長正在籌組專屬智障兒的基金會,叫做「心路」。從這天起,我腦海裡便怎麼樣也擺脫不了這件事。
我自認盡了一切努力照顧昆霖,卻無法改變一個殘酷的事實--他沒有辦法接受正常教育,無法正常上班工作。等到有一天我們老了,沒辦法照顧他了,怎麼辦?如果能結合其他家長的力量,彼此加油打氣,情況會不會有所不同?
我來來回回想了好幾天,決定去找心路基金會的創辦人宗景宜。
宗景宜的女兒仙仙到一歲多才發現是重度智障,沒有口語能力,經常突然生氣,哭到昏厥,光是訓練她握住湯匙吃飯就花了三年時間,這跟昆霖費了八年工夫才站起來很有得拚。我們聊了一會兒,發現兩人理念滿接近,應該可以共事。
從此,我踏出長久以來蟄居在家的日子。
這是一條需要長期奮鬥、無法回頭的路,不管多麼困難,為了孩子,我們只能往前衝。 我常說,人的一生會碰到什麼樣的人,遇到什麼樣的事,本來就沒得選。既然這是必修的功課,就認認真真地修吧!歡喜做,甘願受,人生就會有不一樣的風景。 我很感謝昆霖。因為他,讓我急躁的性格變得更有耐性,也更為寬容;因為他,讓我懂得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也體認到人生是多麼難得的一趟旅程。
我在少女時期便經常思考:「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有什麼意義?」胡亂想了半天,都沒什麼結論。現在的我已經有了答案:「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是為了幫助別人。」參與社福工作近三十年,或許我做的還不夠,但只要想到能替身心障礙的朋友多做點什麼,能在未來多留下點什麼,我的人生已有了意義與價值。
我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還算硬朗,不過我終究是個凡人,總有離開的一天。我想在我離開的時候,不會有太多恐懼或哀傷,因為我知道,就算我不在了,昆霖在眾人的關愛與越來越進步的制度下,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不論我能活到幾歲,我的一生,已經足夠。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