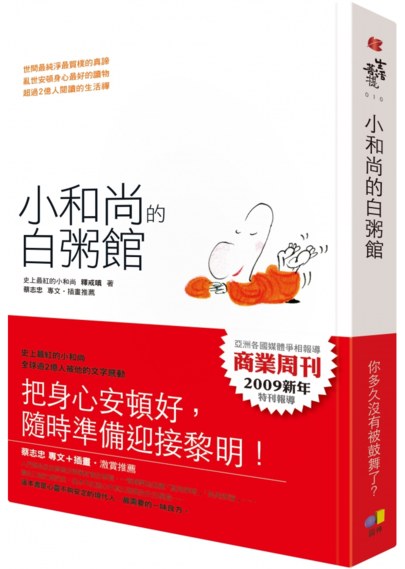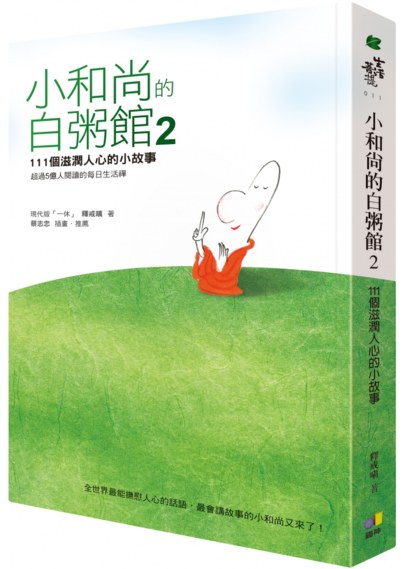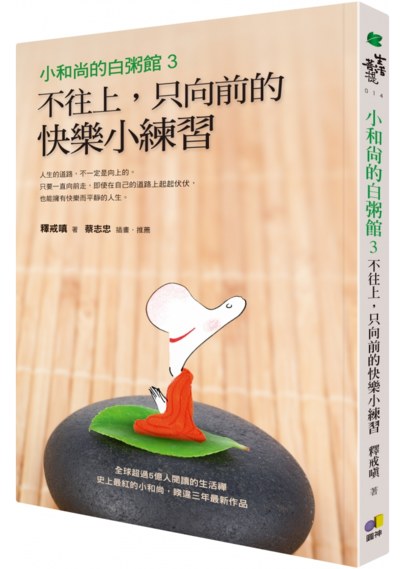快要記不清是哪一年了,應該是戒嗔十一歲那年的事情,那時我還不是和尚,住小山村裡,在山裡的小學校上。
就在那年,學校裡用了很多年的桌椅都換成新的了,當然,新只是相對以前的桌椅而言,新來的桌椅都是城裡小學淘汰給我們的。
坐在新椅子上,一刻不停地搖晃,覺得那是無比的樂趣;以前的椅子,只要使一半力氣就會散架。
書桌上還留著不少使用者的痕跡,比如誰誰誰在此一遊;也有密密麻麻的小字,可能是考試的答案。
課堂裡的光線很好,因為屋頂至少有十處地方透光。
我們有一位女老師,是學校裡唯一的老師,所有的課程都是她一個人教授。她脾氣很暴躁,時常在課堂上把我們挨個兒叫起來訓斥。她嗓門挺大,同學都不願意坐在前排,耳朵很不好受。
不記得從哪一天開始,老師忽然不再罵我們了,偶爾還笑咪咪地表揚我們幾句,走進課堂的時候會哼著小曲。在課間的時候,她就在窗口望著外面出神,一動也不動,嘴角會有微微的笑,那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再後來,老師嫁人了,她丈夫在縣城裡上班,老師自然要跟過去。
走的那天,老師哭了,一屋子小孩茫然地看著,以前都是她罵我們哭。
老師說,我要走了,有個同學忽然放聲痛哭起來,慢慢地感染了其他同學。戒嗔記得自己哭得很難受,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走了以後,托人從縣城給我們帶了一些糖回來,每個同學都分到兩三顆。
糖後來的去向記不清了,吃掉了?被別人吃了?又或者是丟掉了?
但是老師在戒嗔手上打板子的情形,記得了好些年。
人是否都這樣,只記得別人的壞處,不記得別人的好處。
老師離別的傷痛持續了一整天。
第二天開始,戒嗔便和那些不用背書包的同學在山上飛奔了。
山上有棵很古老的樹,有人說有三百年,也有人說是五百年。
大家都喜歡攀在粗大的樹枝上,遠望自己的家。這裡是山的頂端,每根樹枝都讓你望得更遠。
那次手握著斷枝,從樹上摔下來的情形,一直沒有忘記過。
我重重地摔在地上,聽見圍觀的人哄笑,想站起來卻沒有力氣,側頭看身邊,一片殷紅。有人驚恐地呼喊著我的名字,記憶就在這裡斷裂了。
在處處漂浮著消毒水的屋子醒來,我看見挺著大肚子的她正和醫生交談,大夫一邊說,她一邊流淚。
我沒有在醫院住很多天,縣城裡的醫院太貴。我回到家裡,依然吃著很苦的藥,想吐出來。她告訴我,藥很貴,不能吐掉,一口口咽下去,因為很貴。
在床上睡了很多天,慢慢的又開始能行走、又能跳動了。
我聽見有嬰兒的哭泣聲,弟弟出生了,我十二歲了。
一直以來戒嗔想問她一個問題:「為什麼當年有人願意收養弟弟,而妳為什麼一定要送我上山?」
每年見到她,只有一兩次;每次見到她都想問,總覺得有種說不出的理由,讓戒嗔不能張口。

還記得第一次上山的那一刻,她在前面走。
我說,我以後不爬樹了。
她沒有說話,頭也沒有回,只是緊緊抓著我的手。依稀記得自己在用力,用力擺脫她的手;她尷尬地望著我,想牽又不敢牽。
有人擺脫你的手,是因為他想離開你;也有人擺脫你的手,是怨恨你不肯抓住他。
記得自己向師父磕頭,不記得磕了多少,我只知道那時的我,沒有一個是情願的。
聽見師父的嘆息聲,師父默默地點頭,她笑著哭了。
站在寺門下,看著轉身而去的她,我們之間第一次背道而馳。
她沒有回頭,我回頭了,跟在那個手有殘疾的師父後面,走進曾經不屬於我的所在。
隨風而動的羽毛,微不足道,輕輕停靠在天明寺的匾額上面。
你心中可曾像我一樣不停地回頭在看?
那個問題,困惑了戒嗔很久,不敢問寺裡的師父們,因為不想從那裡得到答案。不是所有問題都願意拿出來求解,有些問題,求解的總是自己。
曾經想換上在家人的衣服,找個不認識的施主問問答案,也許在家人對俗事的理解,可能比出家人還要強。最後也沒有去,即便是去了,有多少人認出戒嗔是和尚呢?
出家人被塵緣困惑是不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呢?其實不奇怪,如果依照經文做標準,或者是件奇怪的事情,但如果依照你做標準,或許只是一件小事了。
你我之間,差別只不過一個字而已。
深夜也曾常常難眠,偷偷摸出床下出家人不應該看的書尋找答案,一本兩本,一無所獲。
以為靜心打坐可以得到答案,也未有得,戒嗔一直以為自己修行不夠。
有一天在寺裡看電視,信號不好,不像鎮裡已經用了天線,只能收到幾個台,雪花點也很多,聽到電視中有人問起:「你想知道什麼答案?」
在禪房中沒有領悟的答案,在這裡終於找到了。那一刻戒嗔不再困惑,在不能改變結果的事情面前,答案顯然已不重要。
沒有恨了,是否就真的空了?為何在雪地中為她奔跑?原來還有愛!
無惑了嗎?當然還有,只是戒嗔已經把它們藏於心底了。
伸手摸摸頭上那塊曾經讓戒嗔差點丟掉性命的傷疤,已經不再那麼明顯了,是時間的緣故吧。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