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分分秒秒醞釀著,積累著——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們輸了。
波娜德律師站在我面前。你大概還記得,她是一名年輕嬌小的律師,出庭戴的假髮底下露出紅褐色頭髮,目光冷冷的,說話很輕,穿上黑色律師袍時髦高雅,看不出險惡心計。她散發沉著冷靜、值得信賴的氣質。我上證人席兩天了,很累,真的很累。後來,我會明白這個時刻是波娜德律師刻意挑選的。下午稍早,她花了許多時間詢問我的求學經歷、婚姻狀況和興趣嗜好,用了形形色色的問話手法,害我起先以為這一套新的盤問方式其實無關緊要。時間逐步醞釀,迎向高潮的一刻。
法庭後方的時鐘顯示為下午三點五十分。氣氛沉滯,眾人疲憊不堪,法官也不例外。
我喜歡這位法官。他會細心做筆記,也會客氣地舉起手請證人說慢一些。他常擤鼻涕,看起來有些虛弱。他對律師嚴厲,對陪審團卻很客氣,其中一名團員宣誓時結結巴巴,但他只是微笑點頭說:「女士,慢慢來沒關係。」我也喜歡這個陪審團,成員組合令人滿意,女性略微超過半數,包括三名非裔與六名亞裔,年紀從二十歲左右到六十來歲都有。很難想像這樣一群容易心軟的人會送我進大牢。現在看到他們坐得懶懶的,就更難想像了。此刻的他們比起剛開庭時截然不同,不再腰桿挺直,也不再滿臉發光得意洋洋,自覺身負重任而精神百倍。他們當初大概跟我一樣,沒想到每日開庭時間竟然這麼短,最早從上午十點開始,持續到午餐時間,最遲四點結束。然而現在我們都懂了,累人的是一切進行得十分緩慢:開庭至今,我們飽受瑣碎枝節的折磨。他們感到煩悶,跟我一樣不懂波娜德律師的問話到底有何用意。
至於待在被告席的木板隔間,那片強化厚玻璃後方的人,就是你:與我同列被告的你。在我站到這裡之前,我們並排而坐,雖然中間隔著兩名法警。律師建議過我,其他證人接受訊問時,我不該偷瞄你,免得讓人覺得我們是串通好的。打從我自己站上證人席,你就看著我,不帶感情地看著我,那份目光冷靜無比,近乎茫然凝視,我不禁感到心安,因為我知道你是在鼓勵我保持堅強。我心裡明白,當你看見我孤立無援地站在這裡,受人注視、受人評斷,你會覺得想保護我。對於不認識你的人而言,這樣的眼神空洞冷淡,但我經常看你露出這般刻意隨興的神情,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八號法庭照不到陽光,很惱人。天花板嵌著一格一格的日光燈,牆上則是白燈。整座法庭乾淨現代,外觀冷肅。無論是木板牆面或鋪著綠色椅墊的下拉式座椅,統統和這一切毫不相稱:讓我們置身此地的緣由轟轟烈烈,訴訟程序卻是貧乏無趣。
我環顧整座法庭。書記官坐在法官的前一排,垂著肩膀。蘇珊娜坐在旁聽席,旁邊有一群大概在一小時前跑進來的學生,還有一對從開庭就在的退休夫婦,據我所知,這對夫婦和我們的案子毫不相干,只是愛看戲又付不起倫敦西區劇院的門票。就連蘇珊娜也一邊如同往常地看著我,一邊三不五時瞥向手表,等待開庭時間結束。大家都不覺得現階段會有什麼重大進展。
「我想請妳回顧一下先前的職業生涯。」波娜德律師說,「還請稍加忍耐。」整段訊問過程,她始終對我謹慎有禮,但我依然十分怕她。她展現超凡的沉著鎮定,似乎握有別人毫不知悉的絕妙高招。我猜她小我二十歲,年紀頂多三十五歲左右,不比我的兒女大多少。她鐵定在律師界竄升得很快。
陪審團最右邊是一名穿粉紅上衣的中年非裔男子,正誇張地打哈欠。我瞄向法官,他神情堅定,眼皮卻很重。看來在場只有我的律師羅伯特依然清醒專注。他微皺眉頭,兩道斑白濃眉壓得低低的,雙眼凝視波娜德律師。後來,我好奇他當時是否從她輕描淡寫的語調中,察覺了什麼蛛絲馬跡。
「可否請妳說明,」她繼續問,「妳第一次到國會大廈參加聽證會是在什麼時候?距離現在多久以前?」
儘管不該鬆懈,我仍不自覺鬆了一口氣,因為這是個簡單的問題。那關鍵的一刻尚未開始。
「四年前。」我很肯定地回答。
波娜德律師以明顯的動作低頭查看筆記。「妳參加的是下議院的特別委員會——」
「不對。」我說,「其實是上議院的常務委員會。」這方面我一清二楚。「現在已經沒有常務委員會了,但當時上議院共有四個常務委員會,各自針對不同的公眾議題。我參加的是科學常務委員會,負責探討電腦定序運用於基因圖譜的發展情況。」
她發言打斷我。「不過在妳成為自由工作者之前,是在波福中心全職工作對吧?我想全名是波福基因體研究中心……」
一時之間,這個毫無關連的提問讓我困惑了。「嗯,是啊,我在那裡全職做了八年,後來改為每週工作兩天,擔任顧問--」
「波福中心是全英國最負盛名的研究機構之一,對吧?」
「唔,就我的領域而言,波福中心、劍橋和格拉斯哥大學的研究中心都非常頂尖,我——」
「妳可以告訴大家波福中心位於哪裡嗎?」
「在查理二世街。」
「查理二世街平行於帕摩爾街,往南和聖詹姆士廣場花園相連?」
「對。」
「很多機構都位於那一帶吧?研究中心、私人會館和研究圖書館……」她望向陪審團,露出極淺的微笑。「那裡堪稱是權力的中心。」
「我不是……我……」
「不好意思,妳在波福中心工作多久了?」
儘管律師曾交代過要避免,我仍忍不住流露稍不耐煩的語氣。「我目前還是在那裡工作。不過以全職來說,總共待了八年。」
「是的,抱歉,妳剛才說過了。在那八年期間,妳每天都搭公車和地鐵通勤?」
「嗯,幾乎都搭地鐵。」
「妳從皮卡迪利街走過去?」
「嗯,通常是從皮卡迪利圓環站。」
「午餐時間和下午茶時間,妳在那附近的很多地方吃過東西?工作完也會上酒吧之類的?」
這時普萊絲檢察官輕輕呼了一口氣,舉起一隻手。法官望向波娜德律師,她舉手回應。「閣下,不好意思,我就快切入正題了……」
閣下。我原本對法庭的印象全來自電視劇,還以為她會稱法官為「庭上」。不過這裡是俗稱「老貝利」的中央刑事法院,因此以「閣下」稱呼。有人跟我說過,法庭上的假髮與人們彼此的稱謂可能顯得古怪嚇人,結果我覺得兩者都不可怕,反倒滑稽可笑。我真正怕的是這所有折磨人的過程:官僚體系、一部部筆電、一支支麥克風、不斷喀嗒喀嗒打字的速記員,以及逐字逐句不斷增加的關於我的檔案資料。
凡此種種,教我毛骨悚然。我彷彿是一隻田鼠,掉進聯合收割機不斷轉動的巨大刀片中。儘管我準備充分,依然心驚膽顫。我先生考量過這一點。他聘請了一群最頂尖的律師,每小時四百英鎊,只求我能做好出庭的萬全準備。多數時候,我都記得回答問題時要看著陪審團,而非直覺地轉頭看我的律師。他們建議我,最簡單的方式是腳尖從頭到尾都朝向陪審團,這樣自然就會記得了。我始終肩膀往後,保持冷靜,與陪審團眼神接觸。我的律師團認為我表現得很好。
波娜德律師朝法官致意,然後轉頭看著我。「所以妳前後一共在西敏市⁎工作和活動了十二年?或是更久?」
「也許更久吧。」我說。就在這時,分分秒秒開始積累,迎向那一刻。我內心某處深深感到不安,好像神經叢被輕輕拉住似的。我不明就裡,但仍察覺得到。
「因此呢,」她聲音變得緩慢輕柔,「既然妳會進出那裡的地鐵站,還會在那一帶用午餐什麼的,可見對那個區域十分熟悉?」
時間持續累積。我的呼吸變得用力,感覺到胸膛起起伏伏,起初不明顯,然而我越想控制,呼吸就更加費力。法庭的氣氛緊繃起來,大家都有同感。法官正盯著我。是我在幻想嗎?或者我視線最旁邊那個粉紅上衣的陪審員確實稍微坐直了些,在座位上往前靠呢?剎那間,我不敢直視陪審團。我不敢直視被告席的你。
我點了點頭,突然說不出話來。我知道再過幾秒我就會出現過度換氣的症狀。我就是知道,儘管我從來不曾過度換氣。
波娜德律師的聲音低沉而迂迴。「妳很熟悉那裡的商家、咖啡館……」我的後頸因為流汗而隱隱刺癢,頭皮也在發麻。她暫停下來。她留意到我在緊張,想讓我知道我猜得沒錯:我知道她要把問題導向何處,而她曉得我知道。「妳很熟那裡的小路……」她再度停頓片刻,「很熟那裡的小巷……」
於是關鍵時刻到了。那一刻,一切急轉直下。這一點我知道,坐在被告席的你也知道,所以你才會用雙手摀著臉。我們都知道我們即將失去一切:婚姻毀了,事業完了,我會失去兒女的尊敬,連我們的自由也危在旦夕。
我們努力打造的一切、盡心保護的一切,即將統統毀於一旦。
此刻我在眾人的面前過度換氣,大口喘息。我可憐的律師羅伯特盯著我看,滿臉疑惑與擔憂。檢方出擊的部分早已結束,無論他們的開場陳述或所請證人全在意料之中,而我現在面對的是你的律師,她也同屬被告律師團,我們雙方的抗辯算是處於同一陣線。我看得出羅伯特正想著:現在到底是怎麼了?他看著我,表情寫道:她有事情瞞著沒告訴我。他不曉得接下來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只曉得自己一無所知。碰到沒準備過的突發狀況,想必是所有律師的心頭夢魘。
檢方坐在證人席後面離我最近的桌子,他們也正盯著我。在場的人包括代表英國政府的檢察官,旁邊是她的助理,後面一桌是皇家檢控署派來的女性人員,再後面幾排坐著倫敦警察廳的資深辦案警官、專案人員與物證人員,門邊則是被害人的父親,他坐在輪椅上,親屬連絡員陪在一旁。我對這群登場人物就像家人般熟悉。所有人緊盯著我,只有你——我的愛人——除外。你不再看著我了。
「妳很熟吧?」波娜德律師的口吻迂迴柔滑。「妳很熟悉那條叫『蘋果園』的小巷吧?」
我非常緩慢地閉上眼睛,彷彿不願面對此刻之前的整個人生。法庭鴉雀無聲。坐我前面的某人挪動了腳步。為求效果,波娜德律師停頓下來。她知道我會閉著眼睛一陣子,因為我得花時間接受這一切,緩和呼吸,多爭取一點時間。然而,時間繼續流逝,像水流過指縫般,流得一點也不剩。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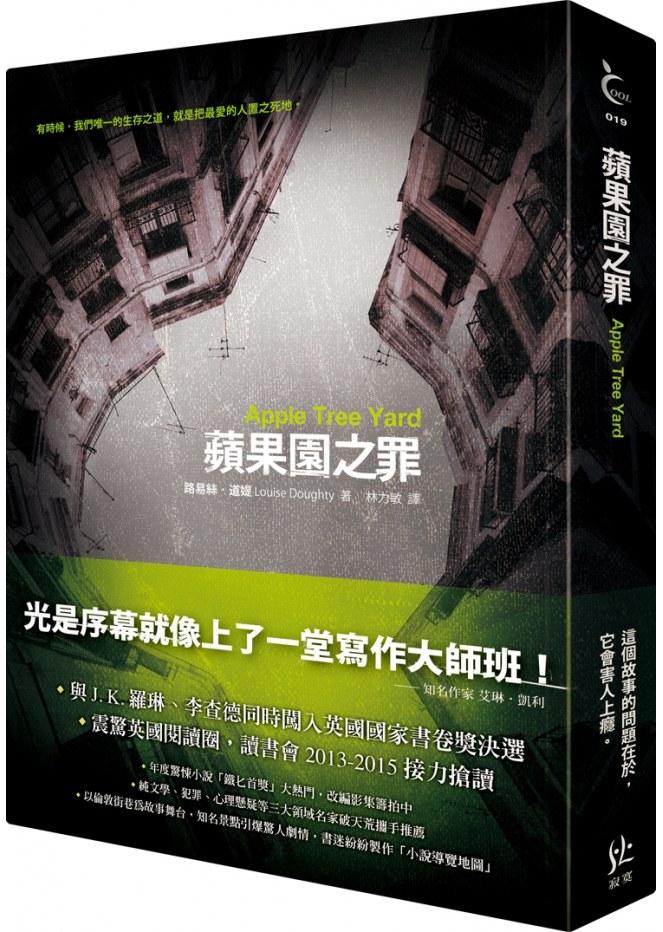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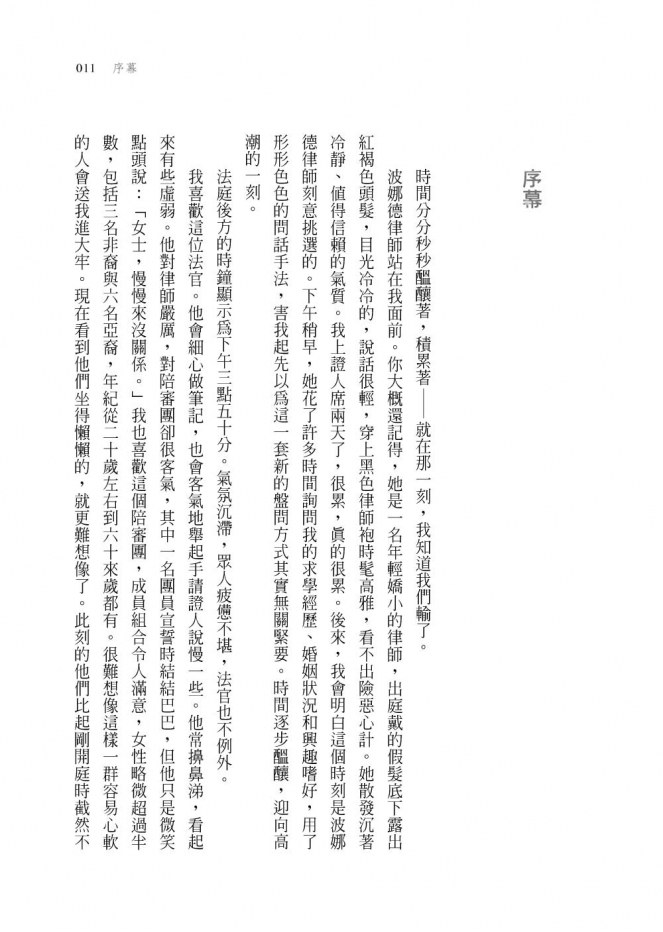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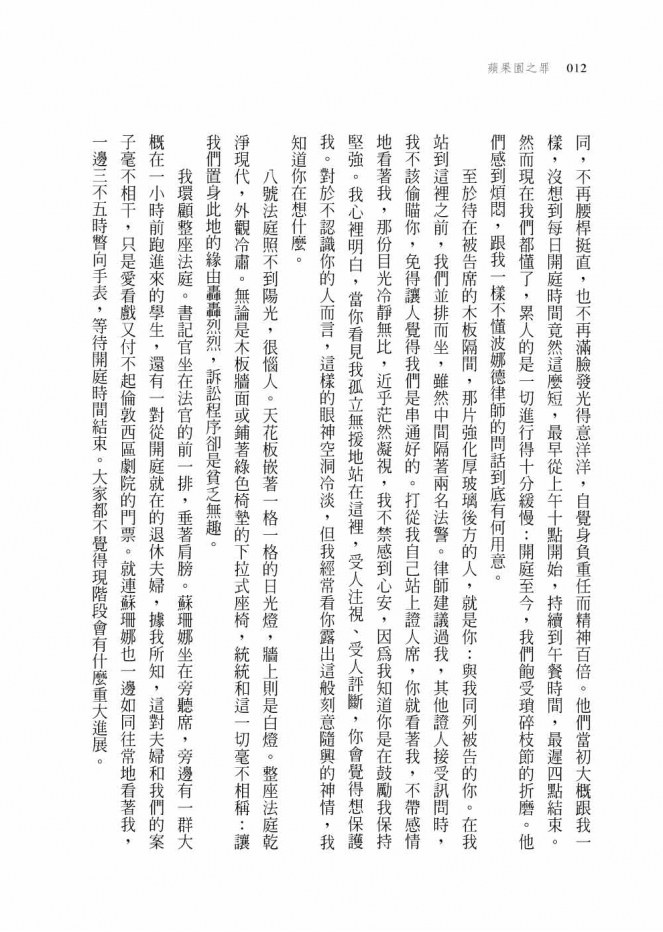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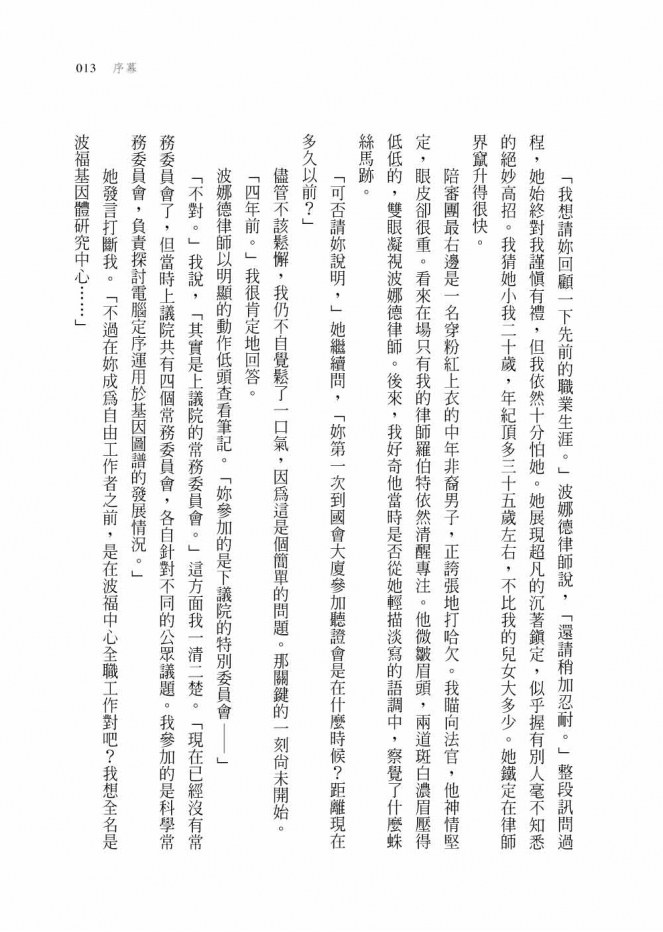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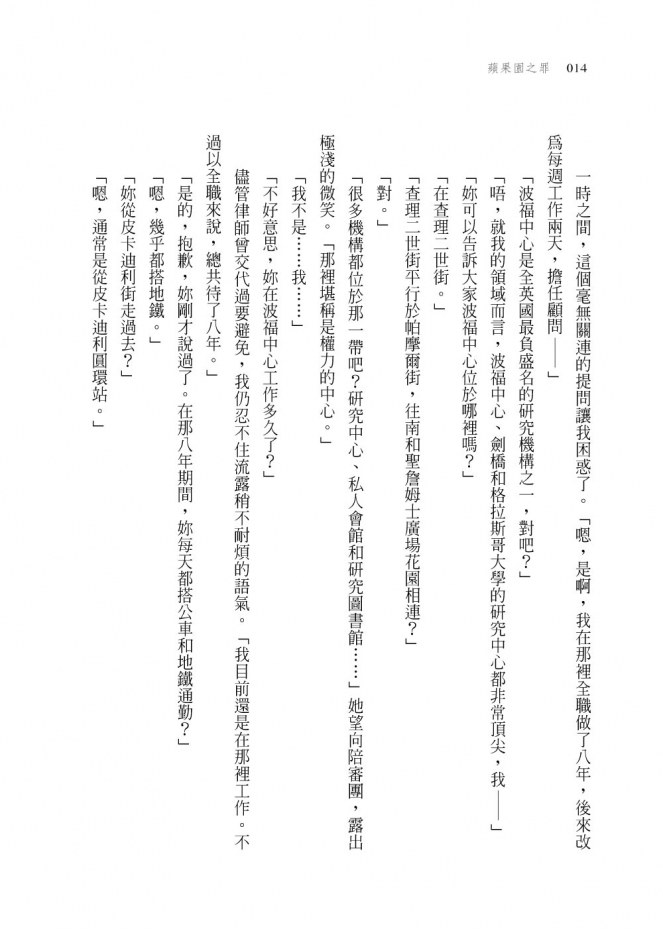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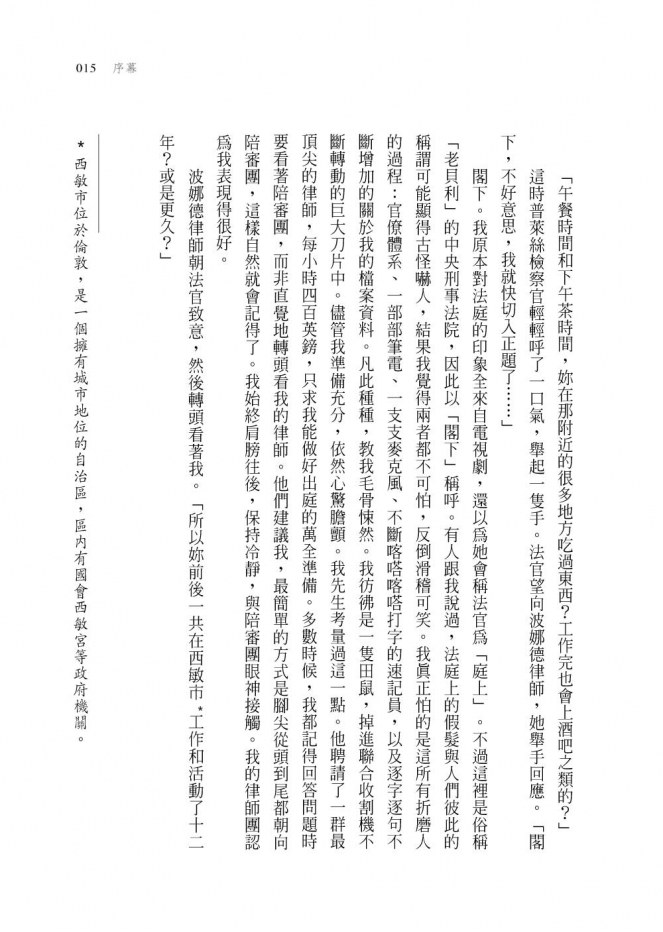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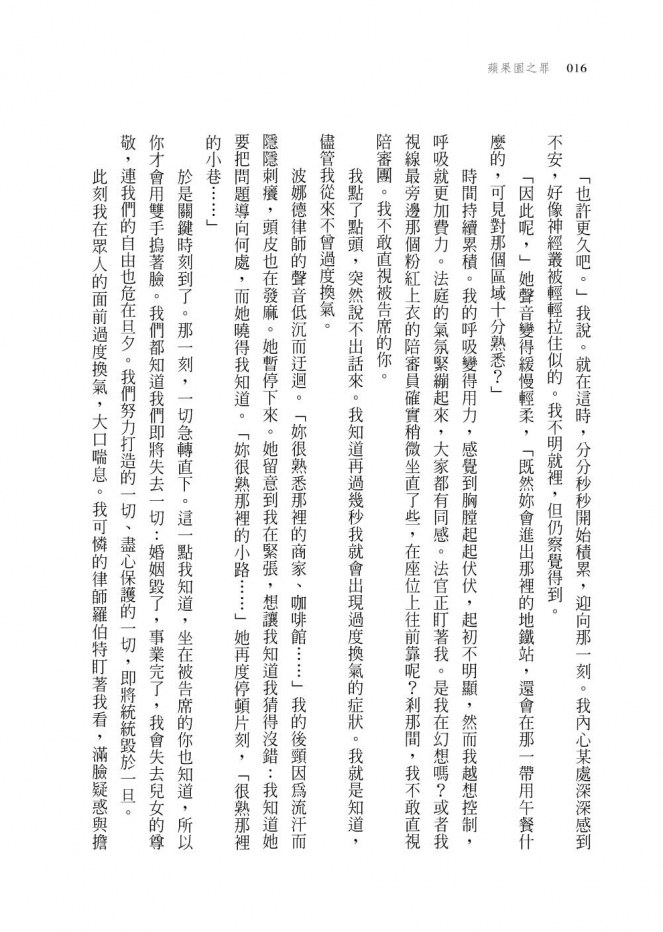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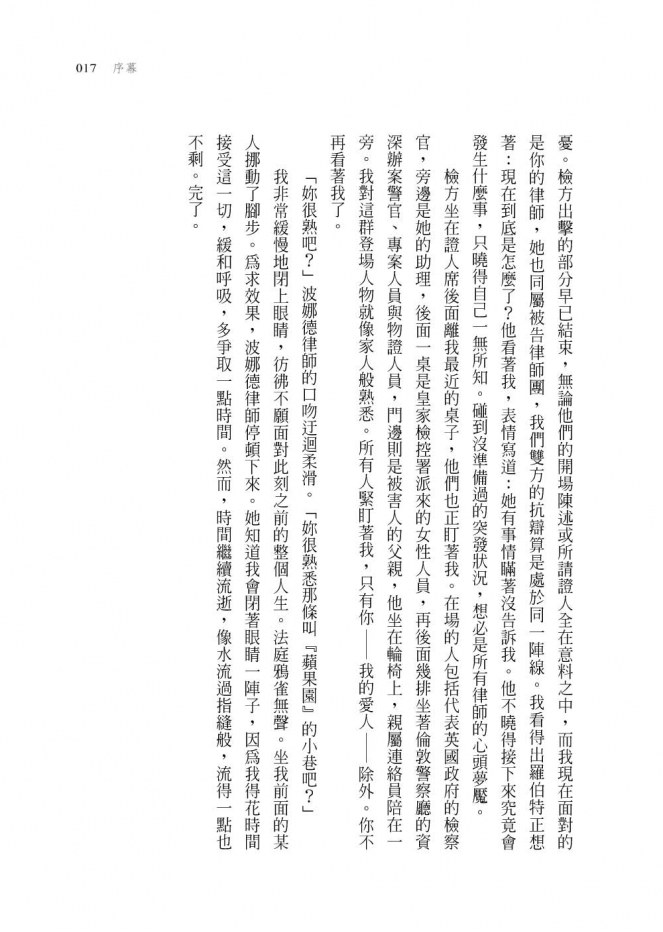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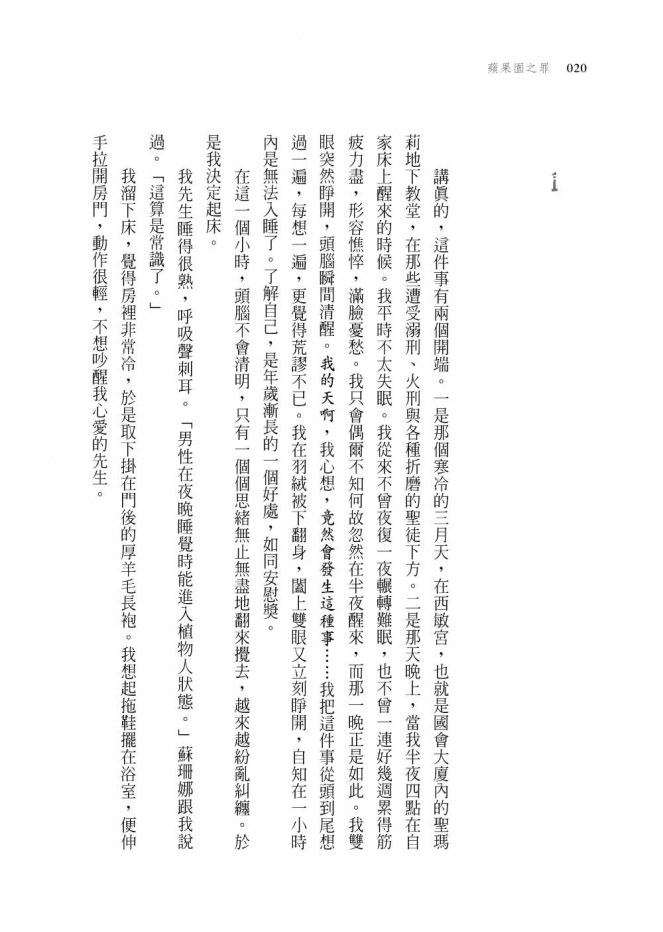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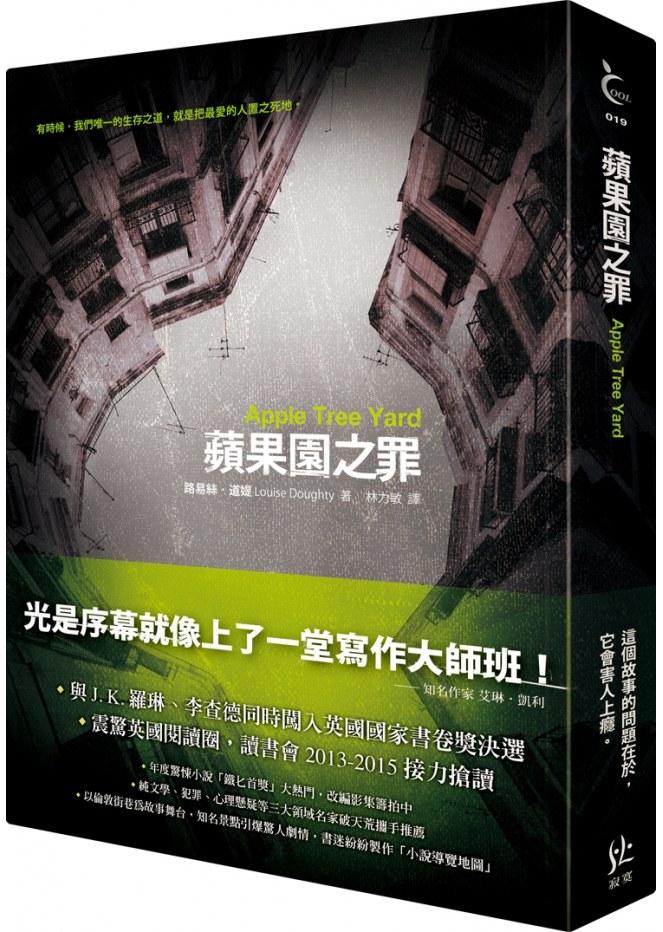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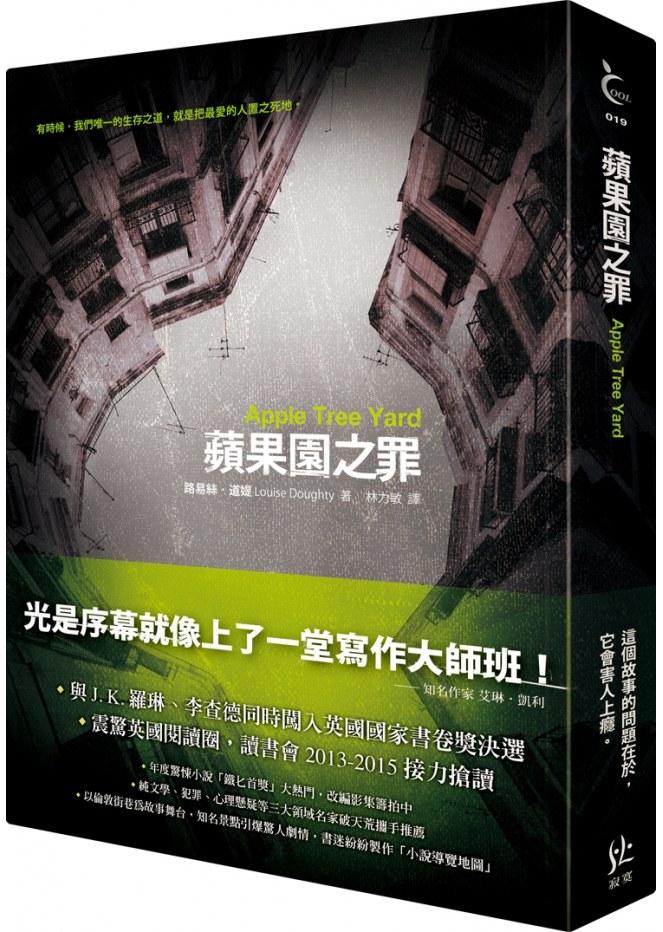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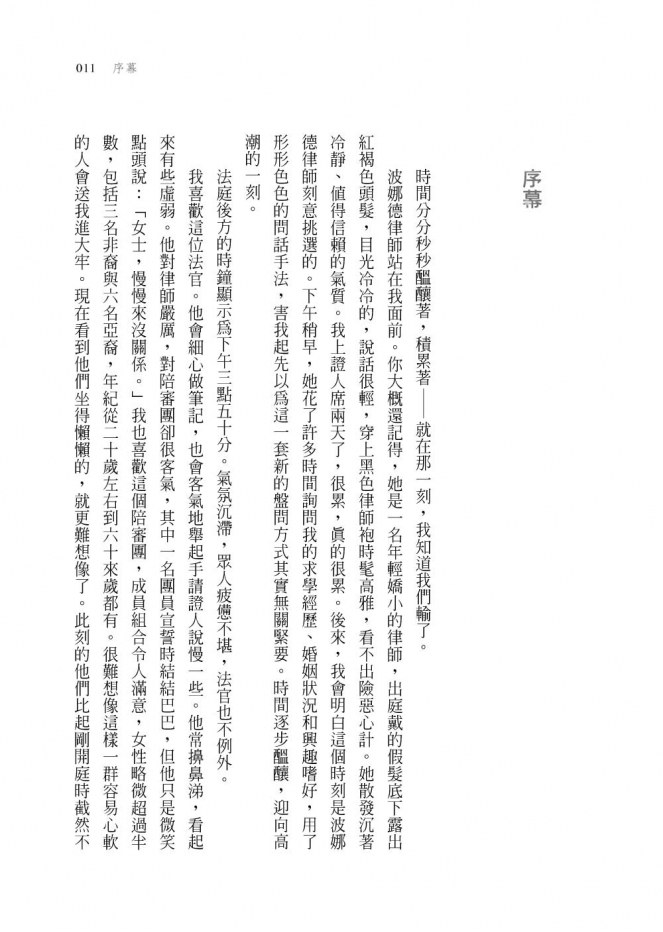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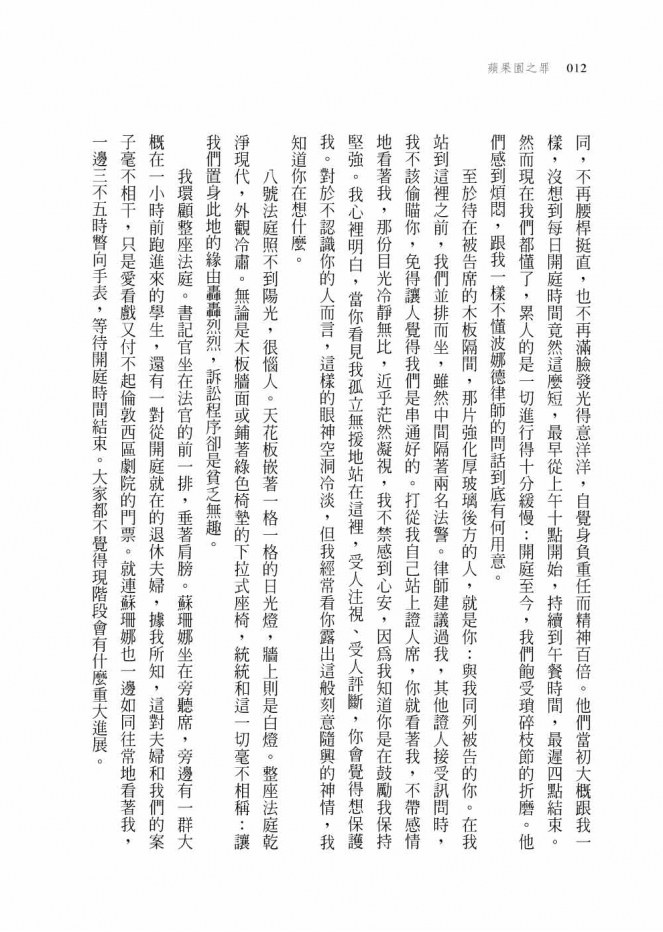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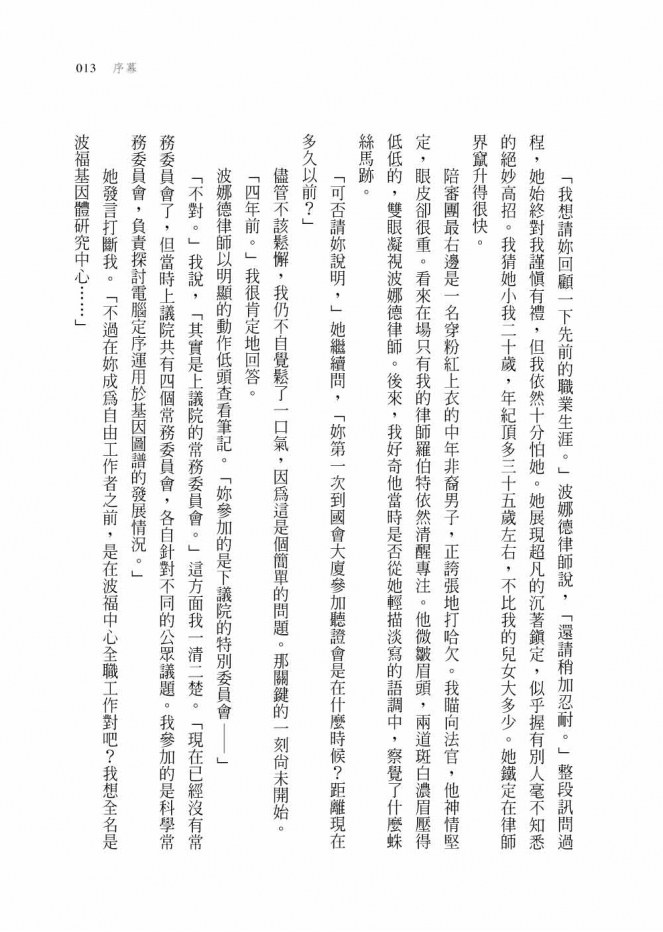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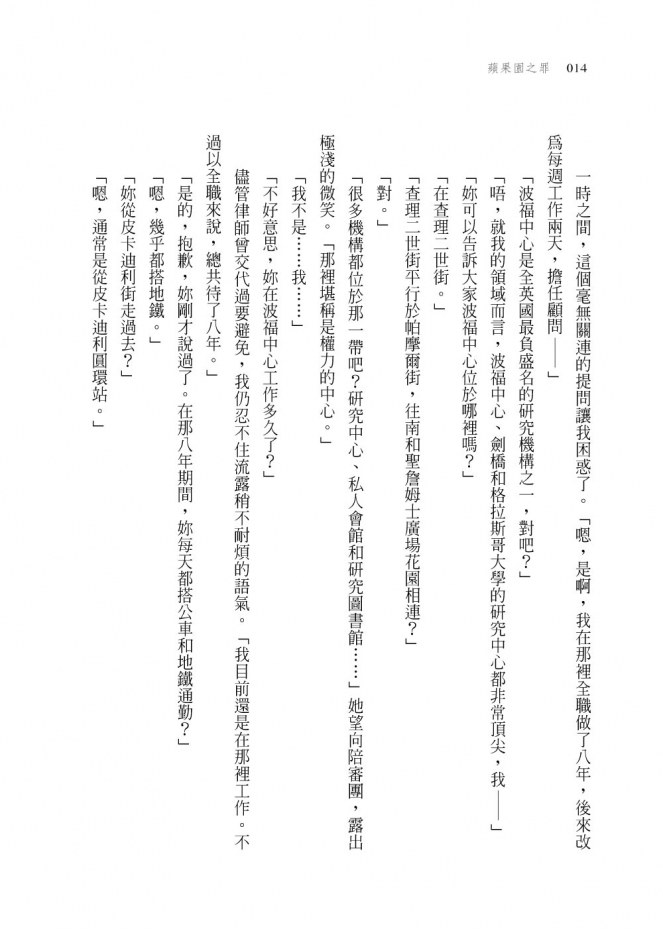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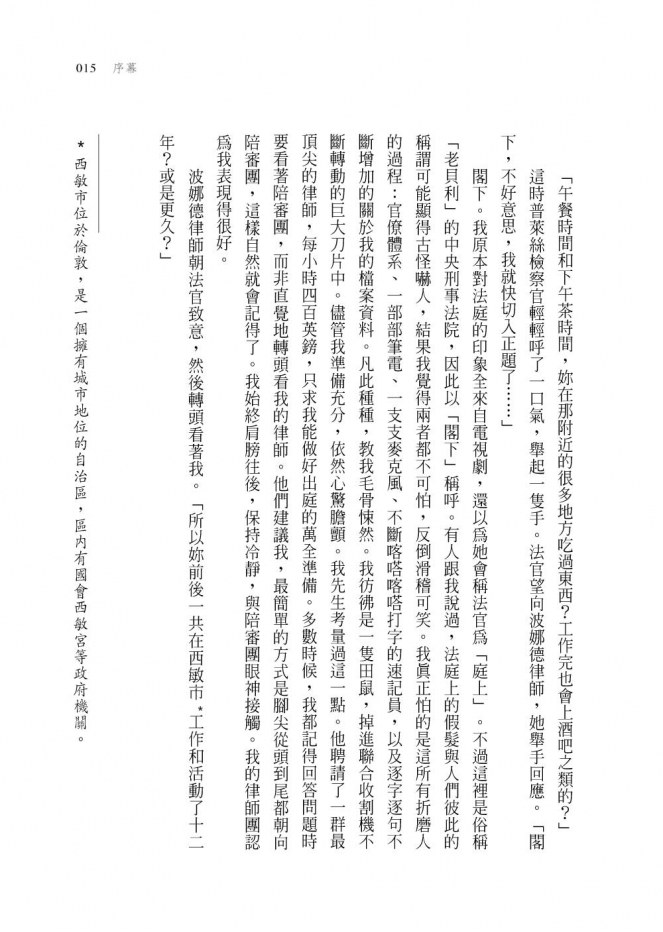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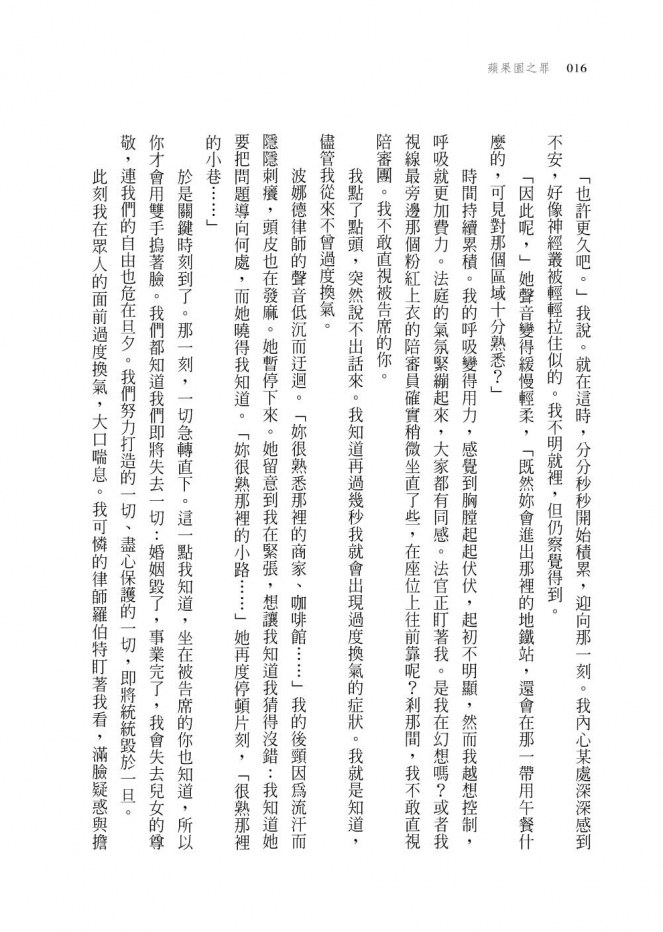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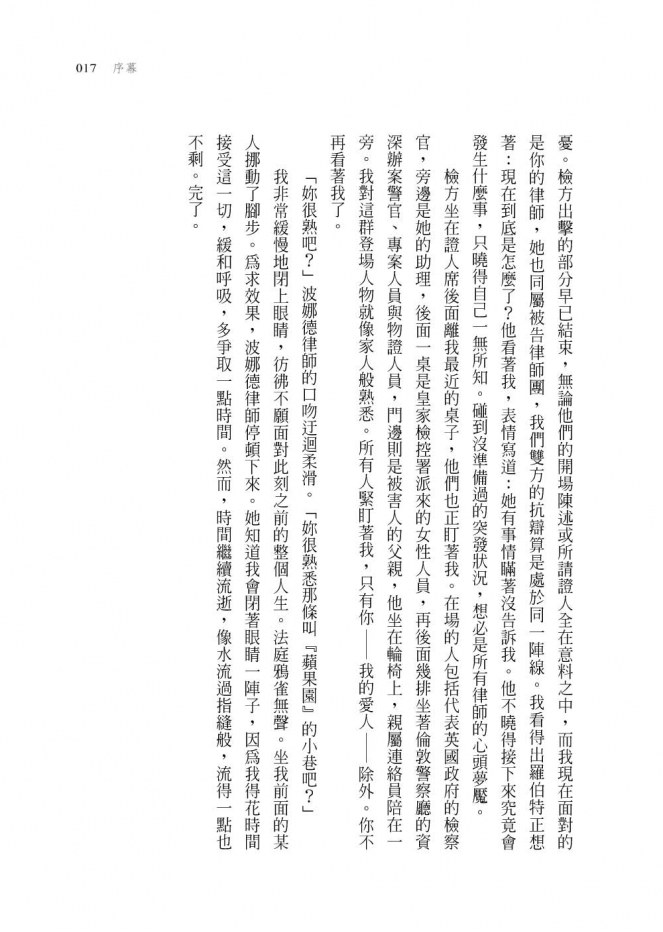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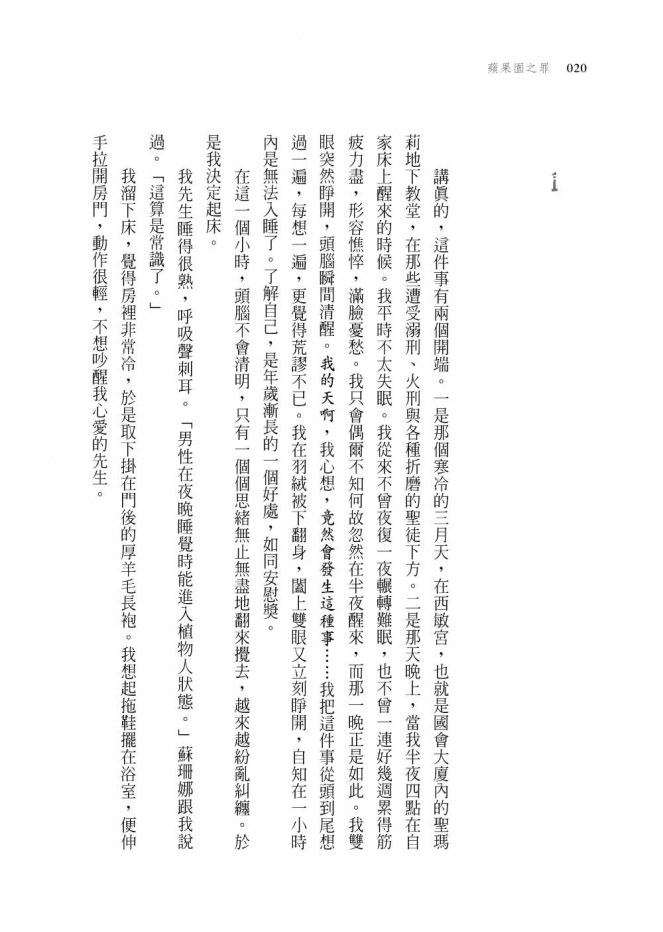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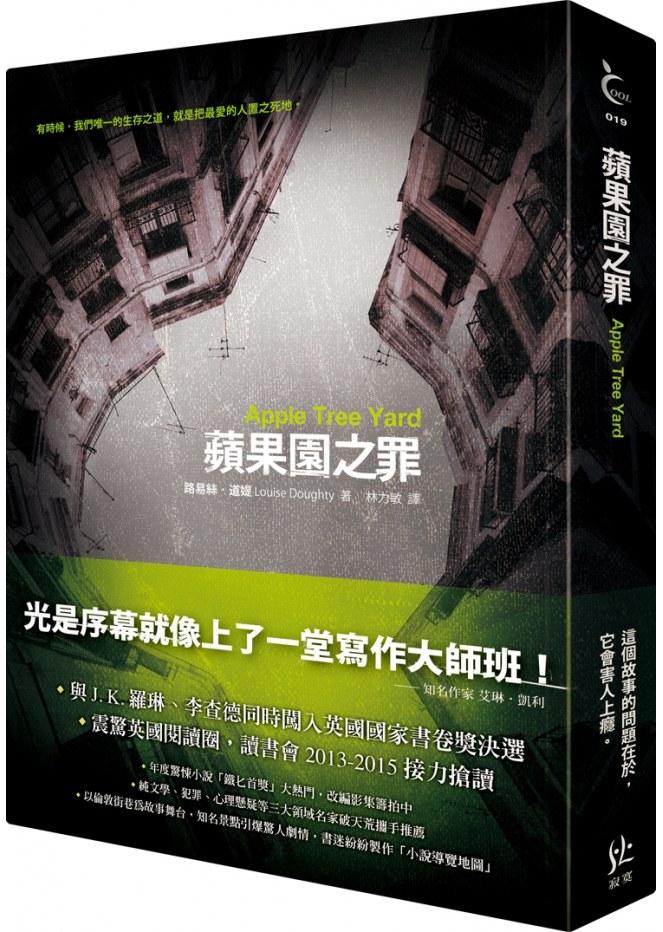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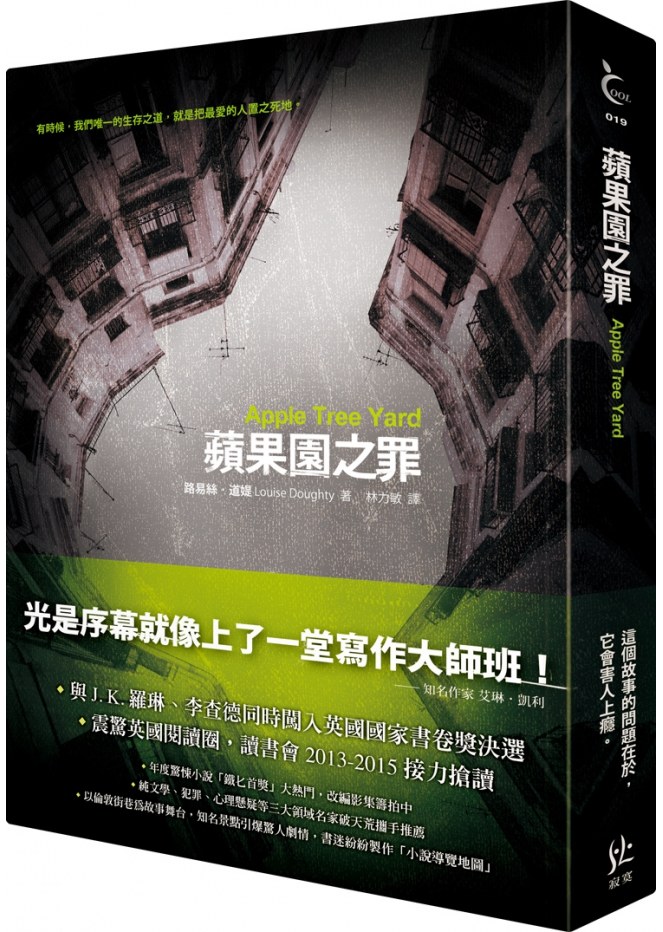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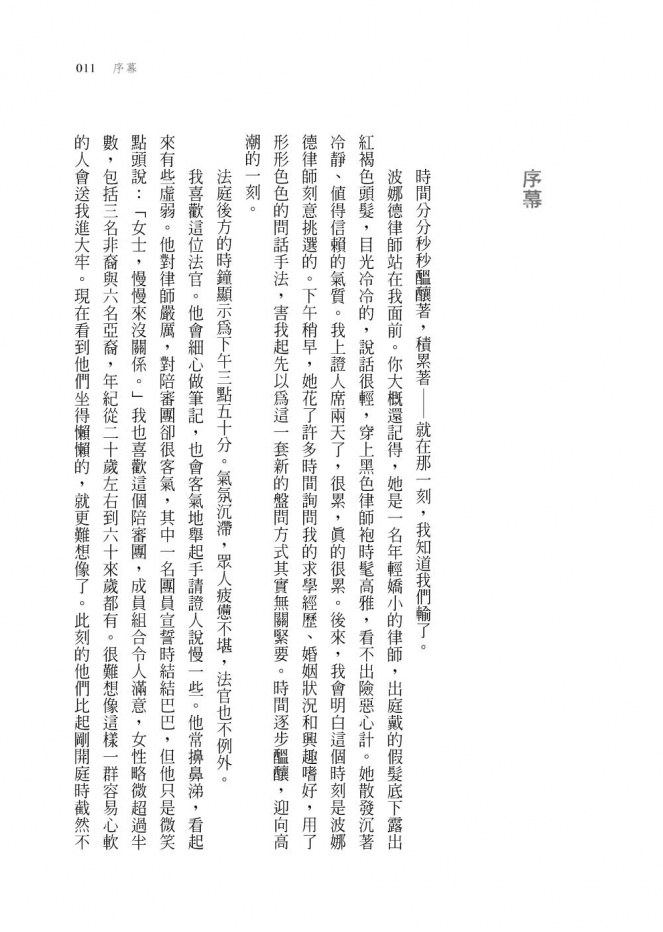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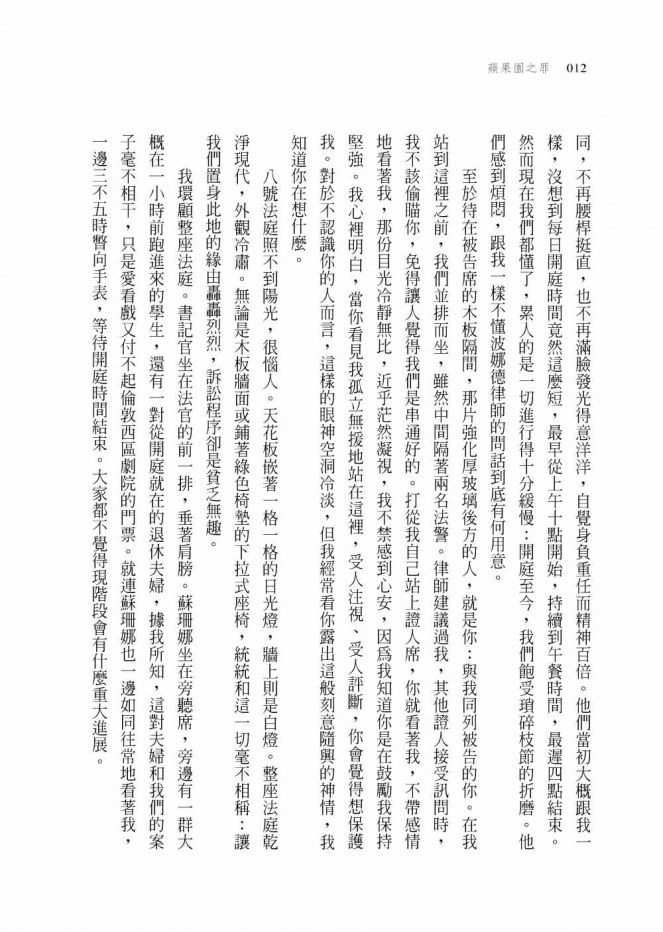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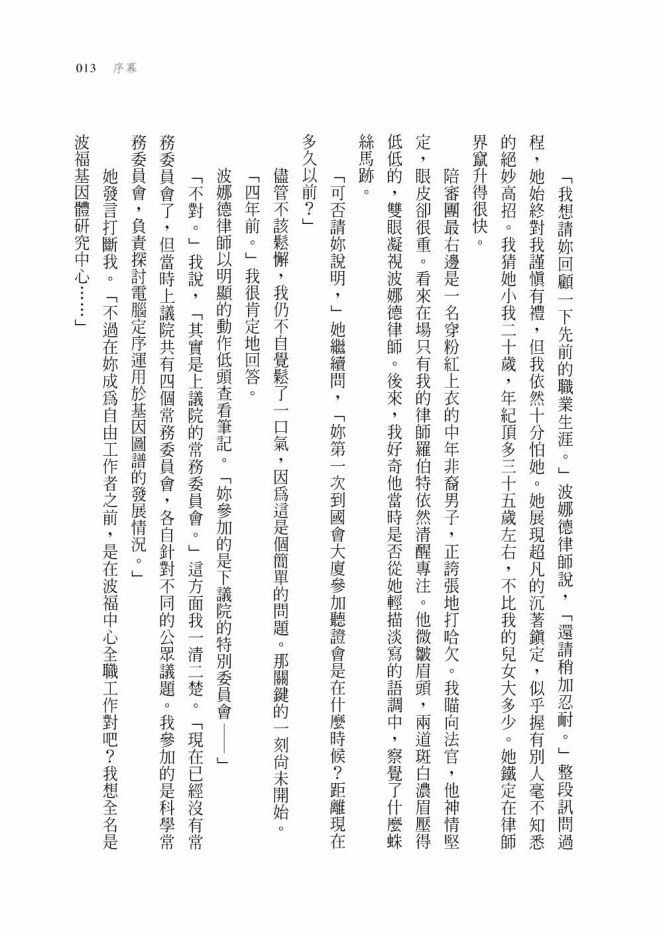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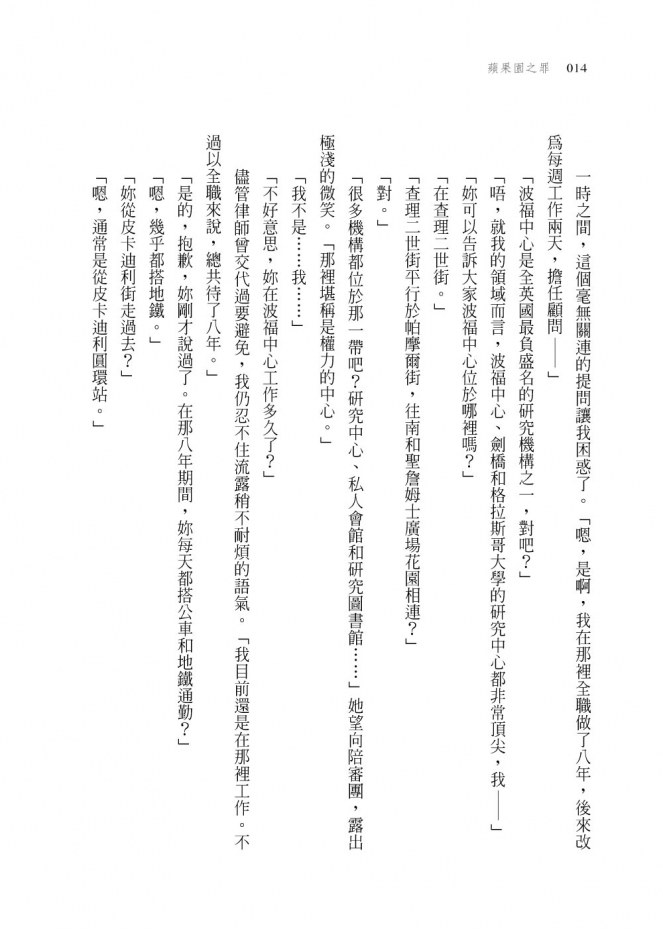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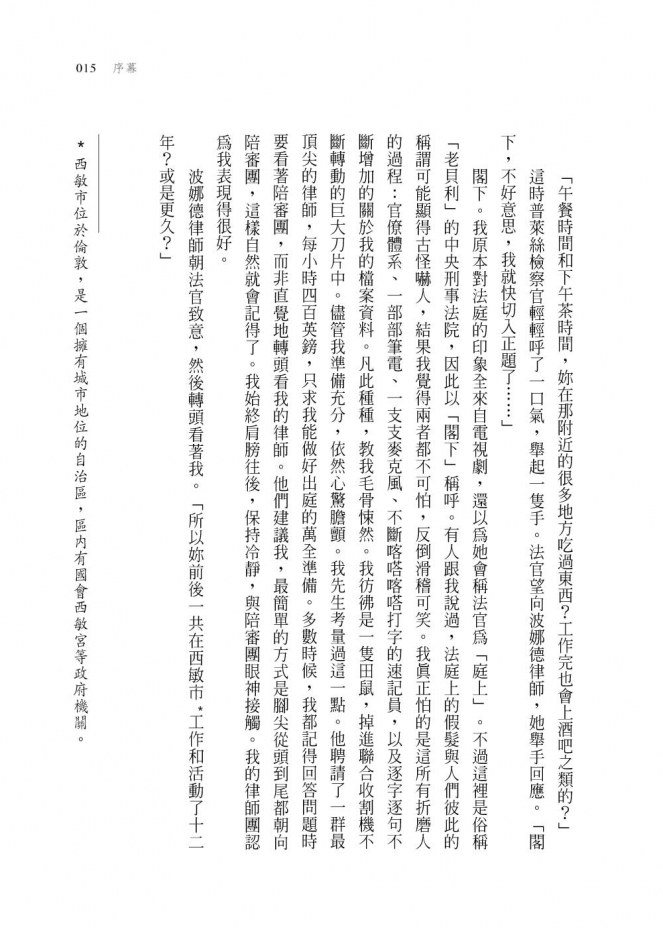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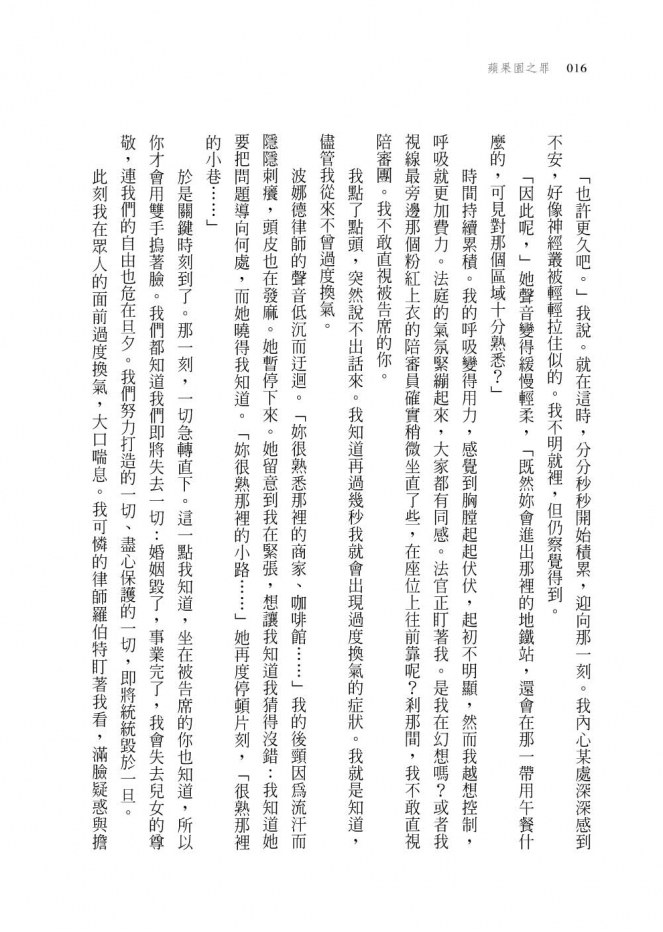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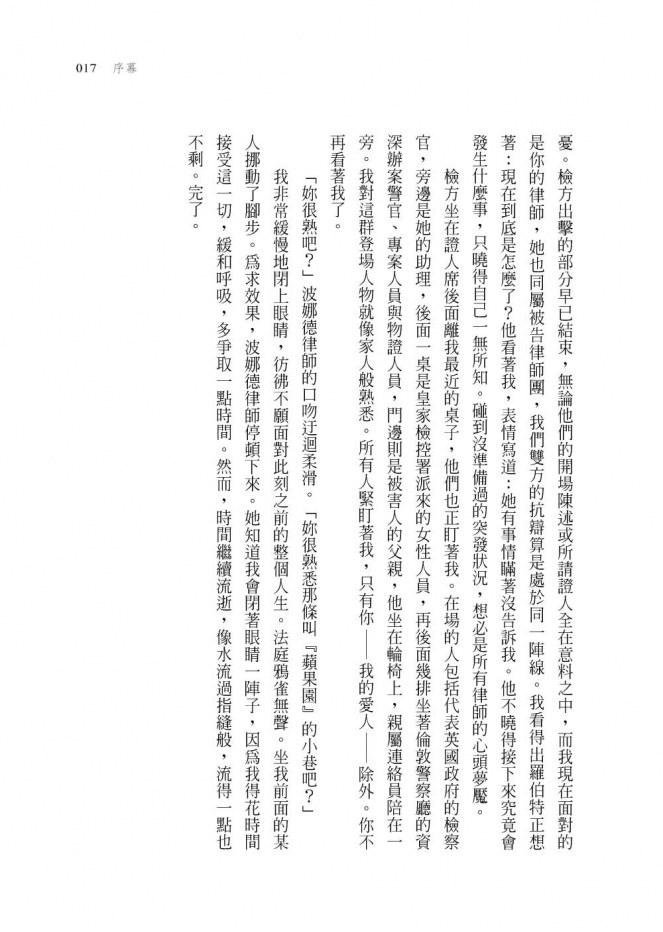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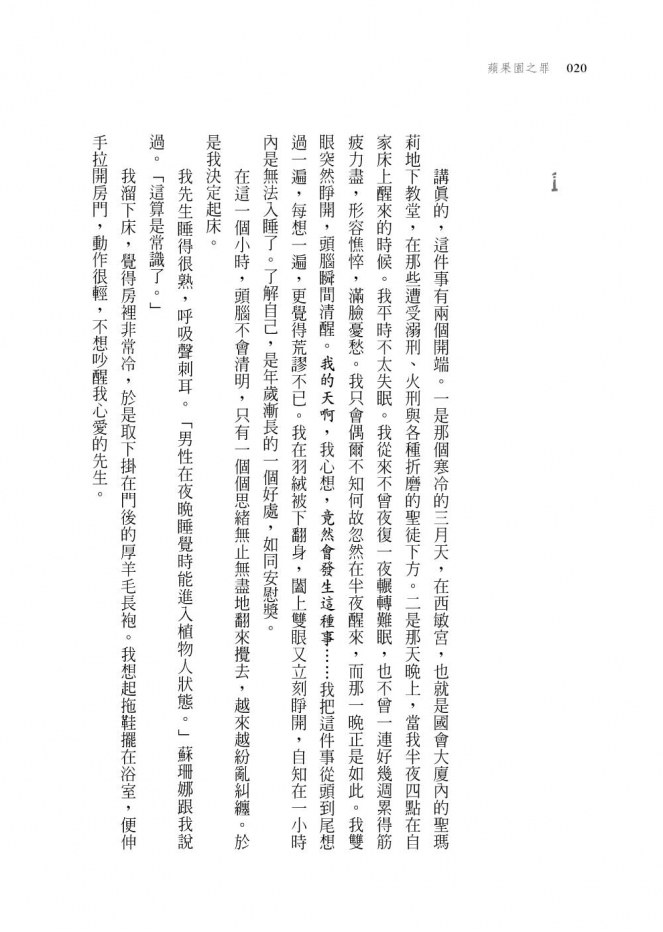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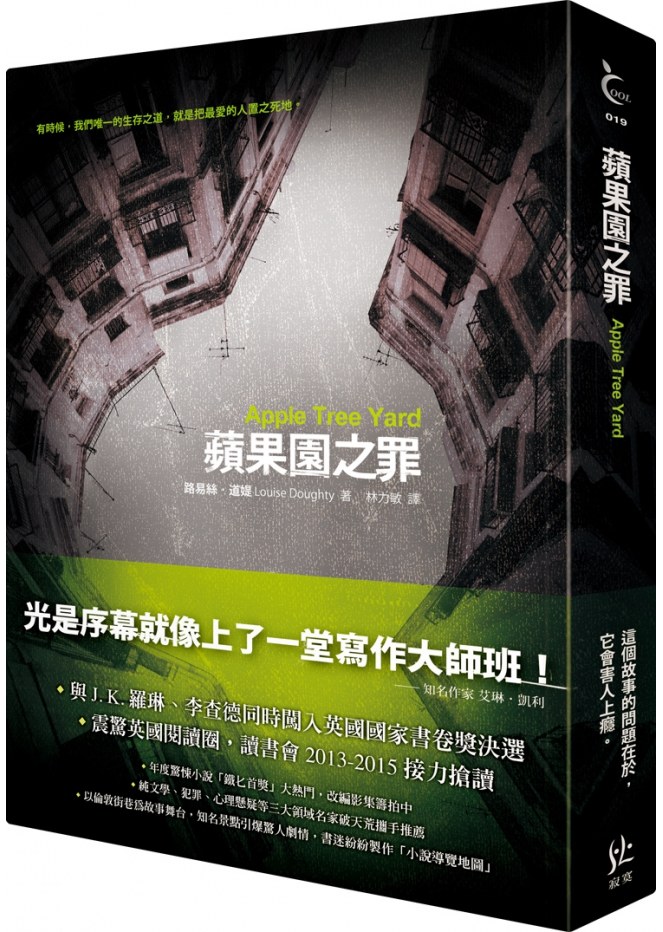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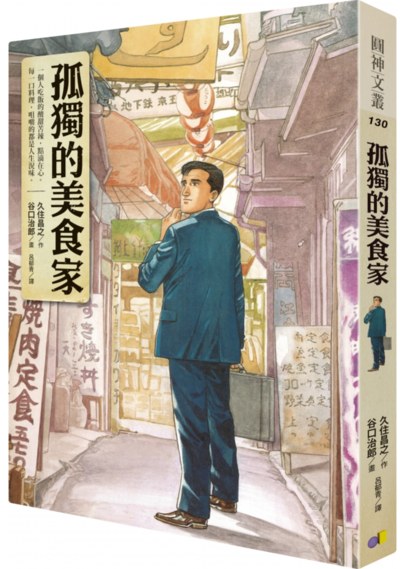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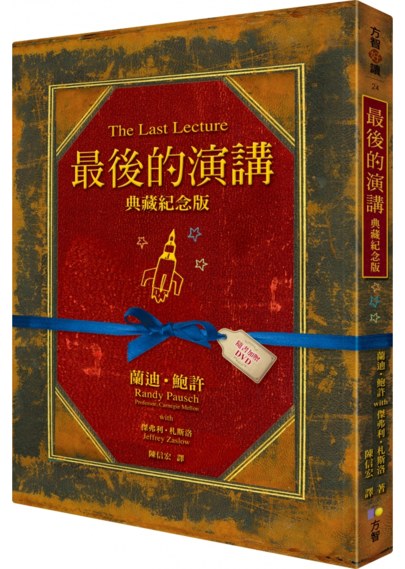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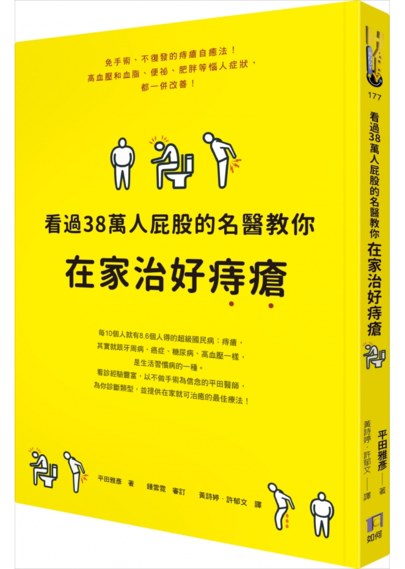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