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一九九○年七月抵達芮達爾大宅的那日。雖然再過兩天才是我的十四歲生日,但我當時相信自己對一切早已瞭若指掌。至少知道幾項基本事實。爸媽破產了。他們已經申請破產,位於康乃狄克州的房子沒了。爸爸經營生意失敗—這是破產的主因之一,這件事也讓他們的關係陷入緊張。我知道媽離開爸爸跟我,回她位於英格蘭的娘家暫住療傷。我也知道爸爸要帶我去西雅圖,尋訪一棟詭異的大宅,讓我看看自己的出身,了解一下家族的歷史。我從未來過芮達爾大宅,也從未見過爺爺或姑姑。爸爸希望我認識自己的親人。這就好像你是一隻雞,某天公雞爸爸拿來一顆蛋擺在你面前,對你說:「你就是從這裡生出來的。」我懂。
我還知道,媽搭機回英格蘭,爸搭機回西雅圖,並非各自過暑假那麼簡單,而是暫時分居的第一步,他們那陣子處得很差。一對夫妻吵久了,不光是在身上留下傷痕,最終還會傷害對方的心,兩人就此崩潰。就算曾經那麼相愛,就算現在仍然愛對方,也是一樣。
學校裡已有好些同學的父母離婚了,他們的狀況我都看在眼裡。有些人吹噓他們可以過兩次聖誕節:禮物加倍,愛也加倍。但即使我那時還小,也能從他們的眼神看出,這不過是自欺欺人。過熱的車輪跑不了多久,因為車軸很快會變彎,輪子再也無法正常前進。遙控車雖然好玩,但是等你發現自己找不到遙控器,就沒那麼有趣了。
那段期間家中愁雲慘霧,銀行收回我們的房子,進行拍賣。爸媽還帶我去現場看拍賣過程,或許他們覺得該讓我見證這難得的人生教訓,但我覺得這麼做實在不智。現場並不像電視上看到的古董車或名畫拍賣那麼刺激,可說是相當無聊:某人先宣布一個價錢,另一個人再遞給他幾張紙條,然後他用力敲下槌子:「這棟房屋由阿拉巴馬州某某公司買下。」
我只覺得失望,不,或許不只是失望而已。我以為爸爸有能力救我們,我以為去那裡可以看到他打敗其他買家,贖回我們的家。我以為他會舉起一隻手,拍賣主持人指指他,問是否還有人要競標—當然是沒有—然後我們就能重新回到正常生活。
但他沒有。我們跟其他人一樣離開會場,雙手插進口袋,裡頭空空如也。
住進紐哈芬機場附近的汽車旅館那天,氣溫非常高,是七月常見的熱浪。旅館本身並不差,還算乾淨,有個大停車場,泳池周邊圍上高高的鐵柵欄。我一直是家中獨子,所以我曉得該怎麼做。我穿上泳褲,來到泳池邊,泳池還可以,儘管有幾個德國觀光客的小孩在玩一種奇怪的球類遊戲,三個小孩輪流打一顆浸濕的網球,你來我往,網球如飛彈一般輕巧掠過水面。打得非常激烈,我很擔心要是被球擊中,牙齒可能會不保。我喜歡這個泳池,但因為網球老是飛來飛去,我覺得危險,只得跨出泳池,用小推車裡取來的幾條毛巾圍住身體,在爸媽旁邊的塑膠休閒椅上躺下。當時他們倆正吵得不可開交,沒注意到我。
「看看我們的生活。」媽媽對爸爸說,「什麼都沒了。你成天生氣,對誰都不耐煩。」
爸沒吭聲。
「瓊斯,我一直在忍耐。」媽繼續說,「真的忍很久了。我想盡量幫你的忙,但你也得振作啊。瓊斯,我愛你;從某些方面來說,我永遠愛你,不過你得了解,『決定性的一刻已經到來』。」
接下來是一片沉默,沒人說話。我全身裹住毛巾,我想他們應該沒看到我,不知道我在旁邊聽他們講話。我大部分資訊都是這麼來的:悄悄在一旁偷聽。
「妳每次跟我背詩,我就覺得自己像個傻瓜。」爸最後開口了,「這次是誰的詩?又是柯律治?」
「其實是T. S. 艾略特。」
媽難過地搖搖頭。
「你還沒走出那個地方的陰影,」她說,「你總是說已經走出來了,但其實你沒有。無論你去哪裡,總是擺脫不了它。」
「很難擺脫。」他說。
「不。拆解原子很難,但面對自己的過去,是你必須做的事。我已經答應讓你帶崔佛去看看你成長的地方,去芮達爾大宅看看。讓他看看你是誰,為什麼成為這樣的人。或許你也會在那裡找到自己,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就會明白各自站在什麼樣的位置。」
那天晚上,趁爸爸在沖澡,房裡只有我和媽,我再次求她跟我們一起去芮達爾大宅。
「噢!崔佛,」她說,「你的人生經歷太少,根本不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也許我是不懂,但我記得當時想得很清楚,至少我明白兩件事:第一,爸爸一定是在哪裡走岔了路,媽因此不再愛他;再來呢,我有辦法讓他變好,重新振作起來。我相信只要我圓滿達成任務,不必等到秋天,就能把父親送回母親身邊,到時他會變成正常、慈愛的人,如同他倆初次相見時那樣。
然後呢?嗯,到時只能看她的心是否還在他身上。一個孩子能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了。
* * *
我不喜歡芮達爾大宅。這房子時不時嘰嘎一聲,聽起來像哀鳴或嘆息,彷彿有生命似的,又像是在風中搖晃的老樹,哀嘆不由自主的命運。
我偷偷溜下樓,不想驚醒爸爸,心想他可能在午睡。我走出去,站在前廊上,迎面是白花花的陽光,酷熱異常。日頭像是拿光線當武器,正使出全力擊潰這間大屋;接近傍晚的熾熱陽光讓我難以看清周遭的一切。也因為這樣,我才沒留意到身邊有人。
「你是誰?」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嚇了一大跳,舉手放在額上遮住光線,瞇起眼睛,看聲音打哪兒來。我看到木頭搖椅上坐著一名老人,旁邊的小茶几上放著兩個杯子,和一壺看起來像是檸檬汁的飲料。老人滿像大廳那幅畫像上的伊萊賈.芮達爾,白髮像是一條條糾結的粗繩,滿臉倦容,鼻子跟耳朵特別大。霎時間我以為他就是伊萊賈.芮達爾,但是不可能。邏輯和常識告訴我—現在可不是在拍恐怖片—這人是山謬爾爺爺。
我推測是我爺爺的這人表情糾結痛苦,身體在椅子上挪了挪,拿出一條手帕揩拭額頭。他想必覺得很熱,因為他穿著黑長褲、黑色T恤,陽光最愛折磨穿黑色衣服的人。
「你是誰?」他又問了一次。
「我是崔佛。你是山謬爾,對嗎?是我爺爺。」
「我想是吧。」
「我是你兒子的兒子,瓊斯.芮達爾的兒子。很高興認識你。」
我往前走幾步,這時注意到他T恤上印著幾行字: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但我們在深山裡墜機,我只好吃了祂。
「真好笑。」我說。
「什麼?」
「你的衣服啊,好好笑。」
他陷入沉默,就像大多數老人那樣,不斷反芻。「反芻」一直都是我最喜歡的字眼,山羊跟牛都會反芻,先咀嚼食物、嚥下肚子、再吐回嘴裡繼續咀嚼,再嚥下去,反覆好幾回。所以如果你不斷思考某件事,等於把某些想法嚥下去,再吐回嘴巴,反覆思量。直到現在,我仍然喜歡這個意象。
「我想要一件這樣的T恤。」我最後說出這麼一句話。
山謬爾爺爺低下頭,拉起前襟像是要看上面的字,想想還是算了,聳了聳肩。
「我的衣服是賽琳娜買的。」
「我可以喝點檸檬汁嗎?」
他考慮良久,然後倒了一杯遞給我。我在他身旁坐下,兩人不再說話。我們都在反芻,這完全是禪的境界。太陽熱辣辣地照射在我們身上,我們喝著檸檬汁。喝光以後,他重新斟滿兩杯,於是我們繼續在日頭底下曝曬。我忍不住想,要是現在在家—當然前提是爸媽能夠維繫這個家,讓我有家可回—我可能在看棒球轉播,或者看書,總之在殺時間,但絕不會是在反芻。我猛然驚覺,莫非我遇到了地球上最有智慧的人?爺爺不像大多數成年人一樣,不停地問問題,問完後又不肯聽我回答。他也不會引用自以為有趣的奇聞軼事,甚至不關心我是否好好利用時間,也沒叫我擦防曬油。我們坐在一起,就那樣坐了快一個小時,無事可做,直到賽琳娜走出大宅的雙開大門,來到門廊上叫我們為止。
我居然沒發現她走近身旁,實在教我訝異,這房子很容易發出吱嘎聲,照理會聽到她從走廊上走過來才對。我往下看,發現她已經脫掉靴子。噢,難怪沒聽到,用不著大驚小怪,光著腳走路當然沒有聲音。我想移開視線,但辦不到。她的腳真美,形狀和尺寸恰到好處,微彎的足弓十分優美,腳趾細緻,塗上亮藍色指甲油,令人目眩神迷。我對自己說不要一直看,但顯然沒能成功,因為她笑著對我說:「我在家一向光著腳走路,這樣才能維持優美的體態。」
「當然囉。」我回答,因為我已經快十四歲,忍不住有生理反應;而這就是快滿十四歲又會勃起的男孩會說出口的話。
「去洗個手準備吃飯吧。你已經見過爺爺了。老爸,你對崔佛好嗎?」
「我請他喝檸檬汁。」山謬爾爺爺說。
「是嗎?嗯,你人滿好的嘛。」
「他喜歡我的T恤。」
「唔,其實把上帝跟吃掉同類放在一起,好像沒什麼關聯,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那不能叫吃掉同類,」我希望讓賽琳娜看看我有多聰明,「首先必須是同類,才叫作同類相殘。所以嚴格說起來,吃掉上帝不能算同類相殘。我的意思是,假如附近真有個神可以吃的話。」
「你好聰明喔!聰明的崔佛。」
「就叫賽琳娜。」我脫口而出。
「沒關係,你可以跟我開玩笑,用不著不好意思。大聲一點!」
「就叫賽琳娜。」我順從她的要求,聲音大了些。
「哈!」爺爺大叫一聲,猛拍自己的大腿,跟著喊:「就叫賽琳娜!」他聲如洪鐘,頭朝後一仰,開始笑個不停。
「真有你的!爺爺居然跟你同一國,拿我開玩笑。」她說。
等爺爺安靜下來,她說:「好啦!兩位小朋友,快去洗手。」
* * *
賽琳娜。藍指甲的腳趾、柑橘清香、一雙亮灼灼的貓眼。
餐桌上堆滿了一盤盤食物,四個人絕對吃不完。有剛烤好的麵包(廚房裡熱氣蒸騰,充滿麵粉發酵的味道)、自家炸的炸雞、切成三角狀的西瓜、蘿蔓沙拉和馬鈴薯沙拉、蒸玉米棒、甜豌豆、一壺檸檬汁,裡頭插了幾枝迷迭香—這是賽琳娜的獨門絕招。
「哇!」我說。
「手邊有什麼就隨便弄弄。」
爺爺坐下來,賽琳娜從櫃子裡拿出一個藥瓶。
「上樓去叫你爸爸好嗎?」她拿出兩顆藥丸放在爺爺面前,一面對我說。「我跟他說晚餐已經好了,但他一直沒下來。」
「吃藥。」我離開餐室時聽到這一句。
我走上樓,敲了下房門,就進去了。爸爸坐在床沿,雙手捂住臉,身體往前傾。他已經換上乾淨的卡其褲,依舊穿著帆船鞋,這是他唯一會穿的鞋,除非換上那套西裝,就會改穿一雙黑色平底皮鞋。但我注意到他穿著一件乾淨的襯衫,一定是媽媽替他打包的,因為爸生性邋遢,搞不懂要怎麼熨出袖口的折痕,也不懂何以要這麼熨。我進房時,他抬起頭看我,我玩笑似的往後跳。爸已經刮掉鬍子。就那麼簡單,賽琳娜叫他剃,他就剃了。這也證明我的理論是對的:媽故意不催爸爸刮鬍子,如此一來,她只要看他一眼,內心就會湧上一陣厭惡;而爸爸呢,根本不是存心要留鬍子,只消媽說一聲,他會二話不說馬上刮乾淨。爸根本不曉得自己也是宣判婚姻死刑的幫凶。
爸沒了鬍子,看起來年輕得多。原本長滿濃密鬍鬚的下巴,如今膚色蒼白,但臉頰、前額和耳朵都曬成棕色,看上去有點像浣熊。他那樣坐著,身上穿著筆挺的白襯衫,剛洗過的頭髮梳得一絲不亂,簡直像個小孩。我為他感到難過,覺得自己好像突然闖進他房間,硬逼他去跟大人同桌用餐,或者根本是要逼他跨進毒氣室。
我試圖開玩笑,便說:「要不要說說臨終遺言?」爸卻開始顫抖。
他站起來,深吸一口氣,伸出手臂環抱我肩膀,帶我走出房間。
「答應我,晚餐時多講點笑話。」他說,「因為我只覺得想吐。」
我不曉得爸爸和爺爺處得怎麼樣。來到這裡之前,山謬爾爺爺從未在我的生活中出現,平常連提都很少提,彷彿他已經死了。我沒跟他說過話,也沒看過他的相片,或爸爸其他家人的相片。我從來不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不過那時候對我來說,爸爸本身也是個謎。我們很少相處,就算偶爾在一起,也不大說話。有時他會提起童年時候的事,但往往說到一半突然住口,像是不太願意記起那段日子,又像是已經關上門,把那部分的人生擋在門外,再也不願開啟。
我攙扶他下樓(要不是我扶著他一階階走下來,他隨時可能兩腿一軟向前仆倒),賽琳娜和山謬爾爺爺抬起頭來。
「噢,這樣多好看!」賽琳娜看起來興高采烈,「我就知道在那叢亂草底下,是一張俊俏的臉。老爸,看看他是誰。是瓊斯老哥啊!」
爺爺和爸爸小心打量著對方。
「哈囉,爸爸。」我爸說。
「哈囉,兒子。」山謬爾爺爺敷衍似的點了一下頭,根本沒抬眼看他。
「我最喜歡親熱溫馨的重逢啦!」賽琳娜尖聲說,「嘿,你們可不要太激動啊!待會兒有的是時間聊。瓊斯,坐下一起吃吧。」
我們各自坐下,開始傳遞食物,沒人說話,餐桌上一片死寂,只用手勢示意、微笑、點頭,大夥兒彬彬有禮。然後是進食的聲音:咀嚼、吞嚥、咕嘟一口喝下,偶爾拿起餐巾輕拭嘴角。除此之外,只有風扇的聲音。
最後爺爺探身向我,輕聲說:「給我一點西瓜。」我把盤子遞過去時,才發現他左手缺了兩根手指,食指連根齊斷,中指上面那根指節也不見了。
「阿弟打電話來說,他有事絆住了。」賽琳娜突然宣布這項消息,指了指那個空位。其實我早就注意到那個位置,卻不敢開口問。
「阿弟是誰?」爸爸問。
「笨,我男朋友啊。」賽琳娜說,「不然這些年寂寞的夜晚,我要怎麼度過?」
「我不知道妳有男朋友。是認真交往嗎?」
「瓊斯老哥,以我的年紀,任何關係都是認真的呀。」
「妳幾歲了?」我正在想爺爺似乎沒跟上聊天內容,他就突然冒出這麼一句。
「老爸,問女生這種問題,可不太禮貌。不過顯然你不記得我是何時來到這世上,那我就告訴你。我比瓊斯老哥年輕五歲,他今年三十九歲。爸,這樣你會算嗎?」
「我當然會算。」爺爺顯得很不高興。
「你不能只吃西瓜。」
我轉頭看爺爺的餐盤,西瓜堆得高高的,沒別的東西。
「可是我愛吃西瓜!」爺爺大聲抗議。
一時間我只想捧腹大笑。爺爺很像連環漫畫上的人物,手掌大,頭顱也大,頭髮披散在臉上,剛剛他說「愛吃」兩字時,手臂舉高,引得我目不轉睛盯著他的斷指瞧。
「看到了沒?」賽琳娜對爸爸跟我說,「這就是我每天要面對的情況,他有時候滿正常,有時什麼都記不住。他得把事情寫在紙上,不然就會忘記,而且就算寫下來……」
「我愛吃西瓜!」爺爺繼續抗議。
賽琳娜對我們做了個鬼臉,意思是真教人受不了。
「吃點雞肉。」她說。
「我不喜歡雞肉,」他開始抱怨,「雞肉有筋。」
「爸,所有動物都有筋,那是肌腱。」賽琳娜說,「有肌腱和韌帶,也有肌肉和內臟、纖維和結締組織。骨組織是一種結締組織,這個你知道吧,崔佛?我敢說你一定在生物課學過。我們以為骨骼是身體的鋼條,但其實骨頭是柔軟的器官,非常有彈性,除了幫助組織連結,也具備其他重要功能,比方同時製造紅血球和白血球。」
餐桌上一片沉默,似乎全被賽琳娜那段關於骨骼的即席演說嚇到了。不過也許她是故意的,故意用這種方式化解山謬爾爺爺對筋的抱怨。
「就好像骨骼有彈性,」她繼續往下說,「我們和別人的關係也應該有彈性,才能和諧相處。我們得承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變數,不斷在變化,有時候不得不劃下句號。瓊斯老哥,你最近剛跟芮秋分居,不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嗎?」
「不算真的分居。」爸說。
「不算分居?那麼算是什麼?她在英格蘭,而你在這裡,在我看來距離非常遙遠。」
「我是說,法律上我們還沒分居。」爸爸瞄我一眼。
「瓊斯老哥,法律是用來調節經濟,沒辦法處理心的問題。不管法律上怎麼樣,你跟妻子是分開了,我說錯了嗎?」賽琳娜說。
「可是他們還會在一起。」我衝口而出,賽琳娜轉過來看著我。
「只是暫時分開,」我支持爸的說法,「不會永遠都這樣。」
「如我剛才所說,關係是充滿變數的東西,」她聳了聳肩,彷彿表示我是在支持她的論點。「老爸,請你吃點雞肉,你需要蛋白質。」
「我不喜歡雞肉。」
「你必須吃點東西。」
「這棟房子鬧鬼嗎?」我只想轉移話題,不想再聽肌腱了。
賽琳娜繼續吃東西,過了一會才回答:「你怕鬼嗎?」
「不怕。」
她繼續吃馬鈴薯沙拉,然後指了指那盤炸雞,對爺爺說:「吃雞肉。」
「有筋。」他撇撇嘴。
「孩子,為什麼突然問鬼的事?」
「因為我聽到怪聲,應該是人的聲音。」
「這樣的房子會跟你說話的,」賽琳娜說,「它有很多事要告訴你。」
「比方什麼?」
「芮達爾大宅快要一百歲了。」賽琳娜聳了一下肩,叉了塊東西送進口中。「想想這層地板有多少人走過,地板認得這些人,我可不認得。晚上有人在樓上的跳舞廳跳舞,你爺爺聽見過。不過他有老年癡呆症,所以沒人當一回事。」
「所以芮達爾大宅現在鬧鬼?」
「這要看你如何定義『鬧鬼』囉。」
「賽琳娜,拜託別再說了。」爸爸說。
「班很緊張。」爺爺喃喃地說,然後站起來走到電話桌旁,拿起筆在便利貼上不知寫些什麼,邊想邊寫,神情很專注。
「他在做什麼?」我小聲問賽琳娜,「誰是班?」
「他什麼事也記不住,所以習慣把事情記在便利貼上。都是莫名其妙的廢話,沒有一句有意義。人家說阿茲海默症後期,頭腦會變得像吸飽水的海綿一樣,想像一下吧。」
「這是要緊事,」山謬爾爺爺哇拉一喊,抬頭看著天花板,終於寫完了,回到餐桌上來。
「剛才說到哪裡了?」賽琳娜說,眼睛骨碌碌地轉了兩下,「喔對了,說到鬧鬼的事。瓊斯,你還沒跟崔佛聊過那件事嗎?」
「聊什麼?」我問。
「聊存在和意識的狀態啊。你爸跟我小時候吃晚餐時經常聊到這個,我們的母親最愛跟我們說這個。我的意思是,我們有那麼多不明白的事,怎麼能自以為很懂?老爸,我真的必須逼你吃點雞肉。」
賽琳娜舉起叉子叉一塊炸雞,放到爺爺的盤子裡,爺爺屁股往後挪,呼一下把雞腿掃到桌面上。
「屋子裡有那種東西嗎?」我問。
「先說說你對『東西』的定義。」賽琳娜說,「我們必須用一套術語來表達。除非先針對字的定義達成共識,不然討論起來會非常混亂。」
「賽琳娜,閉嘴!」爸大聲咆哮,「我是說真的。妳嚇到他了。」
「我認為你太小看崔佛了,他不像你以為的那麼無知。是他問我的。」
賽琳娜起身,從老式大火爐旁的長桌上拿來一盒火柴,把火柴盒扔在我面前,重新坐下。
「這間屋子用來躲藏的地方可多了。」她說,「當初在蓋芮達爾大宅的時候,很多東西都教人害怕。當然不是印第安人,西北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性情溫和,不管是跟自己人或白人交易,都是高高興興的。不過這一帶有小偷跟盜賊,專門對有錢人下手,一有機會就綁架富豪,叫家人付贖金。至少伊萊賈是這麼認為。不過他一向討厭跟人來往,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實很難說。總之,這棟房子有很多祕密通道跟小密室,好讓伊萊賈覺得安全,他們說這是『神父密室』,早在英國的宗教改革運動時就有這個詞,那時天主教徒會把神父藏起來,以免被新教當權者抓到。你知道宗教改革時期,他們在牆壁裡的小密室找到神父,會怎麼做嗎?」
「會怎麼做?」
「吊死他,或者活活把他燒死。當然吊得好也很刺激,不過沒什麼比得上烤生肉的氣味在空氣中飄散,再從密室逼出一、兩個神父來。我想你應該能夠想像。」
「賽琳娜!」爸爸喝斥她。
「芮達爾大宅有一道祕密樓梯,」賽琳娜一口氣說下去,「我不知道在哪裡,那是祕密,不是嗎,瓊斯?媽媽只告訴你,我那時還太小,她不肯讓我知道。崔佛,這裡有一道祕密樓梯,要是你能找到樓梯,劃亮火柴,你會在一閃即逝的微光中看到一個鬼魂,那就是芮達爾大宅的魂魄。但我們不該說這個的,老爸會不高興,他覺得談論鬼魂是不對的。瓊斯老哥,你還記得老爸那天晚上手握斧頭跑上樓梯嗎?」
「早知道我就不回來了。」爸爸一臉惱怒,咕噥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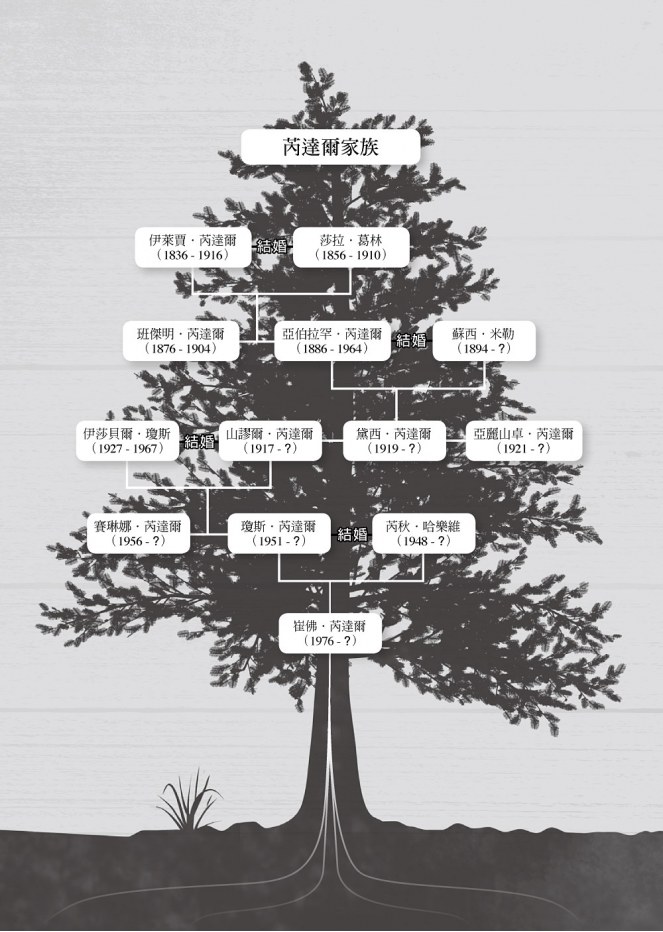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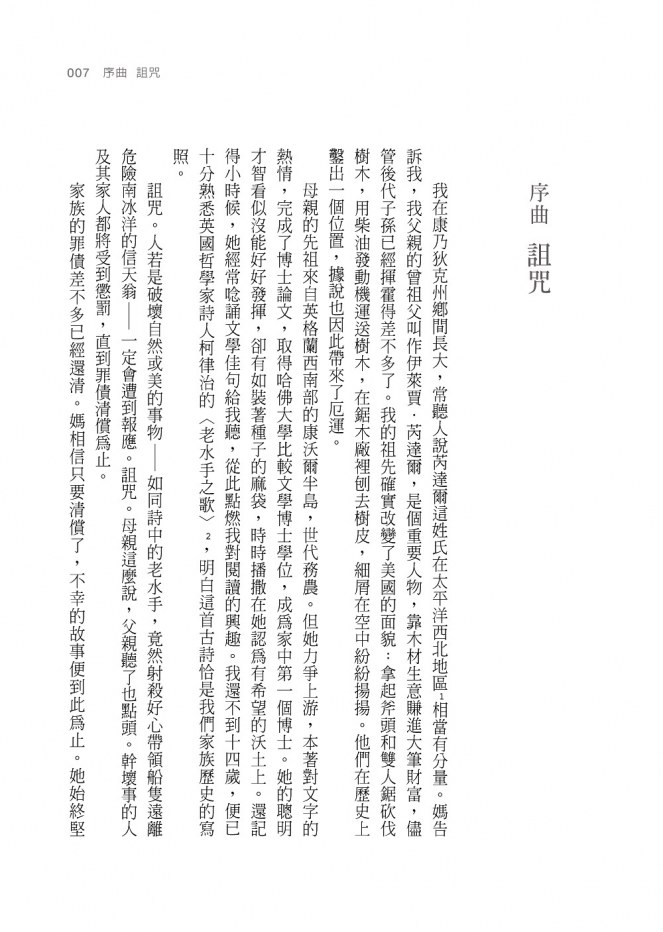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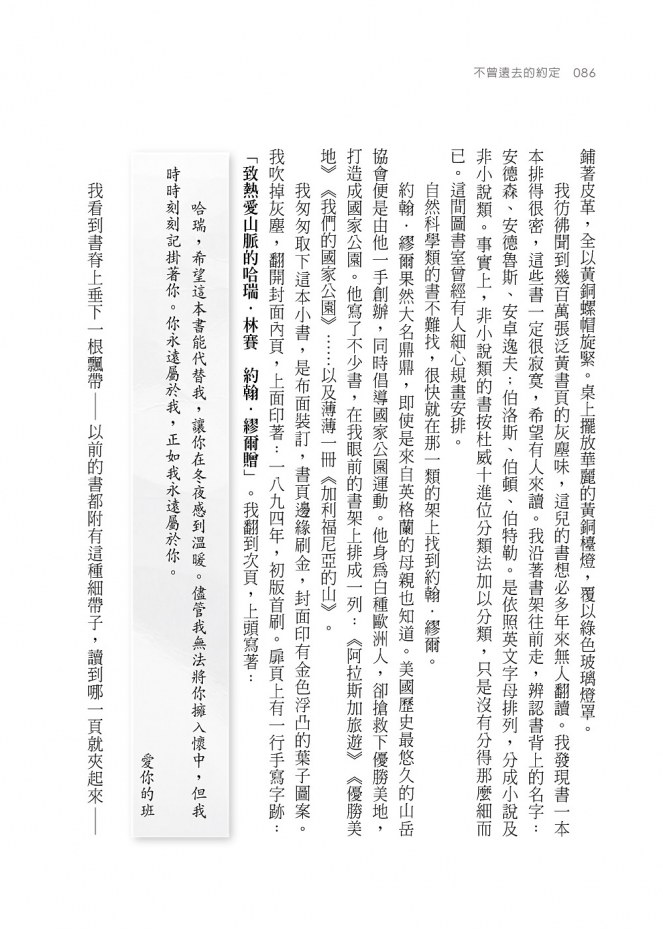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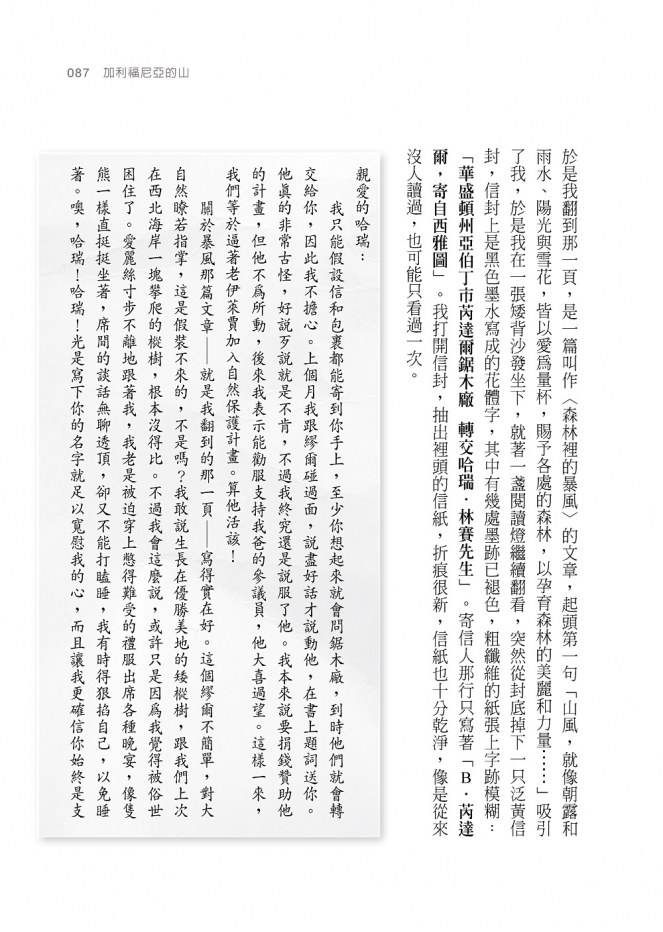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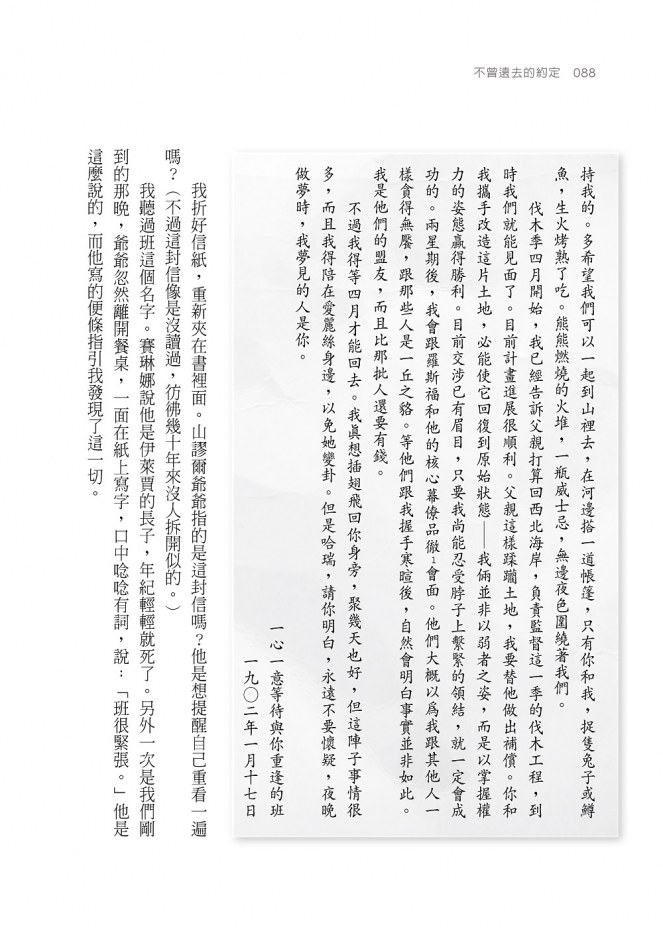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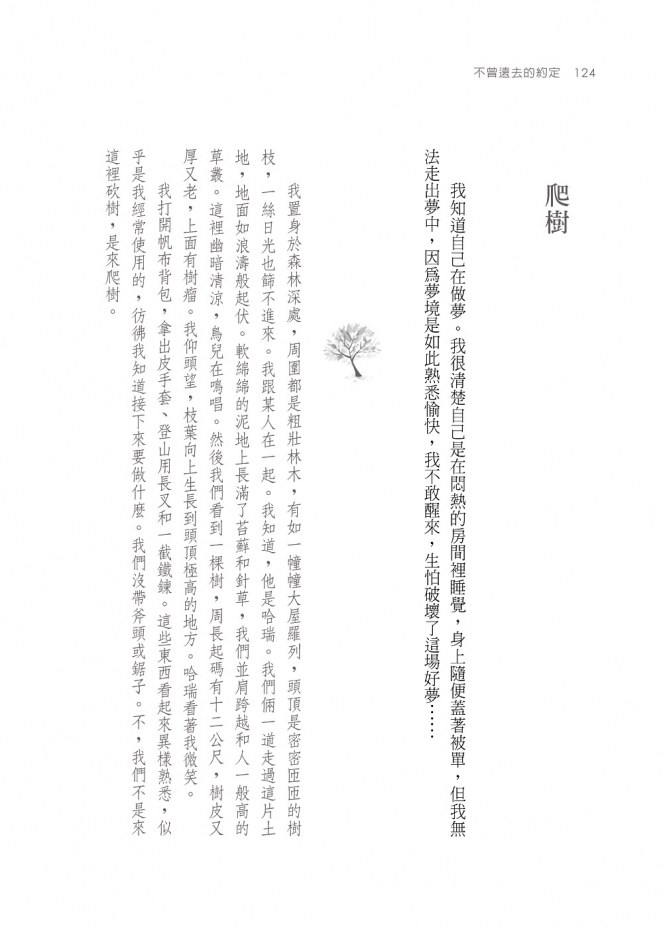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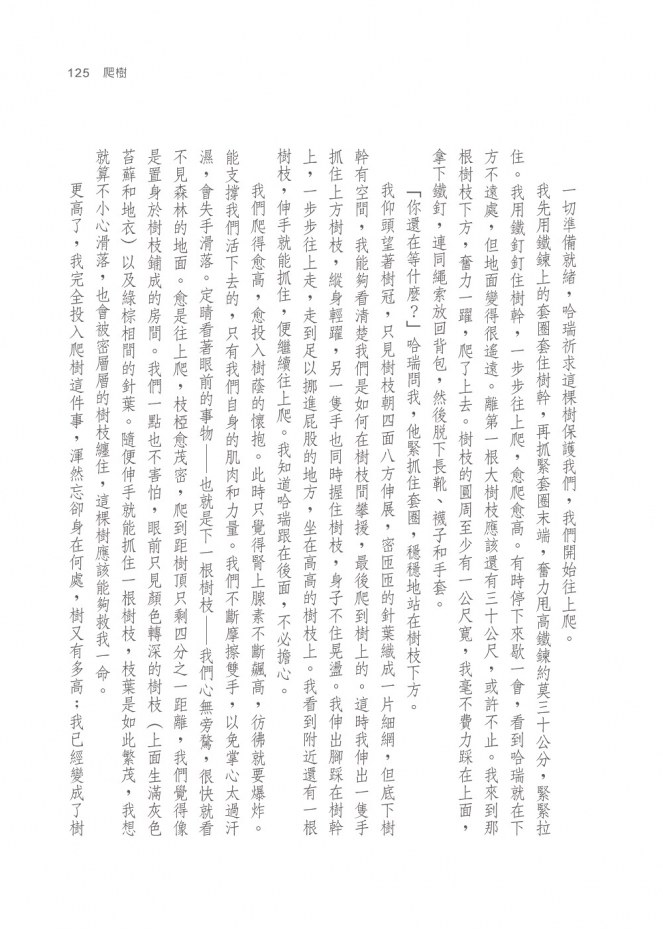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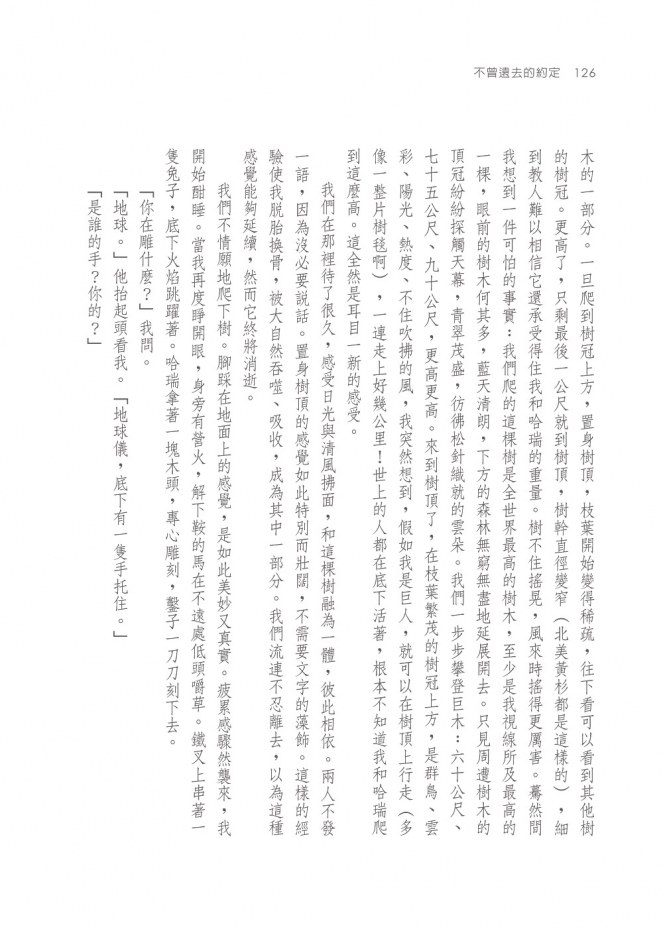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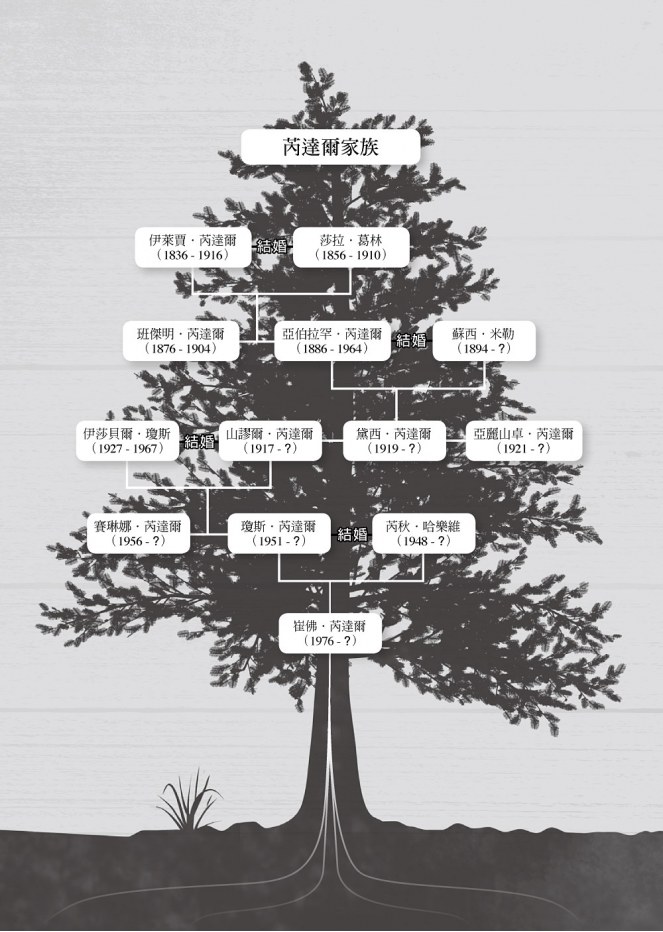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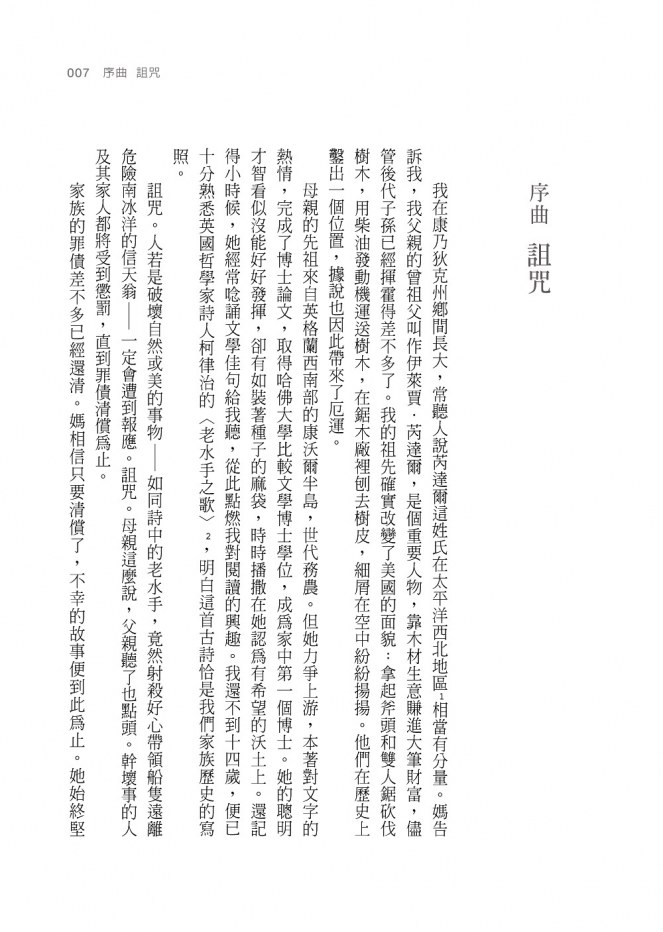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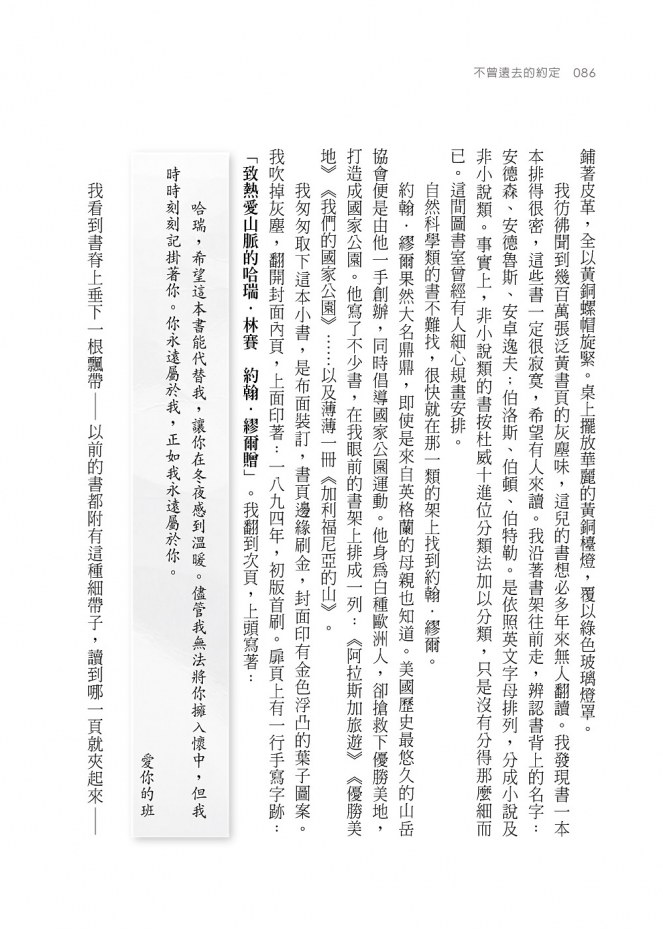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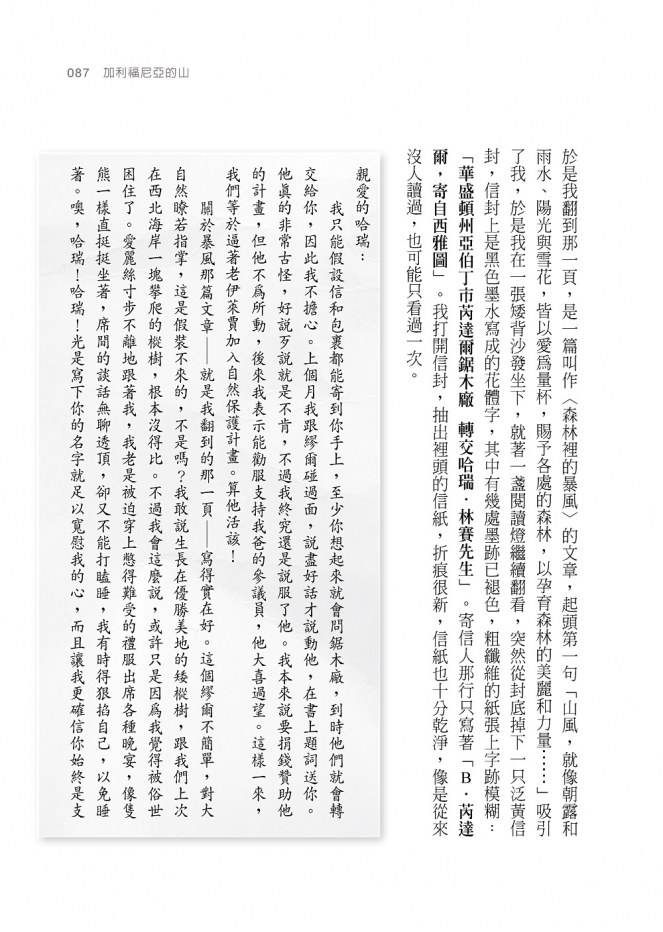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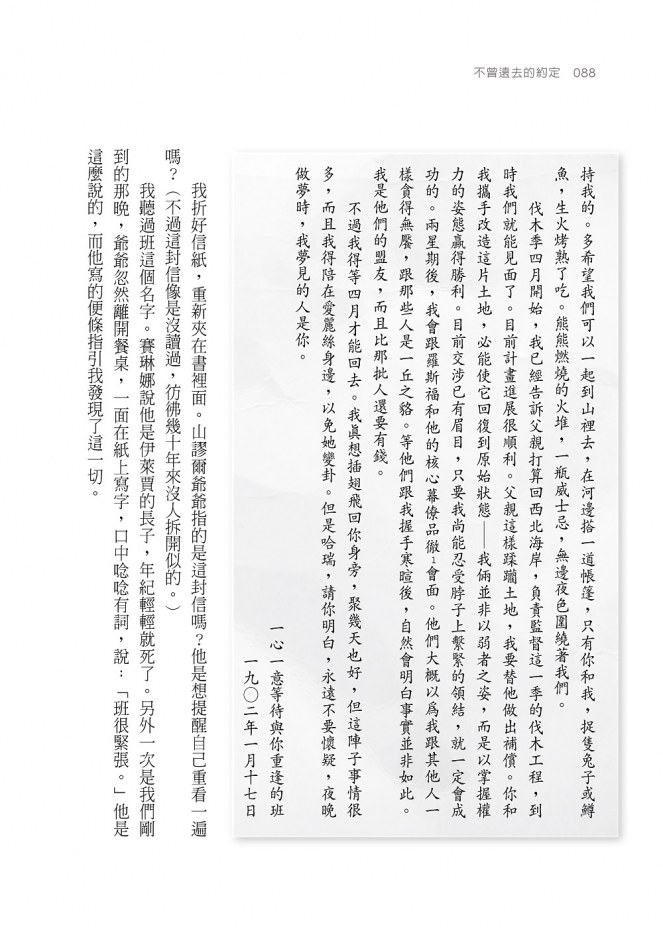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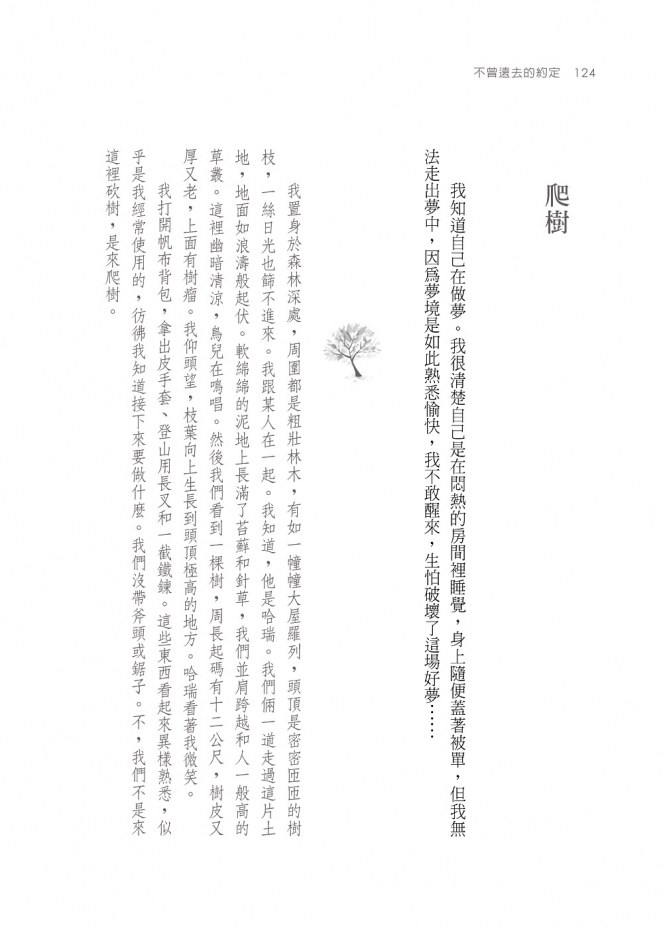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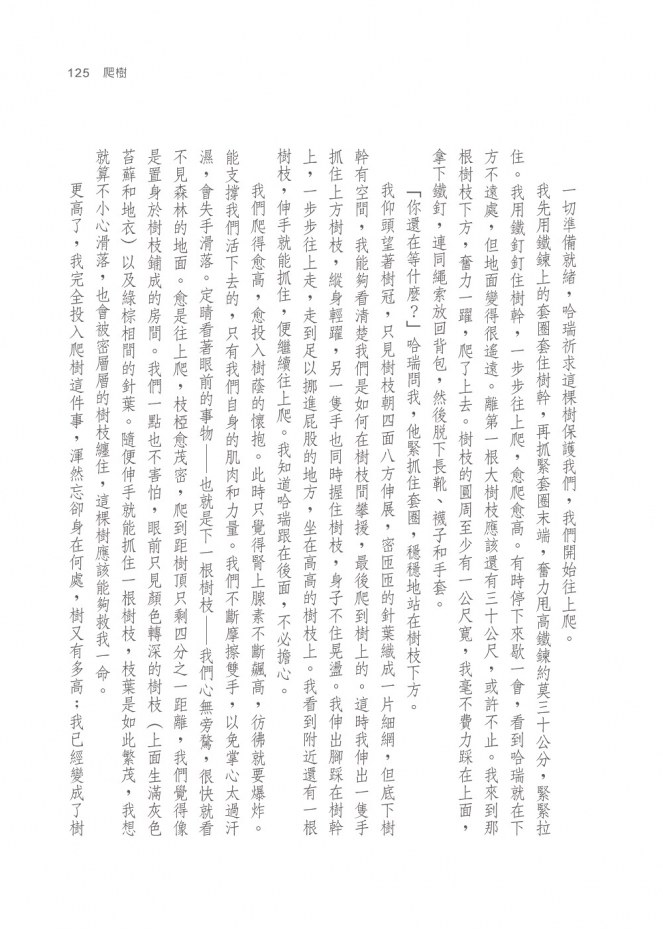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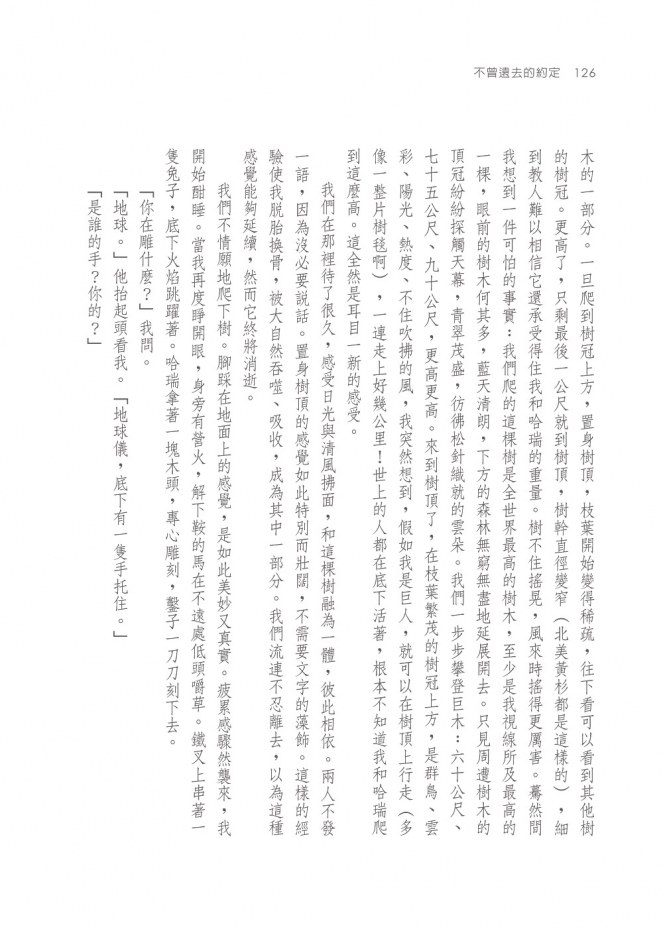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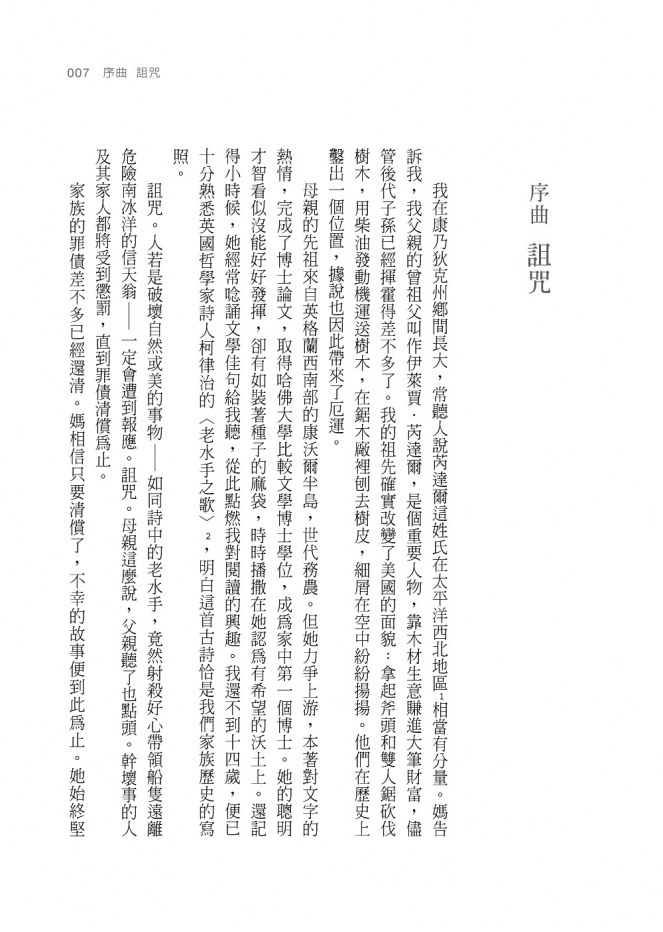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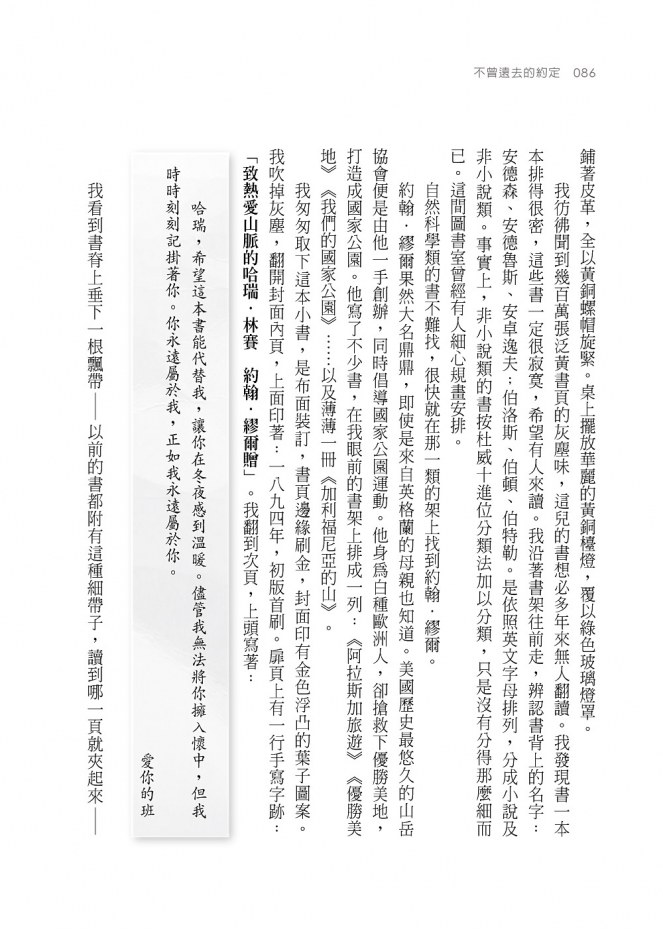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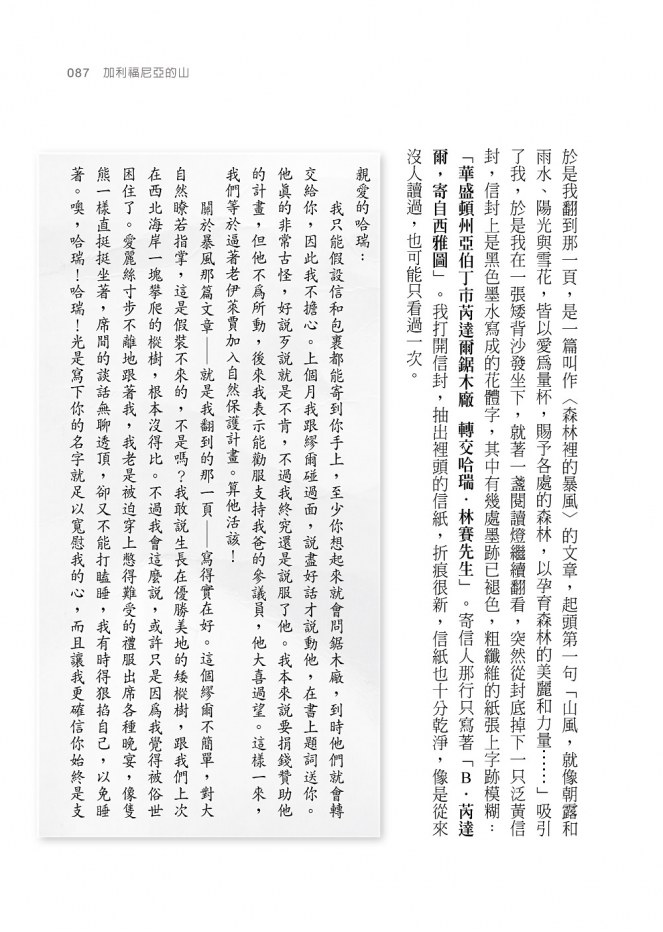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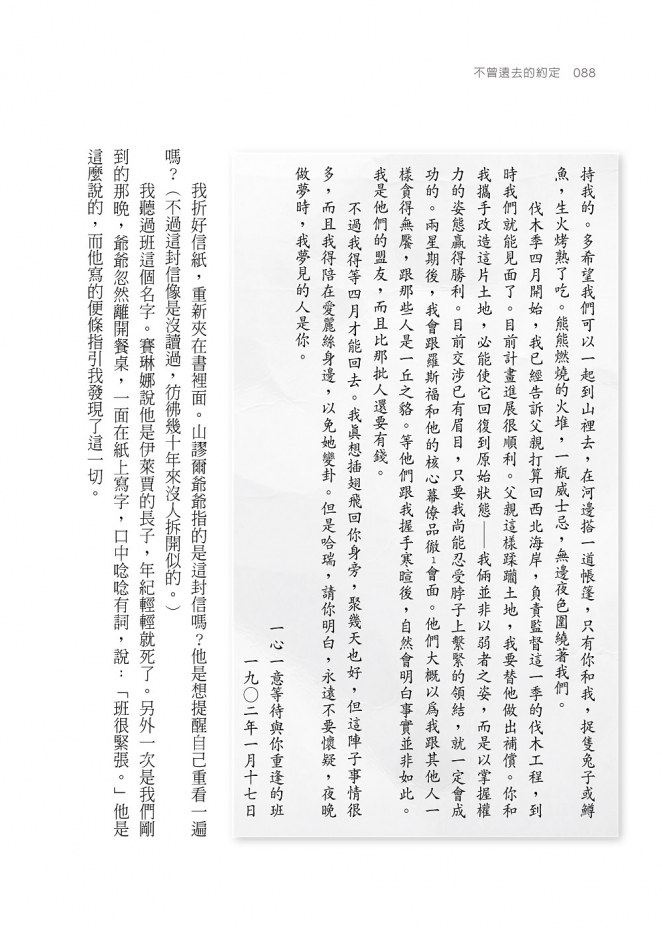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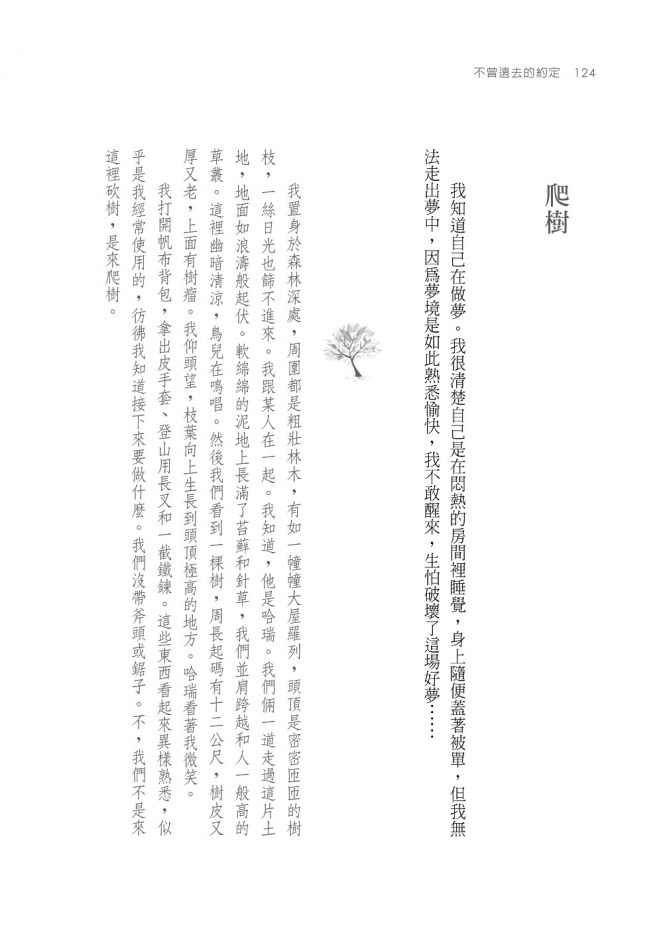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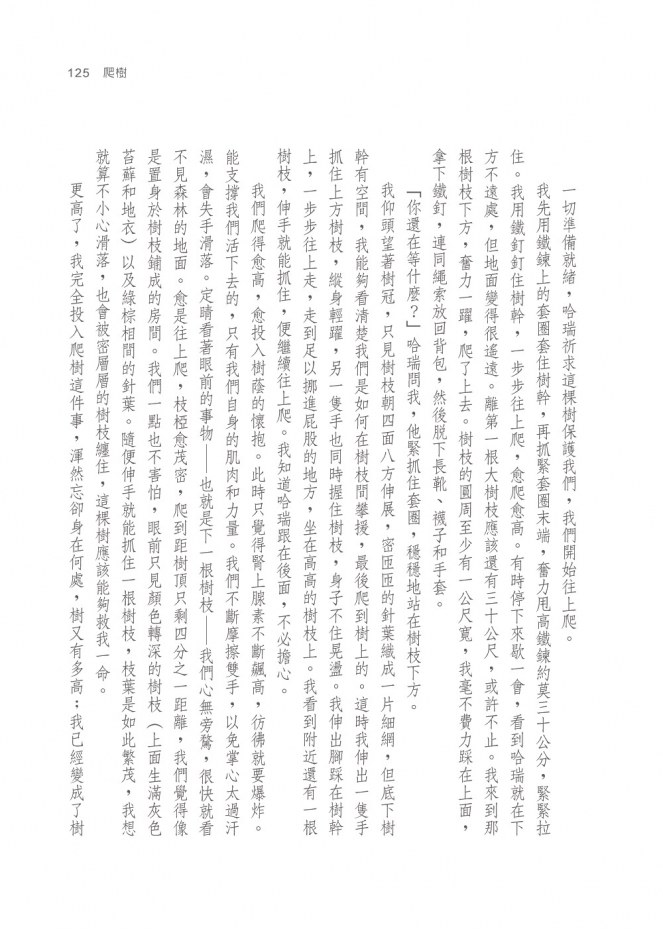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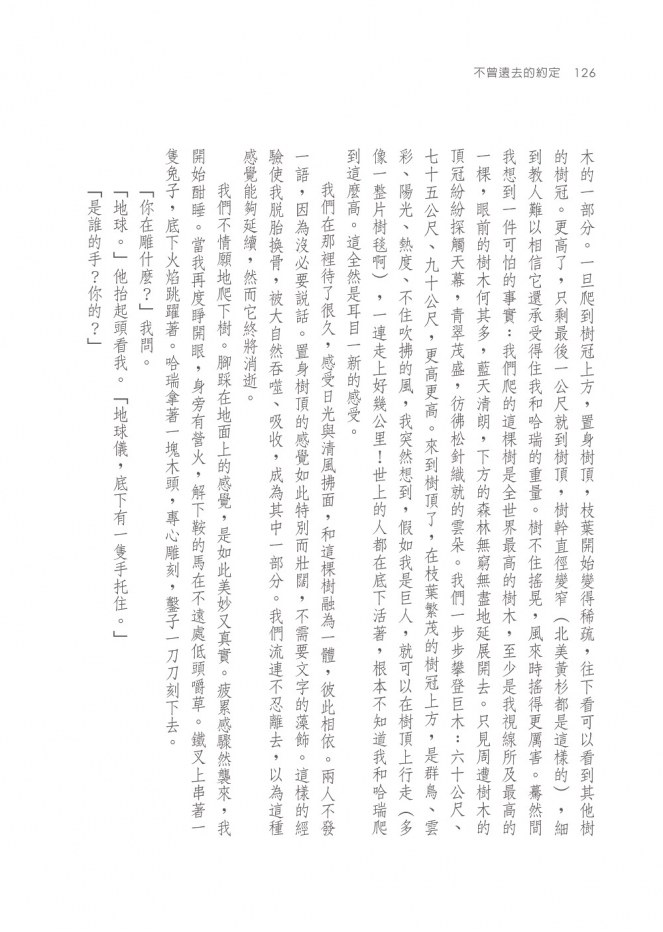



.jpg)
 美國知名暢銷作家,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畢業後以製作紀錄片為業,多年來參與執導、製作與協製,多次獲得獎項。1998年以小說首作《渡鴉偷月》在文壇初試啼聲。2005年推出《單身伊凡》,獲頒2006年太平洋西北書商公會圖書獎,並榮獲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美國知名暢銷作家,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畢業後以製作紀錄片為業,多年來參與執導、製作與協製,多次獲得獎項。1998年以小說首作《渡鴉偷月》在文壇初試啼聲。2005年推出《單身伊凡》,獲頒2006年太平洋西北書商公會圖書獎,並榮獲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