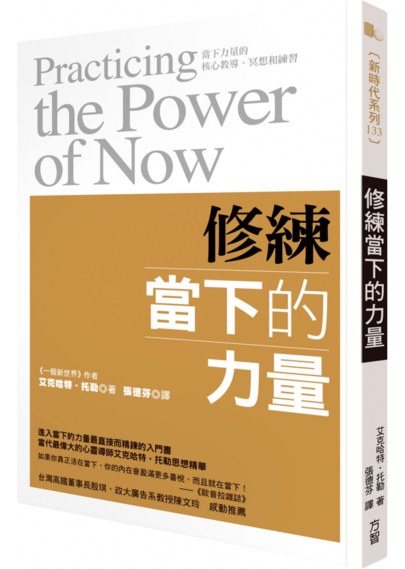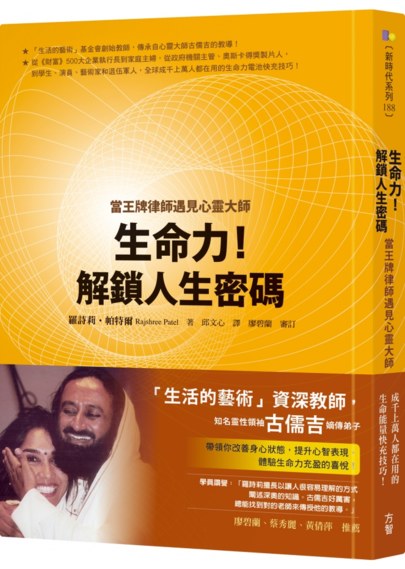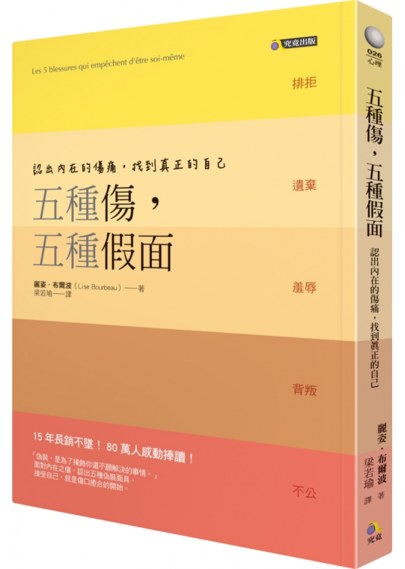1 不想活的行屍走肉──柯塔爾症候群
宣稱「我不存在」的那個人,是誰?
亞當.澤曼醫師永遠不會忘記那通電話。他形容,就像一通蒙地蟒蛇劇團的惡搞來電。打電話來的是一位精神科醫師,他要求澤曼趕緊到精神科病房,有個宣告腦死的病人。澤曼覺得自己像是要被緊急召喚去加護病房,而不是精神科病房。然而他說:「那通電話跟平時加護病房的緊急來電很不一樣。」
病人名叫葛拉罕,四十八歲男性。和第二任妻子分手後,葛拉罕陷入深度憂鬱,試圖自我了斷。他躺進自己的浴缸,把一部電暖器拉到水裡,想要電死自己。幸運的是保險絲燒斷了,葛拉罕逃過一死。「電擊似乎沒有對他造成任何身體傷害,但是幾週後,他開始形成一種信念,相信自己的大腦已經死了。」英國艾希特大學的神經科醫師澤曼說。
那是種頗為明確的信念,也讓澤曼醫師因此經歷了幾次非常奇怪的對話。「瞧,葛拉罕,你聽得見我說話、看得見我,也可以理解我在說什麼。你記得你的過去,也能表達自我。顯然你的大腦一定還運作著。」澤曼會這麼對葛拉罕說。
而葛拉罕卻會答道:「不對、不對,我的大腦死了。我的意志活著,但我的大腦死了。」
更糟糕的是,葛拉罕為他失敗的自殺舉動感到心煩意亂。「他簡直是行屍走肉,或者可說是半生不死,」澤曼告訴我。「他甚至有好一段時間會到墓園徘徊流連,因為他覺得在那裡可以與自己同在。」
澤曼醫師對葛拉罕進行測驗,以了解這個信念的根據。問題漸漸明朗,看來有什麼至關根本的東西偏移了。葛拉罕自身的主觀經驗和他的世界已經改變。他不再覺得自己需要進食喝水,那些曾經帶給他歡樂的事物也不再起作用。「他深吸一口菸,卻一點感覺都沒有。」澤曼告訴我。葛拉罕宣稱他再也不需要睡眠,因為他不睏不倦。當然,他還是在做這些事,他吃飯、喝水、睡覺,但是他對這些需求的渴望以及感受的強度已經大幅削弱。
葛拉罕失去了某些我們都有的特質,也就是我們對自身欲望及情緒的敏銳感受。受到人格解體障礙所苦的病患也常會描述像這樣的情感鈍化或情感扁平,憂鬱症也會造成類似的存在狀態,讓情緒失去邊界,但是這些病患並不會繼續發展出自身不存在的鮮明妄想。在葛拉罕的案例裡,生動情感的消失程度相當極端,所以「根據他在感受上所遭受的變動,使他得到自己的大腦必然已死的結論。」澤曼醫師說道。
澤曼醫師認為在這樣根深柢固的妄想裡,有兩個關鍵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一是對自我和世界的感知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在葛拉罕的案例裡,就是他在情緒上頓失支柱的感受),其二則是失去釐清這種體驗的能力。「在葛拉罕的案例裡,這兩個要件似乎都成立。」澤曼醫師說。
反面證據對葛拉罕的妄想不起作用。澤曼醫師希望能在對話裡讓葛拉罕舉手投降,看清自己的妄想是虛假的。葛拉罕或許會承認自己的腦力在各方面都完整無損,因為他能看、能聽、能說話、能思考,可以記住事情,諸如此類。
所以,澤曼醫師對他說:「葛拉罕,顯然你的心智是活的。」
他會回答:「對,對,心智是活的。」
「心智和大腦有關,所以你的大腦當然是活的。」澤曼醫師會這樣刺激他。
但葛拉罕可不會上鉤。「他會說,『不,我的心智活著,但我的大腦死了,在那次洗澡的時候就死了。』」澤曼醫師告訴我。「可能只差一步就讓他不得不承認你想到的論點是確鑿的證據,但他不會接受。」耐人尋味的是,葛拉罕已發展出如此明確的妄想,他認為自己死了,因為他的大腦死了。而在法定死亡定義排除腦死的時代,他的妄想會不會有所不同?
在醫療實務經歷裡,澤曼醫師只見過另外一個宣稱自己死亡的案例。八○年代中期時,澤曼是英國巴斯的住院醫師,當時他必須治療一名婦女,她動了曠日廢時的腸道手術,深受嚴重的營養不良所苦,身體飽受接二連三的手術摧殘。「她因此變得非常消沉,並形成自己已死的信念,」澤曼說。「從某個奇怪的角度來說,對我而言這似乎是可理解的,因為她經歷的那種創傷太可怕了。她覺得自己死了。」
澤曼醫師在葛拉罕身上辨認出同樣的症狀,診斷他罹患了科塔爾症候群。法國神經科暨精神科醫師儒勒.科塔爾最早確認這種症候群是一種獨特的失調症狀。
我思,故我不在?
走過巴黎第六區的醫學院街,你會看見一排巨大的柱廊,那是法國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典範之作。柱廊構成笛卡兒大學(又稱巴黎第五大學)的一道門廊。出自建築師貢杜安在十八世紀晚期的設計,建築立面恰如建築師所希望的那樣引人注目,同時又讓人感到開放,迎人入內。
我走進這座建築物,造訪醫學院圖書館的珍稀手稿區,查看一份關於科塔爾生平的文件。這份文件是科塔爾的友人兼同事安東萬.瑞堤在一八九四年寫成的一篇悼詞文本,那時幾乎是科塔爾過世五年後了。科塔爾一直全心全意在照顧患了白喉的女兒,但是後來自己也感染了同樣的疾病,並因此死於一八八九年。我們對科塔爾的所知大多來自瑞提的悼詞,而其中一份悼詞就藏身在一本皮革裝訂的古老書籍書頁裡,那本書的書背上以法文簡單寫著「綜合傳記」。我翻到悼詞所在的頁次,第一頁題有手寫給當時醫學院院長的獻詞:「致上深深的敬意」,瑞提以名字縮寫署名。
科塔爾最為人所知的事蹟是描述了我們稱之為「虛無妄想」的症狀,但是在科塔爾想到這個專有名詞之前,他在一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的醫學與醫學心理學會會議上,曾提出一名四十三歲女性的病例,首次提到「重度憂鬱性疑病症造成的譫妄」。這位病患宣稱「她自己『無腦、無神經、無胸、無內臟,只有皮膚和骨頭』,所以『無論是上帝或惡魔都不存在』,而且她因此不需要食物,因為『她永生不死,會一直活下去』,她曾要求別人用火活燒她,也多次嘗試自殺。」
不久之後, 科塔爾自創了「否定的譫妄」這個說法,而在他死後,其他醫生以他的名字命名該症候群。隨著時光流逝,「科塔爾妄想」被用來指稱這個症候群裡最引人注目的症狀:相信自己已死的信念。然而,單單「科塔爾症候群」這個專有名詞就代表了一大群症狀,並不見得一定要包含死亡或己身不存的妄想。其他症狀包括相信某些身體部位、器官消失或腐爛的想法、罪惡感、認為自己受人定罪或譴責的感覺;矛盾的是,甚至還包括了永生感。
而「自身不存在」的妄想,向哲學提出一個令人玩味的挑戰。一直以來,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主張「我思,故我在」都是西方哲學的基石,他建立了一套心靈和身體的清晰二元論。其中身體是屬於物質世界的,會占據一定的空間,並在時間內存在;而心靈的本質是思想,並不會延伸到空間裡。笛卡兒所謂的「思」並不意謂思考僅止是「清楚而獨特的智能感受,獨立於感官之外」。根據哲學家湯瑪斯.梅辛革的看法,笛卡兒的哲學暗示了「人不可能誤解自身心智的內涵」。
透過包括阿茲海默症在內的許多失調症狀,笛卡兒的這個想法已經被證偽了,因為阿茲海默症患者常常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科塔爾症候群也是個謎團,梅辛革認為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罹患科塔爾症候群會有怎樣的感覺(哲學家稱之為失調的現象學)。「病人可能不只明確主張自己已死,而且還會說自己根本就不存在。」一個顯然活著的個體主張自己並不存在,雖然這在邏輯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這正是科塔爾現象學的一部分。
我離開圖書館,又回頭踏上醫學院街,轉過身來再看了一眼那蝕刻在柱廊上方石材的幾個大字:「勒內.笛卡兒大學」。在以笛卡兒為名的大學裡研究科塔爾,真有點耐人尋味。與科塔爾同名的妄想症對笛卡兒的概念會有怎樣的說法?科塔爾症候群的病患是不是會說:「我思,故『我不在』?」
對自我的感知是大腦和身體交互作用的產物
「知道血肉之軀之我的這個『我』是誰?即使時間推移,仍對自身有所理解、能夠感知認同的那個人是誰?知道我具有『統我』(自我概念下的各方面)之奮鬥的那個人是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全都知道,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知道。但是那個如此心領神會的人又是誰呢?」
的確,到底是誰呢?美國心理學家高爾頓.奧爾波特這段抒情的沉思說出了身而為人的中心難題。我們可以直覺又熟悉地知道他指的是什麼東西,而這個「什麼東西」在我們醒來時就在那裡,當我們入睡後又悄然溜走,或許又會在我們的夢境中重現。那是我們被錨固在自己所擁有且能控制的這副身體內會有的那種感覺,我們就是從身體裡來感知這個世界的。那是橫越時間的某種個人認同感,始自我們最初的記憶,延伸到某個想像中的未來。種種感覺連結到一個連貫的整體,那就是我們對自身的感知。然而,儘管我們和自己有這樣的個人親密關係,闡述自我的本質仍然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綜觀史冊,顯然人類一直對自我感到著迷和困惑。羅馬統治時期的希臘旅行者保薩尼亞斯寫到刻在德爾菲阿波羅神廟前殿的七賢人銘言,其中一篇銘言寫道:「汝需知道自己。」《由我奧義書》是一部著重分析及形上學的印度教經文,它的開頭則這麼寫著:「心靈朝著目標前進,是受誰的指令及指引?……人開口說話,是依誰的意志而為之?又是什麼力量在指引耳目呢?」
聖奧古斯丁對「時間」有以下的看法,但是他大概也會用同樣的話來描述「自我」:「如果沒人問起,我知道那是什麼;但如果我想向誰解釋,我就又不知道了。」
因此,這就是從佛陀到現代的神經科學家、哲學家所面對的難題,人類一直在思索自我的本質。「自我」是真實抑或幻覺?若它存在腦中,那是在腦裡的何處呢?神經科學告訴我們,我們對自我的感知是大腦和身體之間複雜交互作用的產物,來自無時無刻不斷更新自我的神經過程,而這些片刻串在一起,便帶給我們一種緊密無縫的人格感受。我們常聽到有人解釋自我何以是一種幻覺,是大自然最複雜的魔術手法,但是這些詭計和幻覺的說法混淆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若移去自我,就沒有受詭計耍弄的那個「我」,也沒有能感受幻覺的主體了。
科塔爾症候群揭露了自我的運作方式
從巴黎笛卡兒大學出發,沿著學校街走三十分鐘,經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就能抵達皮提─薩佩提醫院,科塔爾在一八六四年就是在此地,以一名實習醫師的身分開始他的醫療生涯。我來這裡見大衛.科恩,他是這所醫院的嬰幼兒和青少年精神病學科主任。
在科恩醫師的住院醫師和實務經歷裡,他已經見過幾位罹患科塔爾症候群的病患。有鑑於這是一種罕見的失調症狀,相對大量的樣本數讓科恩特別注意科塔爾症候群。我們談論到一位特別的病患,十五歲的梅,她是有留下紀錄的科塔爾症候群病例中相當年輕的一例。科恩醫師收治該名病患,並在她痊癒後與她進行過廣泛的討論,使得他能夠將梅的妄想和她的個人歷史加以連結,得以一窺自我(即使是在像是科塔爾症候群的妄想狀態下)如何受到個人敘述、甚至是優勢文化規範的影響。
大約是在梅到科恩醫師的診所就診的一個月前,她開始感到極度悲傷和沮喪,並逐漸出現與她自身存在有關的妄想。等到確診時,她已經變得重度緊張、沉默和麻木。「就連護士都被她嚇到了。」科恩醫師告訴我。但是在經過幾天的住院照護後,梅有了些許好轉,恰好足夠讓她一天說出幾個字,護士很用心地記了下來。藉由梅零星說出的這些暗語,還有與她父母的討論,科恩醫師拼湊出梅的故事。
梅出身中產階級天主教家庭,她有兩名手足,包括一個哥哥和一個姊姊。姊姊比梅大十歲,嫁給一位牙醫。這個家庭有憂鬱症病史,他們的母親在梅出生前曾受嚴重的憂鬱症所苦,而梅的一位阿姨也接受過電擊痙攣休克治療法,這種治療法包括傳送溫和的電脈衝到腦部以抑制癲癇,通常而言這是很有效的療法,不過幾乎都是最後才會用上的一招。
梅的妄想症狀是典型的科塔爾症候群。「她一直告訴我們她沒有牙齒、沒有子宮,而且她有種已經死去的感覺。」科恩醫師說。他很費力地想用英語描述梅的情況。「我不知道這個字的英語怎麼說……morts-vivants!」他說。我後來查了資料,直譯是「活死人」。
「她一直等著要……躺在棺材裡,被埋起來。」科恩醫師說。
即使經過六週的治療和藥物療法,她的病情還是沒有改善,科恩醫師建議使用電擊痙攣休克治療法。基於該家族的憂鬱症經驗,她的雙親立刻就同意了。在六次治療後,梅似乎痊癒了,所以科恩醫師終止了電擊痙攣休克治療法,但是她隨即復發,於是科恩醫師繼續進行療程。這次她確實康復了,除了還有一些頭痛、輕度的認知混淆,以及輕微的記憶錯亂。當她開始開口訴說,她說話的方式就好像自己已經從一場夢魘中醒來。
科恩醫師在與梅的討論中,要求在他提起她的妄想時,隨意說說腦中出現的任何聯想。他們的討論揭露了驚人的事實。舉例來說,她認為自己沒有牙齒的妄想似乎與她的牙醫姊夫有某種關連。科恩醫師看出了端倪,梅或許曾對自己的姊夫懷有愛意。她提到她永遠不想接受姊夫的治療。科恩醫師又一次掙扎著尋找正確的英文字眼,以描述梅表達自己的方式。他以法語說「pudique」,意思是「端莊」。梅談到自己的姊夫時,「你看她說話的樣子就會明白,她永遠不會在他面前赤身裸體。」
她失去子宮的妄想似乎和她的手淫行為有關。「她對手淫很有罪惡感,所以覺得自己可能會不孕。」
科恩醫師提出的重點是,妄想的特異之處,與個人生平及文化脈絡有關。為了說明病例和文化脈絡的關連,他回想起在一九九○年代向他求診的一名五十五歲男性,科恩醫師診斷他罹患了科塔爾症候群。他的妄想之一是他認為自己得了愛滋病,但事實上他沒有。這名病患同時也有躁鬱症,他在躁鬱症的狂躁期具有極高的性欲,因而產生罪惡感,科恩醫師發現他的妄想可以連結到這股罪惡感。在一九七○年代,如果科塔爾症候群病患的疑病性妄想牽涉到性病,幾乎都會和梅毒有關,而梅毒正是那個時代在文化上所認定的天譴。有趣的是,這名男子年輕時確實曾在軍中感染過梅毒(科恩醫師檢測他的抗體,確認了此事),但是在數十年後,他在科塔爾症候群發作時的妄想卻和梅毒沒有關係,而是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愛滋病。愛滋病已經在較廣泛的文化上取代了梅毒,成為「上帝對肉體罪惡的懲罰」(梅毒幾乎不再出現在科塔爾症候群的疑病性妄想裡了)。「這只是單一病例,(但)我認為這起病例提供了很多資訊。」科恩說。
對科恩醫師而言,科塔爾症候群揭露了自我的運作方式。這種失調症狀對個人的存在是一種感受深切的干擾,而且顯示出自我與個人的身體、故事以及個人所屬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是有連結的。大腦、身體、心智、自我和社會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牽連。
我壞到骨子裡了,我不該存在
回到英國的埃克塞特,澤曼醫師遇上了與葛拉罕類似的事。在葛拉罕的病例裡,他的妄想是自己的心智活著,但是大腦已經死了。「那是科塔爾妄想的當代更新版,要得到大腦已經孤立死去的結論,(你需要)……有腦死的概念,而『腦死』是相對晚近的醫學發展。」
在澤曼醫師的發現中,更有意思的是葛拉罕的妄想裡固有的二元論(身心二分法),也就是「非物質」的心智可以獨立於大腦和身體而存在。「我認為大部分人所傾向的二元論得到了相當優美的演示,」澤曼告訴我。「心智可在大腦死去的情況下仍存活,這樣的概念是二元論相當極端的表達方式。」
撇去哲學繆思不談,澤曼醫師發現葛拉罕的處境其實很悲傷。「他的表達方式既遲緩又扁平,話音裡少有情緒性語調。(我)偶爾會瞥見一抹微笑,但是他只有非常少的臉部表情,」澤曼醫師說。「你可以感受到,對他來說,存在是相當乏味的事,而且要費力才能思考。」
罹患科塔爾症候群的病人常感到極度憂鬱,程度之劇遠超過大多數人所能理解,有另一位法國的精神科醫師讓我得以一窺內幕。這位醫生名叫威廉.德卡瓦略,我和他也是在巴黎會面,就在他位於雨果大街上的辦公室裡。他畫了一幅線條圖,向我說明科塔爾症候群在憂鬱症量表上的位置。他先在左邊標上「正常」,在右邊等間距加上「悲傷」「抑鬱」「非常抑鬱」「憂鬱」,然後加上一系列小點,此時級數不再呈現線性,接著他在這些小點的最末端寫上「科塔爾症候群」。「有了科塔爾症候群在圖上,就像是有一道從地球延伸到土星的黑色大牆,你沒辦法看見牆後。」德卡瓦略醫師說,他是個短小精悍的法籍塞內加爾裔男子,對用字遣詞很有一套。
德卡瓦略醫師有一間私人執業的診所,但同時也在巴黎聲譽卓著的聖安娜醫院工作。他記得在一九九○年代早期治療過的一名科塔爾症候群患者,該位患者顯露出「憂鬱歐米伽」的典型症狀。「憂鬱歐米伽」這個詞源自達爾文在他的著作《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一書中對憂鬱症的描述:「這個臉部表情包括皺起鼻子上方和眉毛之間的皮膚,看起來很像希臘字母歐米伽。」達爾文寫到有關臉上這些「悲傷肌肉」,而德國精神科醫師海因里希.舒勒則根據達爾文的生動敘述,在一八七八年發明了「憂鬱歐米伽」這個專有名詞。
德卡瓦略醫師的病人是一位五十歲的工程師兼詩人,他曾假裝試圖殺害自己的妻子,他把雙手掐在她的脖子上,然後停住,要她打電話報警。等警察到達後,看見一個心理失常、極其古怪的男人,所以他們沒把他帶回警察局,而是直接把他送去聖安娜醫院(男子的舉動帶有模仿的性質,身受憂鬱症所苦的法國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在一九八○年勒死了妻子,他也是先被送去精神病院,而不是押入大牢)。
這起事件隔天,德卡瓦略醫師在聖安娜醫院與這名男子會面。「我問他:『為什麼你想殺自己的妻子?』他說:『這個嘛,因為這樣的罪可以讓我人頭落地。』他希望自己被殺死,儘管法國並沒有死刑。」
這名男子所表現的是科塔爾症候群另一種特徵性症狀的極端形式,也就是罪惡感。「他告訴我,他在那一刻比希特勒更壞,而且他要求我們想辦法讓他被處死,因為他對人類來說太邪惡了。」德卡瓦略醫師說。
這名病患的體重變輕,一臉過長的亂糟糟鬍子,他也不再洗澡,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淋浴的權利,無權使用太多水。院方決定在他還會為了科塔爾症候群而苦苦掙扎的時候,拍一部他的影片(做為建檔之用)。在影片攝製期間的某個時間點,這名病患拉起一條白色床單蓋住頭。「我壞到骨子裡了,我不想要看影片的人染上這股邪惡。」他對負責製片的德卡瓦略醫師這麼說。德卡瓦略告訴他,這只不過是部影片,他不可能透過影片影響到任何人,「他卻說:『我知道,但事情就像我說的那樣。我壞透了。』」德卡瓦略醫師對我說。我們又一次看到,較廣泛的文化影響了他的妄想,他相信自己對愛滋病的疫情負有責任,而且其他人有可能光是看他的影片就會染上愛滋病。
過了好幾個月,在這名男子康復之後(治療包括了電擊痙攣休克治療法),德卡瓦略醫師和他這位「前病患」一起觀看了影片。在十二分鐘影片結束時,男子轉身面對德卡瓦略醫師,然後說:「嗯,影片很有意思,但影片裡的人是誰?」德卡瓦略醫師以為他在開玩笑。
「那是你啊。」德卡瓦略對他說。
「不,那不是我。」男子回答道。
德卡瓦略醫師很快就意識到,試圖說服他是沒有意義的,他已經不是墜入名為科塔爾症候群的黑暗中的那個人了。
既然科塔爾症候群會帶來如此極端的憂鬱症,精神科醫師都很納悶為什麼大多數的患者並未試圖自殺。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患者動不了,就像是被車頭燈照個正著的鹿;但是德卡瓦略醫師認為他們不試圖自殺,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死了。「而你沒辦法再死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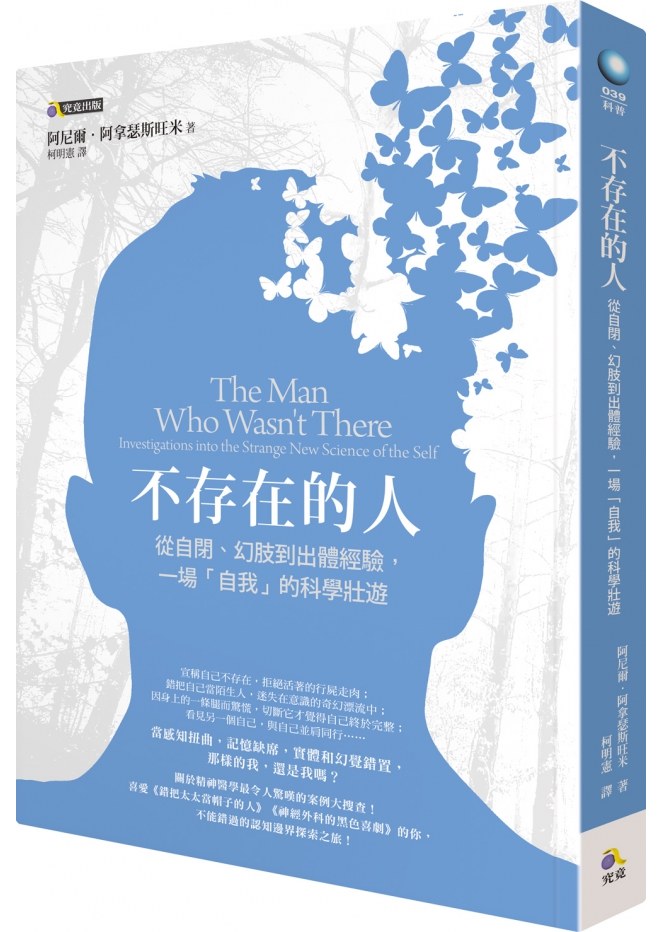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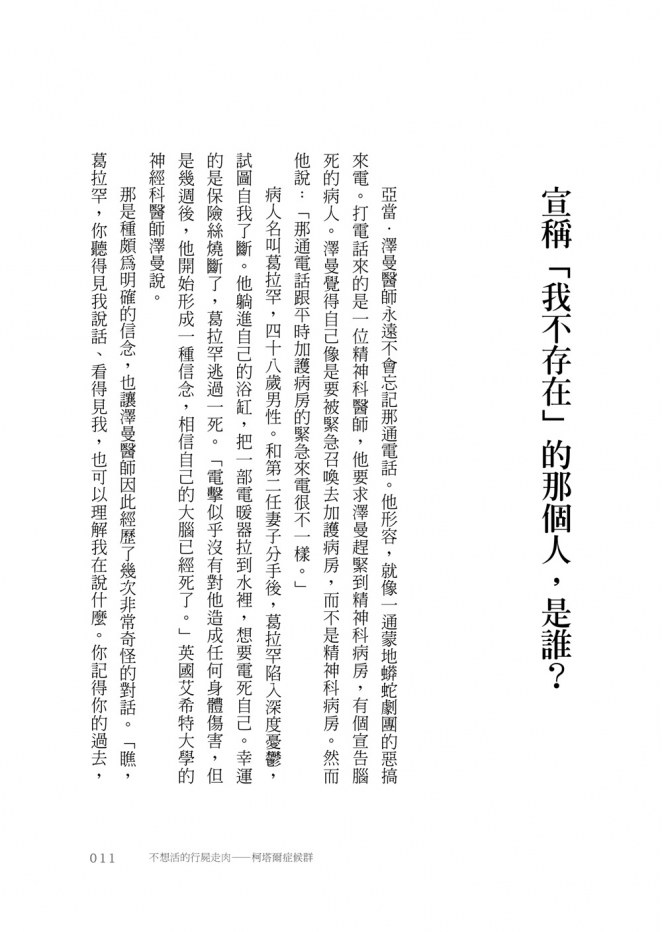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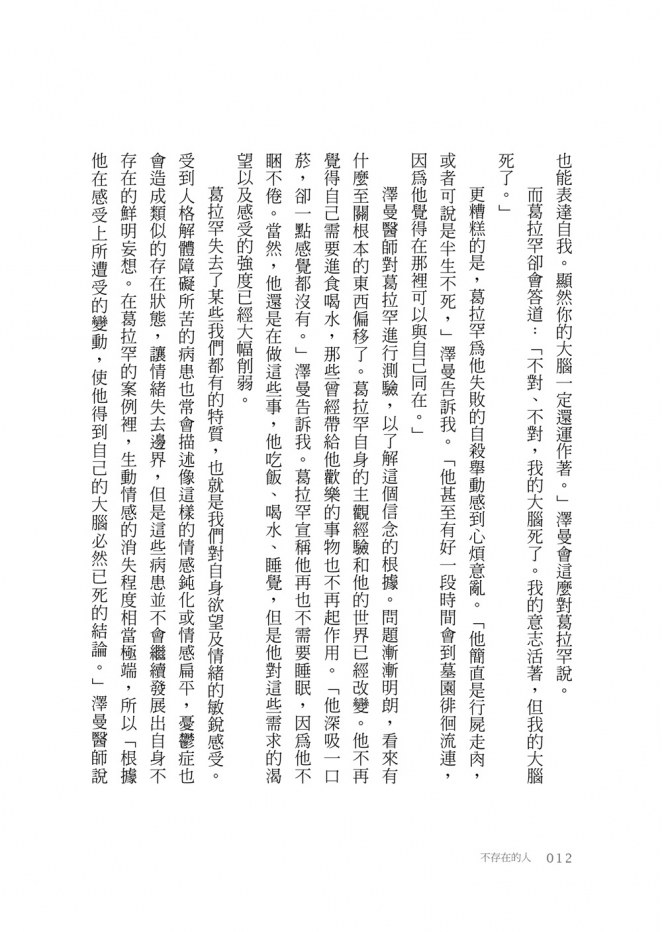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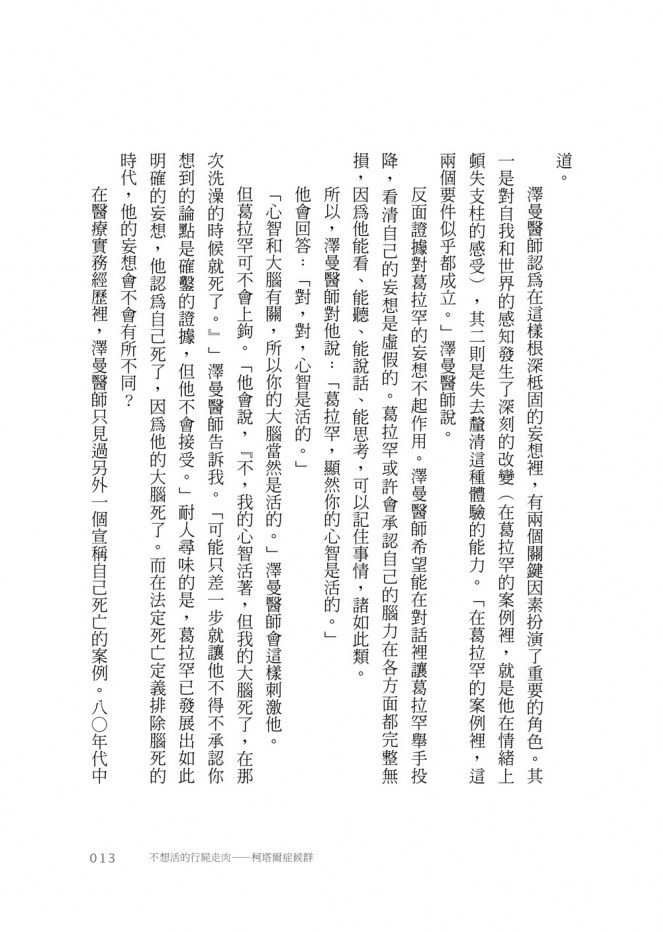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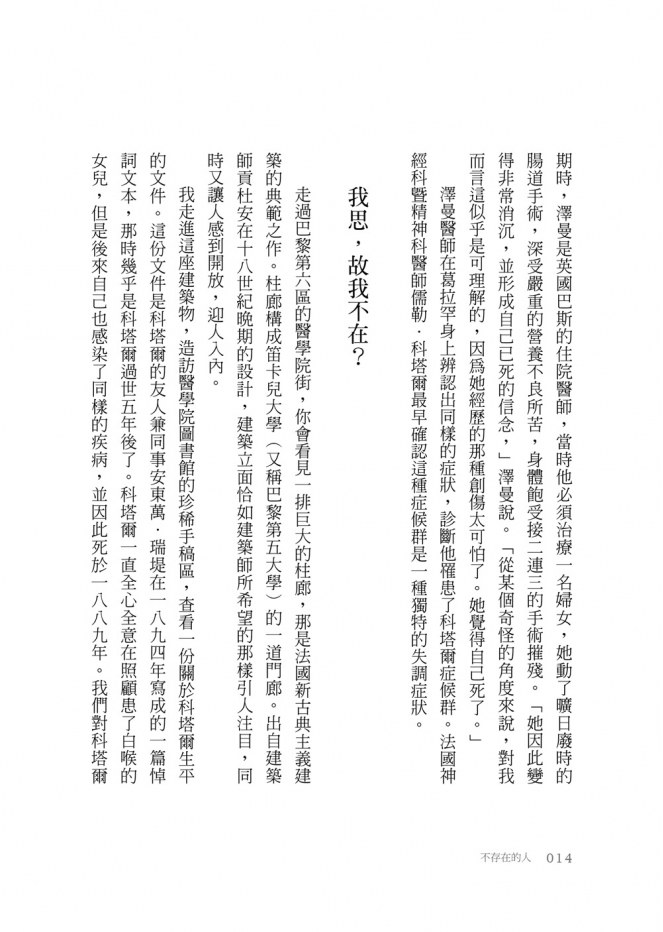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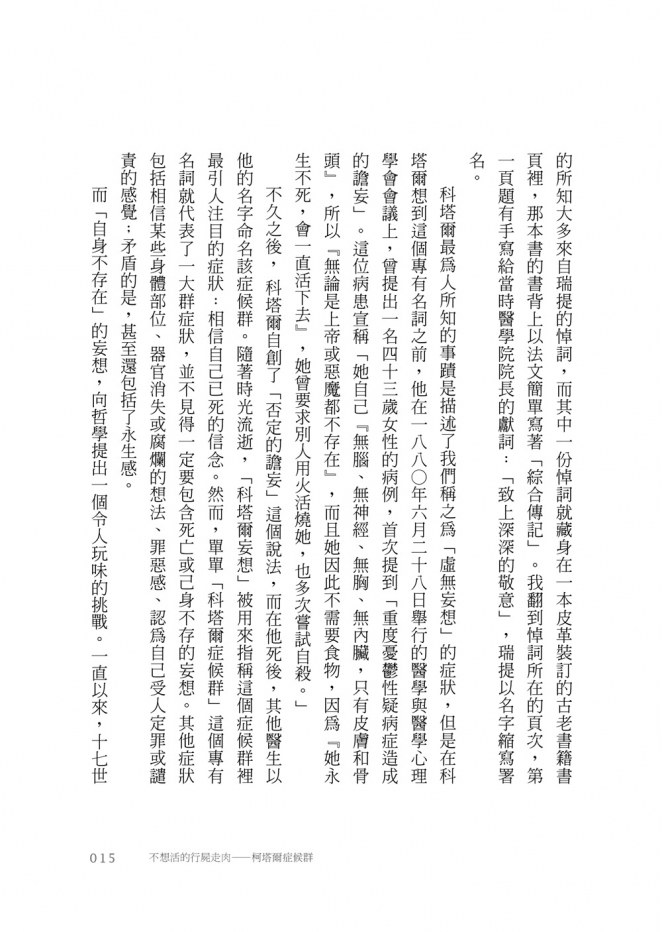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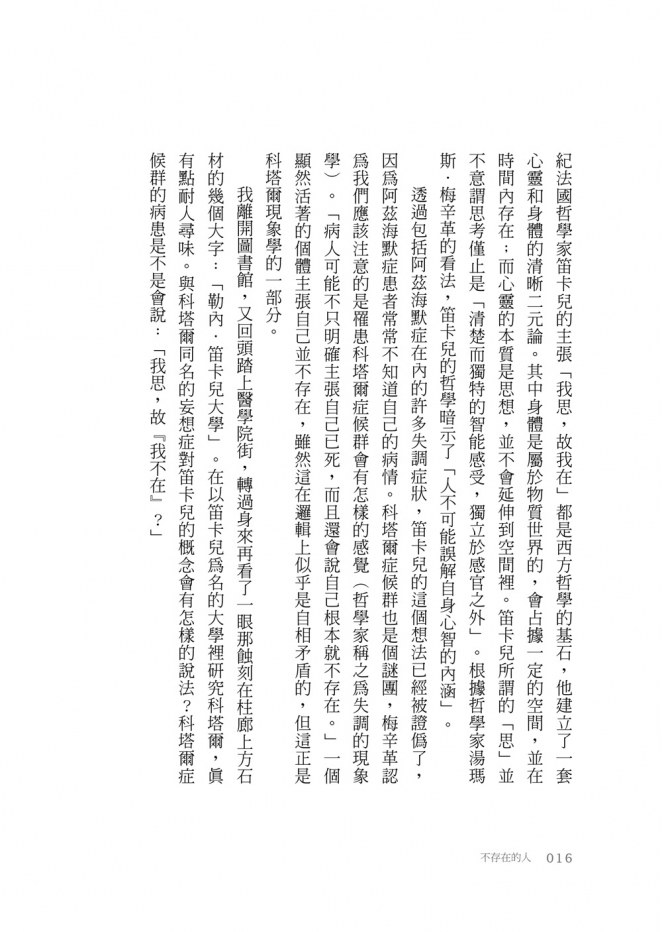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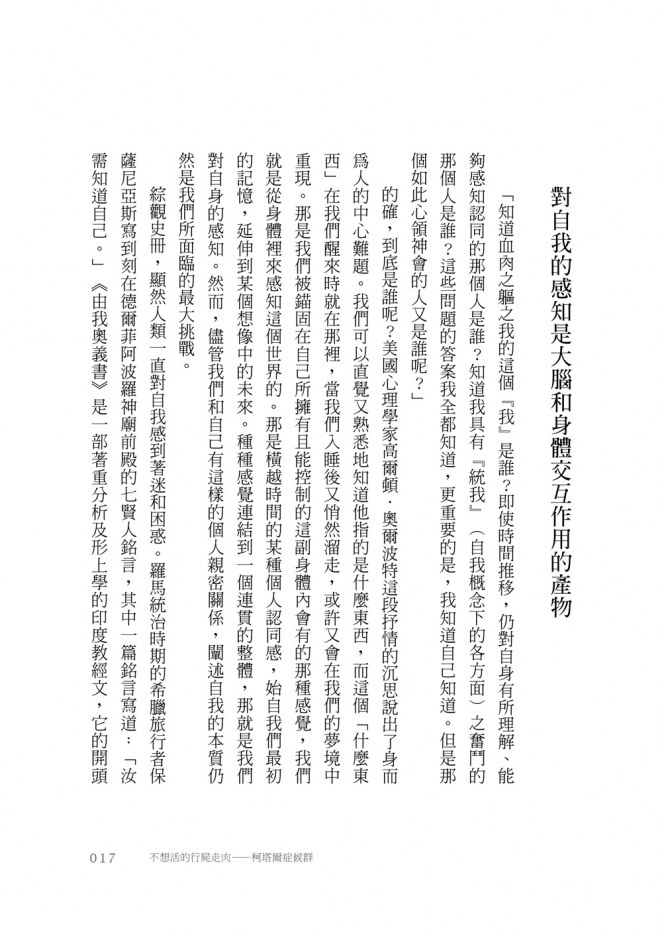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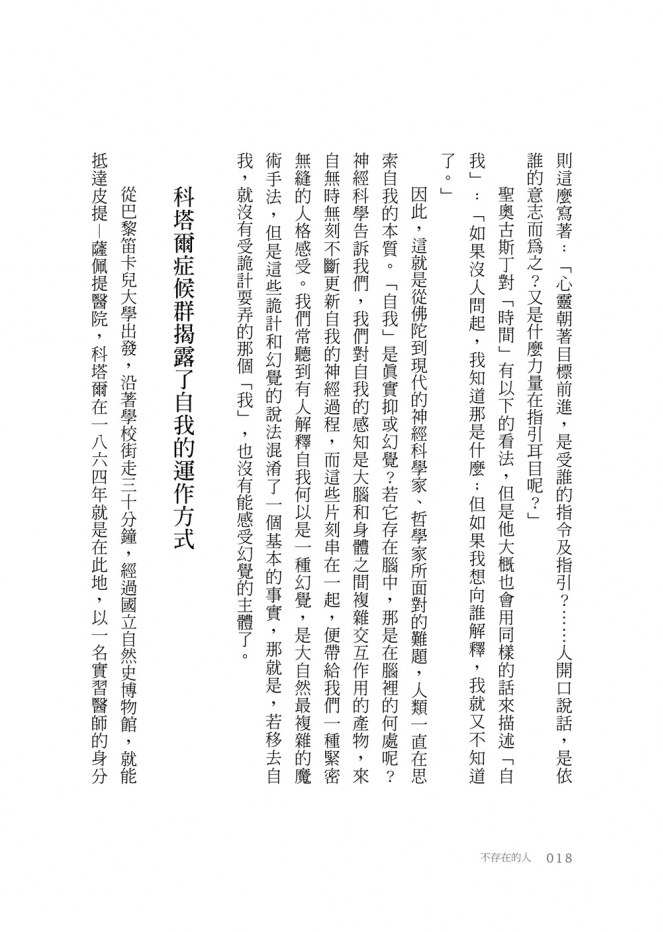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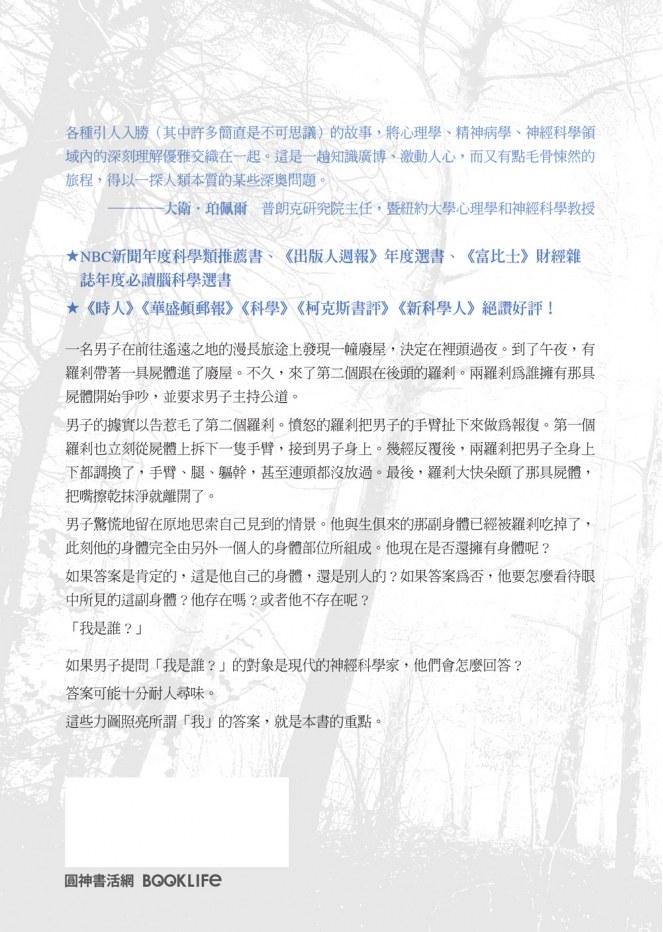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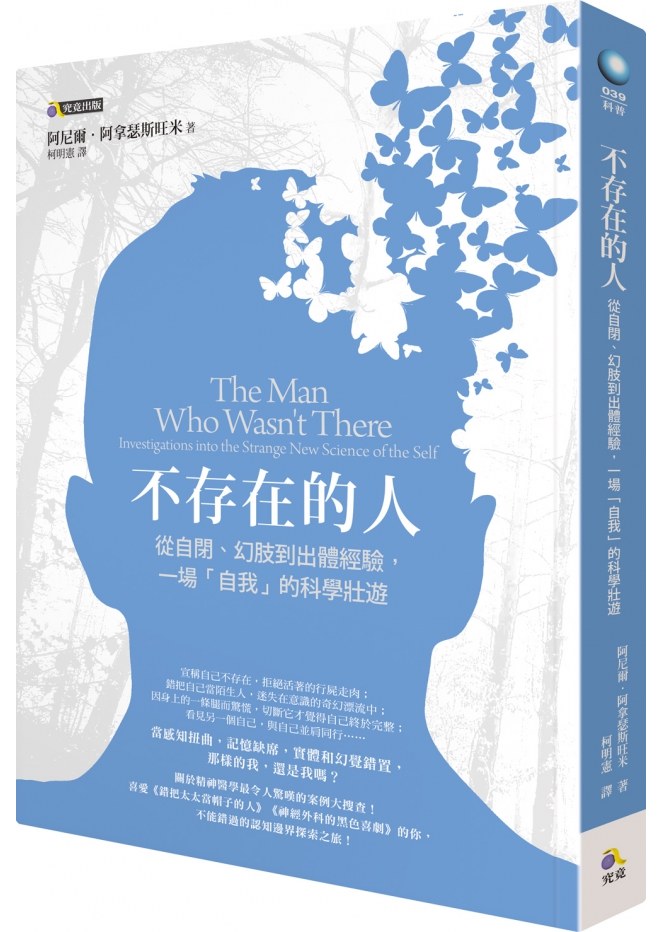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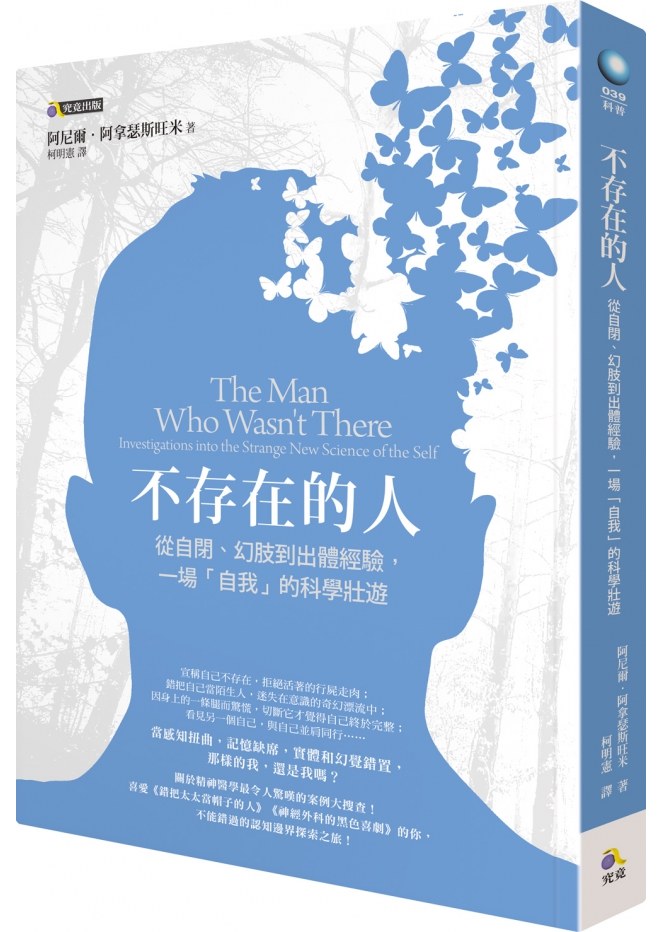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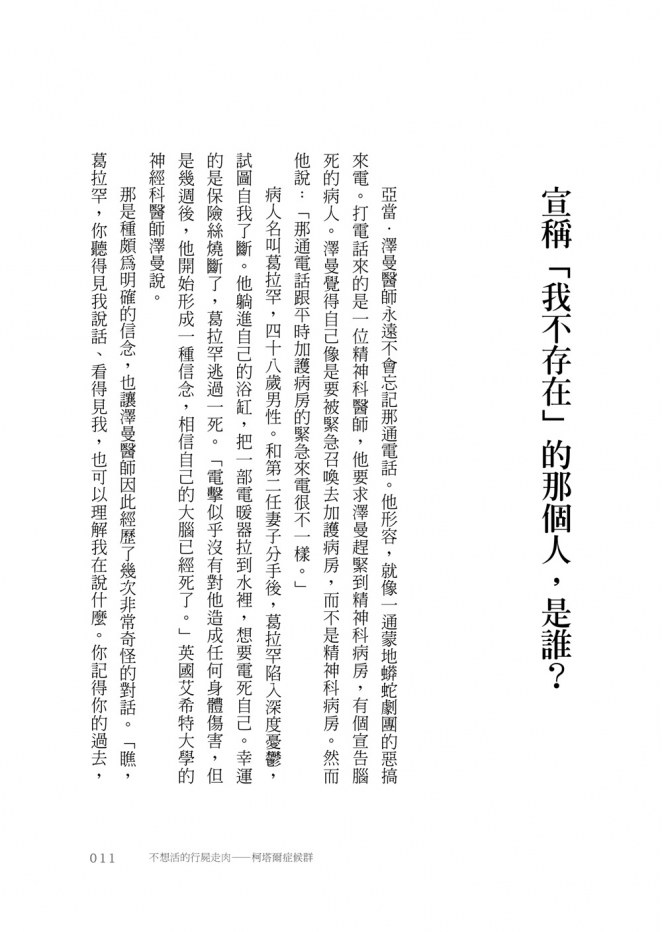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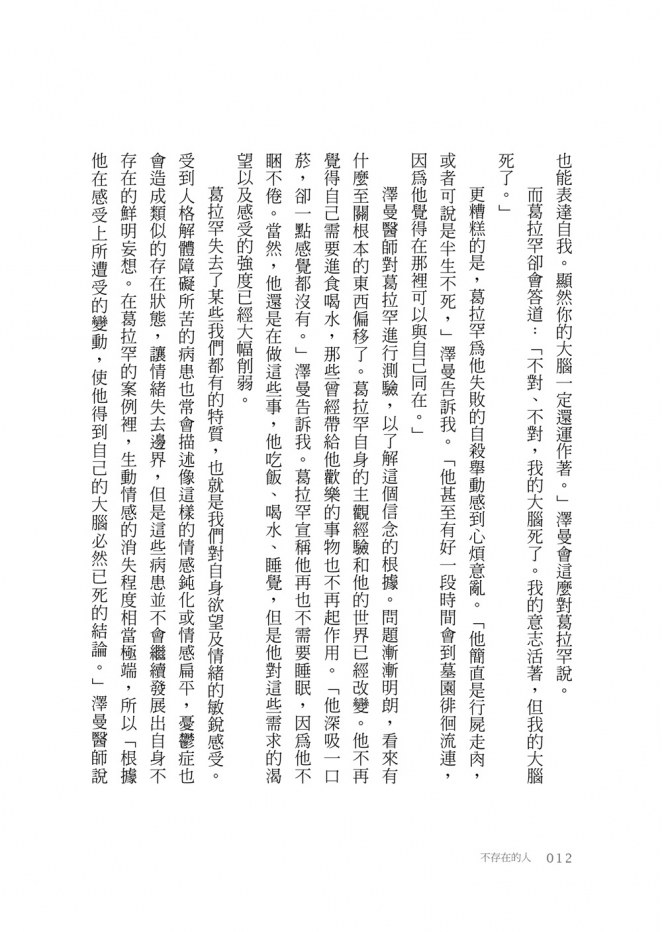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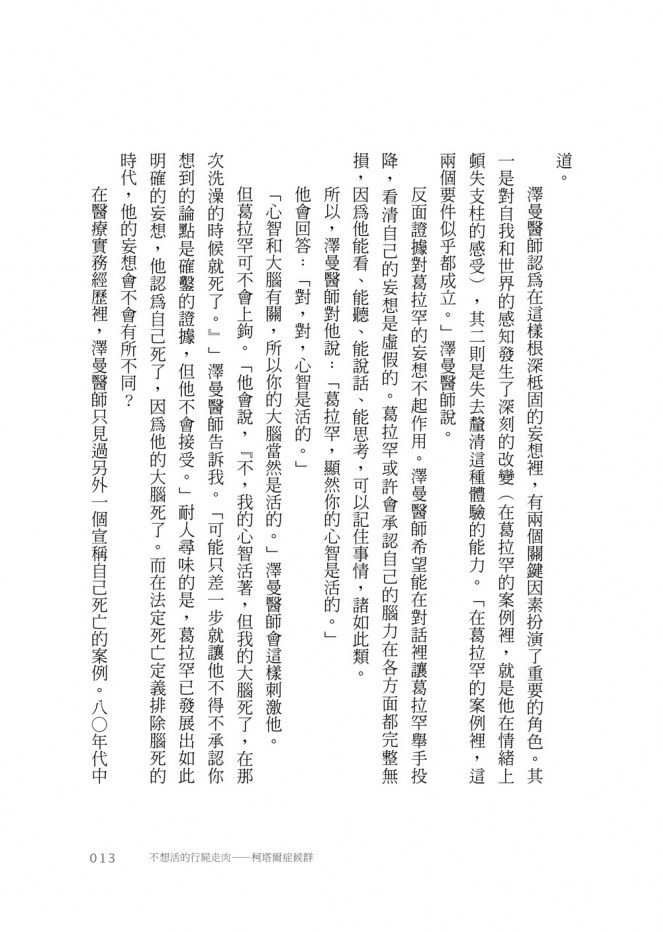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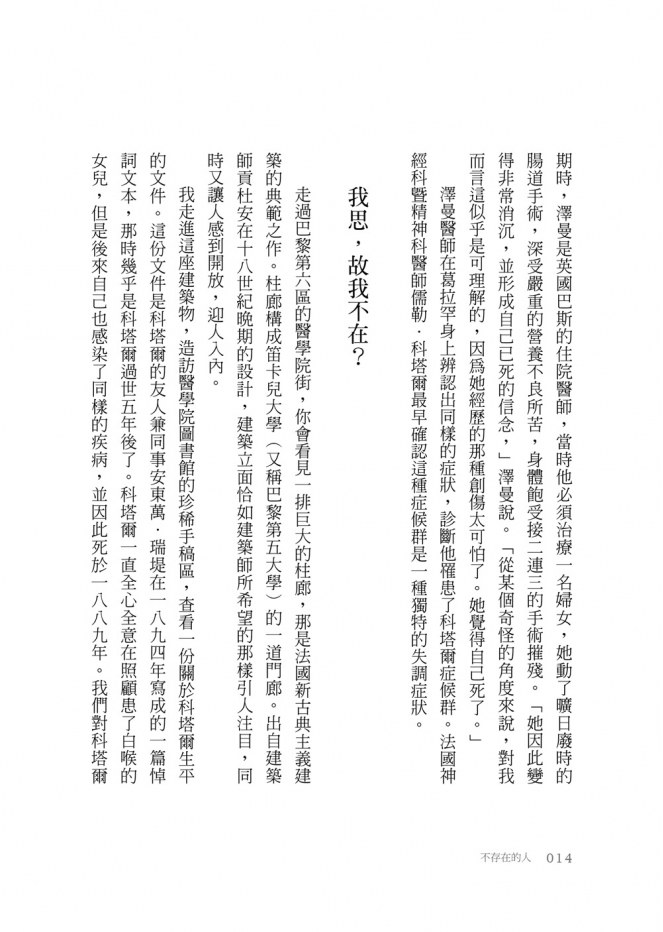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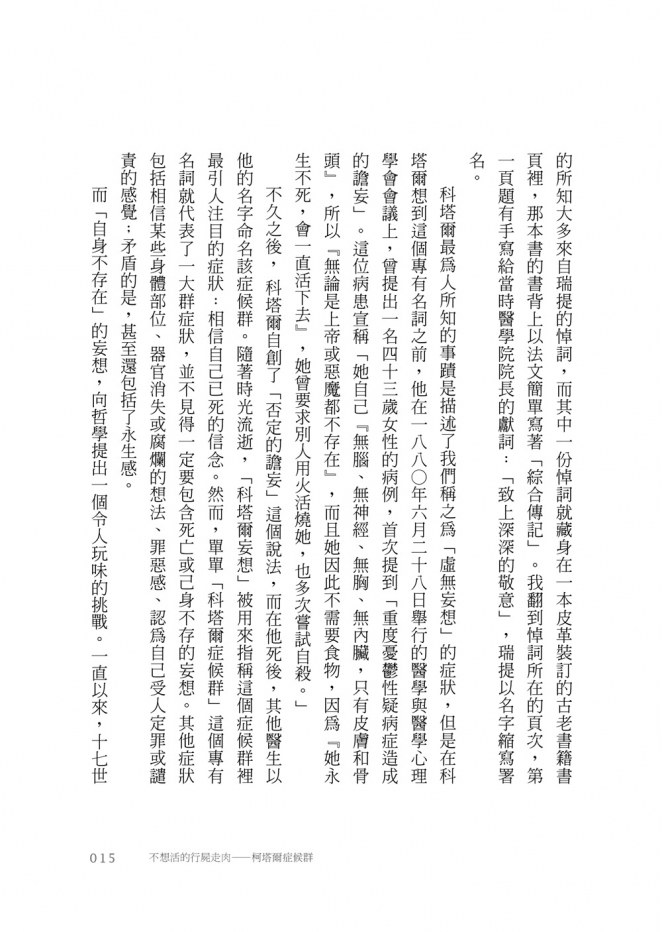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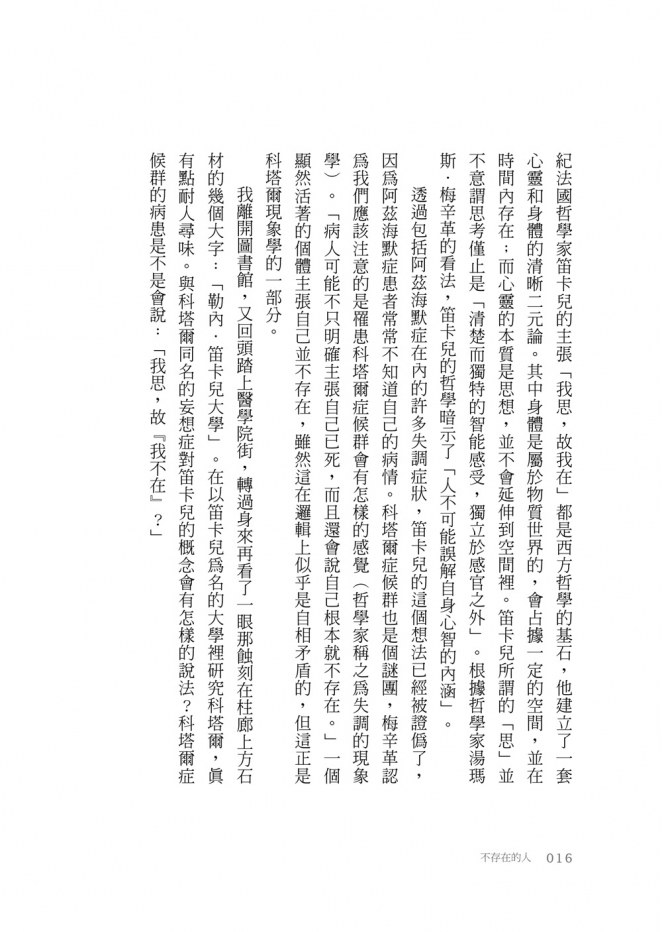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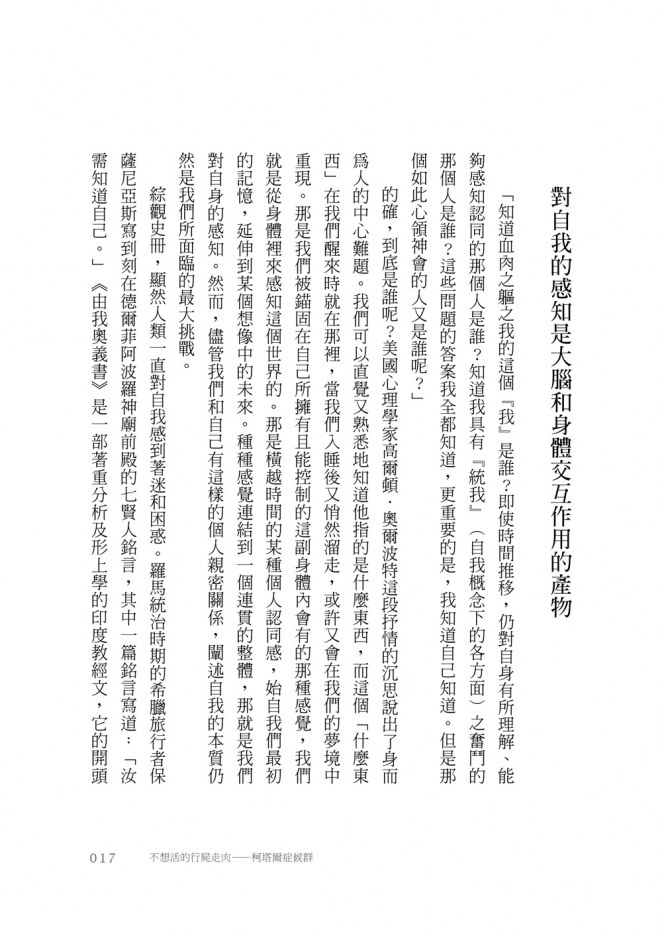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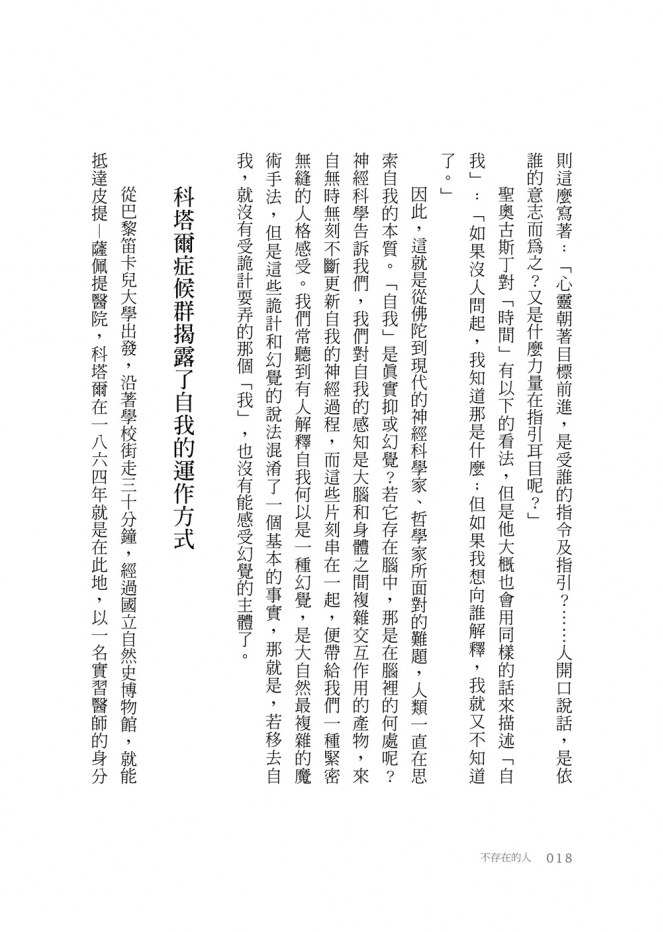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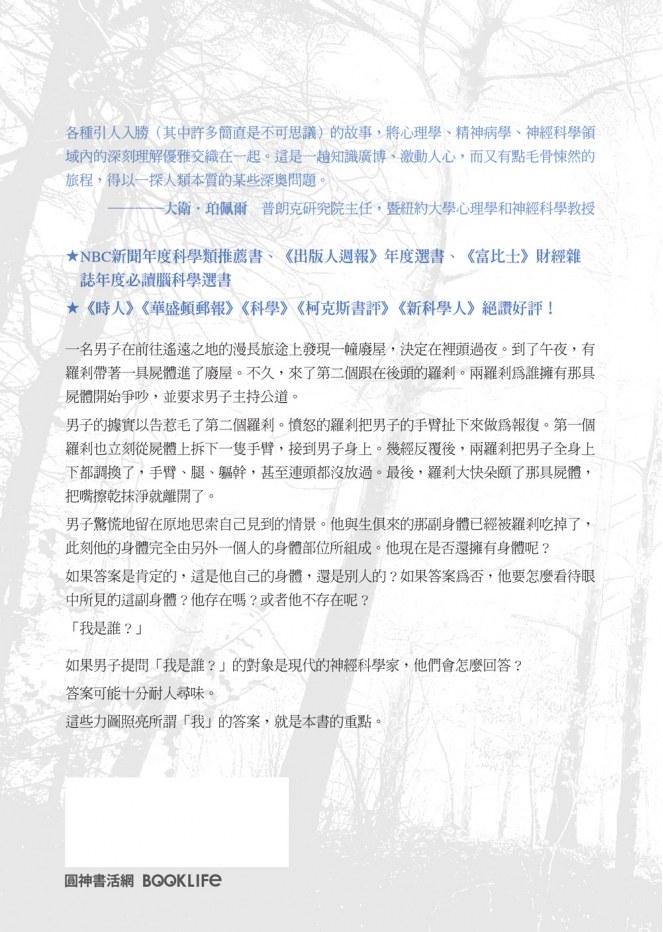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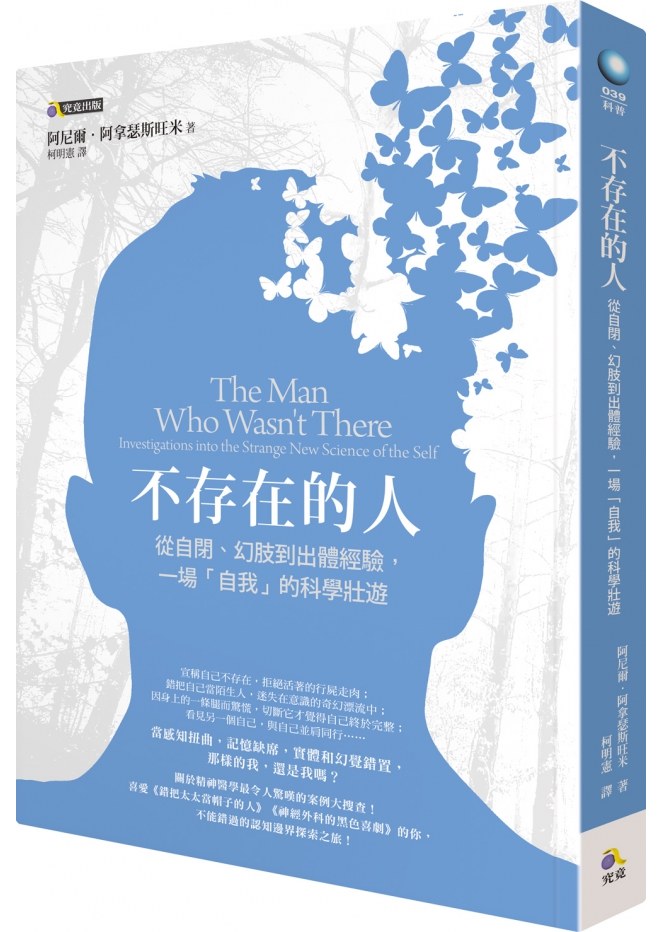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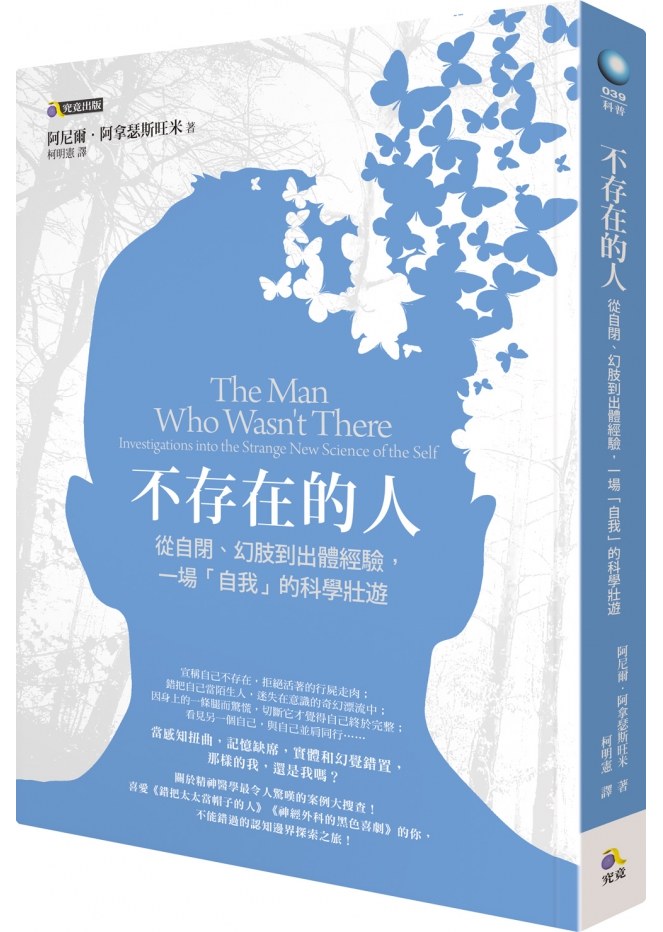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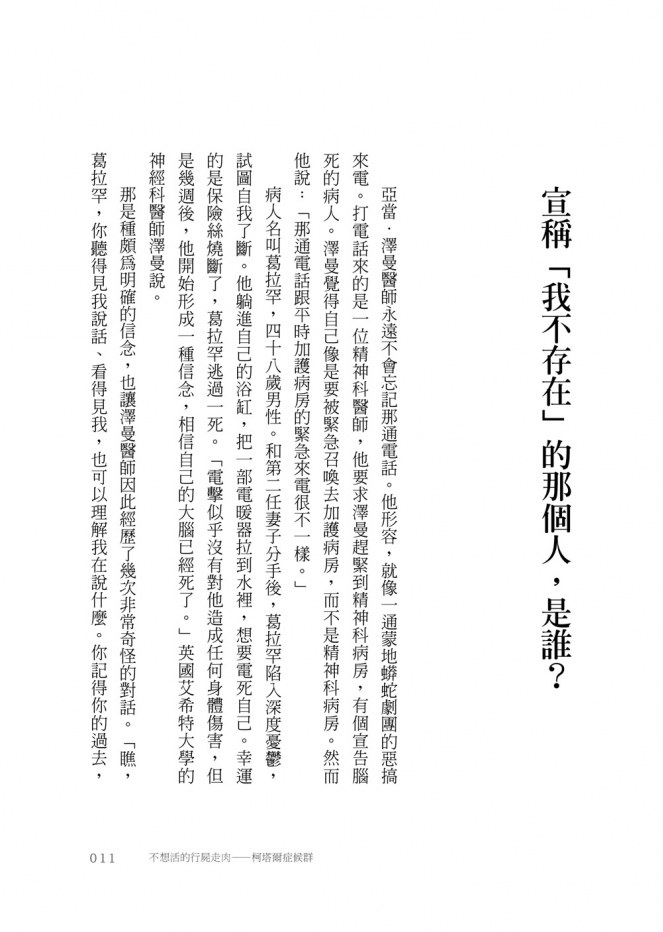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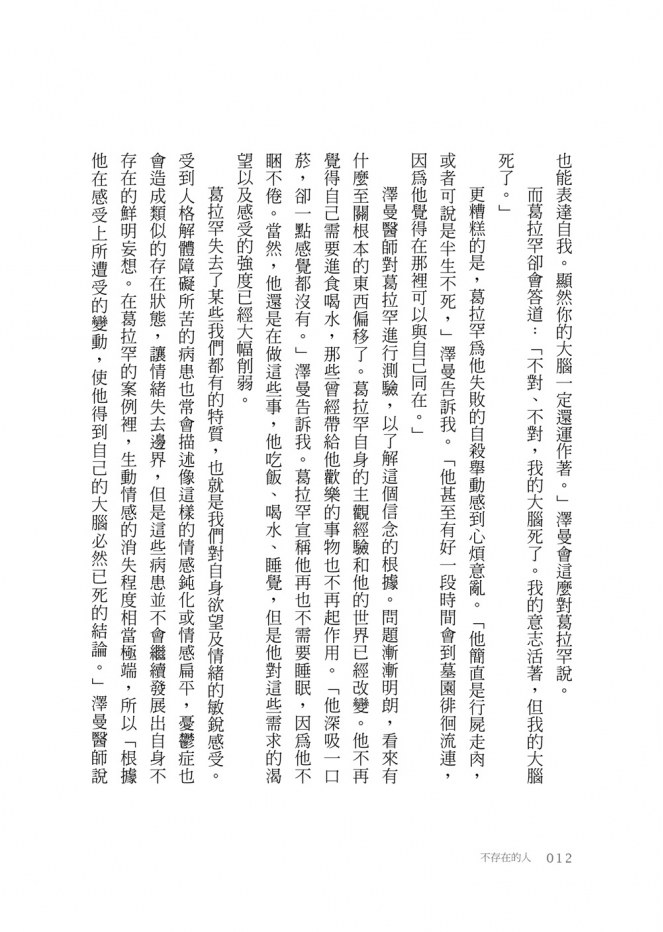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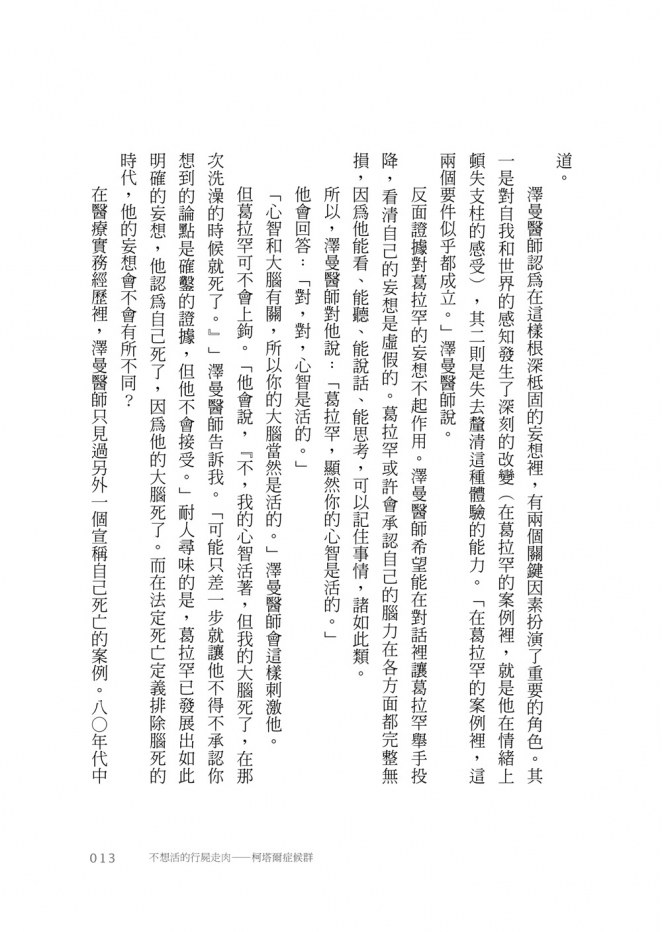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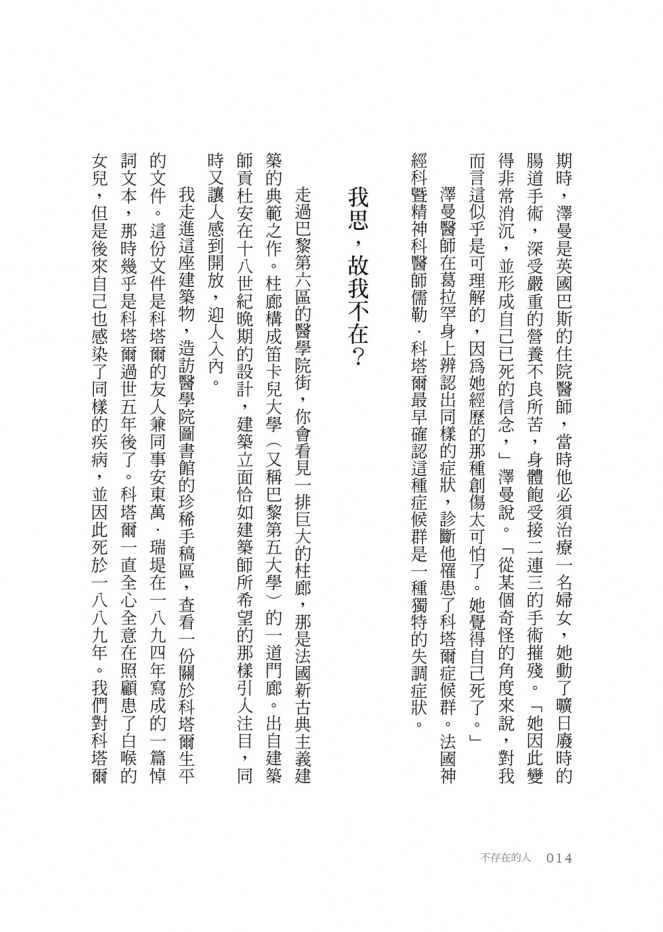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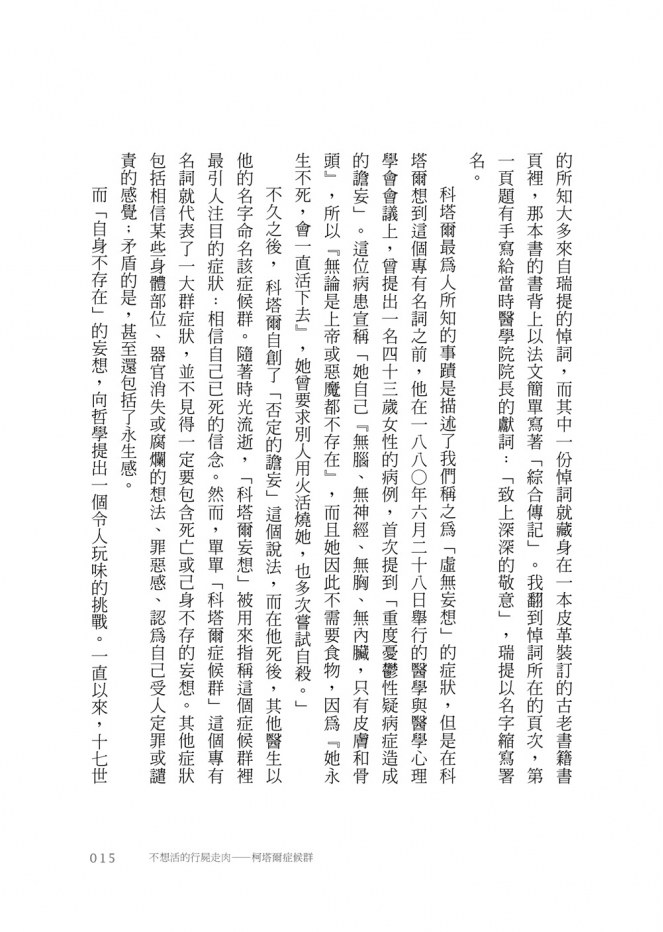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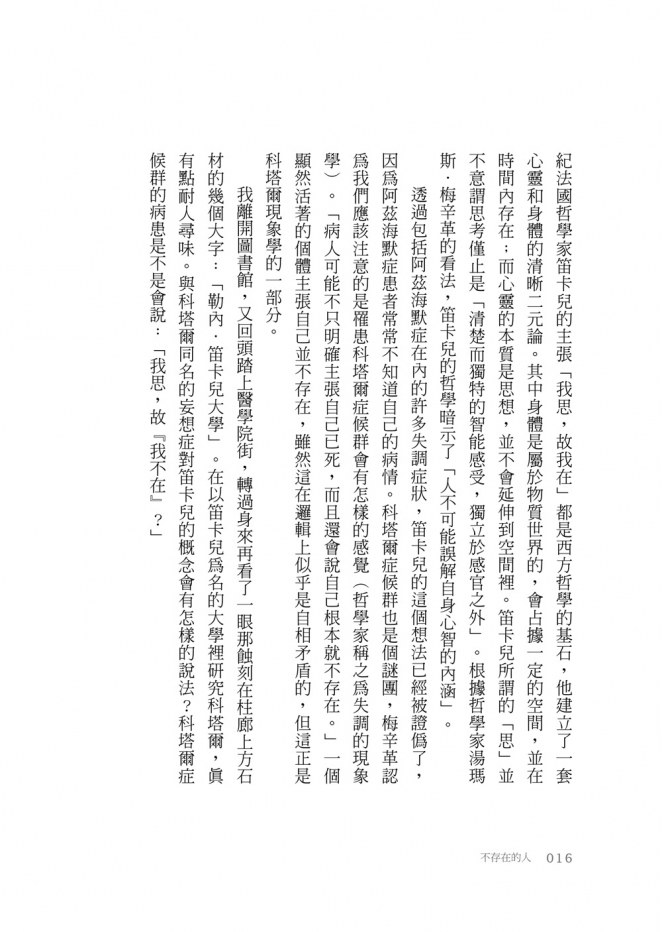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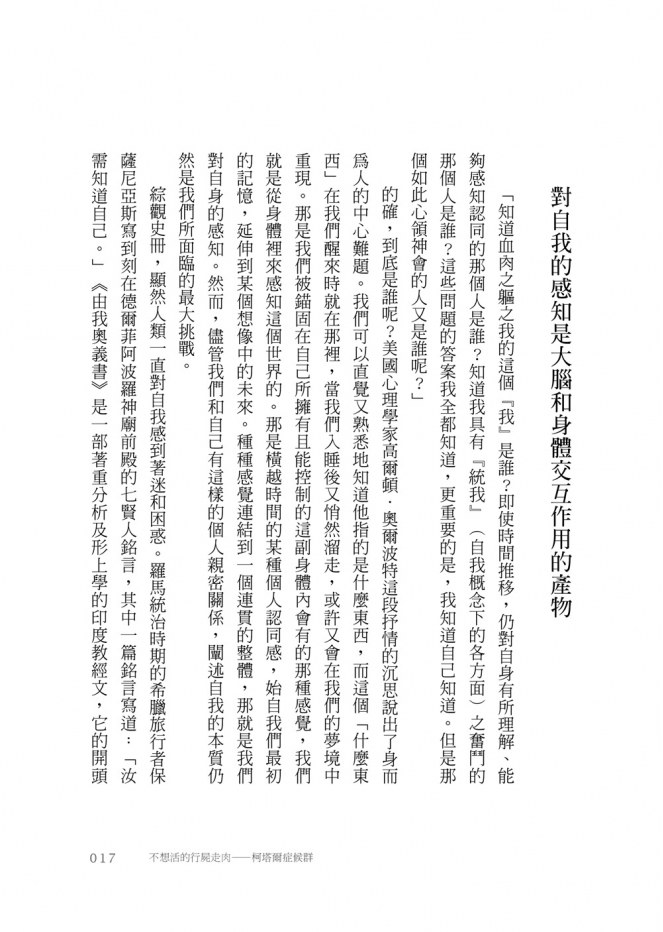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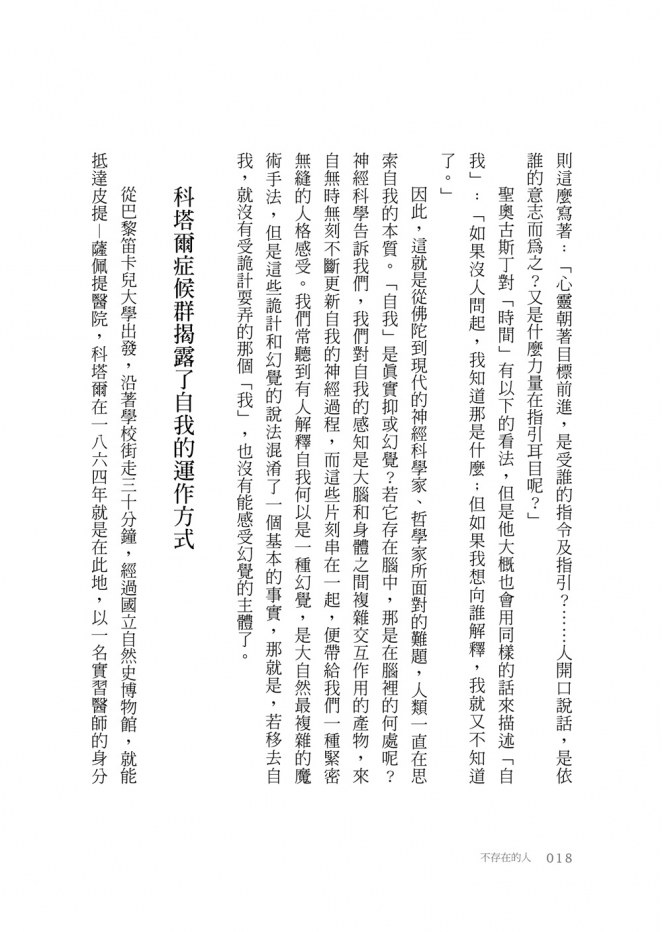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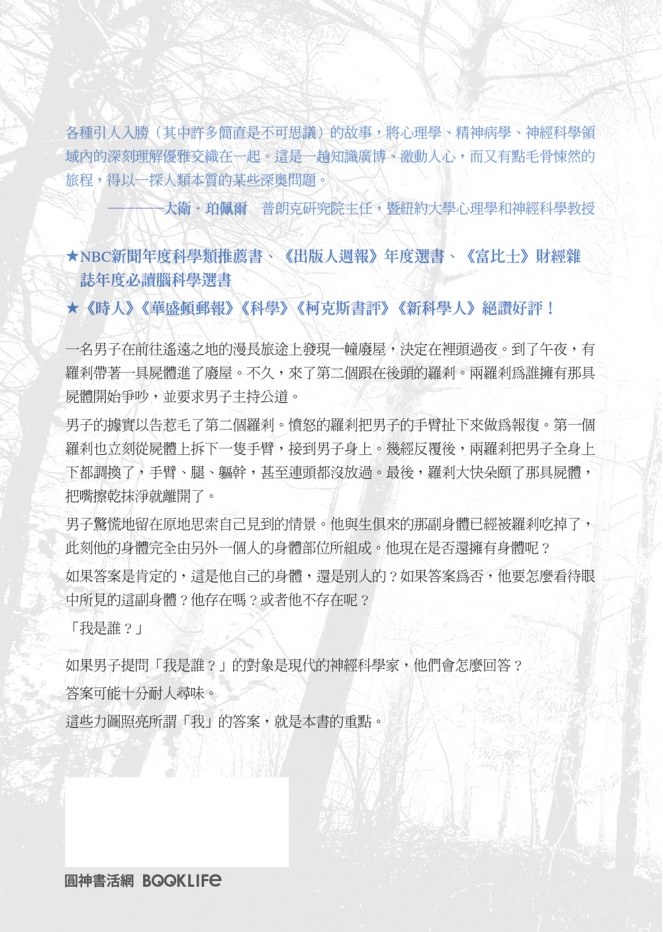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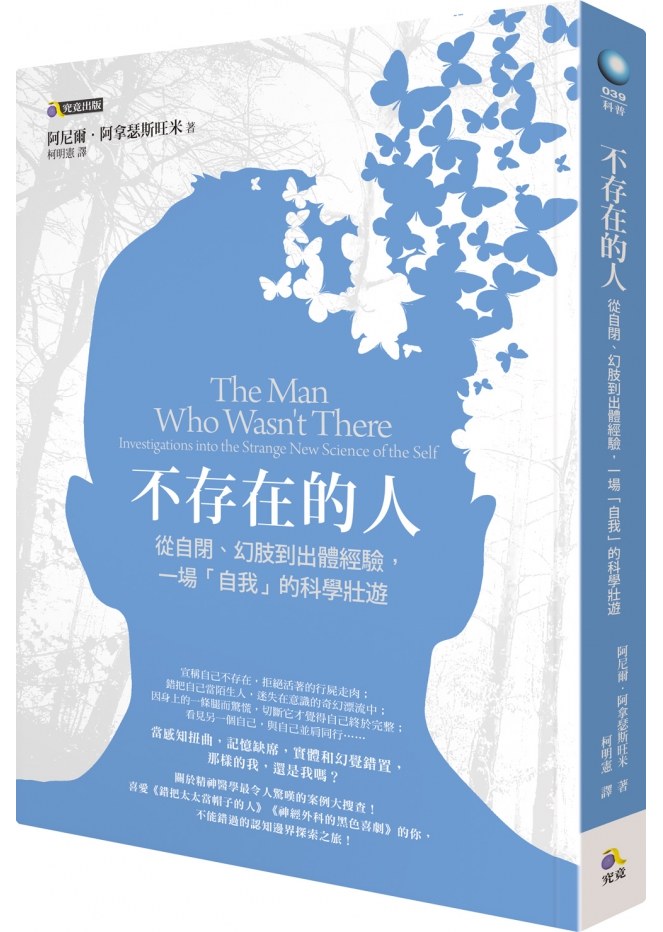
 那條腿一直都是個異物、一個冒牌貨、一種侵擾。他醒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像失去腿的自由,他會用自己「好的」那條腿單腳站立,坐時則把腿推到一邊。
那條腿一直都是個異物、一個冒牌貨、一種侵擾。他醒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像失去腿的自由,他會用自己「好的」那條腿單腳站立,坐時則把腿推到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