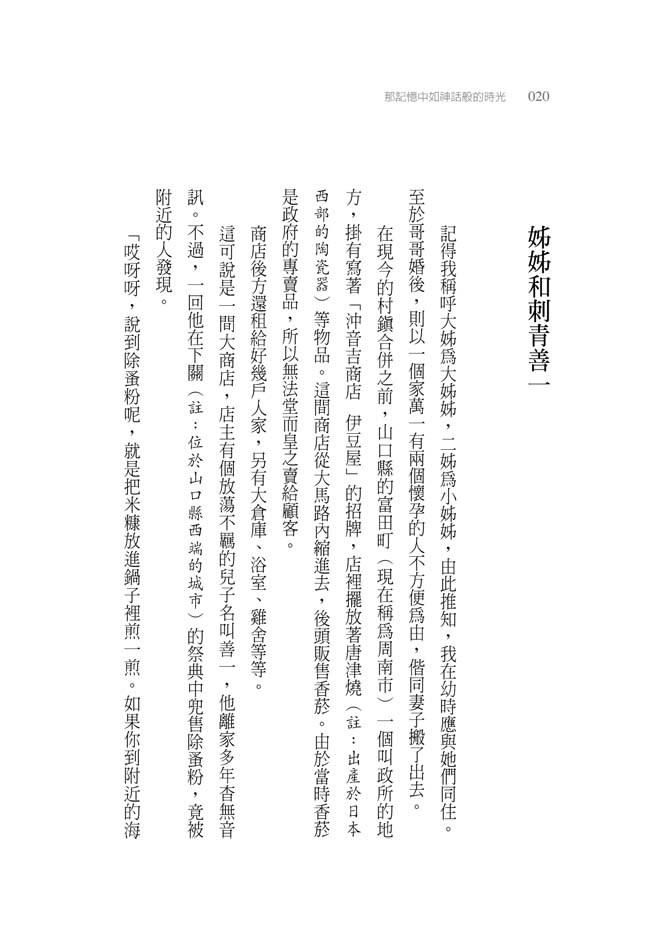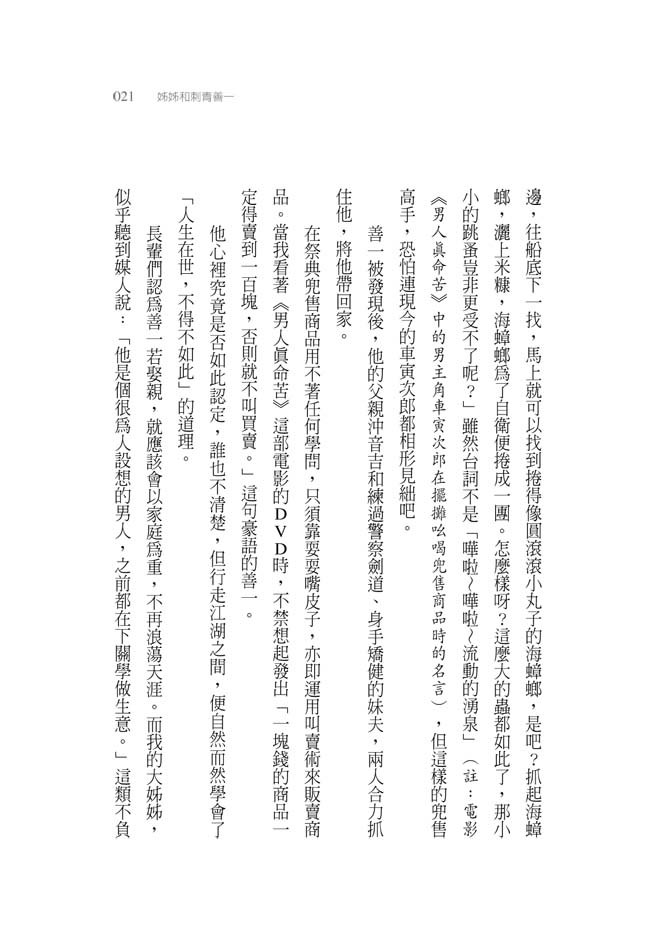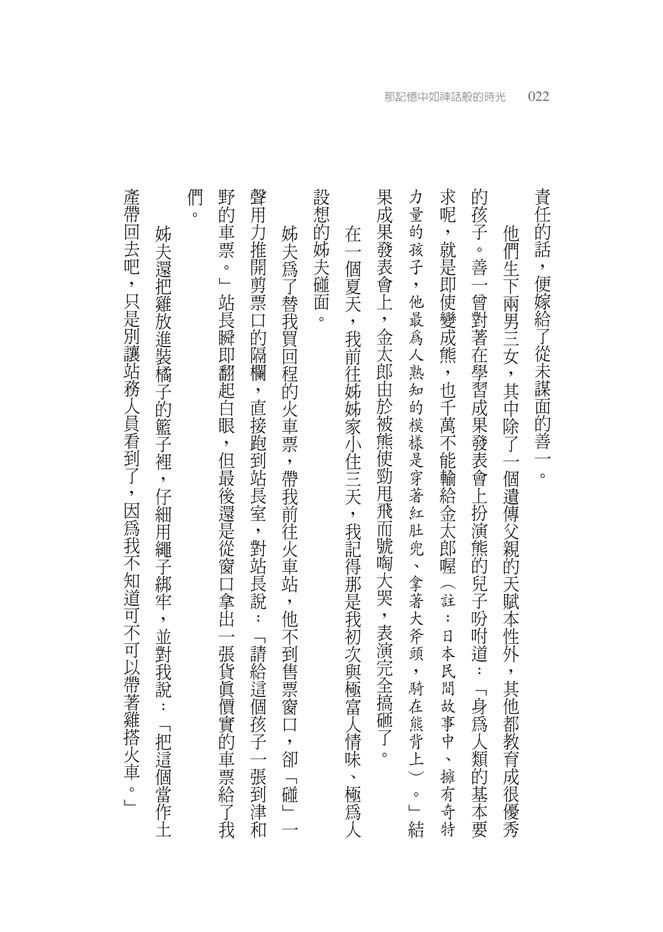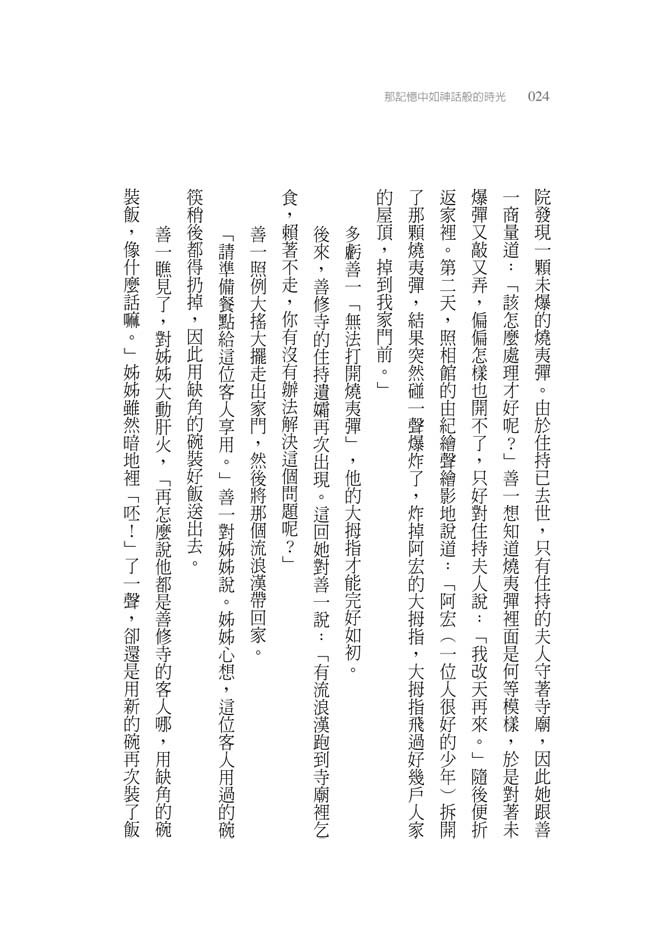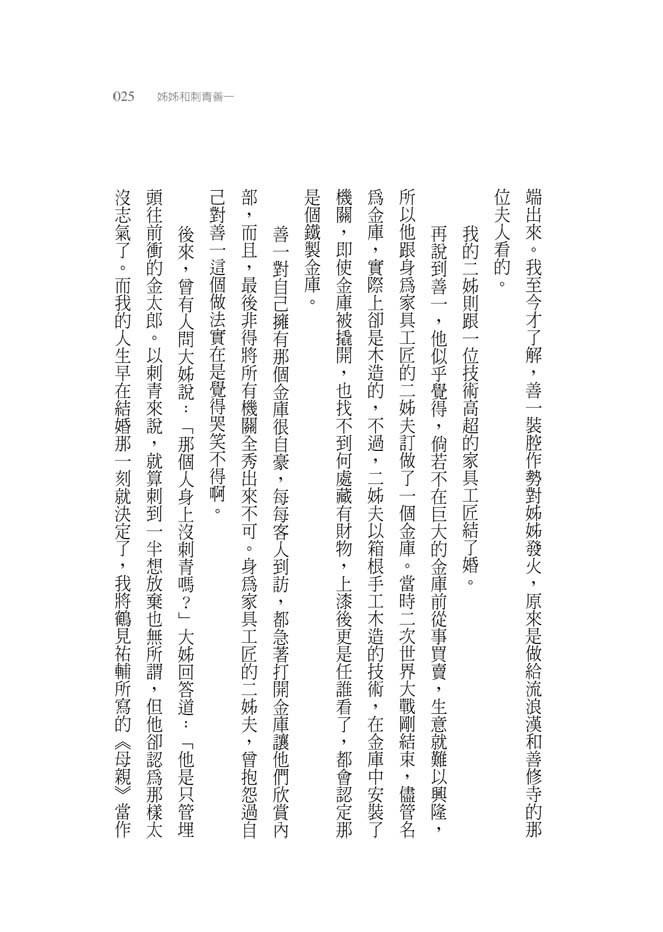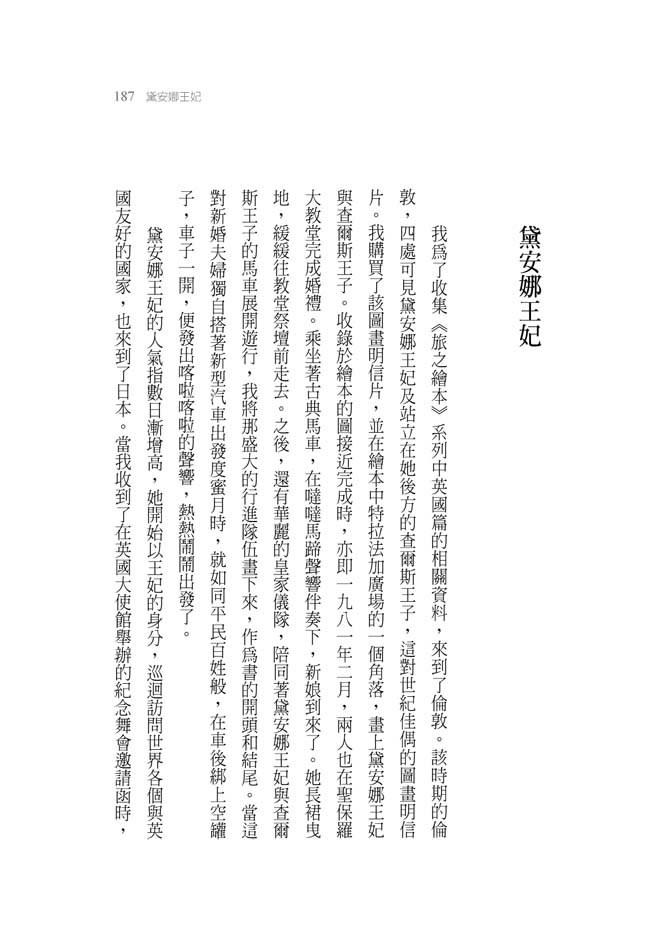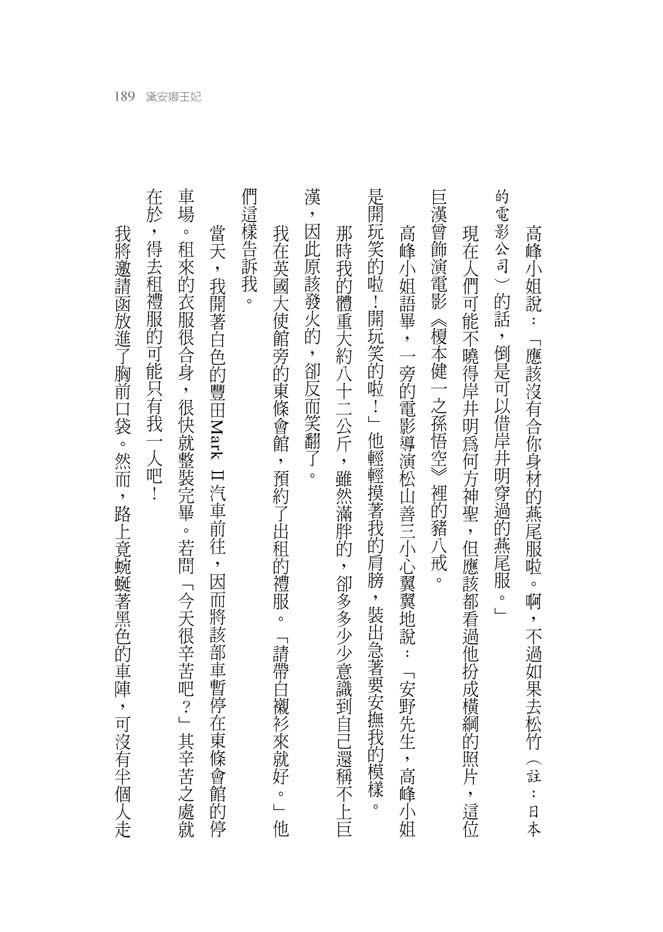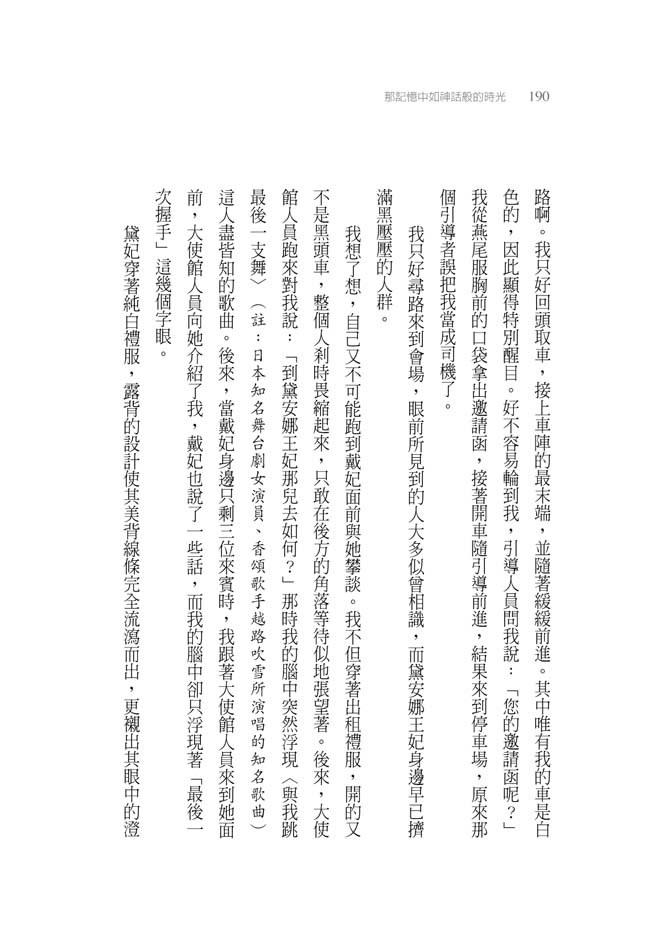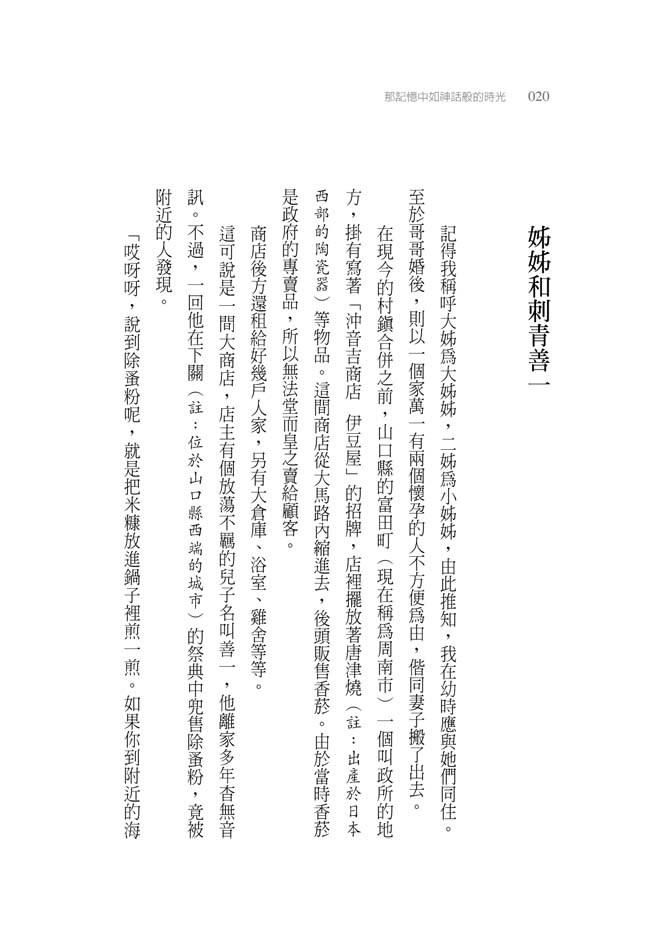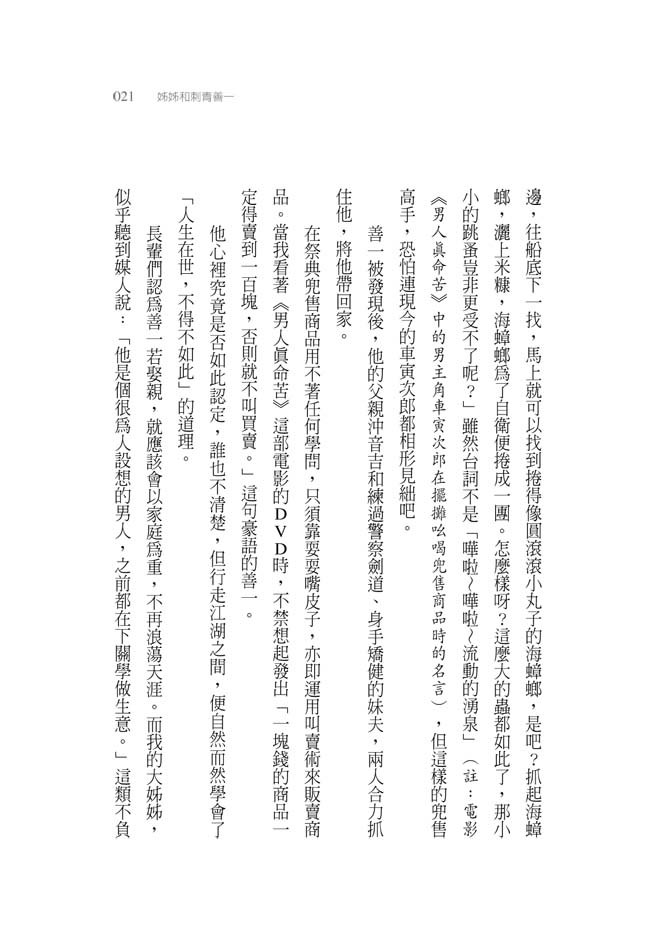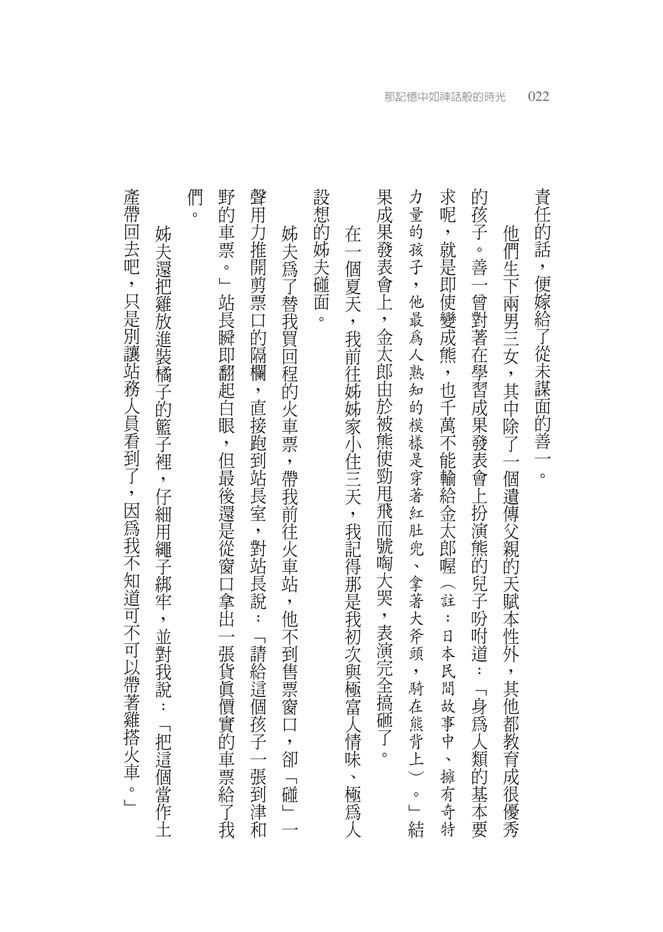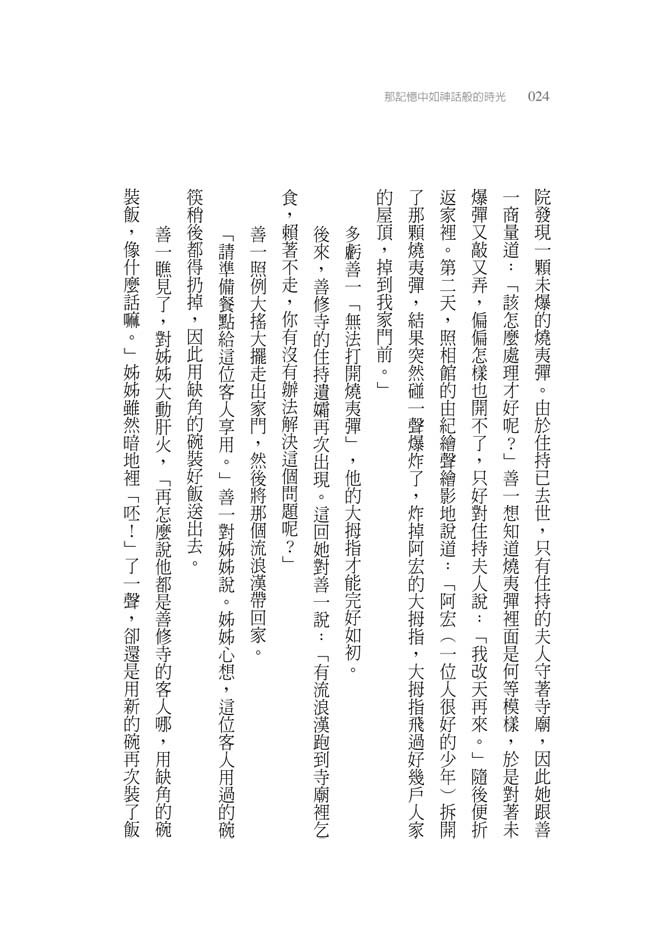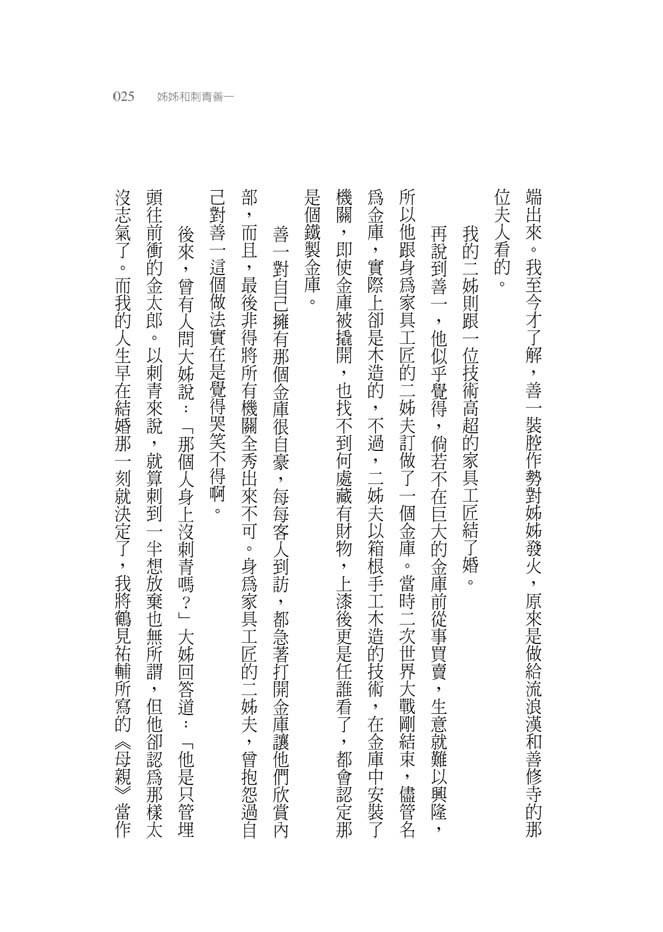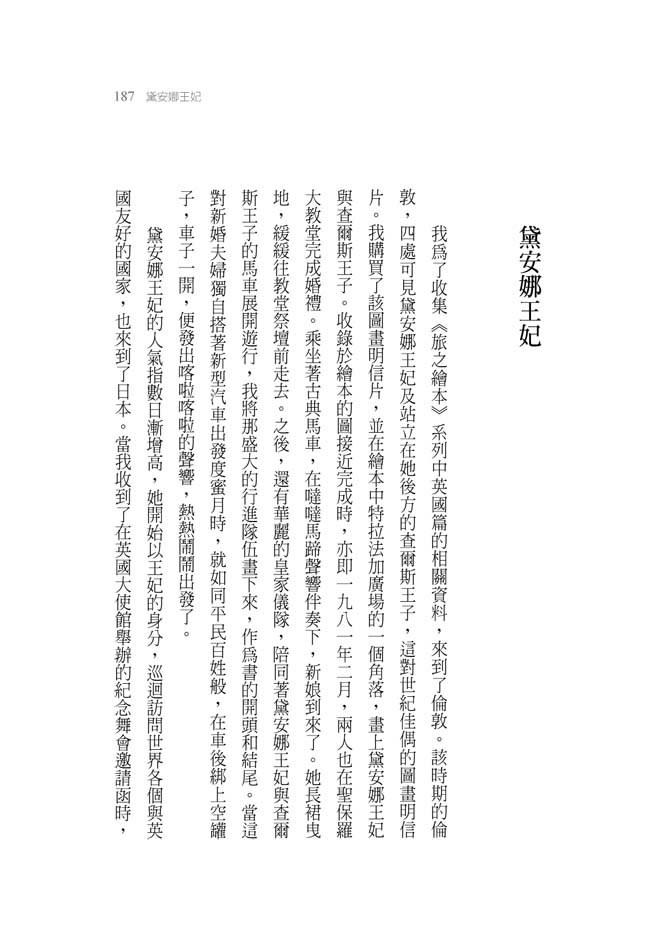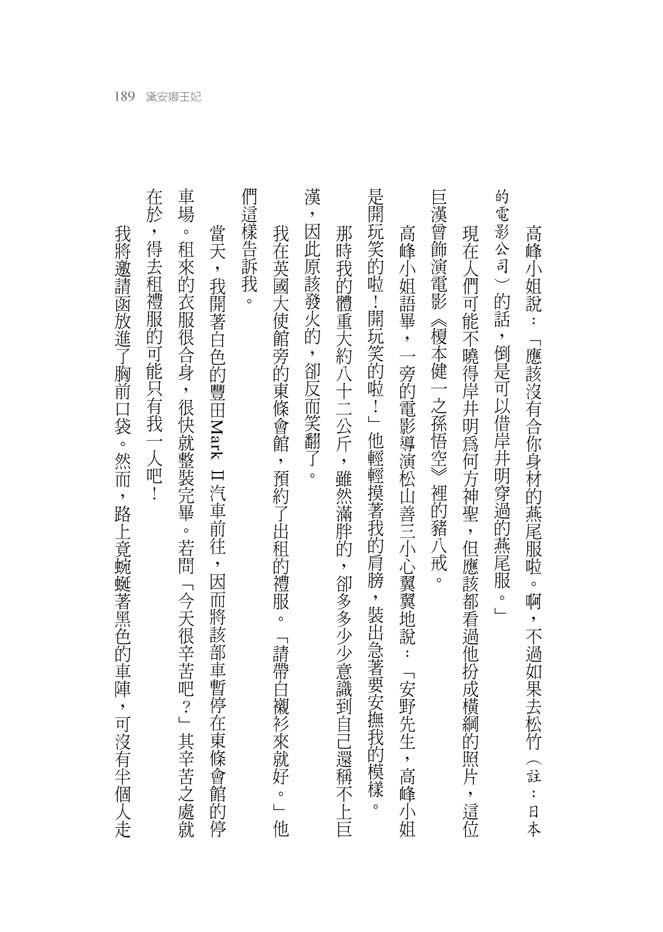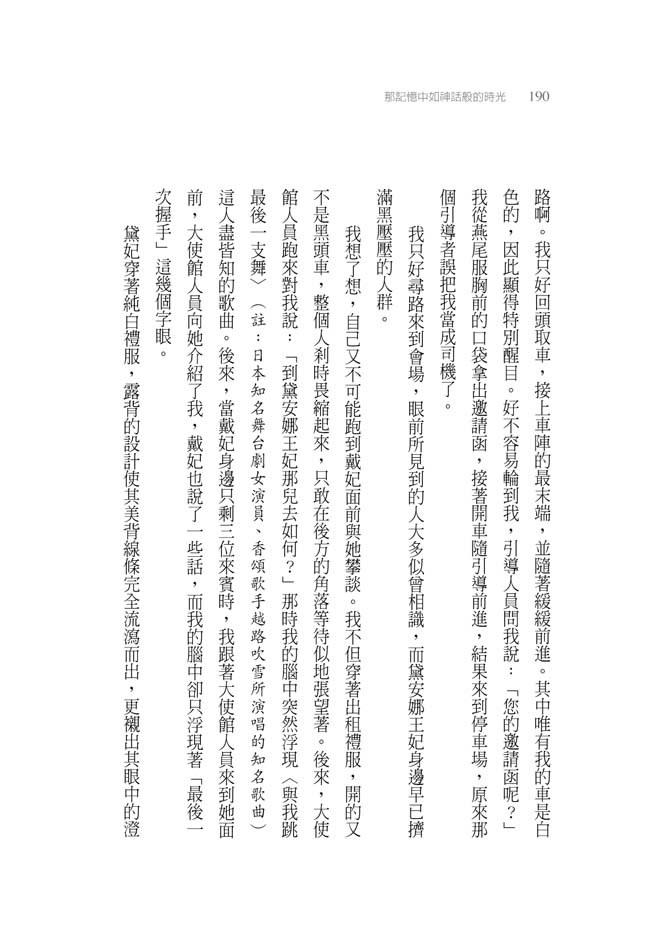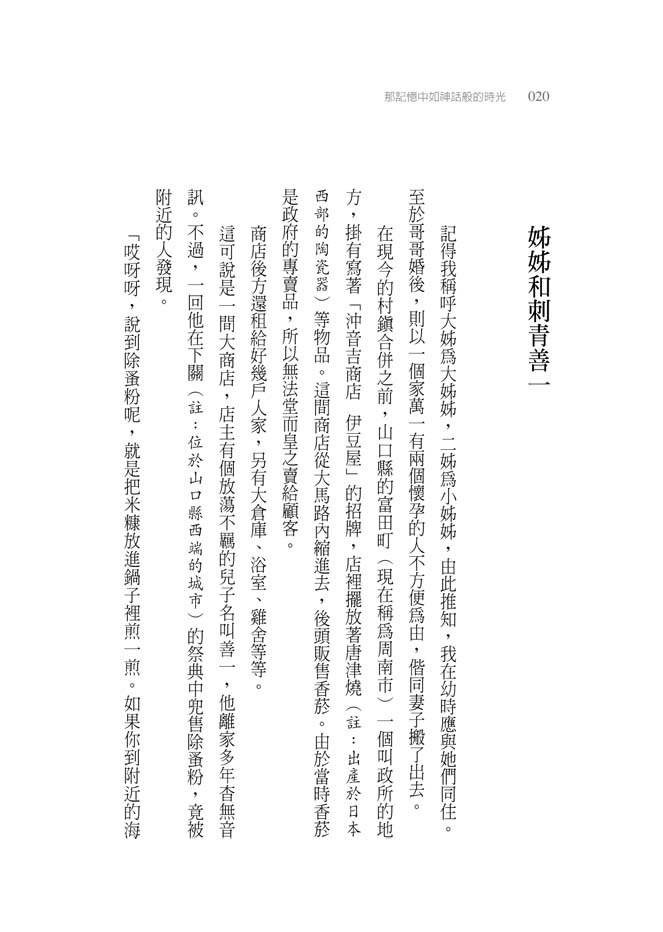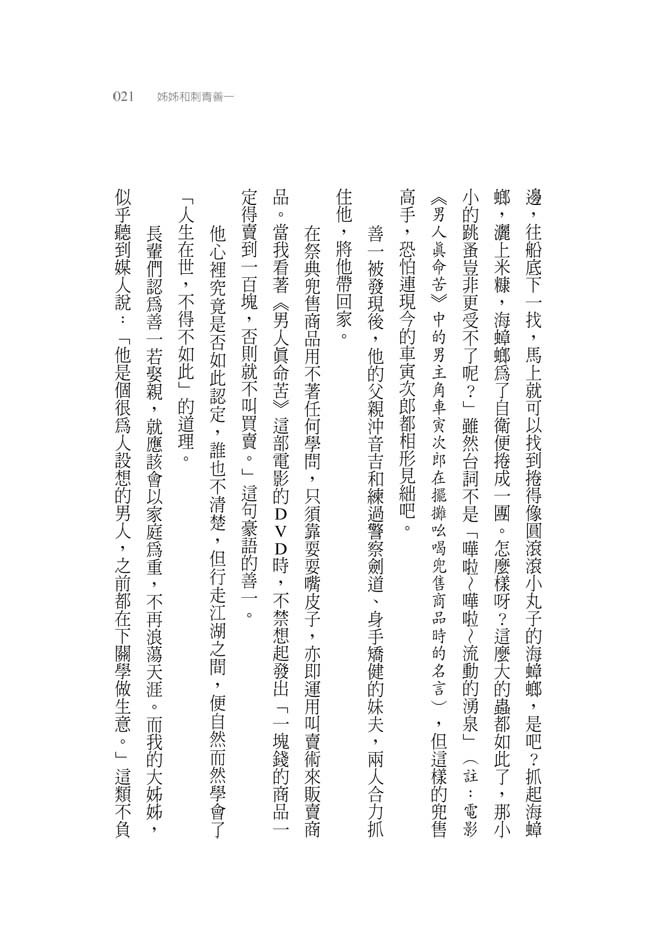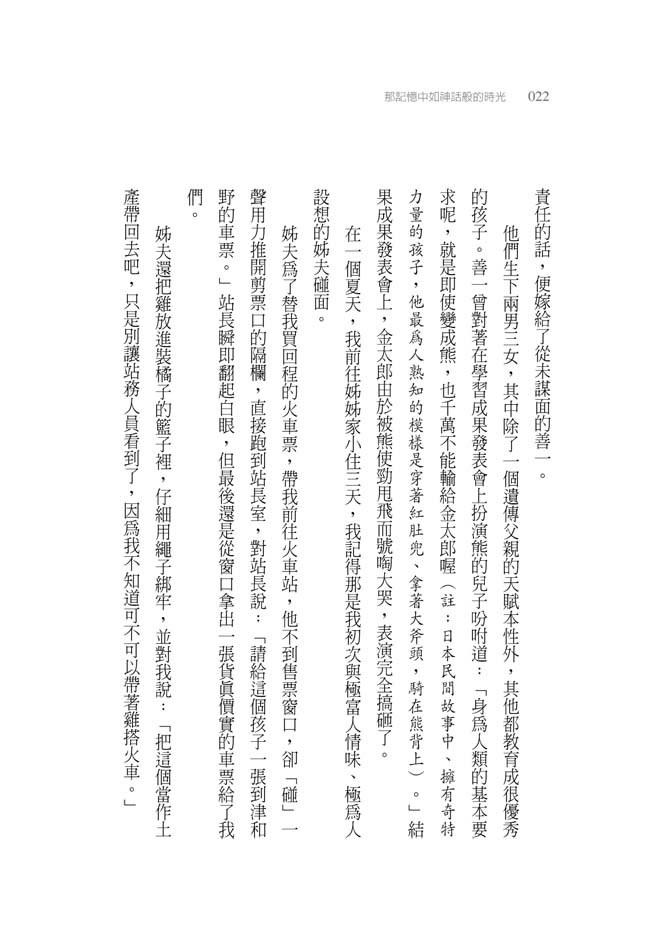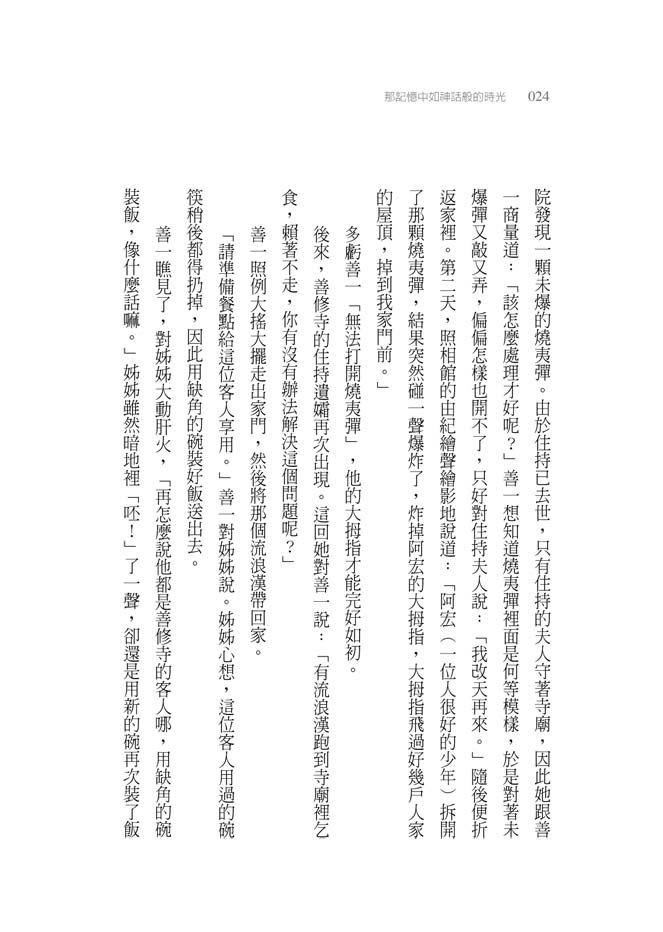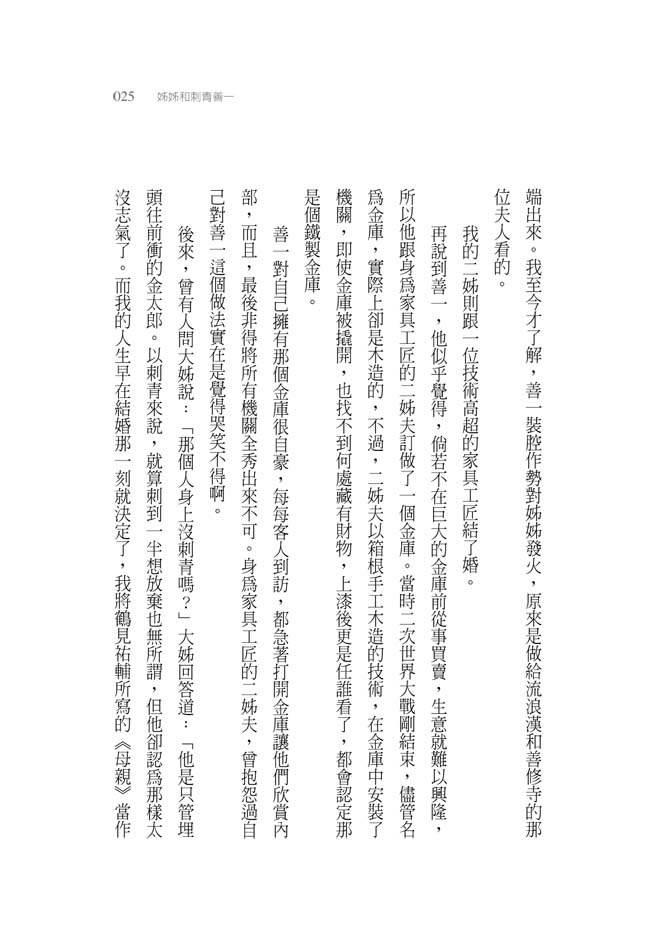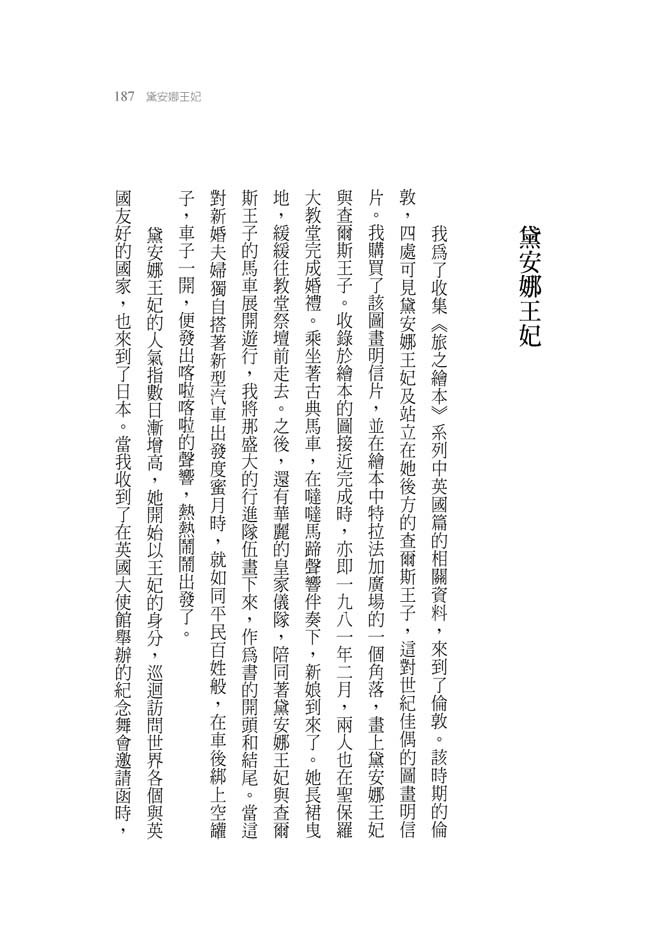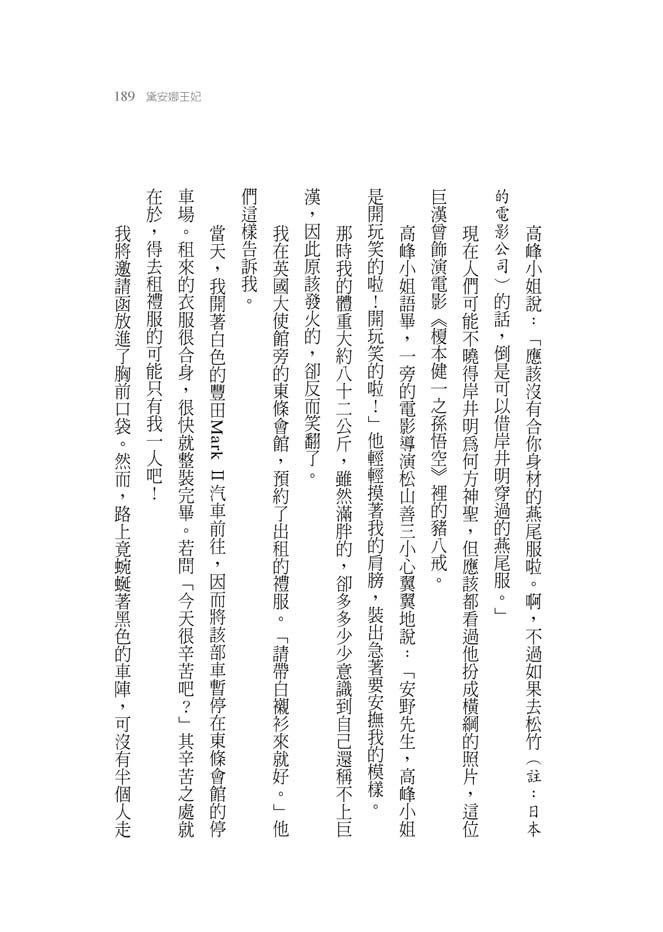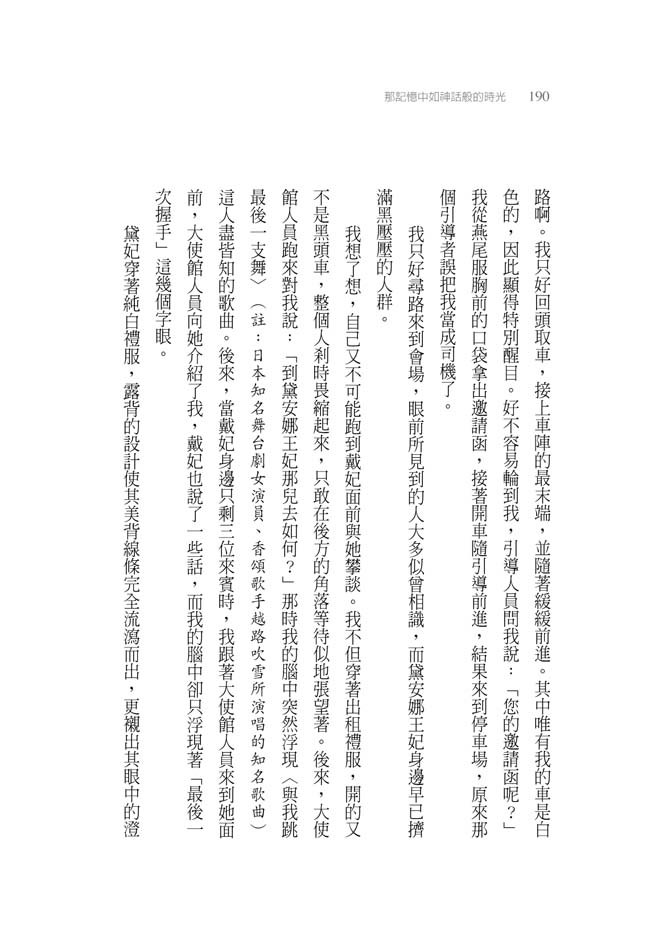姊姊和刺青的善一
記得我稱呼大姊為大姊姊,二姊為小姊姊,由此推知,我在幼時應與她們同住。至於哥哥婚後,則以一個家萬一有兩個懷孕的人不宜為由,偕同妻子搬了出去。
在現今的村鎮合併之前,山口縣的富田町(現在稱為周南市)一個叫政所的地方,掛有寫著「沖音吉商店 伊豆屋」的招牌,店裡擺放著唐津燒(註:出產於日本西部的陶瓷器)等物品。這間商店從大馬路內縮進去,後頭販售香菸。由於當時香菸是政府的專賣品,所以無法堂而皇之賣給顧客。
商店後方還租給好幾戶人家,另有大倉庫、浴室、雞舍等等。
這可說是一間大商店,店主有個放蕩不羈的兒子名叫善一,他離家多年渺無音訊。不過,一回他在下關(註:位於山口縣西端的城市)的祭典中兜售除蚤粉,竟被附近的人發現。
「哎呀呀,說到除蚤粉呢,就是把米糠放進鍋子裡煎一煎。如果你到附近的海邊,往船底下一找,馬上就可以找到捲得像圓滾滾小丸子的海蟑螂,是吧?抓起海蟑螂,灑上米糠,海蟑螂為了自衛便捲成一團。怎麼樣呀?這麼大的蟲都如此了,那小小的跳蚤豈非更容易受不了呢?」雖然台詞不是「嘩啦~嘩啦~流動的湧泉」(註:電影《男人真命苦》中的男主角車寅次郎在擺攤吆喝兜售商品時的名言),但這樣的兜售高手,恐怕連現今的車寅次郎都相形見絀吧。
善一被發現後,他的父親沖音吉和練過縣警劍道、身手矯健的妹夫,兩人合力抓住他,將他帶回家。
在祭典兜售商品用不著任何學問,只需靠耍耍嘴皮子,亦即運用叫賣術來販賣商品。當我看著《男人真命苦》這部電影DVD時,不禁想起發出:「一塊錢的商品一定得賣到一百塊,否則就不叫買賣。」這句豪語的善一。
他心裡究竟是否如此認定,誰也不清楚,但行走江湖之間,便自然而然學會了「人生在世,不得不如此」的道理。
長輩們認為善一若娶親,就應該會以家庭為重,不再浪蕩天涯。而我的大姊姊,似乎聽到媒人說:「他是個很為人設想的男人,之前都在下關學做生意。」這類不負責任的話,便嫁給了從未謀面的善一。
他們生下兩男三女,其中除了一個遺傳父親的天賦本性外,其他都教育成很優秀的孩子。善一曾對著在學習成果發表會上扮演熊的兒子吩咐道:「身為人類的基本要求呢,就是即使變成熊,也千萬不能輸給金太郎喔(註:日本民間故事中、擁有奇特力量的孩子,他最為人熟知的模樣是穿著紅肚兜、拿著大斧頭,騎在熊背上)。」結果成果發表會上,金太郎由於被熊使勁甩飛而嚎啕大哭,表演完全搞砸了。
在一個夏天,我前往姊姊家小住三天,我記得那是我初次與極富人情味、極為人設想的姊夫碰面。
姊夫為了替我買回程的火車票,帶我前往火車站,他不到售票窗口,卻碰一聲用力推開剪票口的隔欄,直接跑到站長室,對站長說:「請給這個孩子一張到津和野的車票。」站長瞬即翻起白眼,但最後還是從窗口拿出一張貨真價實的車票給了我們。
姊夫還把雞放進裝橘子的籃子裡,仔細用繩子綁牢,並對我說:「把這個當作土產帶回去吧,只是別讓站務人員看到了,因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帶著雞搭火車。」
我將提在手中的籃子放進座位下方,雙腳像踩在上頭似的,雞數度掙扎,那騷動直接傳抵我心臟,再加上車掌不停來回巡視,不但讓我原本雀躍的心情一掃而空,更絲毫沒有心思,趁著這個稀有搭火車的機會,欣賞一下窗外風光。回到家,我發現那隻雞已經死了,直到現在,我都還認為牠很可能是被我踩死的,因而內咎不已。
同樣在政所,有間名為善修寺的大寺廟。人們在寺廟庭院發現一顆未爆的燒夷彈。由於住持已去世,只有住持的夫人守著寺廟,因此她跟善一商量道:「該怎麼處理才好呢?」善一想知道燒夷彈裡面是何等模樣,於是對著未爆彈又敲又弄,偏偏怎樣也不開了,只好對住持夫人說:「我改天再來。」隨後便折返家裡。第二天,照相館的由紀繪聲繪影地說道:「阿宏(一位人很好的少年)拆開了那顆燒夷彈,結果突然碰一聲爆炸了,炸掉阿宏的大拇指,大拇指飛過好幾戶人家的屋頂,掉到我家門前。」
多虧善一「無法打開燒夷彈」,他的大拇指才能完好如初。
後來,善修寺的住持遺孀再次出現。這回她對善一說:「有流浪漢跑到寺廟裡乞食,賴著不走,你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
善一照例大搖大擺走出家門,然後將那個流浪漢帶回家。
「請準備餐點給這位客人享用。」善一對姊姊說。姊姊心想,這位客人用過的碗筷稍後都得扔掉,因此用缺角的碗裝好飯送出去。
善一瞧見了,對姊姊大動肝火,「再怎麼說他都是善修寺的客人哪,用缺角的碗裝飯,像什麼話嘛。」姊姊雖然暗地裡「呸!」了一聲,卻還是用新的碗再次裝了飯端出來。我至今才了解,善一裝腔作勢對姊姊發火,原來是做給流浪漢和善修寺的那位夫人看的。
我的二姊則跟一位技術高超的家具工匠結了婚。
再說到善一,他似乎覺得,倘若不在巨大的金庫前從事買賣,生意就難以興隆,所以他跟身為家具工匠的二姊夫訂做了一個金庫。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儘管名為金庫,實際上卻是木造的,不過,二姊夫以箱根手工木造的技術,在金庫中安裝了機關,即使金庫被橇開,也找不到何處藏有財物,上漆後更是任誰看了,都會認定那是個鐵製金庫。
善一對自己擁有那個金庫很自豪,每每客人到訪,都急著打開金庫讓他們欣賞內部,而且,最後非得將所有機關全秀出來不可。身為家具工匠的二姊夫,曾抱怨過自己對善一這個做法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啊。
後來,曾有人問大姊說:「那個人身上沒刺青嗎?」大姊回答道:「他是只管埋頭往前衝的金太郎。以刺青來說,就算刺到一半放棄也算不了什麼,但他卻認為那樣太沒志氣了。而我的人生早在結婚那一刻就決定了,我將鶴見祐輔所寫的《母親》當作聖經,因而能存活下來。」
鶴見祐輔這位政治家,乃哲學家鶴見俊輔的父親。他所寫的《母親》是一部十分知名的作品,享有極高的評價。(註:描繪存活在大正時期亂世的母與子的形象;全書鑲嵌了許多的人生格言,且傳達出過去面對逆境的女人的生活態度,以及女性的強韌、真知灼見和勇氣,深具啟發性。)
杖子
教室前,一年級的我們正在整隊,右列為男生,左列為女生。老師吩咐道:「請大家手牽手,到禮堂參加朝會。」有時我旁邊的人會故意往前站或往後站,因為我左手小指頭與手掌交接處長了雞眼,女生都說雞眼會傳染,所以不想跟我牽手。我很擔心若不牽手,會挨老師罵。那個常被筆芯所染黑的雞眼,我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我卻一點也不記得它後來在何時消失了。
升上二年級後,重新分配座位,坐我隔壁的女同學名叫杖子。她是單親家庭,只有父親,母親已不在。她沒帶便當時,用餐時間便獨自在運動場玩耍。儘管我坐在她旁邊,卻無法為她做點什麼,只能拚命耍寶,逗她發笑。
杖子是個愛笑的開朗女生,或許因為她早意識到,這並不至於有任何損失,而自己除了笑之外,也沒有其他能做的了。她身上洗得泛白的洋裝、長長的辮子及兩顆門牙,都令她極為引人注目。
據說,之前杖子的父親在位於附近村子的笹谷礦山進行爆破時發生意外,導致雙眼全盲。
她的父親後來當了琵琶法師,穿上褪色的黑色僧服,替鄰居們誦經消災祈福。我家替水井大掃除時,也請他來向水神祈福。祈福一結束,他將供奉的生米撒向空中,然後用手掌接住,問道:「手裡有幾粒米呢?」根據手中米的數量來預測若干事,然而我家卻不信這套。我和到家裡來的杖子一起玩,等待著祈福結束。杖子的父親手拿拐杖,她則握著柺杖在前引領,負起充當父親眼睛的任務。
我聽杖子的鄰人說,他們回家時,必須沿著水田旁狹窄的斜坡路往上走,那是即使張大眼睛仔細留意,也都十分危險的一段路。
當我們升上三年級,開始男女分班,杖子也被編進其他班級。
傳為佳話的「肉彈三勇士」(註:指一二八事變中,有三位日本士兵在上海市郊的廟行鎮陣地,抱著爆破桶破壞蔡廷鍇十九路兵修築的鐵絲網成功,三人因而身亡),就出現在此時期。大家爭相畫著勇士圖,從紙鎮、鉛筆盒到墊板,沒有一樣物品上頭看不到勇士圖,有人稱他們為昭和的軍神,所有日本人更高唱著這首勇士之歌:
廟行鎮是敵人的陣地
我們的友隊已展開攻擊
那時正好是冰封的農曆二月
二十二日的早晨五點鐘
查證後,我發現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的事。我憶起一九三三年,松岡洋右全權大使(在滿州國獨立和日本的權益不受承認的狀況下)不得不遵從國家指示,在國際聯盟總會的會場上,宣告日本退出此聯盟。當時松岡洋右於會場上,僅說了一句「再會」,便拂袖而去。這張新聞照片不斷出現在當時的壁報上,也在後來的新聞影片中一再被播放,簡直如同演員從貫通觀眾席的舞台側邊通道退場似的,全日本所有人都為他鼓掌叫好。松岡洋右本人曾說過,原以為自己回日本後,將被大批群眾圍勦,未料卻受到極盛大的歡迎,令他至感驚訝。
當時仍是孩子的我們,紛紛議論著:「那個松岡洋右用英語演講耶,是英語喔。」因而對他充滿敬意。後來我才知道,松岡洋右的家鄉在山口縣的光市。
我後來曾待過位於光市室積的師範學校研究科。由於英語被認定為敵國語言,在戰爭期間完全不可使用,因此我們認為會講英語的人都很了不起。
退出國際聯盟時,日本等於背離世界,陷入孤立,並開始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路。不過,連銅像都已豎立、並有歌曲傳唱的「肉彈三勇士」故事,到今日卻很少被人提起。
在那之後,我不曾與杖子交談,也斷了音訊。大約相隔六十年後,才有機會再與她見面。那是因為我有個電視節目計畫在津和野進行拍攝,NHK松江電視台的長谷川芳弘,打算以「面對面」對談的型態呈現。他告訴我只要是我想見的,不管任何人,他們都會幫忙找到。於是我跟他們說了「杖子」這個名字。
看過這個電視節目後,有人對我說:「安野先生,我看到你和以前的女朋友重逢的情景喔。」竟然導致某些觀眾有這樣的誤解,製作人在企畫前最好考量周詳點呀。
杖子說她已經結婚,有四個很優秀的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由於家裡種田,除了擔心野豬毀壞莊稼外,再無其他煩惱。
邊耕地種田,邊拉拔四個孩子念書著實了不起。我深切地認為,兒時吃的苦絕不會白費。像我才不過供兩個孩子念大學罷了。
同班同學中,許多人的家庭遠比杖子來得富裕。我卻想:「比她幸福的人有幾位呢?」
我認為在杖子的心底深處,一定有一股想超越貧困的強烈自尊。
杖子的故事二○一一年二月五日刊載於《日本經濟新聞》「我的履歷表」專欄時,這一段引起了極大迴響。許多人因此重新思考了「到底何謂幸福?」
「到底何謂幸福?」依據現今日本的狀況而言,不外是:一定得先考進東京大學,如此一來便較為容易進入一流企業或當上政府官員。接下來娶個好妻子,過著安穩的生活,然後生下優秀的孩子。」這樣的想法,在不知不覺中,有如蝴蝶效應般地在人們的腦子裡烙下這就是「幸福之路」的印象。就連我也不得不如此認為。
為了走上這條道路,雙親從孩子一出生,就成了教育媽媽。孩子爭相進補習班補習,給考生用以準備考試的出版品異常蓬勃,學校也以考進東大的錄取率來互相競爭。這幅圖畫描繪出的升學熱,不管何等正確的言論都難以抵擋。
我之前曾看過NHK所播放《世界記憶力選手權》的節目。一旦開始認為記憶術有助於考試,記憶力強的人腦袋比較聰明,所以學問被過分簡化為記憶力的問題。以我的想法而言,記憶,所記住的多是經查證就能知道的事,少有創造的成分存在。
現今的考試,考的多半是記憶力,且為了便於計分,往往採取電腦閱卷,即使完全不思考,也可能猜中答案。另一方面,即使想出好題目,卻也由於考量到難度過高,難以招生,於是捨棄不用。最後,考試的形態竟可笑地決定了教育的方向。
正岡子規(註:日本明治時代的文學宗匠)曾斷言,由於存在著這種型態的考試,教育將變樣,如同一滴墨汁滴在清水裡,清水就變了色。
回到杖子的身上。我想因為這個故事而感動的人中,應該多少對於「四個孩子都大學畢業」這點深有所感吧?
或許有人感到疑惑:之前所寫到的「何謂幸福」,竟用「進大學」來作為評斷的標準,豈非過於功利嗎?
但確切來說,杖子的幸福並不在於「讓四個孩子都進了大學」。她的人生儘管從一開始就受苦受累,但最後終於靠著自己的力量贏得幸福。我想,孩子進大學令她深感喜悅,或許是她從中獲得幸福了吧。人們必須好好思考:「幸福的道路不只一條」,這正是我想表達的。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日,津和野的安野光雅美術館屆滿十週年,當時我們舉辦了小學同學會,我得知杖子依然健在,只是必須坐輪椅,無法行動自如。
朋友帶來小學畢業典禮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裡頭有包括杖子在內的畢業典禮照。由於畢業後男女分校,我因而是第一次見到那張照片。她的眼睛不偏不倚地望向前方,那張臉散發著應該稱之為覺悟的莊嚴感。
父親離世
我當上老師,月薪為一百五十元。那是一小截捲煙賣十元,長雪茄賣十五元的年代。然而,父親完全不清楚所謂通貨膨脹這回事,對於我能擁有一百五十元的月薪感到異常欣喜,而這也意外地成了我最終的孝行。
此外,戰時母親瞞著父親投保壽險,每月規規矩矩交付十五錢,並於戰後領回五百元。以前的五百元可買我家附近的兩層樓房,但戰後的五十條香菸,就能讓這些錢煙消雲散。
加上當時糧食嚴重不足,因此得將炊煮過的大麥與米混合在一起,重新煮過一回再吃。
母親遠行前去拜訪親戚的前一晚,父親會事先將米預備好才去睡,如此一來,隔日早上只消進行煮飯的程序即可。一日清晨,父親似乎想父代母職,大喊著「飯煮好了」,將我叫醒。但我發現米飯半生不熟,難以入口。若等重煮一遍,絕對會遲到,所以我決定不吃就離開。當我準備出門時,送我到門口的父親,竟對我開口說道:「對不起」。
我還以為我聽錯了呢。當時,一片片柿葉的陰影正落在父親的臉龐。
父親年事已高,儘管總給人添麻煩,卻仍為一家之主。例如弟弟要給人當養子,父親亦擁有絕對的發言權。不過,由於家裡的生活費乃由我負擔,所以不知不覺中,家庭的主導權竟轉移至我身上。我走路下山時,一邊自問自答著:「我怎麼至今才意識到這種轉變呢?」那是自我出生以來父親頭一遭向我道歉,我一步步往山下走,臉上的熱淚也一滴滴滾落。
父親七十歲時,由於高血壓引起腦梗塞。我現在常想,將生病的他獨自留在家裡,竟未發生火災,一切平安,實在堪稱奇蹟。此外,我也會想,那個飯未煮熟的早晨,父親究竟吃了什麼才去睡的呢?
不久,父親就臥床了。不過只要打開拉窗,就能看到上學的孩子們走過面向山谷的小路。當我們將菸草塞進菸斗,點上火,讓父親啣著菸斗,他便極為享受地吸起菸來。
想起我十六歲時,曾有樣學樣地學吸菸,由於心想父親可能發火,所以離他遠遠的,未料父親竟對我說:「我有敷島牌的香菸。」並拿出那款高級的香菸來給我享用。我確定父親實在太過溺愛我了,可憐的他四十八歲才得子,以致這般期待我早日長大成人。
他身體健朗時,曾受託去趕走名為青大將的大蛇。上山砍柴,總是揹著足以遮蔽住整個身體的大捆大捆木材。有時他會去幫忙滅火,還會站在脫韁馬匹面前擋其去路,不讓馬匹脫逃。儘管他釣香魚的技術不佳,卻很會製作下河時穿的草鞋以及釣竿。至於酒,他一滴也不沾,因此最討厭發酒瘋的人,即使家裡旅館的客人喝醉酒,他也不肯加以照顧。他常與一位來自奈良縣橿原市經營「大佛堂藥局」、名為喜多的人,一塊兒下圍棋。
我還想起過去有一回,在某家和服店那兒的電線桿前,聚集了黑壓壓的一群人。我從後頭的縫隙望過去,看到一個人倒在那兒,全身直到大腿上端都覆滿沙土,由於他的禿頭與我父親極為相似,我不禁心裡一驚,趕緊飛奔回家,還好父親好端端的,我也才發現自己錯認了。後來又有一回,父親確確實實出了狀況,他沒踩穩梯子,摔下來受了重傷。正好也在現場的喜多,連忙將他送往醫院。自那時起,我心裡總計掛著父親的身體狀況。
過去的勇士而今卻只能攤臥在床上。
母親說,若父親一直躺臥同一側,會長褥瘡,於是我們便替他翻身,每回一翻身,他總忍不住大聲叫痛,也痛進我們心裡。儘管如此,可憐的父親終究還是長出了褥瘡。
插一段題外話,司馬遼太郎、棟方志功(註:日本版畫家)、《阿爾卑斯登山記》的愛德華‧惠波(註:英國登山家、版畫家)以及約翰‧韋恩(註:美國知名演員),都是在七十二歲過世的。
法國文學研究者井上究一郎先生曾寫過:「和父親同干支,年紀相差四十八歲的孩子是父子差距的最極限吧。而我也與我的父親相差四十八歲,屬同樣的干支呀!」
一天半夜,方寸全失的母親將我叫醒,當時父親已經嚥氣了,儘管於茅草屋離世,但他終究回到自己的故鄉,在那裡畫下人生句點,當時他七十二歲。入棺時,抬著父親雙腳的是我的姊夫善一。
黛安娜王妃
我為了收集《旅之繪本》系列中英國篇的相關資料,來到了倫敦。該時期的倫敦,四處可見黛安娜王妃及站立在她後方的查爾斯王子,這對世紀佳偶的圖畫明信片。我購買了該圖畫明信片,並在繪本中特拉法加廣場的一個角落,畫上黛安娜王妃與查爾斯王子。收錄於繪本的圖接近完成當時,亦即一九八一年二月,兩人也在聖保羅大教堂完成婚禮。乘坐著古典馬車,在噠噠馬蹄聲響伴奏下,新娘到來了。她長裙曳地,緩緩往教堂祭壇前走去。之後,還有華麗的皇家儀隊,陪同著黛安娜王妃與查爾斯王子的馬車展開遊行,我將那盛大的行進隊伍畫下來,作為書的開頭和結尾。當這對新婚夫婦獨自搭著新型汽車出外旅行時,就如同平民百姓般,在車後綁上空罐子,車子一開,便發出喀啦喀啦的聲響,熱熱鬧鬧出發了。
黛安娜王妃的人氣指數日漸增高,開始以王妃身分巡迴訪問世界各個與英國友好的國家,也來到了日本。當我收到了在英國大使館舉辦的紀念舞會邀請函時,大吃了一驚。或許將之說成「自天外飛來的邀請函」更為適切吧。
可能因為我在《旅之繪本Ⅲ英國》中描繪了婚禮進行的儀式,英國大使館的某位人士看到了,因而將我寫上來賓名冊。
邀請函上有「Black tie」(註:意為「著正式服裝」)此字眼,我並不清楚其意。我有時會前往女演員高峰秀子家吃晚餐,當晚,我請教了她。「意思是請你穿著燕尾服前往。」我哪有那種東西呀?況且那種衣服不是在變裝舞會上穿的嗎?「只能去租禮服了。」我喃喃自語著。
高峰小姐說:「應該沒有合你身材的燕尾服啦。啊,不過如果去松竹(註:日本的電影公司)的話,倒是可以借岸井明穿過的燕尾服。」
現在人們可能不曉得岸井明為何方神聖,但應該都看過他扮成橫綱的照片,這位巨漢曾飾演電影《榎本健一之孫悟空》裡的豬八戒。
高峰小姐語畢,一旁的電影導演松山善三小心翼翼地說:「安野先生,高峰小姐是開玩笑的啦!開玩笑的啦!」他輕輕摸著我的肩膀,裝出急著要安撫我的模樣。
那時我的體重大約八十二公斤,雖然滿胖的,卻多多少少意識到自己還稱不上巨漢,因此原該發火的,卻反而笑翻了。
我在英國大使館旁的東條會館,預約了出租的禮服。「請帶白襯衫來就好。」他們這樣告訴我。
當天,我開著白色的豐田MARK II汽車前往,因而將該部車暫停在東條會館的停車場。租來的衣服很合身,很快就整裝完畢。若問「今天很辛苦吧?」辛苦之處就在於,得去租禮服的可能只有我一人吧!
我將邀請函放進了胸前口袋。然而,路上竟蜿蜒著黑色的車陣,可沒有半個人走路啊。我只好回頭取車,接上車陣的最末端,並隨著緩緩前進;其中唯有我的車是白色的,因此顯得特別醒目。好不容易輪到我,引導人員問我說:「您的邀請函呢?」我從燕尾服胸前的口袋拿出邀請函,接著開車隨引導前進,結果來到停車場,原來那個引導者誤把我當成司機了。
我只好尋路來到會場,眼前所見到的人大多似曾相識,而黛安娜王妃身邊早已擠滿黑壓壓的人群。
我想了想,自己又不可能跑到戴妃面前與她攀談。我不但穿著出租禮服,開的又不是黑頭車,我整個人霎時畏縮起來,只敢在後方的角落等待似地張望著。後來,大使館人員跑來對我說:「到黛安娜王妃那兒去如何?」那時我的腦中突然浮現「與我跳最後一支舞」(註:日本知名舞台劇女演員、香頌歌手越路吹雪所演唱的知名歌曲)這人盡皆知的歌詞。後來,當戴妃身邊只剩三位來賓時,我跟著大使館人員來到她面前,大使館人員向她介紹了我,戴妃也說了一些話,而我的腦中卻只浮現著「最後一次握手」這幾個字眼。
黛妃穿著純白禮服,露背的設計使其美背線條完全流瀉而出,更襯出其眼中的澄澈清純與如花朵般盛放的美麗。
後來,她和查爾斯王子出現婚姻破裂的傳聞,所有人皆打抱不平地說道:「那個老女人卡蜜拉到底哪裡好啊?」
甜蜜的時光極為短暫。黛安娜王妃和查爾斯王子在一九九六年正式離婚。戴妃命途多舛,也因此正好成了媒體追求收視率的犧牲者。一九九七年八月將要結束的那天,由於受到狗仔隊的追蹤,在沿著塞納河的隧道中,黛妃所乘坐的賓士轎車方向盤失控,猛烈撞上塞納河該側的柱子。黛妃芳華正盛,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卻因這起事故,在三十六歲時便已殞落。
後來我有機會前往巴黎,曾麻煩司機載我前往戴妃發生車禍的現場。「只能開車經過,那兒無法停車。」司機說。我回答道:「那樣就夠了。」於是司機往前行駛而去。「就是這裡。」「啊!」在這樣極為短暫的對話中,車便滑行而過。接著車子又開了好一會兒,我才下車,塞納河於我眼前悠悠流過。為了那「最後一次握手」,我獻上了短暫的默禱。
和司馬遼太郎先生漫遊街道
我與司馬遼太郎先生一起度過的採訪之旅,是近年不曾有過的愉快時光。晚飯後,《週刊朝日》的前總編輯等人,為了聆聽司馬先生開講,總是蜂擁而至。
由於每晚的節目不盡相同,因此就算得付入場費大家也毫無怨言。司馬先生不知自何處湧現靈感,總是口若懸河,使聽講者懸著一顆心,殷殷期待結尾究竟為何。而今大家皆惋惜地說道,若能將司馬先生所言錄音下來,那不知該有多好。然而說歸說,卻為時已晚。
司馬先生對於他所在意的人,完全不分尊卑上下。就連我初次與他會面,他都自己先伸出手來對我說:「請多多指教。」每當有不曾來過的人加入我們,司馬先生還會將之前大家聊了什麼,也就是截至「上一期」為止的故事大要,向對方說明,好讓對方能立即融入其中。
他提到自己的體質特殊,不能吃蝦蟹類,就連酒都不能與熱開水一起喝。他的夫人狀況與他相仿,所以他說:「不管吃什麼,只要那東西有眼睛的話,我們就得避開。」由於如此,他們夫妻倆若前往國外旅行,簡直像賭上性命似的。就我從旁看來,司馬先生即便工作後收到稿酬,除了買書外,可說完全沒有其他娛樂。
另外,司馬先生所繪的圖十分值得玩味,例如當我初次看到《美國素描》(新潮社)的封面時,受到的巨大的震撼竟讓我忍不住想:「我還需要繼續畫下去嗎?」
司馬先生曾提出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畫出來的蘋果何以比真正的蘋果要來得更美呢?」我總想或許到了某個時點,自己便能明快地說出答案,然而轉眼間都已到了今天。在衫本秀太郎的《京都生活》(筑摩書房)這本書中,有篇很棒的文章對此問題有精闢的回答,但由於篇幅太長,我便不引用了。
這個世界實在很小,司馬先生的夫人和我弟弟的太太,兩人是現今大阪樟蔭大學的同班同學,小說家田邊聖子女士也是她們的同窗。司馬先生還在世時,並未提及此事。我與司馬夫人聊到這件事,她還清楚地記得曾到我家來玩過。
由於為《街道漫步》系列中的《濃尾參州記》進行採訪,我們停留在名古屋。我僅能待一天,就得回東京去,因此似乎有其他人傳言我為了某種理由得趕回東京。我向司馬先生提及此事,他說:「安野先生真要停留在何處,這又有什麼重要呢?」他一說完這些話,他所搭的電梯門就關上了。當時,竟是我與司馬先生漫長相處過程中一個驀然出現的句點。
司馬先生離世時,我的淚水停也停不了。與司馬先生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是如此充實滿足,儘管期盼那樣的時日永無止盡,然而事實上,這世界終究是「白衣蒼狗多翻覆,滄海桑田幾變更」呀!
七十二歲!我的父親去世時同為七十二歲。司馬先生辭世至今已十五年。但電視連續劇《坂上之雲》的播放,證實司馬先生的粉絲絲毫未曾減少。
我所收到的司馬先生的遺物為兩隻鞋子。這雙鞋很不可思議地與我雙腳的尺寸完全吻合。我曾穿著這雙鞋前往東大阪市。由於我說:「東大阪市的道路諸君,如果你們記性極佳的話,一定記得司馬先生曾穿著這雙外國製的鞋子回來過。」不過東大阪市民美術中心的酒野先生看到這雙鞋,卻說:「這是東大阪製造的,因為我父親有一雙同款新鞋,我帶來讓您看看。」我則一副氣焰很盛的模樣說道:「這可是司馬先生的鞋啊!」真可稱得上狐假虎威啊。
為了進行司馬先生《街道漫步》中的《台灣紀行》採訪,我們也前往台灣。
在臺南新營有間名為沈內科的醫院。我與《週刊朝日》編輯池邊史生先生於該間醫院前等待。我們並不知原委,只管瞪大眼睛看著,恰如《間諜大作戰》那部電影的場景般。
過了許久,司馬先生和他的責任編輯村井重俊抵達了。另外還有位我未曾見過、十分寡言的男子。他們到達後,我們一行人便準備前往戰前日本人聚集的區域瞧瞧。
戰敗近五十年,該地已然人事全非,唯有那住宅街依然殘留著日本風情。
那位沉默的男子站在我們背後,一邊伸長脖子,一邊從側邊張望著街道,那模樣極為怪異。
司馬先生說:「他呀,是搶到三島事件(註:指作家三島由紀夫闖入東京陸上自衛隊營區切腹自殺的事件)獨家新聞的人。」
「別看他外表那個樣子,實際上卻絕非什麼怪人。」司馬先生的話裡頭藏有這樣的意思,不過由於並沒有任何人這麼想,所以此辯解除了傳達他是位新聞記者外,還富含暗示的意味。我知道那位沉默男子平白被嘲慣了,但若不用此種嘲弄的說法,要說明他的舉止行為恐怕得花費過多的時間與精神吧。
他名為田中準造,是大阪新聞的記者,童年隨著爸媽來到台灣,當時他被母親揹在背上,在花蓮港下船。
他念小學六年級時,日本戰敗,他也因此離開熟悉的日本人聚集區,從基隆港搭船返日。闊別數十年,他才再度回來,因此理所當然地出現了不同於一般的舉動。
據他回憶,每每他不想去上學,就使出裝病的招數,並被帶到沈內科醫院看病。雙親總是擔心地問沈醫師說:「沒事吧?」沈醫師便回答:「沒事,我已經讓他在嘴裡含了糖球。」
沈醫師的兒子當中,有一位是準造君的同學,他們常常在一起玩得很開心,準造君還將日本的雜誌和書籍借給他閱讀。當時的小學分為普通小學,和只有台灣人念的公學校。以現今的標準而言,這自然稱為差別待遇。當公學校的孩子從普通小學前面經過,一些混帳孩子就對他們丟石頭,公學校的學生四散奔逃,公學校的老師便怒氣沖沖地跑出來罵人,這在當時都是想當然爾的事。
然而日本戰敗了,情勢逆轉。以前念普通小學的沈君也轉到公學校就讀。這下子變成公學校的孩子對著普通小學的孩子丟石頭。這同樣是想當然爾的事。然而,準造君說,當他看到丟石頭的小孩當中有沈君的身影,他體諒了沈君,也認為沈君並沒有錯,但每每一思及此,卻總是忍不住感到鼻酸。
沈君後來成為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的教授。
我記得在我們離開台灣的前一晚,沈君穿越日本人所設下的嚴密警戒線,前來還書給準造君。
那是離別的信號,準造君由於回到了少年時代而忍不住落下熱淚。
我們(池邊、村井,當然還有《週刊朝日》的山本朋史)以《高中三年級生》的旋律填上新歌詞,打算在離別那天,唱給準造先生和他的夫人聽。在填詞過程中,我們也都淚流不止。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歌詞:
啊,新營小學
夕陽染紅了校舍
榆樹的樹蔭下傳來嘻鬧聲
啊,新營小學
儘管我們即將分隔兩地
但同學卻是一輩子的
你拿著我借給你的重要書籍前來歸還
那是離別的信號
啊,新營小學
儘管我們即將分隔兩地
但同學卻是一輩子的
在台灣的最後一晚,我教輔仁大學半工半讀的女學生唱著《仰望師恩》《故鄉》《紅蜻蜓》《朦朧月夜》等歌曲。
準造先生明知無法帶著花蓮港的大理石搭上飛機,卻還是將大理石帶在身上。當時,他的內心激動不已,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