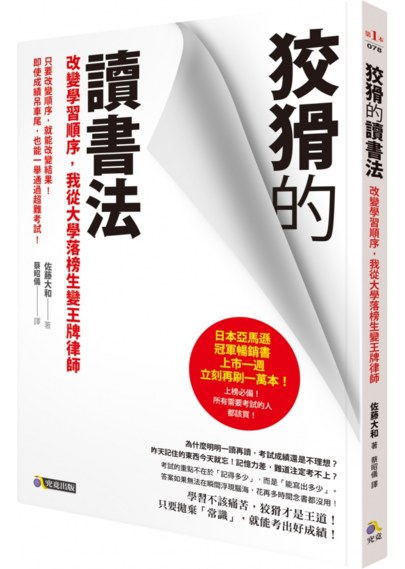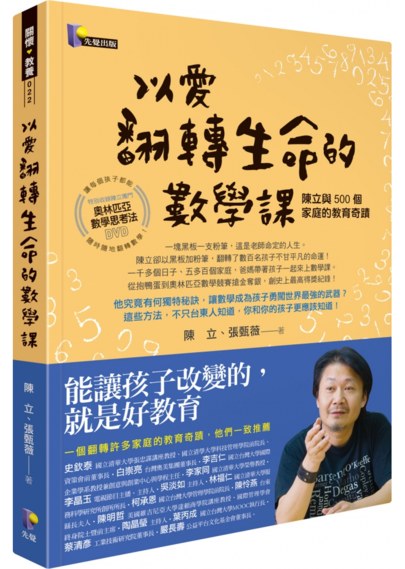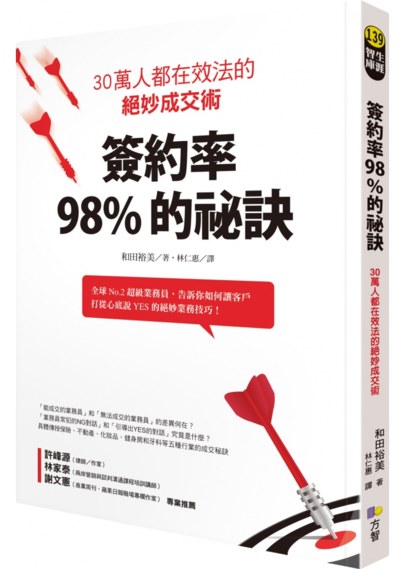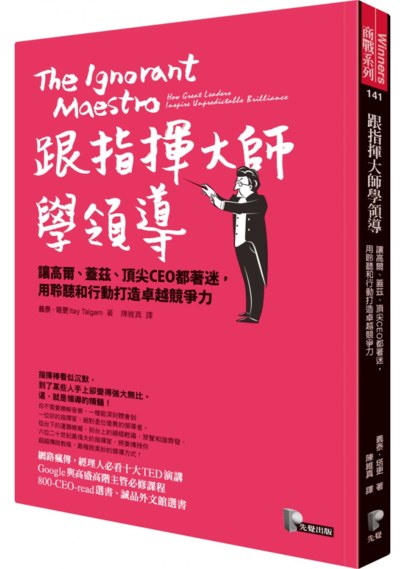日落後,雲層轉厚,遮住了夜空中的星星。席歐妮關燈睡覺時,雨開始落下。起先是稀疏小雨,接著變成傾盆大雨。一陣強風呼嘯過屋簷,吵醒了席歐妮,狂風撕落了牆壁和籬笆上部分的紙幻術,大概沒有任何等級的防水咒能抵抗這麼強大的暴風。
夜間漸漸轉冷,雨勢變成冰雹,劈劈啪啪敲在屋頂和窗戶上,猶如上千封電報一起傳送。席歐妮拿枕頭蓋住頭,躲回夢鄉……
臥室裡,雨水包圍住她。頭上的屋頂消失不見,雨水傾洩,狠狠淋在家具上,將紙藝品從牆上一一剝除。席歐妮穿著有釦白襯衫、黑裙,繫上灰領帶,站在房間正中央。這是她在塔吉斯帕夫魔法天賦學校的學生制服。她站在一個排水孔上方,似乎有某個東西塞住了。雨水在腳邊積成水窪,她一次又一次用鞋子去踹排水孔,試圖想逼水勢往下。
但塞在那裡的東西卻毫不退讓。
她轉過身,卻找不到房門,家具也全部消失,徒留她在這些木頭和雨水中。雨滴漸漸變大,現在落得像是細長的縫衣針,飛濺在她皮膚上,從制服滴下,落進她腿邊那不斷翻攪、不斷漲起的小湖。冷冷的水爬到膝蓋,接著到了大腿。
席歐妮的心跳都要停了。她瘋狂地涉過黑水,尋找任何可以站上去的東西,卻什麼也找不到。沒有桌子,沒有床,沒有梯子或凳子。到處都沒看到門,就連窗臺都消失在不斷衝擊的暴風雨中。
「救命!」她哭喊著,但聲音無法穿透敲打不停、喧鬧不休的雨。雨滴落在她身上的力道越來越重,像玻璃碎片一樣戳刺著她;水洶湧地淹過她的臀部,來到肚臍。
席歐妮不會游泳。她試著回想,努力抬高屁股。艾默瑞就教過她那麼一次,她努力照著他的指示去做。然而,她只是逕自向下沉。
席歐妮的腦袋沉到水下;她手腳亂揮,猛踢地板,想要浮上去。
終於突破水面後,她聽到有人在喊:「席歐妮!」
她朝著那聲音轉過身,在水中濺起水花,不顧一切想把空氣吸入肺中──是她,是狄萊拉。她坐在一個側著浮起來的書櫃上,對席歐妮伸出一手,另一隻手抓的是粉盒化妝鏡──是席歐妮二十歲生日時狄萊拉送的禮物,鏡子上裝飾的凱爾特結壓進她掌心。
「快游!」狄萊拉大喊。
「我不會游!」席歐妮回喊,水灌進她口中,她一陣狂咳。席歐妮不斷用腳趾尋找地面,但地面消失了。除了水和雨之外的一切都消失了。她在無邊無際的水中浮沉,舉目無岸。
狄萊拉把手伸得更長。「快點!」她喊著。
席歐妮又是踢水、又是划動,一次、兩次,她試圖抓住狄萊拉的手指。試到第三次,她終於抓住了狄萊拉的手腕。
但狄萊拉卻皺起了眉,棕色眼珠往眼窩裡翻。她的手臂從身體斷開,斷面參差不齊,鮮血滴入水中,目睹這一切的席歐妮驚駭慌亂。當她朋友剩下的身軀四分五裂,彷彿壞掉的人體模型那樣不斷崩解,直到下沉的書櫃上只剩一團腥紅爛肉,席歐妮不禁放聲尖叫──
席歐妮狂喘著從床上坐起。她的枕頭翻到地上,她眨了好幾次眼,把完全沒有一點潮濕跡象的房間看個清楚。雨水拍在窗上的聲音傳來,冰雹停了。
她用手背拂過額頭,做了個深呼吸,聆聽重重的心跳彷彿鼓聲在耳中敲打。她的頸子因為血液奔流而怦怦作響。
血。
她把毯子往後一翻,在底下到處找──她不知道要找什麼,但什麼都行。她掃視整個房間一遍,只看到睡在椅子上的茴香,除此之外沒有別人。
又是另一次深呼吸,然後再一次。她的心仍在狂跳。席歐妮站起來,踱到房間另一邊,又踱回來,雙手不斷玩弄亂糟糟的辮子。
她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做過這樣的噩夢。這些夢是如此……真實,她真的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淚水刺痛她的眼眶,席歐妮抬頭看天花板,狂眨眼睛,想要逼退眼淚。
她沒能來得及參加狄萊拉的葬禮,因為當時她正昏迷不醒,躺在醫院病床上。後來,那個在紙廠導覽中認識的弄火人學徒克萊門森告訴她,那天下了雨。
光線在窗外閃動,緊接著傳來的是幾乎跟她的心跳一樣響的雷鳴。席歐妮看著自己床上的一團亂,望向茴香。
她吞了一口口水,站起來。靜靜等待,無聲凝視。
她拿起枕頭,輕輕走到門前,把門打開,窺看黑漆漆的走道。極幽微的燭光從右手邊最遠那扇門後流洩出來。艾默瑞完全不想買施了魔法的檯燈。
席歐妮咬著下唇,朝那裡走去。她調整一下自己的睡袍,敲敲門。她的手指微微顫抖,盡可能敲輕一點。要是他已經睡了,她不希望──
「什麼事?」他的聲音透過門傳來。現在都那麼晚了,他竟然還醒著?
她把門打開。艾默瑞正躺在床上,被子蓋到臀部位置,正在看書。但他伸過手,將書放在床頭櫃上。蠟燭只剩不到兩公分的高度了。她來的時間正好。
他對上她的雙眼,皺起前額。「席歐妮,妳沒事吧?」
她漲紅了臉,覺得自己像個小孩。「我……對不起,我只是……我可以在你房間打地鋪嗎?」
艾默瑞的表情絲毫沒變。他坐起來。「妳不舒服嗎?」他似乎打算起身。
「我只是……我……我又睡不好了,」她坦白地說:「我不會出聲。只是……今晚我不想一個人睡。拜託你。」
他抿起嘴唇。他很清楚她那些噩夢。在狄萊拉……在她被……謀殺以後,噩夢的情形就變得嚴重。整整三週,席歐妮都開著燈睡。如今,噩夢偶爾還是會出現,但在那些噩夢中,席歐妮多半充滿了復仇之心。
艾默瑞示意她進來,席歐妮走進房間。「對不起,我──」
「席歐妮,」他淡淡地說:「不要道歉。」
他拉開被子,身子往旁邊挪了挪,騰出多一點空間。
她遲疑著。她從來沒有在艾默瑞的床上睡過。但她渴望有人陪伴,也渴望他。彷彿有條看不見又碰不到的紙鏈將席歐妮拉向他。有咒語能阻止這件事嗎?就算有,她也不知道。
她「砰」一聲把枕頭丟在艾默瑞旁邊,爬到床上。他用伸手捻熄蠟燭,側躺下來,一手攬住席歐妮的腰,把她摟在胸前。
好溫暖。席歐妮靠在他的懷抱中,完全放鬆,一邊聽著艾默瑞那熟悉的心跳、穩定的呼吸,一邊讓自己的吐息與他合拍。
慢慢的,夢魘的畫面從心中退去。席歐妮墜入安然無夢的睡鄉。
※※
席歐妮醒來時右肩又痠又麻,右耳也沒了知覺,右半臉還埋在枕頭裡。床正對面的窗戶毫無遮蔽,日光直直灌進來,讓她不禁眨了眨眼。現在大概是七點半,也許八點吧。她花了一會兒才注意到這個亂七八糟的床頭櫃和窗戶不是她房裡的,而且身上這床毯子絕對是艾默瑞的。
她坐起來,血液流回耳朵。席歐妮掃視了床一下。空的,半邊鋪好。她揉揉眼睛,拔下亂掉的辮子上的髮帶,手指梳過又長又捲的髮絲。
她的胸口漲紅(不過只有一點點),大抵是因為太熱,而且應該不怎麼明顯。她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害臊……畢竟她說過自己可以睡地板,但他若是邀她上床,她也不會介意。要是席歐妮的神智再清楚一點,搞不好還會想占艾默瑞的便宜呢。
她露出微笑,心想要是艾教授耳聞昨晚的情況,這位光藝師不知會露出什麼表情。她一定會怒不可抑。
艾教授當然知道他們之間的「特殊」關係。至少,席歐妮覺得她知道。她曾向過去的導師坦承自己對艾默瑞的感情,但也只說這麼多。不過,艾教授看到席歐妮和艾默瑞在一起時,那副瞇眼神情,以及從喉嚨發出那聲無比清晰的「嗯哼」,再再讓席歐妮感覺這位老練的光藝師知道的更多。目前只希望沒有其他人曉得……至少現在先不要比較好。
門打開來,艾默瑞倒退著走進來,手上端著一個小小的木頭托盤。茴香在他兩腳間亂竄亂吠,到床邊亂嗅,狂搖尾巴。床墊對它來說太高了,跳不上去。
艾默瑞已經穿戴整齊,他將托盤放在床上。上面放了兩片塗了奶油的吐司和半熟蛋。
「艾默瑞,你不用這樣的。」席歐妮說。
艾默瑞聳聳肩。「我也覺得,」他坐在床對角的墊子邊緣,讓出多點空間放托盤。「妳好些了嗎?」
「嗯,」她咬了滿嘴的吐司,吞下去後又補了一句。「謝謝你。」
他只是微微一笑。茴香放棄了跳上床的念頭,轉而蹦到艾默瑞腳邊,開始扯他的褲腳。
「艾默瑞,」席歐妮暫停吃早餐的動作。「昨天那封電報上說了什麼?」
「嗯?」艾默瑞把茴香甩開。有一瞬間,席歐妮想像著自己幫紙小狗改裝堅固的牙齒──可以是塑膠的,也可以是金屬的。但金屬可能會讓它的腦袋過重。況且,她要一隻有金屬牙齒的小狗幹麼呢?
「現在應該可以讓妳知道了,」艾默瑞用手指將頭髮往後梳。「那個,在魔法師資格考負責測驗妳的人,不是我。」
席歐妮的手停在托盤上方,細細思量著這句話。「這是什麼意思?」
「測驗妳的人不會是我。」他又重複一次。
她心中升起一股憂慮,彷彿有艘船正在胸中左右翻滾。席歐妮把托盤移到一邊,在床上往前挪動。「可是……你是開玩笑嗎?學徒手冊序章寫得很清楚,學徒的導師就是在魔法師資格考中幫他們測驗的人。」
「是這樣沒錯,」艾默瑞的表情變得溫和了一些,但他不是在開玩笑。他從床上站起身,走到衣櫃旁,從衣架拿起靛色外套穿上。「這件事我考慮了好幾個月,我想妳一定也有考慮過。」
他再次停在床腳,仔細看了看她,眼中顯出笑意,嘴角卻露出一絲不悅的曲線。「我擔心,要是有人懷疑我們的關係,必定會質疑妳的成績,認為我偏袒妳。」
席歐妮試圖藏起不高興的表情,點了點頭。「我的確想過這個問題一、兩次,但我還沒有跟──」
「親愛的,有時候呢,妳根本不必說出口,」艾默瑞打斷她。「我幫妳做了其他安排。席歐妮,妳是個才華洋溢的摺藝師,差不多就跟我一樣厲害,」他露出自負的笑容。「如果有人因此質疑妳,我一定會相當火大。不管是現在還是以後都一樣。」
席歐妮覺得有些消沉──她實在忍不住。如果不是艾默瑞負責測驗,那麼,這個過程中她又要多面對另一項未知事物。比起早上剛起床,現在她又多出一些不確定因素。而且,如果她沒有趁這次考過,就要再等上六個月才能再考。如果她考三次都不過,就會永遠除名,再也當不成魔法師。之後,如果她想做出任何與魔法相關的行為,就是犯法並要因此入獄。
萬一她考不過怎麼辦?
她吸進一大口氣。「好吧,我就信你這一次。那我可以問一下嗎?是誰要代替你來為我進行測驗呢?」
「可以,」艾默瑞將雙手一拍。「他透過那封電報表示同意了。妳,席歐妮.提爾,將會在魔法師普里溫.貝利的監督下完成魔法師資格考。事實上呢,按照傳統,妳會在考試前幾週跟他和他的學徒住在一起。」
席歐妮張開嘴,過了一下子才問:「所以到底是幾週?」
「二或三吧。」
「魔法師貝利?」她問,食指絞纏著一綹頭髮。這名字很陌生,可是──
她停頓半响,一段記憶似乎正在暗中騷動。這個名字有點……
一瞬間,席歐妮的記憶倒帶回到格蘭傑學院的大廳。這是她和艾默瑞都念過的中學。但那記憶不屬於她,是艾默瑞的記憶。兩年前,席歐妮為了把艾默瑞的心臟從一個叫黎拉的恐怖血術士(此人正好是他的前妻)手中救回來,在他心裡走了一遭。那時她偷看到了一些艾默瑞的過往。她記得艾默瑞曾和另外兩個男孩一起去挑釁一個很有抱負的瘦高摺藝師──他的名字就叫普里。
「普里?」她問:「就是被你霸凌的那個男孩?」
艾默瑞搔搔腦後。「『霸凌』這詞聽起來好幼稚啊……」
「但就是他,對不對?」席歐妮逼問。「普里溫.貝利對吧?他最後還是成了摺藝師?」
艾默瑞點點頭。「其實我們是一起從魔法學校畢業的。不過他的確一點也沒變。」
不知怎麼,席歐妮覺得鬆了一口氣。「所以你們現在和好了?」
紙魔法師爆出大笑。「喔,我的老天──當然是完全沒有。我們從畢業之後就沒說過話了──除了這封電報之外。說實在,他恨死我了。」
席歐妮的眼睛都要突出來了。「那你還把我送去他那邊?」
艾默瑞微笑。「當然囉,妳這幾天就要去了。如果不是把妳的前程放到普里溫.貝利手中,還有什麼方式能證明考試結果絕對公正、毫無偏頗?」
席歐妮瞪了他好久。「我要被丟到地獄了,是吧?」
「親愛的,注意妳的措詞。」
她壓著前額。「我要讀的書比想像中還多,我死定了!我……我得去換衣服。」
她從床上起身,急忙衝到走道上,手還壓著前額,茴香緊追在她腳後跟。
「妳的蛋還沒吃啊!」
但席歐妮得面對的事比一顆蛋還要複雜太多了。
※※
席歐妮再次細讀艾默瑞給的那本論文。為了集中精神,她時不時捏捏自己,才能專心讀進每一段冗長又枯燥無味的段落 (而且那些咒語她早就知道了)。即便如此辛苦,她也不願意只是隨便翻翻、大略看過。席歐妮決定當自己從沒聽過什麼對半摺,拚命用心研讀圖表。至少這本論文的繪圖風格對她而言的確是前所未見。
之後,席歐妮決定練習一個極為複雜的賦生術。她挑了一種從來沒做過的動物:火雞。她參考了幾張圖片,小心摺出尾羽,並且將紙張摺皺,做出球狀身體。她用三張正方紙做脖子,再用一張做頭,然後小心剪下用來形塑鳥喙和嘴邊垂肉的紙。她花了大半天來做這隻禽鳥,並對牠施展賦生術。第二天,她拿更多紙製作出一隻更大的火雞,並仔細確認每一個零件都環環相扣,好讓它能行動自如。花了兩天做這件作品讓席歐妮不禁有點擔心,跪了好幾個小時,膝蓋上的壓痕會不會永遠都消不掉了?
艾默瑞知道考試對她的重要性,但他似乎覺得放在心裡就好,沒必要說出口。然而,他偶爾會冒出來提供一些忠告,說服席歐妮稍微休息一下,或是煮點東西。對於這些委婉含蓄的小動作,席歐妮也只能一笑置之。
但在這週的最後,席歐妮因為論文集和賦生術的關係,徹徹底底地精疲力竭,所以她躲進衣櫃偷偷研究起橡膠魔法。她把橡膠釦子製成動物的腳底肉球(不過前兩個成品得丟掉,因為她不小心切錯形狀了),用固定咒把肉球黏在茴香的腳底。這麼一來,它的腳掌就不會那麼容易磨損,就算踏進淺一點的水灘,也不會皺縮成濕透的一團紙。完成作品後,她打量了一下,對自己點點頭,覺得茴香腳上這小小的改造工程算是及格。一定不會有哪個魔法師多看它一眼的。
不過,弄到最後,席歐妮已經不想再碰魔法了。星期五晚上,她早早上床睡覺,但午夜過後卻被吵醒了。感謝老天!不是噩夢,而是聽到隔牆傳來的微弱「喀喀」聲。音量不大卻足以吵醒她,而且那聲音很熟悉,使得席歐妮在夢與夢的中間醒了過來。
她從枕頭上抬起頭,屏住呼吸,確認自己沒有聽錯。那個噪音持續傳來,喀、喀、喀、喀、喀。是電報。
她從床上坐起,小心不吵醒茴香。它今晚睡在她床上,就蜷在腳邊。她揉揉眼睛,赤裸的雙腳踩到地上。大半夜的,有誰會傳電報來呢?現在萬里無雲,為什麼不派隻紙鳥來就好?難道普里的睡眠時間也跟艾默瑞一樣「與眾不同」嗎?這個訊息是打算來取消安排的嗎?假如是為了通知取消,席歐妮倒是一點也不介意。
她走出房間。艾默瑞的門縫底下一片漆黑,因此她走到藏書閣,打開門。
電報機在桌上規律地「喀喀喀」響,但就在席歐妮踏進這個黑暗的房間前,它停了,留她獨自站在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片死寂裡。
席歐妮伸手去摸電燈開關,打開來。從藏書閣天花板掛下來的電燈泡閃爍亮起,但只亮了一會兒就茲茲熄滅,藏書閣又陷入一片黑暗。席歐妮眨掉眼中閃過的紫色光點,開開關關電燈好幾次,卻徒勞無功。難道又斷電了?他們距離主要城市太遠,艾默瑞家的電路一向令人失望。
她走過房間,熟門熟路地避開會發出最大聲響的地板,將手伸到桌子那裡試試檯燈,但這燈打不開。她轉而去點旁邊的蠟燭,拿起捲起的電報紙。這封簡短的訊息似乎是用極短時間草草寫成。她把訊息掃過一遍,但一時間腦子無法理解。她又試了一次,這次讀得慢了一點。
普藍迪送往普茨茅斯處決途中逃脫
應通知你。艾弗德
她的手指抓著那張紙,麻木而沒有知覺。碰觸紙時,她本應感到一陣刺麻,但這次沒有。這張紙感覺像是死的,了無生氣,沉重如鉛。
艾弗德。自從被蓋瑞斯折磨過後,她就再也沒見過魔法師艾弗德.修斯了。那次之後,她就再也不用跟犯罪部門糾纏不清了──至少她內心是如此希望。
席歐妮的雙眼死瞪著電報上的第一個字──
普藍迪
賽瑞吉.普藍迪,蓋瑞斯養的瘋犬,二度出手殺她的血術士──而且原因只不過是圖個方便。這傢伙甚至威脅了她的家人及愛人的生命。
現在,他又重獲自由。
※※
燈又亮起,在席歐妮的視線中燒出光點,一時間她看不清紙上普藍迪的名字。
蠟燭閃爍,門的鉸鏈嘎吱響。
「席歐妮?」艾默瑞問,但話才說到一半就被呵欠打斷。「妳在做什麼……有電報啊?」
席歐妮沒有回應。她的思緒從家人居住的地點一路飛快轉到那條吞沒出租車和司機的河流(艾默瑞和她也差點淹死)。這些念頭往東衝向達特佛,遠遠來到造紙廠新建好的牆面。
艾默瑞碰碰她肩膀。席歐妮把電報遞給他,轉身走開。從離開電報到走回臥室,她這一路都神思恍惚。打開臥室的燈時,茴香翻動了一下。她走到書桌前,拿出一張正方形白紙和鉛筆,瘋狂書寫著,字跡亂得全然無法對齊。她才準備寫第二句,就聽見艾默瑞用溫柔的語氣問:「妳在做什麼?」
「我要警告我的家人。」
「席歐妮,他不知道他們現在住在哪裡,」艾默瑞聲線輕柔,一如夏日微風。他緩緩地進入房間,腳步彷彿一頭行走在森林草地的鹿。「艾弗德會把他們列為第一優先要務──說不定他已經去執行保護工作了。」
席歐妮搖搖頭。
紙魔法師的手再次來到她肩上,輕輕用手指扣住她。「我很抱歉。」他低聲說。
席歐妮把鉛筆丟到桌面,摔斷了筆尖。她轉向艾默瑞,覺得眼淚刺痛了眼角。「為什麼他們還沒處決他?」她問。這個問題令她舌尖熱燙。「他們有整整兩年的時間,想想他傷害的那些人……」
艾默瑞捧起她的臉,拇指掠過她眼睛下方,接住一顆眼淚。「他們沒了蓋瑞斯和黎拉,只剩賽瑞吉一人握有那個黑暗世界的資訊。」
「那些又不重要!」
「我也不是不同意妳的看法。」艾默瑞的音量很小,他用自己的前額抵著她的額頭。
席歐妮垂下眼神,從他的懷抱中抽身,但隨即又往前一靠,倚著他的肩膀。艾默瑞用雙臂攬住她,他的溫暖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心感。「要是賽瑞吉還在追殺他們……或我們……那怎麼辦?」她喃喃地說。
「他跑不遠的。我們把這件事交給魔法師內閣會。他們會處理的。」
「如果什麼都交給魔法師內閣會,那我們就死定了。」
他撫摸著她的頭髮。「不管怎樣,賽瑞吉第一要務一定是逃亡。他已經沒有任何理由要追殺妳了。我也懷疑他還會浪費時間來騷擾我。他應該會先往海岸逃,抱著也許能跨越海峽的希望。如果艾弗德還有時間送訊息給我們,那麼就可以假設,他必定早就派人跟著賽瑞吉。」
席歐妮呼出長長一口氣,想讓自己沉溺在艾默瑞做出的保證中,就像裹著溫暖的毛毯一樣。她稍微冷靜下來,也比較放鬆了些,但還是有那麼一點憂慮牽動著她的心跳。賽瑞吉做的事都非常扭曲迂迴,極難預測。要是他的目標仍是她的家人,那該怎麼辦?
蓋瑞斯的聲音撩撥著席歐妮的心緒,她彷彿聽見他重複說著父母的名字。席歐妮不禁渾身發起抖來。
但至少艾默瑞不會再捲入這團混亂了。自從賽瑞吉被逮捕,他就沒跟犯罪部門合作了。畢竟他的前妻跟這些事已毫無牽連,因此艾默瑞就沒有理由跟血術士糾纏,魔法師內閣會也接受了這件事。
她又在艾默瑞的懷中靠了一下才離開,艾默瑞輕輕吻了她。
「如果能讓妳覺得好一點的話,我答應等到早上,我再想辦法多挖點消息,」他表示。「但現在能做的就是好好休息。」
「──還有對房子做出防護──」
「房子的防護早就做好了,」他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妳很安全,席歐妮,他們也很安全。我跟妳保證。」
她點點頭。艾默瑞又等了一會兒才將嘴唇貼在她前額,沒說什麼就離開了。她今晚還是可以跟他一起睡,管他什麼禮教矜持!但是,她最終還是沒提出請求。她當然相信艾默瑞,也不希望他誤以為她是不信任他。但他怎麼可能確定賽瑞吉.普藍迪會去哪裡?會做什麼?
茴香抬起頭發出一聲吠叫,席歐妮嘆了口氣,拿起寫了一半的訊息,用手捏皺,一邊發出命令「碎」,一邊丟向垃圾桶。
她關掉燈、爬上床,呼喚紙小狗過來躺在她頭旁邊。沒錯,她現在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睡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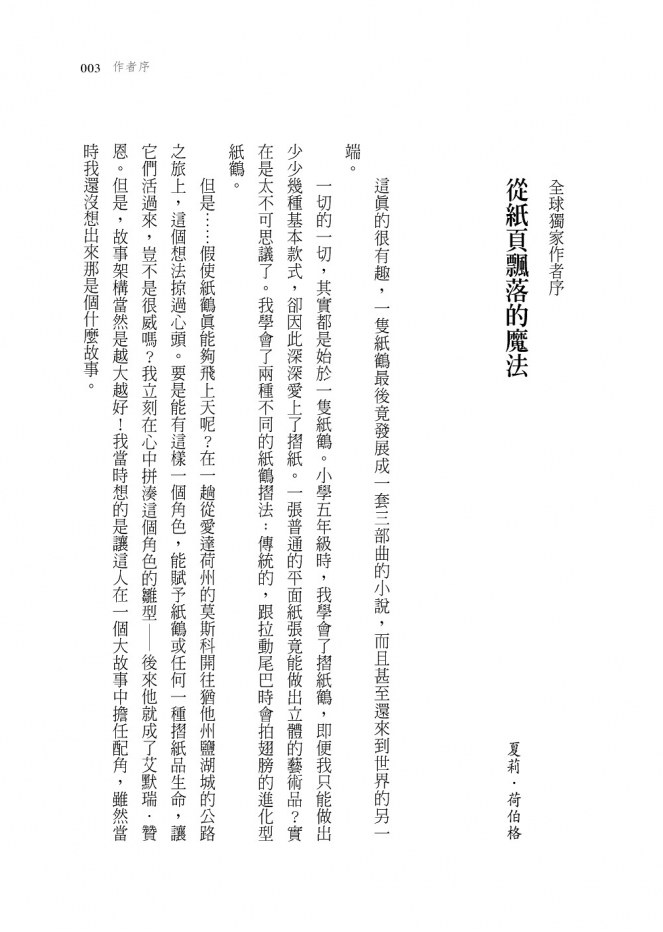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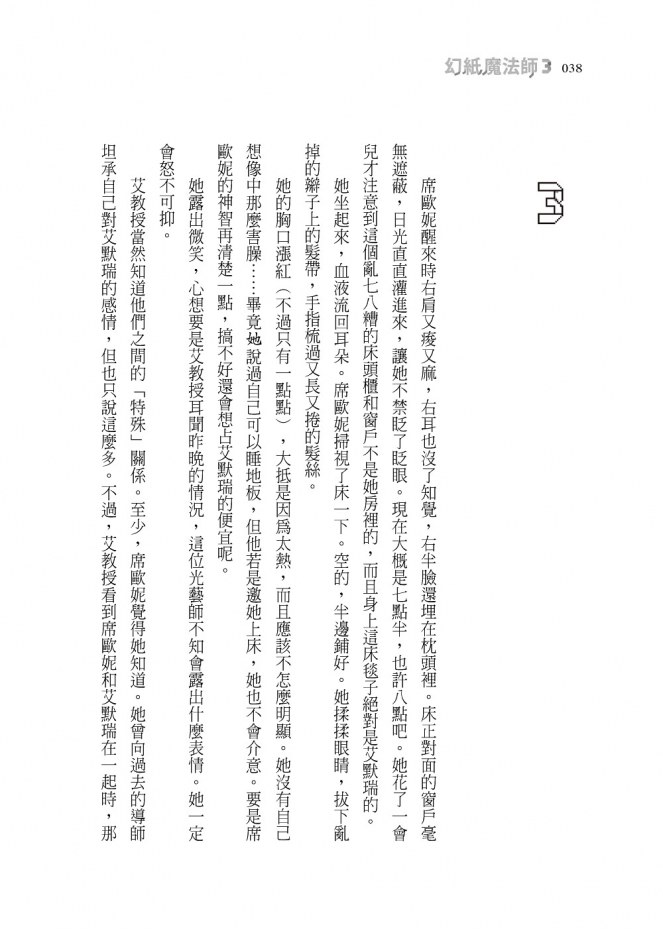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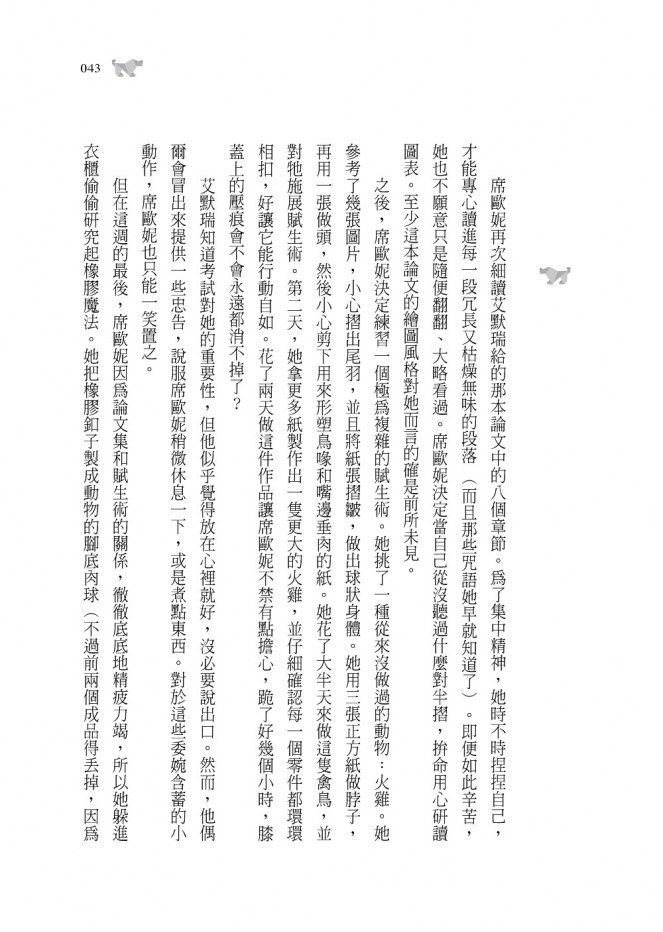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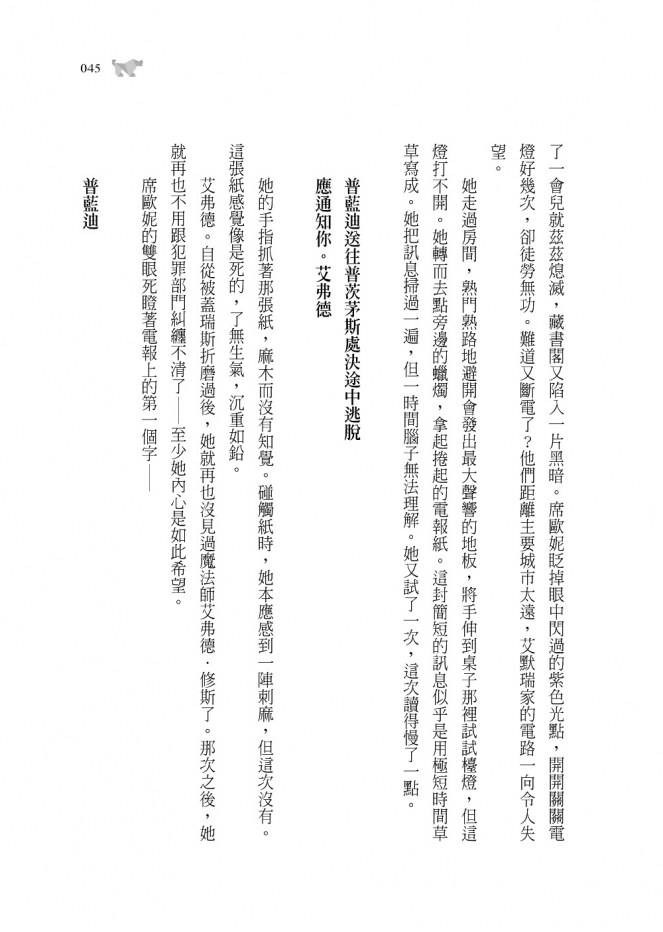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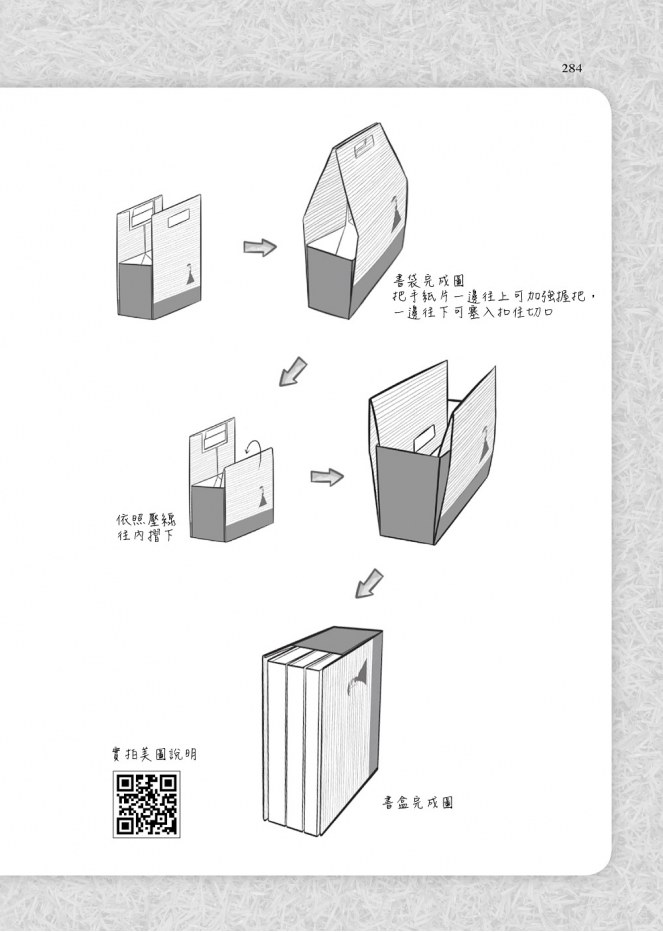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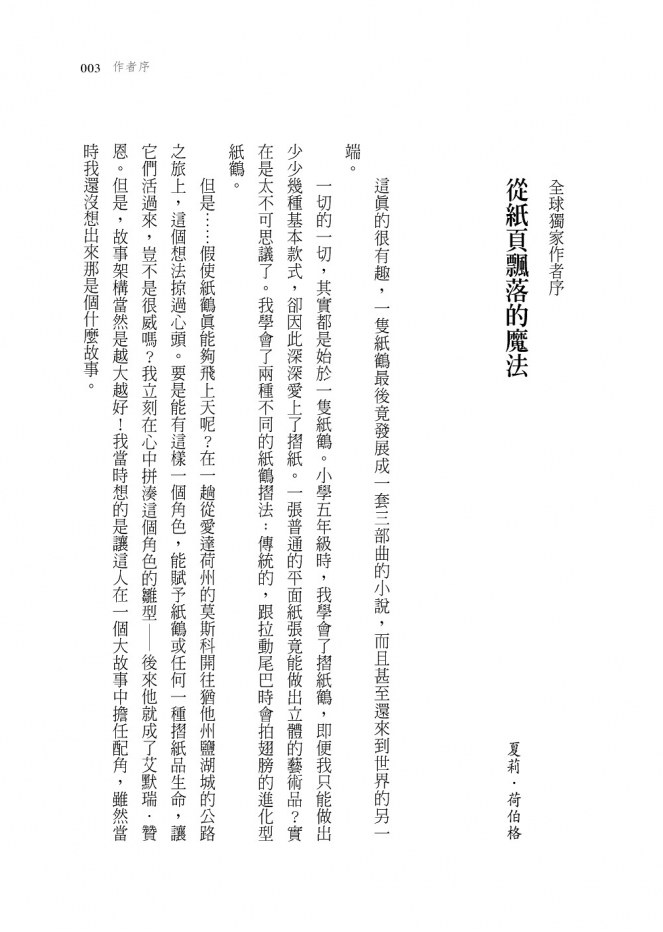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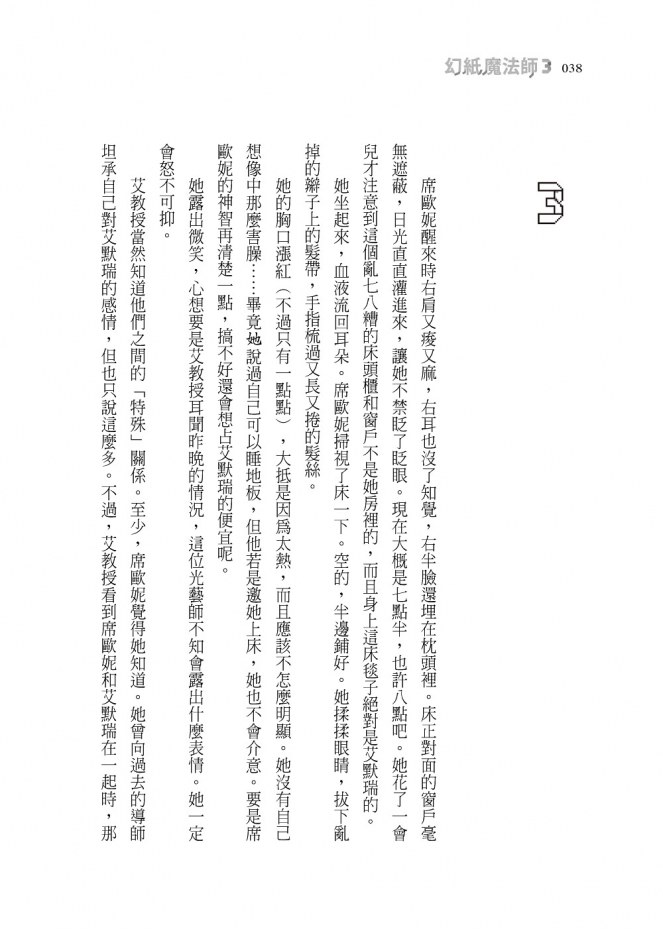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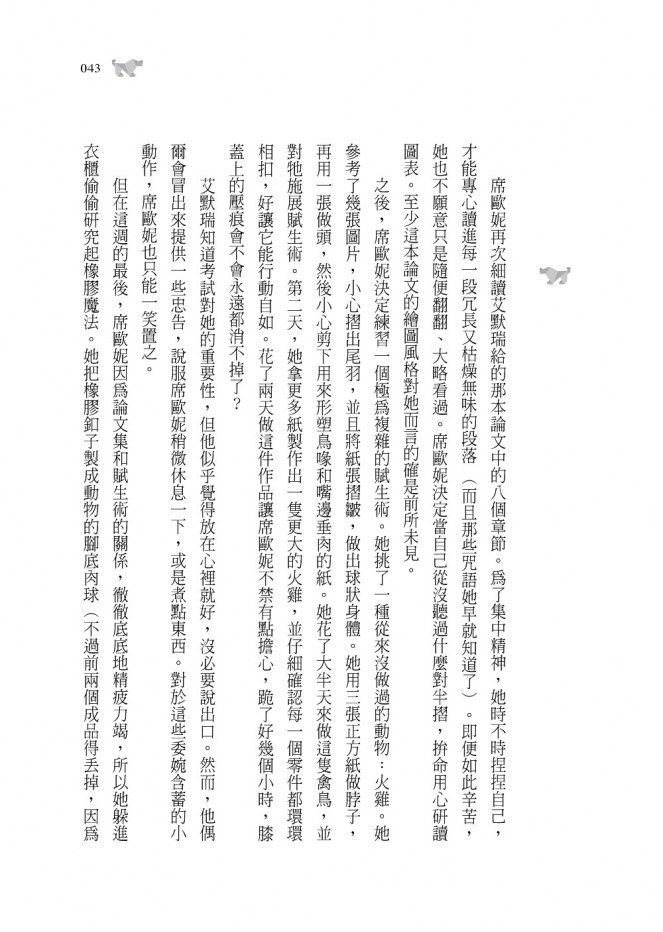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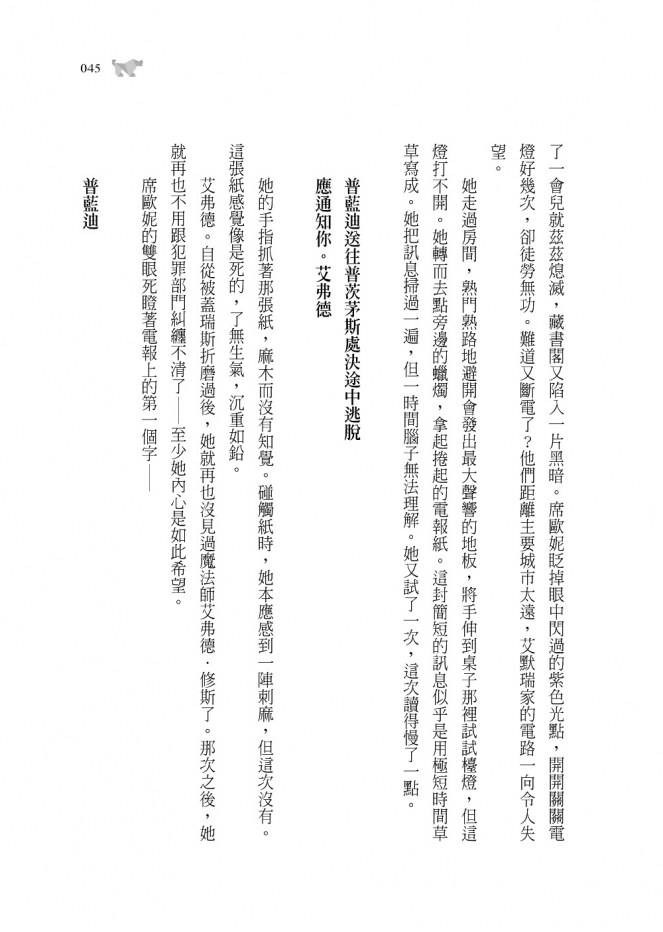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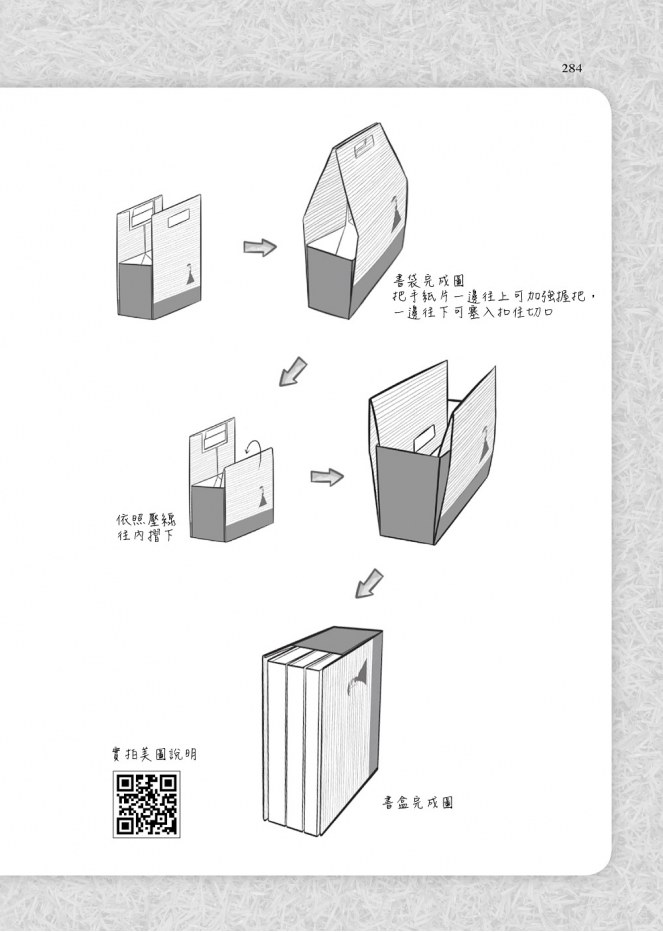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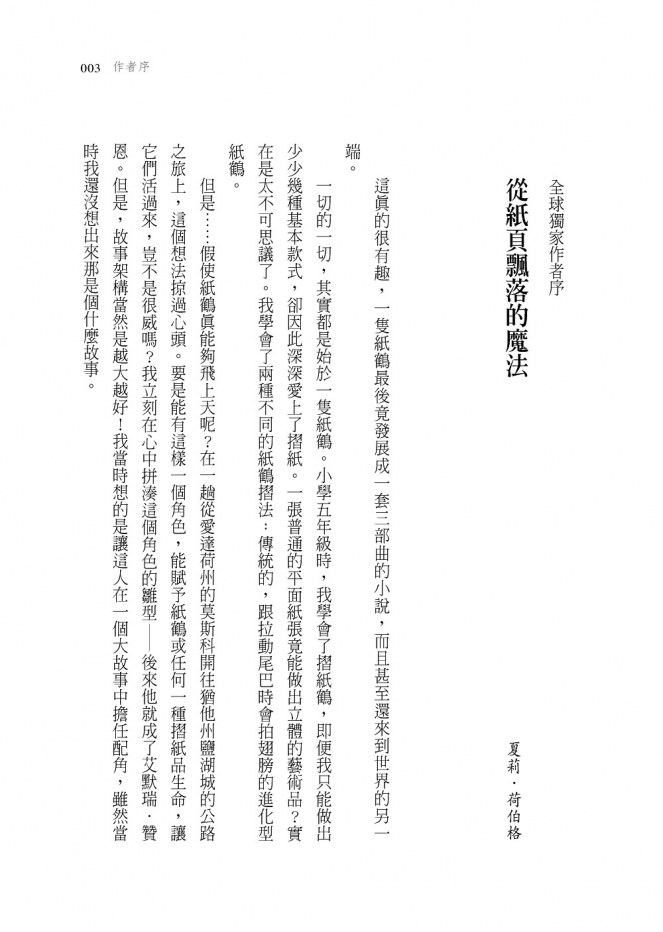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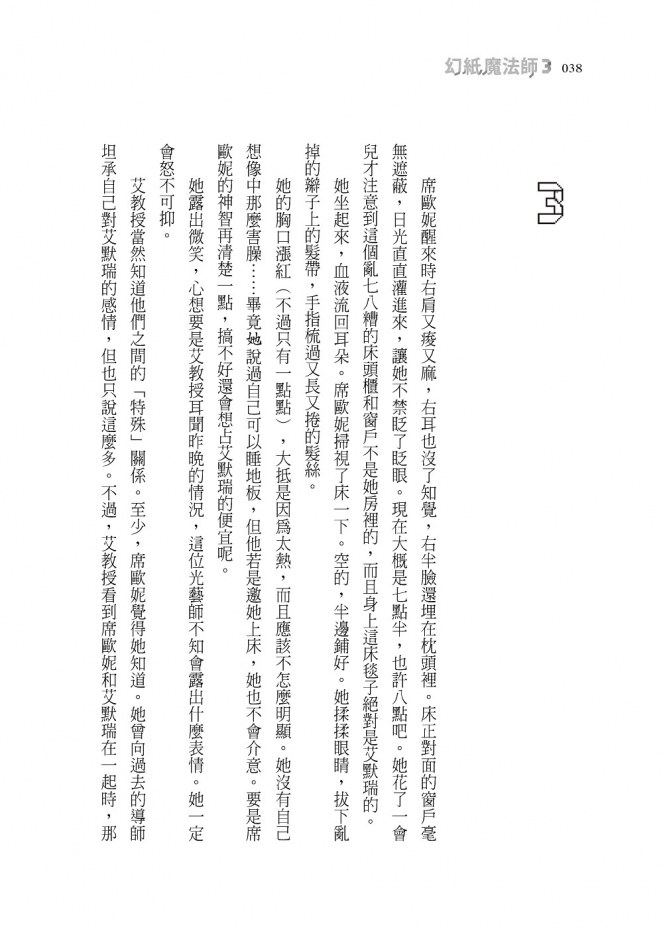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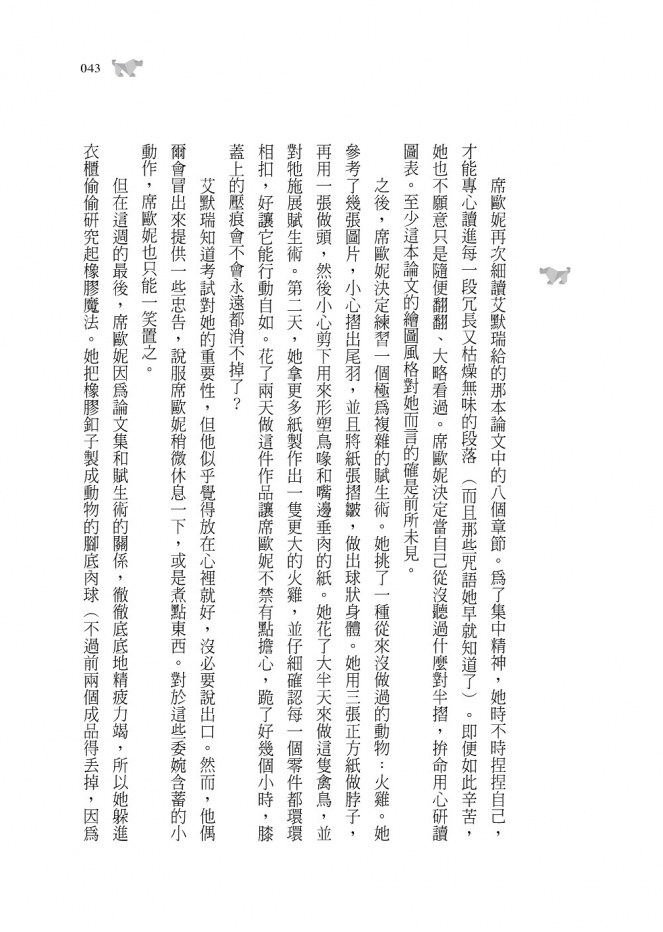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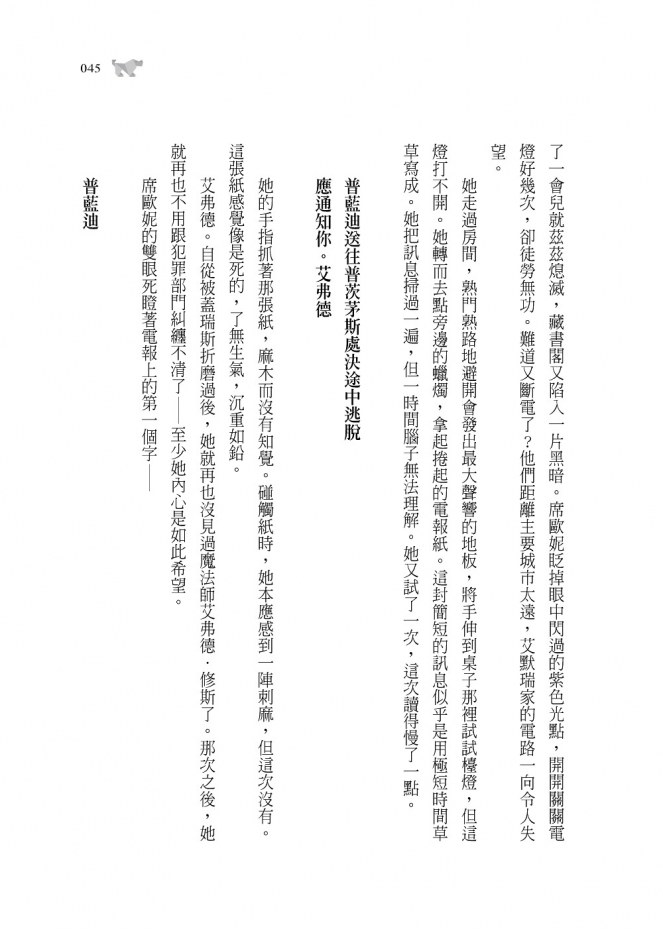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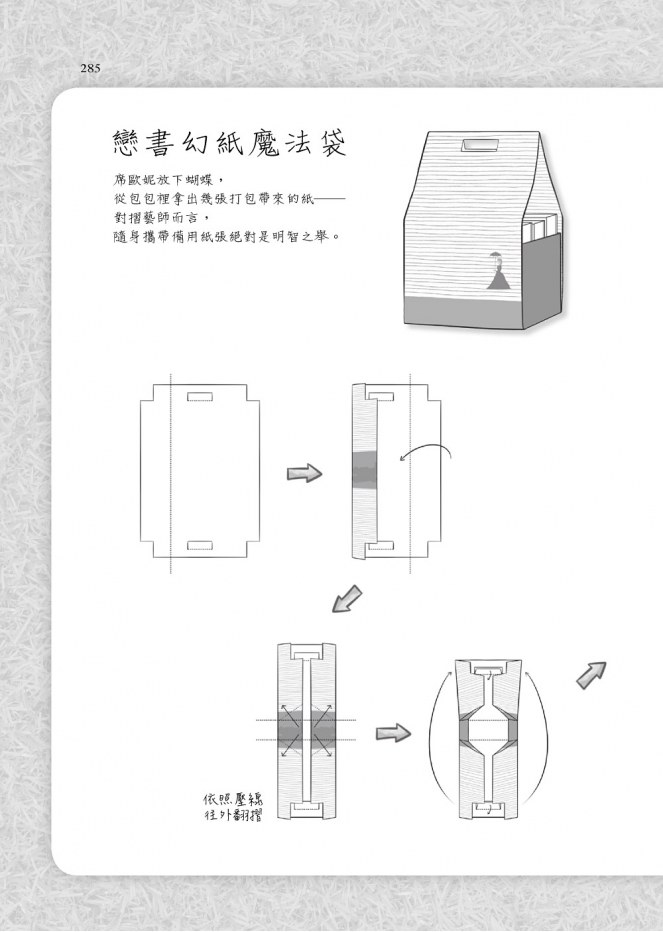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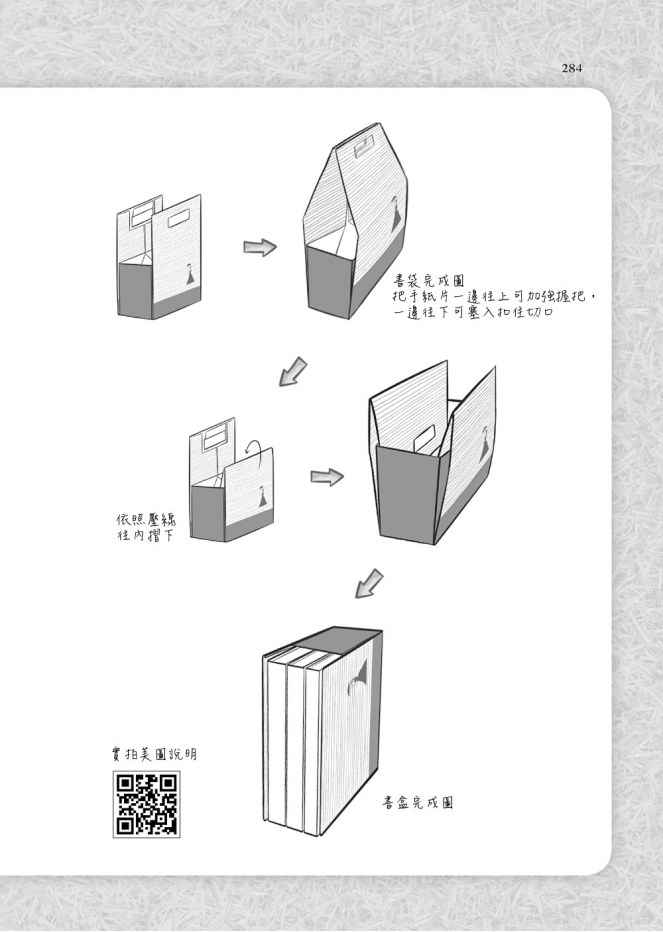

 擁有一對犧牲奉獻型的父母,他們期望給懶散的女兒良好教育,結果卻造成夏莉從七歲起就很討厭制服,討厭背誦。
擁有一對犧牲奉獻型的父母,他們期望給懶散的女兒良好教育,結果卻造成夏莉從七歲起就很討厭制服,討厭背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