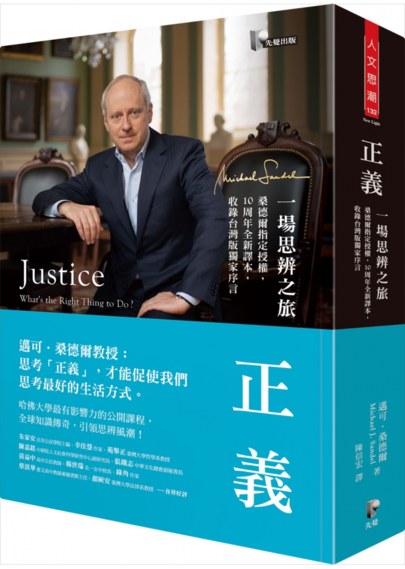「爸爸說的故事給我一種印象:那些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採收、曬乾並包裝咖啡的人,是他的同事。毫無疑問地,我想要了解這個世界的強烈欲望,就是從咖啡袋裡的硬幣和爸爸在世界地圖前所講的故事開始。這種欲望逐漸演變成一輩子的痴迷,最後成為我的職業。」--漢斯‧羅斯林《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
以《真確》聞名於世的漢斯‧羅斯林,是我們這個時代了不起的公衛學家和教育家,漢斯出身自瑞典工人家庭,他的父母親雖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在父母的引導下,還年幼的他建立起對世界的認識,一個渴望理解、尊重他人的價值觀。
慶幸漢斯留給我們《真確》,和這本他述說自己的人生故事,漢斯說:「這本書裡探討那些與人交流,使我眼睛一亮,重新進行思考的人事物。」而我們也能透過他的人生,重新思考世界、教育、我們的價值觀。

"我8歲時從父親那理解「他們是否相信上帝,並不重要,重點是他們如何對待其他人。」"
我爸晚上下班回家的時候,身上總是散發出咖啡味。他在林德瓦爾咖啡股份公司位於烏普薩拉的研磨廠上班,這使我在開始有喝咖啡的習慣以前,就愛上了咖啡的味道。我常待在外面,等他騎著腳踏車順著街道一路下來,再從車上跳下,然後擁抱我。那時,我總會問同樣的問題:
「你今天有沒有找到什麼?」
他研磨的咖啡一袋接一袋地被送進研磨廠,在輸送帶上被清空。不過這些咖啡豆必須先通過一塊磁性很強的磁鐵,這塊磁鐵會吸走所有在咖啡豆曬乾與包裝的過程中,剛好掉進袋子裡的金屬物體。爸爸把這類的金屬物體帶回家給我看。他告訴我每個物體的故事,因此它們變得很引人入勝。其中有一些是硬幣。
「你看,它來自巴西,」他會這麼說,「全世界生產最多咖啡的國家。」
我坐在爸爸膝蓋上,聽他講述每一枚硬幣的故事,一張世界地圖便在我們眼前展開。
「它是一個氣候溫暖的大國。裝著這枚硬幣的袋子來自桑托斯。」他一邊說,一邊指著這座巴西的港口城市。
他提到所有置身於這條產業鏈中,使在瑞典的我們能坐在桌前享用咖啡的工人。我很早就認識到,在這條產業鏈中,咖啡採收工人獲得的報酬是最低的。
在另一個晚上,我們談論的硬幣來自瓜地馬拉。
「來自歐洲的白人擁有這個國家的咖啡園。最先住在那裡的原住民從事採收咖啡豆的低薪工作。」

"「我該如何展示全世界的進步,好讓世人理解當前正在發生的變化呢?」--漢斯‧羅斯林"
當他某次帶著一枚銅幣回家時,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一枚來自英屬東非(即今日肯亞)的五分錢硬幣,中央有一個小孔。
「那名將咖啡豆放在沙灘上曬乾,然後將它們倒回袋子裡的男子,脖子上大概掛著一條帶子,這枚硬幣就綁在帶子上。那條帶子想必是斷掉了。當他要撿起硬幣時,這一枚掉進裝著咖啡豆的袋子裡,所以被遺漏了。現在它是你的了。」
到了今天,我仍然將爸爸給我的硬幣保存在一個木箱子裡。他利用那枚來自肯亞的東非硬幣為我解釋了殖民主義。我八歲時就知道肯亞茅茅起義對自由的追求。
爸爸說的故事給我一種印象:那些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採收、曬乾並包裝咖啡的人,是他的同事。毫無疑問地,我想要了解這個世界的強烈欲望,就是從咖啡袋裡的硬幣和爸爸在世界地圖前所講的故事開始。這種欲望逐漸演變成一輩子的痴迷,最後成為我的職業。
事後我理解了,爸爸用講述歐洲對抗納粹主義歷史的方式,說明世界各地對殖民勢力發動的起義。週末,當我們在森林中徜徉時,他對我詳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我父母的政治傾向其實一點都不極端,他們幾乎就是非常普通的平凡人,對極左派與極右派同樣反感。我爸爸對所有為正義與自由而戰的人感到敬佩。
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宗教信仰,但有著強烈、分明的價值觀。比如說:「他們是否相信上帝,並不重要,重點是他們如何對待其他人。」以及:「某些人上教堂,其他人則走進森林,享受大自然。」
我們家那台用塗著棕色亮光漆木料製成的小收音機,就放在餐桌上方的架子上。晚餐時,我們總是收聽瑞典國家廣播電台的晚間新聞。小時候,對我產生影響力的並不是新聞本身,而是我父母的說明。我媽總會評論國內的問題,而我爸則對國外的問題發表看法。我爸的反應常常相當強烈。他會停止咀嚼,在椅子上坐挺,全神貫注地聆聽,要我和媽媽別作聲。然後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討論剛才所聽到的新聞。
---

在我讀小學的最初幾年,爸爸經常帶我去旁聽勞工教育協會主辦的夜間演講。主講人是幾個經歷豐富的探險家與旅遊者,對當時七歲的我來說,這真是個魔幻般的夜晚。能和爸爸旁聽為了大人所舉辦的活動,聽到關於遠方被殖民國度人民生活的故事,我感到神往不已。而這些演講,也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
艾瑞克.倫奎斯特是最受歡迎的講者。他是一名瑞典籍的林務官,在一九三○年代前往印尼,在荷蘭殖民統治的行政體系中工作。他娶了一名印尼女子,而後成為著名的作家,以對大自然生態系和他曾工作、生活過的當地社會的理解著稱。我爸媽都讀過他的書。在當時的瑞典,他是最主要的反種族主義者之一。
史坦.柏格曼是另一名講者及探險家。演講時,他放映一部自己在新幾內亞那座村莊內拍攝的黑白默片。在這部影片裡,他豎立起一根約四公尺高,表面光滑的木樁,有一把漂亮的斧頭固定在木樁的尖端。然後他在木樁表面塗抹肥皂。村民努力想要攀上表面溼滑的木樁,拿到那把斧頭,卻都徒勞無功。這些畫面全被他拍攝下來。影片播放到一半,我爸就站起身來,牽住我的手,說:「我們走。」我們離開時,我看到爸爸臉色蒼白;他只有在憤怒時才會臉色發白,而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他低聲告訴我:
「他不尊重這些人。史坦.柏格曼是個紈褲子弟。他逼迫那些人去拿那把斧頭,使他們變成笑柄。他們住在森林裡,本來就很需要斧頭。我受不了他的態度。」
---
我爸十四歲時完成了小學六年的義務教育,開始在磚石廠擔任搬運工。在今天,這叫童工。年長的工人常虐待這些小男孩,但對一名年輕男子來說,弟妹人數愈來愈多,他當然必須為家裡的生計盡一分心力。
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蕭條時期,十七歲的他和許多人一樣都失業了。隨後的二戰期間,爸爸被徵召進入瑞典陸軍,服役三年,協防與丹麥、挪威、芬蘭接壤的國界。他總是重複地說,自己服役期間,部隊從沒遭到攻擊,真是幸運。
他提醒我,對那些負起重責,奮力擊潰德國及其盟友的士兵與國家,必須心懷感激。
「我們要挺身對抗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我爸總是這麼說。
「我們」這個詞彙,很早就將我包括在內。他說話時從來不煽情,然而對那些曾被德軍佔領,卻又對殖民地發動戰爭的歐洲國家,他感到驚懼不已。
摘錄自《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
一個慷慨無畏的靈魂,如何以他的思辨與抉擇撼動世界?
《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逝世前堅持寫下的人生自述!
更多漢斯故事:即使在最艱困的時刻,你是否仍能尊重他人的尊嚴?--漢斯‧羅斯林《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
【誠品選書】一起到書店尋找漢斯‧羅斯林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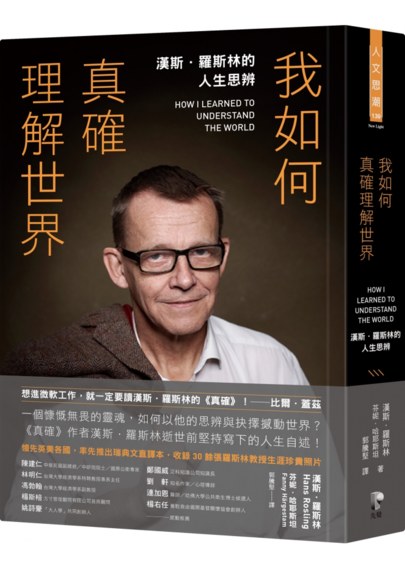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