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過庇護營第一個告示,大約位於溫德罕和南邊海岸之間,正要繞過一條大馬車道。跨越車道時,看到了那個告示牌,於是我們偷偷接近。木板上用白字寫著:
九號庇護營,往南十公里,議會歡迎你們!
保障你我,大家都安全!
生活無虞,物資充裕,付出勞力,就有公平報酬。
庇護營:生活艱困時的最佳去處。
歐米伽上學是違法的事,但不管像我一樣在家,或是去非法的學校,許多人設法習得基本閱讀能力。我不知道究竟多少歐米伽經過庇護營告示牌時,能看懂上面寫的訊息,這當中又有多少人相信。
「生活艱困時。」派伯嘲笑說。「怎麼不提生活艱困都是因為他們稅收太重,或把歐米伽逼到貧瘠土地害的。」
「或者說就算熬過艱困時候,你也沒了選擇。」柔依接口。「一旦進去就出不來。」 我們全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那代表歐米伽會半死不活地漂浮在玻璃缸裡。安全地困在可怕的玻璃空間中,他們的阿爾法生活就不會再受拖累。
我們遠離大路,躲在山溝和樹林順著路向前。愈接近庇護營,我的腳步愈沉重,動作也愈來愈緩慢,那是我不安的源頭。日出時分,庇護營映入我們眼簾,每一步都彷彿是走在河中,逆流而上。天剛破曉,我們冒險躡手躡腳靠近,最後我們來到緩坡頂的樹叢俯瞰庇護營,相距大約三十公尺左右。
庇護營比我想像中還大,規模幾乎可比一座小鎮。四周城牆比議會在紐霍巴打造的牆還高。牆不是木造,而是磚砌,高度超過四公尺,頂端纏繞著鐵絲,彷彿有隻巨鳥把好幾個巢扔在一塊。牆裡,我們看到幾棟房子的屋頂,混雜搭建了各式各樣的建築。
派伯指著西方邊緣的一棟巨大建築。那房子占去大半的庇護營,牆面仍帶著松木清淡的黃色,可見是新砍下的木材,和其他建築老舊灰暗的木頭相比,顯得格外明亮。
「沒有窗戶。」柔依說。只有四個字,我們就全明白那意思了。那棟建築中放了一排排玻璃缸。有些會是空的,有些仍建造到一半。但我腹中湧起一股揮之不去的噁心感,無庸置疑,許多玻璃缸已裝著人。好幾百人活生生浸泡在黏稠液體裡,倒胃的甜氣滲入他們眼耳口鼻。萬物死寂,四周只有機器嗡嗡聲。
庇護營慢慢擴張,建物幾乎都在圍牆中。東方邊緣有一大片農地,四周只有低矮木欄,但是卻難以攀爬,柱子中間雖有間隙,人卻鑽不過去。從那裡看得到整齊排列的作物,一個個工人彎著腰,拿鋤頭辛勤地在甜菜和西葫蘆田工作。大概有二十個工人,他們全都是歐米伽。西葫蘆結得又肥又大,每個果肉都比我們吃的上一餐還多。
「至少不是所有人都關到玻璃缸裡了。」柔依說。「總之,現在還沒。」 「這片田多大?兩公頃?」派伯說。「看這地方多大。尤其那棟新建築。島上的紀錄寫著每年有上千人投奔庇護營。最近收成不好,稅收增加,人數更有增無減。光這個庇護營就容納了五千人以上。他們不可能靠這塊田養活所有人。連養守衛都不夠。」
「這是做給大家看的。」我說。「像表演一樣,呈現庇護營美好的形象。但這只是為了吸引人裝出來的。」
庇護營還有其他事情讓我感到不安。我一直找、一直找,卻遍尋不著。後來發現那裡一點聲音也沒有。派伯說應該有上千人在牆裡生活。我回憶起紐霍巴市集和島嶼街道的喧譁,連愛爾莎的收容之家都不斷有著孩童玩耍的聲響。但庇護營唯一傳來的就是鋤頭落在結霜土地的聲音。背後沒有人聲,建築物中我也感受不到任何動靜。我想起在溫德罕看到的玻璃缸室,那裡只有電力嗡嗡聲,一條條管子像是酒瓶的軟木塞緊緊堵住喉嚨。
往庇護營的路上有東西在移動。不是騎馬的士兵,而是三個旅人,他們背著行囊,腳步沉緩。
走近之後,我們看出他們是歐米伽。最矮的那人手臂只到手肘,另一人瘸著走,一條腿長得像漂流木一樣。兩人之間是個孩子。雖然他瘦到看不出年紀,但我猜他頂多七八歲而已。孩子低著頭,手緊緊牽著高個男人,跟隨他向前。 他們骨瘦如柴,頭顱在身體上顯得異常巨大。最讓我心痛的是他們的行囊,一捆捆包裹得十分扎實,一定都是難以割捨的東西,包括全新生活的必需品及生命中最珍貴的寶物。高個子肩上有把鏟子,另一人行李掛著兩個鍋子,每一步都哐啷哐啷響著。
「我們必須阻止他們。」我說。「告訴他們裡頭是什麼狀況。」
「太遲了。」派伯說。「守衛會看到我們。那樣的話一切就完了。」
「就算我們偷偷攔住他們,我們要說什麼?」柔依說。「他們會覺得我們瘋了。看看我們。」我望向柔依和派伯,再低頭看自己。我們全身髒兮兮,也餓得半死,衣衫破爛,還沒擺脫荒地死灰色的污漬。
「他們憑什麼相信我們?」派伯說。「我們又能給他們什麼?我們以前有島嶼,可以給他們一個安全的避風港,或至少找反抗軍的避難點收容他們。現在島嶼毀了,聯絡網也一天天在瓦解。」
「總比玻璃缸來得好。」我說。
「我知道。」派伯說。「但他們不會信的。而且我們要怎麼解釋玻璃缸的事?」
石牆一道門打開。三個穿著紅色束腰長袍的議會士兵走出來迎接三人。士兵一派輕鬆,雙臂插在胸前,靜靜等待。扎克的計畫既無情又有效,令我感到不可思議。扎克什麼都不用做,繁重的稅金會把歐米伽逼進用稅金蓋好的庇護營。到了裡頭,玻璃缸會吞噬他們,進入再也無法浮出的黑暗之水。
東方圍欄後的田野忽然出現騷動。其中一個工人在揮手。他跑到圍欄旁,激動地朝路上的三人招手。他不斷向旅人揮手,意思再清楚不過了。快逃,快逃啊。他的舉止有著巨大的反差,動作激動卻沒任何聲音。我不知道他是啞巴,還是他不想引起守衛注意。田裡其他工人都望著他,一個女人朝他走幾步,也許是想幫他或想阻止他。不論如何,她一瞬間僵住了,然後她回頭。
有個士兵從田野後方的木屋跑出來,撲向揮手的男子,重重擊打他的後腦。第二個守衛過來時,那個歐米伽男子已倒在地上。他們將他拖回屋裡。另有三名士兵出現,一人沿著圍欄走,眼睛盯著其他工人,工人馬上彎腰繼續工作。從遠方看,這一切彷彿皮影戲一般迅雷不及掩耳,但完全沒有聲音。
士兵反應很快,事情剎那間結束,我覺得新來者對剛才的事渾然不覺。他們頭仍低垂,穩穩走向十五公尺外站在大門口前的士兵。就算真看到了警告,他們逃得掉嗎?守衛光用跑的也能馬上追上。也許警告根本沒用,但我還是佩服那挺身而出的人,只是我不知道他現在會有什麼下場,想到這點我不禁身子縮了縮。
兩個男人和男孩走到大門口。他們停在那裡,和守衛簡短地交談。一個守衛伸出手,要高個子把鏟子給他,高個子將鏟子交到他手中。三人走向前,士兵開始關門。高個子的歐米伽轉身,望著眼前的平原。他根本看不到我,但我不禁舉起手,動作跟那瘋狂揮手的工人一樣。快逃,快逃啊。雖然我只是隨著本能,但這麼做一點意義也沒有,就跟溺水的人不由自主在水中大力吸氣一樣。門漸漸關上,那人轉身走進庇護營。門碰一聲關起。
我們救不了他們。還會有更多人投奔庇護營,附近聚落的歐米伽會思考行李該帶什麼,然後他們會關上家門,永遠不再回來。而這只是其中一座庇護營。大陸上還有更多裝設了玻璃缸的庇護營。派伯在島嶼上的地圖標示了將近五十座庇護營。現在每一座都有一棟令人生不如死的建築。我目光無法從新建築物上移開。就算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外觀也夠教人毛骨悚然。而知道之後,每一棟彷彿是一塊塊恐怖墓碑。派伯用手肘頂頂我,拉我退回樹叢,我的肺才恢復正常,顫抖地吸入空氣。 * * *
離庇護營幾公里處,派伯感覺東方樹叢有動靜。到那裡時,乾地上不見任何足跡,草卻有人踩過。隔天,我和派伯躲在一處洞中睡覺,負責站哨的柔依聽到蒼頭燕雀鳴叫,便把我們叫醒,她輕聲說,早冬的蒼頭燕雀應該不會叫,恐怕是某種哨音或暗號。派伯和她繞著營地檢查時,我把刀拿了出來,但他們什麼都沒找到。我們那天提早拔營,太陽沒下山就出發,夜深之後仍避開毫無遮蔽的路。
半夜,我們穿過一個充滿金屬柱的山谷。我們正從谷底往上爬時,一人從生鏽柱子後衝出。他抓住我的頭髮,我還來不及尖叫,就被扭過去,一把刀抵住我的喉嚨。
「我一直在找妳。」他說。
我目光從刀柄移開。派伯和柔依剛才只在我身後幾步,現在兩人刀已就手,隨時準備擲出。
「放開她,不然你會死在這裡。」派伯說。
「叫你的人放下武器。」那人對我說。他語氣冷靜,好像手執飛刀的柔依與派伯根本不成威脅。
柔依翻白眼。「我們不是她的人。」
「我很清楚你們是誰。」他回答她。
我喉嚨上的刀不偏不倚靠在祭師留下疤痕的地方。他下手時,那塊粗糙的皮膚能讓刀刃慢下來嗎?我歪頭,試著去看他的臉,只看到他深色的頭髮。和派伯及柔依不同,他的鬈髮鬆垮雜亂,垂至下巴,搔著我的臉頰。他不理我,只專注抵著刀。我又慢慢把頭多轉一點,每個動作都讓脖子跟刀貼得更緊,最後我看到他緊盯派伯和柔依的雙眼。他年紀比我們都大,但可能還不到三十歲。我以前在某處看過這張臉,但記憶太朦朧。
派伯比我早一步認出。
「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你是誰?」他說。「你是團長。」
我這才想起自己在哪裡看過他──我在島嶼上看過他的畫像。
「放下武器。」團長又說了一次。「不然我會殺死她。」
柔依和派伯身後黑暗之中冒出三個人。兩人手拿著劍,一人拿著弓。我聽到弓弦繃緊的聲響,箭瞄準派伯的背。他沒有轉身,但柔依原地一轉,面向士兵。
「如果我們真的放下武器,難道你不會殺了她嗎?」派伯平靜地問。「或殺了我們所有人?」
「沒有必要我不會殺她。我是來談話的。不然你以為我為什麼沒有派大隊人馬過來?為了找到妳,和妳對話,我冒了不少險。」
「那你來幹什麼?」派伯語氣再次變得不耐煩,彷彿是在酒館和一個煩人精說話。
「我必須和先知談談她的雙生子。」團長說。
「你談話之前,都要在對方喉嚨架把刀嗎?」派伯問。
「我們彼此都清楚這不是尋常對話。」我身後的團長動也不動,但士兵微微地開始動作。一人劍鋒映著光,一步步逼近派伯,弓箭手將弓拉得更緊,箭尖不住顫抖。
「威脅我們的話,就沒什麼好說了。」我說。我說出每一個字,都感到刀卡在脖子邊。
「你必須了解,我不會沒事威脅別人。」他將刀稍微舉起,我下巴不得不抬高。我感到自己的脈搏貼著刀跳動。刀刃起初十分冰冷,現已變得溫暖。柔依慢慢移到派伯背後,雙眼緊盯他身後的士兵。弓箭手離她只剩幾公尺,他瞇起一眼,目光沿著箭尖瞄準她的胸口。
派伯動作時,一切似乎變得緩慢。他手臂延伸,一根手指順勢彈出,好像在指責團長一樣,隨即飛刀脫手。柔依同時撲出,手中兩把刀向弓箭手擲出,身子向側邊翻滾。一瞬間,三把飛刀、一支箭,劃過空中。箭從弓中飛出,射向柔依剛才站的位置。
團長用刀將派伯的飛刀「噹」一聲擊開。聲音未落,派伯的刀再次和團長的刀相撞。同時間,弓箭手身中飛刀,發出哀嚎,柔依的第二把刀擊中一旁金屬柱。弓箭從我左肩擦過,飛入黑暗中。
「停手。」團長對手下喊。我手抓著脖子,摸剛才被刀抵住的地方,原以為會感到痛楚,溫熱鮮血會從指縫汩汩流出,但什麼都沒有。我的脖子上只有舊疤,脈搏在我手指下劇烈跳動。
* * *
好幾秒鐘,我們全都靜止不動。團長蹲在我身前,刀指著派伯,和派伯的刀只距離三到五公分。柔依又抽出了兩把飛刀,站到派伯背後。弓箭手在她面前皺著臉,手抓著鎖骨上的飛刀。其他兩名士兵已逼近,劍執在身前,剛好停在柔依砍不到的距離。
我伸手去拿腰帶上的刀,但團長唰一聲收刀入鞘。「退下。」他頭一擺對士兵說。他們退開,受傷的弓箭手咒罵一聲。我看不到他的血,但那股如生肝一樣的腥味,讓我想起剝了皮的兔子,以及島上的屍體。
「我想我們都清楚彼此的態度了。」團長說。「我是來說話的,但你現在應該明白,如果非要動手,我也不是省油的燈。」
「再碰她一次,我就剁了你舌頭。」派伯說。「你就沒機會說話了。」
他繞過團長,把我拉回柔依站的地方。她已放下刀,但還沒收起。
「讓我們獨處一下。」團長對士兵喊,手不耐煩地揮了揮。他們退開,臉孔慢慢沒入黑暗之中,弓箭手粗重的呼吸聲也漸漸聽不到了。
「妳還好嗎?」派伯對我說。
我的手仍按著脖子。
「他原本可以割破我的喉嚨。」我低聲說。「就在你射刀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殺妳。」派伯回答。「尤其和妳對談若真有那麼重要的話。這是他的策略。」他現在提高音量,讓團長聽清楚。「靠著虛張聲勢讓我們知道,他是個大人物。」
我抬頭望著派伯,心想,不知道對局勢了然於心是什麼感覺。
柔依觀察山谷。「你其他士兵在哪裡?」她對團長說。
「我跟妳說了,我只帶了偵察兵來。萬一我和你們見面的事傳出去,你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轉過身。他的手下在約二十公尺外謹慎地望著我們。拿刀的士兵仍拿著刀,受傷的士兵放下弓,靠在彎曲的金屬柱上,但馬上又掙扎挺身,彷彿碰觸禁忌比胸上的飛刀更難以忍受。
「你怎麼找到我們的?」我又轉回來,面對團長。「議會找我們好幾個月了。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是現在?」
「妳哥哥和將軍覺得機器能讓他們掌握一切。或許在祭師協助之下,一切都還算順利。但他們從來沒搞懂傳統的方式。如果他們願意像我一樣好好聽點意見,就會從資深議員或士兵身上學到不少東西。多年來,溫德罕到海岸半數聚落裡的小鬼都拿過我的錢。需要探聽各地消息時,一個貪心的孩子,再加上一枚銀幣,保證比任何機器有用。有時候的確很浪費,因為他們往往只回報些流言,純屬虛驚一場。但時不時會挖到珍寶。德魯里來了個消息說,有人可能目擊到你們。後來又有人來找我,告訴我三個陌生人出現在玟羅西。其中最有趣的消息是有個阿爾法女生跟兩個歐米伽在一起。我派偵察兵追蹤你們四天了。」
「為什麼?」派伯打斷他。
「因為我們有共同之處。」
派伯大笑,黑暗中他的笑聲顯得更響亮。「我們?拜託你照照鏡子吧。」
團長也許經過長途跋涉,但他仍保有議員光潔的打扮。從他飽滿的雙頰看來,他不曾在漫漫旅程中,挑掉蘑菇上的蛆蟲之後,將就吃下肚,也不曾花十分鐘從蜥蜴骨頭上吸吮最後一絲肉屑。我們的飢餓彷彿是脫不下的衣服,當我看到他健康的臉,忍不住和派伯一起大笑,身後的柔依則朝地上呸了一聲。
「我知道你們笑什麼。」團長說。「但我們的共同之處比你們知道的多。我們想要的是同一件事。」
「我猜猜。」派伯說。「你忽然之間關心起歐米伽的死活了?」
「不。我完全不關心。」柔依原本想打斷他,但聽到他如此坦白也一時語塞。 團長一臉坦然繼續說。「我關心的是阿爾法。我希望他們好。那是我的工作,就像你為你們的人民著想。」
「我再也不負責領導全民大會了。」派伯說。他比著自己的破衣和髒臉。「我看起來像是反抗軍領袖嗎?」
團長不理他。「改革者和將軍現在在做的事,或者說,試著完成的事,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威脅。不管阿爾法和歐米伽都一樣。」
「你在說什麼?」我說。
「不要跟我裝傻。」他說。「妳從溫德罕的城堡脫逃時經過了玻璃缸室。妳知道他們重新啟用機器以及電力。還有關於祭師的檔案庫,我懷疑妳根本全都知道。改革者信誓旦旦說是祭師的雙生子『單獨』害死了她,但我一點也不信。」
我不答腔。
「多年來我和將軍、改革者緊密合作。」他說。「我甚至容忍他和祭師如此親近。」他上唇噘起,露出噁心的表情。「至少她很有用。但到了某個階段,我們的看法相左。事情漸漸明朗,妳的雙生子和將軍再也不相信禁忌的事。他們只做表面工夫,明明知道大眾對機器仍有所顧忌,卻一直暗中發展,積極投入。
「儘管他們行動隱密,但無法獨自成事。過去這幾年,有些他們私人軍團的士兵會來找我。告訴我他們看守的東西,例如玻璃缸和檔案庫。我和改革者與將軍不同,儘管『將軍』取了一個軍方的頭銜,但我才是軍人出身,慢慢爬到如今這個位子。我懂士兵,懂得聆聽正常人的想法。我知道禁忌在人們心中多麼根深柢固。妳的雙生子和將軍對機器著了魔,低估了多數人對機器有多厭惡和恐懼。」
「比起歐米伽,他們更怕機器?」我問。
「兩個是一樣的事。」他說。「大家都知道。機器造成大爆炸,大爆炸造成雙生子和歐米伽。」
這就是他看我們的方式,我們是突變,和大爆炸一樣可怕,也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他繼續說。「祭師被殺、檔案庫被毀之後,我希望一切就此劃下句點。但妳哥哥和將軍對機器執迷不悟到走火入魔了。議會中唯一有權力公然反對他們的人就是司寇。一直到最後,即使他們抓了他的雙生子,司寇仍然嚴守禁忌不可碰,因為他知道如果他都不能接受,大眾更不可能接受 。所以他們一發現自己不需要他,便殺了他和他的雙生子。」
「議會其他人呢?」派伯說。「他們知道改革者和將軍在做什麼嗎?知道他們的計畫嗎?」
「知道的人不多。他們多半默許,但不敢深究。成功的話,他們很樂意享受其中的好處,如果失敗,他們就不想捲入其中。」
我心想,真是奢侈啊,能選擇不知情,能輕描淡寫拋下知情的重擔。
「還有一些人沒有選擇。」他說。「他們來不及保護好自己的雙生子,改革者和將軍搶先下手了。」
「你的雙生子呢?」我問。
「在我這裡。」他說。「沒關在監管室,但有人看守,都是我能信任的士兵。」 我脖子肌肉緊繃,忍著身子竄上來的寒意。我不時仍會夢到自己在監管室,一天天在無聲中逝去,而我永無止境地成為時間的囚犯。
「你覺得那樣比關在監管室好?」
「比較安全。」他說。「對她和對我來說都是。以現在的情況看來,我覺得我無法在溫德罕保護她的安全。甚至在監管室也一樣。」
「你為什麼來找我們?」我說。
「我需要妳的幫忙。」他說。「幫忙我阻止妳的雙生子和將軍,不要讓他們繼續使用機器。」
感覺太荒謬了。他是個議員,手中握有無數士兵和金錢,與衣衫襤褸、瘦弱、絕望的我們相比,他擁有著我們難以想像的權力。
「你想要找人幫忙?」派伯說。「去問你議會的好友啊。」
團長大笑。「你真以為我們是一個快樂大家庭,在議會廳裡團團坐,搭肩搖,和樂融融?」他目光從派伯轉向我。「妳在監管室的時候,妳以為改革者想提防誰?議員最大的敵人就是最接近他的人,一旦他失勢,其他議員就能得到最多好處。看看司寇的下場。」
「我們為什麼要幫你對抗他們?」派伯說。「你來找我們只是因為你漸漸失去權力,你別無選擇。」
「失去權力?」團長和派伯四目相交。「你肯定懂這感覺。」
我插嘴。「在機器這件事讓你們產生矛盾之前,你選擇和他們合作。況且我們為什麼要跟厭惡歐米伽的人合作?」
「因為我能提供歐米伽比活在玻璃缸裡更好的方案。幾十年來,庇護營系統運作得十分健全,也是處理歐米伽問題相對人道的方式。稅金能長年支持庇護營的需要,這方案是可行的。只要除掉你哥哥和將軍,事情就能照舊。」
「這就是我絕對不會和你合作的原因。」我說。「世上沒有所謂的歐米伽問題。所有問題都是議會所造成的。議會不但課重稅,更逼迫我們不斷遷移到更貧瘠的土地。在我們頭上烙印,施行各種限制,是議會逼得我們無法生存。」
「那些現在都無關緊要了。我們都清楚,現在唯一重要的是阻止玻璃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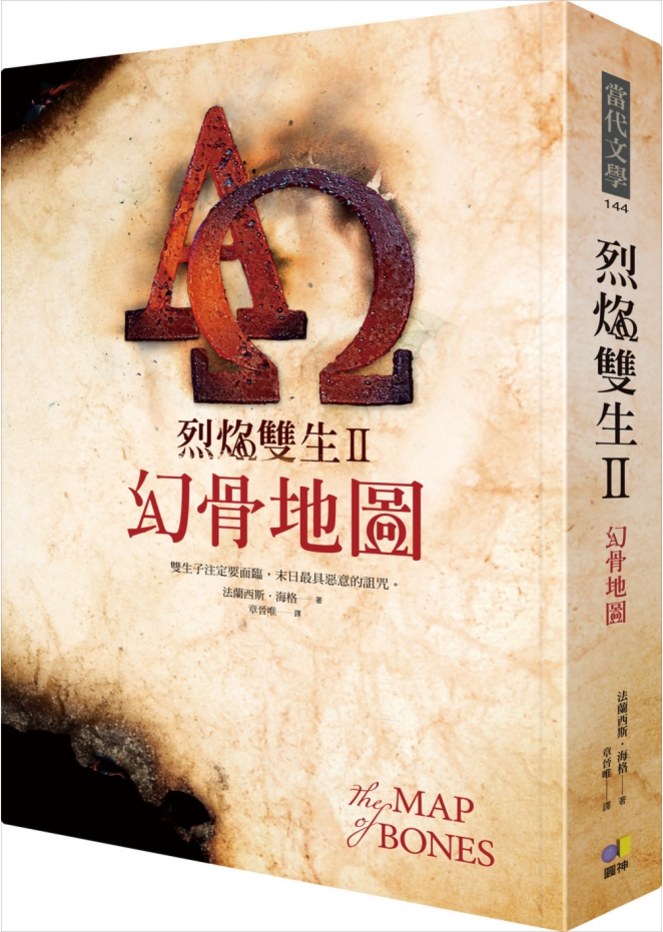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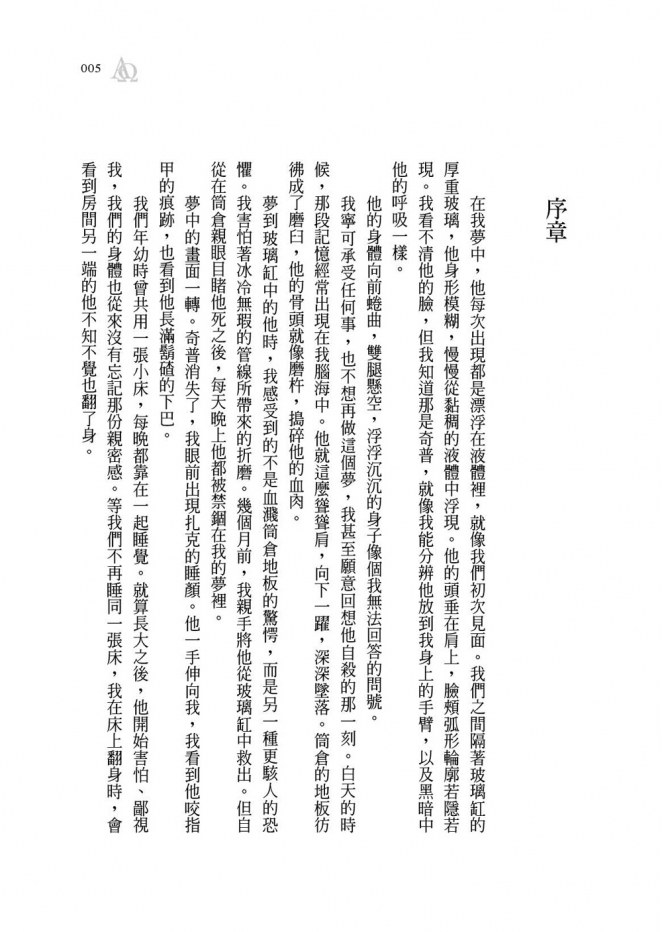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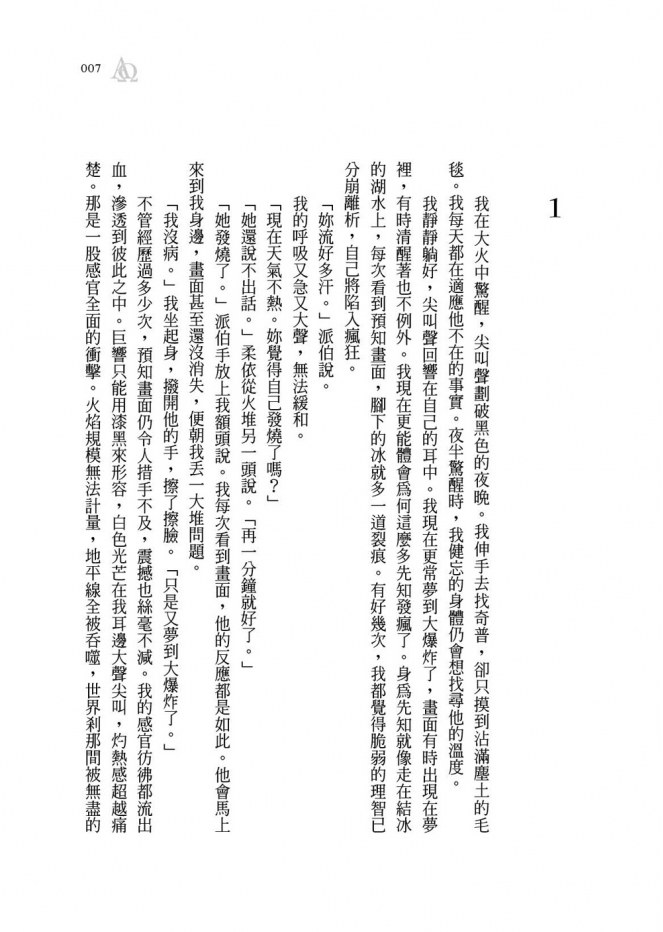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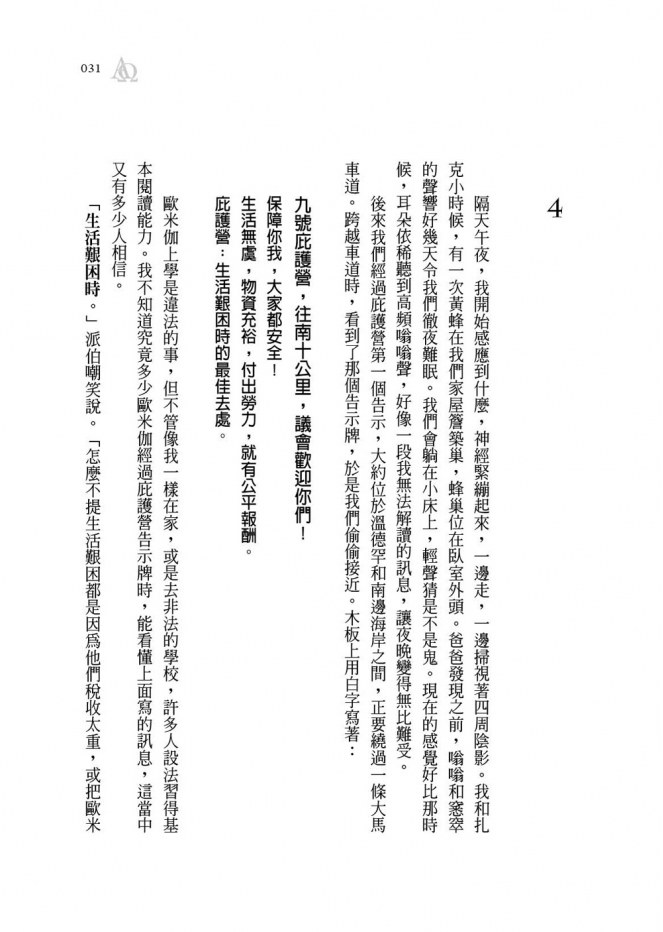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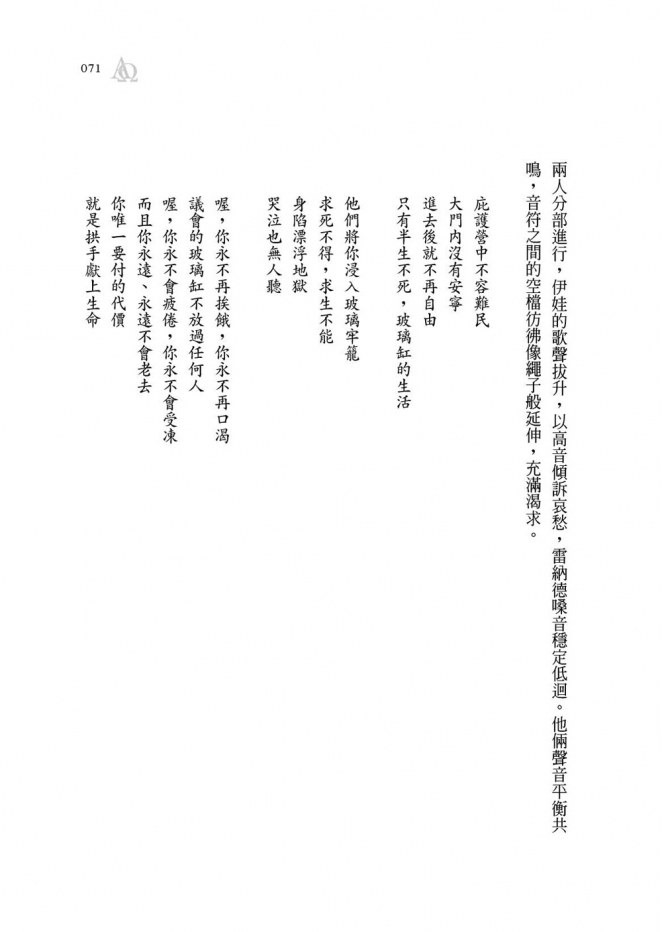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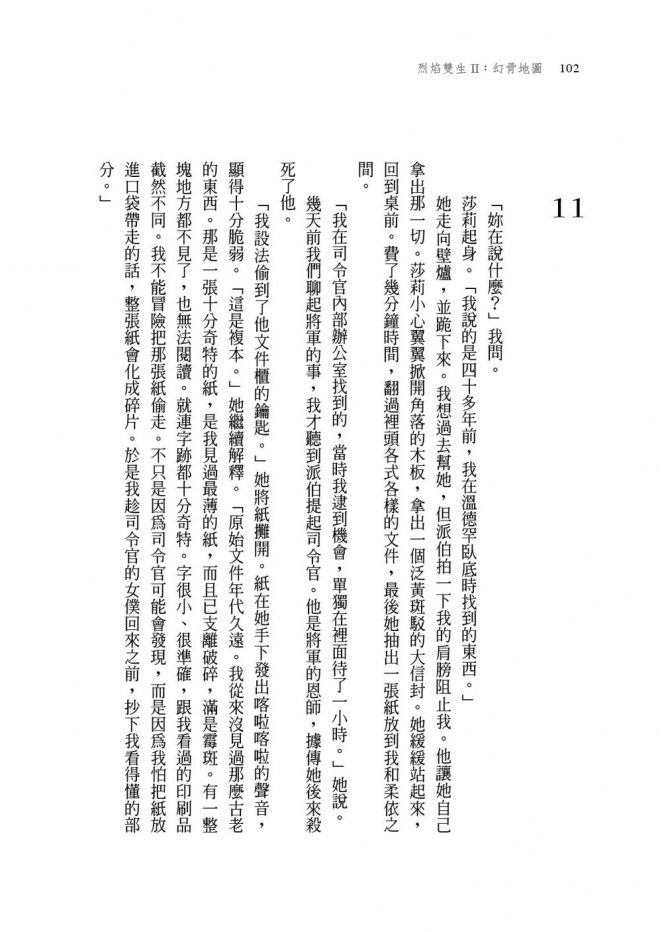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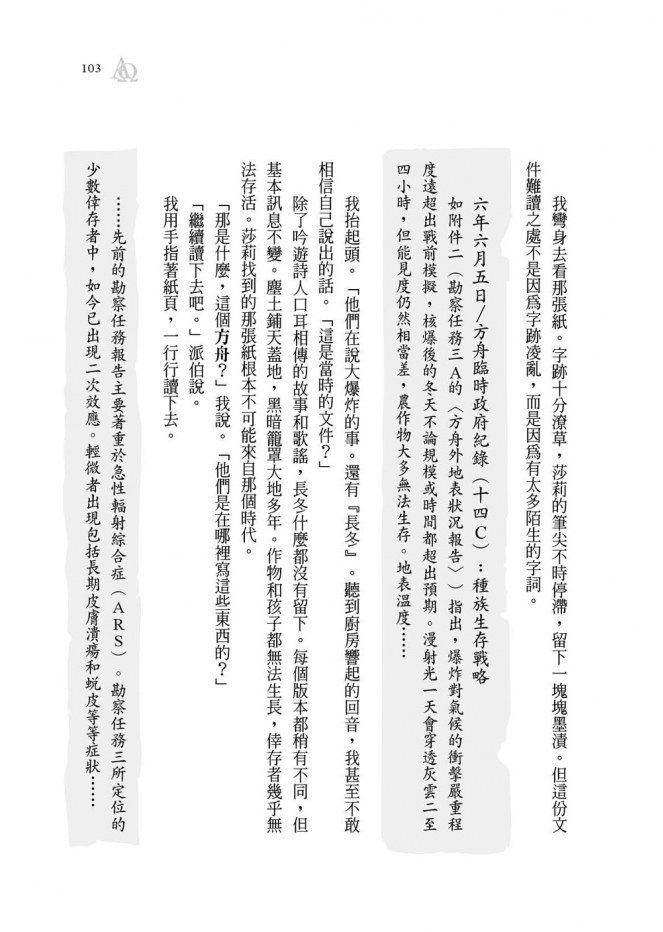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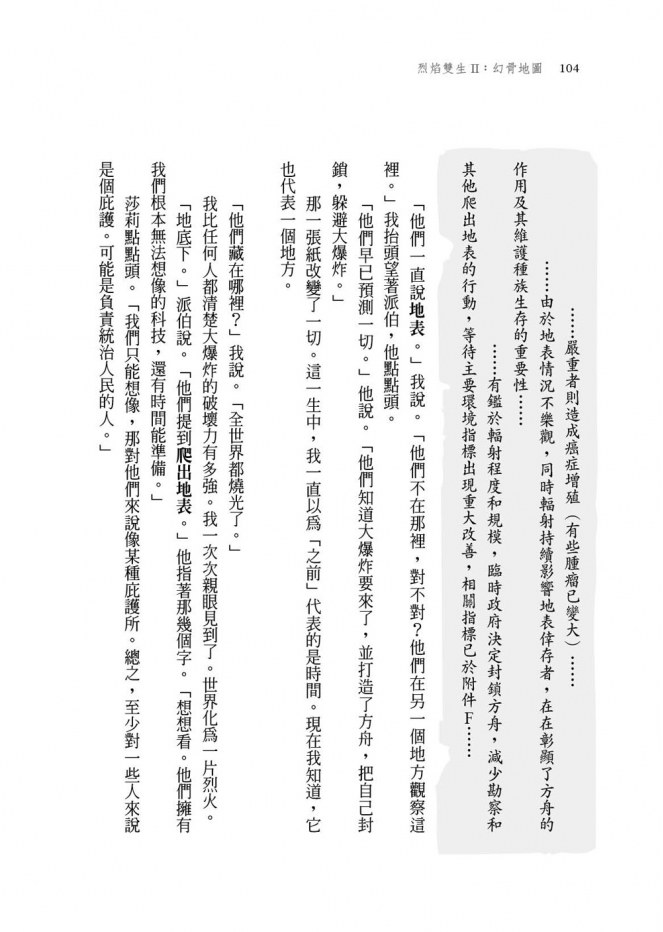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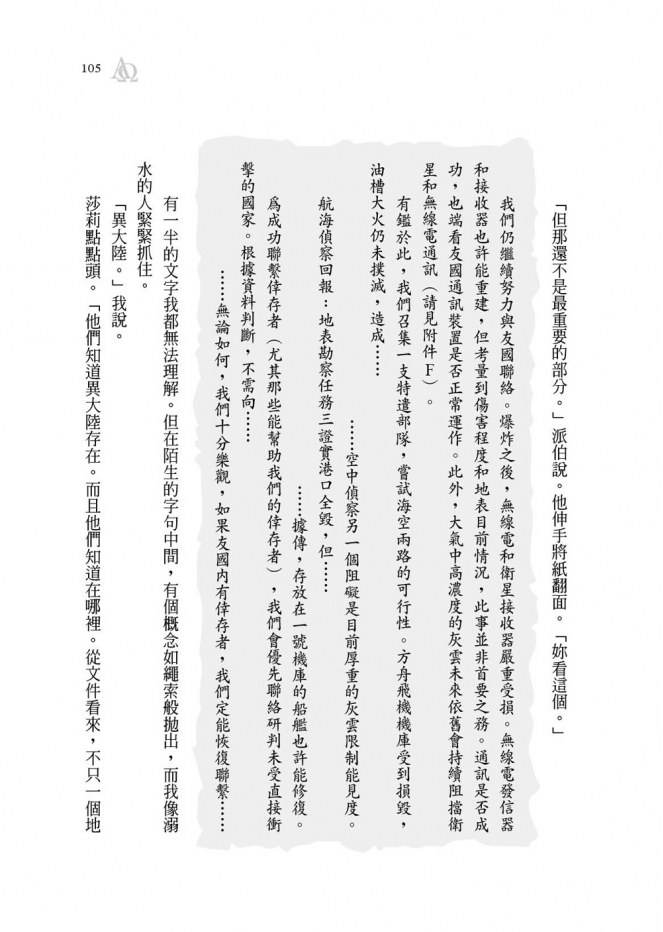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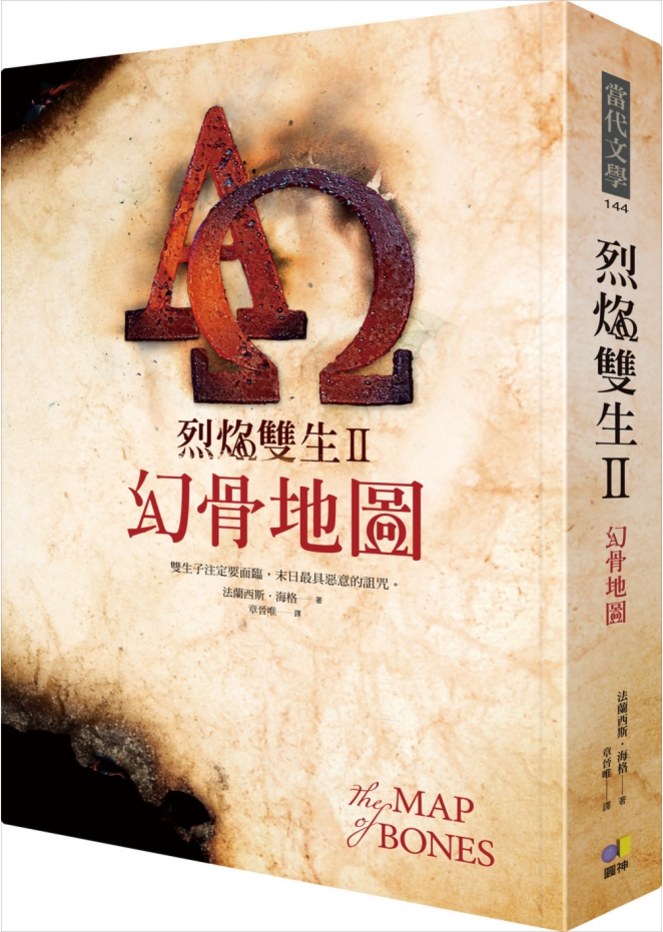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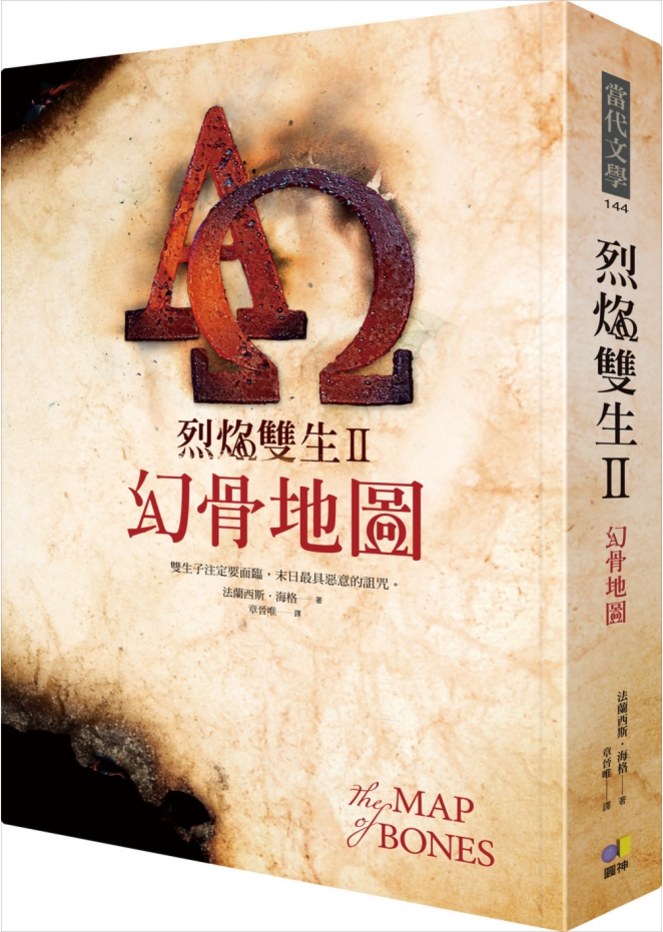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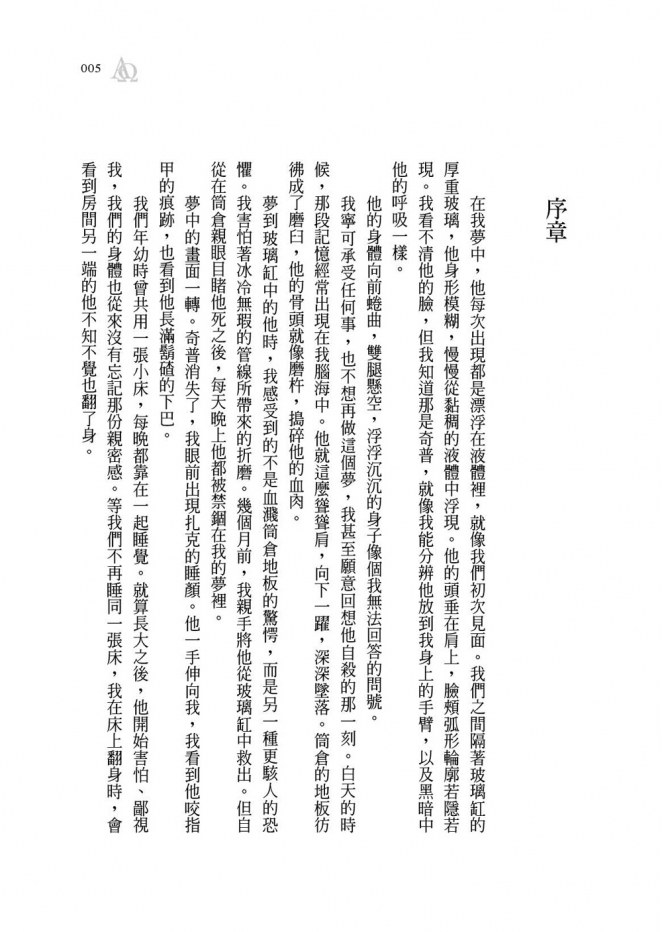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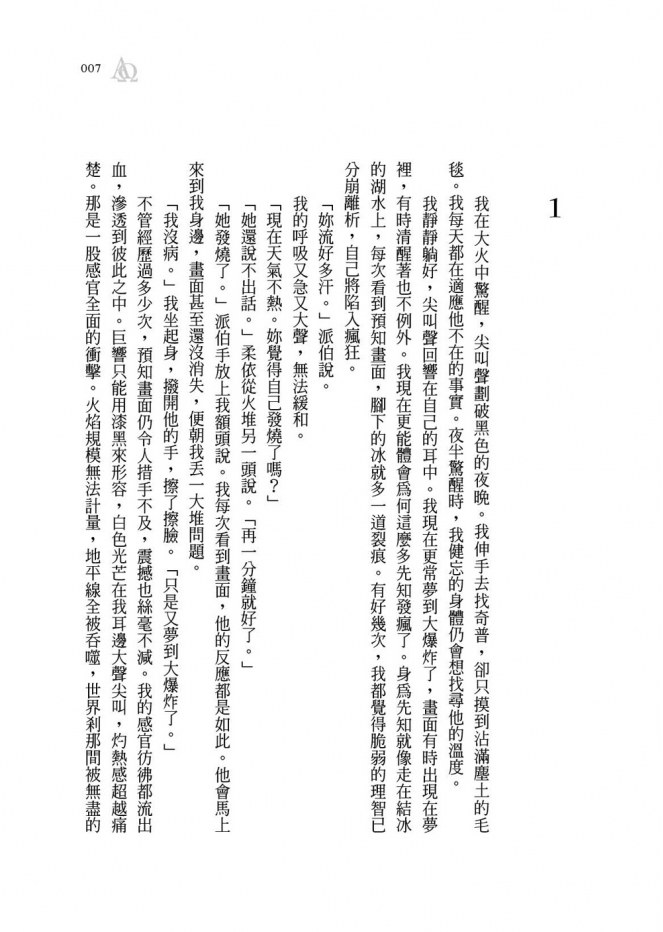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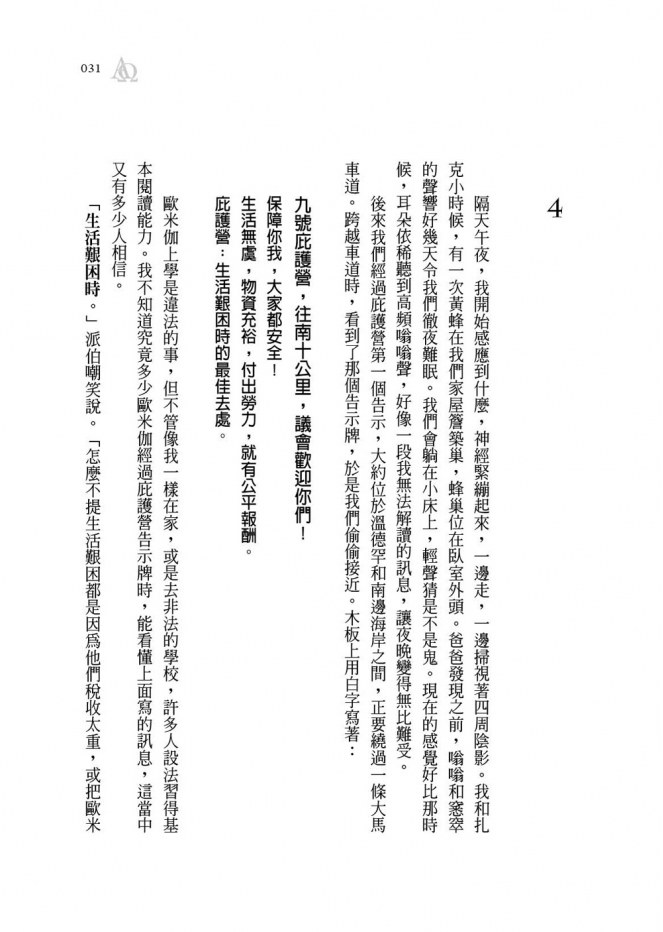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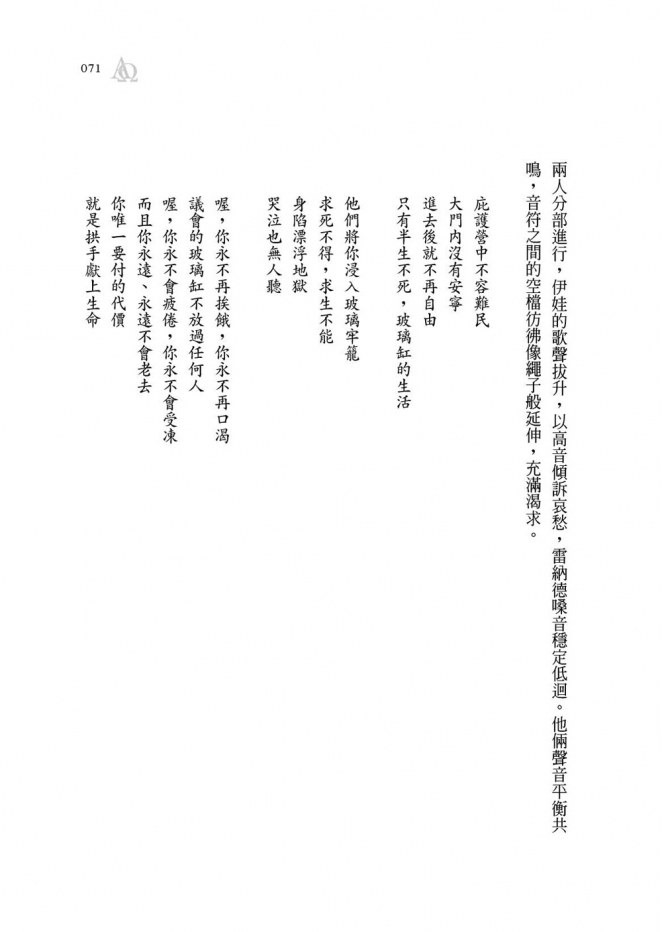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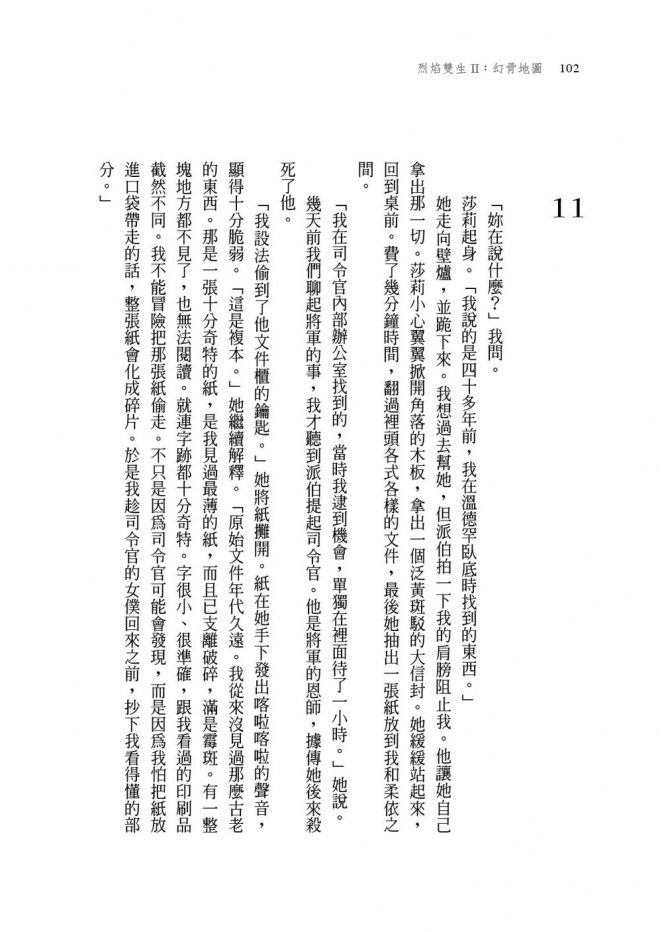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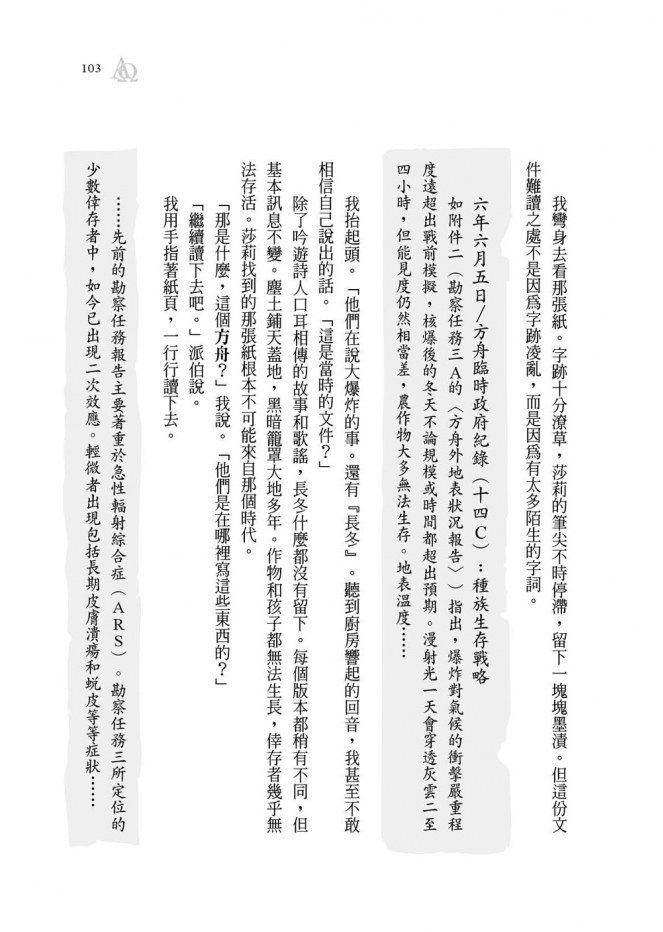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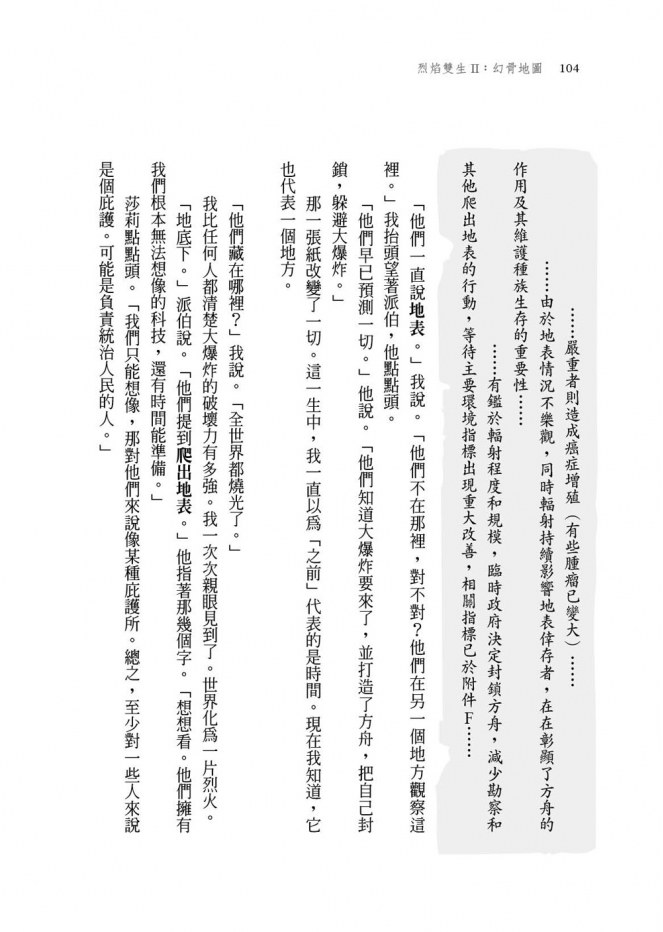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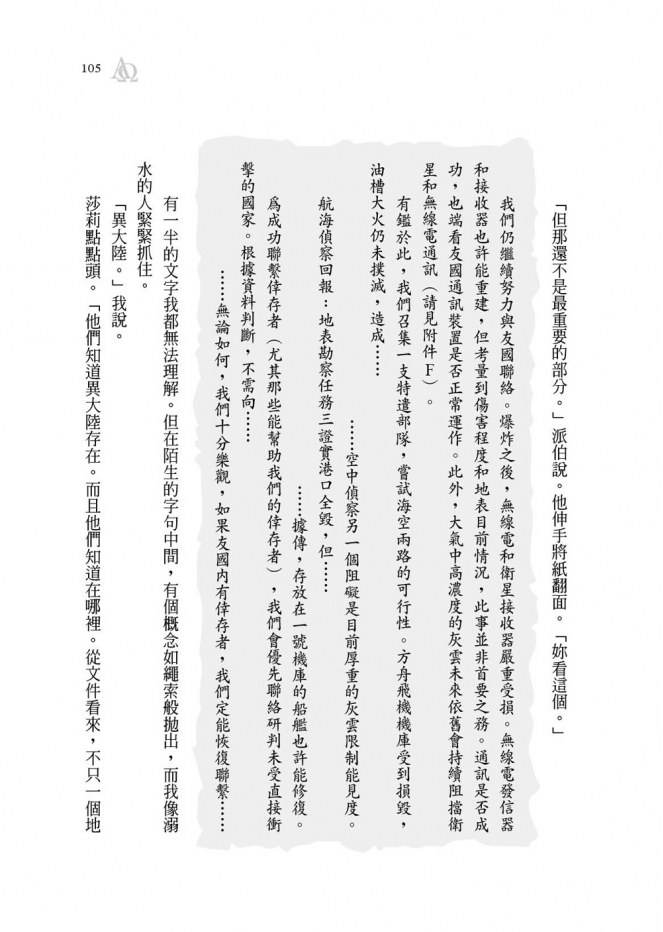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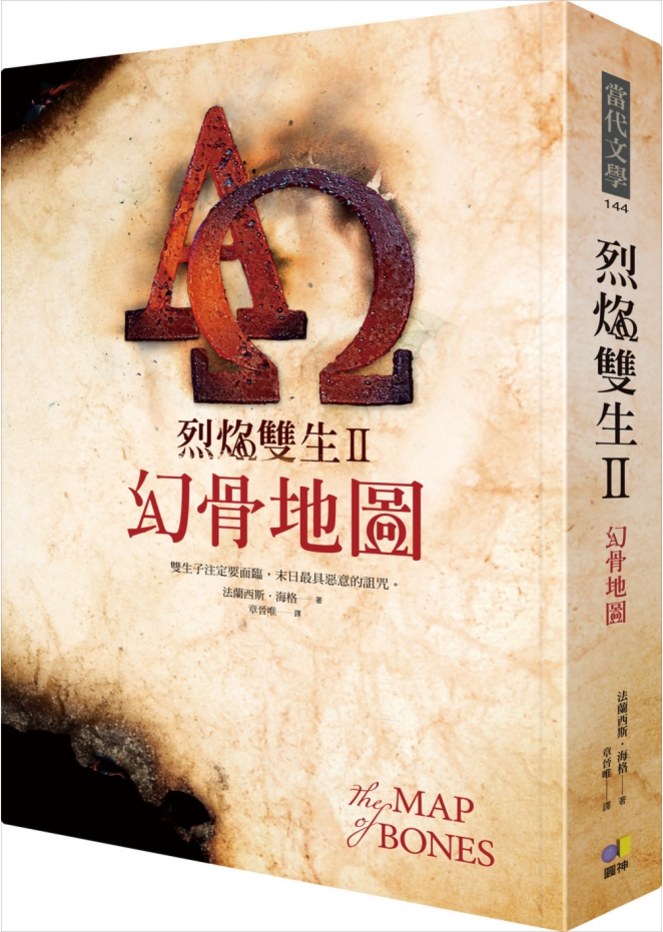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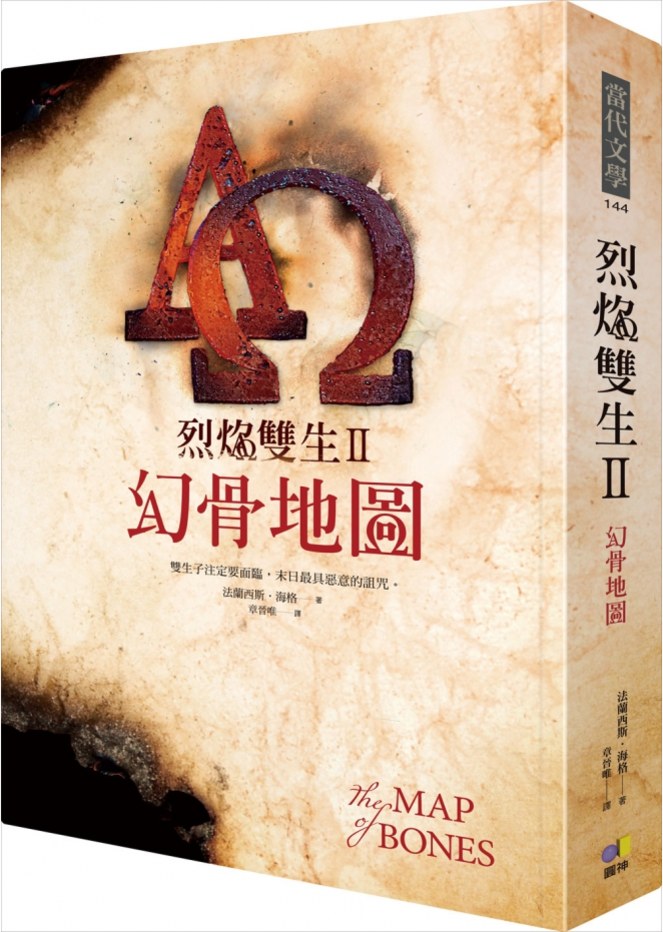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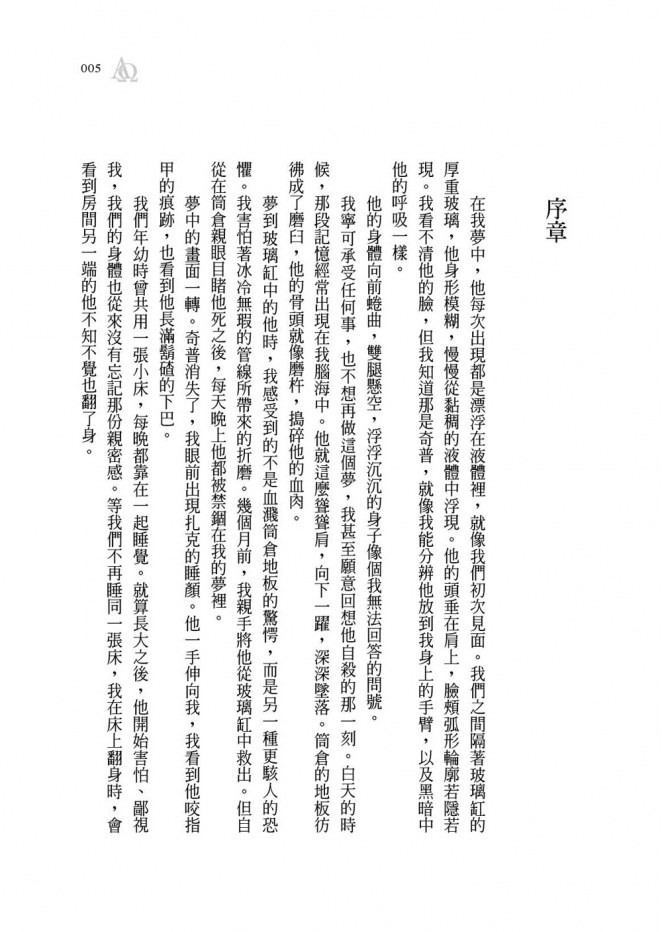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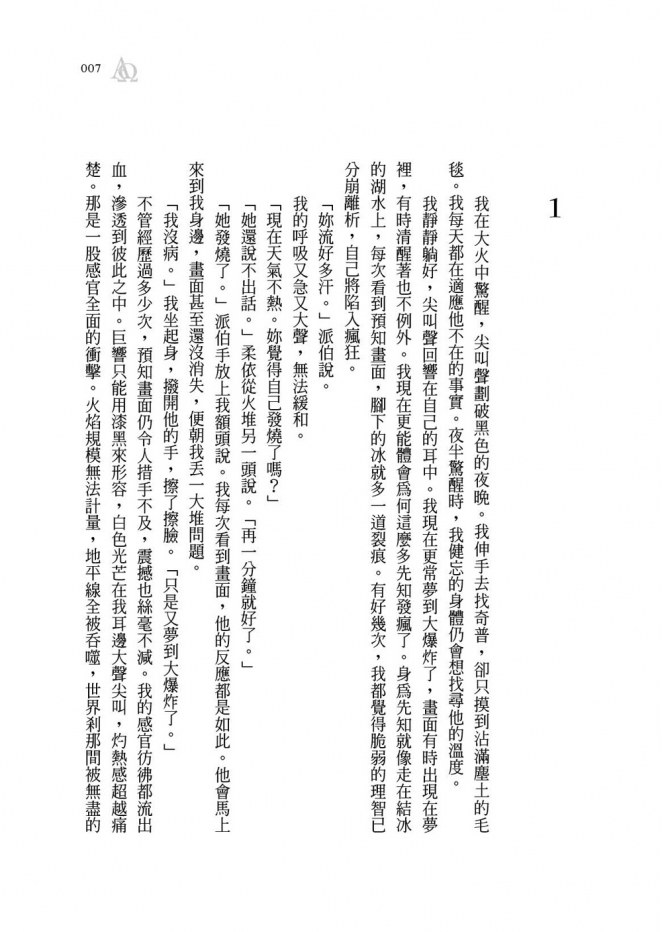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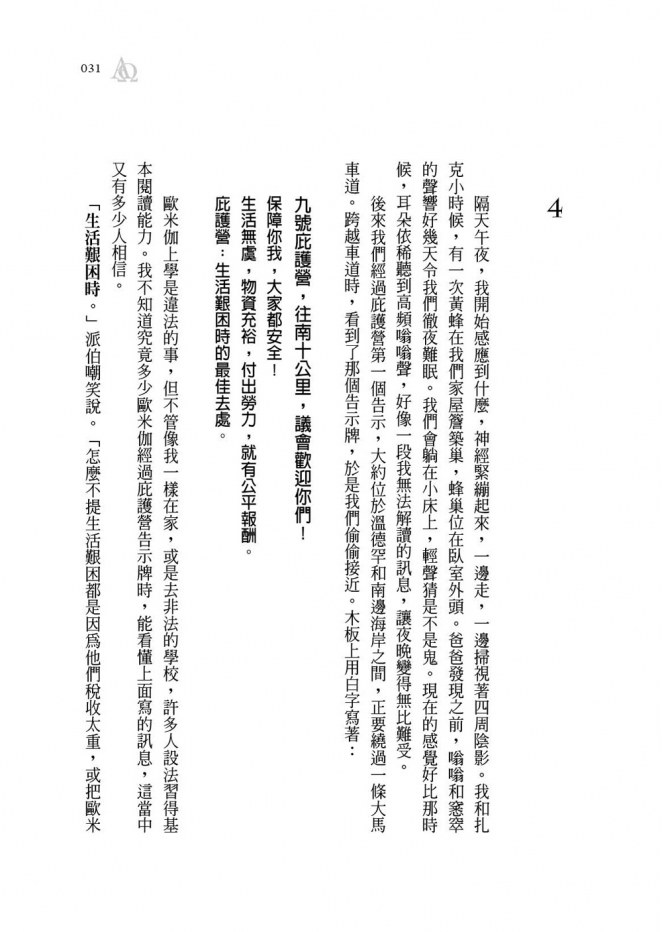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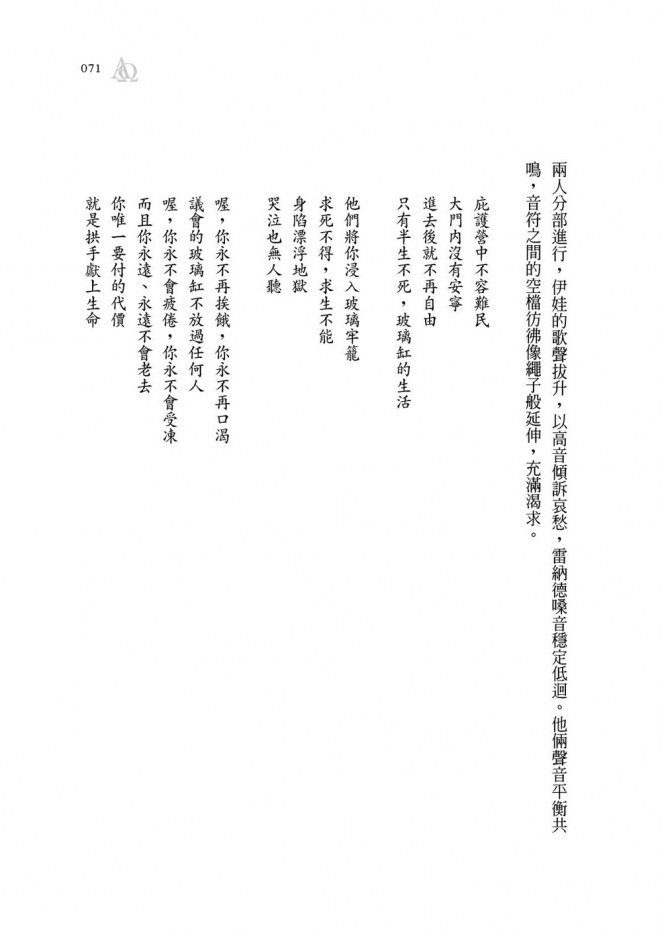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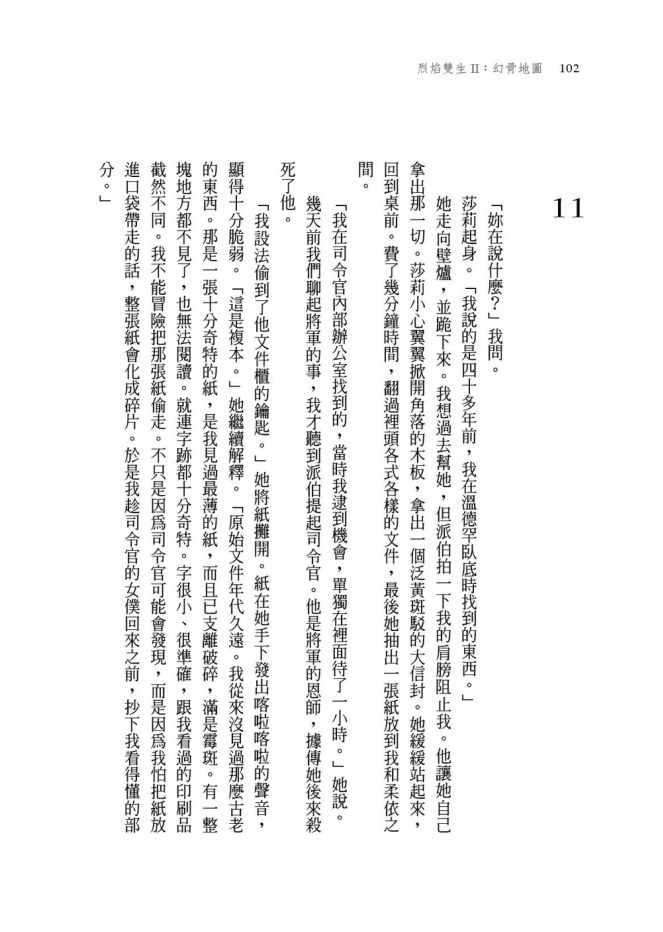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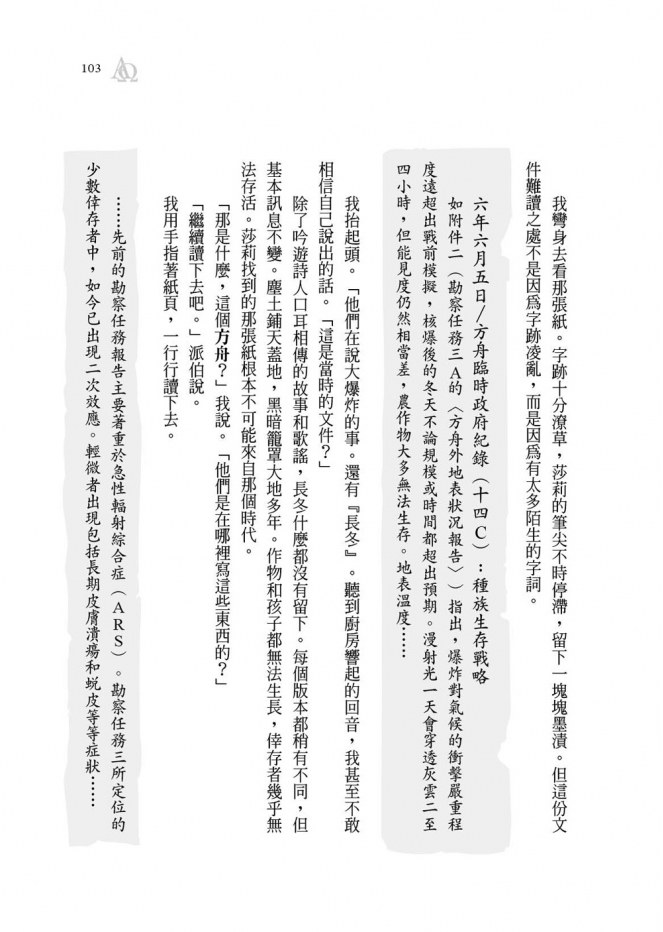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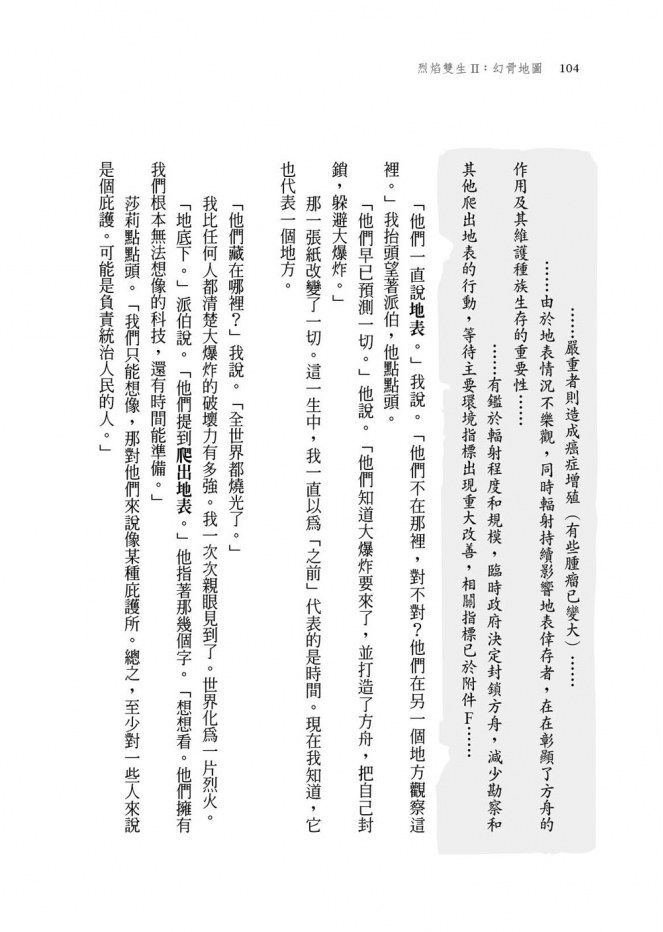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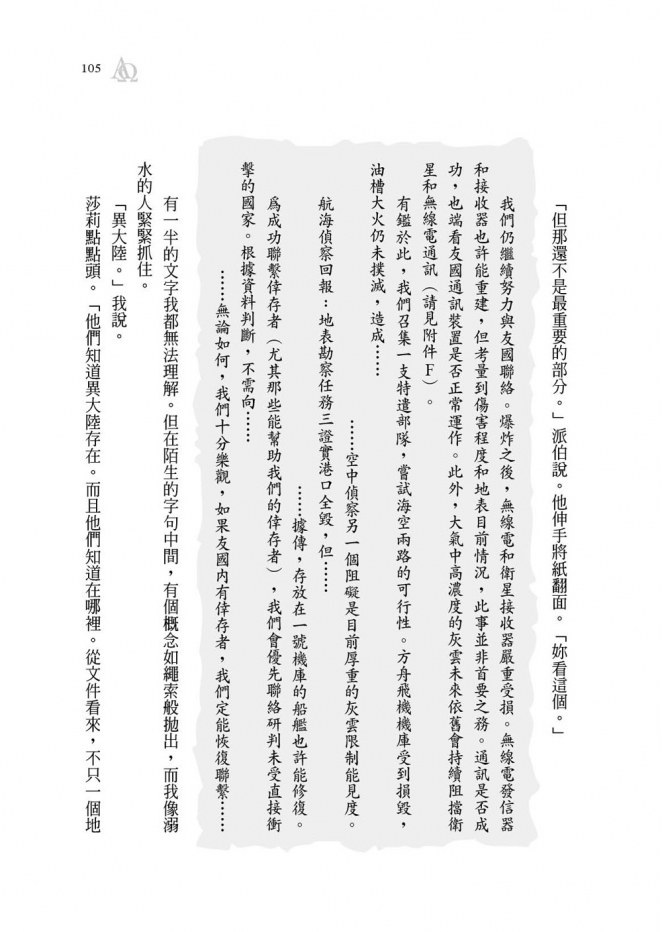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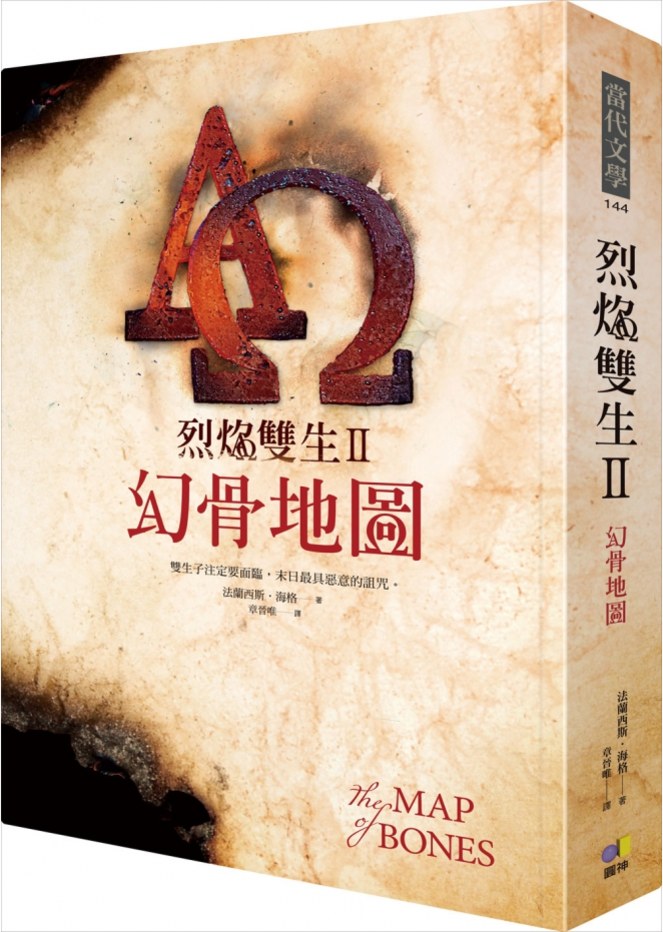
 在澳洲塔斯馬尼亞島的荒野美景中成長,取得墨爾本大學博士學位後,進入英國柴郡切斯特大學擔任講師。海格常在英、澳文學刊物發表詩作。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水之身》,便獲得安艾德詩學大獎佳作。2015年,小說處女作《烈焰雙生》出版,不但引起各國競標版權,夢工廠亦高價搶下改編權。如今海格與丈夫兒子一同定居倫敦。
在澳洲塔斯馬尼亞島的荒野美景中成長,取得墨爾本大學博士學位後,進入英國柴郡切斯特大學擔任講師。海格常在英、澳文學刊物發表詩作。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水之身》,便獲得安艾德詩學大獎佳作。2015年,小說處女作《烈焰雙生》出版,不但引起各國競標版權,夢工廠亦高價搶下改編權。如今海格與丈夫兒子一同定居倫敦。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