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2 初學者之心:克服無聊感
我在教瑜伽時,常看到有些學生做某些熟悉的姿勢,感覺就像在不經意間坐起時般的習以為常。他們可能練習某個姿勢不下百次,已經變得非常熟悉,但那個姿勢卻因為熟悉而缺乏力量。學生們充其量只是在擺動身體,並沒有扎實融入該姿勢當中。如果因為熟悉而變得不在意,那麼就算原本是要練習增加正念的方式,也會養大心中失念的怪獸。
一行禪師曾在佛教期刊《香巴拉太陽》(Shambhala Sun) 中的一篇文章,以再平常不過的喝茶過程,詳細解釋所謂的初學者之心:
有很多時候,你喝茶,卻不知道自己在喝茶;因為你一心沉浸在憂慮之中……如果你不知該如何以正念的方式專心喝茶,你就不是真正在喝茶。你喝下的是悲傷、恐懼與憤怒──而快樂也會變成不可能。
有多少次我們喝茶的同時,其實是喝下悲傷?我們喝茶的當下,心裡卻在擔心其他事情。在這段深具啟發性文字的字裡行間,我們看到,如果能抱持正念,專心做每個動作,結果會帶來多麼大的喜悅。專心可以點燃當下的喜悅,也能創造生活中各方面的正念。因為在真正喝茶的當下,就是在練習如何覺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行禪師教導我們,要得到最大的智慧,就必須無時無刻培養專注之心。如果我們懂得訓練自己專心生活,快樂與智慧便會持續增長,而悲傷與恐懼則會減弱。
我看著握在雙手中的金黃色茶水。「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敏銳專注的重要性。」這一點我心裡很清楚,但要做到卻很難。
我曾參加過一場覺知溝通的工作坊,是由一名結婚逾四十年的男子所講授。課程結束後,一名學生上前詢問講師:「先生,這麼多年來,你是怎麼做到不會對同一個女人產生厭倦?」
講師回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請你解釋一下。」
學生嘗試重新提問:「呃,你不會渴望有多一點變化嗎?」
講師再次問他:「我還是不懂你的問題,很抱歉。你究竟想問什麼?」
學生說:「先生,如果可以的話,我這麼說好了……你難道不曾想過跟別的女人在一起嗎?」
講師問他:「你所謂跟別的女人在一起,確切的定義是什麼?」
學員有點緊張地說:「先生,我的意思是說,你難道不曾想過,呃……跟別的女人發生關係嗎?」
講師回答:「我為什麼會想跟別的女人發生關係呢?我的妻子大概有三百多種人格特質,而且我可能才見識過其中的一百多種。我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都很期待看到她的另一面!」
雖然一行禪師十六歲就剃度出家,他對愛情關係的見解倒是非常有見地。他在《香巴拉太陽》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
看著你所愛的人的雙眼,以完整的你、全心全意問她:「親愛的,妳是誰?」如果你沒有對所愛之人付出絕對專注,這就是某種形式的扼殺。如果你在思緒中迷失,以為自己清楚她的每一件事情,那她將會在你心中慢慢死亡。但保持正念,你會發現許多新鮮與奇妙的事情──她的喜悅、隱藏的天賦,以及內心深處的抱負。如果你沒有賦予適切的專注,你又怎麼能說你愛她?
此刻,齋堂的地板閃閃發亮,而這群懷著愉悅心情打掃的比丘尼也已將抹布與海綿放回櫥櫃。齋堂只剩下我一人,壁爐裡的藍色餘燼閃爍著,讓人恍惚;而我心中思忖著佛教中最具挑戰性的狀態—初學者之心。小孩子最神奇的特質,即在於他們可以深深融入各種事物當中;對年輕的小人兒來說,生命中的事物都是新鮮的。作為成年人,我們逐漸變成只有在學習某種技能、展開新奇旅程,或是開啟一段新戀情時,才會發揮跟孩子們一樣的專注力。隨著人事物變得熟悉,新鮮感也隨之消失。我想,這種想要的熱情與片刻感傷的心情,都只是我在這裡的眾多經歷之一。
愛因斯坦曾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永遠不要停止發問。好奇心有其存在的道理。當人類思量著永恆、生命與現實中許多神奇結構的奧秘時,總會不由自主展現出敬畏之心。如果人們可以每天嘗試去了解一小部分的奧秘便已足夠。永遠不要失去這份神聖的好奇心。」
如果我在世界上所踏出的每一步都能保持正念,我又怎麼可能會破壞地球環境呢?如果我做任何事情都能維持正念,我又怎會無法做到最好呢?如果我知道我所愛之人是個超級複雜的人物,我又怎會不想知道所有關於他的事情呢?──要認清這種不可能性就夠刺激了。如果我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死,我又怎能浪費在這世界上的片刻時光?我做不到。就像那位結婚四十多年的男子,總是能以歡喜之心發掘妻子各式各樣的人格特質;當我清楚了解自己與世上所有生物的關係時,我也將發現所有事物的美麗與複雜;但這到目前為止,仍是未解之謎。
爐火將盡,我的茶杯也空了。我從壁爐旁的長椅起身,意識到在這裡的兩個小時,一位美麗的比丘尼與一群快樂的師父,已經以禪法完成清掃齋堂的工作,也讓我學到以孩童般的新鮮心情來接觸、面對生命中各種事物的智慧。至少,增進好奇的初學者之心有助於不斷發現喜悅,藉以維持長期的浪漫關係。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Day 5 洞察之心(慧):壞掉的魚所教我的事情
二十歲那年,我跟當時的男友到巴西的海邊城市雷西斐度假。有天傍晚,我們兩人手牽手在旅館前方沙灘上散步時,三名街頭流浪孩童圍住我們,其中年紀最大的用槍抵住我們的胸膛。
***
午後時分,我躺在床上閱讀《佛陀之心:一行禪師的佛法講堂》。一行禪師描述在越戰中的一次偶發事件,有一名美國士兵對著一名學僧吐口水,一行禪師為此深深難過。這名僧人是第一位由一行禪師親自傳法的比丘,他為此心中感到十分受傷;而如父般的一行禪師,輕輕搭著年輕僧人的手臂整整三十分鐘,才得以轉變他深受傷害的感覺。一行禪師接著對學僧說,希望他不要憎恨那個美國士兵。他說:「我的孩子,你不是出生來拿槍的。你出生就是要當一名僧人,而懂得愛、懂得了解他人,才是你應有的力量。那個美國士兵將你視為敵人,那是他的錯誤觀念。」
讀到這裡,我想起這跟有些人被訓練成動物殺手是類似的道理。是美國軍隊讓那名士兵相信殺害越南人是正確的行為,而這也順理成章成為士兵的觀點。
越戰期間,一行禪師寫下五正念練習—即倫理生活的原則。二○○九年,一行禪師修正練習方法。以下是第一項練習的更新版──尊重生命:
我決定不殺生,不教他殺,並且不支持世上任何殺生的行為,包括我的思想與生活方式在內。看到由主觀心與分別心所產生的憤怒、恐懼、貪婪和不寬容,進而引發的傷害行為,我將培養開放、無分別心及無成見的觀點,以求能改變生命中與世界上的暴力、盲信與武斷之行為。
也就是這項原則,讓那位殺貓、對感情隨便的男子,從悲慘生活中變成一名穿著花罩衫的快樂禪修者。
這項訊息很直接──錯誤的思維是殺生的基礎。我以前從未深思過這一點。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有人會殺害他人,我可能會回答:暴力背後有許多原因存在。但是,就如同許多偉大的上師,一行禪師總能將複雜概念簡化,將最單純的核心概念傳達給世人。「在戰爭中,有一種封閉、錯誤的觀點認為,人與人之間都是獨立的個體。支持戰爭的人,看不見人與人之間緊密的連結關係,就是這種無知加深了恐懼與憤怒。一旦有危險因子促使錯誤念頭萌芽,該因子即會刺激並引發暴力行為。」我闔上書、閉上眼睛。
「為什麼一個小孩子會拿槍指著我?這個年紀的孩子應該要盡情玩耍的啊。」在巴西發生那場意外事件後,這是我當時安全回到旅館後心中的想法。但是稍晚,我意識到這些非常貧窮的孩童之所以能以手持槍、隨時準備好使用武器,正是因為他們亟欲求生存。
現在回想起來,我看得出引導巴西流浪孩童朝暴力之路發展的脈絡。一行禪師讓我有機會仔細檢視錯誤的主觀意識。孩子們會發展出這種錯誤信念,當然不是他們個人的責任,而是因為他們從小就在巴西貧民區、在發展錯誤觀念的環境中成長。對某些年輕人而言,單純玩耍都是一種奢侈、遙不可及的享受。「暴力行為並不是孩子的錯,而且要原諒小孩比較容易—他們可能連自己在做什麼都搞不清楚。」我心想。「但是一行禪師選擇原諒士兵,原諒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卻仍做出羞辱一位溫和僧人的行為。」一行禪師迅速了解到,對著一名祥和的佛教僧人吐口水,如此無禮的行為,不該歸咎於那名美國士兵。一行禪師的睿智之處即在於,對他而言,凡事都像水晶般清澈透明,沒有任何人該為任何事情受到責備。這是多麼開明的思想。
一行禪師上午的佛法開示結束後,一位較資深的比丘起身,告知大家一行禪師接下來會接受提問並回答問題,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一名年輕俊秀的澳洲男子迅速舉手,看起來他心裡的問題似乎壓抑很久了。再過幾天,同一名男子會在大家面前承認自己對女性的態度很糟糕。在第三項正念練習時—與性責任有關—他會對眾人坦述一切。聽到他過去的荒誕行徑後,我開始感謝以前非常尊重我的男友們。
澳洲男子起身發問,他的問題很簡單,就是他是否該出家。他的問題讓我有些驚訝。看著他輪廓分明的下巴,我心想,他的外表與提出的問題感覺上十分衝突。他當著大家的面前表示自己一直都想出家,但最近卻出現強烈的抗拒感,並且想回家。他凝視著一行禪師問道:「我應該留下,還是應該回家?」
現在,你可能會猜想,一個選擇出家的僧人,應該會鼓勵其他人作出相同選擇,但一行禪師的回答是:「留下或離開並無差別。」我很喜歡他的說法。「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你是否能看透自己的內心,碰觸並認清自己的真實感覺,然後清楚你所覺知的一切,其實都只是事實的一小部分?你必須從其他角度觀察,不能將自己局限在單一觀點裡。你必須放開視野,終會找到最適合的答案。」
我沒料到一行禪師會給予如此深奧、睿智的答案,但我心裡很清楚,他就是有辦法引導大眾深入理解。一行禪師接著以水中的魚作為例子,進一步說明:
你從什麼方向看,那就是你所看到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觀點。如果你從前方看魚,你看到的就是魚頭,這就是你對魚的觀點。另一個人也許是從尾巴看魚,所以看到的就是那個角度。從魚的兩側看,畫面又不一樣。這幾種角度看到的都是魚。但最終,以你的一雙眼睛,是無法一次看到魚的完整面貌。因此,某種程度上,你對魚的認知仍有所局限。
在一行禪師解釋的同時,我閉上眼睛,了解到我是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一行禪師接著說:「如果你只相信自己看到的觀點,你就會認為他人的觀點是錯誤的。」
我想像有一條銀色的魚。舉例來說,如果我一直執著想要抓住這條魚的左鰭,那我永遠沒有機會知道這條魚其他部位的模樣。所以,該怎麼做呢?一行禪師建議我們:「如果你能傾聽他人的觀點,便能從他人觀點中學習。」我想起一句名言:「設身處地。」我看著坐在室內最右邊的師父。如果這條虛構的「魚」在屋裡的正前方,坐在最右邊的師父所看到的魚形,可能與坐在屋內最左邊的我,所看到的形狀大不相同。一行禪師接著開示:「從他人的觀點中學習,將帶給你另一番深度智慧。你會得到完整的觀點。」但如果要從他人觀點中得到智慧,他終於說道:「你必須學習真正放下自己的觀點。」
你必須懂得謙虛,否則永遠學不到任何東西。
一般來說,人們常會陷入「自己觀點永遠正確」的迷思,這麼一來也就抹滅其他的可能性。「我們真的常這麼想。」我心想。一行禪師表示,封閉的心態可能會造成傷害;最糟的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暴力行為。
今天稍早前,一行禪師曾說:「如果你的心是純淨的,自然會展現出美麗的言行舉止;如果你的心是醜陋的,你的言行舉止將會帶來大災難。」
今天僅是我這趟旅程的第五天,但我已經發現,一行禪師並非一味地闡述人世間的悲苦。他知道世界上有痛苦,但也承認世界上有快樂。兩者都是事實。而且很顯然地,他非常希望能減少痛苦、增加喜悅。稍早之前,一行禪師的話讓我們幾個人都笑了。在他強調不帶個人觀點的必要性時,提到有位著名的佛教宗師曾說:「佛的聖體就是牛大便。」基本上,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佛法都是狗屁!」這位有名的禪師之所以說出這驚人的話語,便是為了警醒大家,希望人們了解到,就算是佛法,也不過是帶領我們尋找智慧的工具。一行禪師常說,佛法就像一艘船,這艘船是要用來帶你過河。一旦到達彼岸,如果你還緊抓著船、帶它上路,就只是在身上徒增無謂的重量。所以,若要加深個人觀點的全面性,就必須先懂得如何放手,當然也包括你對佛法的洞悉在內。
我再次思考剃掉一頭金色長髮的可能性。
今年梅村冬季禪修活動開始前,一行禪師人在印度弘法。今早開示時,一行禪師憶起偉大的印度領導者聖雄甘地。甘地曾說:「在我尋找真理的過程中,我摒棄許多想法,也學到許多事情。」從這句話來看,一行禪師認為,很明顯的,甘地懂得如何放下自己的看法,而這正是使他充滿智慧的原因。
很高興聽到一行禪師提起甘地。因為在我前往梅村、在巴黎停留時,很幸運地聽到消息,在書店見到來法國推廣祖父傳記的拉杰穆罕──他是甘地的曾孫。那是在聖日爾曼德佩廣場附近的一間書店,裡頭非常擁擠,我只能坐在樓梯邊緣,專心聽著精采的演講。事實上,拉杰穆罕什麼都能說,我也什麼都想聽。能與如此傳奇、偉大的和平領導者後代面對面共處,我整個人沉浸在喜悅之中。
拉杰穆罕結束談話後的問答時間,有一位聽眾問他,他人生中最想達成的目標是什麼。拉杰穆罕表示,他希望能覺察並對抗自己心中不正義的念頭,如此一來,才能對抗世界上不公不義之事。
那個夜晚發生許多出乎意料的事情,在我心中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
稍晚,我走回巴黎短租公寓、回想拉杰穆罕的話的同時,突然感到一陣噁心,還有些盜汗。我猜是晚餐的鮭魚,雖然在魚店時看起來很新鮮,但可能已經壞了。我想的沒錯。我的情況變得很糟。幸運的是,我是在回家後才把胃中所有恐怖的食物傾瀉吐出。回到住處,獨自一人處在生病且虛弱的狀態,感到無比的脆弱與絕對的孤獨。但這般脆弱也釋放出某種獨特勇氣,我記得當時心裡想著:「我只想要當個好人。」
漫漫長夜裡,我想辦法從浴室地板、靠著自己站起來。我打開電腦,向所有聯絡人發送以下訊息:「如果你收到這封信,代表你可能是我的家人、摯友、朋友、同事、點頭之交,甚至只有一面之緣的人……但不管如何,我只想讓你知道,我想念你,你一直都在我心裡。」
***
一行禪師今天稍早還說,智慧往往伴隨痛苦而來,藉此開啟心靈。那晚我身在繁華的巴黎,卻因為食物中毒而度過孤單悲慘的一晚,這個經驗一點都不愉快。但我現在知道,我對人生的看法,卻因為那晚而變得寬廣。我意識到,讓生命中的親友知道我非常關心他們、希望一直關心他們的重要性。我甚至把這種訊息寄給我不喜歡的對象,還有一些可能因為收到我突如其來、毫不掩飾的情感而感到尷尬的人。在健康的情況下,我對表達感情向來謹慎。我只希望父母還在人世,能收到我的這封信,而且他們肯定會是第一個回信給我的人—事實上,如果我生病的話,他們也會希望我打電話告知。
在法國那個孤單的夜晚,失去父母的感覺更加強烈,但反胃、嘔吐也為我帶來另一段故事。隔天,在身體稍稍好轉以及寄出一堆示愛的電子郵件後,我收到許多令人愉悅的回信,而且還收到許多意料之外的收件人回覆。頭頂上絕望的烏雲已然飄離,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燦爛光明。
我意識到,見到甘地的曾孫與食物中毒的痛苦,都讓我的思想有所突破、擴展,甚至打開我的心—這正是一行禪師今天所說的事情。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有「突破的機會」。但如果沒有把握該經驗的突破時機,機會便會溜走。禪師瓊.桑德倫(Joan Sutherland)的說法是:「如果沒有(該經驗的)加深與拓展,並以此維繫活生生的關係,則該關係可能從此消失匿跡,或變成令人沮喪的回憶。」
今晚入睡前,躺在像哈比人居住的寮房裡,我想起巴西的那一夜。看到舉在空中的槍枝,握在青少年的小手中,在生與死之間,我的注意力瞬間變得非常敏銳。我知道自己絕對沒機會扭轉局面,所以我保持沉默,不緊張,不否認,也沒有特別的情緒;男友則在事後放馬後砲說,他覺得手槍並未上膛。我記得在當下一觸即發的氣氛中,我看到年輕男孩扣扳機的手指因壓力而緊張。下一秒,在充滿死亡氣息的氛圍中,我對漫不經心的男友使了個沉默而堅定的眼神,示意他我要逃跑。他隨即迅速跟上。
絕對不要低估手槍上膛的可能性—這是我逃跑時心中浮現的念頭。
一行禪師所教的是「入世佛教」,而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證。他總是能以智慧面對複雜的情況。要融入世界、體驗世界,且行事不偏不倚,既如花崗石堅硬,也不失柔軟的力量。出家並非無憂無慮。如果有人認為出家代表遺世而居,活在像極樂世界般的夢境,那這些人肯定不懂出家人的真實生活。
Day 6 暫停腳步:鐘聲的訊息
父親進行心臟三重繞道手術當天,我和哥哥、弟弟在多倫多各自的家中,完全不知道父親正躺在渥太華醫院的病床上。父親不讓母親告訴我們,他即將進行具有生命危險的手術。父親的一生幾乎是不停地工作。他每天早晨五點起床,進辦公室前,會先在家裡工作數小時;其他家人起床後,看見的是父親埋首在餐桌上成堆工作文件中的畫面。父親從公司返家、和全家人吃完晚餐後,他的夜晚模式也是一成不變──在餐桌上工作。就連週末也在工作。
「如果你現在的生活方式,跟過去二十年一模一樣,那麼很明顯地,你人生中最精采的時刻永遠不會到來。如果你無法停下腳步,也就無法洞悉生命。」
一行禪師的這句話警醒了我—即便他本人不在現場。今天下午,我跟其他幾位同修,一起坐在禪堂觀看佛法開示影片。「我們是要練習『融入其中』,而不是『有做就好』。要學習享受當下你所做的每件事情。」我凝視著一行禪師在電視螢幕上的影像。他清楚表示,如果不停下腳步,就永遠無法深入了解生命的意義。暫停腳步能引導我們真正認識自己、了解世界。以佛家的話來說,這種探索過程稱為「觀」。所謂「觀」,並非單指增加知識層面的理解。「唯有透過經驗,方能啟發智慧。」這位睿智僧人所點破的事實,再度證明我離開有形的家,飄洋過海到這遙遠之地的必要性──為了增加勇氣的深度。
今天稍早,我在倒綠茶的同時,看到一位栗色短髮、身材修長纖細的婦女,她戴著金屬框眼鏡,突然停在齋堂與洗碗區之間的門邊。那是個很滑稽的畫面,她以詭異的僵硬姿勢停下腳步,靠在半掩的門邊以求平衡,看起來就像一隻緊張兮兮的松鼠,試圖穿越滿街車輛的道路。
這位剛到新村的同修,其實是在練習梅村特有的生活規則:聽到鈴聲時—不管是擊缽聲、電話鈴聲,或是附近教堂的鐘聲—每個人都要停下腳步。停下腳步的同時,要專心練習呼吸、保持安靜,並且靜止片刻。雖然我一開始覺得這種練習方式很奇怪,但現在也漸漸習慣了。原來,我們只是不想停下來罷了。面對生活中的靜止狀態,我們往往會像那位停在門邊、修長僵硬的婦女一樣,表現得手足無措。
有個流傳已久的佛教故事,內容是描述一名騎馬奔馳的男子,其速度之快,讓旁人以為男子要前往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路人對男子大喊:「你要去哪裡?」馬背上的男子回答:「我不知道,你問馬兒吧!」如果這個禪法故事還不足以說明何謂徒勞無益,那麼就聽聽哲學家怎麼說吧。梭羅曾說:「騎馬一分鐘奔馳一哩路的人,其所要傳遞的,不見得是最重要的訊息。」
其實,是文化扭曲了移動速度的概念。幾年前,我到紐約拜訪友人,在一個極其炎熱的八月午後,我們正要前往蘇活區,當時我的步伐大約落後友人三步。以我走路的速度,在濕熱空氣中的我,依然揮汗如雨。前方的朋友轉頭、非常直接地說:「瑪莉,妳在紐約,要走快一點!」不用說,接下來的一整天,她無時無刻都是處在濕汗淋漓的狀態。我親愛的朋友──我是真的喜歡她──已經習慣快步行走,她就跟許多活在現代世界的人們一樣,單純就是因為習慣。如果我住在一個永不休息的城市,或許我接下來的人生都會活在快速奔馳之中吧。
來這裡禪修前,這是我每天會在倫敦和巴黎街頭看見的畫面:每條街上都是緊繃的臉孔,跟鐵軌一樣纖瘦的人們,穿著黑色服裝,一手拿著外帶咖啡,一手拿著手機,急忙前進—彷彿時間是個發怒的暴君緊追在後。
當一行禪師表示,人類的習慣能量猶如脫韁野馬時,我心裡再認同不過了。
一行禪師接著啟發聚集在禪堂的四名禪修者,我們四人就像專心、迫不及待想聽故事的小學生──只不過禪師所說的故事是真實的。
「就知識層面來說,你知道生命是美好的,但卻因為自身的悲傷、憤怒與恐懼,而無法碰觸這份美好。因此,你必須解放自己,不再受限於渴望、妒忌與情感投射的束縛⋯⋯汲汲於追求名聲、權力與成功的你,永遠無法獲得自由。」
二○○七年,《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吉尼.溫加騰曾在華盛頓特區的地鐵站進行街頭實驗。
在寒冷的一月早晨,一名男子站在華盛頓特區的地鐵站前拉小提琴。他演奏了六曲巴哈的作品,時間長達四十五分鐘。在忙碌的尖峰時刻,數千名旅客在地鐵站裡進進出出,大部分的人都趕著去上班。
三分鐘之後,一名中年男子注意到有人在演奏。他放慢腳步,停下數秒,但隨即又加快腳步離開。一分鐘後,一名婦女在罐中投入一元,但沒有停下腳步。有一名男子靠在牆上聆聽,但不久後也看看手錶,繼續前進。現場有一個人很專心在聽—是個三歲的小男孩;但他的母親將他拉走,即便那孩子一路不斷回頭看著音樂家。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幾個小孩身上;孩子們的父母同樣不做多想,直接拉著孩子繼續向前。
這位音樂家表演的四十五分鐘裡,只有六個人停下來聆聽片刻,約有二十個人投入零錢,但沒有停下腳步欣賞。他總共得到三十二美元。沒有人注意到他的表演結束,也沒有人鼓掌,更沒有人認出他是誰。
這位音樂家是約夏.貝爾,世界知名的傑出小提琴家之一。他透過小提琴,在詮釋巴哈樂曲方面出神入化,一場演出價值三百五十萬美元。在地鐵站表演的前兩天,他在波士頓音樂廳演出的票已經售完,每個座位的平均價格為一百美元。
約夏.貝爾在地鐵站匿名演出,正是這實驗的一部分,實驗目的在於測試人們的感知、品味與優先順序。根據《華盛頓郵報》指出,這個實驗要探討的問題是:在一個非常普通的環境裡,在不適切的時間點上,我們有辦法接收到美麗的訊息嗎?我們會停下腳步欣賞嗎?我們在無預期的情況下,能辨認出有才情的人嗎?如果因為太過匆忙而無法辨認如此傑出、優秀的音樂家在演奏世界知名精細複雜的樂曲,那我們究竟還錯過多少事情?
一行禪師今天的開示內容,還包括人們是如何以睡夢般的方式過生活—大部分的人都還沒覺醒,還沒認清「活在當下,尋找真正的平靜與喜悅」的必要性。我想,這就是在梅村必須練習行禪的原因之一。一行禪師教導大家如何走路。今天,透過電視螢幕,一行禪師解釋進行這項常見動作的適當方式:
當你跨出步伐,請告訴自己:「我現在已經抵達此處。」這不是陳述,而是覺知。你的一生都處於不停前進的狀態,但卻哪裡也到不了。給自己一個抵達的機會──你所跨出的每一步,都必須投入百分之百的心力……才能真正抵達。將心完整地放在步伐之上,接下來所跨出的每一步就會變得踏實。你所踏出的每一步,都猶如帝王的印記,上頭還寫著:「我已經抵達了。」
幾天之後,我將再度聽到一行禪師親自解釋行禪的意義。
在僧院裡沉思的步行方式,和我在紐約街頭快速行進的過程大不相同,也與我在倫敦和巴黎街頭所見,滿街拿著咖啡、面無表情的人群迥異。我心想,如果我把快速前進的倫敦人攔下來,建議他們將心擺在步伐上,不曉得他們會不會覺得我瘋了。在忙碌的城市裡,有可能以這種方式行走嗎?我花了一點時間,思考以正念方式行走的話,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行禪師稱這種走路方式是「像佛陀一樣走路」。這幾天下來,我仔細觀察一行禪師的走路方式,他的舉止之間,其動作品質與我截然不同。他踏出的每一步都是謹慎而堅定,平均而持續,而且緩慢。相較之下,我所踏出的每一步都缺乏思考、不平均且缺乏節奏。我總是想走在眾人之前──一直都是如此。但是當我有機會停下來觀察人流時,在寶貴的片刻時光中,我覺得時間彷彿靜止了。一行禪師認為,這就是深深融入當下時光的影響。在這罕見的時刻裡,我感到很愉快;不必擔心過去,也不必急於計畫未來。更重要的是,我並未因此與真正的自己斷了聯繫。我的心與身體始終在一起。
今天是我在梅村的第六天,我開始愛上鐘聲。想起今天早上看到在門邊進退兩難、手足無措的婦女,這是她的第一天。我想,或許再過幾日,她會放鬆的。現在,我喜歡這種暫停時刻。停下腳步讓我有機會檢視自己,或許我的呼吸隨便,也可能對某人說些不該說的話。我發現這種暫停時刻讓我有反思機會,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藉此調整自己的行為。響起的鐘聲帶我進入沉思之境,雖然停止動作感覺還是有點奇怪,但我漸漸了解,一行禪師所說的「止」或「停」的用處──這是禪修極重要的一部分。
我是否必須要飄洋過海、到遙遠的僧院,才能聞到濕潤土地上的青草香氣?我在這裡、在法國的鄉間,環繞在自然之美當中。從房間向外跨出一步,外頭滿是連綿山丘,成排的紅蘋果樹與梅樹,成片交織的葡萄藤蔓,以及淡棕色的向日葵花田。我的感官與注意力都受到環境所刺激;我清楚覺知周圍事物,也察覺其中的美麗。為什麼我平常在家時沒有這種覺知呢?
屬於工作狂父親的記憶,伴隨我走過新村的濕潤草地。母親最後終於說服父親,讓我們在他進行手術前,知道有這件事情是多麼的重要。那天,我和哥哥、弟弟趕到渥太華的醫院,看到父親順利結束手術。雖然是因為母親被診斷出罹患癌症,父親才提早幾年退休,但這次的心臟繞道手術也使他正視死亡。對健康的恐懼,促使父親提升與家人相處時間的品質。
當一行禪師說,「像佛陀一樣走路,像個自由之身」時,我想起了父親。如果父親終其一生都不停地過度工作,他的人生會變成怎樣?在充滿過度咖啡因、過度忙碌,每樣事情都太超過的人類世界裡,我們是否能了解,要以更有智慧、更輕鬆的方式來工作,而不要等到疾病上門,才知道要停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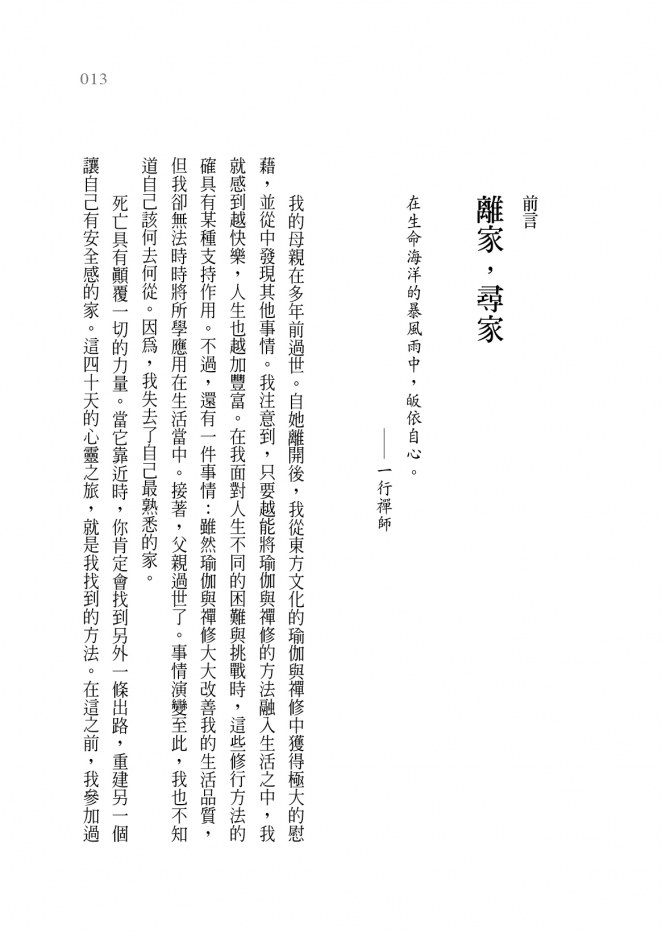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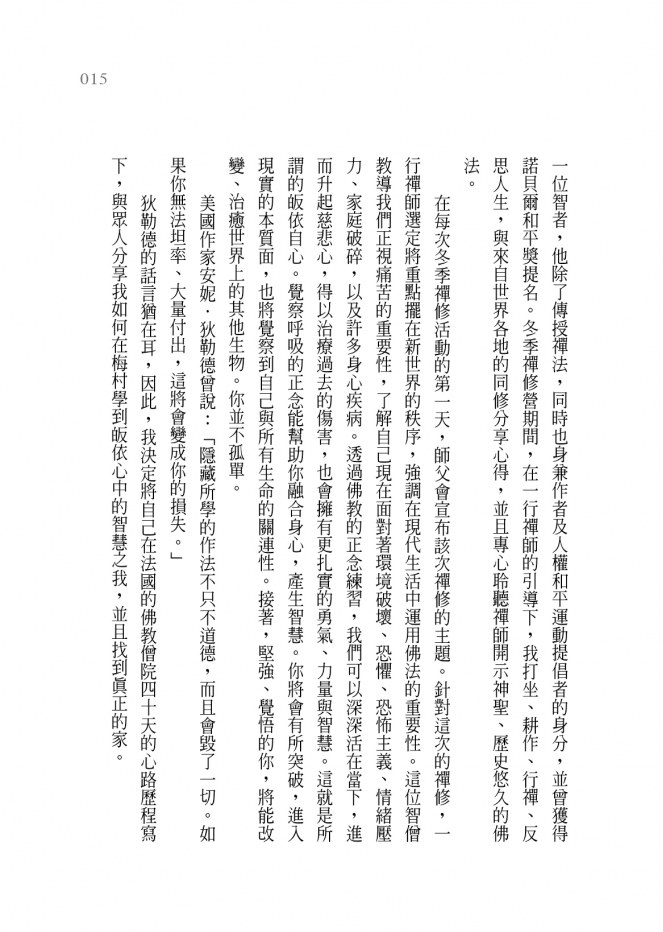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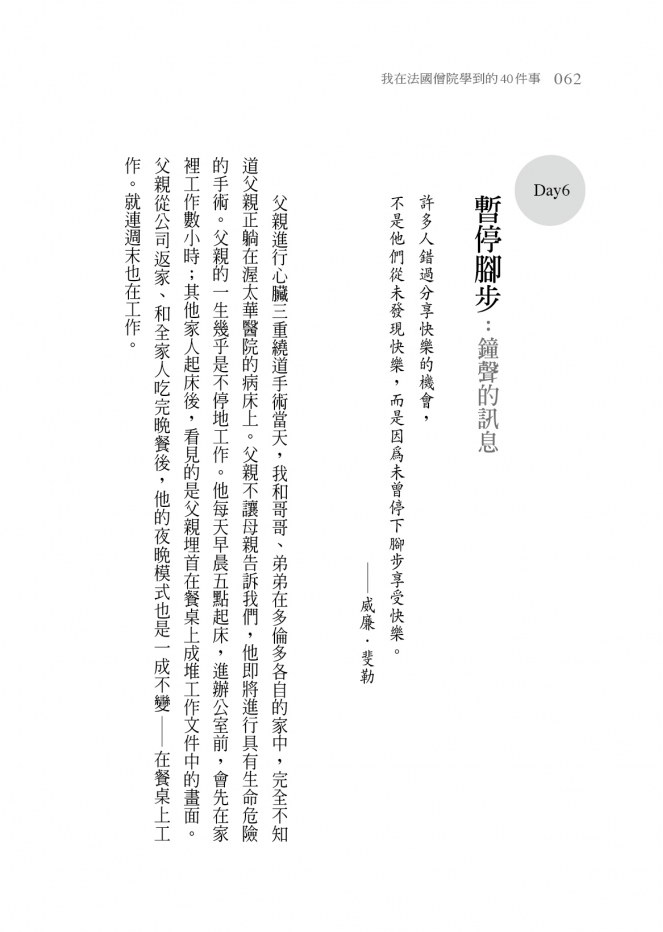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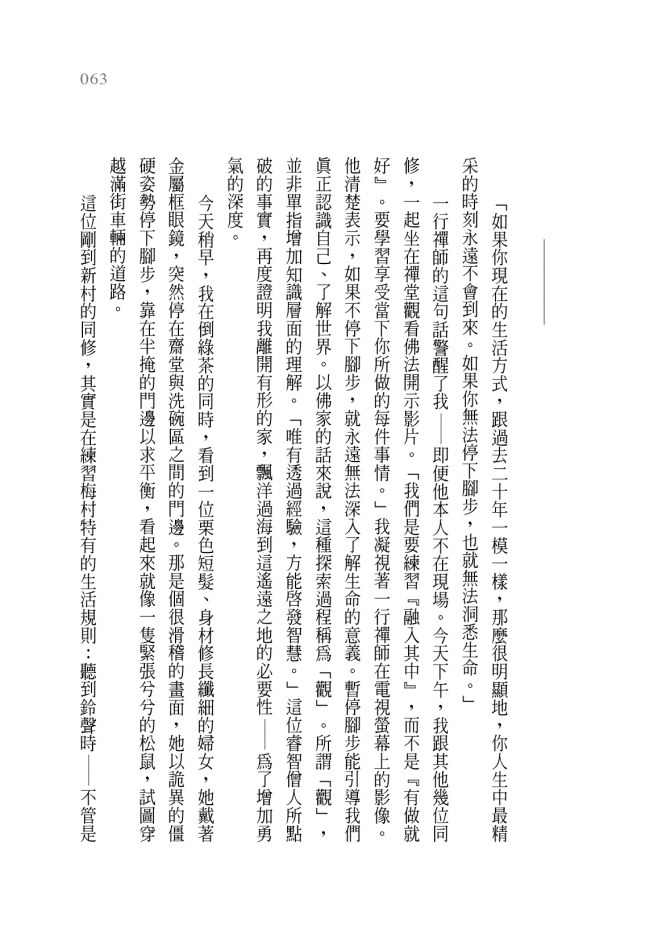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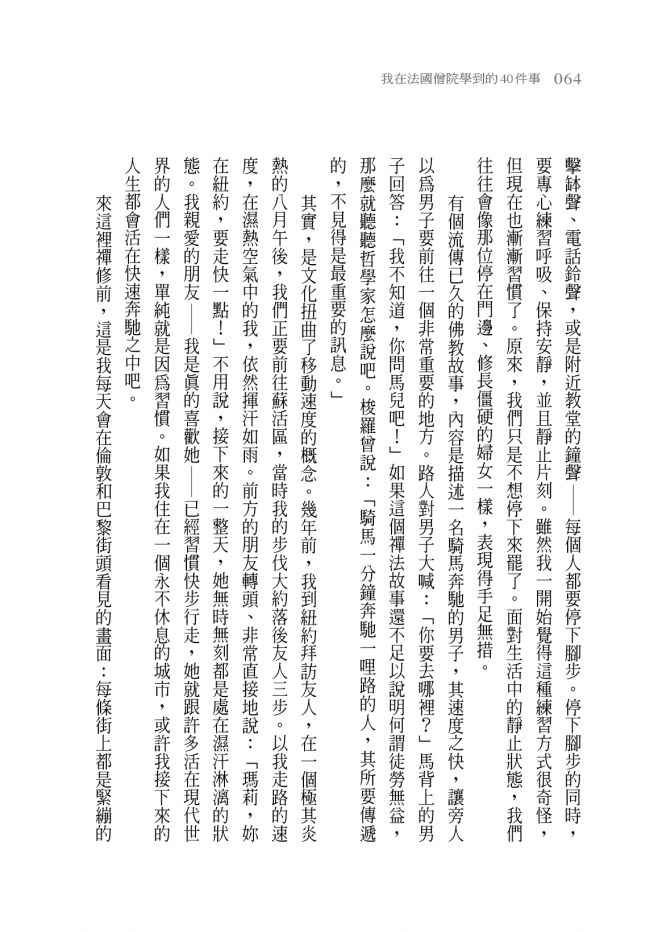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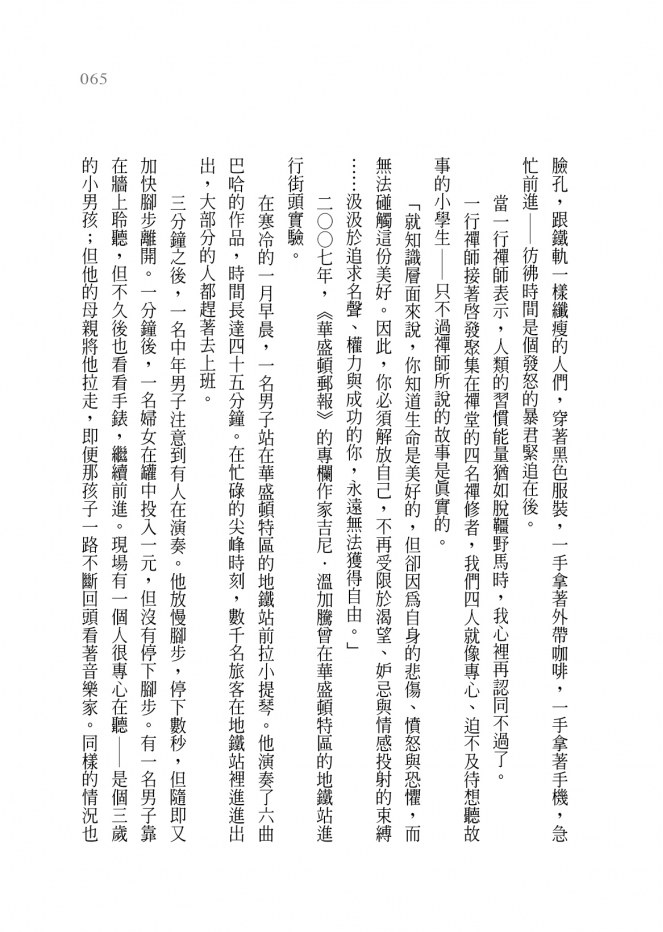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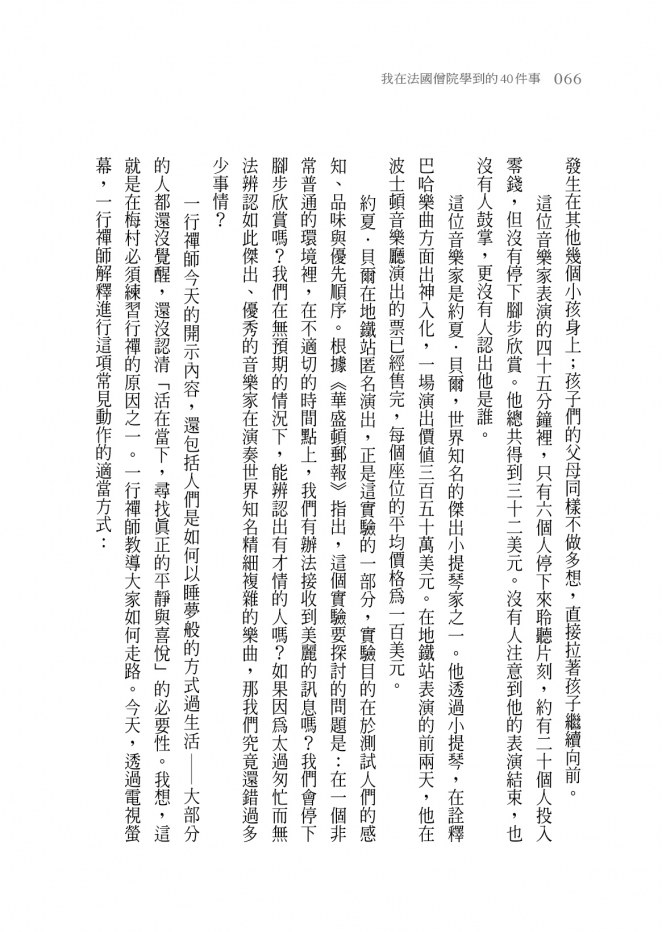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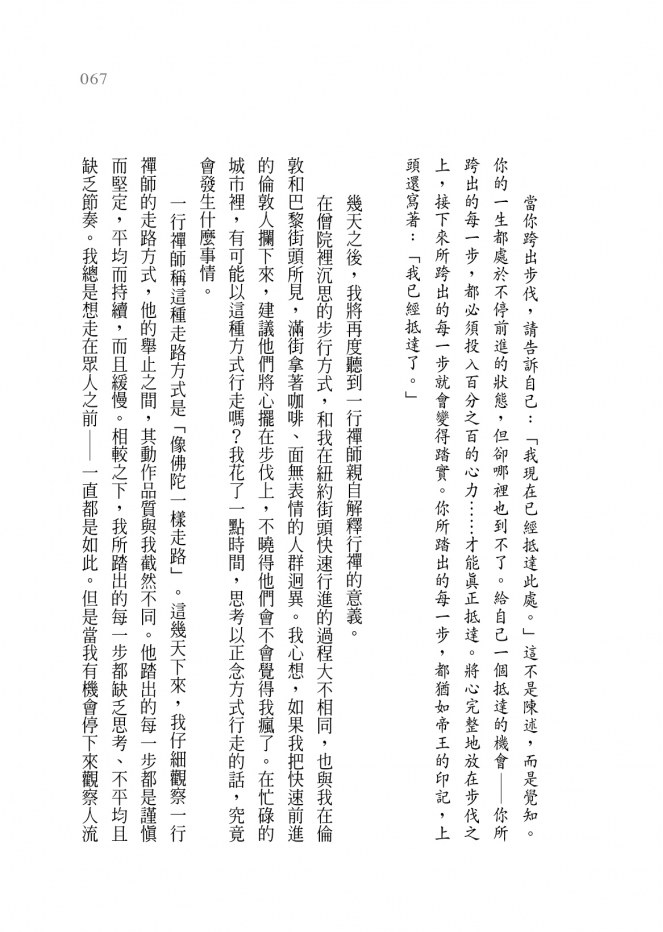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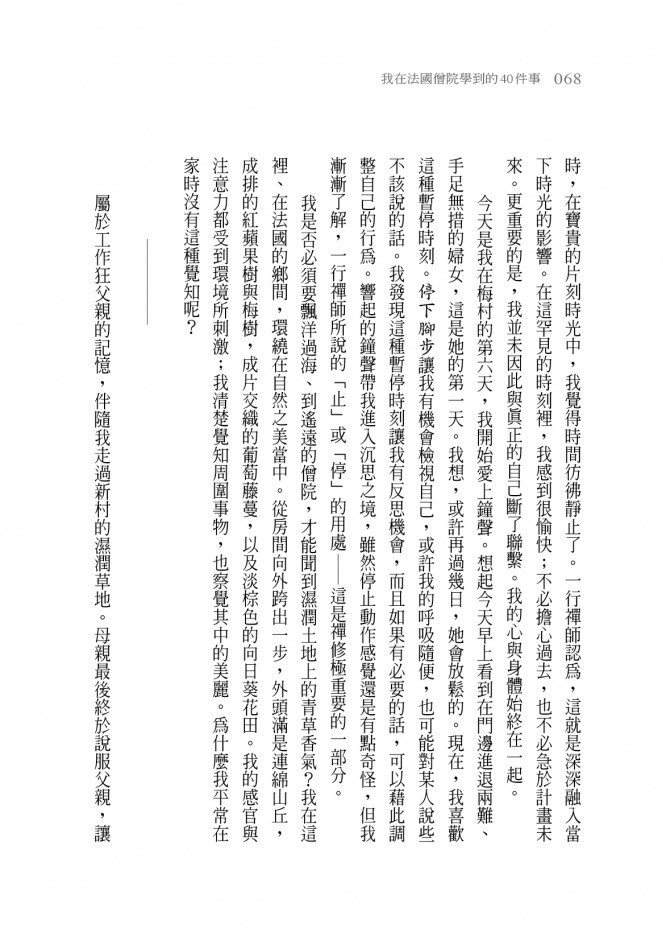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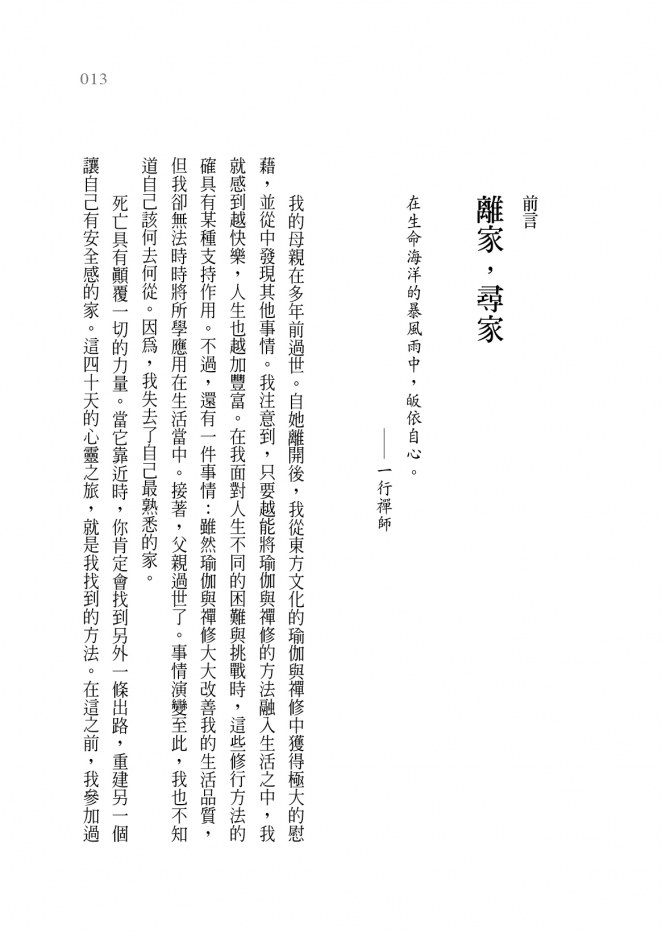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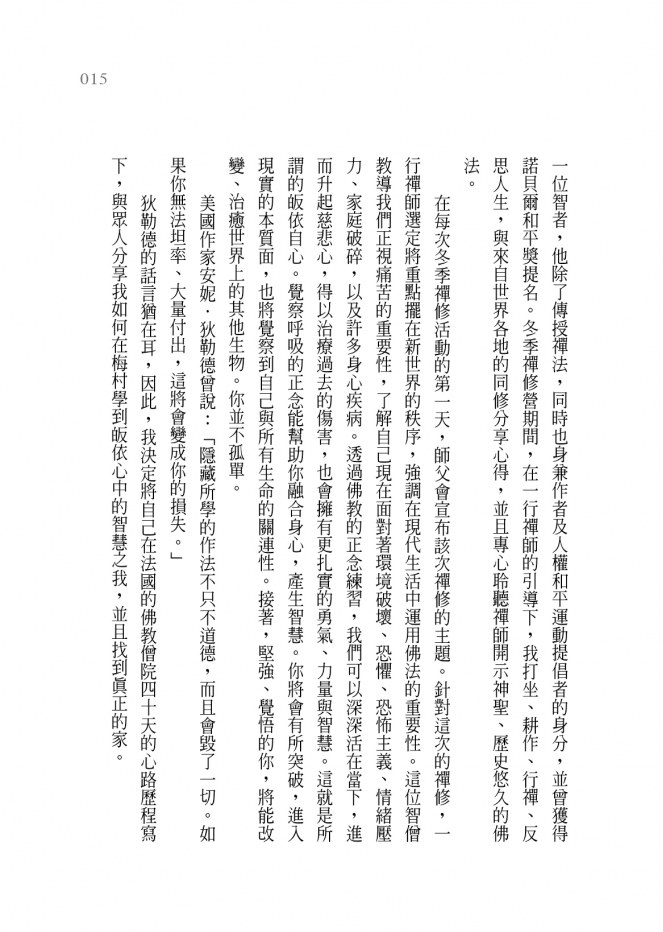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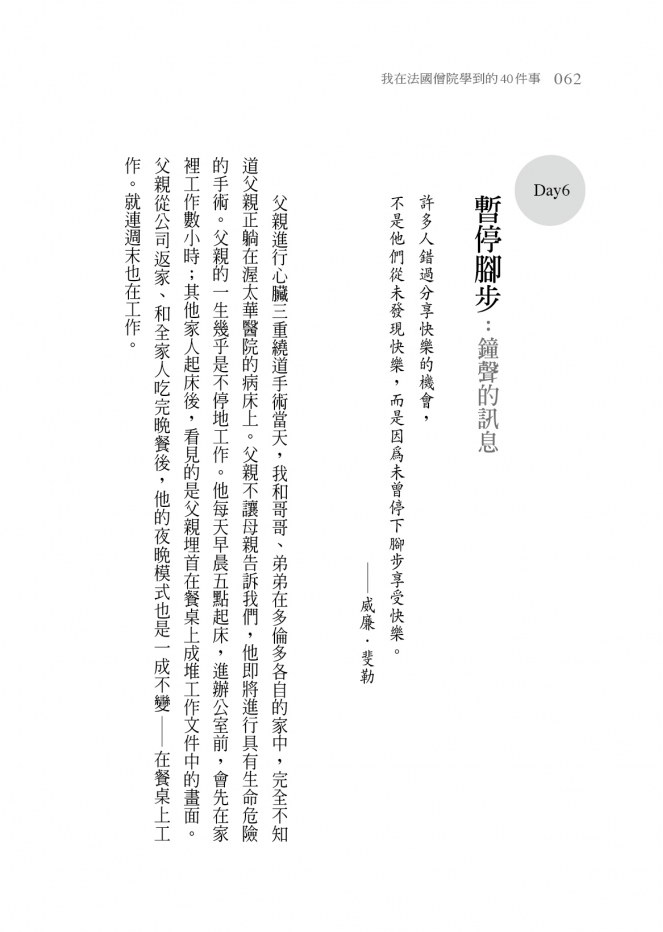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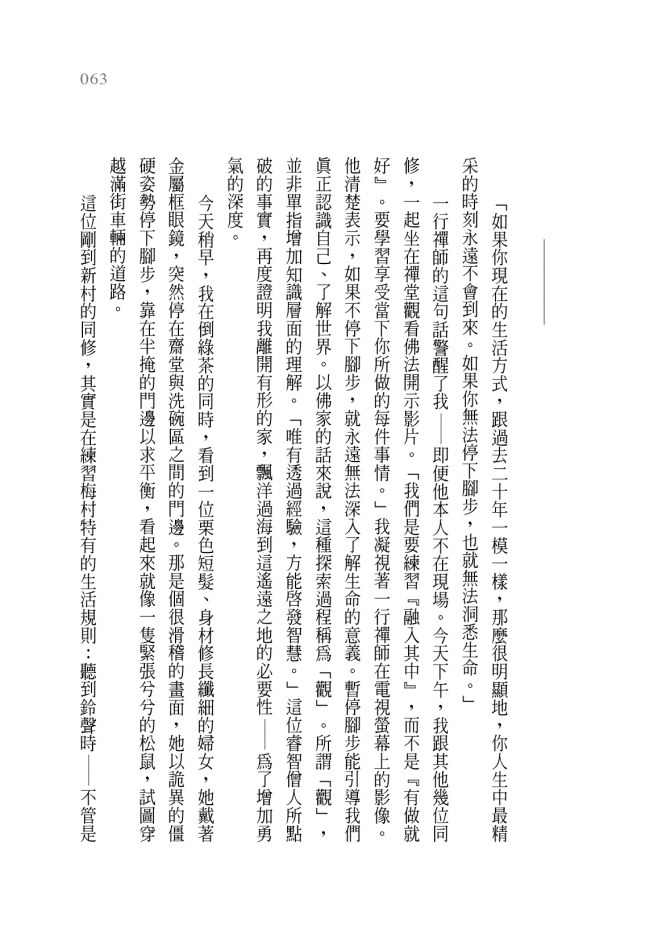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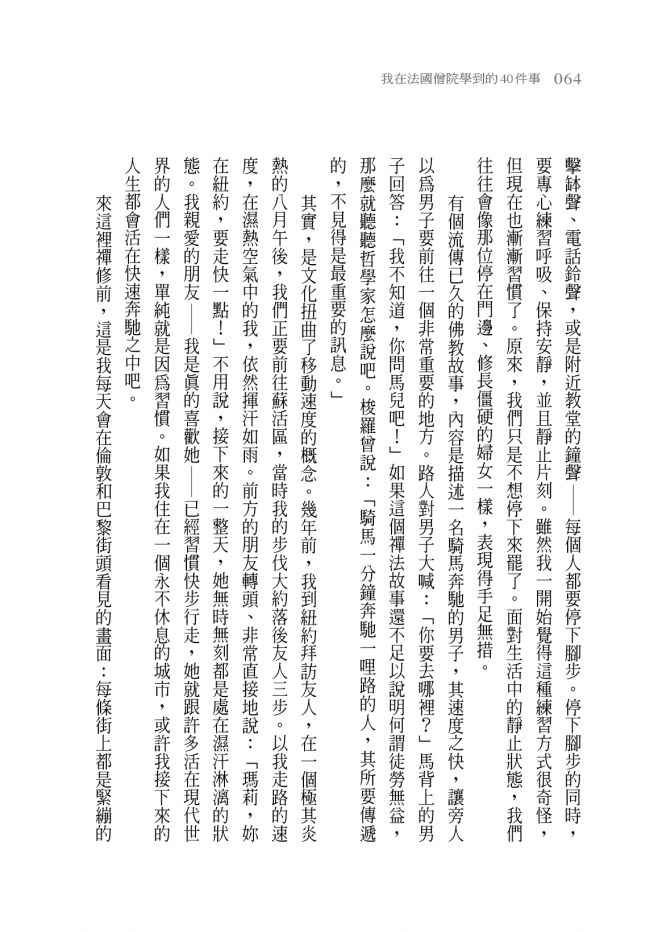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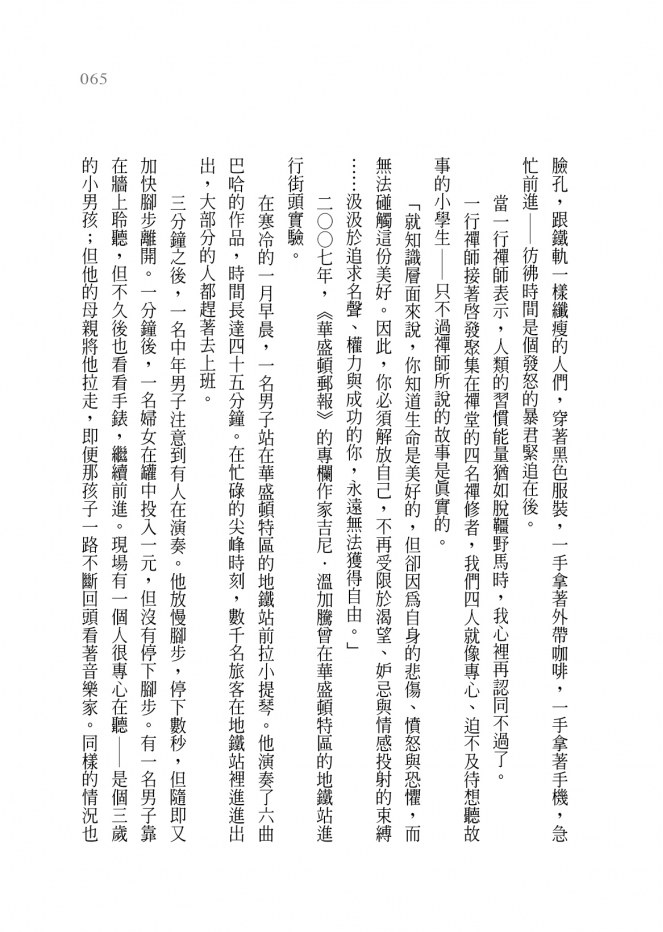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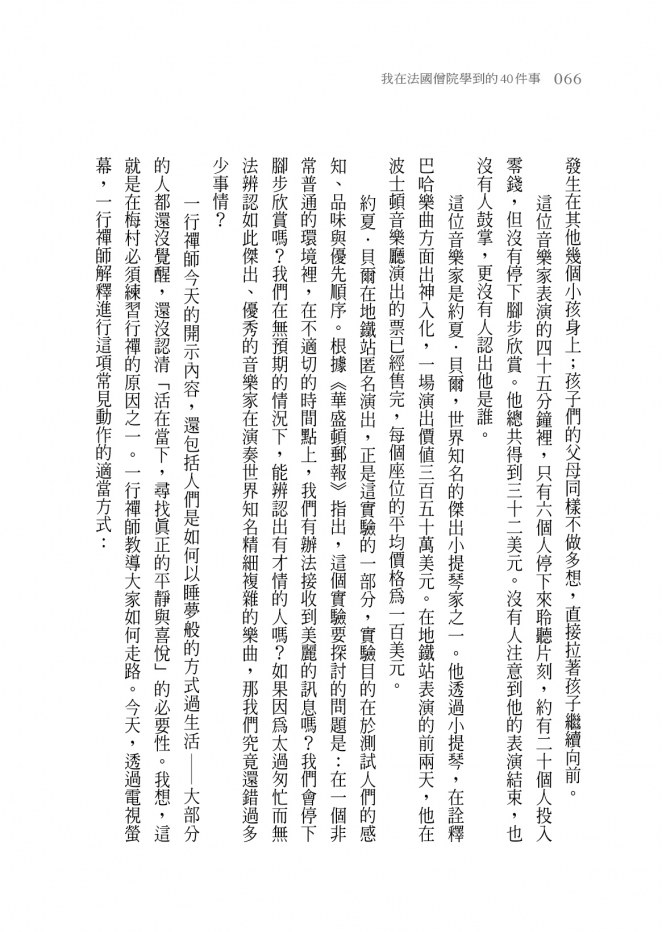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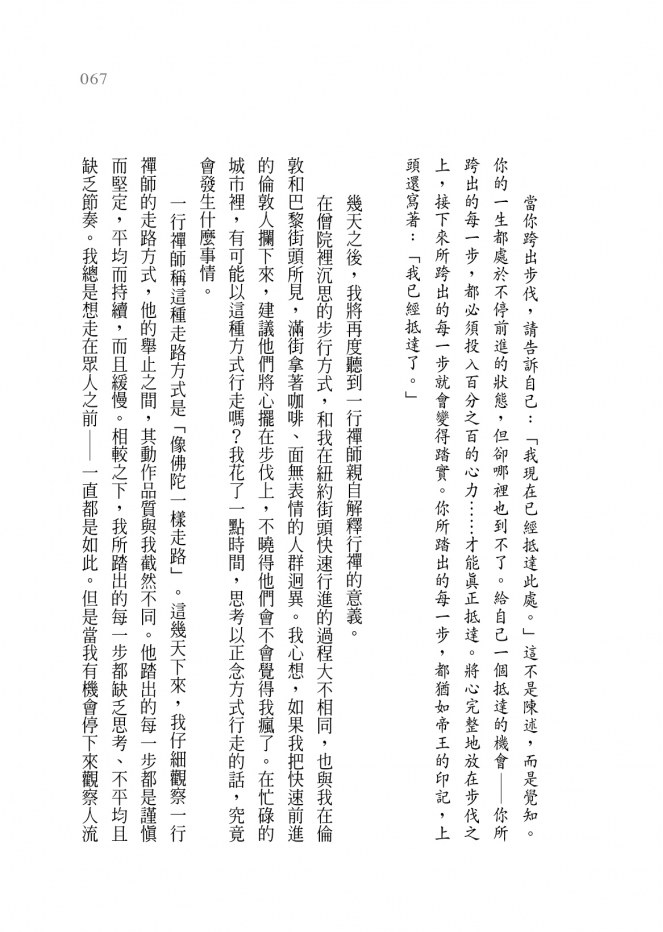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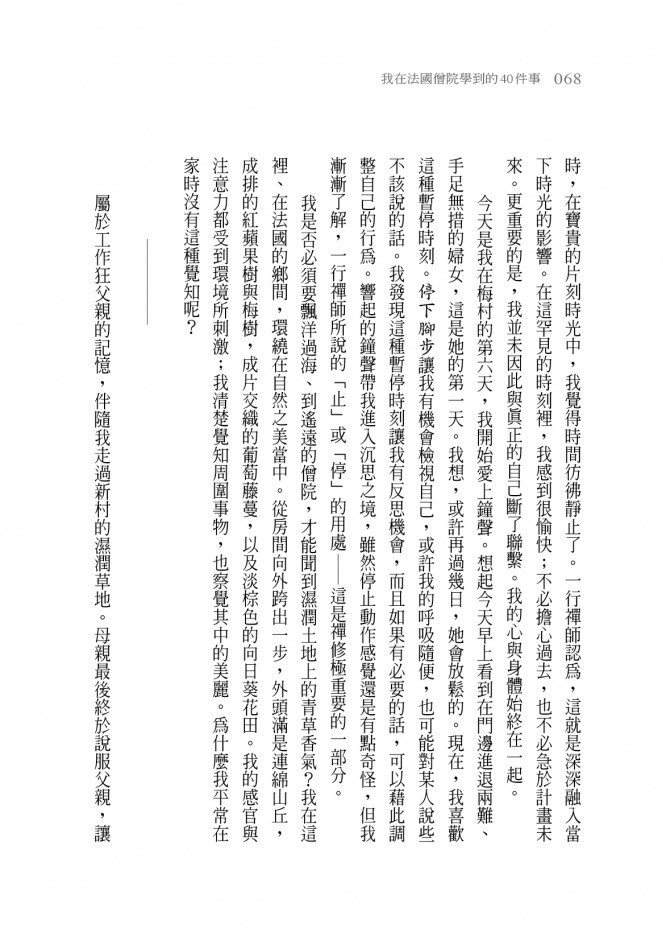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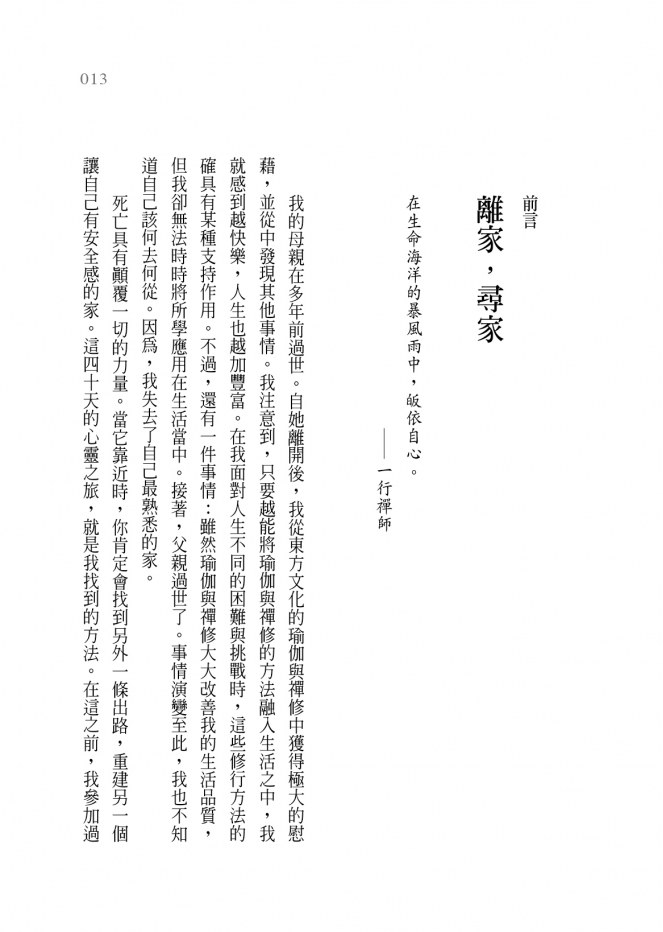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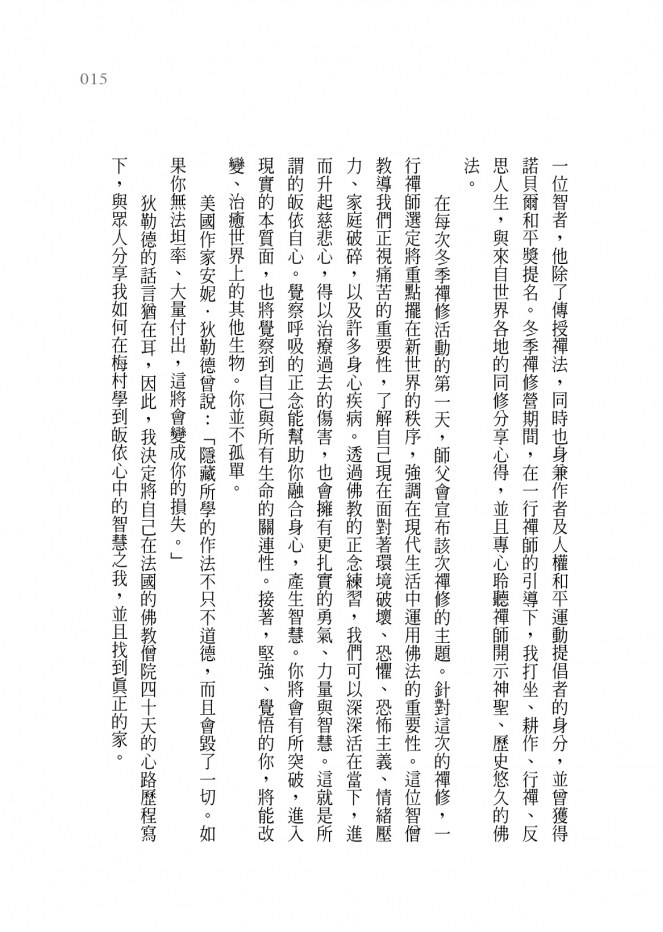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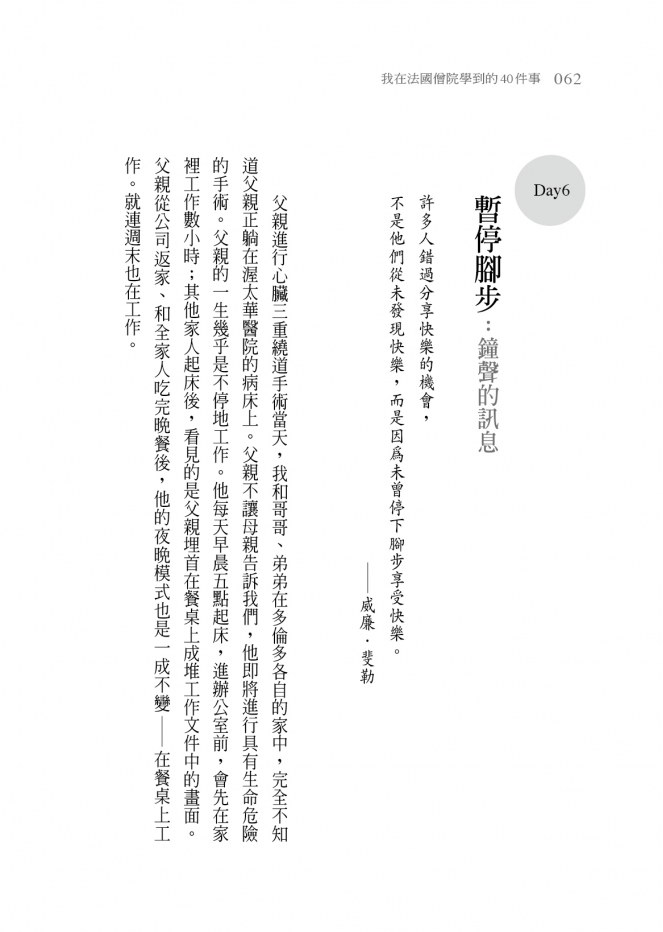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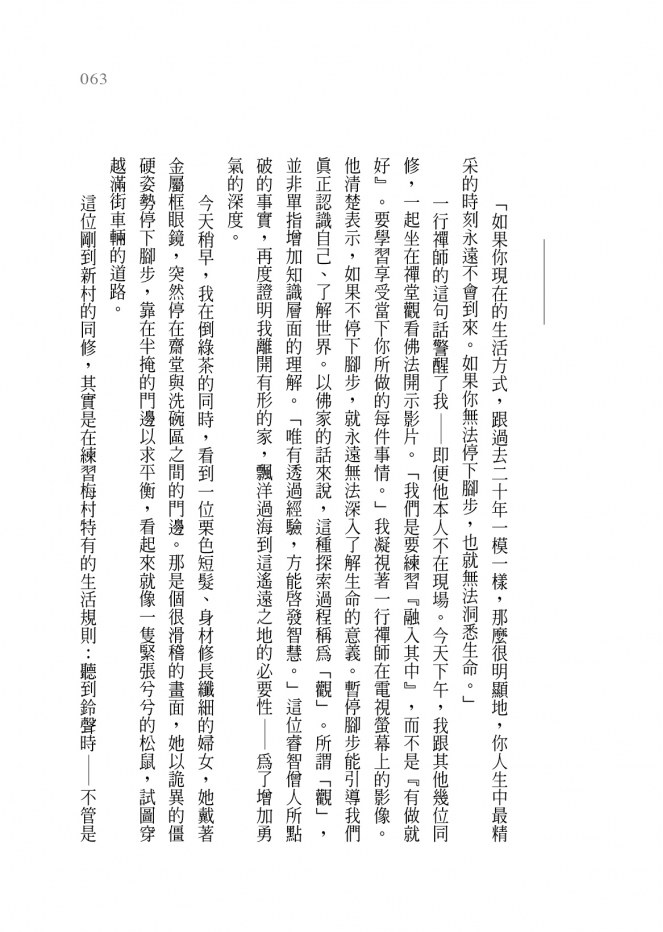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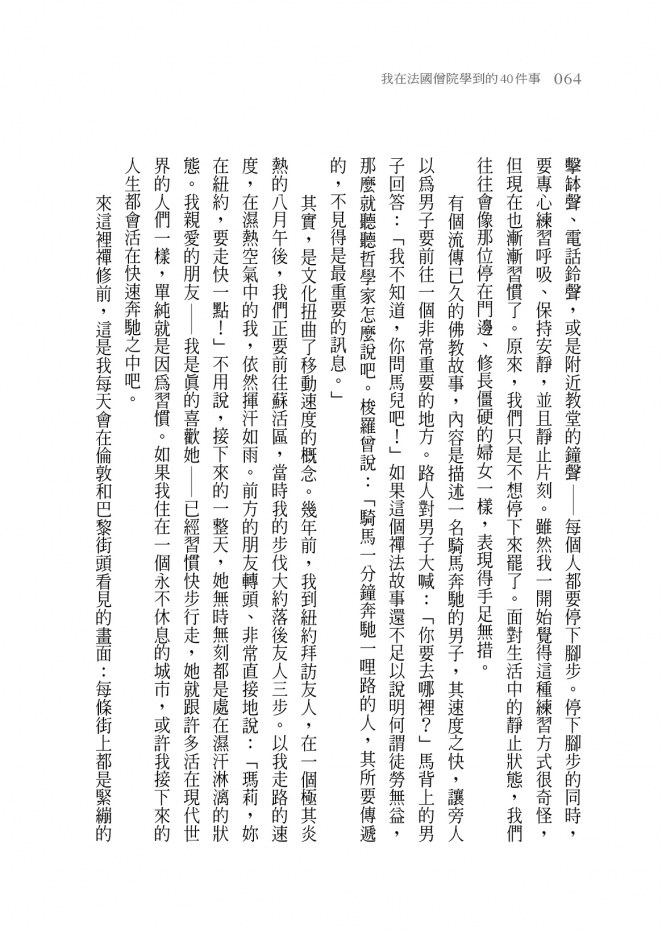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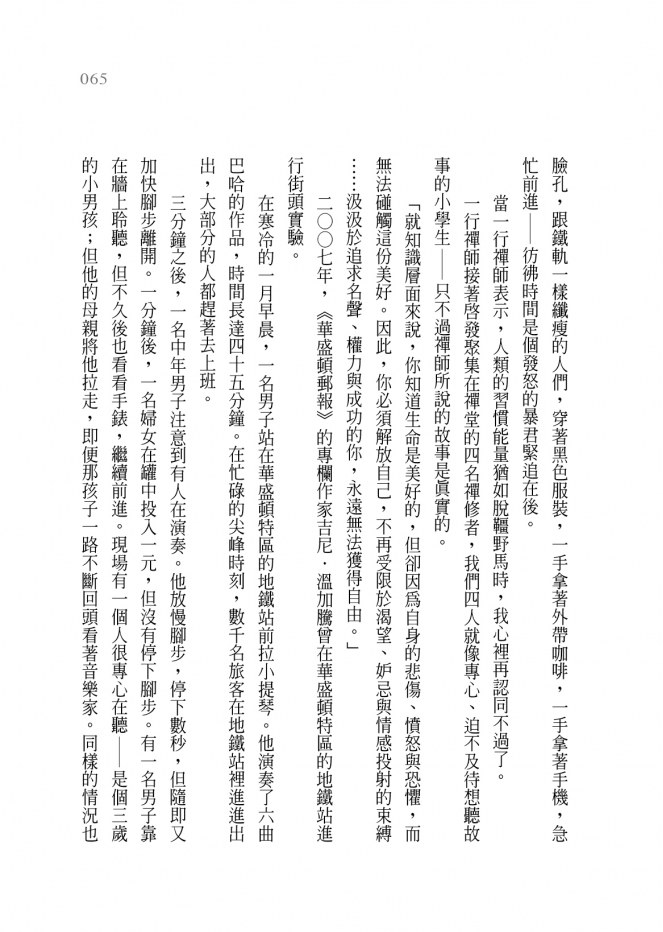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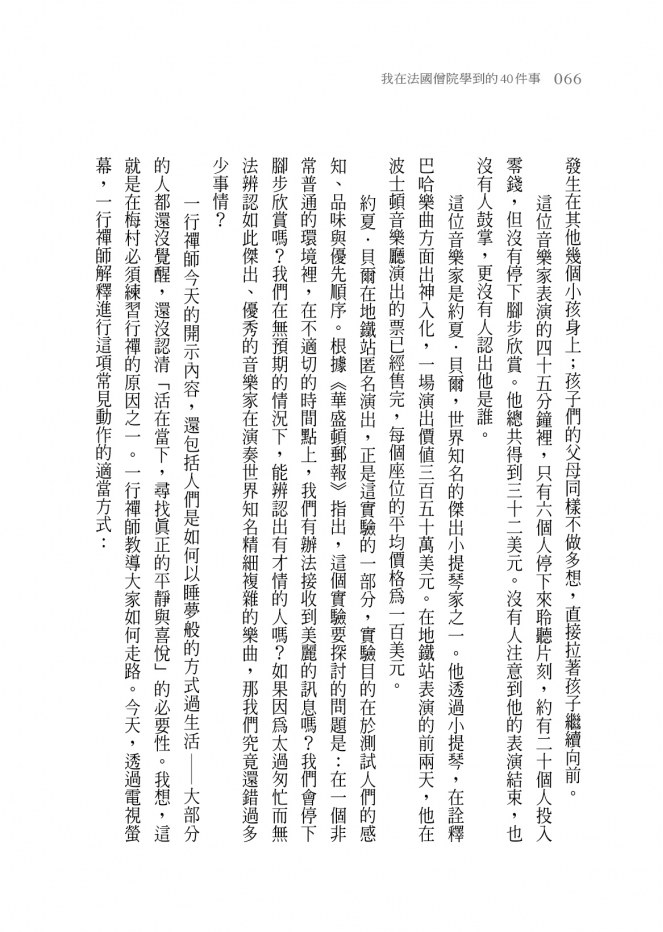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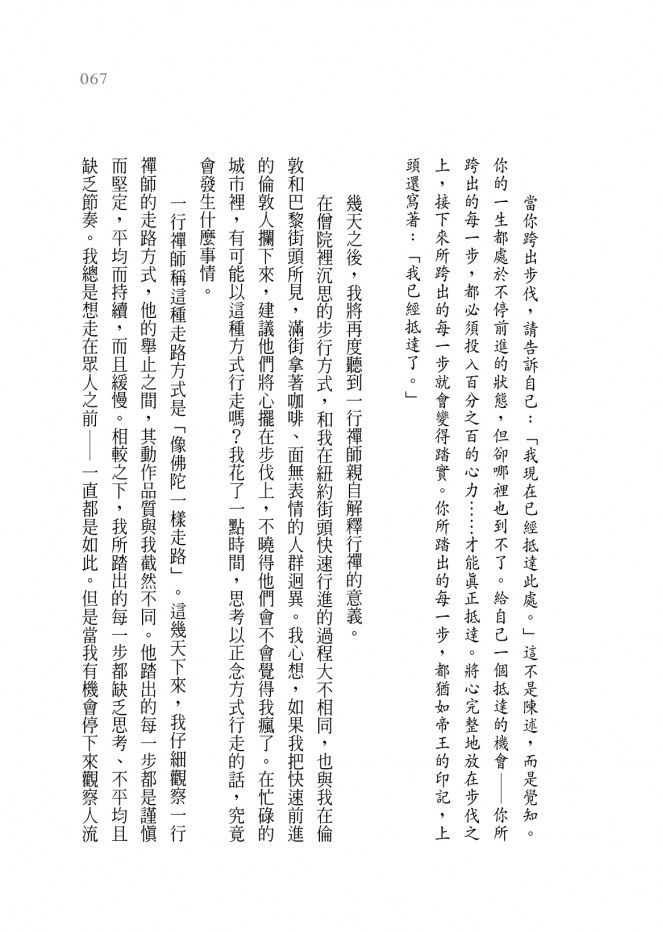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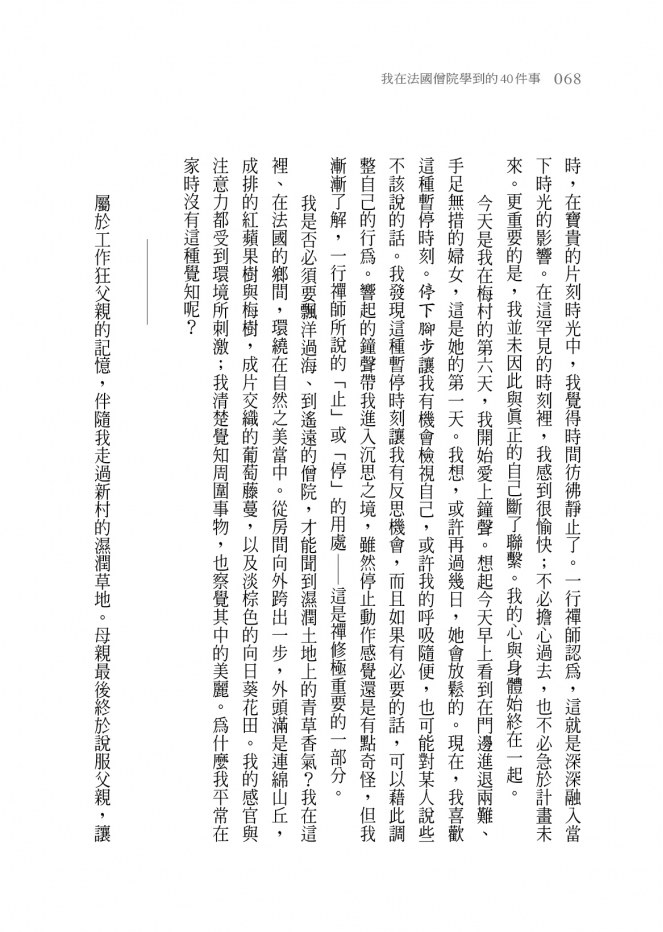

 關於作者
關於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