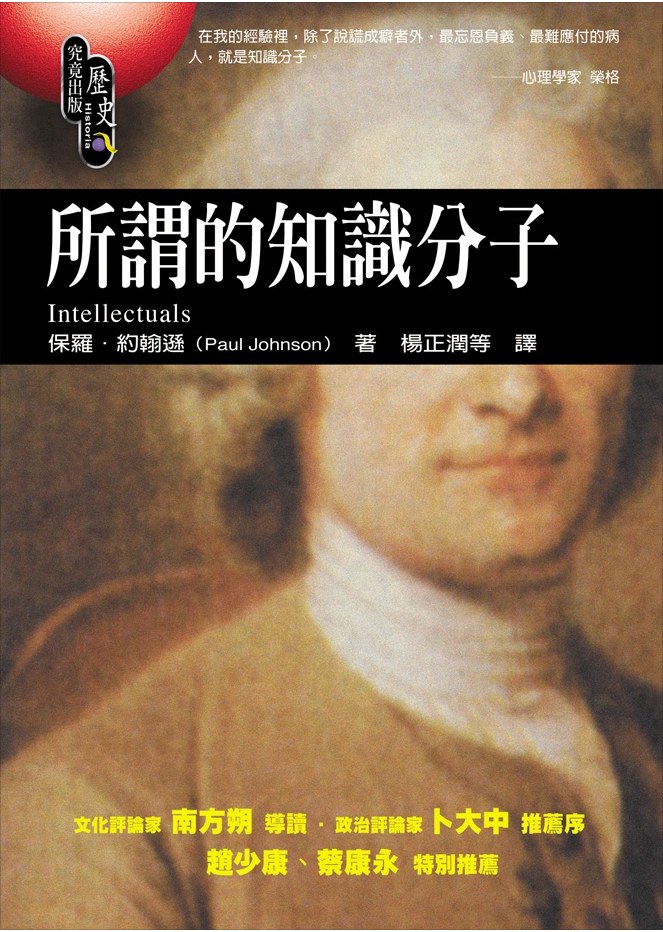
cl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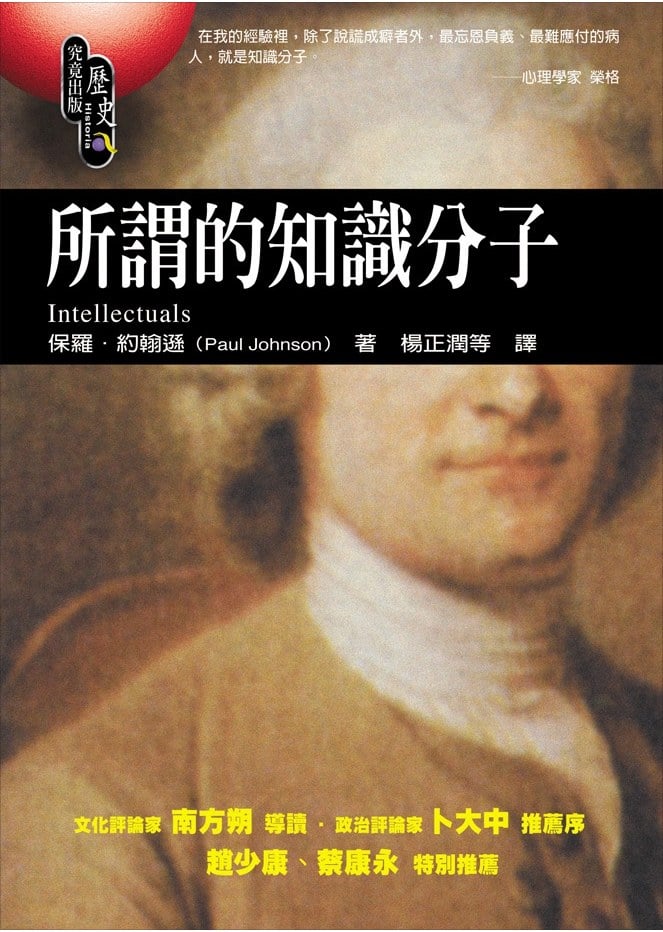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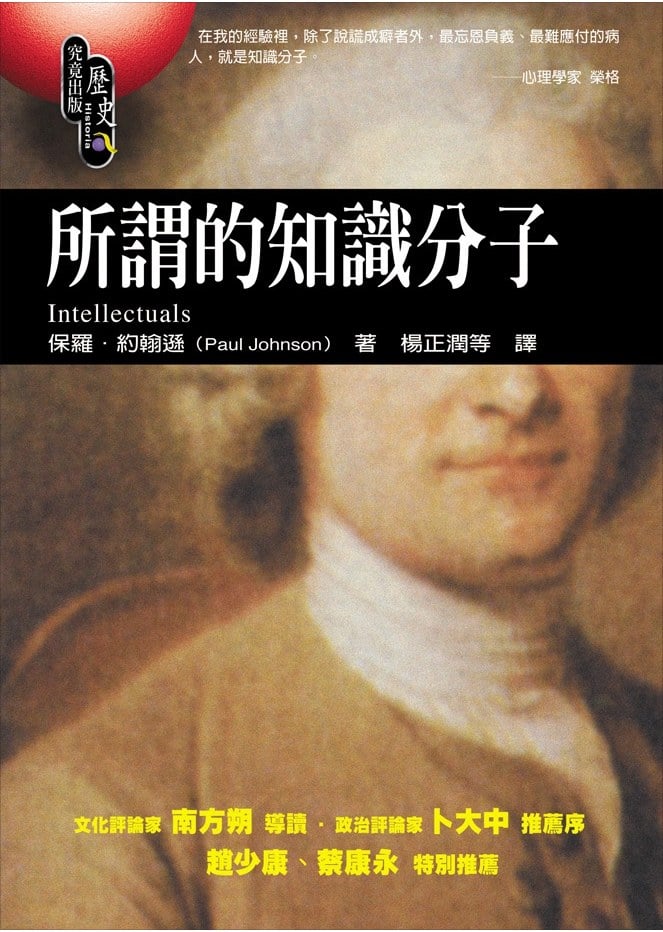
內容簡介
★作家董橋:約翰遜學問文筆都好,立論頭頭是道,讀來不能不驚嘆於他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
史識。
★《紐約郵報》:「任何人拿起這本書就很難再放下。」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 導讀
政論家卜大中 推薦
本書所收錄的人物多是讀者耳熟能詳、影響歷史進程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盧梭、雪萊、馬克思、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沙特等,以及讀者未必熟悉,但也是深具影響力的人物,如英國出版家高蘭茨、美國作家威爾遜、好萊塢劇作家海爾曼等。
作者抽絲剝繭,將這些知識分子放在聚光燈下探照,現出他們的:表裡不一、利慾薰心、欺世盜名、愛慕虛榮;眼花撩亂的兩性關係、錯綜複雜的親友問題。他們總是居高臨下指導別人,私下的生活卻自相矛盾。
盧梭自稱生來是為了愛,其實他最是忘恩負義,對一再襄助他的養母兼情婦華倫夫人袖手旁觀,任她貧病而死;他一面鼓吹兒童教育,一面卻把五個親生孩子送進棄嬰收容所。雪萊的愛像火焰,經常灼傷靠近他的人,他在性關係上的混亂令後人瞠乎其後。托爾斯泰大談博愛,其實從沒愛過具體的人,他自認是上帝的兄長,結果卻把自己的家庭帶入荒野。沙特、羅素、布萊希特、海明威等人,利用名作家的地位,誘惑眾多女性,有的組成「後宮」,有的「追逐每一個穿裙子的人」……。
約翰遜就像是一位「道德偵探」,他清掃歷史的塵埃,重新檢視這些知識分子頭上的光環,並語重心長的說:「任何時候我們必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作者介紹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當代著名的歷史學者,美國《時代雜誌》票選2000年100大人物。英國人,1928年出生,牛津大學麥格德林學院畢業。上尉軍階退伍之後,在巴黎擔任《真相》月刊(Realites)的助理編輯。1955至1970年間任職英國《新政治家》雜誌。他曾為全球最著名的報紙及雜誌寫稿,到過五大洲採訪新聞,替報社及電視專訪過各國總統及總理,以及為大學與企業開班授課。閒暇時,喜歡畫畫及爬山。
著作等身,包括《猶太人史》、《當代》、《英國人民史》等,其中最有名、爭議也最多的就是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
譯者 / 楊正潤
南京大學教授,負責第2、11、12、13章的翻譯與全書審稿(除第3章外)。
施敏、孟冰純、趙育春
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分別譯了第1、6、8章,第7、9、10章及第4、5章。
林志懋
台大哲學系畢業,翻譯第3章。
史識。
★《紐約郵報》:「任何人拿起這本書就很難再放下。」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 導讀
政論家卜大中 推薦
本書所收錄的人物多是讀者耳熟能詳、影響歷史進程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盧梭、雪萊、馬克思、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沙特等,以及讀者未必熟悉,但也是深具影響力的人物,如英國出版家高蘭茨、美國作家威爾遜、好萊塢劇作家海爾曼等。
作者抽絲剝繭,將這些知識分子放在聚光燈下探照,現出他們的:表裡不一、利慾薰心、欺世盜名、愛慕虛榮;眼花撩亂的兩性關係、錯綜複雜的親友問題。他們總是居高臨下指導別人,私下的生活卻自相矛盾。
盧梭自稱生來是為了愛,其實他最是忘恩負義,對一再襄助他的養母兼情婦華倫夫人袖手旁觀,任她貧病而死;他一面鼓吹兒童教育,一面卻把五個親生孩子送進棄嬰收容所。雪萊的愛像火焰,經常灼傷靠近他的人,他在性關係上的混亂令後人瞠乎其後。托爾斯泰大談博愛,其實從沒愛過具體的人,他自認是上帝的兄長,結果卻把自己的家庭帶入荒野。沙特、羅素、布萊希特、海明威等人,利用名作家的地位,誘惑眾多女性,有的組成「後宮」,有的「追逐每一個穿裙子的人」……。
約翰遜就像是一位「道德偵探」,他清掃歷史的塵埃,重新檢視這些知識分子頭上的光環,並語重心長的說:「任何時候我們必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作者介紹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當代著名的歷史學者,美國《時代雜誌》票選2000年100大人物。英國人,1928年出生,牛津大學麥格德林學院畢業。上尉軍階退伍之後,在巴黎擔任《真相》月刊(Realites)的助理編輯。1955至1970年間任職英國《新政治家》雜誌。他曾為全球最著名的報紙及雜誌寫稿,到過五大洲採訪新聞,替報社及電視專訪過各國總統及總理,以及為大學與企業開班授課。閒暇時,喜歡畫畫及爬山。
著作等身,包括《猶太人史》、《當代》、《英國人民史》等,其中最有名、爭議也最多的就是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
譯者 / 楊正潤
南京大學教授,負責第2、11、12、13章的翻譯與全書審稿(除第3章外)。
施敏、孟冰純、趙育春
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分別譯了第1、6、8章,第7、9、10章及第4、5章。
林志懋
台大哲學系畢業,翻譯第3章。
規格
商品編號:T0100011
ISBN:9576077648
頁數:496,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576077648
ISBN:9576077648
頁數:496,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576077648
各界推薦
推薦序:知識分子的道德貧困 卜大中
導讀: 從污名化裡找回利齒 / 南方朔
有些書,如果沒有先看導讀,就最好不要讀下去。對這樣的書,導讀是「批判式閱讀」和「創造式閱讀」的先決條件。
由英國保守派機關刊物《新政治家》主編、知名歷史家保羅‧約翰遜所寫的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即是這樣的一本著作。在他的筆下,曾對現代文明有過巨大貢獻的十餘位傑出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與事功都被完全略而不提,而卻徹底著墨於他們的生活。於是,這些思想人物一個個都成了貪財、愛名、寡情、自私、性關係錯亂的卑瑣角色。在他似真還假、但無疑花了許多功夫搜尋資料的著作裡,「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已遭受到嚴重的「污名化」攻擊。面對這本十分八卦、但也不得不承認非常好看的著作,思慮周密的人就會追究下去;這本著作之立意何在?它的時代背景是什麼?而它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當我們有了這樣的疑問,就已走出了「批判式閱讀」的第一步。
而研究英美近代「反知識分子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人都知道,這本著作並非孤立的出版事件,它乃是一九八○年代後期出現的有關「知識分子」角色論爭裡重要的一環。
眾所周知,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狹義而言,乃以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發生於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為其濫觴。一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為公平正義而與當朝者相抗衡。但就廣義而言,「知識分子」的歷史當然沒有這麼短暫。從啟蒙時代以降,「知識分子」就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分出現。他們以願景勾勒未來,推動時代前行。而在英國,過去兩百年裡,「進步知識分子」和「保守知識分子」間即一直處於一種長期的緊張狀態中。由於英國「進步知識分子」始終以工黨和工黨的周邊組織為基地,進步與保守間的攻伐,使得「保守知識分子」在戰術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傳統,那就是以犬儒式的態度,對「知識分子」的生活行為展開抨擊。這種情況在第二次大戰後始終未曾間斷。
而據兩名英國學者詹寧斯(jeremy jennings)和坎普│威奇(anthony kemp-welch)所編的近著《政治中的知識分子:從德雷福斯事件到盧布迪》一書所述,這種情況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出了一個引爆點,那就是從七○年代後期開始掌權的保守黨柴契爾夫人,由於「進步知識分子」不滿她的種種作為,一九八五年牛津大學在教授們投票後,決定取消原擬頒授給她的榮譽學位。這是重大的導火線,加上其他問題,親保守黨的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和牛津教授,以及保守派刊物如《旁觀者週刊》和《週日電訊報》、《新政治家》等,遂開始了攻擊。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於一九八八年出版,即是這場論爭的產物。除了這本著作外,牛津的保守教授凱瑞(john carey)於一九九二年出版《知識分子與群眾》,對蕭伯納、威爾斯(h. g. wells)、維琴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勞倫斯(d. h. lawrence)、福斯特(e. m. foster)等展開抨擊,也是保守派這方的力作。一九九三年英國親自由派的bbc,特邀後殖民先驅薩依德(edward said)至倫敦,做了一系列專談「知識分子」角色的演講,即是「進步知識分子」這邊的主要回應。由這樣的脈絡,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為何要如此寫,意義就很清楚了。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英美一體。從一九八○年代中期引發的這場論爭,勢不可免地延燒到美國,加上一九八九年起東歐及蘇聯瓦解,對整個西方的知識界造成極大的衝擊,這些因素的相互激盪,遂使得這場有關「知識分子」角色的論爭一直在持續中,縱使到了現在,也仍然未曾停止。後續的發展甚至已超越了狹義的「知識分子」角色這個課題,而更深入到檢討當代思想趨勢這個新的方向。
在當代有關「知識分子」角色這場論爭裡,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的雅可比(russell jacoby)乃是不容忽視的總論型人物,他先後有過《最後的知識分子們》及《烏托邦的終結》等著作。在這些著作裡他指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教育體系擴張,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分子」,即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分子」開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識分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為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務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業的情況下,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這種情況就像是法國著名「反叛知識分子」德勃艾(regis debray)所說的,從一九六○年代後,「知識分子」已越來越和「名流」同義。而這種情況隨著東歐及蘇聯的瓦解,已變得更為嚴重。因為就保守派而言,東歐及蘇聯的瓦解,所肯定的乃是資本主義現狀的優越性。既然優越,任何對它所做的批判遂彷彿都變得失去了正當性。九○年代之後,西方主要「知識分子」皆大幅退卻,有些重要思想人物如英國的柯亨(g. a. cohen)在哈佛所出的近著《如果你是平等主義,你的如此富裕由何而來?》裡,甚至無力地將不平等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宗教情懷。這都充分地顯示出,由於東歐及蘇聯瓦解,「社會主義」已被污名化,在「進步知識分子」這一邊,已出現嚴重的「政治枯竭」(political exhaustion)。在當代重量級人物裡,著名的羅蒂(richard rorty)更明白自承:「我不認為我們能像祖父輩那一代一樣,替人的尊嚴、自由和平等未來問題有所感覺。我們沒有能力從現實走到理論上可能的未來。」在這個「政治枯竭」也不再有願景的時代,已有人指出一個嚴酷的問題,那就是如果現在出現越戰一樣的戰爭,是否還會和以前一樣出現反戰運動?
這也就是薩依德所謂的:當代「知識分子」已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齒」(defanged)。而除了不再有願景、怯於批判,使得「知識分子」淪為體制裡「製造同意」的合謀者之外,當代新的思想在這樣的變化裡,也淪為蓋爾納(ernest gellner)所謂的「誇張式的瑣碎」(conspicuous triviality),或休斯(h. stuart hughes)所謂的「矯揉做作的反叛」(sophisticated rebel)。當代思想已不再談論實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等方面之不公不義,但卻對虛擬的文化、語言文本等異常耽溺,思想問題則變成了文化或文本問題,而願景與行動則毫無生存的空間。當代思想只在瑣碎地方賣弄小聰明,但對世界上日增的強凌弱、富暴窮等現象無動於衷,難怪雅可比教授要感慨地說,這是一種「零售清醒,批發瘋狂」了!
人類的歷史現在已走到了一個新的「默然苟存的時代」(era of acquiescence)的階段。「知識分子」已在時代的變化裡被收編、被污名化、被自我放棄。他們看得到文本的細節,看不見滔滔濁世裡越來越多的野蠻與不平。法國當代保守派「知識分子」領袖列維(bernard-henry ly)諷刺的寫下如此墓誌銘:「知識分子、雄性名詞、社會及文化範疇,在德雷福斯事件時興起於巴黎,二十世紀末死於巴黎。」
二十世紀初,德國思想家曼海姆(karl manheim)主張「知識分子」應獨立飄浮,替世界代言。他說過,只有獨立知識分子的存在,始可能勾勒願景,讓人類歷史走向更好的未來,而不只是隨著盲目的力量而浮沉。因此,「知識分子」是有用的。過去,「知識分子」可能太過專擅,因而會造成極端的烏托邦;但今日,卻走到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冷漠、無能,甚或瀕臨絕種。這兩個極端都不對,已必須重找新的良心基礎、新的願景、新的分析方法,以及新的實踐動力。而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乃是要找回它業已失去的批判利齒。
這篇導讀,希望對讀者諸君閱讀本書能有幫助。
導讀: 從污名化裡找回利齒 / 南方朔
有些書,如果沒有先看導讀,就最好不要讀下去。對這樣的書,導讀是「批判式閱讀」和「創造式閱讀」的先決條件。
由英國保守派機關刊物《新政治家》主編、知名歷史家保羅‧約翰遜所寫的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即是這樣的一本著作。在他的筆下,曾對現代文明有過巨大貢獻的十餘位傑出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與事功都被完全略而不提,而卻徹底著墨於他們的生活。於是,這些思想人物一個個都成了貪財、愛名、寡情、自私、性關係錯亂的卑瑣角色。在他似真還假、但無疑花了許多功夫搜尋資料的著作裡,「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已遭受到嚴重的「污名化」攻擊。面對這本十分八卦、但也不得不承認非常好看的著作,思慮周密的人就會追究下去;這本著作之立意何在?它的時代背景是什麼?而它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當我們有了這樣的疑問,就已走出了「批判式閱讀」的第一步。
而研究英美近代「反知識分子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人都知道,這本著作並非孤立的出版事件,它乃是一九八○年代後期出現的有關「知識分子」角色論爭裡重要的一環。
眾所周知,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狹義而言,乃以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發生於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為其濫觴。一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為公平正義而與當朝者相抗衡。但就廣義而言,「知識分子」的歷史當然沒有這麼短暫。從啟蒙時代以降,「知識分子」就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分出現。他們以願景勾勒未來,推動時代前行。而在英國,過去兩百年裡,「進步知識分子」和「保守知識分子」間即一直處於一種長期的緊張狀態中。由於英國「進步知識分子」始終以工黨和工黨的周邊組織為基地,進步與保守間的攻伐,使得「保守知識分子」在戰術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傳統,那就是以犬儒式的態度,對「知識分子」的生活行為展開抨擊。這種情況在第二次大戰後始終未曾間斷。
而據兩名英國學者詹寧斯(jeremy jennings)和坎普│威奇(anthony kemp-welch)所編的近著《政治中的知識分子:從德雷福斯事件到盧布迪》一書所述,這種情況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出了一個引爆點,那就是從七○年代後期開始掌權的保守黨柴契爾夫人,由於「進步知識分子」不滿她的種種作為,一九八五年牛津大學在教授們投票後,決定取消原擬頒授給她的榮譽學位。這是重大的導火線,加上其他問題,親保守黨的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和牛津教授,以及保守派刊物如《旁觀者週刊》和《週日電訊報》、《新政治家》等,遂開始了攻擊。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於一九八八年出版,即是這場論爭的產物。除了這本著作外,牛津的保守教授凱瑞(john carey)於一九九二年出版《知識分子與群眾》,對蕭伯納、威爾斯(h. g. wells)、維琴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勞倫斯(d. h. lawrence)、福斯特(e. m. foster)等展開抨擊,也是保守派這方的力作。一九九三年英國親自由派的bbc,特邀後殖民先驅薩依德(edward said)至倫敦,做了一系列專談「知識分子」角色的演講,即是「進步知識分子」這邊的主要回應。由這樣的脈絡,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為何要如此寫,意義就很清楚了。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英美一體。從一九八○年代中期引發的這場論爭,勢不可免地延燒到美國,加上一九八九年起東歐及蘇聯瓦解,對整個西方的知識界造成極大的衝擊,這些因素的相互激盪,遂使得這場有關「知識分子」角色的論爭一直在持續中,縱使到了現在,也仍然未曾停止。後續的發展甚至已超越了狹義的「知識分子」角色這個課題,而更深入到檢討當代思想趨勢這個新的方向。
在當代有關「知識分子」角色這場論爭裡,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的雅可比(russell jacoby)乃是不容忽視的總論型人物,他先後有過《最後的知識分子們》及《烏托邦的終結》等著作。在這些著作裡他指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教育體系擴張,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分子」,即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分子」開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識分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為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務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業的情況下,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這種情況就像是法國著名「反叛知識分子」德勃艾(regis debray)所說的,從一九六○年代後,「知識分子」已越來越和「名流」同義。而這種情況隨著東歐及蘇聯的瓦解,已變得更為嚴重。因為就保守派而言,東歐及蘇聯的瓦解,所肯定的乃是資本主義現狀的優越性。既然優越,任何對它所做的批判遂彷彿都變得失去了正當性。九○年代之後,西方主要「知識分子」皆大幅退卻,有些重要思想人物如英國的柯亨(g. a. cohen)在哈佛所出的近著《如果你是平等主義,你的如此富裕由何而來?》裡,甚至無力地將不平等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宗教情懷。這都充分地顯示出,由於東歐及蘇聯瓦解,「社會主義」已被污名化,在「進步知識分子」這一邊,已出現嚴重的「政治枯竭」(political exhaustion)。在當代重量級人物裡,著名的羅蒂(richard rorty)更明白自承:「我不認為我們能像祖父輩那一代一樣,替人的尊嚴、自由和平等未來問題有所感覺。我們沒有能力從現實走到理論上可能的未來。」在這個「政治枯竭」也不再有願景的時代,已有人指出一個嚴酷的問題,那就是如果現在出現越戰一樣的戰爭,是否還會和以前一樣出現反戰運動?
這也就是薩依德所謂的:當代「知識分子」已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齒」(defanged)。而除了不再有願景、怯於批判,使得「知識分子」淪為體制裡「製造同意」的合謀者之外,當代新的思想在這樣的變化裡,也淪為蓋爾納(ernest gellner)所謂的「誇張式的瑣碎」(conspicuous triviality),或休斯(h. stuart hughes)所謂的「矯揉做作的反叛」(sophisticated rebel)。當代思想已不再談論實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等方面之不公不義,但卻對虛擬的文化、語言文本等異常耽溺,思想問題則變成了文化或文本問題,而願景與行動則毫無生存的空間。當代思想只在瑣碎地方賣弄小聰明,但對世界上日增的強凌弱、富暴窮等現象無動於衷,難怪雅可比教授要感慨地說,這是一種「零售清醒,批發瘋狂」了!
人類的歷史現在已走到了一個新的「默然苟存的時代」(era of acquiescence)的階段。「知識分子」已在時代的變化裡被收編、被污名化、被自我放棄。他們看得到文本的細節,看不見滔滔濁世裡越來越多的野蠻與不平。法國當代保守派「知識分子」領袖列維(bernard-henry ly)諷刺的寫下如此墓誌銘:「知識分子、雄性名詞、社會及文化範疇,在德雷福斯事件時興起於巴黎,二十世紀末死於巴黎。」
二十世紀初,德國思想家曼海姆(karl manheim)主張「知識分子」應獨立飄浮,替世界代言。他說過,只有獨立知識分子的存在,始可能勾勒願景,讓人類歷史走向更好的未來,而不只是隨著盲目的力量而浮沉。因此,「知識分子」是有用的。過去,「知識分子」可能太過專擅,因而會造成極端的烏托邦;但今日,卻走到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冷漠、無能,甚或瀕臨絕種。這兩個極端都不對,已必須重找新的良心基礎、新的願景、新的分析方法,以及新的實踐動力。而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乃是要找回它業已失去的批判利齒。
這篇導讀,希望對讀者諸君閱讀本書能有幫助。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