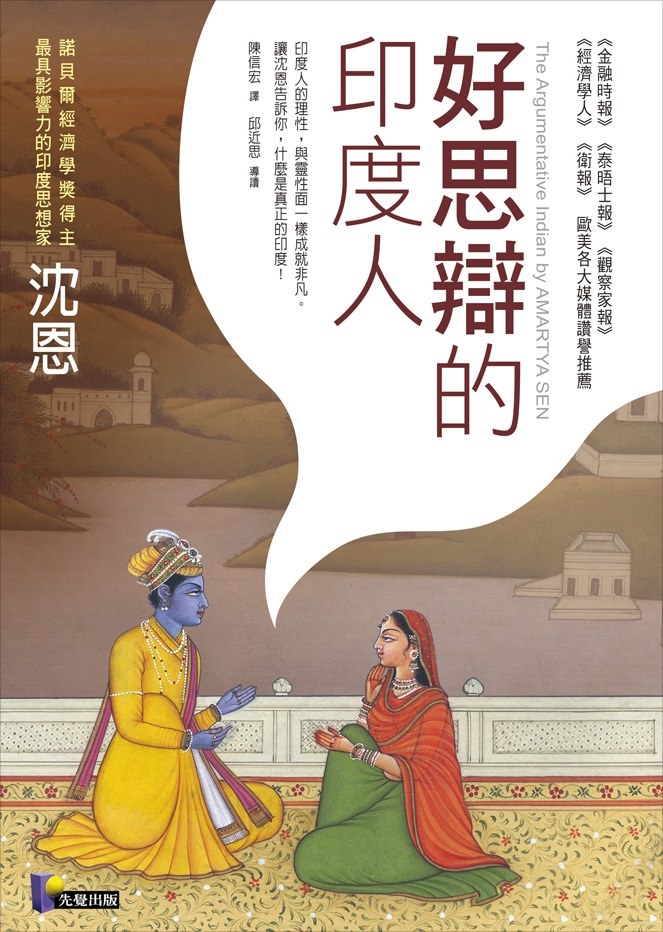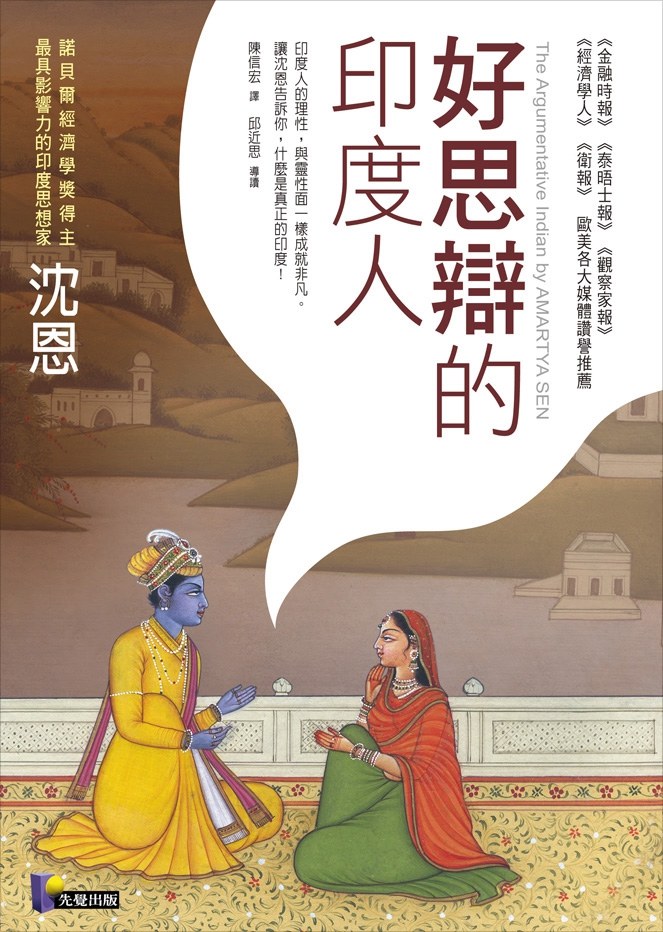第一章
好辯的印度人
我們印度人對於喋喋不休的現象一點都不陌生,每個人都具有長篇大論的能力。印度國防部長克瑞施納.梅農(Krishna Menon)在聯合國創下連續九個小時沒有中斷的演說紀錄,已是五十年前的事情(當時他是印度代表團團長),但至今仍然無人可及。其他印度人在能言善道的面向上也有各種過人表現。我們確實是個愛說話的民族。
這不是新近才出現的習慣。古老的梵文史詩《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雖然常被人比擬為《伊里亞德》與《奧德賽》,但樸實的荷馬所寫出來的作品,長度和印度史詩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單是《摩訶婆羅多》就比《伊里亞德》和《奧德賽》加總起來還要長七倍。《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確實都是偉大的史詩作品。每次回想初次接觸這兩部史詩的情形,我就滿懷欣喜。當時的我正在躁動不安的年輕時期,到處尋求知識的啟發和感官的娛樂,結果這兩部作品深深充實了我的人生。這兩部史詩都講述一個又一個故事,全部環繞著主要的中心情節,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對話、難題,以及各種不同觀點。其中也有許多激烈的爭辯,提出各種論證和反駁的論點。
對話與各種論點的重要性
這些論證通常頗為貼近現實。舉例而言,著名的〈薄伽梵歌〉是《摩訶婆羅多》當中的一個小章節,其中敘述了兩種道德立場的互相拉扯——一方面是奎師那強調的個人義務,另一方面則是阿周那主張的避免不良後果(並且促成良好的結果)。這場辯論發生於《摩訶婆羅多》情節中最重要的大戰前夕。這場大戰的一方是正直公義的皇室家族潘達閥,另一方則是作惡多端的篡奪者庫拉閥。潘達閥無人能敵的戰士阿周那看著兩軍備戰,從而對他們所作所為的正確性提出了深沉的質疑。阿周那指出,人是否應該只關注自己擁護正義的責任,而對戰爭必然造成的苦難和屠殺視若無睹,即便自己的親人可能因此受害也在所不惜?天神下凡的奎師那(也是阿周那的戰車駕駛)與他爭論,提出印度哲學中一再反覆出現的行動原則,認為善盡責任是人的優先要務。奎師那堅決認為,不論阿周那對後果的評估如何,都有義務上戰場打仗。這是一場正義之戰,阿周那身為潘達閥這一方所仰賴的戰士與將軍,對自己的責任絕對不能有所動搖,不論後果如何。
奎師那遵崇義務的論點贏得了這場爭論,至少就宗教觀點而言是如此。奎師那與阿周那對話的這篇〈薄伽梵歌〉,後來成為印度教哲學當中深具神學重要性的文獻,尤其把重點放在「消除」阿周那的疑慮。奎師那的道德立場後來獲得世界各地許多哲學與文學評論家的推崇,例如伊塞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與艾略特(T. S. Eliot)。而且,伊塞伍德還把〈薄伽梵歌〉翻譯成英文。讚賞〈薄伽梵歌〉,尤其是認同奎師那的論點,在歐洲文化中已是長久存在的一種現象。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在十九世紀初就曾經這麼讚揚這篇作品:「在所有已知的語言當中最美麗的詩歌,可能也是唯一真正哲學性的詩歌。」在《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其中一首詩裡,艾略特則是以告誡的形式概述奎師那的觀點:「毋需考慮行動的後果。/勇往直前。」他解釋道:「不求結果順遂,/只需勇往直前,各位旅人。」
不過,正如許多正反兩方都理由充足的辯論,《摩訶婆羅多》也依序詳細呈現了這兩種相反的論點。在史詩末尾,經歷了戰亂殺伐的土地(主要是印度河—恆河平原)那幅荒寒悲涼的景象,甚至也可視為是印證了阿周那的深沉疑慮。不論〈薄伽梵歌〉的「訊息」是什麼,阿周那的論點畢竟沒有徹底遭到駁斥。除了「勇往直前」之外,我們還是有相當的理由追求「結果順遂」。
歐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率領美國團隊,研發出終極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後來他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看到首次核爆產生的可怕力量,也不禁引用奎師那的話(「我已成為死神,世界的毀滅者」)。一如當初奎師那告誡阿周那善盡戰士的義務,為正義的目標而戰,因此身為物理學家的歐本海默也大可為自己研發原子彈的行為找出正當的理由。畢竟,他所在的那一方很顯然是正義的一方。他後來以批判的眼光審視了自己的行為,說道:「你一旦看到技術上非常吸引人的東西,就會立即著手去做。等到在技術上獲得成功之後,才會討論該對研發的成果怎麼辦。」儘管我們有「勇往直前」的衝動,但也還是有理由省思阿周那的疑慮:殺害這麼多人怎麼可能帶來善果?我又為什麼應該為自己這一方尋求勝利、統治權,或者快樂?
這些論點的重要性在當代世界絲毫沒有稍減。善盡個人義務的論點自然相當具有說服力,但儘管認為自己的義務合乎正義,我們又怎麼能夠對這麼做所可能帶來的後果完全視而不見?我們省思世界上各種顯而易見的問題(包括恐怖主義、戰爭、暴力、傳染病、動盪不安、嚴重的貧窮狀況),或者印度本身關注的議題(諸如經濟發展、核武對峙、區域和平),除了考慮奎師那善盡個人義務的論點之外,也必須把阿周那的後果分析納入考量。〈薄伽梵歌〉的「單一訊息」需要由《摩訶婆羅多》較為廣博的論辯智慧加以補充,因為〈薄伽梵歌〉只不過是整部史詩的一小部分而已。
本篇論文和後續的其他論文,都將檢視印度論辯傳統當中許多爭論的影響範圍和重要性。我們不但該注意在爭辯中獲勝(或是表面上獲勝)的論點,也必須注意其他留下記載的觀點。在爭辯中落敗的論點如果沒有就此消失,必然有其不容忽視之處。
性別、種姓以及意見表達
不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則是論辯傳統是否只存在於印度的一部分人口當中——也許只存在於男性菁英階層裡。當然,辯論的參與本來就不可能平均遍及社會所有成員,但印度在性別、階級、種姓、社群等方面也確實向來具有深切的不平等現象(社群的不平等現象會在稍後談到)。如果弱勢群體無法參與爭論,那麼論辯傳統對社會的重要性就將大幅縮減。不過,這種問題其實非常複雜,絕非短短一句話可以概括。
我從性別開始談起。在印度,男性向來在辯論中握有主導權,這點無庸置疑。但儘管如此,女性在政治領導與知識追求上的參與也不是完全不值一顧。這點在今天明顯可見,尤其是在政治上。的確,印度許多主要政黨(不論全國性還是地區性的政黨)領導人都是女性,而且這種現象自從過去以來就是如此。而且,在國大黨領導的國家獨立運動當中,也有許多女性擔任重要職務,比俄國和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女性人數加總起來還多。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則是印度國大黨在一九二五年就選出了首位女性黨魁奈都(Sarojini Naidu),比英國早了五十年(柴契爾夫人在一九七五年當選保守黨主席),後來又在一九三三年選出第二位女性黨魁內麗.森古普塔(Nellie Sengupta)。
不論時間早晚,這些發展畢竟都是近代的事情。那麼遙遠的過往呢?印度女性在爭辯與討論當中的傳統角色確實不像男性那麼突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想必也都是如此)。不過,要是因此就認為女性在印度過往的歷史上從來不曾取得重要的發聲地位,可就大錯特錯了。即便追溯到印度古代,有些最著名的對話還是有女性參與,其中最尖銳的問題也經常來自女性。這種現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奧義書——這些辯證論文約寫於公元前第八世紀,經常被人視為印度哲學的基礎。
舉例而言,《布瑞哈得—阿冉亞卡奧義書》裡提到著名的「論爭」,由祭皮衣仙這位出色的學者暨老師面對一群專家的提問。其中一位名叫賈姬的女學者提出的問題最為尖銳,而且她加入這場論爭的時候也沒有特別羞怯:「可敬的婆羅門,如果你們許可,我只要問他兩個問題。他如果能夠回答這兩個問題,那麼你們在闡釋神的本質這項議題上就絕對不可能打敗他。」
賈姬雖然是學者,不是軍事領袖(不像另一名女性英雄占西女王那樣,在十九世紀中葉和「叛黨」一同英勇反抗英國統治——英國歷史作家弗雷澤稱她為偉大的「戰士女王」),但她使用的意象卻充滿了軍事色彩:「祭皮衣仙,我有兩個問題要問你。就像毘提訶或迦尸【今天的貝拿勒斯】的統治者那樣的英雄後代,自己拉上弓繩,抄起兩根羽箭,昂然迎向敵人;我也帶著兩個問題來挑戰你。」不過,祭皮衣仙的答案倒是讓賈姬頗為滿意(我無力評斷這段對話的神學價值,所以不在此評論他們問答的實質內容)。賈姬大方肯定了對方的回答,但仍然沒有過度的謙讓:「可敬的婆羅門,你們如果服了他之後還能全身而退,就算相當了不起了。在闡釋神的本質上,你們絕對沒有人能夠勝過他。」
值得注意的是,祭皮衣仙曾經和妻子彌裏討論財富對人生的各種問題和困境能夠帶來什麼幫助,尤其是財富做得到與做不到的事情有哪些,結果彌裏提出了一個深具重要性的動機問題。她納悶道,如果「充滿財富的整個世界」都屬於她一人所有,是否能夠藉此達成長生不老的境界。「不可能,」祭皮衣仙回答道,「你的人生會過得和富人一樣,但財富絕不可能帶來長生不老。」彌裏接著又問:「我該怎麼處置那些不能讓我長生不老的東西?」
後來印度宗教哲學經常引述彌裏的這句問話,用來說明人類困境的本質以及物質世界的局限。不過,這段對話還有另外一個更引人關注的面向,則是人生中各種事物之間的關係與距離,例如收入是否等於成就?我們能夠買到哪些商品,是否表示我們就一定享受得到這些商品的用途?擁有經濟財富,是否就能夠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經濟繁榮雖然有助於我們達成自己重視的目標,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不一定非常緊密。彌裏的世俗擔憂很可能具有宗教上的重要性(印度宗教評論家在數百年來已經多次討論過這一點),但也絕對適用於世俗事務上。我們如果重視自己享有長壽美好人生的自由,關注的焦點就必須直接放在生死上,而不只是財富和經濟繁榮。
在史詩與古典故事或者歷史記載當中,女性人物提出的論點不一定都合乎一般認知裡溫柔和善的女性形象。在《摩訶婆羅多》裡,正直的國王尤迪斯提拉不願發動血腥的戰爭,許多人於是勸他以「適度的憤怒」對抗有意篡奪王位的惡徒。其中最能言善道的,就是王后朵帕娣。
在詩人巴拉維於六世紀寫成的《野人和阿周那》這部作品裡,朵帕娣這麼勸她的丈夫:
讓女人勸諫像你這樣的男人
幾乎算得上是侮辱。
然而,深切的擔憂卻迫使我
超越婦女行為的界限,
逼得我開口。
你父祖輩的國王都像戰神因陀羅一樣勇敢,
長久以來統治世界不曾間斷。
但現在你卻打算
親手拋除這一切,
就像發情的大象
用象鼻扯掉頸上的花環……
你如果不願採取英勇的行動,
認為逆來順受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那麼就請丟棄象徵王權的弓,
把頭髮編結成辮,
待在這裡向聖火獻祭吧!
由此不難看出朵帕娣重視的是義務還是後果。後來阿周那與奎師那的辯論也是針對同一起事件,只不過當時尤迪斯提拉已決定出戰(而不是像他妻子以毫不掩飾的嘲諷口吻所說的那樣,拋棄王位過起隱士的生活)。
必須了解的是,印度的論辯傳統不但不是由男性獨占,而且參與辯論的雙方通常也不受階級與種姓的限制。實際上,質疑正統宗教信仰的聲音多半都來自於社會弱勢族群。當然,所謂的弱勢只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婆羅門制度在古印度時代遭到其他族群爭論的時候(包括商人與工匠),提出異議的人士通常都頗為富有。但必須注意的是,在婆羅門居於主宰地位的社會裡,那些人仍然確實是相當弱勢的一群。這點也許特別有助於理解促成佛教在印度迅速傳播的階級因素。削弱教士種姓的優越性,在耆那教與佛教這類以造反姿態起家的宗教運動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中帶有一種「反階級」的特點,不但反映在這些宗教標舉的人類平等訊息裡,也可見於它們對地位崇高者的優越性所提出的質疑。佛教與耆那教的早期文獻都有許多表達抗議與反抗的內容。
反對種姓區隔的運動在印度歷史上多次出現,成效有好有壞,但都懂得善用深具說服力的論證質疑傳統信念。這類反駁論點有許多都記錄於史詩當中,可見即便在種姓制度初期,反對階級體系的聲音也不曾缺席。我們不知道記載中提出這些質疑的人士,究竟是這些論點真正的發想者,抑或只是表達出早已存在的疑問。不過,這些反對不平等的論點在史詩及其他古典文獻裡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還是能夠讓我們更全面了解論辯傳統的影響範圍。所謂「印度教觀點」的僵化解釋絕對不可能帶來如此深刻的理解。
舉例而言,在《摩訶婆羅多》裡,波利怙向巴拉多迦表示,種姓制度乃是以人的生理特徵加以區別,主要是膚色的差別,結果巴拉多迦不但指出每個種姓當中都存在相當程度的膚色差異(「如果不同膚色代表不同種姓,那麼所有種姓必然都是混合種姓」),也提出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所有人顯然都同樣受到慾望、憤怒、恐懼、悲傷、擔憂、飢餓、勞動所影響,那又為什麼會有種姓的差異呢?」另一部古代文獻《往世書》,則是提出親系的質疑:「四大種姓的成員既然都是神的子女,那麼他們就應該都屬於同一個種姓。人類只有一個父親,同一個父親的子女不可能分屬不同種姓。」這類質疑沒有獲得勝利,但在記載辯論的古代文獻裡還是存留了下來。
許久之後,在十五世紀的「中世紀神祕詩人」傳統中,有不少人都受到印度教虔信派與穆斯林蘇菲派的平等主義所影響。他們廣泛反對社會壁壘的言行,也就明確突顯出打破種姓與階級區隔的論點對後世的影響有多麼深遠。這些詩人有許多都來自於低微的經濟與社會背景,因此他們質疑社會劃分與不同宗教之間的隔閡,反映的也就是一種企圖破除這些人為限制的深切嘗試。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異端主張的倡議者有許多都來自於勞工階級:其中最偉大的詩人迦比爾是編織工,達杜是刷羊毛工人,拉維達斯是鞋匠,錫那則是理髮師。此外,這類運動的許多主導人物都是女性,除了著名的密羅.跋伊(她的歌曲在四百年後還是廣受喜愛),還有安達爾、妲雅—跋伊、薩哈究—跋伊、克賽瑪等人。
當前這個時代的不平等議題將在下一章討論,但如果要探究論辯傳統對這種議題的重要性和影響範圍,則必須了解這項傳統對於抗拒和改善當代印度社會裡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有多少貢獻。如果認為結構完善的論證比較具有說服力,所以論辯傳統整體上而言必然對優勢族群和受過良好教育的階級有利,這種想法可是大錯特錯。在印度思想史上,有些最有力的論證都是關於最弱勢族群的生活,因此這個族群也就吸取了這些論證的實質力量,而不必仰賴習練而來的辯證技巧。
公共論理的民主
豐富的論辯傳統對印度當今的生活是否有重大影響?我認為有,而且影響面向非常多。這項傳統形塑了我們的社交世界和我們文化的本質,也使得異端主張成為印度的自然現象(這點稍後再談):持續不斷的爭辯是我們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不但深刻影響了印度政治,而且我認為在印度的民主發展與重視政教分離的態度當中尤其扮演了要角。
民主在印度歷史上的根源非常值得一提,因為許多人經常忽略了民主與公共辯論之間的關連,而習於把印度人堅持民主的態度單純歸功於英國的影響(如果英國的民主影響力真的如此之大,那麼數以百計曾經受到日不落國統治的國家顯然也都該對民主抱有同樣的堅持)。不過,這種關連性不是印度獨有的現象:整體而言,全球各地的民主根源都與公共論理密切相關。不過,印度既然特別有幸,能擁有漫長的公共辯論傳統,而且對思想上的不同主張又相當寬容,因此這種關連在印度也就特別緊密。印度在五十多年前獨立,隨即成為非西方世界中第一個毅然選擇民主體制的國家;當時印度不但學習歐洲與美國(尤其是英國)的體制經驗,也善用了本身公共論理與多元辯論的傳統。
印度身為西方世界以外的健全民主國家,締造了許多不尋常的紀錄。從英國統治下獨立之後,不但印度人民一致支持建立民主的政府體制,而且這項體制也頑強地延續了下來,不像其他國家的民主常常總是轉瞬即逝。更重要的是,軍方(不像亞洲與非洲許多國家的軍方那麼跋扈)和所有政黨(不論是主張共產主義的左派,還是擁護印度教的右派)都全面認同公民治理的優先性,不論民主統治表面上看起來有多麼缺乏效率,多麼彆扭,多麼易於取代。
印度民主發展過程中有許多決定性的經驗,其中一項出現在一九七○年代。當時曾有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主張降低印度的民主程度(理由是國家面臨相當迫切的「危機」),結果在一九七七年的大選中遭到選民明確的否決。(注四)印度的民主雖然不完美,在不少方面上都有缺陷(第九至十二章還會深入談到這一點),但克服這些缺陷的方法和手段卻都可從論辯傳統中獲得高度啟發。
有兩個陷阱絕對需要避免:(一)把民主單純視為西方世界的贈禮,印度只是在獨立的時候接受了這項贈禮而已;(二)以為印度歷史上有什麼獨特的因素,所以才會特別適合民主制度。真正的重點其實是民主與公共討論和互動論理這兩者之間的緊密關連。公共討論的傳統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不是西方世界的專利。社會只要能夠善加運用這項傳統,民主就會比較容易落實,也比較容易鞏固。
雖然常有人說民主基本上是西方的觀念與習俗,但這種觀點其實過於狹隘,因為其中忽略了公共論理與民主發展之間的密切關係——當代哲學家已經對這種關係做過深刻的探究,最著名的是羅爾斯(John Rawls)。公共論理能夠為公民提供參與政治討論與影響公共選擇的機會。投票只是促使公共討論產生效果的其中一種方式,只不過這種方式非常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投票權必須結合聆聽和表達的權利,而且是毫無恐懼的聆聽和表達。人民有沒有公開的公共討論機會,是決定投票行為的影響範圍和效力的關鍵要素。
由比較廣泛的角度理解民主(而不只是僅僅把民主視為選舉和投票的自由),不但是當代政治哲學的關注重點,也可見於「社會選擇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這兩門深受經濟推理和政治觀念影響的新興學科。重要公共決策一旦經過公開討論,不但能夠為社會和個人重視的事項提供更多資訊,也有助於修改既定的選擇。誠如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布坎南(James Buchanan)所言:「把民主定義為『討論的治理』,表示個人價值觀確實可能在決策過程中改變。」印度論辯傳統的影響範圍不只限於價值觀的公共表達,也及於價值觀的互動形塑——印度的世俗主義形式就是一個例子(這點將於下一節討論)。
我在其他地方提過,公共討論的漫長傳統可見於世界各地。不過,印度在這方面倒是的確有其獨特之處——而且和本文的主題也頗有關係。希臘與羅馬遺留下來的公共討論傳統確實值得稱許,但公共審議的重要性在印度也有一段相當值得注意的歷史。即便是征服了大半個世界的亞歷山大,在公元前四世紀闖蕩於印度西北部的時候,也不免受到政治訓誡。舉例而言,他曾經問一群耆那教哲學家為什麼對他這個偉大的征服者視而不見,結果對方提出了以下這段反對帝國主義的回答(據說答話者是阿里安):
亞歷山大大王,每個人能夠占有的土地,就是自己腳下所踩的範圍。您和我們一樣是凡人,只不過您總是忙著為非作歹,千里跋涉遠離家鄉,勞累自己也煩擾他人!……您不久也會死,到時候您擁有的土地,也不過就是用來埋葬您的那一小座墳墓。
在印度的公共論理發展史上,有相當大的功勞都必須歸諸印度的佛教徒,因為他們一向堅定信奉透過討論促進社會進步的做法。這種堅持所帶來的其中一項結果,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公開集會。這些所謂的「佛教徒會議」,目的在於解決不同觀點之間的爭執,與會的代表不但來自不同地區,也來自各種不同的思想學派。四大會議的第一場舉行於王舍城,時間就在釋迦牟尼逝世後不久;第二場約於一百年後舉行,地點在廣嚴城;最後一場則是在公元第二世紀舉行於喀什米爾。不過,規模最大也最著名的第三場會議,則是在阿育王的贊助下,於公元前三世紀召開,地點在當時的印度首都華氏城(今名為巴特那〔Patna〕)。這些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要解決宗教原則與儀式的不同意見,但顯然也探討了社會與公民義務的要求,而且還鞏固也促進了公開討論爭議性議題的傳統。
最引人注意的是,阿育王雖然統治了印度次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境內),卻致力於確保公共討論能夠平和進行,而且也贊助了這些會議當中規模最大的一場。他訂立宣揚的公共討論規範,應是世界上的首例,有點像是十九世紀的《羅伯氏會議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舉例而言,他規定「言詞必須節制,不得在不適當的場合讚揚自己的宗派或者貶抑其他宗派。即便是在適當的場合,言語也應保持溫和」。就算是在爭論當中,也應該「隨時在各個方面對其他宗派表達適切的敬意」。
阿育王提倡公共討論的行為,在後來的印度歷史上也有人呼應,但倡導最力的大概要算是近兩千年後的蒙兀兒皇帝阿克巴。他支持並且贊助不同教派信徒間的對話,而且他的核心主張是:要處理困難的社會和諧問題,必須透過「追求理性」,而不是「仰賴傳統」。因此,他非常贊同理性的對話。皇室的贊助不是公共論理發展的必要因素,但這種現象卻為印度論辯史的影響範圍增添了另一個層面。公開討論不管是否獲得政府的贊助,都顯然和民主的萌發脫不了關係。民主雖然也必須有其他要素,但在參與治理當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公共論理,卻是宏觀層面上的一個重要元素。我稍後會再回頭探討這種關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