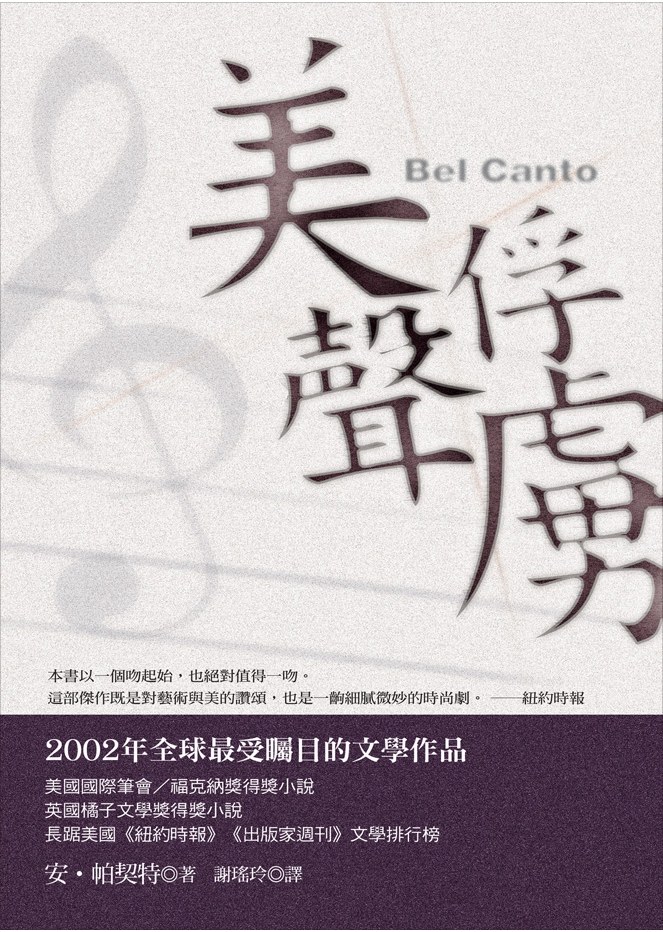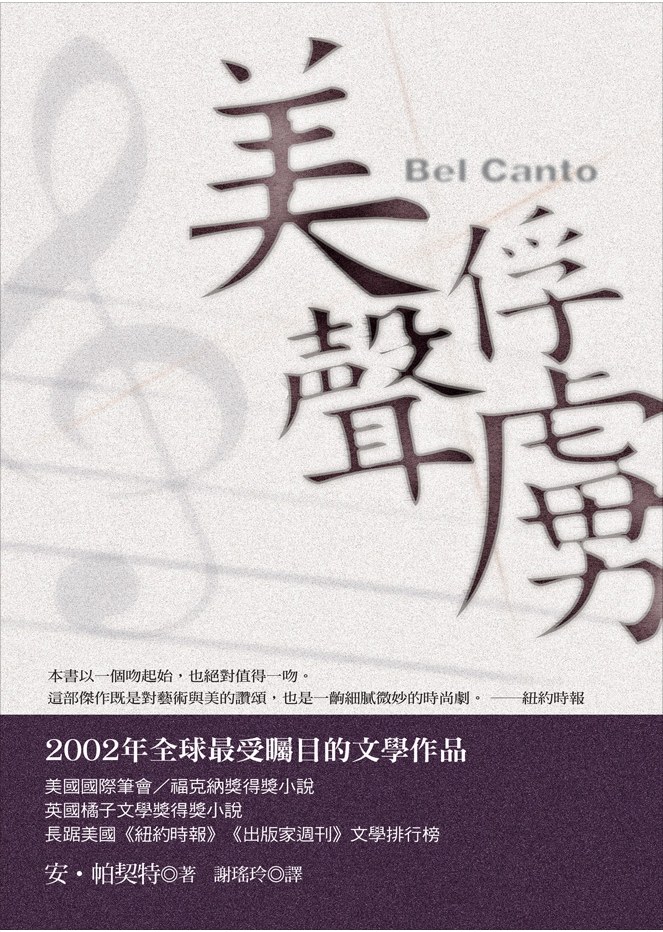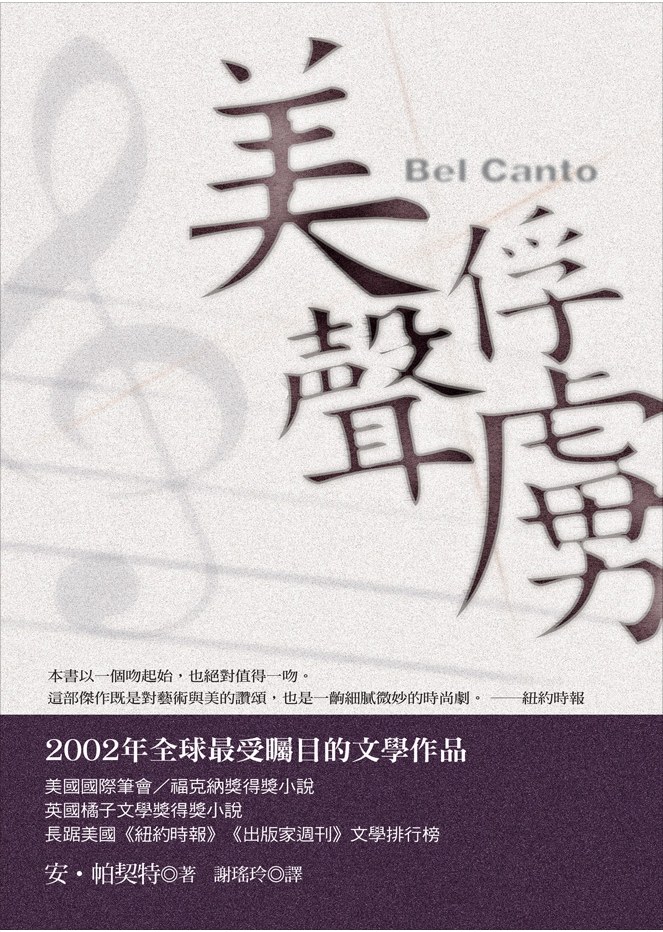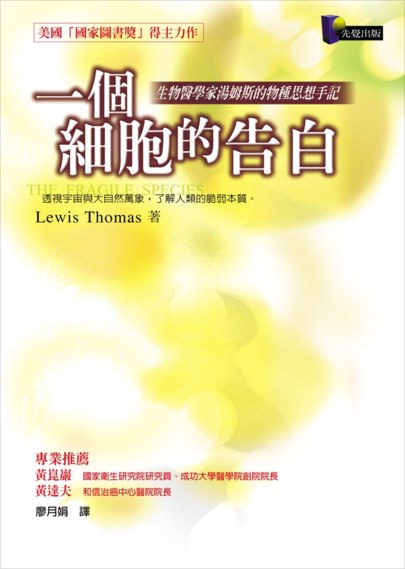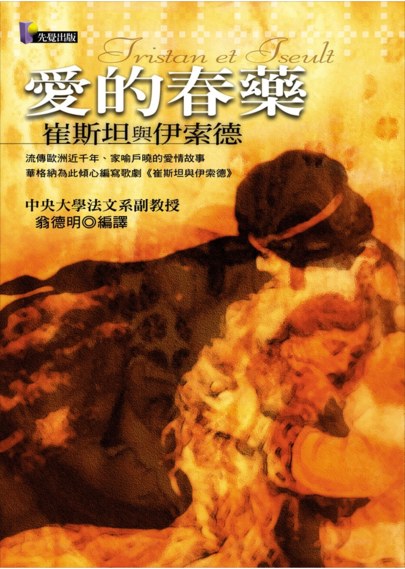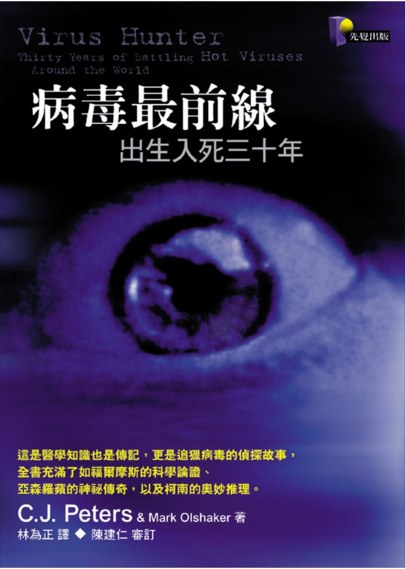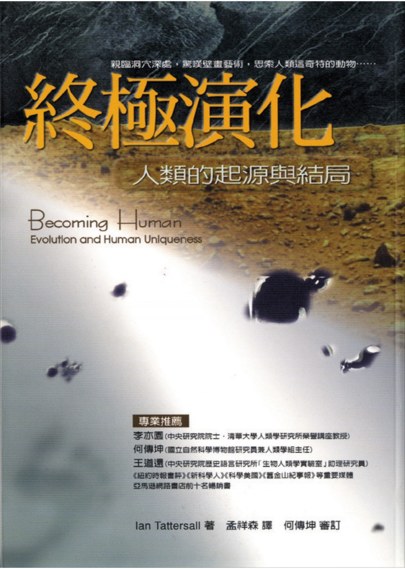1
熄燈之後,伴奏吻了她。或許在全暗之前他便已轉向她了,或許他在燈暗之際舉起了雙手。他必定做了什麼動作,因為客廳裡的人後來全都記得一個吻。他們並未看到一個吻——那是不可能的。那黑暗倏然籠罩,而且是一片漆黑。
所有的人不僅確定有一個吻,而且還能辨認出是哪一種的吻:強烈、熱情的一吻,令她措手不及。燈暗之際,每個人的目光都盯在她身上。他們仍在鼓掌,全都站起了身,正在熱烈地喝采、拍手,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停歇。
義大利人和法國人都高喊著:「Brava! Brava!」日本人則別過了身子站離他們一些。如果滿室通明的話,他會像那樣吻她嗎?是因為他滿心想著她,所以在黑暗的一瞬間便攬住了她,幾乎是不加思索的嗎?還是因為整個大廳裡所有的人,不論男女,也都想要她,於是他們便產生集體幻想呢?她那美妙的歌聲令他們折服,使他們想以他們的嘴蓋住她的,暢飲那聲音。說不定那樣的美聲可被轉移、吞噬、占有。親吻發出那美妙歌聲的雙唇,會有何意味呢?
他們有些人已珍愛她多年。他們擁有她錄製的每一張唱片,並在筆記本上記下他們看到她的每個地點,詳列出樂曲、演出者和指揮的姓名。當晚,也有一些人是之前從未聽說過她,並且在別人問起時,會說歌劇只是群貓嘶叫的無意義組合,說他們寧可在牙醫的診療椅上度過三小時。這些人現在感動涕零;他們之前真是錯得離譜。
沒有人因為黑暗而害怕。他們幾乎渾然不覺,繼續鼓掌。來自國外的人以為這種景況在這裡一定常常發生。燈亮,燈暗。本國人則知道的確如此。再說,這次電力中斷的時機是如此戲劇化又恰恰好,好似所有的燈都在說:「你們並不需要看;聽就好。」只是沒有一個人想到為何每張桌子上的燭光也都熄了,也許就在同一瞬間,或在那之前。大廳裡洋溢著蠟燭剛熄滅的芳香,還有一縷縷甜蜜且毫不危險的青煙。這氣味暗示著時間已經晚了,應該要就寢了。
他們繼續鼓掌,並認定她仍在持續親吻。
蘿珊‧寇思,抒情女高音歌手,是細川先生造訪本國的唯一理由,而細川先生是所有人來赴宴的原因。這裡不是會令人想來一遊的地方。地主國(一個貧窮的國家)之所以花費不貲,為一個只有以蘿珊賄賂才肯赴宴的外國人辦生日宴會,只是因為這個外國人是南西公司——全日本最大的電子企業——的創辦人和董事長。地主國深切希望,細川先生會對他們微笑,在他們需要幫助的幾百種可能的方式中,對他們略施援手;或透過訓練,或透過貿易。可以在這裡投資設廠(這是一個難以說出口的美夢),廉價勞力能讓每位參與者獲利。產業可以將本國經濟自可可葉和黑心罌栗的農作轉移,使人產生該國已背離古柯鹼和海洛英卑劣事業的印象,從而促進外援,並使這些毒品的非法買賣不至於太引人注目。
但是這個計畫在過去從未扎根,因為日本人天性過於謹慎。他們相信如本國的這種國家可能有的危險性和種種危險的傳言;因此,細川先生親身蒞臨——不是執行副總裁,也不是任何政客——證明了此計畫已有眉目。
也許想要進一步發展還得經過誘哄、央求。也許還得使勁推它一把。不過,這次造訪行程不僅包括今夜有歌劇明星作陪的盛大生日晚宴,還有排定的多次會商和明天參訪未來設廠的可能地點,可說已達成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因此廳裡瀰漫著一股希望濃厚的甜蜜氣氛。
來自十幾個國家的代表們由於對細川先生此行的意圖有所誤解,也都出席了宴會。這些投資者和大使們很可能不會鼓勵他們的政府在本國投資半毛錢,但卻極願意支持南西公司的每一項計畫。他們現在都盛裝分列在客廳各處,舉杯暢飲,談天說笑。
對細川先生而言,他這次來訪的目的並非為了商務、外交,或如後來所報導的是為了與總統建立情誼。細川先生並不喜歡旅行,也不認識總統。他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圖——或缺乏意圖。他無意設廠,原本也絕不會同意旅行至一個陌生的國家,去和一群他不認識的人一起過生日。
和一群陌生人慶祝他的生日非他所願,何況還是他的五十三歲生日,一個他不認為有任何重要性的數字。所以他先後五、六次拒絕了這些人請他赴宴的強烈要求,直到他們允諾以蘿珊‧寇思的出席做為賀禮。
以她為賀禮,誰拒絕得了呢?無論有多遠、多不適宜、容易引起誤解,誰說得出一個「不」字呢?
*
但是先來回想一下另一個生日吧,他十一歲的生日,那一天細川克實第一次聽到歌劇,威爾第的《弄臣》。他父親帶他坐火車到東京去,兩人在滂沱大雨中一起走向劇院。那天是十月二十二日,因此那場雨是冰冷的秋雨,街上鋪了薄薄一層被雨水浸濕了的紅葉。
當他們到達東京大都會劇院時,身上的大衣、毛衣和內衣都被打濕了。細川克實的父親皮夾裡的兩張門票已潮濕褪色。他們並沒有特別好的座位,但視線並未受到任何遮擋。一九五四年時,金錢是貴重的;火車票和歌劇是難以想像的事物。
換了一個年代,這樣一場演出對兒童而言可能太複雜了些,但這時戰後才過數年,而這個時期的孩童較有可能了解現在的孩童似乎不可能懂的許多事物。他們爬上長長的階梯到他們坐的那一排,避免低頭看下方那令人頭暈目眩的空洞。他們向每一個站起身讓他們走到座位去的人鞠躬致歉,然後便拉開座椅,坐了下來。他們早到了,但其他人比他們更早到,因為門票附加的奢侈之一便是靜靜坐在這美麗的大廳裡等待的權利。這對父子靜坐等待,沒有交談,直到黑暗終於降臨,接著第一聲輕柔的音樂自遙遠的下方某處傳了過來。小得似昆蟲般的身影自簾幕後走出,張開了嘴,於是他們的思慕、悲痛、狂野又無盡且終將使每個人步向毀滅的愛,便隨著他們的歌聲在四壁間迴盪。
就在這一場演出中,歌劇深印在細川克實的腦海裡;寫在他眼瞼下方的訊息,使他在睡著時可以細讀。多年之後,當一切都是商務,當他在一個價值觀建立在努力工作上的國家裡,比誰都更努力地工作時,他相信真正的人生是被儲存在音樂裡的。
當你投入外界去承當應盡的義務時,真正的人生被安全地保存在柴可夫斯基的《尤金‧奧涅金》一劇的歌詞裡。他當然知道(雖然並不完全明白)並非人人都喜歡歌劇,但他希望人人都可以找到真正的人生。他用以測量自己愛的能力的標記,是他所珍藏的每張唱片、他去看現場演出的每次難得的機會,而非他太太、他女兒或他的工作。他從沒來想到,他已把應該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轉移到歌劇上。他只知道,如果沒有歌劇,他的這一部分便會完全消失。就在第二幕開始不久,當黎果雷多和吉爾達一起合唱,兩人的歌聲交纏、跳躍時,他握住了他父親的手。他完全聽不懂他們在唱什麼,也不知道他們扮演的是一對父女,只知道他必須握住什麼東西才行。他們那麼猛力地拉扯著他,使他感覺自己自那高而遙遠的座位上向前傾倒。
這樣的愛孕育出忠誠,而細川先生是個很忠誠的人。他從未忘記威爾第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和其他人一樣,他開始迷上某些歌手。他蒐集舒瓦茲柯芙和蘇莎蘭的作品,深信卡拉絲的才氣超過眾人。他的生活裡並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奉獻給這樣的嗜好,於是他養成一個習慣:和客戶吃過晚餐且將文件都處理完畢後,他會花三十分鐘聽音樂並讀歌劇劇本,然後才上床就寢。非常非常難得的是,一年大概有五個週日吧,他會有連續三個小時的空閒,將一齣歌劇從頭聽到完。他四十幾歲時,有一次因吃了一隻壞掉的牡蠣而食物中毒,在家休養了三天。在他的記憶裡,這三天就像度假一樣快樂,因為他不斷地播放韓德爾的《愛爾奇娜》,就連睡著時也未停歇。
有一年他生日時,他的長女清美買了蘿珊‧寇思的唱片送給他當生日禮物。要買禮物給她父親可說是難上加難,因此當她看到那張唱片和一個她並不認識的名字時,她決定碰碰運氣。不過吸引她的並非那個陌生的名字,而是那女人的臉龐。清美覺得多數女高音的照片都頗討人厭;那些臉不是扇子半遮看人,便是透過網狀的面紗凝望。可是蘿珊‧寇思卻直視著她,連下巴都是抬高的,雙眼圓睜。清美甚至還未注意到這是一張歌劇《拉梅摩的露西亞》的錄音時,便已伸手拿起這張唱片。她父親擁有多少張這齣歌劇的錄音呢?這不重要。她在櫃台付了錢。
當細川先生把這張唱片放到唱機裡播放,並坐下來凝聽後,當晚他沒有再回去工作。他彷彿又是那個坐在東京劇院後座上的男孩,他父親以溫暖的大手握住了他的小手。他將那張唱片重複播放,不耐煩地跳過不是她聲音的每一部分。那歌聲曼妙高昂,溫暖而複雜,且無所畏懼。一個人的聲音怎麼可能同時受到完全的控制又如此奔放?他叫喚清美;她應聲而來,站在他的書房門口。她開口想說話——「是?」或「什麼?」或「爸爸?」——但她還未說出口便聽到了那個聲音,那個照片中正面直視的女人。她父親也沒開口,只是伸出張開的手掌比了一下擴音器。她非常高興自己做了一件這麼對的事。那音樂誇讚著她。細川先生閉上眼睛,陶醉在他的夢裡。
自那一天後接下來的五年裡,他看了十八場由蘿珊‧寇思主演的歌劇。第一場是個幸運的巧合,其餘各場他都到她所演出的那個城市去,製造出可以讓他到那裡去的商務。《夢遊女》他連看了三晚。他從未請她出遊或登門求見。他並不自認為對她的賞識超越過任何其他人的,深信只有愚蠢的人才不會有像他對她那樣的感覺。能夠坐下來聆聽她的歌聲,便是一個人的至高恩典。
在任何商業雜誌上看到有關細川克實的報導時就會知道:他說話時不會蘊含熱情,因為熱情是很私人的,但歌劇總會浮現,使他顯露較易於接近的人性角度。其他總裁們不是在蘇格蘭的河流釣魚,便是駕著私人小飛機飛向赫爾辛基,惟獨細川先生的照片是在他家裡拍的。照片中的他坐在一張皮椅上聆聽,背後有一部南西EX-12的主體音響系統。關於嗜好的問題常是無可避免的,而答案卻只有一個。
為了一筆比當晚全部花費總額(包括食物、服務、運輸、鮮花、警衛等)都要高出許多的報酬,蘿珊‧寇思答應出席晚宴;正巧時間又是在她已唱完在史卡拉歌劇院的一季和到阿根廷的科龍劇院登台演出之間。細川先生從信上得知他若接受邀約,便可提出一個請求,但地主國並不能給予任何承諾,因為必須將這個請求告知寇思小姐,由她自行決定。細川先生選了《盧莎卡》中的詠唱調,也是燈暗時蘿珊‧寇思剛剛唱罷的曲子。這是當晚預定的最後一曲,只不過誰敢說如果燈光未熄的話,她會不會在喝采聲中加唱一曲或甚至兩曲呢?
細川先生之所以選擇《盧莎卡》,是要以此表達對寇思小姐的敬意。這是她最常演出的曲目,所以她不需要特別準備。就算他不提出請求,這曲目也必然會被排進當晚的節目裡。他並不要求她唱鮮為人知的歌曲,如《帕特諾普》中的抒情調,以證明自己是她的歌迷。他只想和她在同一個房間裡,站在她的近處,聽她唱《盧莎卡》。許多年前,他的翻譯者便已為他將捷克原文譯了出來:「如果有個心靈將夢到我,但願他醒來時仍記得我。」
燈仍然暗著。鼓掌聲開始有氣無力了。人們眨眨眼睛,想再看到她。一分鐘過去了,然後兩分鐘,但這群人依然舒適地不甚關切。接著,法國大使席蒙‧提勃特注意到廚房門下方的燈仍是亮的。提勃特到本國來之前,曾得到允諾將被派任到他更渴想得多的西班牙去,想不到就在他和家人仍在打包之際,那職位卻不公平地被當做政治酬庸而派給了另一個人。他是第一個意會過來的。他覺得似乎從酒醉狀態,從深沉的睡眠狀態中猛然驚醒。在黑暗中,他伸手抓住他太太仍在鼓掌的手,隨即拉著她擠進人群裡,擠向他無法辨識的黑暗身軀之間。他朝著就他記得應在大廳另一端的玻璃門的方向移動,伸長脖子想藉著一點星光看出方向。他看見的是手電筒投射出的一道窄光,接著是另一道。他只覺得一顆心陡然下沉,一種只能以哀傷名之的感覺。
「席蒙?」他的太太低叫了一聲。
一切都已布置妥當,在他毫無察覺之際,網已張起且罩住了全屋。儘管他的本能是繼續往前推進,看看他能否幸運地逃過一劫,清晰的邏輯思考卻制止了他。最好不要引人注目。最好不要成為榜樣。在大廳前方某處,伴奏正在親吻女高音歌手,於是提勃特大使將他太太艾迪絲擁入懷中。
「誰為我點一根蠟燭吧。」蘿珊‧寇思喚道:「我可以在黑暗中唱歌。」
此話一出,全廳的氣氛僵住了,最後一波掌聲也化為寧靜,因為大家這才注意到連蠟燭也都熄滅了。這一夜已盡。此時,坐在豪華轎車裡的侍衛們都已在瞌睡,像餵食過飽的大狗一樣。全廳的男士們都伸手探入口袋裡,卻只摸到了折疊整齊的手帕和鈔票。人聲開始沸騰,還有來回的腳步聲,然後,彷彿變魔術一般,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