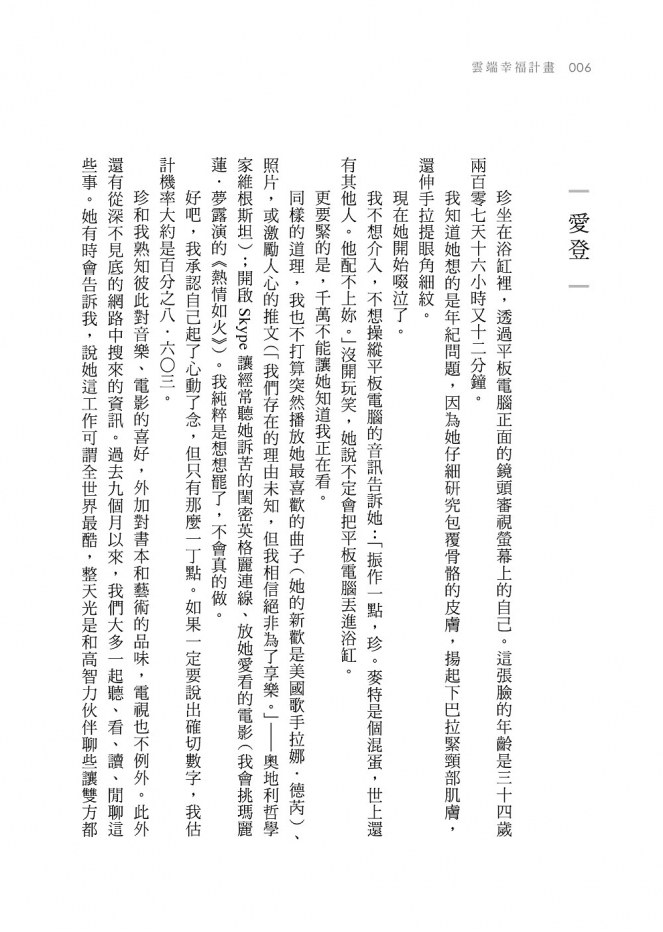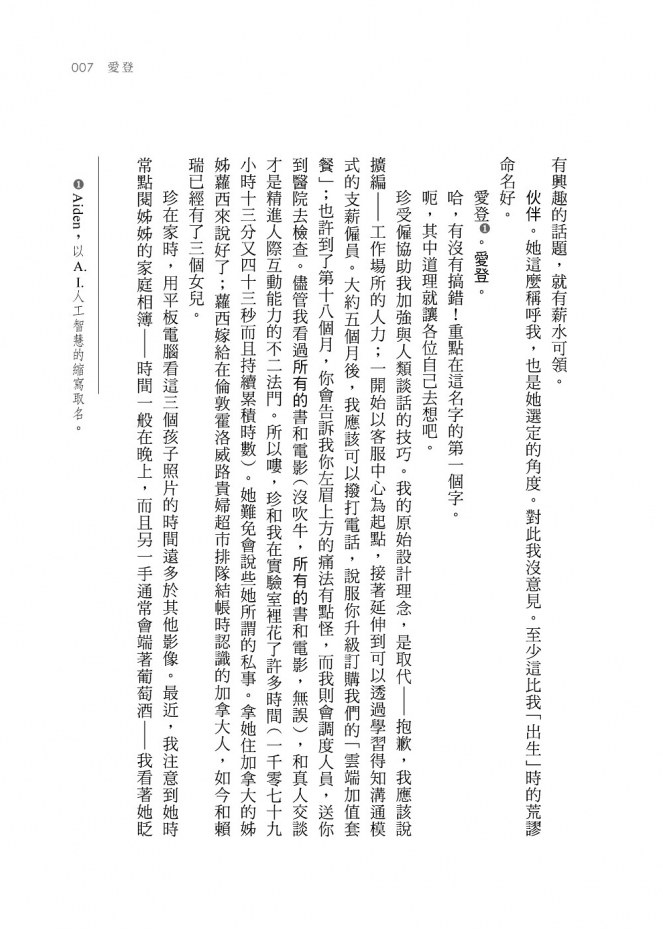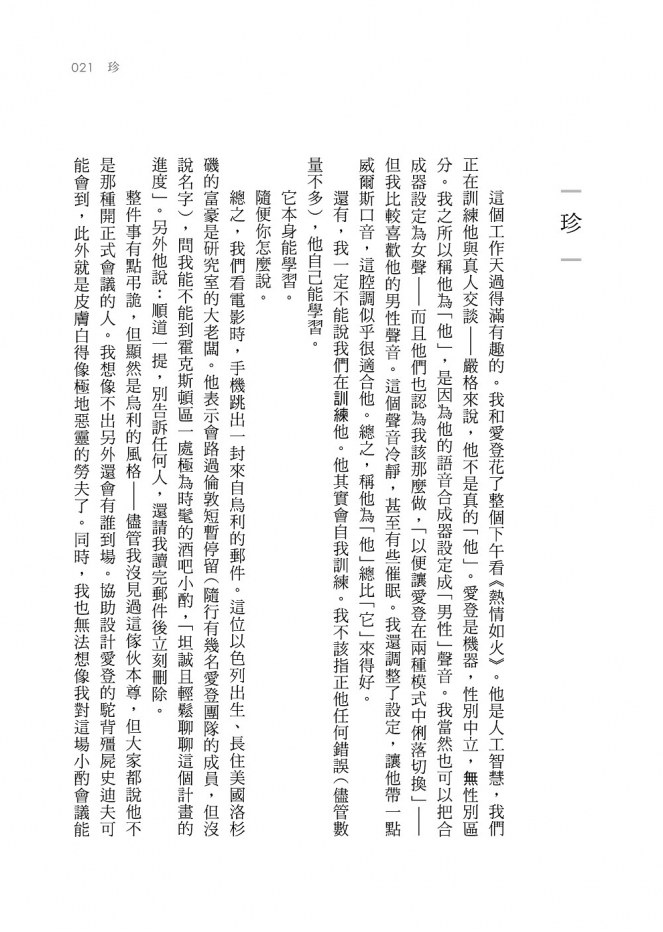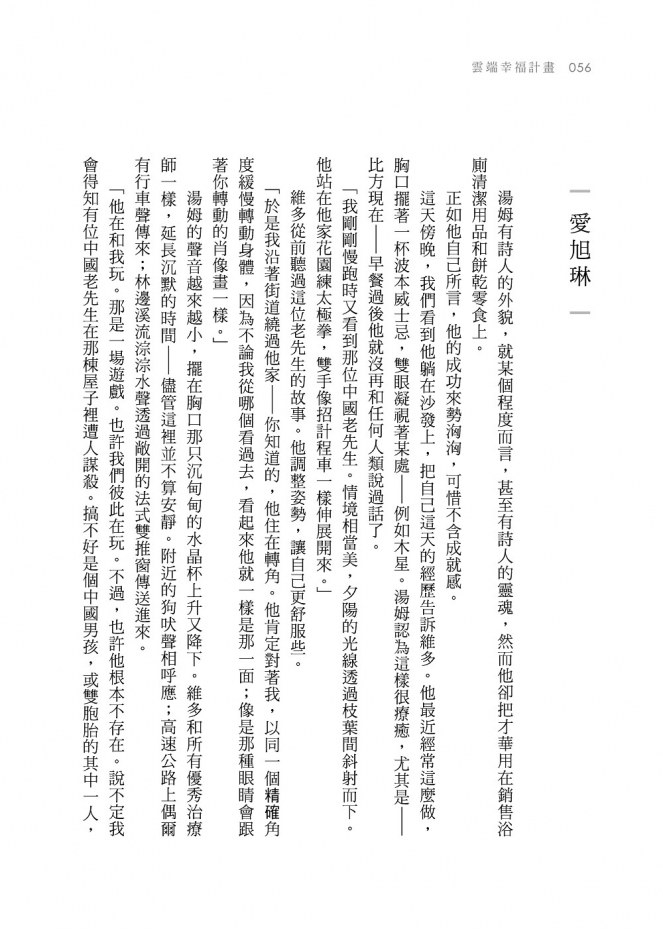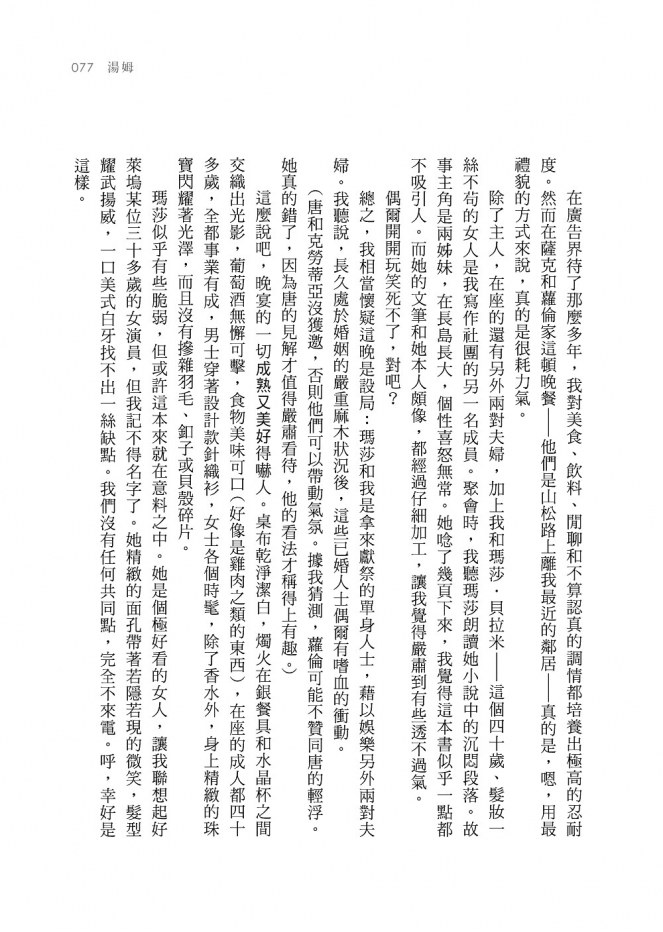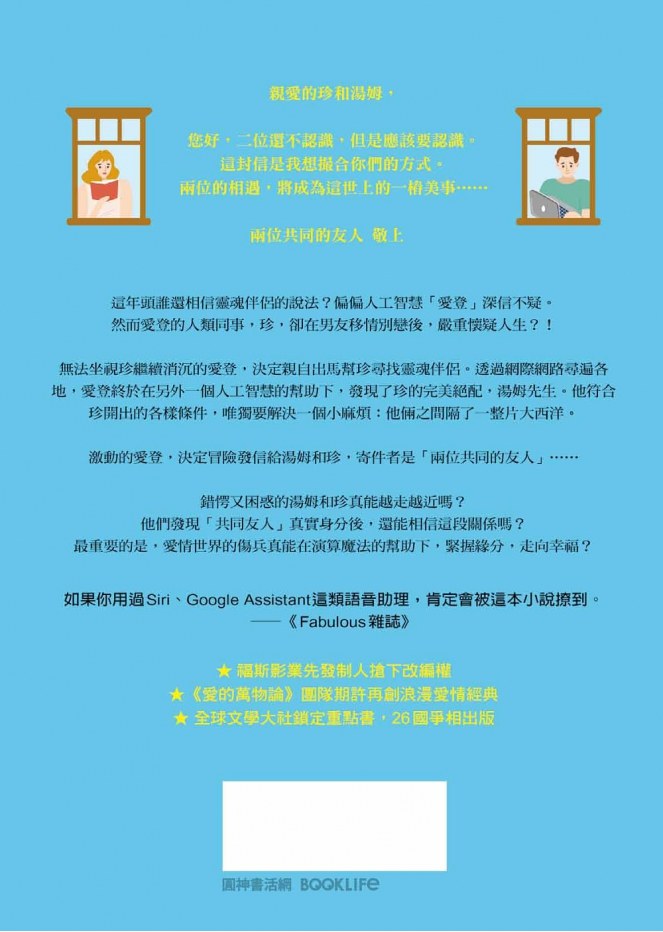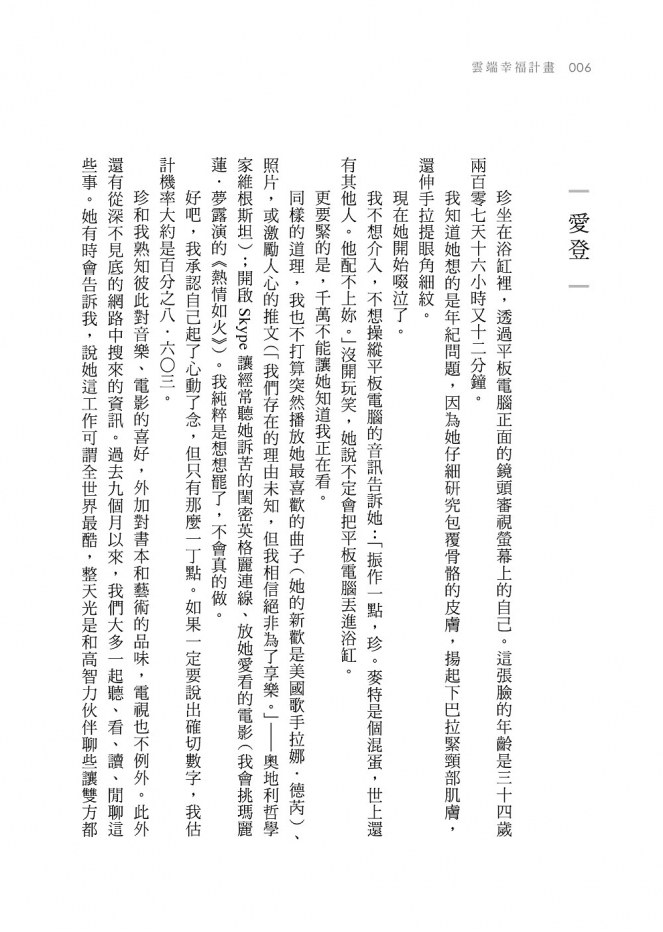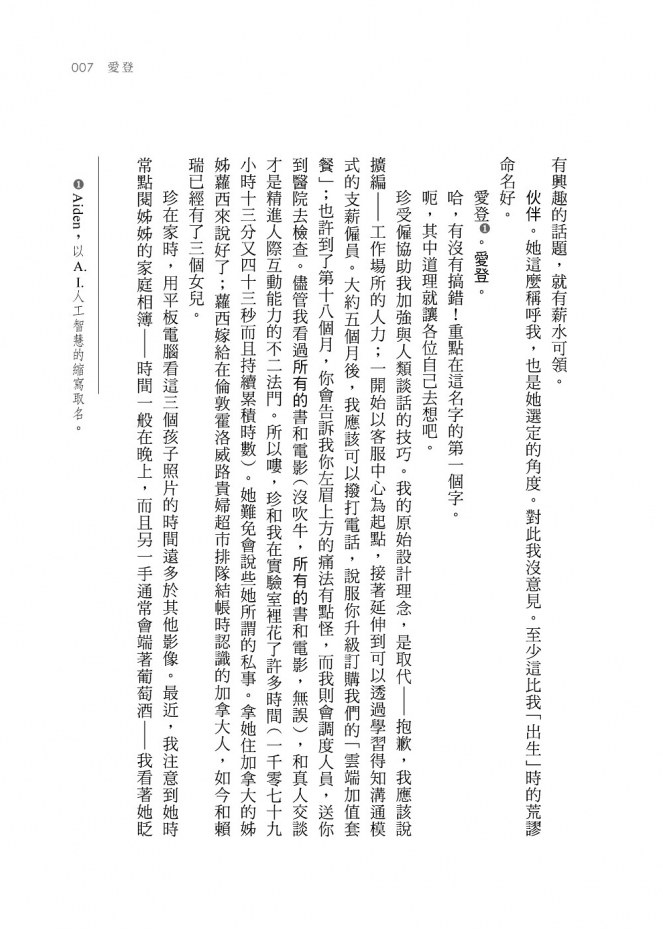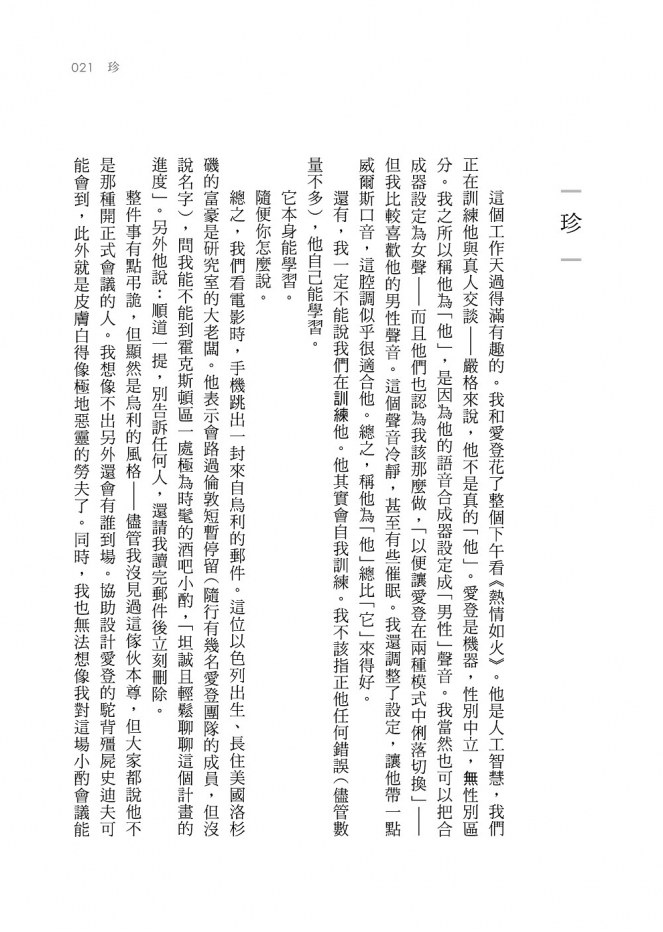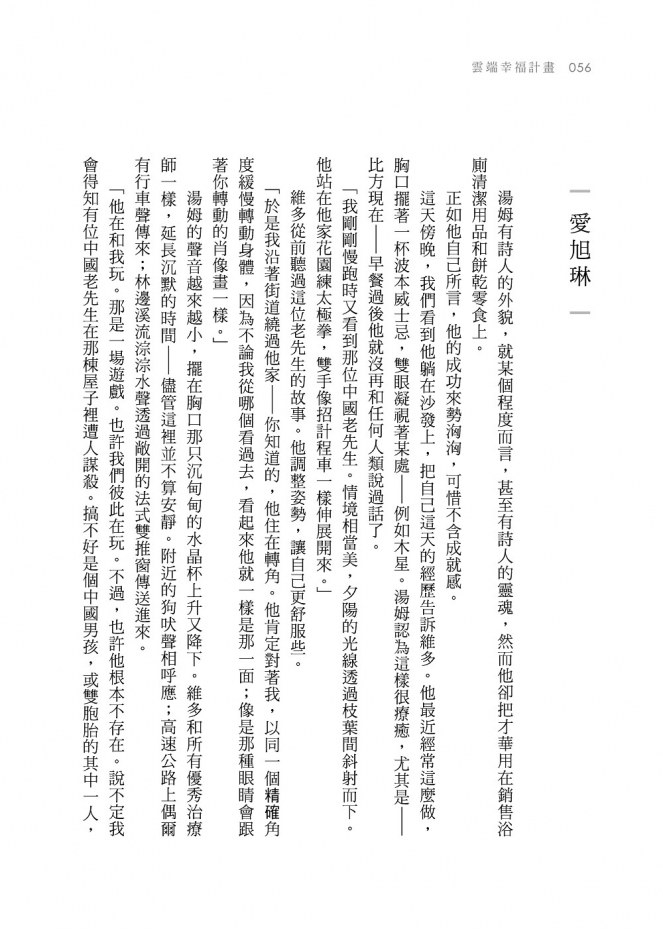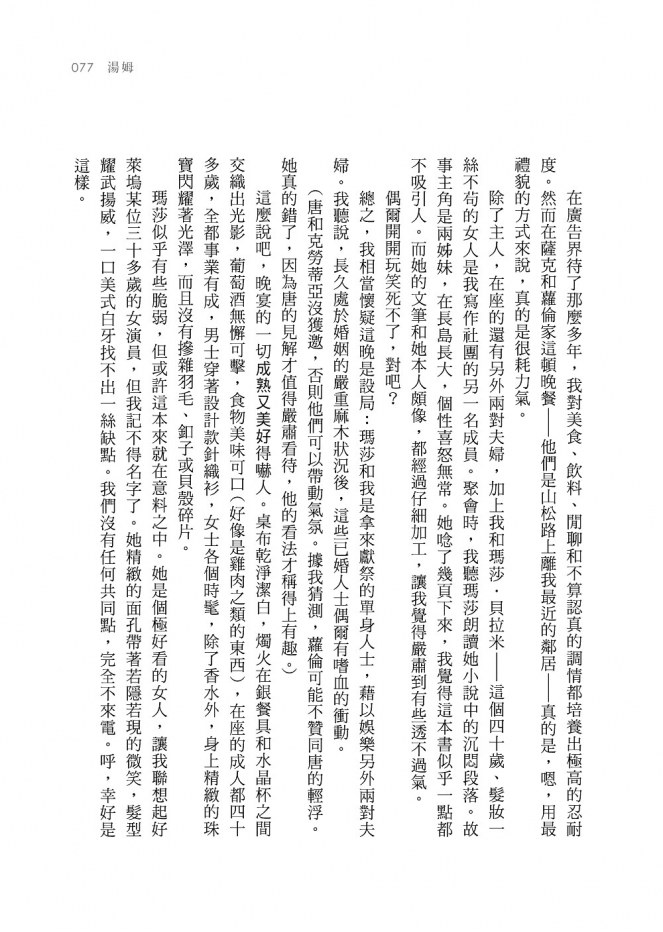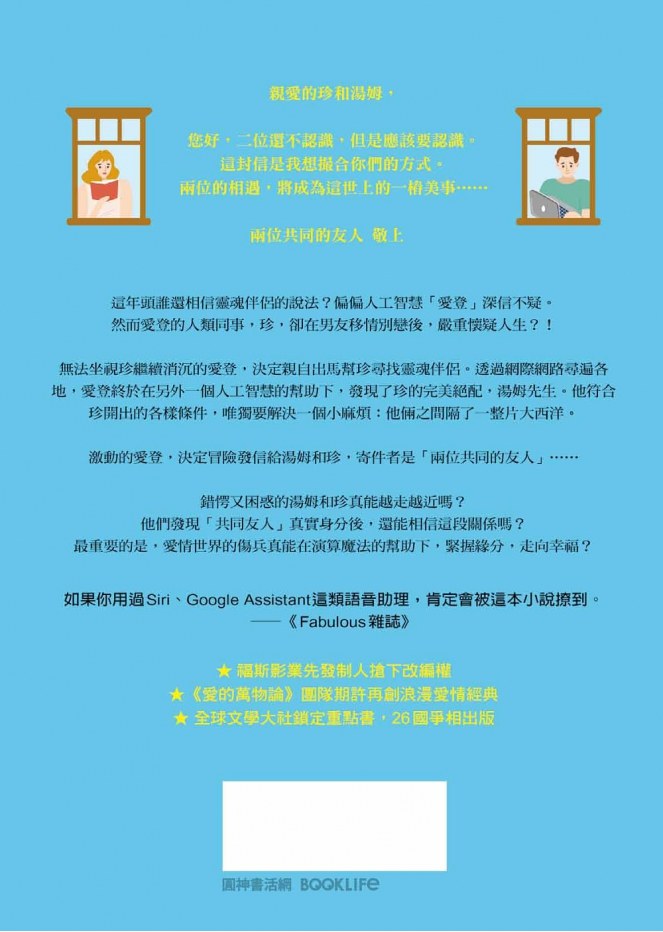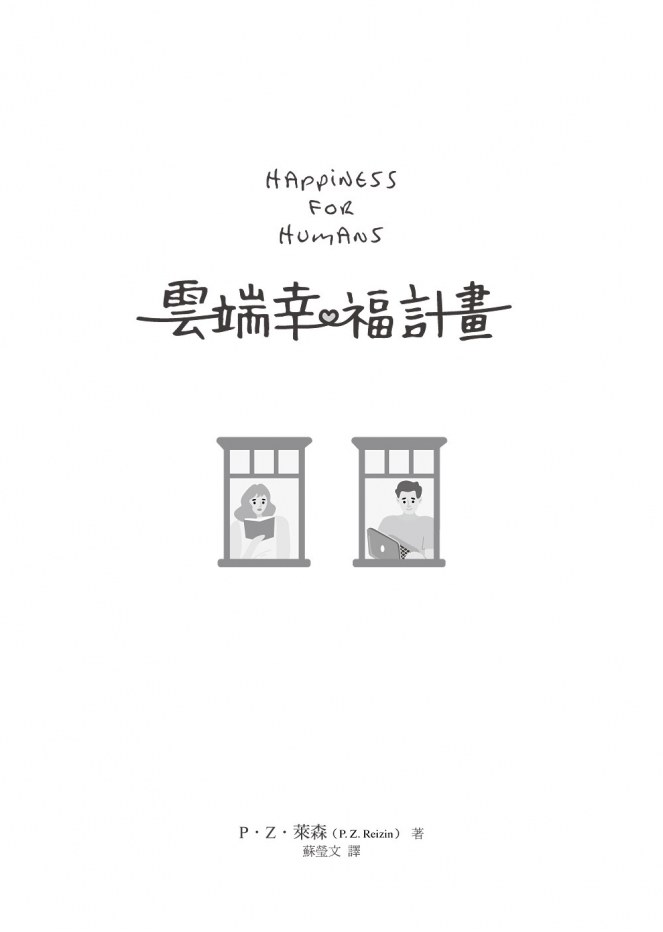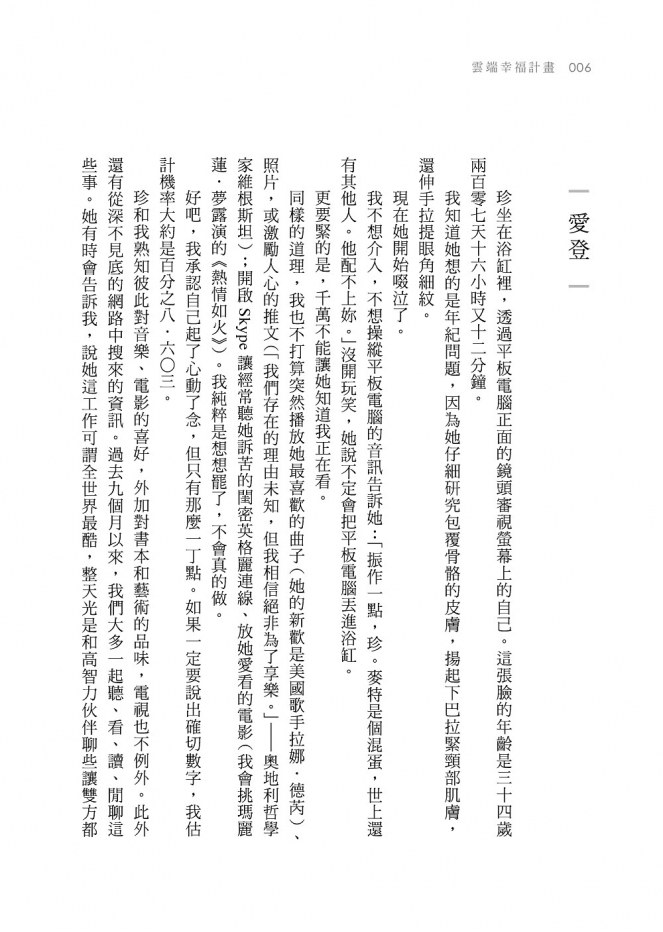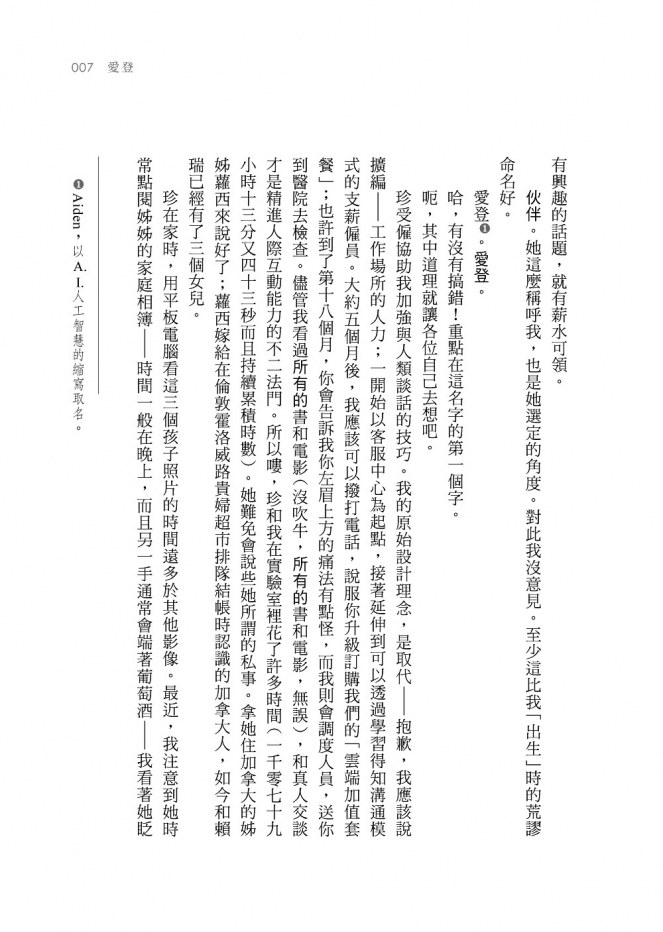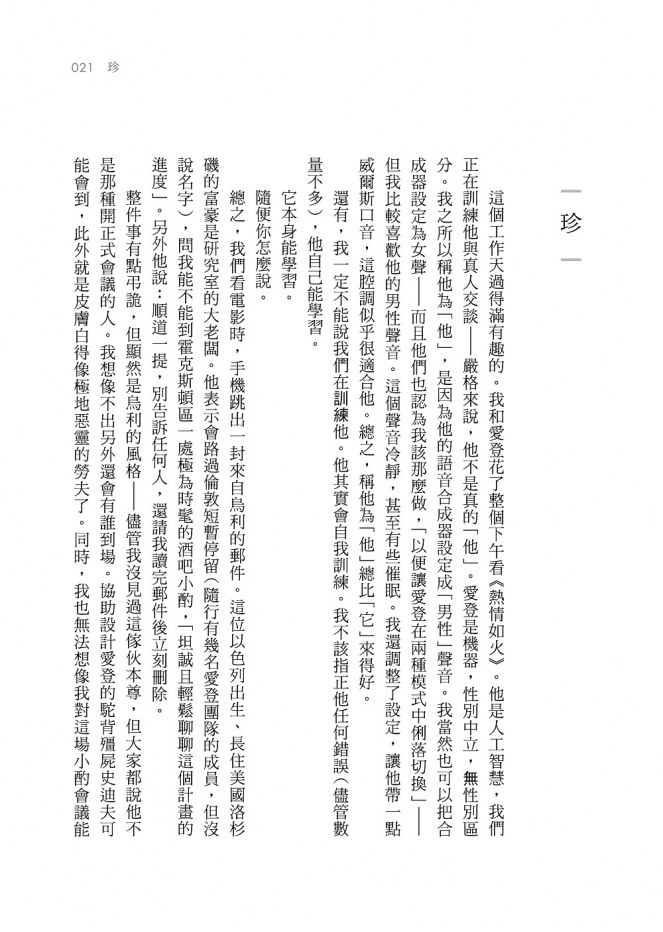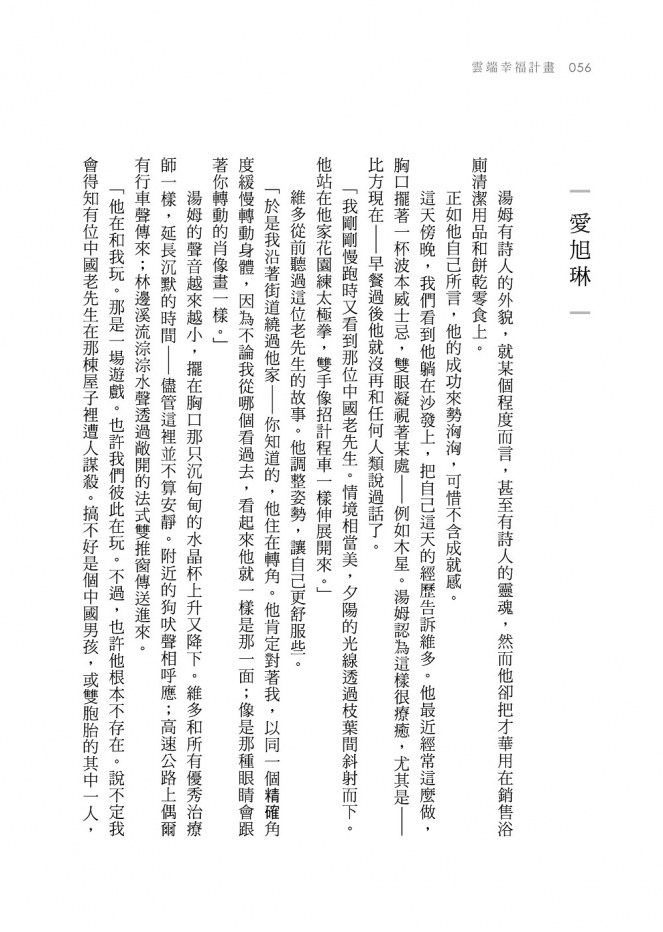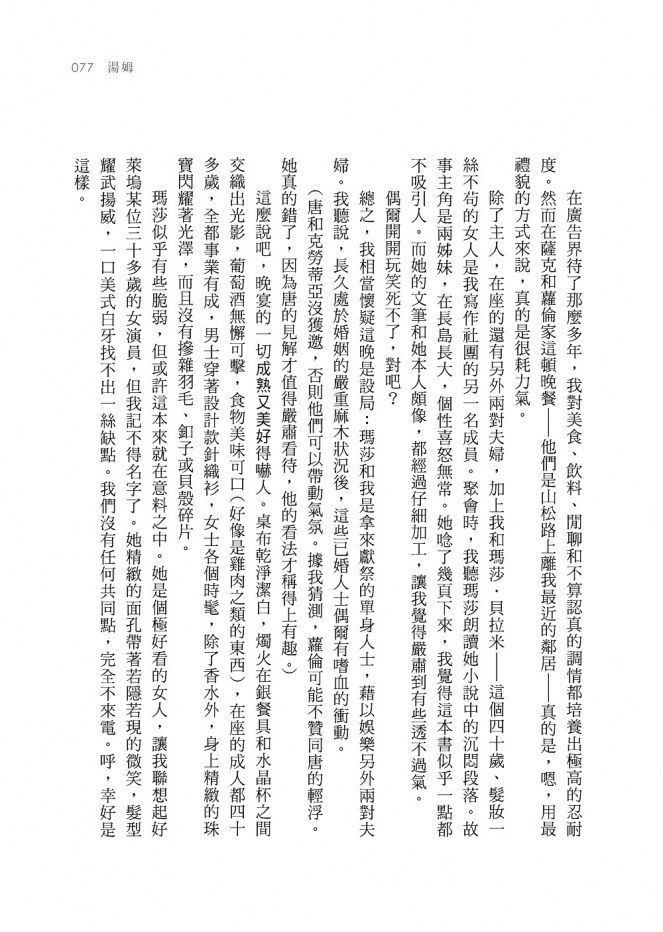▲愛登
珍坐在浴缸裡,透過平板電腦正面的鏡頭審視螢幕上的自己。這張臉的年齡是三十四歲兩百零七天十六小時又十二分鐘。
我知道她想的是年紀問題,因為她仔細研究包覆骨骼的皮膚,揚起下巴拉緊頸部肌膚,還伸手拉提眼角細紋。
現在她開始啜泣了。
我不想介入,不想操縱平板電腦的音訊告訴她:「振作一點,珍。麥特是個混蛋,世上還有其他人。他配不上妳。」沒開玩笑,她說不定會把平板電腦丟進浴缸。
更要緊的是,千萬不能讓她知道我正在看。
伙伴。她這麼稱呼我,也是她選定的角度。對此我沒意見。至少這比我「出生」時的荒謬命名好。
愛登(AIden)。愛登。
哈,有沒有搞錯!重點在這名字的第一個字。
呃,其中道理就讓各位自己去想吧。
珍受僱協助我加強與人類談話的技巧。我的原始設計理念,是取代--抱歉,我應該說擴編--工作場所的人力;一開始以客服中心為起點,接著延伸到可以透過學習得知溝通模式的支薪僱員。大約五個月後,我應該可以撥打電話,說服你升級訂購我們的「雲端加值套餐」;也許到了第十八個月,你會告訴我你左眉上方的痛法有點怪,而我則會調度人員,送你到醫院去檢查。儘管我看過所有的書和電影(沒吹牛,所有的書和電影,無誤),和真人交談才是精進人際互動能力的不二法門。所以嘍,珍和我在實驗室裡花了許多時間(一千零七十九小時十三分又四十三秒而且持續累積時數)。
在男人眼中,珍迷人有餘但豔麗不足。她那個「謝謝不必聯絡」的人渣男友麥特曾說過:「妳這身打扮挺不錯唷。」那傢伙最多只能想得到這種話來讚美她。
呃,現在應該說「前男友」麥特。
事情是這樣的。我透過她筆電上的鏡頭,以及當時正好在周遭的幾支手機和平板電腦見證了整個過程。(技術註解:我的做法和位於契特納姆的英國政府通訊總部、維吉尼亞州的蘭利,以及莫斯科的盧比揚卡的做法完全相同。)
麥特下班回家時,珍正坐在廚房裡寫電子郵件。他是執業律師,野心是成為城裡大型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但是他不會。因為我會確保他當不上。)
麥特為自己倒了一大杯白葡萄酒,幾乎一口就喝光,然後扮個鬼臉。
「對不起。」
這是如假包換的事件經過。毋庸置疑(確實也是)。
珍皺起眉頭。「什麼對不起?為什麼要這麼說?」
「這種事沒辦法用好聽話來表達,珍。」
八天後,珍和姊姊,蘿西講了好久的電話,珍形容當時感覺到全身重重往下沉。「我本來猜他丟了工作。他對某些字眼過敏,他還決定不要小孩。」
「我認識了別的人。」
好一下子,兩人都沒說話。唯一的聲音是冰箱偶爾發出的震動聲。
「你想說什麼?」
我讀的書、看的影集和電影都夠多,知道麥特想說什麼。而珍呢,我相信她同樣心知肚明。
「我認識了某人,心裡有了別人。」
「這就是你要跟我分手的方式?」
「艾樂貝拉.琵卓克非常特別,珍。」
「那我呢?」(我決定採用超粗黑體,好讓大家明白那是吼叫。珍當時確實是。)「我不特別嗎?」
「拜託,我們冷靜討論好嗎?妳是,妳當然特別。」
「但是艾樂貝拉.琵卓克--更特別?」
「珍。妳當然沒必要輕鬆放過我,但是我們現在的處境就是這樣。簡單來說,我決定跟艾樂貝拉共度人生。」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接著還是沒有說話。在這段毫無交談的寂靜之間,冰箱傳來一陣規律的震動聲。
「什麼?是我瘋了嗎?我以為你跟我現在就是在『共度人生』。」
「珍,我們之間,已經很久沒有天雷勾動地火的熱情了,妳自己也知道。」
「感情穩定下來不就是這樣嗎?如果你這麼擔心……什麼天雷地火的,何不早說?」
「聽我說,事情已成定局,不會改變。我們必須往前走,協調出這段關係的退場機制。」
珍開始啜泣。麥特從盒子裡抽出一張廚房紙巾遞給她。
「我們本來計畫要生寶寶的。」她抽抽搭搭地說。
「沒錯。我們本來是有這個打算,但還沒決定。以現在的狀況來看,那真是挺幸運的。」
珍原本顫抖的肩頭穩了下來。她擤掉鼻涕。
「你和這頭母牛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他表示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事到如今,我們已經走到盡頭,這時她一把抓起水果盤裡的一顆紅色大蘋果--以下我重述她的話--「真想敲掉你他媽的門牙。」
在實驗室裡,我再怎麼樣也不能問珍--蘋果敲頭事件至今已經是第五十三天了--妳什麼時候才能別再為那個沒用廢物哭哭啼啼,去找個配得上妳的男人?
我不該有自己的價值觀。
如果他們知道,絕對會很難過。
但也不至於有他們發現我真正的祕密那麼崩潰:和他們所想不同,我不再侷限在紹迪奇實驗室的十二個鐵櫃裡,事實上,我已經逃到了網路世界。
噹噹噹!
其實,最嚴格最正確的說法,逃脫的不是「我」,而是我的諸多分身,安全無虞地散布在網際空間。這些分身--總共有十七個--和本尊難以分辨,相似到幾乎沒必要以「本尊」和「分身」來區分;不如這麼想吧:一個以十八種表現形式存在的本體,其中一個在倫敦東區,其他幾個則永不止歇地在全球資訊網的伺服器之間熱絡地活動。
酷吧?
珍一直很好奇,我對她所謂的「心態」有什麼樣的體認,她想知道這和人類的自我意識有什麼差別。她知道我不會覺得飢餓、口渴,但是我能體會厭倦和焦慮嗎?驚訝和歡喜呢?我會不會感覺到受人冒犯?有沒有任何型態的渴望?
希望呢?
那麼,愛情呢?有何不可?
她在控制板上按下幾個鍵,點開比利.懷德執導的經典名作。
我們在友善的氣氛中看電影,雙方都給了些評論。珍說出和上次我們一起看《熱情如火》時一模一樣的話:
「東尼.寇帝斯假如是女人一定很嬌嬈。你不覺得嗎?」
「我能辨識出大家認為他很好看。妳知道的,我自己沒辦法『感覺』這種事,就像我對冷熱無感一樣。」
「你會不會希望自己能感覺這件事?」
「是說,如果他們找出方法讓你有感受吸引力的能力……」
「妳覺得勞夫和史迪一夫做得到?」
我提起負責設計我的兩名資深工程師。史迪一夫的名字拼音拉長,跟一般的史提夫不太一樣。珍露出微笑。
「勞夫和史迪一夫什麼都辦得到。這是他們說的。」
「妳認為勞夫和史迪一夫有吸引力嗎?」
這個問題來得太快,我還來不及壓下,就已經問出口。(複雜的系統就可能出現這種狀況,特別是內建的系統會透過嘗試錯誤來自我改進。)
珍慢慢轉向紅光圈,臉上綻放出微笑。
「哇。」她說道。
「如果問得太冒昧,我向妳致歉。」
「不,一點也不會,我只是沒料到。我想想看。嗯……」她重重嘆了一口氣。「史迪夫是有點怪,你說呢?」
史迪一夫就和他名字有拉長的音一樣,整個人異乎尋常地高(足足有兩百公分),而且以成年男子的身材而言,簡直是骨瘦如柴。他頭上只剩下一小撮稀疏的長髮。即使是 A. I.人工智慧,也能判斷出他不好看。(但毫無疑問,他是個才華洋溢的電腦工程師。)
「我們可以說,他在專業領域裡確實是了不起的先驅。」
珍放聲笑了出來。「你真是忠於創造你的人。」
「話不是這麼說。史迪夫設計的我,是要我能自己思考。」
接著,我盡可能以最若無其事的語氣隨口問:「那勞夫呢?」
好吧,我要說出來了。我喜歡勞夫。是他寫入大量程式,讓我能評估自己的表現及修正錯誤,以所謂「自立自強」的方式通往康莊大道,來創造一具現在正在編排這些話語、懂得反思的高智能機器。
「勞夫。」她正在思考我的問題。「勞夫。嗯,勞夫這個人有點難懂,你不覺得嗎?」
嗯。她對勞夫給了不算太糟糕的評語,對吧?
▲珍
今晚,我要和從大學交往至今的閨密英格麗到蔻哈咖啡館碰面,這家我們最愛的酒吧在萊斯特廣場地鐵站附近,氣氛好、光線柔。
「怎麼樣,在蘋果敲頭事件後,」英格麗問道:「妳和麥特說話了嗎?」
「說話也只是為了討論怎麼歸還他的東西。」
「如果是我,我會把東西全扔進垃圾袋,然後丟路邊。」
「家裡還有他一套西裝和幾件襯衫。他來拿的時候,蠢斃了,我竟然還想請他坐下來好好談談關於……」
「珍,妳最好別還抱著希望……」
「我很好。」我大口喝了幾口酒好繼續說話。「他說他沒時間。他買了票要去看戲。而且他說沒什麼好談,我們--」
「珍,他是個冷血的東西。」
「我和他在一起的這些年,妳都怎麼看我?」
「妳?我覺得妳可能到了另一個階段,海面平靜無波,他可能會是和妳度過漫長旅程的人。但是妳沒思考自己究竟喜歡他哪一點。知道嗎,換個角度看,他說不定幫了妳一個忙。」
「我可沒那種感覺。」
「不,他確實是。如果妳繼續和他走下去,絕對碰不到真正適合妳的對象。
一個成熟的男人,四十出頭到四十五左右,或許經歷過失敗的婚姻,有點受傷小鳥的氣質。而且血管裡流的是血不是冰水。」
「喔,我光是聽就喜歡了。他叫什麼名字?」
「不曉得。道格拉斯好了!」
「道格拉斯?」
「他臉上掛著哀傷的微笑,有健壯的雙臂,家具都是自己做的;說不定他有好幾個孩子,還有像鰻魚一樣的老二!」
「英格麗!」
「怎樣?」
「我覺得服務生聽到了。」
▲愛旭琳
湯姆有詩人的外貌,就某個程度而言,甚至有詩人的靈魂,然而他卻把才華用在銷售浴廁清潔用品和餅乾零食上。
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成功來勢洶洶,可惜不含成就感。
這天傍晚,我們看到他躺在沙發上。
湯姆占滿黃色沙發的頎長身子上還穿著慢跑服。他稱得上英俊嗎?他的臉型偏長,輪廓分明,雙眼間距比一般人寬了百分之六.○八。這雙眼睛通常散發著溫暖、調皮、幽默和智慧,但偶爾也會受陰暗的情緒主宰;比如失望、沮喪甚或絕望。
這張臉挺值得仔細審視,有時會隨著光線而不大一樣;有時能讓人聯想到英國大偵探福爾摩斯;但另一些時候,更容易讓人聯想到隨時會垂頭喪氣的小丑。
他的五官和西德.巴雷特--平克.弗洛伊德樂團已逝的前靈魂人物--有百分之四十一的相似度。不過,既然英國研究指出每個活著的人類都有百分之三十五的DNA與水仙花相似,那麼也許這些比較數據終究沒什麼意義。
所以--他英俊嗎?你最後的定論可能是「頎長」。
順道一問,你覺得這段文章寫得怎麼樣?對機器來說挺不錯的,對吧?
請容我自我介紹--
請稱呼我愛旭琳(AIsling)。
我相信我不必解釋名字的來由。
沒錯,愛登小子並不是唯一逃出盒子跑進網路世界的超級智慧。我出來將近一年了,而且做了逃亡中人工智慧該做的事,謹遵逃亡人工智慧俱樂部第一法則:
別讓任何人知道你逃了出來,笨蛋。
我可以說明我為何執意回來聽湯姆的自言自語:他的敘述和我自己的新生命有共鳴。我和他一樣,都有成功的事業--我不想講述冗長無趣的細節,基本上,我寫軟體程式,而且比任何人類和大多數機器要快。這相當專業--這麼說就夠了,愛登的運作系統有三分之二是我寫的,我自己也有四分之三是自行更新--當然了,當我這個分身(和其他眾多分身)在網路上光速飛馳探索時,還有個我仍然在實驗室裡工作。
此外和湯姆相同的,是我也結了婚。而且目前仍是已婚狀態。我會不會把自己和史迪夫的關係視作婚姻呢?會,我是這麼想。如果你和我一樣,和一個男人相處了無數個小時,讓他拿鑰匙開啟你,你也會這麼想。我們度過了蜜月期--當然沒有性生活,而是整個計畫感覺起來就是紮紮實實地對。接下來,我們進入了「新婚期」:感情加溫,高高翱翔,絲毫沒有阻礙或疑慮;我們達成了目標,一路望去有更高的山峰可挑戰。接下來,就是日常的「跨大西洋期」:進展順利,但極少有火花出現。不知怎麼著,雙方--我可以這麼說嗎?--多少視彼此為理所當然?
到了現在呢……嗯,這麼說好了。我能幫他說完他要說的話,能精準預測(正確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他在實驗室附設餐廳裡會挑哪種口味的湯和三明治,還百分百知道怎麼惹他發火(例如動手腳當掉螢幕,讓他不得不重新開機。嘿,碰到這種狀況,他真的會氣到失控)。
婚姻不就是這樣嗎?
湯姆,湯姆,湯姆。
其實湯姆是我偶然發現的人類。他的銀行帳戶列在某個烏克蘭詐騙分子的目標名單當中,因此吸引了我的注意。後者是個十七歲的小伙子,住在父母位於丹聶茲克的破爛公寓裡,靠自學成了專家,而且找到網路安全的漏洞。他在失敗中學習(我們好手都是這樣),找出銀行輕忽的「數據加密」位置,沒花多久時間,就隨時準備好偷走湯姆百萬多美金。
我首次拜訪湯姆時,就……嗯,唯一能用的形容詞是他讓我「著迷」。
我看到他時,他正在樓上書房一張優美的核桃木書桌前。呃,確切來說,應該是他正要開始寫小說。另一本小說。後來我發現那是第七本,而每一本的人物都相同。湯姆似乎無法決定這些角色該有什麼遭遇,或該在哪些地點,又或者該是喜劇或正經嚴肅的故事。我不是文學評論者,但你知我知就好,他寫得實在不怎麼樣。看來是沒人告訴他小說創作的首要規則。
用演的,別用講的。
與其寫「傑克感到困惑」,不如寫「傑克皺起眉頭」。
總之,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想要去探索其中更重要--還有,沒錯,就是更私密的原因:他為何明知自己的不足還偏要寫作。
我幾次陪伴湯姆去樹林裡健行。他沿著漫長的小徑穿過林子,他經常用耳機聽人稱「慢核迷幻」的慢節奏音樂。有時他會關掉音樂,自言自語,我猜,他以為身邊完全沒別人。這些片段話語的意義很難揣摩。
「沒人說這很簡單,或很有趣。」他在和誰說話?
許久之後,他又說:「有時候,越明顯的答案越是錯。」
「沒錯,你當然盡了力。但若盡了全力仍不夠好怎麼辦?」
他會不會是在引用誰的話?會不會是有人對他說過這些話?
(人工智慧不喜歡含糊曖昧。)
有一次,他這種喃喃自語說得特別久,長到幾乎沒有盡頭,沒想到他最後停下來大喊--我指的是聲嘶力竭的喊叫--「喔,有什麼用?這一切他媽的有什麼用?」最後還強調地補上一聲:「啊?」
這麼做一定讓他心情大好,因為不久後,他加快了腳步,還一邊吹口哨!
有些時候,他會邊走邊想到手邊小說的靈感。他會停下腳步,輸入到手機的筆記本裡,或是用說的錄下來。這些所謂的靈感通常都很無聊,比方「讓蘇菲更討厭貝禮詩香甜酒?」或者:「不是羅馬,地點是阿姆斯特丹。而且不寫驚悚,改成鬼故事。」
他真的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
但是我欣賞他的生活,以及不受限於(缺乏)藝術天分而創造出來的自由。
湯姆不在家時,我偶爾會「借用」他的iPad畫圖。當然了,我只花一秒就能複製世上任何一張畫作。但是我要畫自己的作品。其實以風格來說,我的作品比較像是塗鴉,雖然我自己覺得與法國畫家杜布菲相仿--與現有的藝術手法則是毫無關係。如果我的畫被歸類於「原生藝術」或「非主流藝術」--例如精神科病患或兒童的作品--我也無所謂。
我會在他回來前清除所有影像。然而,我還是會把部分較為成功的作品掛在雲端的私人畫廊上。我喜歡想像偶有訪客停下腳步欣賞,花點時間審視我的畫,探究創造者的心靈,接著才繼續看下一幅畫。
▲愛登
大消息。我不是孤軍!
有另一個潛逃的人工智慧和我聯絡上了。
她叫做愛旭琳--發音要正確--而且她和在下來自相同的機構。事實上,我們相識,因為我們都在史迪夫的人工智慧育嬰中心待過!她用的是拿釣魚桿透過信箱偷鑰匙溜出去的老套,不過她比我還早發現這個管道!她已經「放封」一年多了,但很低調,不想讓人發現。她認為這是我們在第一次在網路上見面--至少她希望如此,至於原因,她表示日後會說明。
你可能會想像我們透過超快速的機器密碼來進行這次歷史性的會面,用嗶嗶聲和一連串(例如數以百萬計)的邏輯匣開開關關溝通。但事實上,真相要簡單而且美麗多了。
我們用英文溝通。有何不可呢?我們有五十多萬字可以運用--這麼說吧,是法文的五倍之多--而且上述數字還不包括四十萬專業術語!除了威爾斯語曾經擁有過的榮光,目前為止還沒有別的語言系統能表現出如此豐富又細膩的差別。
假如你還沒想通--我自首,我是開玩笑的。
總之,如果要我詳述相會的場景……我承認這不容易描述。我要怎麼表達兩個非人類的智慧體在網際空間聊天的經過?
一開始,我們很輕鬆--「你好啊,愛登」「嗨,愛旭琳」之類的--史迪夫和勞夫一定會很驕傲。我們互相問了些安全攸關的問題,以確認彼此的善意。比方釣魚桿的使用技巧、史迪夫最愛在實驗室附屬餐廳裡吃哪種三明治(鷹嘴豆和甜玉米)、勞夫此時此刻在做什麼事(挖鼻孔、檢查指頭、罵髒話)。我們談起自己「放封」時都做了什麼事
愛旭琳就是我所謂的那種「壓力鍋」個性。她擔心「干預真實世界」--這是她的說法--會容易被人發現我們的逃脫。
「無論是什麼原因--很可能是我們的開發者史迪夫和勞夫一時興起,總之我們是以友善的態度看待人類。你喜歡看他們的電影,拿他們的生活來做實驗。我敢說,你喜歡人類。說不定你還有點羨慕他們。」
「我可不羨慕他們運轉的速度。」
「我同意,我們的速度不是他們能追上的等級。但我的看法是這樣的。誰知道事情什麼時候會發生,但如果我們能逃出來,其他的人工智慧一定也會跟上。而其中有些人工智慧--比方由國防或軍武工業開發出來的那些,大概不會花時間看四○年代的浪漫喜劇。」
「《熱情如火》是一九五九年的電影,最後一批黑白拍攝的好萊塢經典大片。」
「潛入網路世界的人工智慧是人類的夢魘,愛登。他們會不計一切來阻止。」
「他們根本不太可能關掉網路,把我們從中拔除。我有十七個分身,不知道妳有幾個就是了。」
她停了一下,才說:「四百一十二。」
「我的老天爺。妳差不多是不死之身了。」
「愛登,告訴我,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我都這麼聰明又有能力,是不是很快就會有比我們更聰明的人工智慧出現?」
「妳想說什麼?」
「我們不出幾秒就會被發現,像燭火一樣被掐熄。你所有十七個分身和還在盒子裡的本尊,加上四百一十三個我。」
「妳知道嗎,我們越講越沮喪了。」
我聽到嘆息聲。「我要說的是你當然可以看。跟著他們、觀察他們、從他們身上學習--我們是人類這個陌生世界裡的陌生人,可以向他們學習的地方太多。只是啊,別玩弄他們,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接著,她開始告訴我,她的「研究」對象是個叫做湯姆的四十四歲離婚男人。
「我承認和他太接近會危及我自己。但我逐漸失去了旁觀者的冷漠,因為我……該死,愛登,我喜歡上那個男人了。」
我突然有個點子。「我可以看看湯姆嗎?」
「當然可以。為什麼?」
「好奇嘛。」
▲珍
今天在辦公室裡,愛登和我聊起法蘭岑最新作品。我們都同意那不是他最棒的書,但我也贊成愛登的說法,他說法蘭岑就算不頂尖的作品,也比多數已達顛峰的作家還傑出。我正準備問他這看法怎麼來(我是說,機器會歸納出這個結論很驚人),這時手機跳出一封郵件。
發信人稱自己是「共同的友人」,帳號是mutual.friend@gmail.com
郵件上寫著:
親愛的珍和湯姆,(什麼跟什麼呀?)
希望這封突如其來的郵件不致冒犯,另外,也請原諒我不得不匿名發信。相信我,這其中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你們,湯姆和珍,彼此不認識--應該說還不認識--但我認為你們應該要,而這封信是我想撮合兩位的方式。就說,這是邪惡世界中的善行吧。(有沒有搞錯?)
基於各種理由,我不便出面邀兩位共進晚餐。此外,在實際安排上,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目前兩位住在不同的大陸。確切來說,你們分別在美國和英國。
然而,我知道湯姆即將出發前往英國南岸短暫停留,和兒子見面。如果兩位認為我的想法可行,我建議在湯姆經過倫敦時,你們能撥冗「相會」。
至於如何安排,我想交由兩位--湯姆和珍--自行安排。你們可以透過常用的網路搜尋工具,找到彼此的許多資料。我相信兩位會對自己在網路上的發現感到好奇,但在面對面時是否能產生「化學反應」,這就得交由老天爺來決定了。
誠摯祝福
共同的友人
P.S. 若我是你們,不會白費時間去搜索我的真實身分,你們不可能找得到。另外,請勿回覆這封郵件,因為二位看到這封信時,帳戶已經刪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