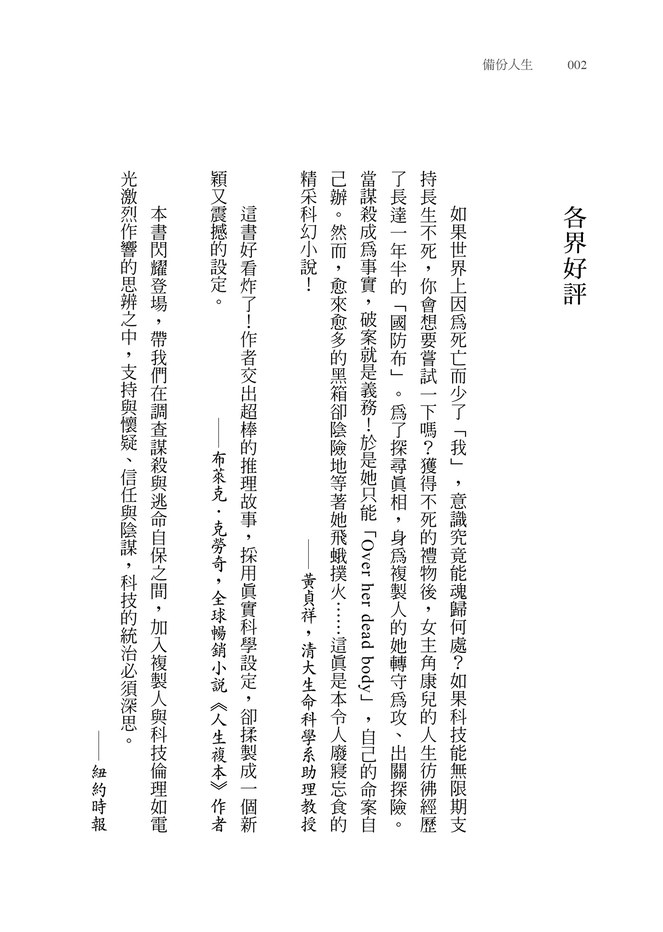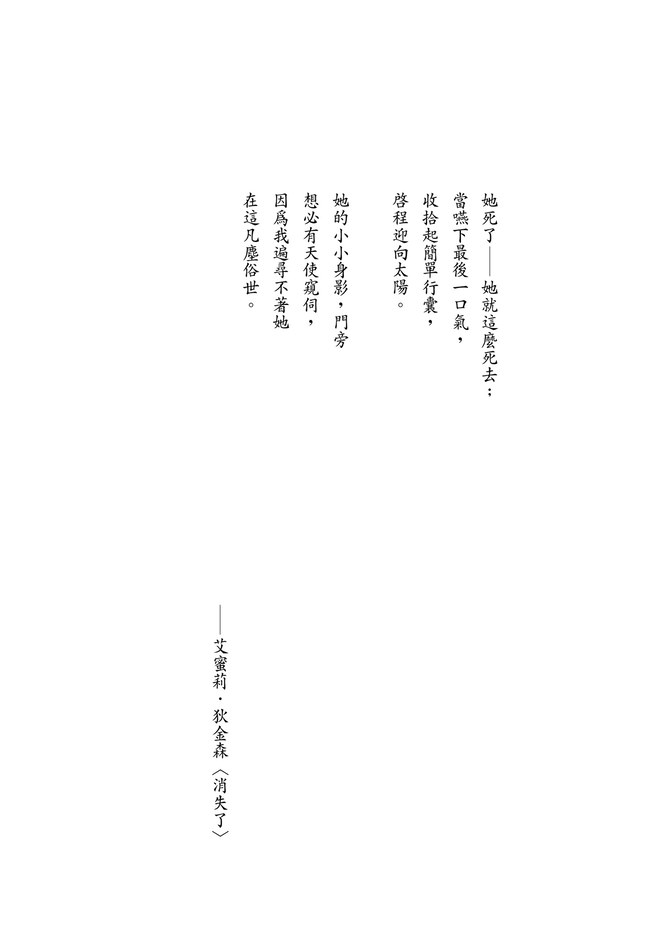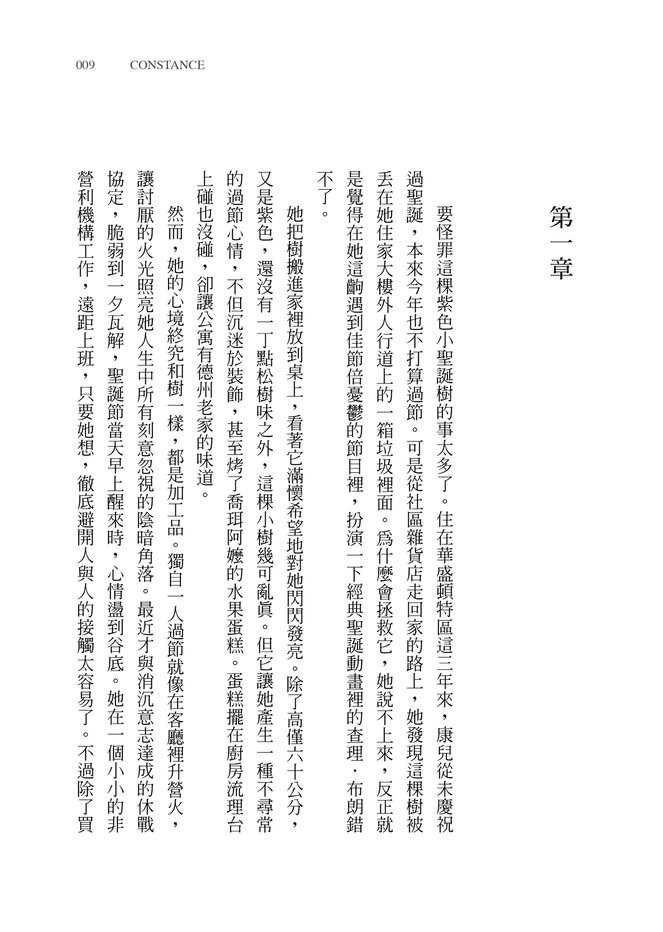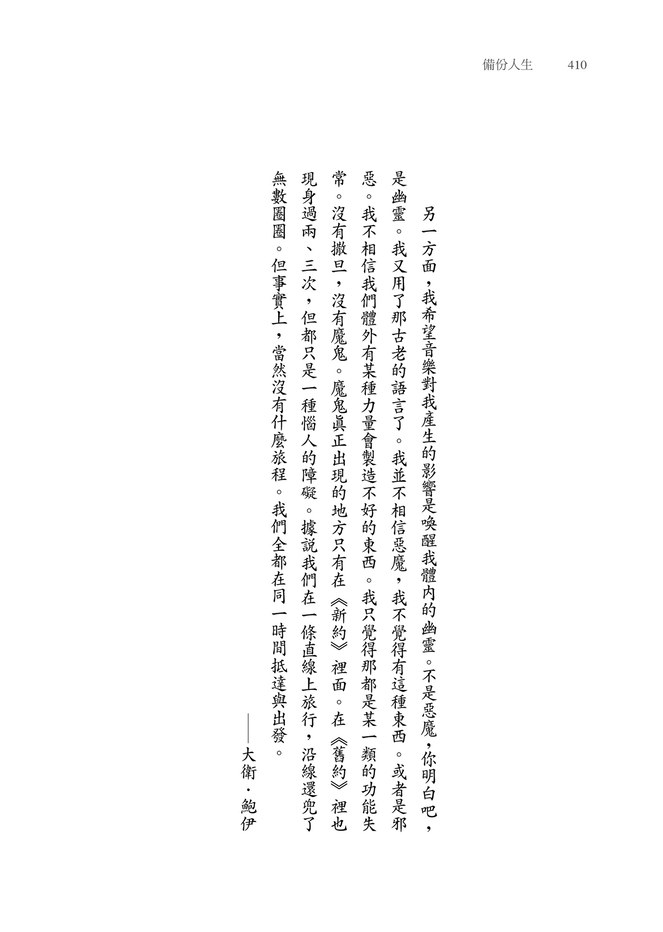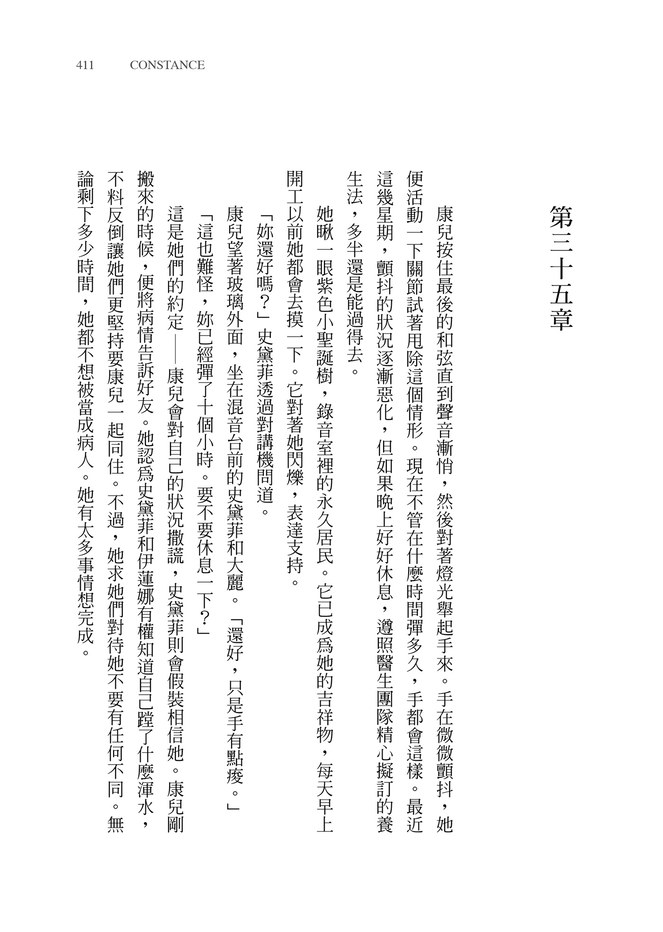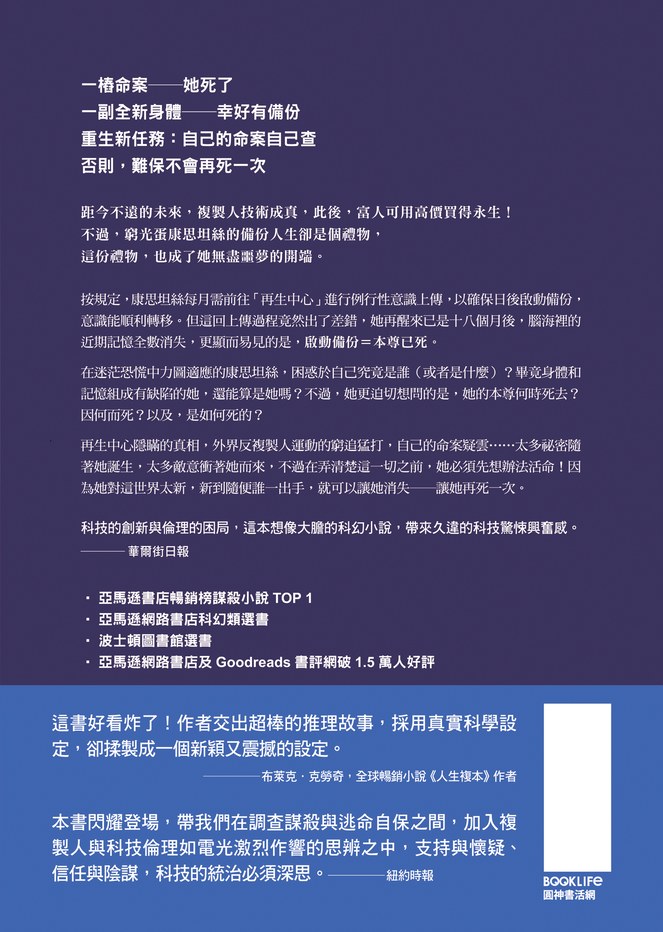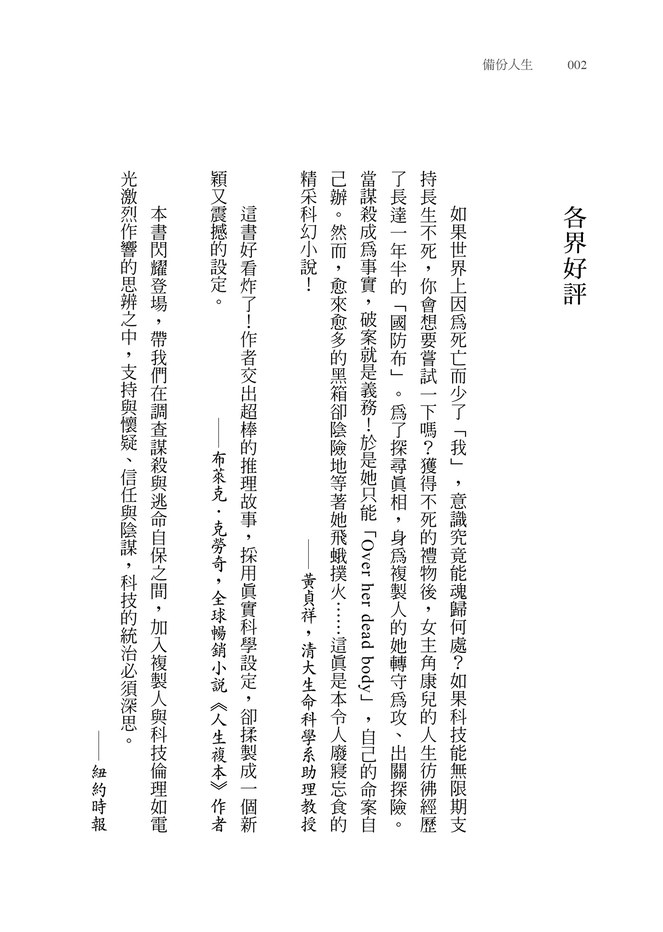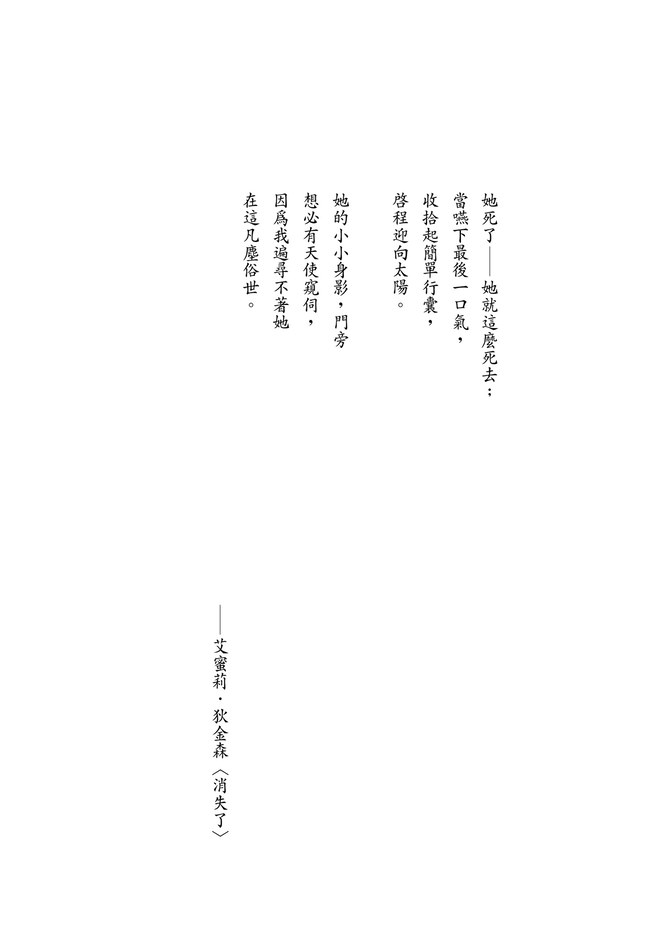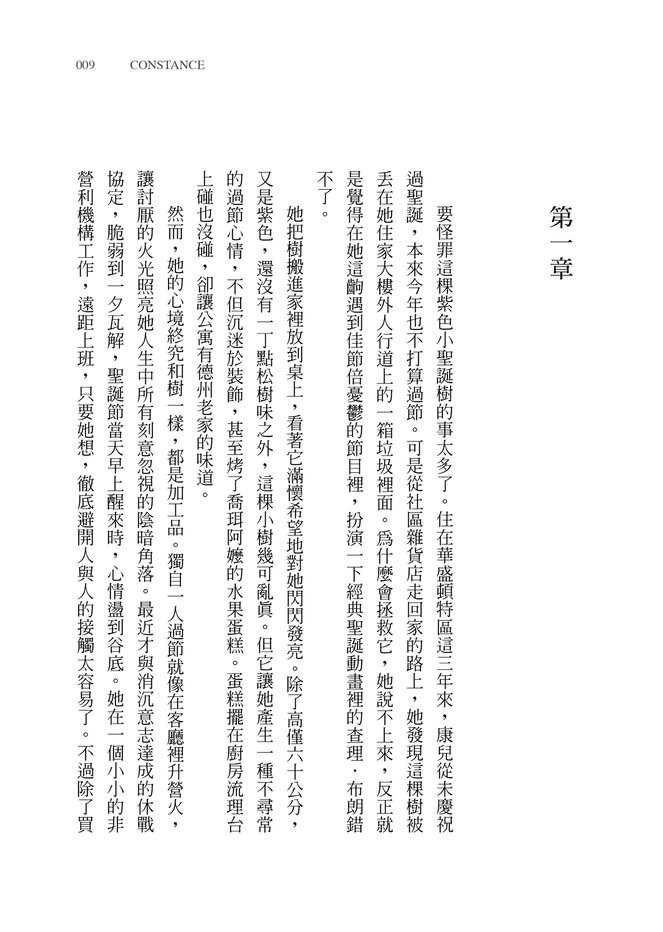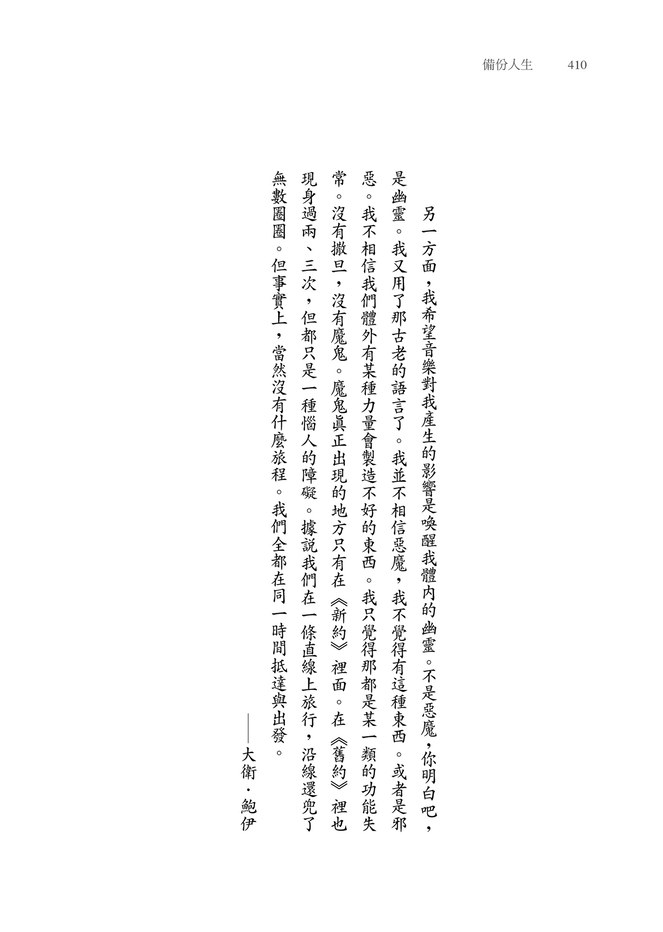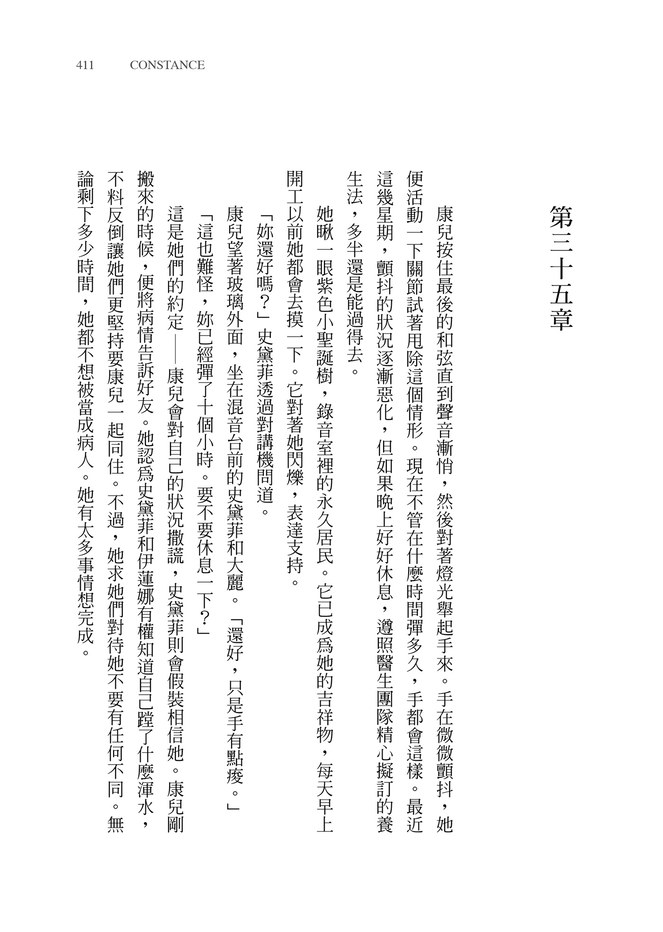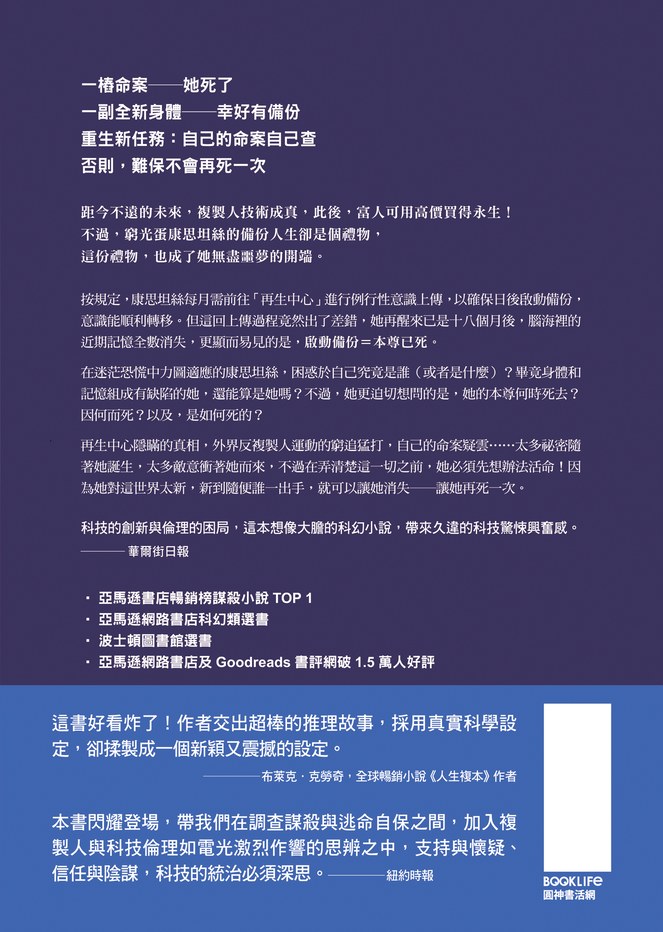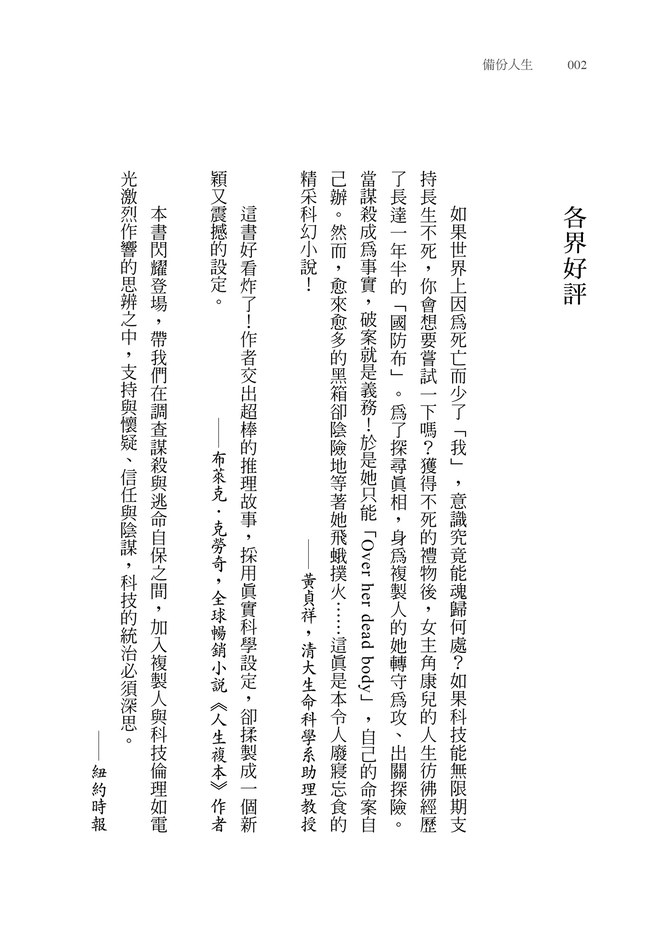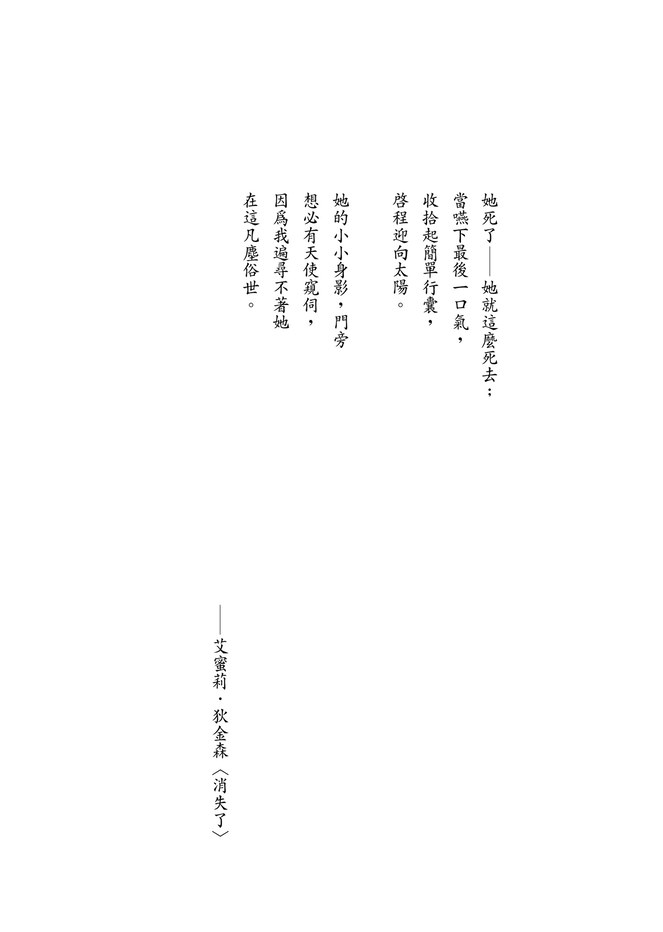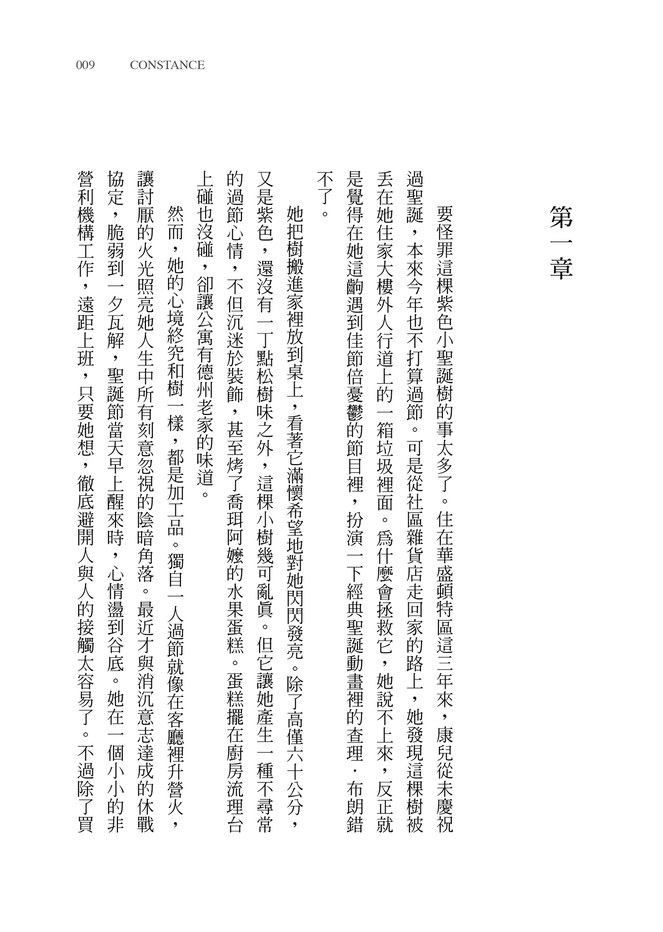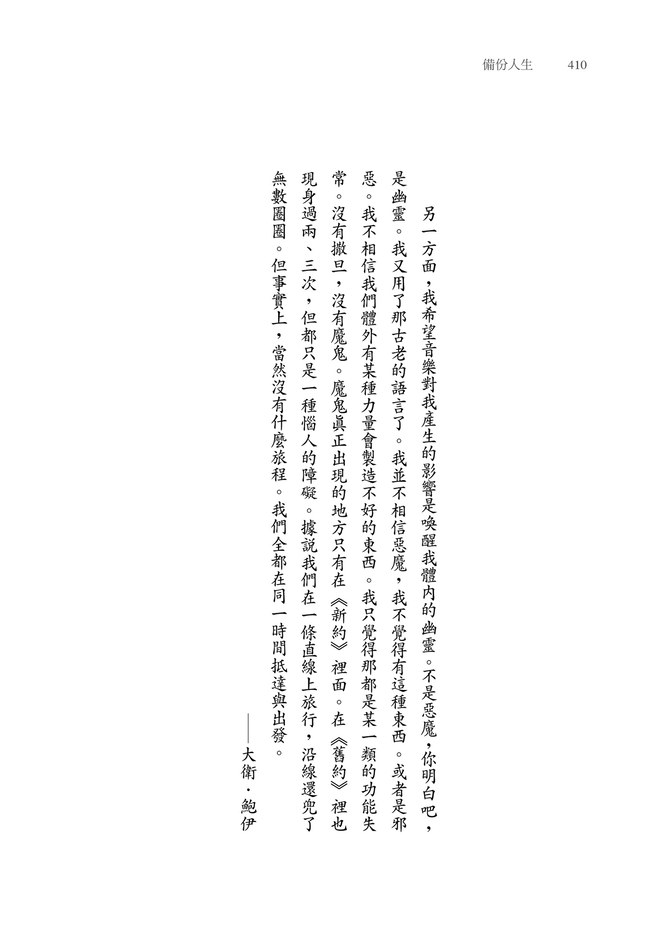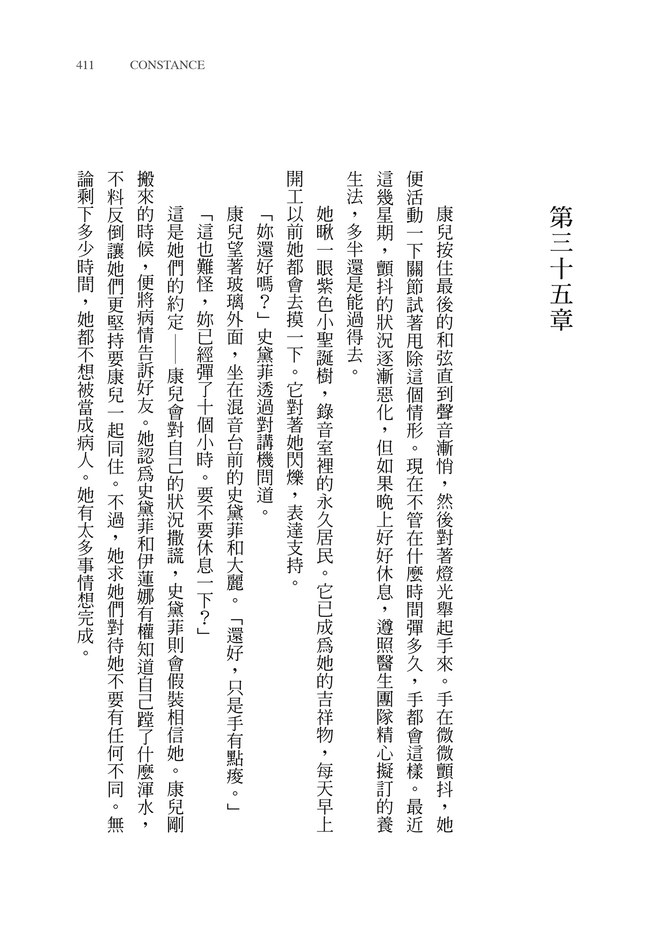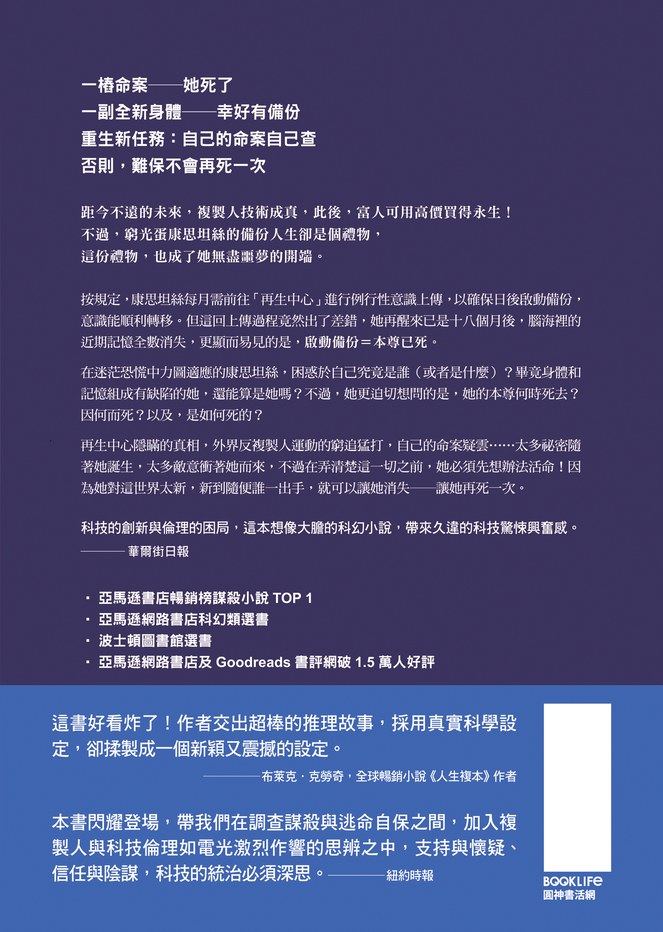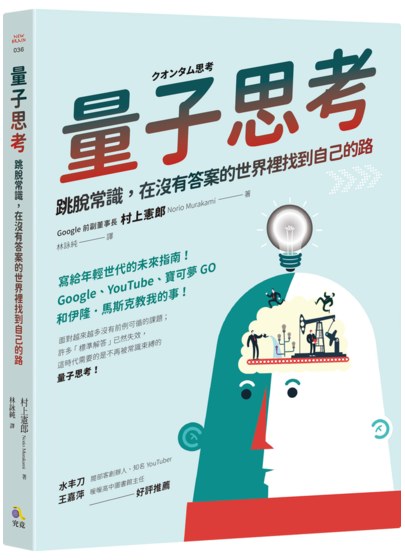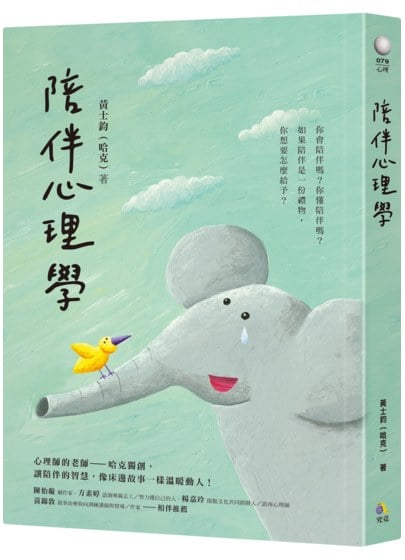今天,二○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天氣晴朗無雲,最高溫大約三十五度。
又是酷熱的一天。已連續第八天,但距離華盛頓十二月底的高溫紀錄還遠得很。行事曆提示康兒今天得上再生中心。她呻吟一聲翻身側躺,想換個舒服的姿勢睡回籠覺,卻是徒然。每個月例行的更新時程已經過期,她想起自己是特意約在聖誕節隔天,診所都沒人的時候。她這是自以為聰明,殊不知這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才上午十點,氣溫卻已超過三十二度。再生中心外擠滿抗議人潮,以挑釁、裂帛似的聲音高喊口號,康兒奮力擠過這群凶神惡煞般的民眾。她刻意安排聖誕節隔天回診,就是希望能平靜一回,不料抗議群眾聲勢未減,人數恐怕是她先前所見的三倍之多。也許放假期間,他們也無處可去。
抗議群眾不分晴雨從不缺席,他們縮擠在黑傘底下,使得黑傘成了此次運動的非正式象徵。這些人是「亞當之子」──美國境內唯一且最大規模的反複製人組織──的突擊隊。他們會放哨監視全國每一間再生中心,可是對於位在華盛頓的這個總部特別情有獨鍾。在他們看來,這裡是起點,是複製人技術的發源地。此一族類便是在這裡開始脫離人性。
群眾忽然開始交頭接耳,雨傘激動搖晃──診所的前門開啟。大家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有顧客到了。兩名白人警衛走出大門來到陽光底下,二人都穿著防彈背心,沒有走離大門太遠,只以目光在人群中找尋康兒。
她不敢大聲喊他們,總之暫時還不敢,得等她離得更近、更近以後。萬一抗議民眾發覺敵人就在他們當中,她知道他們會有何反應。診所大門極少使用,因此堅守在此抗議只是更添沮喪且徒勞無功,他們想必是迫不及待要展現內心的憤怒。康兒將帽沿拉低,蓋住眼睛。其實應該沒有人會認出她來,但光想到這個可能性就夠她害怕的了,她還拍下每個月回診時的穿著,以免重複穿同一套衣服。
群眾蜂擁上前,康兒被人潮托離地面,一時間無法呼吸。她已經歷過夠多衝撞場面,知道不能對抗人潮,較安全的做法是順應潮流、保留體力,等待機會游向岸邊。
「不分娩,沒靈魂!不分娩,沒靈魂!」
「上帝不要你們!」
「高級假肉!」
群眾每喊一句就往前一步。依法,抗議人士必須與診所大門保持十二公尺的距離,但警察大多支持示威行動,與其強制民眾嚴守法定緩衝區,還不如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通常這也不打緊,負擔得起再生中心費用的人不會徒步前來。這裡的顧客都是有九位數身家的富人,為了避開大門外的一切醜態,他們寧可使用隱密的地下停車場。
當然,康兒是例外。她的戶頭存款極少破三位數,甚至有些時候還只是勉強破兩位數。上一輛速克達被偷之後,她甚至沒錢買一輛新的二手車。所以每個月要準時回診的話,她只得冒險跑一趟,別無他法。倒不是說她現在真的還能「跑」,只是內心仍存有些許鬥志罷了。她張開手肘推擠過人群中的縫隙,從抗議隊伍的最前方鑽出來。大門,以及警衛的安全防線,就近在咫尺。
康兒企圖逃離,一面蹣跚地走向大門,一面暗自乞求重建的膝蓋別卡住。示威者發現受騙,發出怒吼。那是一種屬於史前的可怕聲音,康兒振作起精神抵擋抗議群眾的手,以免被拉回魔掌中。這是她最痛恨的部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真是諷刺,想當初她有多熱愛登台啊。她曾經面對多達五千名的觀眾演唱,而現在這群人頂多為數四百,卻讓她緊張到胃揪成一團。但就在此時,警衛看見她後急忙上前,一人架住一條手臂,將她從嗜血咆哮的群眾間匆匆帶入診所。
隔音大門在他們身後緊緊閉合,抗議者的喧囂聲沉靜下來。在倏然降臨的安靜中,康兒面帶疑惑地看著警衛。
「外面是怎麼回事?」她邊喘氣邊問道。
「妳沒聽說?」較高的那人說:「艾比蓋兒.史提克林昨晚死了。」
「死了?」他的搭檔說:「你是說她沒帶降落傘就跑到門羅飯店去定點跳傘。」
康兒聽到消息驚愕不已,但這也說明了為何今早有那麼多抗議者。艾比蓋兒.史提克林博士,複製人技術之母兼再生中心的共同創辦人,一再出現於無數陰謀論中的妖人,死了。自殺身亡。對「亞當之子」與認為無性生殖技術令人髮指的任何人而言,這應該是值得慶賀的勝利日子。
「要不是沒帶降落傘,就是女巫忘了帶掃帚。」前一名警衛說。
他的搭檔暗笑,同時吹了一聲口哨,像是有什麼東西從高處重重落地。康兒不發一語走開來,警衛也不再出聲,沉默地跟隨在後。很好,她心中暗想。艾比蓋兒或許是備受爭議的人物,但她同時也是康兒的姨媽。所以說,這兩個碎嘴傷人的警衛,去死吧。不過諷刺的是,康兒對姨媽也有類似想法,除了媒體上看到的訊息外,她對這個女人幾乎一無所知。
上一次見到姨媽是在父親葬禮的騷動中。儀式舉行前,她母親與姨媽爆發了激烈爭執。直到今天,康兒仍不知道母親為什麼大動肝火,但從小在母親身邊長大的她知道,未必真的有什麼大不了的原因。史提克林家是個大家族—兩個姊妹四個兄弟—隨時都能享受選邊站的樂趣。康兒的舅舅們都聯手支持喪夫的寡婦對抗艾比蓋兒,大家一致認為她自從去波士頓念書以後就很會裝模作樣,也認為她對於仍在理論階段的複製人技術感興趣是犯了傲慢自大之罪──卑劣地玷汙了上帝的構思。
到最後,連艾比蓋兒自己的父母都不歡迎她到家裡來。她的名字再不曾被提起,甚至到後來,大家都當作沒她這個人。康兒對姨媽的認識若非從媒體上得知,就是從喬珥阿嬤那兒聽說的。打從一開始,喬珥阿嬤就根本不想和史提克林家有瓜葛,她兒子何以追求瑪麗始終是個謎。也許正因如此,她才會欣欣然回答孫女無法去問其他人的問題。
對於家人的迴避,艾比蓋兒自己倒是泰然處之,從此離開德州西部,再也沒有回來。六年後,康兒為了反抗母親的嚴格期許,離家去和喬珥阿嬤同住,多少也是受到這位姨媽的啟發。她決定效法姨媽離開連茲柏勒市,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只不過她要走的是音樂之路,不是科學。姨媽奮鬥的結果十分可觀,聞名世界又富可敵國,然而她再也沒有和家人說過話。
一句話都沒有。
直到寄來了信。
兩年前,律師帶著法律文件登門拜訪每一位家族成員,為每個人贈送一個複製人。康兒不得不敬佩姨媽。一個複製人市價多少?兩千五百萬、三千萬美元?家族裡的人從來都沒什麼錢,所以在外人看來,此舉應該是慷慨又奢侈到極點。然而對家人來說,艾比蓋兒是故意送上一樣他們絕不可能接受的東西,藉此炫耀自己的成就。
假如家人對姨媽的意圖有絲毫懷疑,她附上的信函便是清償宿怨的絕佳代表作,信中徹底清算了數十年來撕裂家族的憤恨之情。那最後一句話,康兒每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但願我這份小小心意能讓你們所有人活得長長久久,一起在你們庸碌的人生中打滾。看來,康兒的媽媽並不是家族中唯一會記恨的人。
康兒是唯一接受姨媽餽贈的人,儘管這份禮物以一句加強語氣的「我操」包裹著──但也或許這正是康兒接受的原因。有一個脾氣火爆、身為福音派教徒的白人媽媽,和一個在軍中任職下士、黑人與越南人混血的爸爸,康兒在成長過程中始終像個邊緣人,受盡各年齡層與種族人士的欺凌。求學時期,她必須不斷地奮鬥對抗。由於身材嬌小,勝算不大,反而讓她學會了求生之技。在她雙親的家族裡都蘊藏著一條名為「頑固」的豐富礦脈,康兒從中採集出能容忍一切的意志力。她咬緊牙根,依循以下三個簡單守則捱過艱辛的童年:絕不當眾哭泣;絕不求助;絕不、絕不讓他們知道她心裡難過,以免稱了他們的意。
因此在收到姨媽那封嘲諷的信時,康兒立刻認出這份贈禮的霸凌氣味。她將信撕毀,接受了複製人,儘管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想要它。
自從康兒到了華盛頓,姨媽一次也沒來找過她,即便當她住院動完腿部接合手術後的療養期間也不例外。還有這兩年,就連她不斷來再生中心更新上傳資料,艾比蓋兒姨媽卻連從實驗室出來打聲招呼都沒有。再生中心窗外那巨大的雨傘帳篷在沮喪中顫動,再一次讓康兒想到鳥兒。只不過這次想到的是渡鴉,她童年時期,偶爾會有這種鳥聚集在德州公路旁,等候瀕死的動物放棄掙扎。喬珥阿嬤是怎麼形容渡鴉來著?薄情?對,她暗忖,應該是這樣沒錯。
∪ ∩ ∪
再生中心的特異之處在於,這裡的感覺更像是高級養生會館。康兒被帶領進入的不是單調空洞的等候室,而是一個廣闊的中庭,有感光天窗進行全天候自動調節,室內隨時都是陽光斑駁的破曉時分。瀑布輕輕瀉落嵌在地板中央的鯉魚池內,打在粗鑿的石灰岩壁發出舒緩身心的回聲。淺壁凹處擺放著植物,有種在藍色瓷盆內的鞏膜白色蘭花,也有插在玻璃瓶裡的柳枝。全然看不出在這棟建築物深處,正有人按部就班地改寫自然法則。
中庭沒有服務台,但康兒已熟知作業程序。她耐心地坐在池畔,用指尖撥弄水面,看著橘黑色相間的魚群在碧綠荷葉底下嬉戲。由於好奇世人如何看待姨媽的死,康兒便在LFD上搜尋相關文章。接下來幾個星期,應該慢慢會有艾比蓋兒.史提克林如何影響美國生活的長篇評論出現,但如今才短短幾個小時,因此大多數新聞媒體都只針對自殺進行重點報導。內容大要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晚間十一點三十四分,頗具爭議性的複製人發明者艾比蓋兒.史提克林,從歷史悠久的門羅飯店頂樓跳樓,結束了自己的性命。據目擊者指稱,史提克林博士原本坐在可俯瞰白宮的熱門餐廳『天際線』的酒吧內,邊與酒保聊天邊喝著香檳。結帳後,她爬上頂樓,跳樓身亡。」另有一些餐廳監視器畫面的影片連結,但康兒一個也不想點進去看。
有一篇文章寫道,艾比蓋兒一生未婚,與家人也不親近。這話講得真是輕描淡寫,康兒暗忖。另一篇說她姨媽最近幾年受憂鬱症所苦(這又是一個她們倆的共通點)。文中繼續提到,艾比蓋兒小時候曾被診斷出罹患威爾森氏症,這種罕見的遺傳疾病會導致銅堆積於身體與大腦。雖然病況可用藥物控制,銅卻會干擾人的複製過程,因此該文章以不得體的幸災樂禍口氣解釋,艾比蓋兒不同於再生中心的客戶,她是回不來了。康兒關掉LFD,不知怎的一時間忽然生出想要保護姨媽的心思。
∪ ∩ ∪
遠端牆壁便出現了裂縫。有一道門靜靜地打開,拉蕾.阿斯卡麗隨之現身。她是領有專業證照的護理師,但正式職稱卻是服務員。拉蕾穿的不是醫院的手術服,而是寶藍色筆管裙搭配蛋黃色上衣,亮麗的黑髮高高盤在頭上,只用一支金色髮夾以手術般的精準手法固定住。她的高跟鞋踩在石板地面,幾乎和芭蕾舞鞋一樣悄無聲息。拉蕾精心打扮的復古風韻令康兒讚佩不已,這樣的穿搭她駕馭不了,但拉蕾卻彷彿駕輕就熟。康兒是個暗黑藝術大師,總是一副酷樣,好像根本不在乎穿著。女性當然分辨得出其中差異,但男人從來搞不清楚。
「嗨,康思坦絲!聖誕假期快樂。」拉蕾說話混著英國與伊朗的口音,軟得像絲。再生中心引以為傲的就是個人化服務。從康兒第一次約診,拉蕾就是她的服務員,後來每次接待她都熱情地有如意外重逢的老友。只不過康兒的朋友都知道不要喊她康思坦絲。康兒恨透這個名字──這是母親那邊的家族傳統,老喜歡替女生冠上一些老派的名字。
「關於妳姨媽的事,我真的、真的很遺憾。」拉蕾說:「如果妳想重新安排時間,絕對沒問題。」
「我沒事。」康兒說,但其實她有點嚇一跳。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以為診所裡沒人知道她和創辦人之間的關係。在此之前,拉蕾從未提起過。
「我明白。只是萬一更新過程因此搞砸了而必須重來一遍,實在有點可惜。」
要製造出精確的人類意識影像,受試者必須欣然同意並保持心態平靜,再生中心在簡介時曾不厭其煩地一再強調這點,但康兒看不出這與目前的情況有何關聯。她和姨媽又不是多親近。
「講真的,我其實從六歲起就沒見過我姨媽。沒錯,這是令人傷心的事,但不至於擾亂我。我並不是很認識她。」
拉蕾點點頭,帶她進入更衣室。在更新康兒的神經訊號紀錄期間,她的衣服會整燙好等著她。乾洗牛仔褲和T恤似乎有點誇張,但這是附加服務,不要白不要。
康兒穿上開背式的反穿病人袍,接著套上刺有診所花押字的浴袍與拖鞋。她愛極了這裡的浴袍,彷彿被溫暖的雲朵包裹著,要不是體積實在太龐大無處藏匿,她早就偷一件回家了。有趣的是,康兒非常確定拉蕾會很樂意送她一件,只是她拉不下這個臉。她如此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貧窮,以至於無法開口索取禮物。
回到中庭時,拉蕾將康兒安頓到一張豪華舒適的扶手椅上,並用LFD傳送今日菜單給康兒。康兒的視野中跳出菜單,儘管已經知道想吃什麼,她還是很快地看了一下。在現實生活中,康兒無法盡情大啖壽司,但再生中心請了一位廚師。他們從不使用食物列印機,而是提供道地的養殖鮪魚。她點了彩虹壽司捲和毛豆。如果可以,她真想來點熱清酒緩和緊張情緒,只可惜進行更新前十二小時內不許喝酒。
「修個指甲?」拉蕾問道。診所提供許多舒適服務來轉移客戶的注意力,讓他們暫時忘記來此的真正原因,美甲便是其中一項。最好還是專注於新燙好的衣服、舒服的浴袍和日本錦鯉那安撫人心的美。她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漸漸接受昏迷之際有人碰觸她,不過一醒來就有修得美美的指甲,怎容錯過。
「我想上個淺橘色好了。」
拉蕾微微一笑。「我過幾分鐘回來,妳就先開始吧,好嗎?」
每次更新前,總有同樣的表格要填,同樣的免責切結書要簽。一頁接著一頁全是類似的法律用語,枯燥乏味。拉蕾將表格丟到康兒的LFD,便即離去。康兒脫去拖鞋,盤腿而坐,打開第一頁,她被告知上一次更新是在四十四天前。接著一份詳盡、老套的免責聲明跳了出來,宣稱再生中心強烈建議兩次更新的間隔不要超過三十天,以避免複製人產生神經與心理上的併發症。假如客戶意外早逝,而且距離最後一次更新已超過九十天,再生中心將不會使其複製人重生。這段話等於是用法律術語在說,你倒楣到家了。康兒跳到最底下的框框打勾,證明她已閱讀並了解所有風險。
拉蕾回來後放下一個銀托盤,五錠藥丸雅致地排放在餐巾上──《愛麗絲夢遊仙境》式的藥物,能讓康兒的內心處於有利作業的放鬆狀態。即便吃了藥,倘若意識中有一絲不情願,上傳也不會成功,但無論如何藥物能讓過程順利些。拉蕾等到康兒吃完藥又再次離開,說是等康兒填好了表格再回來。
∪ ∩ ∪
「都好了嗎?」拉蕾問道。
康兒猛地抬頭。本該填寫表格的她,竟神遊發呆起來。嵌在眼窩裡的眼睛好像變得太小。
「什麼?沒有,我還沒吃東西呢。」康兒說著指向一個用餐托盤,上頭除了一些薑片和一小團哇沙米之外,空空如也。是誰吃了她的壽司?她環顧四周尋找罪犯。穿著浴袍的老人也不見蹤影了。巧合嗎?康兒皺起眉頭。但在她的LFD上,一道綠色光環顯示表格已完成。她是什麼時候填寫完的?她注意到自己的舌苔變得好厚,並咂咂嘴唇,愉快地聆聽那聲音。
「妳好美啊,」她對拉蕾說:「妳是筆管裙女王。」
放任、無禁忌是藥物的副作用之一,另外還有短期失憶。也許是因為這樣,她才不記得自己已經吃過藥。康兒只恨不得扯掉那支金色髮夾,看看拉蕾披散頭髮在肩上的樣子。
「謝謝妳。」拉蕾溫柔地說,同時蹲下來替康兒穿上拖鞋。
「所以這地方有多爛,妳是知道的,對吧?」康兒小聲地說,像在分享兩人之間的祕密。
「好啦。」拉蕾邊說邊輕聲笑了笑,彷彿在容忍一個在親子餐廳裡脫光衣服的三歲孩童。「該來一趟小旅行了。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康兒拖著長音回答。
她站起身,搖搖晃晃踩不穩,幾乎是跌坐到等在一旁的輪椅上。拉蕾推著她經過一條走廊,只是廊道似乎愈走愈長。又是藥物的作用,使她的視線變得又長又扁平,就像站在兩面鏡子之間。拉蕾緩緩將她推進更新套房,接下來在她通過醫藥評估可以離開之前,得在這裡待上六個小時。
拉蕾將康兒的LFD移除,幫她脫下浴袍。康兒開心地跌坐進人體工學椅,不管再生中心再怎麼試圖掩飾,這椅子看起來就是像牙科診所的診療椅。拉蕾開始設定更新程序,手指在空中舞動猶如彈著鋼琴作音階練習。感測器從頭靠處彎彎曲曲升起,連接到康兒的頸部與頭皮,並像一隻巨大的千足蟲貼靠上她的脊椎。本該是恐怖至極的事,但在藥物產生的安全朦朧意識中,她只覺得有數十根手指在按摩她的背。有一根平凡無奇的平滑柱子從天花板降下來,停在離她額頭約三十公分處。這時康兒聽到輕輕的嗡鳴聲,她的生命跡象填滿了嵌在牆壁的螢幕上,那是房間裡唯一讓客戶感到安心的東西。
喬醫師出現在她手肘旁,問她感覺如何。拉蕾是康兒的服務員,但喬是分院的主管,會親自監督每一次的更新。他連上拉蕾的LFD,再次檢查她的設定。他如慈父般的存在能安撫人心,加上對待病人經驗老到,總能幫助康兒安下心來。無論能得到什麼樣的幫助,她都需要。他們準備上傳她的意識、她的記憶──造就她成為她的一切──的完美影像,儲存在大型量子電腦中,以防萬一她在下一次回診之前死去。
假如她死了,植入在她頸部的生物辨識晶片會記錄她的死亡並通報再生中心,診所便會立刻將她儲存的意識下載到她的複製人,好讓生命能盡可能無縫接軌。康兒想到這裡格格一笑。又是藥物作用。這並不好笑,但又挺好笑。生命會繼續下去。這實在是病態得太好笑了。
「別再出聲了,康思坦絲。」喬醫師說:「記得要正常呼吸。」
「抱歉,醫生。」她說。
「妳同意進行更新嗎?」他問道。
「同意。」
「好,我們幾小時後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