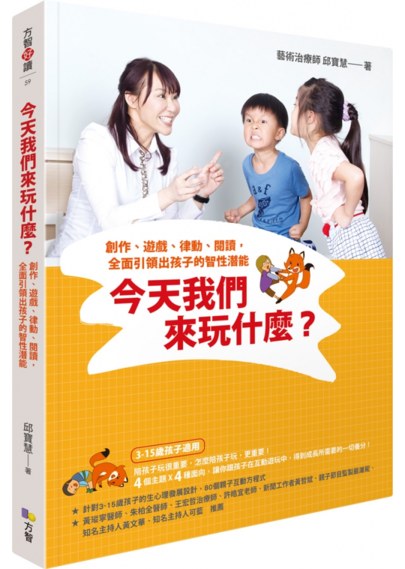<自序>媽媽的乳房──斯土斯民的恩典
一九九六年那個暑假,碧玲受美國政府邀請赴美考察一個月,而孩子們則到員林舅舅家玩。那一個月我獨自在家開始寫這本書,約打了三萬字,把這本書的架構完成。但那時沒有書名,也沒有章節,可說只有骨架,還沒有血肉。之後因為忙碌各種事務,尤其那時我正好投入北投溫泉區的重建與營造,寫溫泉鄉社區營造的論述,是第一要務,就把這本書丟著,一放就是兩年多。
等到一九九九年又拿出來要看時,發現兩個備份磁片都損壞無法閱讀,只好再重新打字,不過這次重寫就準備了比較多的基本資料,這些基本資料例如:(一)泉州安溪仙地西庚許氏家譜、許保贊公派下家譜;(二)烏協公一系全部在日本時代各時期的戶籍謄本;(三)欽地公一系全部日本時代各時期的戶籍謄本;(四)新莊我爸爸所有親人日本時代各時期的戶籍謄本;(五)本書所提到的地名之源流;(六)個人收藏的各種資料如書信、訃文、照片、書法、日記,還有訪談口述筆記……等等。我參照各種資料,將本書所提到的人物,做了一份依時間、年齡順序排列的大事記表,以便書寫時對照使用。當然,收集與研讀這些資料,實在花了不少時間。不過有了這些資料的補充,書寫就非常順暢了,這時本書的字數就擴充到約七萬字的規模了。
二○○○年,我將《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出版之後,接著本想要把本書繼續完成時,我被徵調去擔任忙碌的黨職,接著又去台南市工作,所以這本書就又擱下好多年。二○○八年四月後,烽火連年的外務都告一段落了,我才意識到這本書寫得實在是太久了,趕緊摒除所有外務,在家閉關約五個月,到了二○○八年底,除了先完成一本學術論文外,也把這本書寫到超過十萬字,終於完成了。
其實寫這本書的架構並沒有很困難,因為那是我長久以來的記憶,很多也是我們兄弟姊妹偶爾會回憶的話題。真正的困難,也花了許多時間處理的,是書中我的每一個記憶、每一件事情的細節,還有一些口述資料的查證或確認。謹舉幾例說明:
我的阿嬸是來自日本時代舊名八里坌堡下坡角一百四十六番地。本來我望文生義,以為那裡是位於現在台北縣八里鄉,因為我們小時都稱八里鄉為「八里坌」。後來逐一查證舊名,看了一些學術研究,才知八里坌堡下坡角,位於現在新莊的丹鳳十八份一帶。
新莊老順香糕餅店的地板,我記憶中是糕餅屑不斷累積,以致整個店內地板是黑黑黏黏的,但老順香現在的地板相當乾淨,我也怕我的記憶會有所錯誤,也是專訪了現在的經營者王明朝先生,獲得確認無誤。
民國五十年代台灣漫畫巨星游龍輝先生,已經長年在國外工作。我為了要確認《仇斷大別山》創作的時間與內容,也是費了很大一番功夫,才訪問到游龍輝先生(註一)。而游龍輝先生也贈送我這個癡迷他漫畫幾十年的粉絲幾張親筆漫畫,真是令我喜出望外,讓我非常滿足。我也訪問過小西園的第三代掌門人許國良先生,請教當年新莊戲館巷的情形,才將我模糊的記憶化為詳細的描寫。只是許國良先生,於民國九十三年十月赴泉州洽公時意外身亡,盛年猝逝,令人非常惋惜。
一九九四年初,我曾在新莊市長選舉的一次演講中,請新莊父老代為尋找我小學一年級時的同學張樹木。結果那次演講中的請求居然奏效,一九九八年我在北投溫泉博物館導覽時,偶遇一位曾素月小姐,她說她有去聽那次演講,她們家有人認識張樹木。但我根據她留給我的訊息去新莊找尋後,並沒有找到張樹木。本書完成階段,我靠著網路再度找到曾素月小姐,就這樣我輾轉找到了張樹木先生,也確認書中所寫張素霞是他的堂妹無誤。這樣也某種程度確認我雖與他們離散幾十年,但小時記憶還可算相當正確。
小學三年級時,爸爸買給我的第一支鋼筆,本來我一直認為那支鋼筆是SKB 22型,初稿也是這樣寫。但我查證後,發現出品的時間不對,爸爸當年買給我的應該是830型才對。仔細回想,我之所以會有爸爸是買22型給我的錯覺,是因為後來22型出品後,我一直想要擁有一支,但沒有如願。久而久之,就將「願望」與「事實」混淆了,以致好幾十年間我都誤以為當年爸爸買的是22型。在我查證當年售價是否與我的記憶相符時,才發現爸爸當年買的是SKB 830型,還承蒙文明鋼筆公司盧惠祥先生贈送了一支該公司已停產二十多年,純手工打造的SKB 830型鋼筆,以饗我這個念念不忘四十多年前往事的愛用者,實在是讓我如獲至寶。
民國五十八年我上高中後,爸爸帶我到太平町林三益總店買毛筆,記憶中路經的台北大橋已經是改建後的水泥新橋,但我依稀也記得那幾年台北大橋是在改建,到底我的記憶是否正確,也是查了當時的新聞報導,才確認我的記憶無誤。
當年趙港、黃天海、簡吉等等許多台灣社會運動先驅們,他們聚會編雜誌的地方,流傳的資料是在台北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我的月里三姨回憶,他們與我大妗租屋居住的地方,是同一房屋的不同房間。但我查了大妗在日本時代的戶籍謄本,其記載卻是二十七番地。這樣看來,我大妗與他們應該是隔壁鄰居;當然,三姨的回憶很可能是正確無誤的,那趙港他們的地址,似乎就應該是二十七番地才對。所以我還是以客觀的資料,論述那段故事。
我也特別將家族中眾多的養女與童養媳的來歷與去向記載清楚,因為我媽媽也是養女,那些清楚的記載,正是我表達敬意的一種形式。我想提醒,大家都一樣,都是人女、人子,都是有來歷的。而她們無論去或來自何方,她們都是我的至親。
幼年時環境中的一切,似乎都是浩大的。正如新莊五十六坎,在我小時候的眼中,無論是不時籠罩的壓迫,或是上演百態人生的宅邸街道,都是浩大的巨靈,但如今一看卻變成一條小街道,對我而言,簡直是南柯一夢。因此,本書的一些細節幾乎都是經過仔細的查證,但無論如何,畢竟還是以我個人主觀的回憶為基礎,畢竟也是縱橫百年、札記式的家族史,如果本書有所繆失,所有文責當然由筆者自己承擔。
本書從我小時,爸爸生命中包括我媽媽、「卡將」、潘姓助產士,三個女人的出現作為序曲,再從我母系開台祖保贊公寫到我外祖烏協公,因連生五個女兒,生到我媽媽時,就大嘆夠了!足了!所以我媽媽的名字就叫「許足」,用台語唸就是「苦足」。果然我媽媽一生,真的就不苦到足都不行。三歲時,我媽媽送給堂叔作養女,但不久這位堂叔,我的欽地公,到屏東做工遽然過世,過世前二十多天才生了一個女兒,我的「歐巴將」,沒有看過父親的阿姨,那已是八十九年前的往事了。
我的欽地嬷在欽地公過世後,剛強堅毅,為日本人幫傭打工,結果從日本人那裡學得樣式繁多的日式醬菜,最後自己就在台北上奎府町,後車站附近做起醬菜攤。欽地嬷隨後與加入合作生產醬菜,來自彰化永靖庄的詹福先生成為一家人,這位詹福先生,就成了我的第三位外公。之後,詹公將他故鄉的姪子帶來幫忙,結果生意逐漸擴展,成了一個興隆的食品企業。
我的媽媽在少女時代,曾與這位姪子短暫相戀,但很快就散了。在我的欽地嬷作主之下,這位姪子招入贅與我「歐巴將」阿姨成親,成為我的姨丈,我們都用日語稱呼他「吉將仔」。而我媽媽不知在什麼機緣下,與我爸爸也成家了。我的爸爸與媽媽相差十八歲,我媽媽是爸爸的姨太太。我媽媽這邊的親友,都說我媽媽被我爸爸騙了。我媽媽一直由我爸爸安排在西新莊仔的農場居住,太平洋戰爭時,曾疏開至小基隆三芝舊庄,民國三十八年才舉家遷回到新莊,與我爸爸的大太太,還有新莊阿嬷、阿叔、阿嬸一起住在新莊五十六坎老街的家宅。
我爸爸的大太太,大人要我們稱呼她「卡將」,沒有親生兒女。我的阿叔、阿嬸家庭則有一些不堪的傳言在鄰閭間流傳。複雜的情境,最後大家打壞感情,在大宅院中分灶拆夥,封死第二進與第三進原本相通的門,各自獨立生活,進行慘烈的爭鬧,我媽媽經常在新莊街上被羞辱圍毆。更嚴重的是,我爸爸與接生我三姊與我的產婆,竟離家在外地築巢而居。民國四十九年,我小學一年級時,我們沒有被認知的一家五口小孩及媽媽被掃地出門,可說顛沛流離。
這近二十年,我們已經一一尋獲當年相互爭鬧不休的親友,當然最重要的是我爸爸的大太太「卡將」,雖然沒有正式和解的形式,但實際上大家已經淡忘了過去的衝突,並且相互接納。我也找到我的奶姆「蹺春」……我將整個過程寫下。也幸好這些年來,大家有來往,關係也可算是友善,才讓過去的不幸有了一個了結。對我來說,多少也使人生的重大遺憾有些填補。這本書就是希望翔實記述家族關係,寫家族中的母親群像,寫我們被掃地出門後的陋巷歲月及那些子民,寫我過去年少時無法抒解的傷感,也寫下我對媽媽至深和永遠的懷念。
這本書在二○○○年初稿完成時,我曾拿給幾位在媒體工作的好朋友指教。因為本書中我刻意保留爸爸的姓氏大名,所以有兩位朋友就建議書名取「父不詳」。不過我們早就歸宗於新店赤皮湖許家克蒲祖,沒有後嗣的第五房。我想寫這本書並不是要認祖歸宗,也沒有要控訴任何人,而是要禮讚母親,禮讚家族的母親群像。所以對這些建議就有所保留,最後書名我自己訂為《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
當年,我媽媽知悉我爸爸竟然與接生我與三姊的助產士在外築巢而居,晴天霹靂,精神受不了,就被安排到療養院中療養,一年多後才回家。媽媽從療養院回來的第一晚,去抱我回家時,一歲多的我嚴重認生整晚吵鬧不安。最後,媽媽亮出乳房讓我吸吮,我才逐漸得到安撫,才抱著媽媽的乳房入睡。從此,我睡覺時,一定要抱著媽媽的乳房,才願意睡覺。我小學四年級時,媽媽發現右腋下長了一個硬塊,檢查結果竟是乳癌。媽媽開刀拿掉右乳房,正是我自小習慣抱著才願意睡覺的乳房。媽媽失去平衡與秩序,我則受到驚嚇……再也不要與媽媽睡了,媽媽感到被嫌棄……
回顧媽媽苦難的一生,最具體留給我們的其實是對生命永不看破、永不放棄的身教。一時的希望破滅,必定期待下一個機會;這一年的希望破滅,必定期待下一年的機會;這一代的希望破滅,必定還期待下一代的機會,絕不放棄。媽媽常訓勉我們「一枝草,一點露。」「天無絕人之路」。這是我們能有機會成長,能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的根本因緣。《媽媽的乳房》正是我幼年時生命最重要的依靠,也是生命中最溫暖的回憶。
寫我土地,寫我人民,一直是我這些年很深的想望。在出版寫我土地的《女巫之湯》之後多年,我又能將寫我人民的本書出版,對個人的意義自然是非常地重大。《媽媽的乳房》對我廣義而言,其實正是象徵斯土斯民的恩典。
在本書寫作的過程中,筆者家人不時的鼓勵與親長的協助,是最大的支持力量。特別是淑貞大姊在本書的基本資料,尤其是爸爸家族日治時期全部戶籍謄本的收集上全力幫忙。還有多位親長,提供與協助取得赤皮湖許氏族譜與日治時期的所有戶籍謄本。她們協助取得的資料,還有長期屢屢接受我訪問的許多親長的口述資料,都是書寫本書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碧玲非常忙碌,卻也在看過每一章節初稿時,就屢屢提供心得與看法供我參考。遠在英國修讀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的女兒以心,也為爸爸的書,寫了一篇序。非常謝謝她們。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的志忠兄,看了本書的書稿後,就說他如果自許為出版家,一定要出這本書。也說他看了這本書後,與我竟有一種深深相知的感覺,當然那是出於我們對天下母親都想虔誠禮讚的一種共鳴。志忠兄對出版這樣的認真,也讓我很感動。這本書能這樣呈現給讀者,要謝謝志忠兄。
本書更承蒙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江文瑜教授、作家導演吳念真先生、東海大學中文系許建崑教授、小說家廖輝英女士惠賜推薦序,四位都是著作等身、洞悉人世、文采閃耀的名家,推薦序也分別從不同角度精心觀察,可說是本書的最佳導讀。四篇依姓氏筆畫排列的推薦序,實為本書增添不凡的重量,所以在本書出版之際,要特別致上個人萬分的感謝與再感謝。
‧那個產婆仔
我幼年時,除了媽媽、兄姊之外,我並不清楚家裡應該還有一個叫爸爸的人。一直到我要上小學前,因為左鄰右舍的家庭都有一個爸爸,才漸漸清楚好像每一個家都應該有一個爸爸,而且都應該住在家裡。只是那時年紀太小懵懵懂懂的,雖然開始知道我也有一個爸爸,但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我的爸爸幾乎都不在家裡住,也不知道爸爸到底住在哪裡。記憶中爸爸沒有寫信回家過,且那時新莊一般人家也普遍都沒有裝電話,我家自然也是沒有電話,所以爸爸好像與家裡並沒有在聯絡。只是爸爸會偶爾突然回家,那時候我反而會因很少回家的爸爸突然出現,好像家裡來了一個很特別的客人,而感到很興奮。
進了小學後,我才逐漸由大人的談話中了解,原來爸爸在外面跟一個在做「產婆」的潘姓女人住一起,才沒有住在家裡。
那時我不知道爸爸跟那個女人住哪裡,也不知道那個女人是誰,但因為家人那時都很怨恨,每次提到那個女人時,總是用很鄙夷的口氣叫她「那個產婆仔」,我才知道那個女人是一個「產婆」。知道「產婆」是什麼的一種職業,還有知道「那個產婆仔」姓潘,則是更後來的事了。
另外,還有一個很清晰的印象,從小就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那個印象依稀是媽媽用綁巾背著幼年的我,而媽媽正與一群大人,男的、女的都有,在互相拉扯,叫罵得很激烈。那個記憶的最後一幕是媽媽哭跪在地上並指天詛咒,另一個也在哭的女人則大力地拉扯著媽媽的頭髮。
那個記憶在我似懂事、又非懂事的年紀時,我也弄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只是那個印象,常有事沒事地會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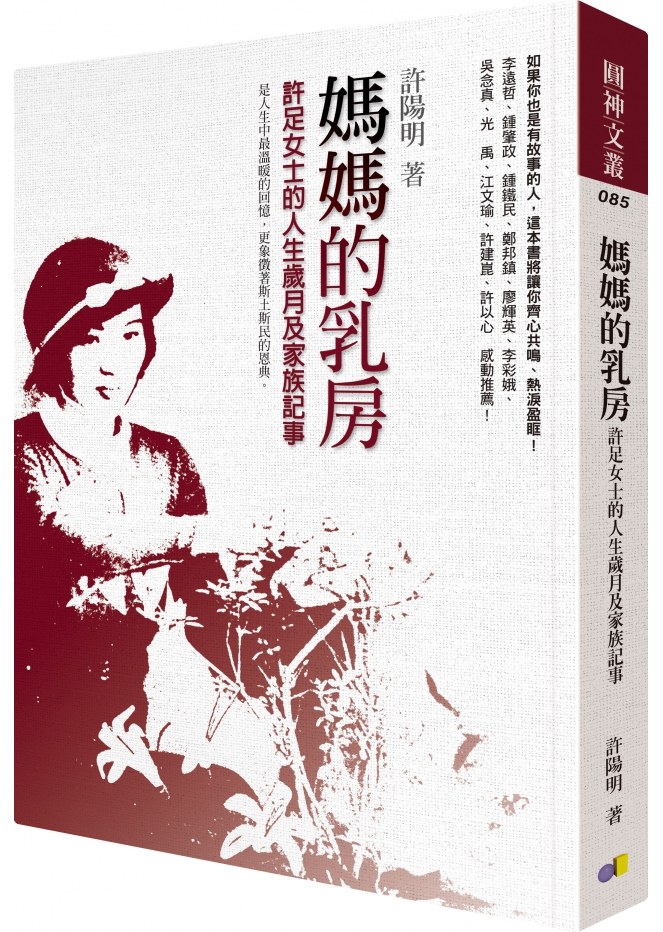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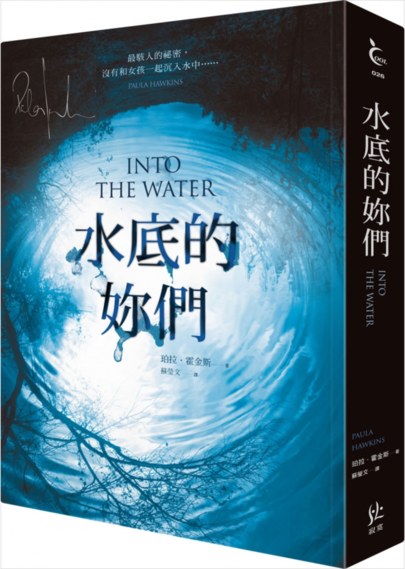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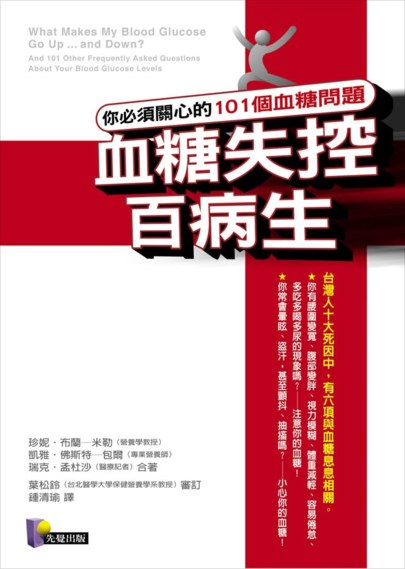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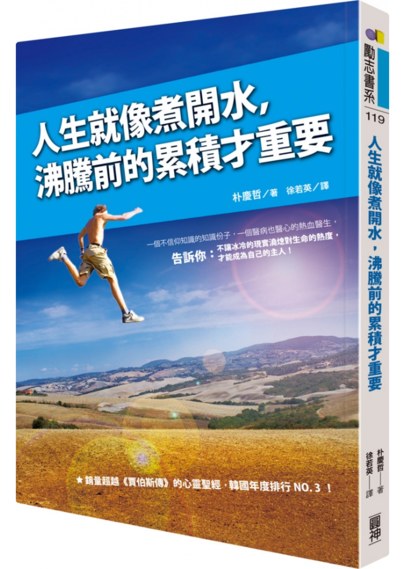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