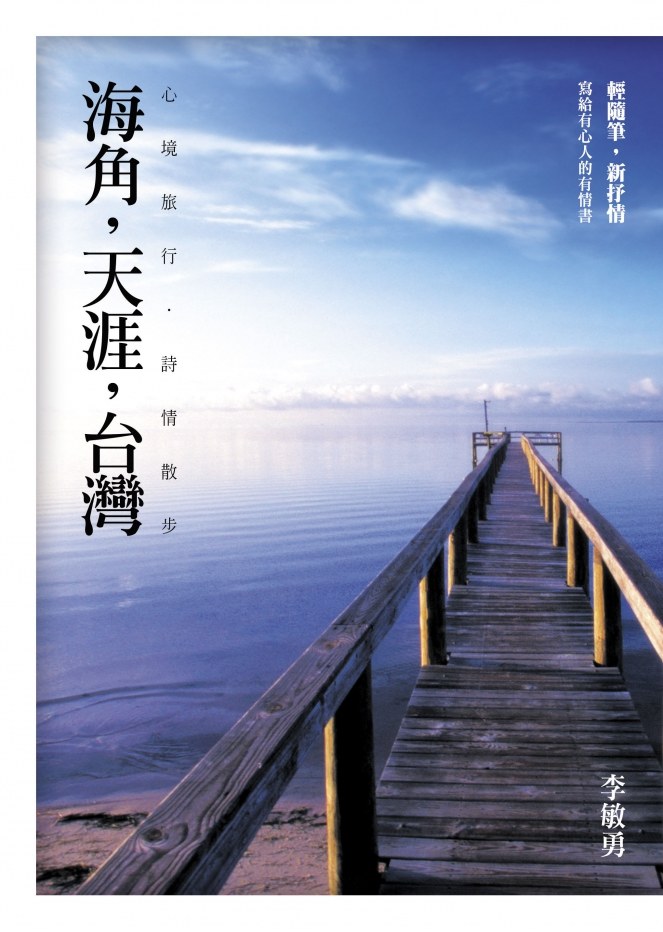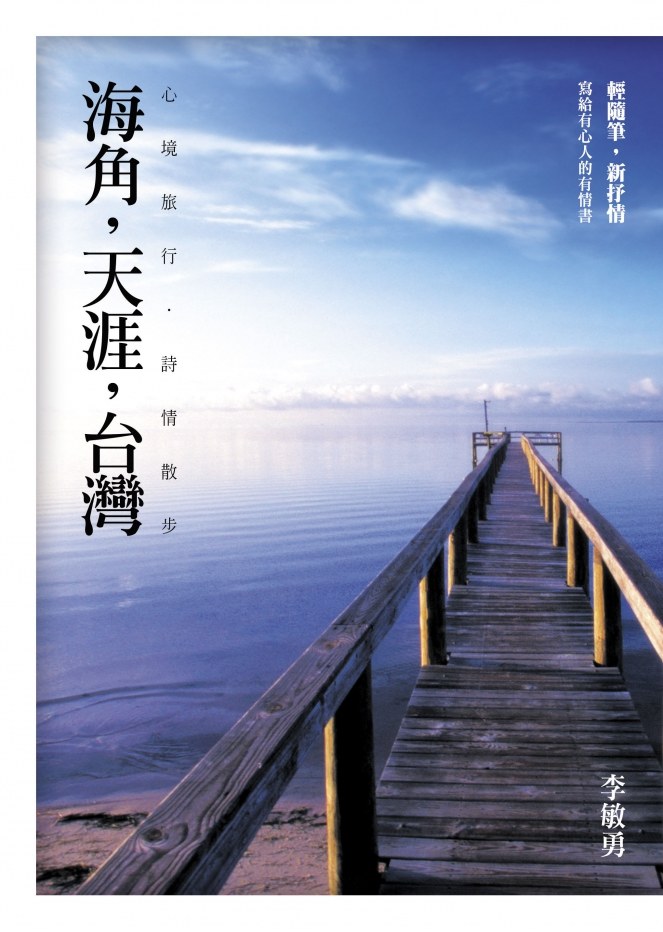◎從0出發
一九七○年代初期,我進入廣告代理業任職,從copywriter做起。那時候,心儀的是大衛.奧格威《一個廣告人的自白》,他是奧美廣告的創立人,大學修習的正是和我一樣的歷史。我的志向是詩人、作家,選擇從事廣告創意工作,是想和自己志向相輔相成。何況,在美國的廣告界,有「不當總統就當廣告人」這樣的說法。
一則大約那時代的日本航空公司廣告,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那是日航為了推廣日本青年學生海外旅遊而展開的廣告campaign,訴求主題是「從0出發」,意思是從原點出發的一種開創精神。大學畢業了,要踏入社會,海外旅遊正是擴大視野的途徑,這是一九七○年代初期,一則日本航空廣告的觀點。
日航的「從0出發」廣告campaign,文案引用了日本詩人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詩〈路程〉。高村光太郎是雕塑家,父親高村光雲也是。他已成為日本國民心目中重要的詩人,更因與妻子智惠子的動人之愛而感動許多人們。
路程
高村光太郎
在我前面沒有路
在我後面路已成形
啊啊
自然啊
父親
使我能自主的偉大父親
不要放棄呵護我吧
不斷添加父親的氣魄給我吧
為了遙遠的路程
為了遙遠的路程
父親的氣魄是這首詩中孩子的訴求,反映的是一個男孩的心意。日航的廣告用來對不分男女的青年們訴求,但在意義上更適合男性。「從0出發」是說:即使完成了學業,也要視為歸零,走向世界的視野才有開拓性。這樣的廣告,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進入廣告代理業工作的我心目中,留下深刻註記。
從0出發,懷抱著走出自己的路的志向,並且尋求從父親得到鼓勵。如果讓我再回到青春時代,回到剛要走出學校、踏入社會的時代,我依然會被這樣的訴求感動,並且做為自己的勉語。人生確是一條路,從男孩子成長到男人的路,會成為丈夫和父親,並且把氣魄傳給下一代。
◎海角,天涯
一個厭倦於在台北玩樂團的青年,憤憤地離開這個異鄉都市,回到故鄉恆春,因緣際會地因為一位老郵差車禍,而代職送信。這位青年的繼父,是鄉民代表會主席,堅持在地的旅館業者必須以當地的人才擔綱音樂活動──總不能開發出觀光休閒設施以後,一切都只是外地人的舞台。
原本安排了到外地樂團、歌手的業者,除了保留一位來自日本的偶像歌手,同意由在地人組成表演者。主辦活動的公關,是一位日本年輕女性,在勉予同意中,其實對演出結果憂心忡忡,但在順其自然的進展中,這個回鄉的歌手和在地的成員,在拼湊的練習中,交織著恆春這個有著美麗海景和樸實漁鄉的人情故事。
被譽為國寶的民謠歌手──一把月琴的滄桑歌聲是沒有舞台的;原住民警察愛音樂,樂在其中;一位推廣小米酒的客家青年貝斯手;甚至一位鍵盤手的小女孩……在島嶼南端的台灣,發展出音樂的,而其實不是音樂,不只是音樂的情事。
代職送信的年輕人,拆閱了一份來自日本的包裹。那是一位日本人過世後,他女兒代為寄給在台灣的父親年輕時代戀人的情書和照片。玩樂團的年輕人開啟了二戰前的這段台灣和日本之間沒有結局的戀情,交叉在電影裡的是那位日本人在二戰後船從台灣返回日本時,一路上的書寫形影。這樣的戀情,後來因為擔任唱片公司公關的日本女孩在年輕歌手家的一夜之宿而緊扣她的心。
「海角七番地」是已消失的地址,因而信件遲遲不能送達,但這個地址就是電影《海角七號》的片名。日本女孩囑付年輕的台灣歌手一定要找到受信人,並且把包裹送達。新的戀情和在歷史裡被回憶的戀情,有些重疊的印記,兩位女性都叫做「友子」,一位是日治時期有日本名字的台灣女性;另一位是日本女性。
拼湊的樂團後來在海灘舞台的演出,是成功的。在地也可以組合出表演的團體,不只結合不同角色,也凝聚了在地的不同角色的聲音。從台北回鄉的年輕人,不只在自己的家鄉找到連帶的力量,他也試著要那位可能離開台灣回到日本去的日本女孩留下來,或和她去日本。當下的一段異國戀情和歷史裡的一段異國戀情,男與女的國度易置,這位台灣的年輕男性伸出挽留日本女孩的手,而不像歷史裡那位日本男性,在他的台灣女友在港口尋覓他身影時仍然離開。
那也許是一種歷史。死後才由女兒以遺物的形式寄出情書給未成眷屬的戀人,相距超過半世紀以上,相隔又何止千里。台灣和日本,日本和台灣。歷史在現實裡被投影;現實也在歷史裡被印證。這也是一種現實,台北和恆春,恆春和台北,地理性的課題成為現實的課題。
台灣和日本,日本和台灣,一種天涯,海角;台北和恆春,恆春和台北,另一種海角,天涯。導演魏德聖,巧妙地編織著動人的電影《海角七號》。這是一部好看、動人的電影。一個星期天,我們兄弟都帶著妻子,並帶著母親,去看這部有我們故鄉恆春場景的電影。
看到許多年輕人進場看這部電影,我也聽到大女兒讚譽這部電影。而魏德聖導演的一部《賽德克.巴萊》簡短樣片,早就留在我們腦海。那部以莫那魯道為主角的電影,應該是他的一個電影夢。多麼希望他這樣的夢能夠實現。
《海角七號》描述了我故鄉的情事,在歷史與現實裡鋪陳人生之歌。這也撩起我詩裡的〈故鄉〉形影:
落山風嗚咽
聲音消失在環繞的海
一把月琴
思想起
◎閱讀啟動人心
關於閱讀,我常想到德語瑞士詩人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的一首詩〈書〉:「這世界的書∕並不是都會給你帶來幸福∕但是,他們會悄悄地∕教你回到自己的內部」這樣的行句之後;赫曼.赫塞也提到光和睿智,認為是重要的。我不喜歡「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樣的觀點。
我也欣賞一個推動閱讀的故事,來自西班牙巴塞隆納。源於巴塞隆納守護神慶典日和莎士比亞生日的四月二十三日。在這一天,發展出男士送一朵紅玫瑰給女士,女士送男士一本書的儀式。後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此為「世界讀書日」,獲許多國家響應和推動。
想想看,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在世界許多國家的城市與鄉村,男生在花店買一朵紅色玫瑰花送給女士,女士則在書店買一本書送給男士,愛與智慧交互輝映的光輝多麼美麗。
台灣也推動閱讀振興,但文化部門的努力似乎沒有真正起動人們的心。世界讀書日興起的時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台灣的文化部門提供花和書,安排了男士與女士互送,既帶動不起愛,也勾勒不起智慧。流於形式的世界讀書日在台灣也就草草了事,既失去了推動讀書的浪漫性,也失去了以文化形式參與聯合國的機會。
在亞洲,日本人讀書的風氣常被人傳誦,電車上的乘客利用行車時間來看書的風氣就是例證。日本人看著書,喜歡閱讀,政治家和經濟人當然也手不釋卷。日本的雜誌常有各行各業的人物書房寫真,常流露出他們得自書中的智慧話語之光。
閱讀如果像啜飲咖啡一樣形成風氣,咖啡館像書店一樣,那麼台灣的閱讀風氣、閱讀風情、閱讀風景,也會令人傳誦。不但有助於文化產業,對於台灣政治的口舌與拳頭現象,也會有所改善。
農曆春節期間,好好閱讀一本書也是好點子。台灣應該冷靜冷靜,沉澱沉澱,多多思考自己的發展方向。太喜歡熱鬧的文化產業和政治節慶,有時冷靜沉澱下來,也很好。春節過後,一年一度的台北國際書展如果只是形式上書的特賣會,還不如每個國民利用春節讀一本書來得有意義。國際書展和國民閱讀風氣也應該連結起來,才會爆發力量。
也許一本書的力量能夠啟動人們的心,對於善美真實進行更深刻的對話;也許一本書能夠爆發動人的力量,發出智慧的光。
◎鄉愁
人有兩種鄉愁;一是自然的鄉愁,來自對於故鄉的思念;另一是精神的鄉愁,在於美的憧憬。
德語作家赫曼‧赫塞(Hermamn
Hesse, 1877~1962)的文學充溢著鄉愁,他的自傳性小說漢譯本被取名《鄉愁》;他的詩也洋溢著鄉愁的基調。
一九八○年代,我在執編《笠》詩刊時,逐期刊載蕭翔文(1927~1998)經由日文譯介的《赫塞詩選》譯序〈我為什麼要翻譯赫塞的詩〉中,蕭翔文述說他日治時期在中學時代看到赫塞全集的印象。那是在一位台灣小說家,也是詩人的張彥勳(1925~1995)家中留下的經驗。一直到一九八二年,他才在日本東京的書店買到角川書店版的《赫塞全集》,並且試譯赫塞的詩。
蕭翔文說,在張彥勳家中看到的日文版赫塞全集,共十幾本,包括小說、散文和詩,以白色封面印著銀色的Hermamn
Hesse,簡單而高雅。文學就這樣深深植入一個台灣少年的心靈,帶領他走上文學之路。
因為,蕭翔文「文學」發生了「鄉愁」。
因此,蕭翔文的人生中烙印著追尋文學的足跡。
赫曼‧赫塞的文學洋溢著鄉愁,一種探索著光與熱、希望與愛的願望。因為反對戰爭,生為德國人的赫曼‧赫塞歸化瑞士。一九四六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他,頌揚其「在悲劇時代擔負了真正的人道精神」。
回想起來,我對文學的鄉愁來自德國作家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那是少年時代的事,是一個暑假在舅舅家,從表哥書架看到的一本書。少年心靈裡播下的文學種子,彷彿一盞燈光,引領我探尋文學之路。
一本書,一本文學之書,會在人的一生中留下某種印記。少小時代,少年時期的心靈,會因為書中所蘊藏的一切,留下影響。這樣的影響如果成為永遠的鄉愁,也許就會讓人走向文學之路。
蕭翔文譯介的《赫塞詩選》,有一首詩〈書〉曾被我收錄在《亮在紙頁的光》這本書裡。這是一本收錄三十九位世界詩人四十首詩,以及我的四十篇解說隨筆的書。
這世界的書,
並不是都會給你帶來幸福,
但是,它們會悄悄地
教你回到自己的內部。
回到自己的內部,也許就是文學的鄉愁。
自己的內部竟蘊藏著什麼呢?自己的內部,是心,是一種純粹的領域,是一種人性的根源,未被塵世污染的秘境。
在那裡蘊藏著你所需要的一切:
太陽,星以及月亮。
……
在自己的內部隱藏著太陽、星以及月亮的光,這樣的想像是浪漫主義式的。而赫曼‧赫塞做為一位浪漫主義、並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作家,他的人道精神來自浪漫主義加人道主義的情懷。
文學的鄉愁常常是自然的鄉愁和精神的鄉愁合而為一或兩者兼容相成的產物。故鄉與美,一種是自然的,一種是精神的,離開故鄉,思念故鄉;憧憬美,追尋美。這樣的藝術秉性在人格養成之路,特別在教育裡,是重要的。
失去對於自然的鄉愁,人沒有土地和根源的連帶感;而失去對於精神的鄉愁,人會成為物質的俘虜。不幸的是,當下的社會充塞著這樣的人,只生存而不是生活;沒有感動,只以肉體的存在,而無精神的存在。所謂「空洞的人」或「空心人」的感慨,就是對於這種現象的憂慮!
◎回歸到0
0,從起點到終點,形成一個阿拉伯數字。
這不只是一個數字,這也是一個符號,一個圓。
歸零,是一種空白狀態,這是開始;完成於零,則是一個圓熟狀態,可以說是結束。人生,從0到0,不就像這樣嗎?或說是一段旅程、一個計畫,從開始到結束。
我的職場經驗裡:教書、採訪新聞,相對於廣告事務是短暫的;但廣告事務相對於企業經理人,也是短暫的。即使這樣,在廣告界的五年工作仍然印記人生的充實行跡。
記得,一九七○年代中期,我在廣告界任職時,從廣告撰文(copywriter),而企畫(planner),進而帶領業務部門(account
executive)及綜理包括業務與企畫的事業部門,促成了我在廣告界任職的機緣。因為無法忘情文學,而且不想陷於以文學謀生的尷尬之境,我在企業的職場印記了人生的光影。
在廣告界經歷的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某種歷史,我曾以〈廣告美學〉〈廣告力學〉和〈廣告哲學〉,為自己服務的廣告公司製作系列企業廣告,嘗試把自己心目中的廣告文化觀點表達出來,並希望成為某種備忘錄或指南。即使後來我離開廣告公司到實業界,仍然有一段時間為一份廣告雜誌撰寫社論,期望廣告更具有文化面相。
日本航空在一九七○年代初,「從0出發」的系列廣告,是我喜愛、推崇的廣告。並不因為它引用了日本詩人高村光太郎的詩〈路程〉,而是它將旅行商品的意義和價值彰顯出來,給人生某種的啟發。那時的感動,或那樣的感動,帶有某種青春年代的憧憬。
相對於「從0出發」的視野,在現在的時間,在我自己的人生從青春而朱夏而進入白秋期的階段,Suntory威士忌的廣告,彷彿從三十多年前跟隨著我,成為這時候的心境。
其一是以黑澤明為訴說者的一支廣告影片:背對著鏡頭,黑澤明坐在導演椅,他正聽著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命運」,熟悉的旋律撞擊著生命,黑澤明轉身過來,他拿起手中的威士忌酒杯啜飲著。響起「Suntory威士忌」的聲音。
另一支廣告影片,是在北海道一個海邊,露營的父親和兒子圍坐著點燃小柴堆。父親問兒子說,你知道這些小柴枝怎麼來的嗎?它們是來避寒的候鳥長途飛行,為了在海面稍事休息而銜在嘴邊的小柴枝,但並不是每隻鳥都能返回牠來的地方。每一枝小柴枝都代表一隻死在這兒的候鳥。話說完時,啜飲手上威士忌,旁白響起「Suntory威士忌」。
如果說:「從0出發」的日航廣告是我昔日的心情;那麼,Suntory威士忌的廣告,就是我此時的心境了。青春和白秋,畢竟是人生的不同階段。如今,我自己的一個女兒也像他父親一樣,走上廣告人之路。在她身上,我彷彿看到自己的過去。我曾經那麼希望廣告能夠展現美學、力學和哲學的文化面相;另一個在文學之路尋的女兒,是我的另一個面向。我也期待自己的女兒有她們的文化視野。
因為有文化視野,才會有意義的形式的要求。人生的每一天,從早到晚,是生命的最微小週期,是日出到日落的生命形跡。然後,一週間、一月期、一年度,經由日、而週、而月、而年,人生的或短或長,彷彿生命不斷地在形式和儀式的呈現。
每個人的人生都去描繪一個圓,或說描繪一個「0」,從起點到終點的歷程,是一個數字,也是一個符號。在人生的許許多多階段,也是一個一個從0開始而結束於0的過程,是一個圓被描繪、被形成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