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沒人穿純白婚紗了。白布太難入手,坐下好好製作十來件以上的禮服,花費太高,太麻煩。即便是領導之子大婚之日也不例外。尊貴如他,也不能迎娶身穿白紗的女孩。
「站好!」凱莉從背後喊道。她冰冷的指關節靠著我的背脊,硬是想拉上淺藍色禮服背後的拉鏈。這件禮服本是為了她的大喜之日裁製,我身型略微高䠷,穿起來不大合身。「好了,」她終於拉上拉鏈,「轉過來。」
我緩緩轉過身,由上往下撫摸柔軟的衣料。我不習慣穿禮服,不喜歡感到衣飾底下自己有多赤裸,心裡恨不得馬上換褲裝,大大喘一口氣,因為上身的馬甲實在太緊,我幾乎無法呼吸。凱莉似乎讀通了我的心思,往下打量,說:「妳的胸部比我還大。」接著咧嘴一笑,「但他應該不會抱怨這種事吧。」
「不要說了!」我這話聽來一點力道也沒有。真沒想到自己會這麼緊張。我早就料到會有今天,我一直都明白這天遲早會來。過去兩年,我分分秒秒都在準備。然而現在時候到了,手指卻止不住顫抖,胃也不住下沉。我不知自己能否成功,只知道別無選擇。
凱莉伸手將我一綹頭髮塞到耳後。她說:「沒事的,」聲音聽來堅毅平穩,「對不對?妳知道該怎麼做。」
「知道。」我抬起頭,聽到她的話讓我堅強許多,我再也不是孩子,不需細心呵護了。
凱莉凝視我良久,雙唇緊閉成一條線。她是不是在生氣,氣我搶走理應屬於她的位置?或者,她反而鬆了一口氣,因為可以不用再當那個身負眾多期盼的女兒了?
「妳們兩個,」父親的聲音從樓下飄上來,「時間到了。」
我告訴凱莉:「妳先走,我等一下就下去。」我需要最後一刻的安靜,最後一次的機會,讓我看看這間房間,往後再也不屬於我的房間。凱莉離開時沒把門帶上,可以聽到父親在樓下不耐煩嚷嚷,凱莉低聲安撫他。
床上擺著嚴重磨損的行李箱。輪子老早脫落,只能用扛的。我從床墊上拿起行李箱,慢慢轉圈環視房間。我心裡明白,自己再也不會睡在這張窄床上,再也不會對著五斗櫃上的鏡子梳頭,再也不會聽著敲打窗戶的雨聲,迷迷糊糊入睡。我閉起眼睛,壓抑突然湧出的淚水,深呼吸。等我張開眼,淚水已乾。我走出房間,沒有回頭。
〥
婚禮舉辦於五月第二個星期六。儘管核爆已經過了好久好久,有幾年還是會降下夾雜著淡淡刺鼻燃燒味的雨水。不過今日晨光清澈,天色明亮蔚藍,雲絮隨著微風輕飄。今天是結婚、嫁做人婦的好日子,然而在前往市政廳的路上,我只注意到自己心跳強烈,以及肩胛骨之間冒出的一排汗水。
父親和凱莉左右包夾,像是看住我不讓我逃跑。我不想費心告訴他們,我哪兒也不去。父親伸過手來,先是撫摸我的手,然後握住。我大了一點之後,他再沒握過我的手,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我嚇一大跳,腳步也絆了一下,還好最後他用力一握讓我穩住。我很感謝他這個親密舉動,雖說他並不常做,也不輕易做。他不是關愛型的父親,況且要是命運早已註定,父女依依不捨並無好處。父親的職責在於使我堅強,我自認有達到他的期望,但也可能是自欺欺人。
「我們都以妳為傲。」父親說完,便捏捏我的手。這次力道很大,幾乎要發痛。隨即他放開我的手說:「妳做得到。」
「我知道。」我回他,但雙眼仍往前直視。不到一個路口,就是石灰岩外牆的市政廳了。路上有其他女孩子和父母一起步上階梯,她們一定很緊張,急著想知道今天結束時,是會成為人妻?或是黯然回家,再度鑽回自己的被窩?我也很急,卻是不同的急法。我確切知道今晚會睡在哪,也知道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我們走到市政廳前人行道上,群眾開始回頭對父親微笑,向他伸出手,拍他肩頭。一些婦人對我溫暖笑笑,說我看起來有多美。
「笑啊,」凱莉附在我耳邊小聲說道,「別光是瞪著大家。」
「說得容易,妳怎麼不來試試?」我低聲反駁,不過還是聽話照做,硬擠出笑臉。
她說:「本來該是我笑,妳忘了嗎?不過我失去機會,現在妳得連我的份一起笑。」
說到底,她還是嫉妒我,也氣我偷走她身為長女本該擁有的權利。我本以為說出此話的她會是雙眼冰冷,然而我一轉頭,發現她注視我的眼神竟充滿少見的溫柔。凱莉就像是父親的女性化身,她遺傳到他的巧克力色雙眼,以及深栗髮色。我一直希望自己更像他們,而不是神似早已過世的母親。我一頭金不金、棕不棕的髮色和一雙灰眸,都是遺傳自母親。然而正因我和凱莉外貌非常不同,看到她,就好像看到更為勇猛,更為自律的自己。看著她,總提醒我自己應該成為的樣子。
我們跟著長長的新娘隊伍走進市政廳。身邊全是身穿淺色禮服的女孩子,有些手中捧著小花束,有些跟我一樣,兩手空空。有人領我們走進中央圓廳,那裡已架好舞台。圓廳後方有道黑幕,我知道後面聚集的都是男孩子,正排著隊,等著揭曉命中註定的妻子人選。
準新娘坐前幾排,新人家屬則坐後幾排。領導拉汀默夫婦坐在舞台上,一如往年。即使他們的兒子就在黑幕後面,他們的位置還是沒變。父親離開前,又再次捏我的手。凱莉則是在我臉上迅速留下冷淡的一吻,「祝妳好運。」如果母親還在世,或許她會擁抱我,叮嚀幾句受用的臨別話語,而不是說些陳腔濫調吧。
我溜進前排找空位坐下,避免與領導以及左右女孩眼神交會,雙眼直視前方,盯著舞台黑幕的一道小裂口。後來旁邊的女孩塞東西到我手上,「欸,」她說道:「拿一份,其他傳下去。」
我聽話照做,把一疊節目單傳給左邊的女孩。他們每年發的節目單都相同,不同的只有紙張顏色和裡面的人名。其實不需如此費事,大家一定早把流程記熟了。今年的節目單顏色是褪了色的淡粉紅,封面「婚禮」兩字字體捲曲,略微模糊。頭兩頁是「我國簡史」。我覺得把人口不滿一萬的小鎮稱為「國家」真是可笑,不過也沒人問我意見就是了。
簡史提到了那場終結世界的戰爭,隨後而來的洪荒、乾旱,以及差點讓人類死絕的疾病。當然啦,我們有幸破土而出,我們這些困頓、厭戰的倖存者,穿越廣闊荒蕪的大地尋找彼此,開疆闢土,重新開始,諸如此類。然而人類的重生,並非沒有衝突、死亡,雙方人馬激戰,企圖掌握這個小小國家的未來走向。由領導之父率領的勝方取得統治權,後來我的祖父山謬爾.西洛帶領的輸家及其黨羽獲得寬宥,重新返回社群,其族之罪也獲得赦免。
我一邊讀,一邊克制自己發出嘲弄作嘔的衝動。
就是因為這段歷史,才有今天的聯姻日:落敗家族要貢獻己方十六歲女兒,嫁予勝利家族之子。今年十一月會有第二場婚禮:由輸家之子迎娶贏家之女。不過那天的典禮會更加陰沉,畢竟是最有身價的女性在冬日陰鬱天空下,被迫嫁給落魄男子。
這套聯姻制度背後有兩層意義。從實際層面看來,我們不再像戰前一樣長壽,養育健康後代比以往更加艱困,所以繁衍很重要,愈早生愈好。另一個層面,卻又比第一個更加「實際」:領導之父很聰明,他知道維持和平的唯一辦法,是讓不順心的那方繼續擁有,他們才會恐懼,因為害怕失去。對方娶了我們這邊的女孩,就能確保我們起義前再三思考。因為殺敵是一回事,但是敵方有自己的女兒,砍倒的是自己的孫子,就又是另一回事。這辦法到目前為止都很有效,雙方之間的和平維持兩代之久。
雖然門沒關,石灰岩牆冰涼,禮堂裡卻很熱。一顆汗珠滴下後頸,我擦汗以後又把頭髮推高一些。之前凱莉幫我盡量綁得服貼一點,但我的頭髮又厚又叛逆,大概不會乖乖合作。右邊的女孩跟我笑了一下,「很好看啊,很漂亮。」
「謝謝。」我說。她頂著悲傷的黃玫瑰花冠,襯著一頭紅髮。溫度太高,花瓣開始凋謝。
「我今年是第二年了,」女孩低聲向我說道:「是我最後機會。」
如果十六歲沒有合適配對,名字會放到明年再抽。有些年會出現這種情形,因為女少男多,但有時侯則是男少女多,總之就是有些人沒機會找到另一半。如果過了兩年還沒找到配對,就可以自由選擇結婚對象,前提是對方也沒有配對成功。如果女性未婚,可以申請工作,當老師、護理師。若是男性,不管未婚已婚,都得工作。不過要是女性結婚,最好辭職回家生子,所以一般公認的「女性工作」,全是沒有配對的女孩在做。
「祝妳好運。」我說道,心裡卻認為就算配不到,未來命運也沒那麼可怕。我的命運就不同了。自從凱莉的名字被移除,我的名字就直接放入配對信封,事情定案,沒得商量。今天在場的女孩,為了完成配對需要接受人格測驗、冗長面試,但這其實不壞,起碼還有一絲可能性與新郎性格相合。我呢?他們只在乎我的出身。
「謝謝妳。我知道妳是誰,我爸之前指了妳爸給我看。」女孩說。
我沒有回話,眼神轉回舞台上,布幕後起了騷動。我深呼吸,讓空氣進入鼻腔,再從口中緩緩吐出。
一名男子從舞台側邊上台,站到講台上,神情緊張,來回掃視觀眾和領導夫婦。「各位先生女士⋯⋯」最後一個字突然破音,室內傳出低笑。他清清喉嚨,重新發言:「各位先生女士,歡迎蒞臨本日結婚典禮。東峽出才俊,西洛有佳人,東西聯姻,象徵吾人奮戰不懈、以致大同……」致辭人年年不同,講稿內容卻永遠一樣。又悲傷又可笑,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我隔壁的紅髮女孩緊握雙手,直到指節發白,她腳尖猛點地板,踏出緊張的節奏。講台上的男子向台邊看不見的人招手,布幕緩緩拉到一旁,刮擦上方的金屬桿,發出長而尖銳的聲響,讓我牙齒打顫。第一批出來的男孩都很緊張,站得不安分,手一下插口袋一下拿出來,碎步挪動。一名矮小黑髮男孩看來不像十六歲,搞不好才十二歲。他不停痴笑,下巴收得很緊,肩膀卻莫名挺起。我暗自慶幸,還好我不是跟他配對。
跟我配對的男孩站在中間,比其他人高出許多,其他男孩走過他身邊就像水流過岩石。相較之下,他沒有一絲孩子氣,想想他的年紀就可理解。他十八歲,比其他人大了兩歲,不過他的成熟不只來自年紀,我根本不覺得他有過孩子氣的時期。他有一股旁人沒有的氣場,站得很挺,而且你幾乎無法想像他傻笑的樣子。他眼神專注、冷酷、淡漠,又帶有微微的一點興味,像是發現了遠方的什麼。他幾乎看都沒看我。
兩年前,他本該上台,我們一直以為他會和凱莉配對。但在典禮前一天,我們接到通知說他不會參加,要等到十八歲再結婚。到時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凱莉,而是我。我猜八成因為他是領導之子,才會出現這種突發奇想。總之,凱莉因此得到特權,可以不用抽籤結婚,這算是個安慰獎,不過我倒希望是自己得到這個獎。
「天啊!妳真走運!」紅髮女孩深呼吸驚叫。
我知道她是一片好意,想用笑容回應,可我就是笑不出來。致辭男子現在將名單交給領導夫人靄琳.拉汀默。她有一頭狂熱紅髮,身材豐腴,走到哪,男人的眼光就跟到哪。然而她的聲線尖苛,甚至可說是冷酷,像是第一口咬下青蘋果那麼酸。
「大家知道,等一下我唱名,男生被叫到請出列。接著我會拆信封,叫到的女生就是他的妻子。」她停頓一下,俯視眾人,接著說:「叫到名字的女生請上台。如果最後沒被叫到,代表委員會認為妳不適合今年的男孩,」她爽朗笑笑,「當然,這沒什麼好丟臉。」但是,沒被選上確實丟人,這事每人都明白,只是都不說破。要是沒有配對,就是女生的錯,一定是她缺少了什麼。從來不會檢討男方。
第一個叫到的是路克.艾倫。他有頭金髮,一排紅糖色雀斑橫過鼻梁。他眼睛短暫睜大,看著領導夫人撕開正面寫有他名字的信封,抽出一張奶油色卡片,唸出:「艾米麗.索恩。」我後面傳來騷動、興奮低語。我轉過頭,有個身材嬌小、太妃糖髮色的女孩,穿過她那排的其他女孩,幾乎是跌跌撞撞地上台,路克急忙向前牽起她的手。我身後一些女孩發出驚呼,一副這是史上最偉大的浪漫舉動似的。我得努力才能克制自己翻白眼的衝動。路克和艾米麗尷尬站著,偷偷打量對方,之後他們被帶到舞台側邊,以便宣布下一組配對。
整個拆信封過程感覺花了數小時以上。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女孩子枯坐,包括我旁邊那位。領導夫人拆開最後一封後,她落下淚來。我好想告訴她,她應該慶幸,應該高興,因為她今天可以回家,可以想清楚除了結婚之外她還能做些什麼。然而我知道自己的安慰派不上用場,因為大家都會記得,她沒訂下婚約;甚至到最後,人們會記得的是,她沒人要。
領導夫人回頭看丈夫,他起身走向講台。領導身材高大,看來他兒子遺傳到他的身高。他的深色髮絲在太陽穴處開始轉為淺灰,下巴中央有道凹陷,顯得性格強硬。他的淡藍雙眼掃視群眾,停留在我這裡,使我打了個寒顫,但我回看,並不閃躲。
他開口:「今天很特別,比以往還要特別。多年以前,戰爭結束之後,要如何重建家園,意見分歧。最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真是有趣,把開戰說成是意見不合,把強迫聯姻當作協議結婚。他總是很有技巧地操弄文字,編織故事。
「……眾所皆知,家父亞歷山大領導的一方,最後取得控制。與之作對的山謬爾.西洛,隨著局勢演變,最後服膺於家父的未來遠見。」
一派謊言。祖父未曾同意拉汀默家族的「遠見」。祖父要的是民主制度,是讓人民生活在有投票權、發言權的世界。他耗費多年時間,帶領逐漸擴增的倖存者團體遷徙保命,後來才找到此處安頓。這番心血被亞歷山大.拉汀默收割,他只想讓自己和後代子孫獨裁統治。
我不敢轉頭找尋人群中的父親和凱莉。多年以來,他們已經相當善於隱藏情緒,但我還是能從他們的眼中看出怒火。我千萬不能露出這樣的眼神。
領導笑著說:「今天,拉汀默家和西洛家,終於有一對新人了。」我覺得那笑容看起來很真誠,或許那並不假。然而我也知道這樁聯姻對他的意義,這是他鞏固勢力的方法,那才是他開心的重點。我結婚後,西洛家除了我父親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男丁。對領導而言,西洛家後繼無人還不夠絕,非得讓西洛家後代改名換姓,才能讓他滿意。
「我們家都不太會生女兒呢。」領導繼續說話,底下的人笑出聲,我知道應該一起笑,卻無法融入其中。笑聲漸散,領導舉起手中信封展示給眾人看,喊道:「領導者之子,建國者之女。」
建國者當然不是父親。是祖父建立這個城邦,也是祖父被亞歷山大及其手下推翻。然而按照先前慣例,建國者頭銜傳給後代,亞歷山大的後代也會承襲領導者的頭銜。建國者頭銜毫無意義,對國家經營毫無發言權,只是典禮上的傀儡,讓人丟在地上踩踏,給人看看我們有多「和平」,看看政府運作得多麼完善。建國者頭銜像是包裝精美的空禮盒,裡面什麼也沒有。但他們就是希望我們會被閃亮外表迷惑,忽略空洞內容。
「畢夏.拉汀默。」領導喊道,聲音清楚有力。接著傳來撕開信封的聲音,我聽了覺得格外刺耳,像是誰在尖叫一般。我可以感到數百雙眼睛注視著我,但我仍舊努力抬頭挺胸。領導急急抽出信紙,往我這個方向笑了一下。我看見他的唇形,唸出「艾薇.西洛」,但我只覺得耳中轟轟作響,心臟怦怦跳,完全聽不見他的聲音。
我最後一次深呼吸,想把空氣當作勇氣,吸進肺裡。我努力抑制如毒液迷走血脈的怒氣,昂然挺身,雙腿比預料中站得堅穩。我往台上走,高跟鞋喀喀作響,身後群眾鼓掌喝采,夾雜幾聲輕浮口哨。才一踏上台階,領導便彎腰伸手,扶著我的手肘。
「艾薇,歡迎妳成為我們的家人。」領導的溫暖眼神讓我覺得自己上當了,他應該冰涼冷漠地看我,這樣才符合他的氣質,不是嗎?
「謝謝。我也很榮幸。」我不卑不亢,聽起來真不像我。
上台之後,其他新人站得更遠,讓我站到舞台中央,畢夏在那兒等我。我讓他用毫無波動的眼神看我。到了台上,我發現他比我想像中更高,不過我也不矮。我難得因為自己的身高如此慶幸;我才不想站在他身旁像個小矮人,畢竟論出身,我已經矮他一截了。
他的髮色深,就像領導一樣。近看可以看到幾束淺色髮絲夾雜在咖啡色頭髮之間。似乎是長時間待在戶外活動,常曬太陽的緣故。這也符合我多年以來聽到的相關謠言:比起待在室內,他更喜歡往外頭跑,所以領導得強迫他參加會議。但他去河邊划船的時間,還是多過待在市政廳裡。
他的冷冽綠眼仔仔細細打量著我,讓我緊張到胃部痙攣。他那眼神,既不帶有敵意,卻也沒釋出歡迎的訊息,反而更像是評估,彷彿我本身是個難題,他得想辦法解決。他沒有先走過來,但我走近他,像之前練習那樣,向他伸出手。他的手靠上來,我發現他的手溫暖有力。他輕輕握了一下,讓我喉嚨哽了一下。他是在假裝善良嗎?是在安撫我?我不知道,但後來偷瞄他時,他卻在看大廳旁邊的官員。
領導宣布:「現在典禮正式開始。」台上眾人各就各位,站在未來配偶身旁。畢夏和我站在中央,所有觀眾都能看到我們。他牽起我的手,我們的手在兩人中間的小小空間交會。
我真想大喊:「一切都搞錯了吧!」我不認識站在身旁的男孩,這輩子沒和他講過一次話。他不知道我最喜歡紫色,不知道我依舊思念母親,卻幾乎快記不起她長相,更不知道我怕得要命。我慌亂看向觀眾,只看到大家笑咪咪回望。不知怎的,這些笑臉讓我覺得更加悲慘,為何大家都參與這場鬧劇?為何無人驚叫,或是阻止自己的孩子和陌生人結婚?
領導的彈藥庫裡,人民的順從是最強大的武器。
到頭來,我也屈從了:其他人唸出誓詞的時候,我也張口。周圍人聲吵雜,我複誦著自己也聽不見的話語。我告訴自己,剛才說了什麼都不重要,得趕快捱過去。終於我撐過去了。我用父親的樸素金戒套住畢夏的手指,他也給我戴上他母親的戒指。皮膚傳來指環套上的異物感,即使尺寸正確,我依舊感到手指又緊又難受。
長官宣布夫妻禮成,畢夏看來根本不打算吻我,連親吻臉頰也不想,我為此感到慶幸。如果他真的有所動作,我可能無法忍受。這種舉動,像是有人在路上突然抓住我,還硬是把嘴湊過來。這不是示愛,是侵犯。然而周圍的新人又是摟抱又是歡呼,幾乎都毫無遲疑地彼此親吻,好像他們不是一小時前才認識。幾個月後,這些女孩腹中會裝載著沉甸甸的嬰兒,她們會明白,自己得永遠睡在陌生人身旁。到那時,她們還會像現在一樣開心嗎?
這些人以為結婚典禮可以保持和平,慶祝傳統;多虧傳統,社會得以鞏固,傳承超過兩代。但我和他們不一樣,我知道這份和平有多脆弱,只憑幾根繃得愈來愈緊的細繩努力維持。我和身邊這些女孩不同。因為和畢夏結婚不是我的人生使命。我的任務,並非讓他開心,並非與他生子,並非與他為妻。
我的任務,是取他性命。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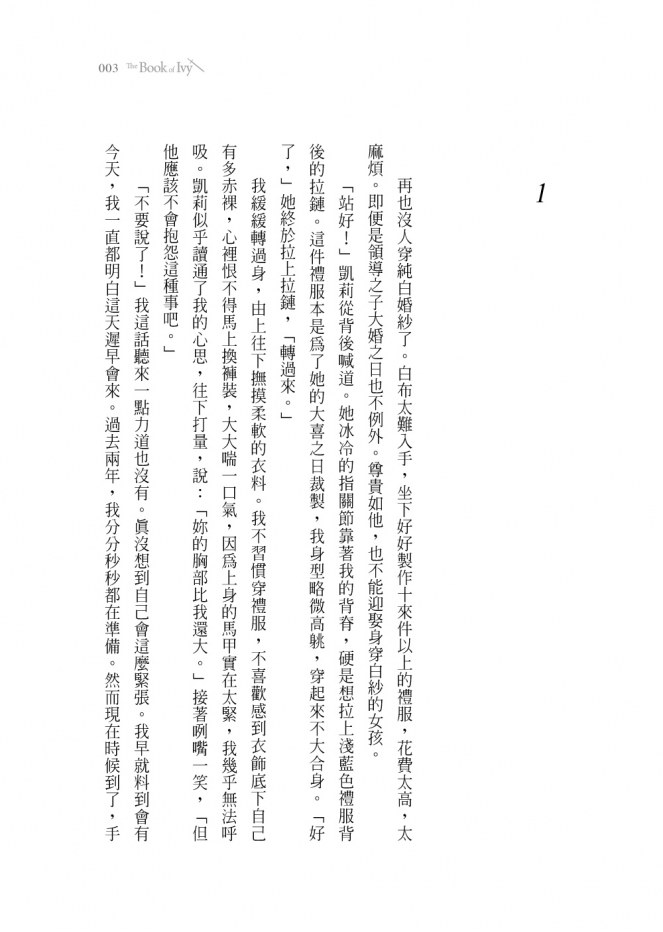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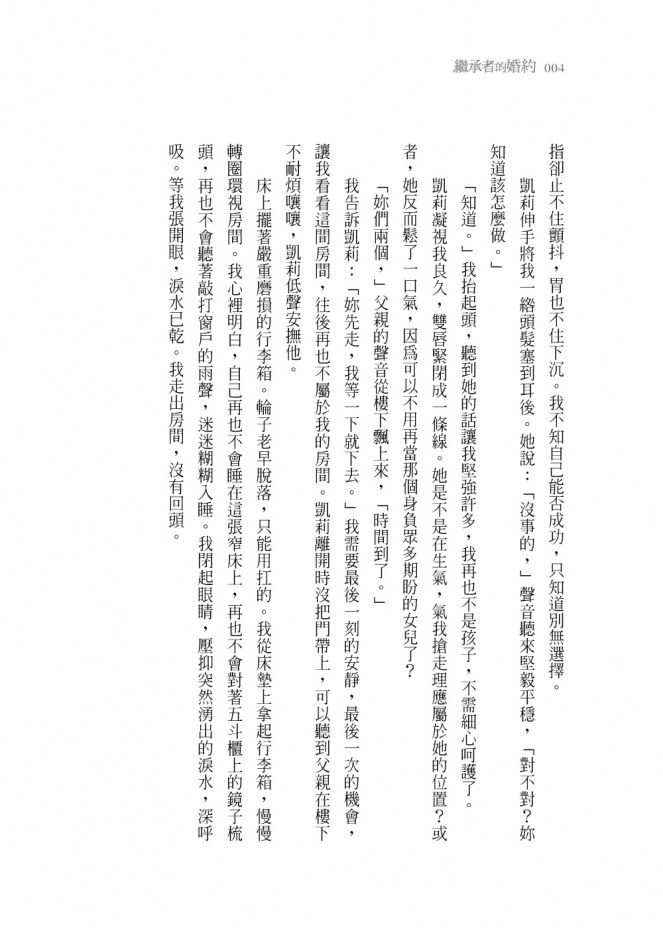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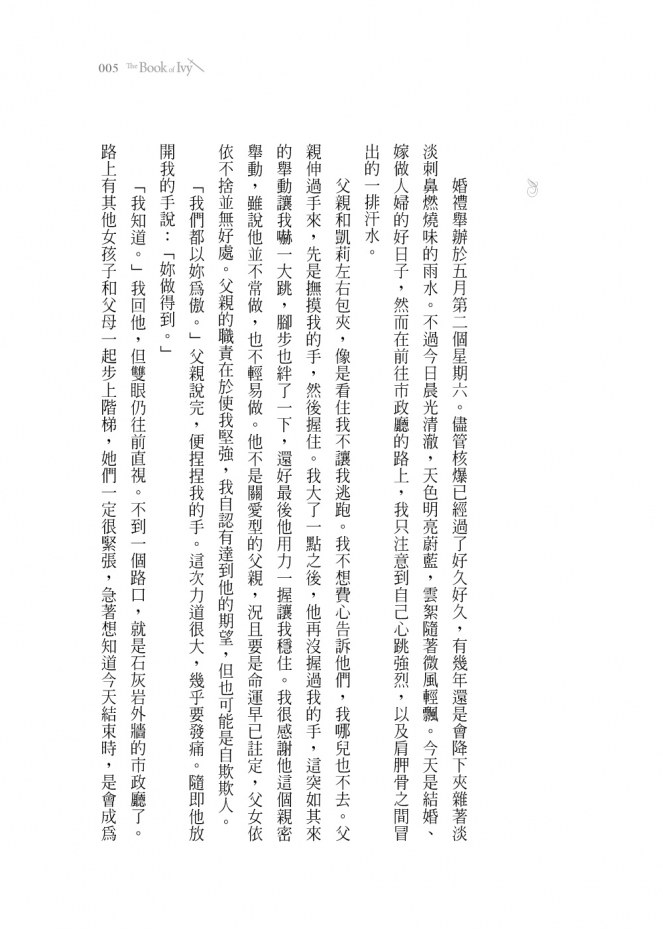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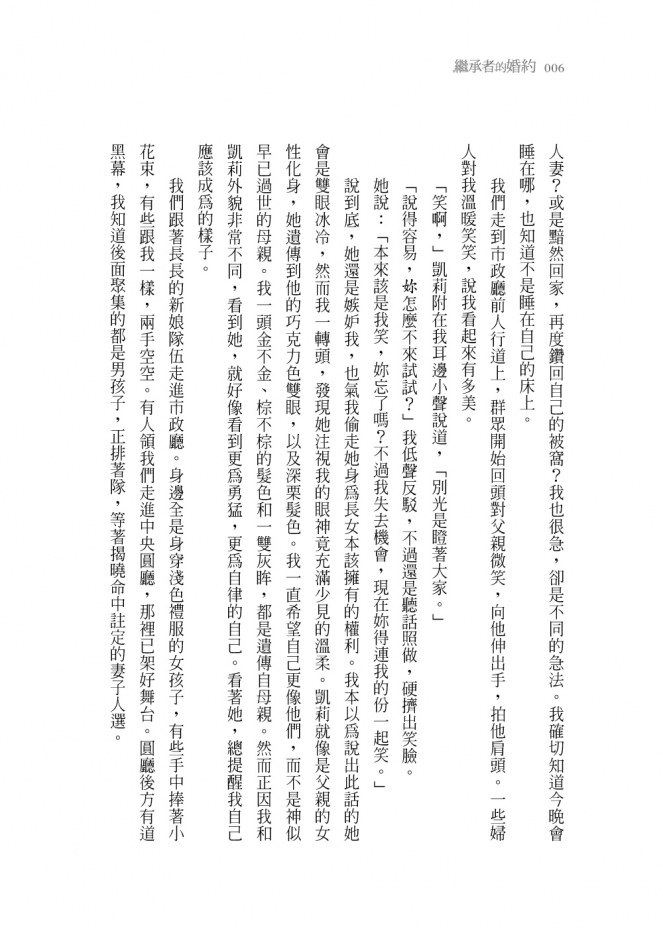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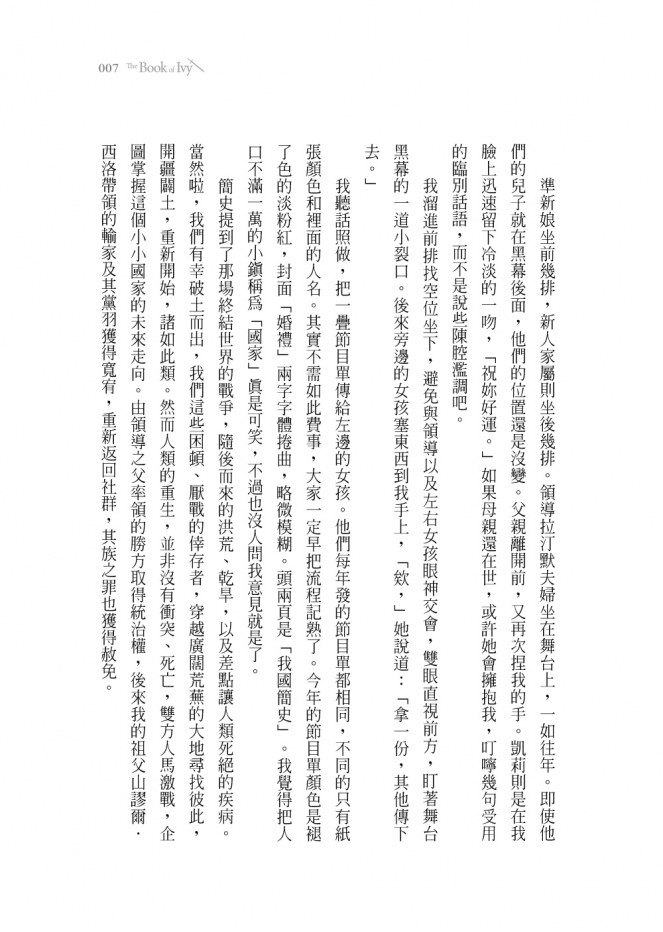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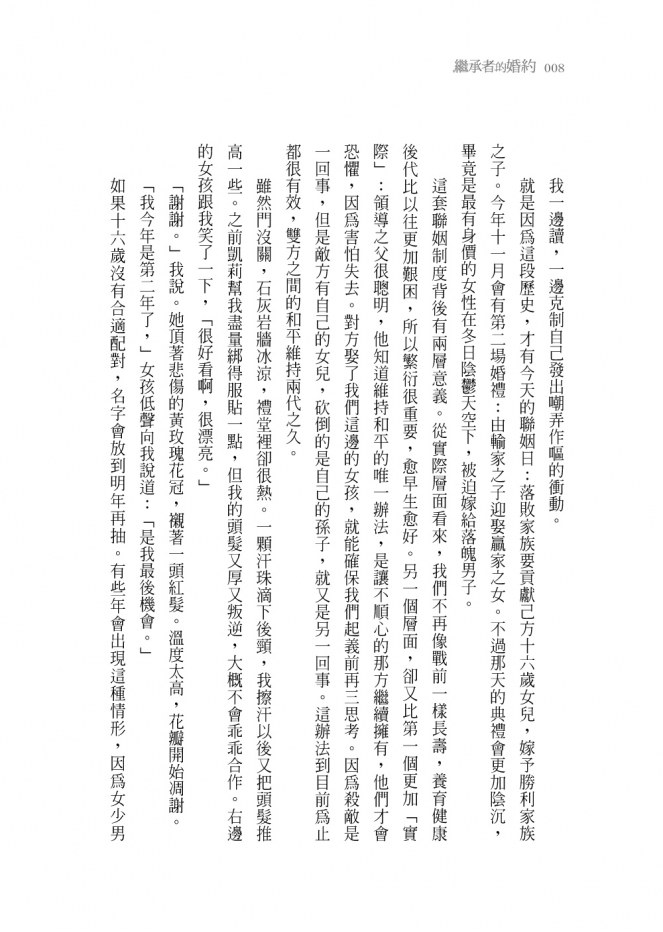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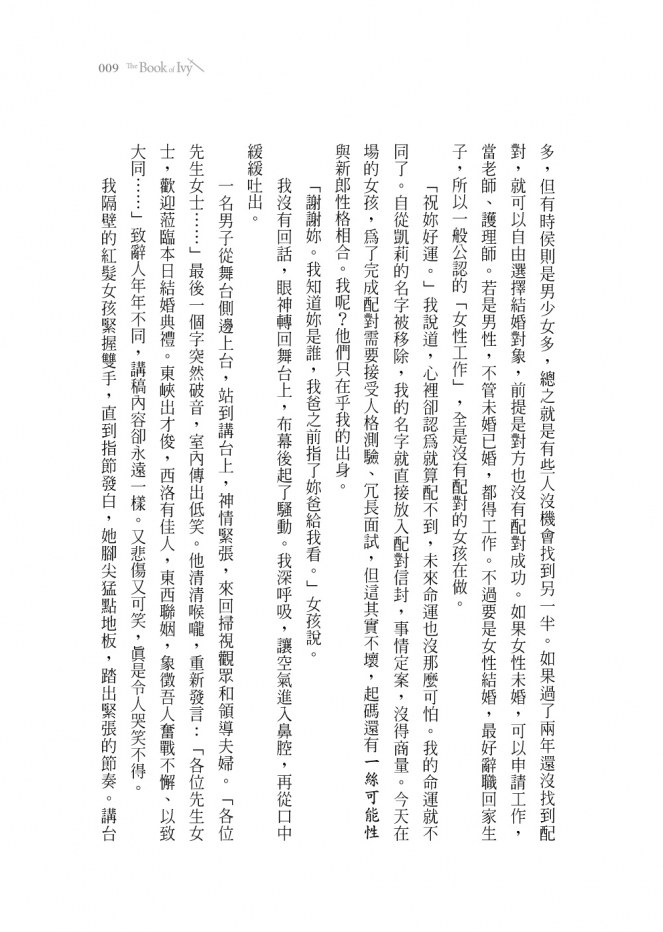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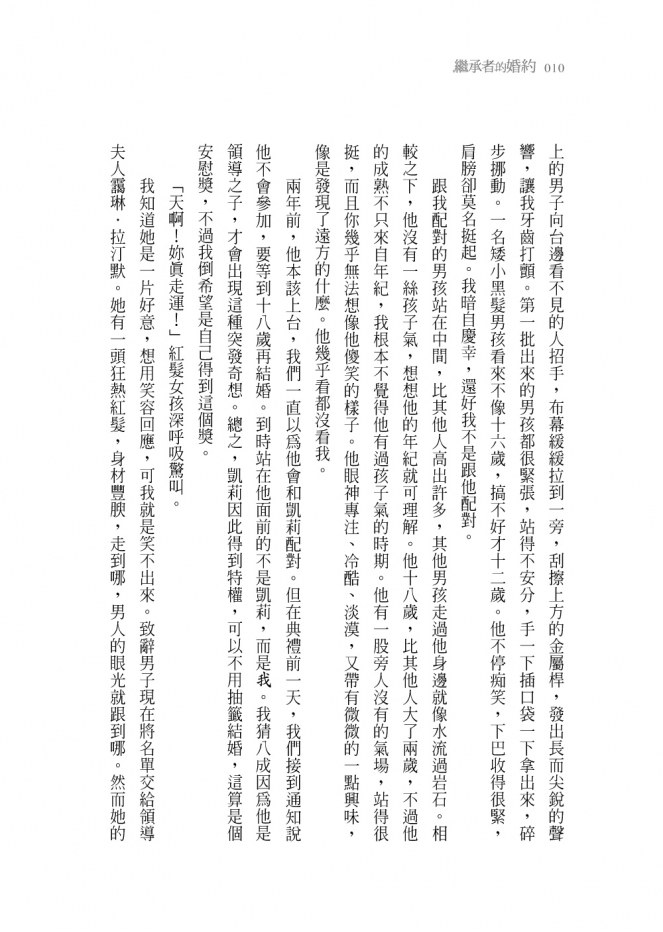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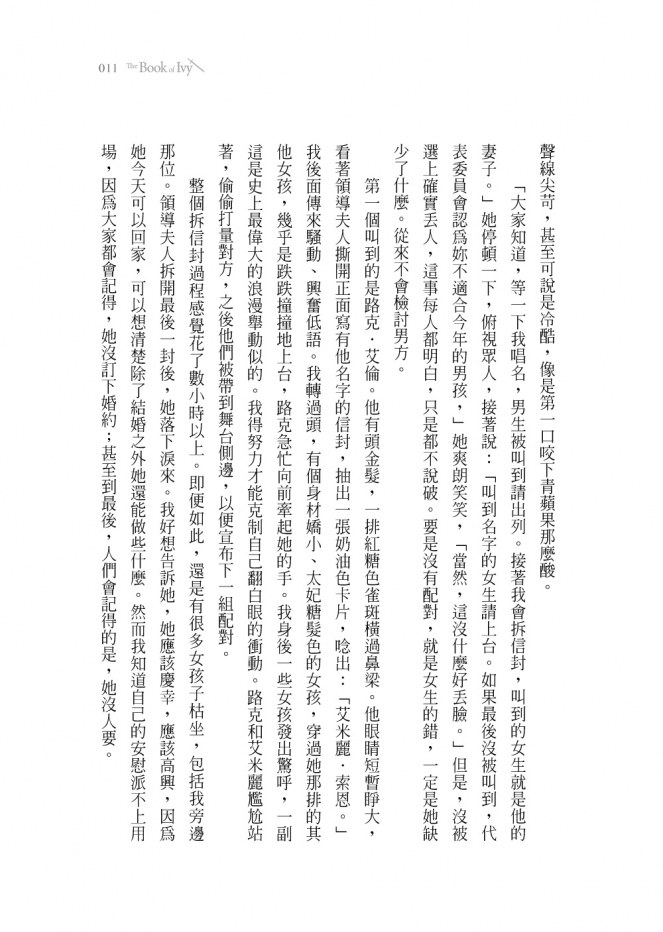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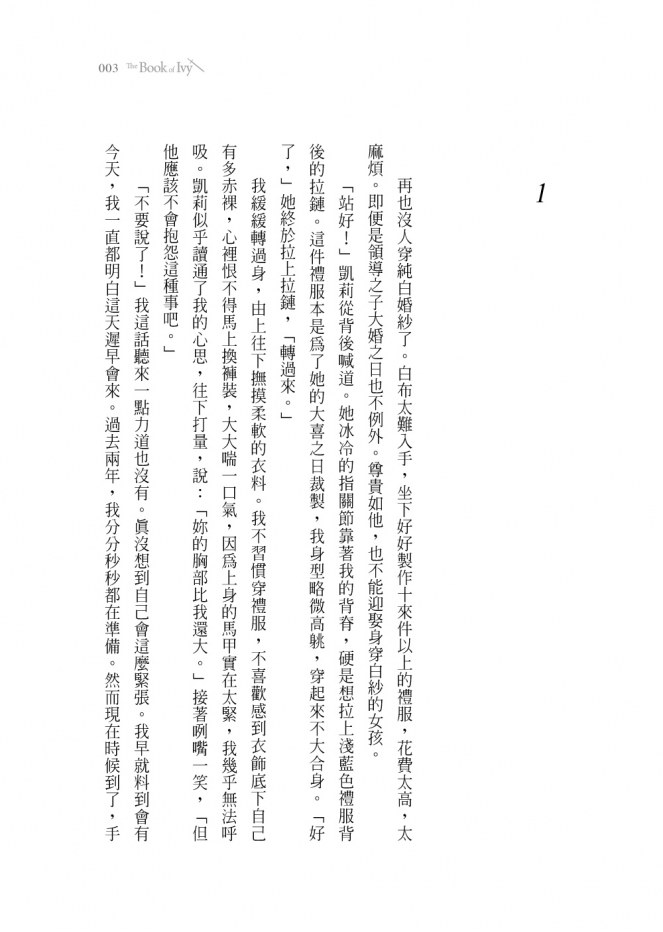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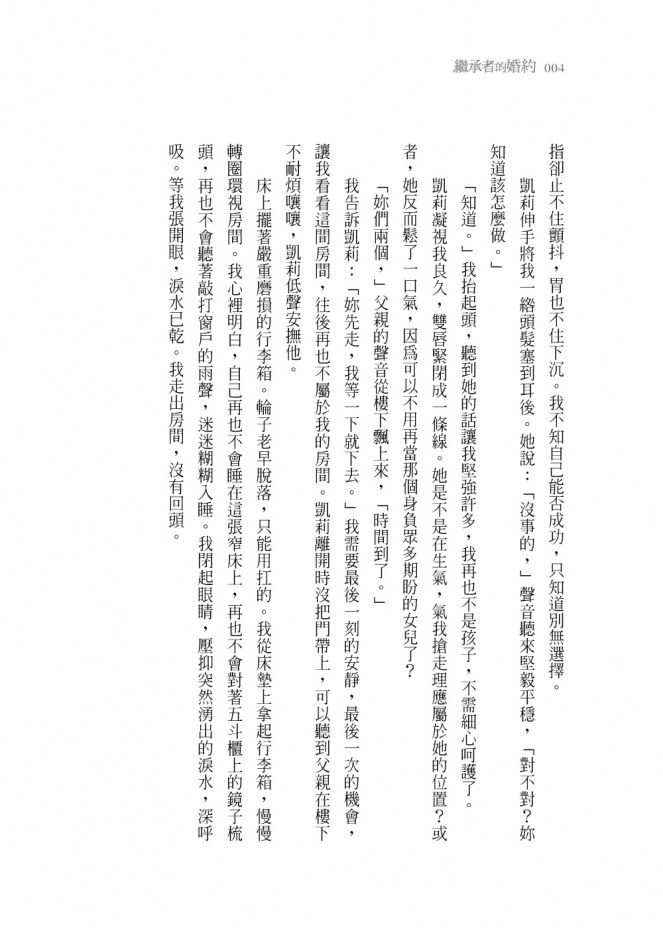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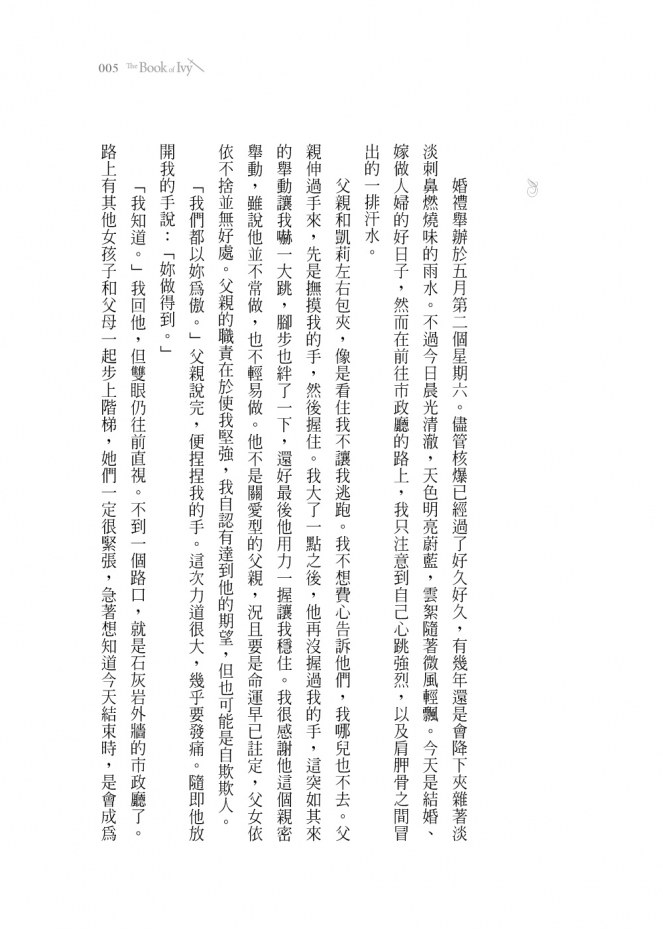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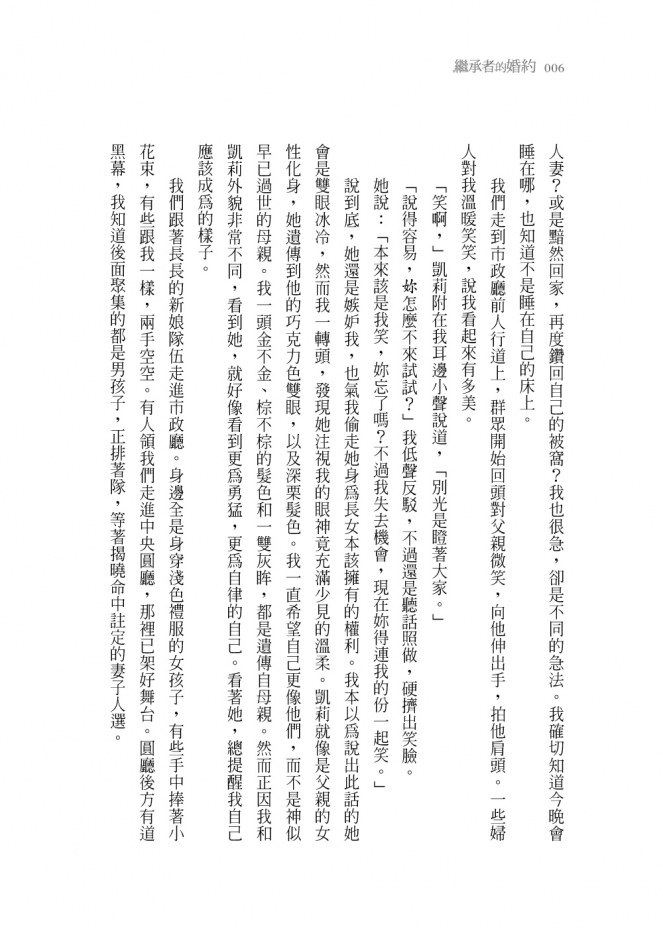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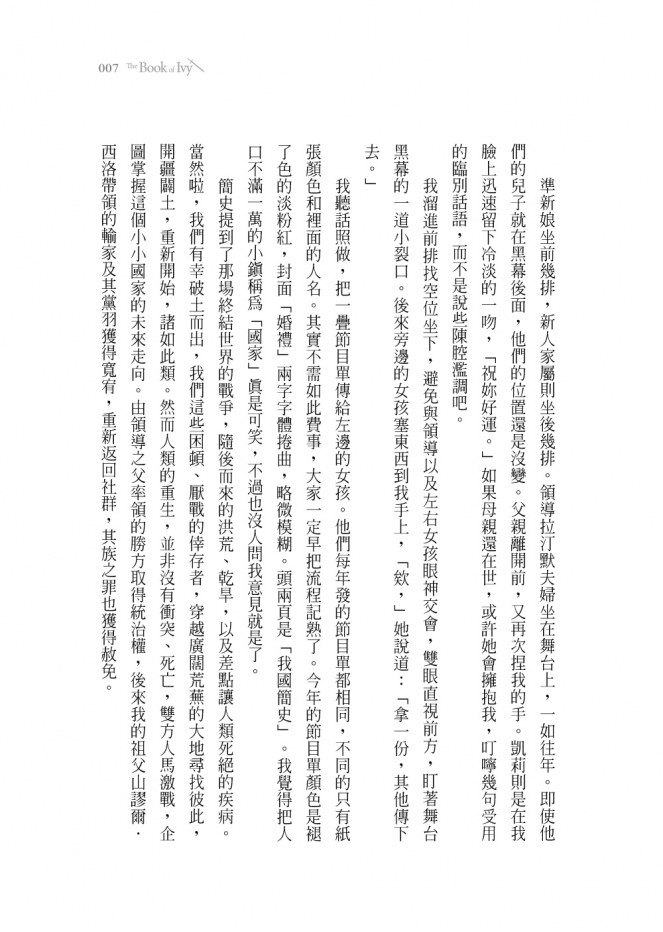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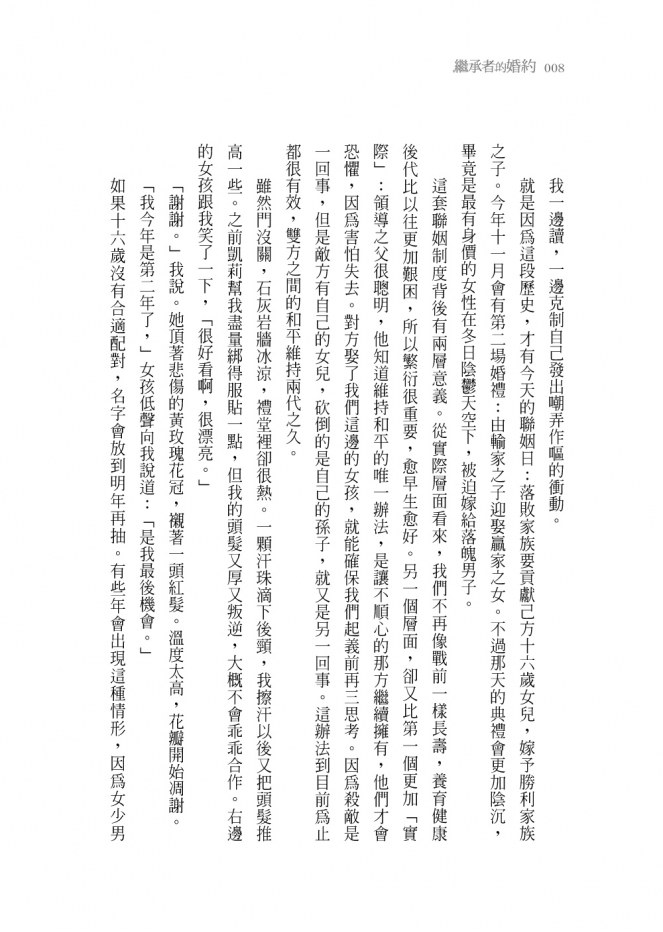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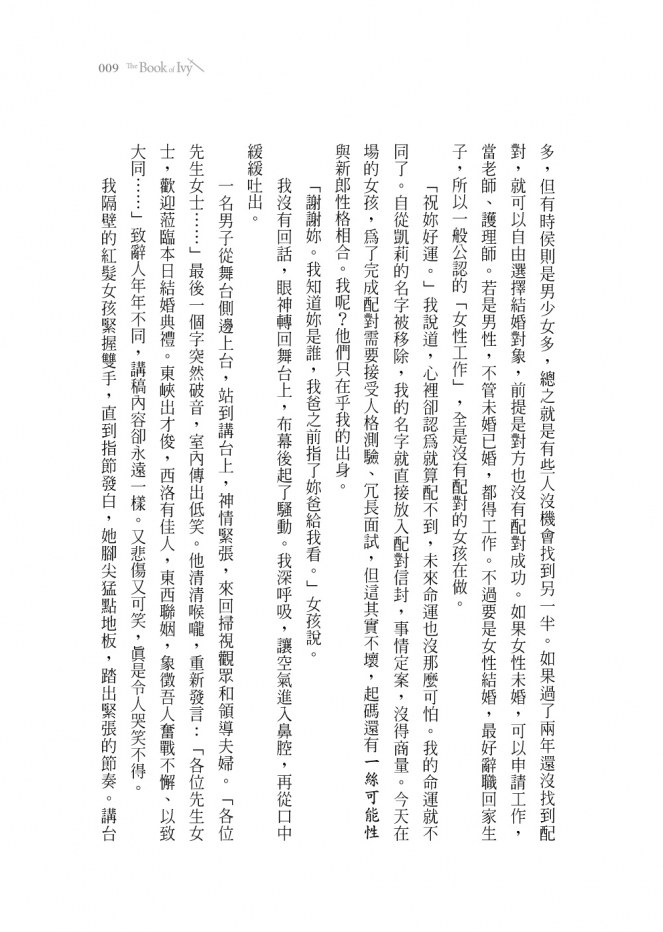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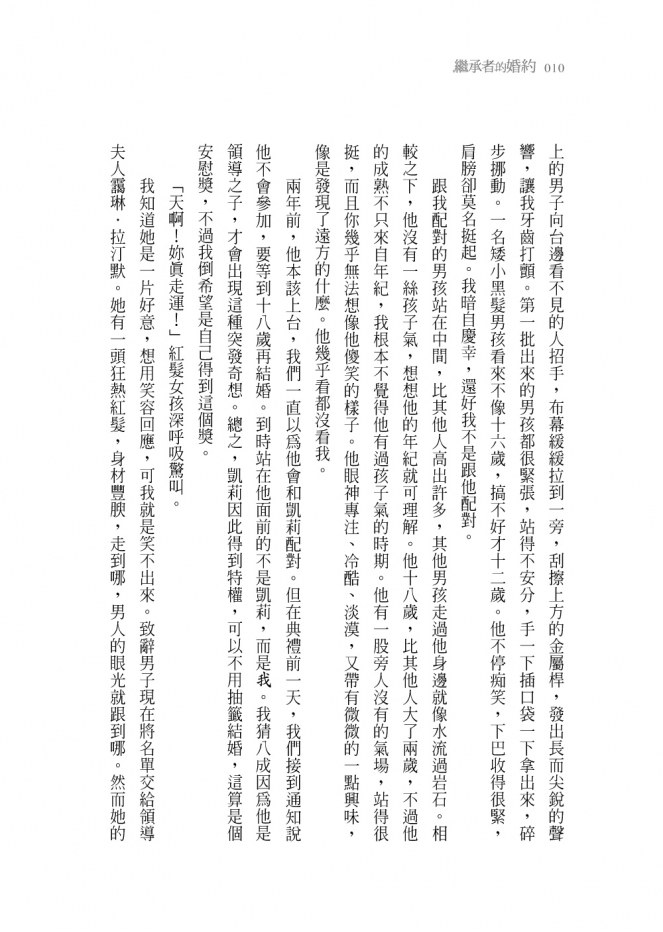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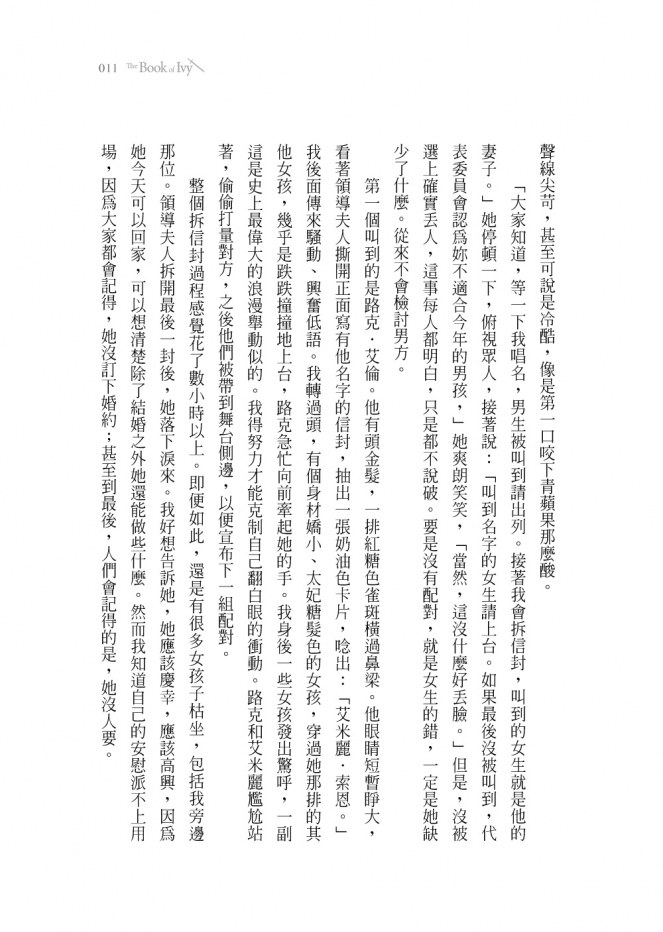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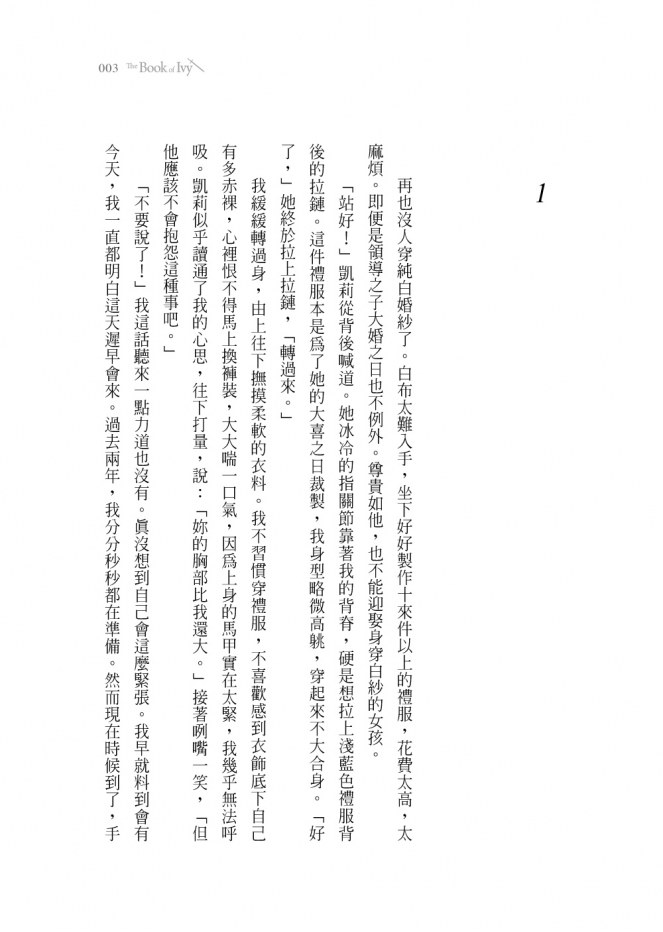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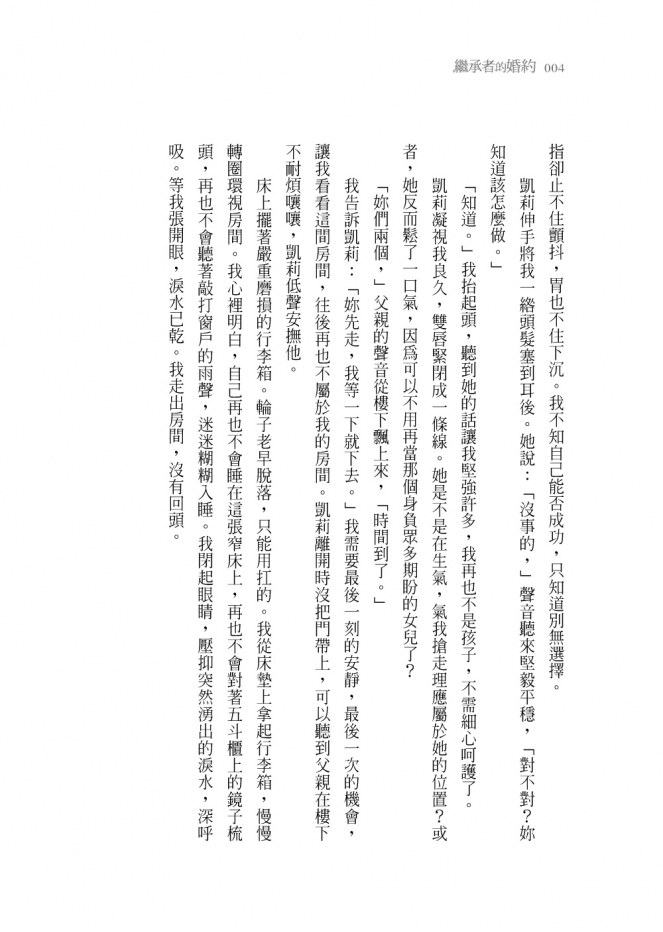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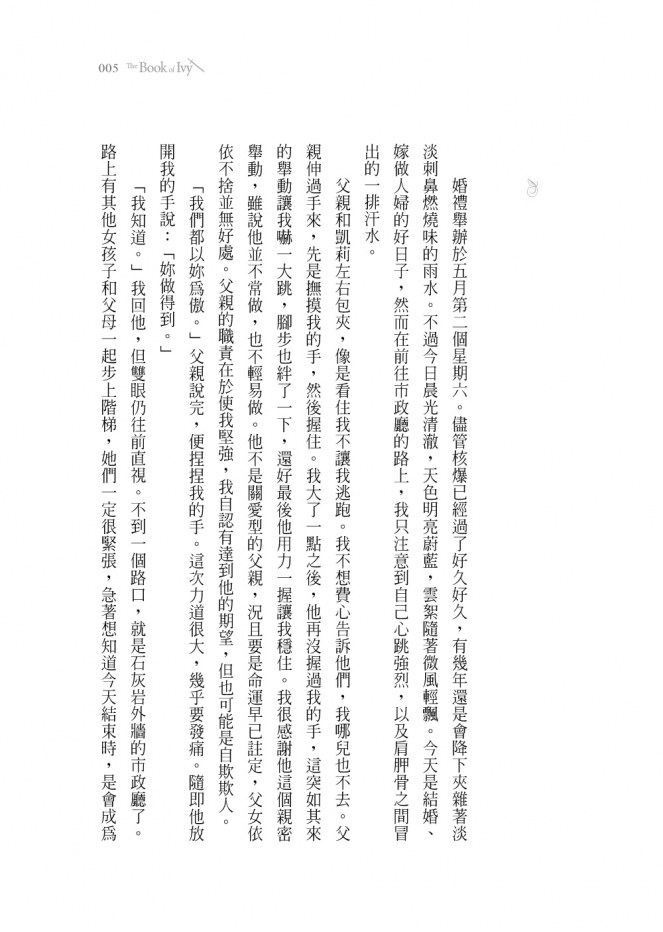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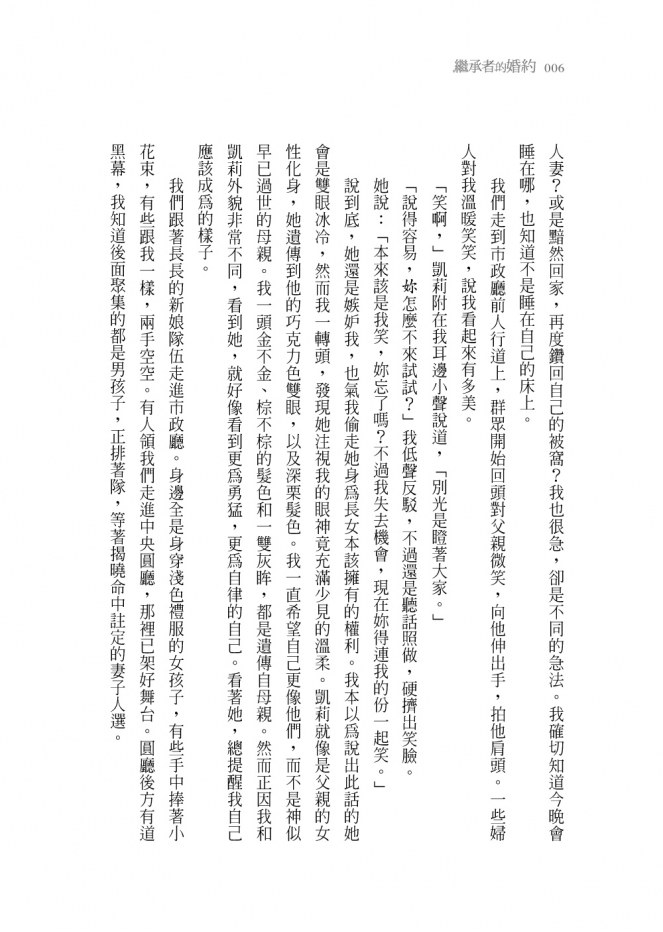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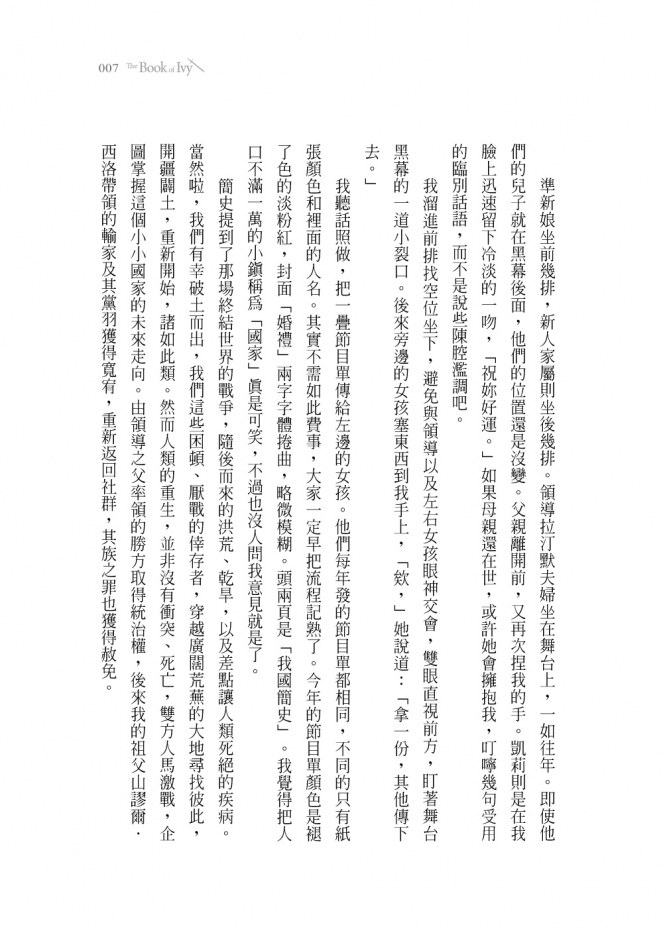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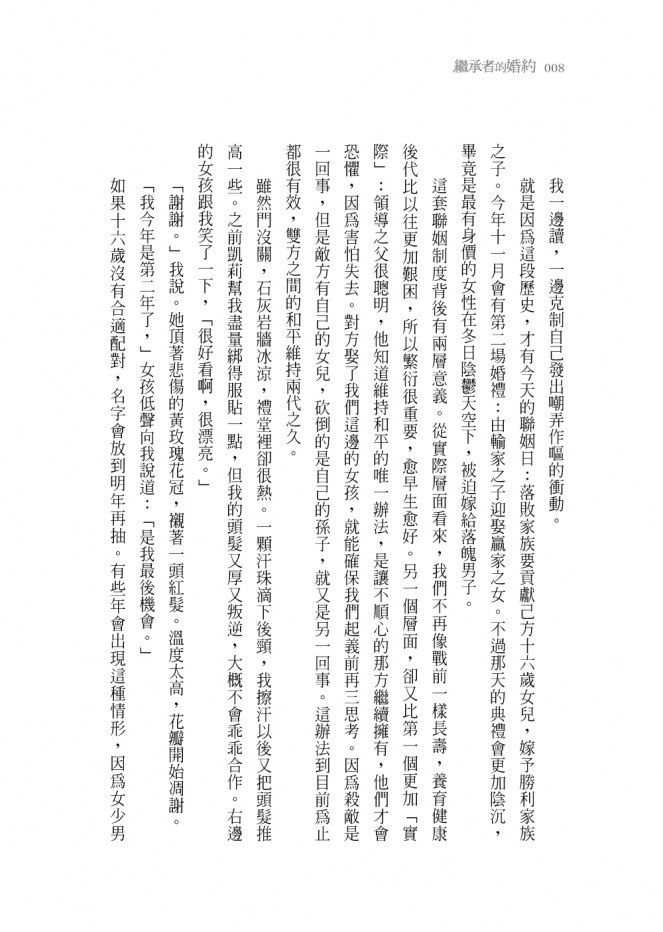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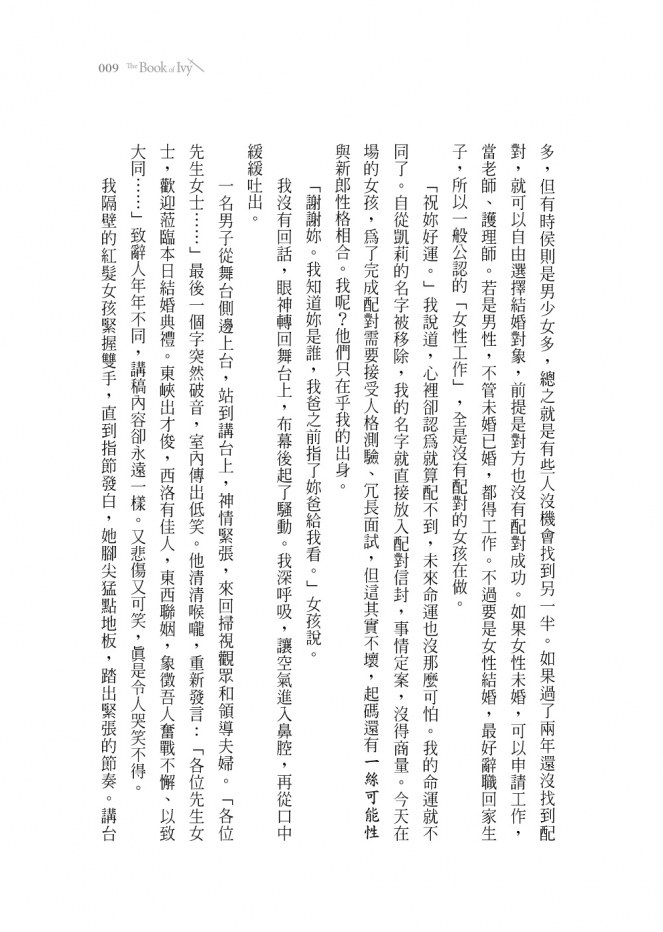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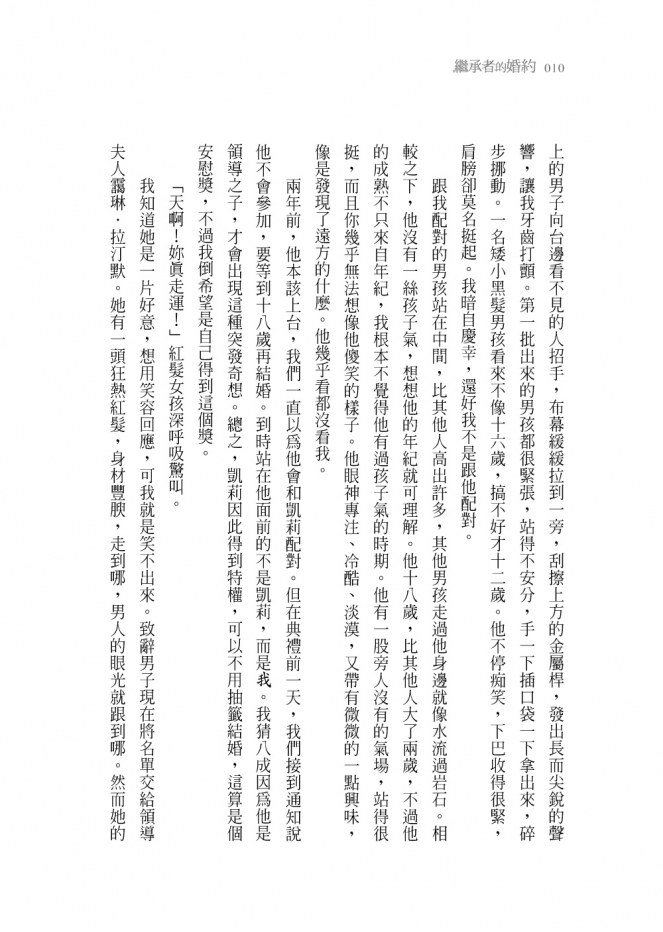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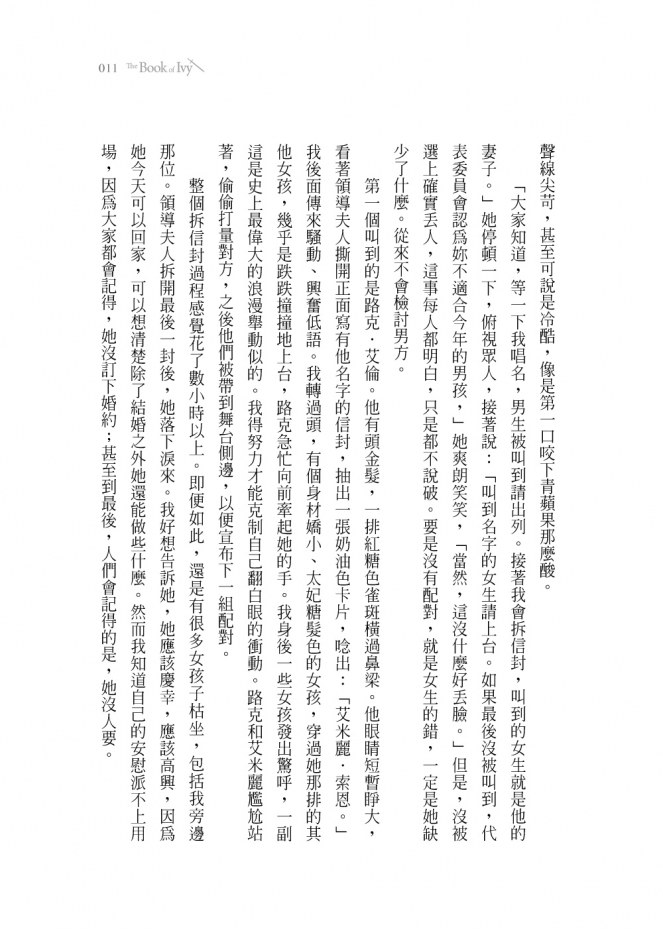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