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不承認事實」的照護敗仗
我是在二○一四年七月明確地發現住在一起的母親狀況不太對勁的。她吵著說:「我找不到存摺」。
我陪著母親一起找,發現存摺就放在平常保管的地方。
當我正鬆了一口氣,過沒幾天母親卻又說:「我找不到存摺」。
我找了一下,存摺就在原處。
這種情形發生了幾次,我發現匯入年金的帳戶存摺裡,被提領出整整一次剛匯入的年金。年金一次會匯入兩個月的錢,換句話說,對母親來說,一筆年金就等於兩個月的生活費,然而卻一口氣領出這麼一大筆錢,實在很不尋常。
我請母親讓我看她的錢包和其他保管現金的地方,卻都沒有發現這筆錢。我出示存摺問:「提這筆錢做什麼?」她回答:「我沒印象,我沒有提這筆錢。」後來我找了很久,但終究沒有找到這筆消失的兩個月年金。母親也不像被人詐騙的樣子,錢到底跑去哪裡了,至今依然不明。儘管我覺得應該就藏在家中某處。
出生於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的母親在這年八十歲。
在開始談照護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的家庭狀況。首當其衝負責照護的我,在二○一四年夏季的時候五十三歲,沒結過婚、單身,在父親留下神奈川縣的老家和母親同住,自稱紀實作家、科技記者,靠著採訪和撰寫文章糊口。家裡還有小我兩歲、擔任公共建設IT技術工作同樣單身的弟弟,以及小我十二歲,已婚有三個孩子的妹妹。弟弟住在東京,但工作繁忙,難以抽身;而妹妹在德國企業上班,一家人住在德國,因此無法期待他們兩人能成為照護的即戰力。
當自由自在的人生遇上照護
雖然發現有點不對勁,但這個階段我只覺得:「哎,媽也八十歲了,開始顯老了吧。」因為在這之前,母親一直相當活躍地享受人生。
我的外祖父是海軍軍人,外祖母是地方望族的么女,母親是四個孩子裡面的老二。海軍的家眷經常隨著調動搬家,母親家也不例外,她兒時在舞鶴、佐世保、逗子等日本各地遷徙成長。戰後外祖父母回故鄉落葉歸根,母親從當地高中畢業後,甚至繼續攻讀大學,專攻英文學,以昭和個位數年代出生的女人而言,相當罕見。母親大學時期沉迷於欣賞戲劇。她曾說:「三島由紀夫只要自己作品的戲劇上演,他就一定會去看」「年輕時的美輪明宏真的很漂亮」這類的事情。
畢業後,母親進入總公司在東京丸之內的某財閥大企業任職。以前母親常告訴我昭和三○年代前半,財閥大企業裡菁英上班族的職場百態,極為有趣,讓我覺得:「啊,原來如此,日本的勞動生產力會如此低落,就是這夥人的這種工作態度造成的。」
後來母親與新聞記者的父親相親結婚,依照當時的常識,結婚就得離職。她成為全職主婦,生下我們三個孩子,扶養長大。雖然是常有的事,但也曾為了婆媳問題爭吵不斷,也有過鬧離婚的時期,但最後總算是克服了危機。後來母親運用她的英文能力,開了家只收少數幾名國中生的私人補習班。五、六十歲時,她靠著開補習班存下的錢旅遊國內外。在母親七十歲的時候父親過世了,之後她也參加合唱團、練太極拳、學習法文、西班牙文和中文,頗為忙碌地享受著人生。
母親的身體向來都很健朗,從未生過大病,因此孩子們心裡總認為:「媽一定會就這樣漸漸地老去,不會給身邊的人造成太多的麻煩,活得很長壽,然後一下就過去了。」
我們錯了。
事後回想,約在二○一三年的夏季,就已經有了徵兆。母親基本上都會把身邊環境打理得很整潔,但她開始懶得打掃,任由東西亂丟。同一時期,牙膏、番茄醬、美乃滋等消耗品都還沒有用完,她卻一個接一個拆新的來用。因為她沒辦法在冰箱或櫃子裡找到用到一半的東西,只好不斷地拆新的。待狀況明朗後,我整理母親的房間,發現她平常總是詳細記錄各種行程的記事本停留在二○一四年二月,後面則是一片空白,她已經沒辦法管理自己的行程了。
母親原本相當注重三餐,但是從二○一四年三月開始,她漸漸懶得煮飯,晚餐只吃生雞蛋拌飯之類的懶人料理,相較於從前的母親,這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她經常吃得一片狼藉,調味也變得不正常,常發生把鹽巴當成砂糖這類的事情。二○一四年六月起,發生了多次鍋子和水壺放在瓦斯爐上忘記關火的意外。「萬一失火怎麼辦!」我罵了好幾次,卻不見改善,便禁止母親使用瓦斯爐,母親抗議:「我要喝茶,不燒水是要怎麼泡茶?」後來妹妹出點子並出錢,買了電熱水壺,我於是嚴格叮囑「以後要用這個燒水」,但母親還是繼續用瓦斯爐,我索性把水壺藏起來,母親這才心不甘情不願地用電熱水壺燒水。
接著七月又發生了「存摺不見了」的騷動,八月以後,我好不容易說服母親,存摺平日交由我保管。
想要當成只是「健忘」
儘管有這麼多的前兆,而且依時間將這些前兆排列起來,可以發現狀況顯然日益惡化,但我卻判斷母親的狀況是「符合年齡的健忘」。
我基於這樣的判斷認為:「即使往後體能會逐漸退化,但母親自己能夠做的事,還是要盡量讓她自己做」。「媽,我幫妳做這個、我幫妳做那個」,這種態度乍看之下是孝順,但搶先替母親辦妥每件事,反而會加速她的退化。即使母親埋怨有些吃力,只要她還有自主行動的意志,就應該讓她自己做。像保管存摺這種交給母親處理會有危險的事情則攬下來,此外的事,則必須盡可能讓她自己處理。不過,這一切的前提都是「那是符合年齡的退化」。
其實我是不願意承認事實。
沒有人想要扛起麻煩。
只要承認眼前的事實,麻煩就會入侵自己的生活。所以我才不願意正視事實也說不定。
如今回想,這真是大錯特錯。
被無止境的照護壓垮,終於對母親動手
退化的腳力,量增加的尿失禁,三番兩次在廁所排便失敗──由於衰老和阿茲海默症一起惡化,二○一六年秋季母親變得衰弱,照護起來更勞心勞力了。進入十月以後,除了這些問題以外,暴食也再次發作。
我總是在晚上六點左右準備好晚餐,但現在只要稍微遲了一點,母親就會亂翻廚房,把冷凍食品丟得到處都是。「我好餓好餓,餓得快死了,誰叫你不做飯給我吃!」──食欲應該是最原始而且最根本的欲望。不管我再怎麼說、怎麼求、怎麼生氣,母親就是不肯停止這種行為。
自我崩壞時,一定都有前兆。
這次的前兆,是呈現為「要是可以把在眼前搗亂的母親痛揍一頓,一定會很爽」的念頭。我的理性清楚這是絕對不可以做的事。對彎腰駝背、連站都站不穩,只是跌倒就會骨折的母親,如果我真的動手打下去,絕對不只是普通受傷的程度而已。如果因為我動手,害母親死掉,那就是殺人,也就是葬送我自己的前途。然而儘管理性這麼想,腦中的幻想卻無法遏止地擴大。
很簡單啊。
只要握緊拳頭,舉起手臂,揮下去就行了。
只是這點動作,就可以讓你痛快無比。
有什麼好猶豫的?這個生物讓你吃了這麼多苦,你只是給她一點教訓罷了啊。握拳,舉起來,揮下去──只是這樣,就可以甩掉你現在感受到的痛苦沉重壓力,暢快大笑。
世上有所謂「惡魔的呢喃」,在我這樣的精神狀態中,所謂的惡魔肯定就是我自己。這呢喃就是精神即將因為壓力而崩潰的聲音。
終於動手了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我比平常晚進廚房。結果母親把冷凍食品丟得到處都是,看到我便直喊:「我餓死了!我餓死了!」明天是星期天,我也得自己做晚飯。我心想「明天絕對要守時」,然而腦中還有另一個清楚的聲音在作響:「揍她,明天她敢再這樣,就揍死她!」
隔天二十四日傍晚,我就像平常那樣出門買東西,結果比預定時間晚了一些。我急忙趕回家時,已經超過晚上六點了。但我記得應該連五分鐘都沒有超過。
我鬆了一口氣,心想趕上了,然而迎接我的,又是丟得整個廚房都是的冷凍食品,以及母親的怨懟:「我餓死了!我餓死了!」
回過神時,我已經打了母親一巴掌。
母親沒有退縮。
「居然打你媽,你這個不肖子!」她握住雙拳,朝我撲打上來。衰老的母親的拳頭捶在身上一點都不痛,然而我卻無法控制已經爆發的暴力衝動。我閃開她的拳頭,又甩出一巴掌。「你竟敢、你竟敢……!好痛!可惡!」母親嚷嚷著打過來,我又是一巴掌。
之所以打巴掌,應該是出於無意識的自制:「萬一用拳頭打下去,就無可挽回了。」回想起當時我的心情,是「快住手」的理性與「幹得好」的解放感彼此衝撞,陷入奇妙的麻木狀態。也毫無現實感,就好像身處在夢境裡一樣,我和母親彼此拉扯,毆打對方。不,互毆這樣的形容對母親並不公平。因為我一點都不痛,但母親一定很痛。我無法阻止我自己,不停地甩母親巴掌。
一直到看到鮮血,我才回過神來。母親咬破嘴巴了。
我一停手,母親立刻一屁股癱坐在地。她按著臉頰,不停地喃喃:「居然打你媽、居然打你媽……」我陷在整個人被撕裂般的無動於衷當中,無計可施,只能看著母親。
漸漸地,母親喃喃自語的內容出現了變化。
「咦?我的嘴巴怎麼破了?我怎麼了?」──無法記住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嗎!瞬間,感情重回我的心中,一陣戰慄竄過背脊。我留下前往洗手間的母親,關進自己的房間裡。我甚至提不起力氣思考,望向手機,發現德國的妹妹傳LINE過來。
向妹妹傾吐,脫離危機
我透過SKYPE告訴妹妹自己做了什麼事。一方面是因為如果不找人訴說,我覺得我會瘋掉,而且我認為必須藉由告訴別人,來預防自己再犯。不管我做什麼,母親都不會記得。我害怕在這種狀態下,暴力變成習慣,逐漸升級。妹妹似乎立刻就掌握狀況了,她說:「好,我來連絡照顧管理專員T先生。我想哥已經到極限了,我們來好好想個辦法吧。」
隔天T先生立刻連絡我:
「我收到令妹的電郵,了解狀況了。我想松浦先生需要休息一陣子。總之先請令堂去短期住宿兩星期吧。透過休息,爭取時間,然後再來思考往後的事。需要的手續,全部交給我處理吧。」
然後他又說:「坦白說,在我看來,我也覺得這陣子的松浦先生已經到了極限了。我覺得你真的夠努力了。」
真的夠努力了──我想對於終於做出暴力行為的家庭照護者,應該已經有了一套固定的範本說詞。但即便如此,這句話還是深深地撫慰了我。
母親告別老家
二○一五年和二○一六年,妹妹過年的時候都帶著三個孩子從德國返鄉,但是二○一六年底,她一個人回來了。因為我們三兄妹要處理麻煩的行政手續,無暇照顧小孩。二○一六年年底到二○一七年初,我們三兄妹在照顧管理專員T先生的帶領下,參觀了各家機構。我們在附近看了約七家特別養護老人院和團體家屋。
這些機構如同字面形容,真的是形形色色。
比方說,一樣是特別養護老人院,有些地方設備充實、員工開朗活潑,但有些地方總讓人感覺陰暗冰冷,就好像走廊角落有死神默默地在守株待兔。而團體家屋會反映出院長的個性和經營主體的經營方針,差異就更大了。看這情況,如果不找到一個適合母親個性的機構,母親就太可憐了。
有一家團體家屋,我們兄妹一致認為「這裡應該會適合母親」。它位在離家距離適中的郊外,就在田地正中央,窗外的景致也不錯。附近有幼稚園,日常生活中也會與幼童進行交流。最重要的是,那裡的方針是「與老人一起生活」,而不是「管理老人」,在各方面都不會過分拘泥規則,我們覺得很適合母親。但這裡也不例外,早已額滿了。
由於可以同時向多家機構提出入住申請,因此包括這裡在內,我們總共申請了五家。其中一家是預定二○一七年四月開始經營的大型特別養護老人院。因為會一口氣收滿一百名,感覺比較容易進去,這家新機構似乎會成為最後的希望。
母親發揮驚人的好運氣
照護機構的入住申請,並不是依「申請順序」入住。
申請入住的文件中,會寫明當事人是什麼狀況而希望入住。各機構如果有空額,就會比較申請人的狀況,從「認為最有需要的人」開始接納。就像前面寫的(P211),特別養護老人院和團體家屋都大排長龍,感覺需要很久才能輪到。參觀的時候我們得到的說明是「如果運氣好,立刻就可以住進來,但也可能要等很久,無法一概而論」。
特別養護老人院因為二○一五年四月的制度修正,原本「需支援二」的人就可以入住,但現在原則上變成「需照護三」以上才可以入住了。因此據說等待時間縮短了一些,不過在二○一七年一月當時,各家機構的第一線,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敢說「變得更容易入住了」。
年節前後,母親在妹妹的照護下度過。比起我粗枝大葉的照護方式,同為女性的妹妹似乎更能體貼入微地照護,母親看起來很高興。也應該說多虧了妹妹吧,十月的時候令我頭痛不已的暴食症狀也完全停止了。妹妹照護的期間,我可以去鹿兒島出差。一月半妹妹返回德國後,母親又去短期住宿。這時遇上了一個問題,就是短期寄宿最多只能占「需照護」有效期間(母親是一年)的一半。這項規定是為了防止家屬利用「短期住宿」把老人丟在機構,實質上當成安養院使用的狀況。如果母親排隊超過半年,就必須另覓其他的方法。
但這些擔心是多餘的。沒想到母親在這時候發揮了強大的好運氣。
一月十八日,我們兄妹一致同意「這個地方最好」的團體家屋,透過T先生連絡「有空額了」。我大吃一驚,連絡團體家屋,K院長說她提前去短期住宿的機構見母親,甚至已經面試結束了。「我們努力以家庭的方式經營,覺得令堂很適合我們,可以在我們這裡一起生活。」沒想到居然這麼快就能入住,運氣好到不敢相信母親兩年前因為跌倒而錯失了難得的新藥臨床試驗機會。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四十一年又十個月
入住的時候,我們必須和K院長一起確認一大堆合約內容,捺下許多印章。但想想先前的種種辛苦,這根本不算什麼。入住費用除了母親每個月的年金全額以外,只要我們三兄妹每個月各出一萬五千圓,就可以持續支付下去。
如果直接說「要送妳去安養院」,母親一定會驚訝、生氣、徹底反抗。我和照顧管理專員T先生多方研究之後,決定在入住的一月三十一日,直接從短期住宿機構轉移過去,並向母親說明「要把妳送去住起來更舒服的地方」。
一月二十日星期五到二十三日星期一,成了母親在自家生活的最後一段日子。搬進團體家屋後,主治醫生也會換成機構的家庭醫師。二十一日星期六,是H醫生最後一次診察。照顧管理專員T先生已經向H醫生說明狀況,醫生說「考慮到現況,我認為搬進團體家屋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由親人照護,無論如何都有極限,不管再怎麼努力,到最後還是會無法保持和顏悅色。放心吧,只要拉開距離,你又可以繼續對令堂溫柔了。」
就像T先生說的「你夠努力了」一樣,H醫生的話,或許也是對家暴者的制式安慰。即使如此,兩年半以來必須一肩扛起照護責任的我聽到這話,還是忍不住感激得流下淚來。
我心想這是最後了,準備了特別豐盛的晚餐。
星期六做了壽喜燒。母親說「好好吃」。
但隔天的星期日一早卻不好了。
一早起床,母親正把被大便弄髒的被子放在膝上,呆呆地看著電視。廁所、床鋪和地板,到處沾滿了糞便。洗衣機裡,被大便弄髒的被單塞進了一半。應該是想要自己收拾善後,拿到洗衣機,記憶卻就此中斷了。我脫掉母親全身的衣物,在浴室用蓮蓬頭沖掉沾在身上的糞便。然後清掃地板,噴上殺菌劑。髒衣物先浸泡氧系漂白劑,接著用流水沖掉全部的糞便,然後丟進洗衣機。連我自己都覺得經過這兩年半的訓練,動作變得相當乾淨俐落。母親不停地說「對不起、對不起,讓你做這些事」,但說到一半就停住了。沒辦法,她的記憶無法維持。
都到了這個節骨眼,我還是對於把母親送進安養院感到十分罪惡。都已經精神承受不了而毆打母親,實在沒資格說這種話,但既然母親還想繼續住在這個家,我還是想要成全她的心願。但是這樣的心情也在清理糞便的過程中消失得一乾二淨了。二○一五年七月母親肩膀脫臼時,我就決定「母親還能自行排泄的時候,就在這個家照護她」。而這天早上的排泄失敗,讓我的心情變得堅定:我能夠做的,都已經做了。
雖然有點擔心母親的腸胃,但再怎麼說,今晚都是母親在家的最後一個晚上。不在這時候讓母親享受,更待何時?所以晚上我不惜重本買了高級牛肉,煎了牛排。因為是多脂的霜降肉,量並不多。母親一樣說著「好好吃」,全部吃完了。事實上,我認為母親腸胃健康,真的是很寶貴的資本。
隔天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母親沒有排便失敗,清爽地起床了。她在居服員的協助下收拾準備好,渾然不知再也不會回到這個家,以為是要去平常的短期住宿,出門去了。
看著她的背影,我的腦中浮現的是──如果要笑我是動畫宅就笑吧──電視動畫《紅髮安妮》(一九七九年)接近尾聲的一集〈馬修離開我家〉。沒錯,是前年七月離職的居服員K女士年輕時曾經在同一個職場共事的高畑勳負責演出的一集。在那一集,領養孤兒安妮的馬修與瑪麗拉兄妹中的哥哥馬修離世,描寫了他的葬禮。
母親在亡父興建的這個家中,度過了一半以上的人生,總共四十一年又十個月。下次可以回家,應該是今年的年底,但從母親老化的速度來看,也不知道她能否再次歸來。
一個家庭的一個時代,就這樣結束了。
看到地毯的痕跡,湧出真實感
其實我沒有太多的時間沉浸在這樣的感傷之中。接下來的幾天忙碌得可怕。照顧管理專員T先生從事務所借來專門接送輪椅使用者的廂型車,附有升降機,我和T先生用那台車把母親的東西載到團體家屋去。電視機、邊櫃、衣櫃、換洗的衣物和內衣褲。不夠的東西以後再送去就行了。床鋪因為上一名入住者(據說過世了)的家人留下來說「請給後面的人使用」,因此我們感激地收下了。
直到最後,我真的受到T先生莫大的關照。T先生說:「這是我份內的工作,不用謝。」但如果沒有他的專門知識和切中需求的照護計畫,我應該沒辦法照顧母親直到今天。我也連絡K院長,討論送母親過去的步驟。我說母親一定又會抗拒到底,但K院長可靠地說:「放心,我們是專家。」
租賃業者到家裡來,回收租用的照護床和廁所輔具。由於照護的主體轉移到團體家屋,如果下次母親暫時回家,需要床鋪時,就不會有政府補助了。到時候必須全額自費租借。
一月三十一日入住當天,我叫了照護計程車,從短期住宿機構把母親送去團體家屋。這是專門接送需要照護的老人的計程車,連輪椅或臥床失能的人都可以載。我先去團體家屋等待,不久後母親坐著照護計程車過來了。
不出所料,她戒心十足地質問我:「不是要回家嗎?你到底把我帶到哪裡了?」
「短期住宿要延長一些,所以我幫妳找了個住起來更舒服的地方。」我搬出預先準備好的「不算謊言的說明」。但母親聽不進去。「這裡是哪裡?」「你要把我怎麼樣?」她不停地問,賴在玄關不肯移動。「接下來由我們接手吧。」K院長不讓母親聽見地小聲對我說。「以前我們也遇過幾次這樣的情形,令堂很快就會平靜下來了。如果看到你在這裡,她也會很激動,所以你暫時回去一下比較好。」
母親還是一樣鬧脾氣不聽話。但我認為似乎已經沒有我能做的事了,趁著母親沒留神的時候,悄悄回家了。
家裡的老狗迎接我回家。
牠也已經十五歲了。或許照顧完母親,接下來就得照顧老狗了。牠身為我們家的一分子,陪伴母親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必須好好地照顧完牠這輩子才行。
母親當成房間使用的起居間地毯,一清二楚地留下照護床的腳的壓痕。地毯上也有黃色的污漬。是母親尿失禁的痕跡。不管怎麼清都清不乾淨。由於母親有可能暫時回家,所以還不能更換地毯。如果要換新,就是母親離世以後的事了。
冷不防地,心底湧出「終於告一段落」的真實感來。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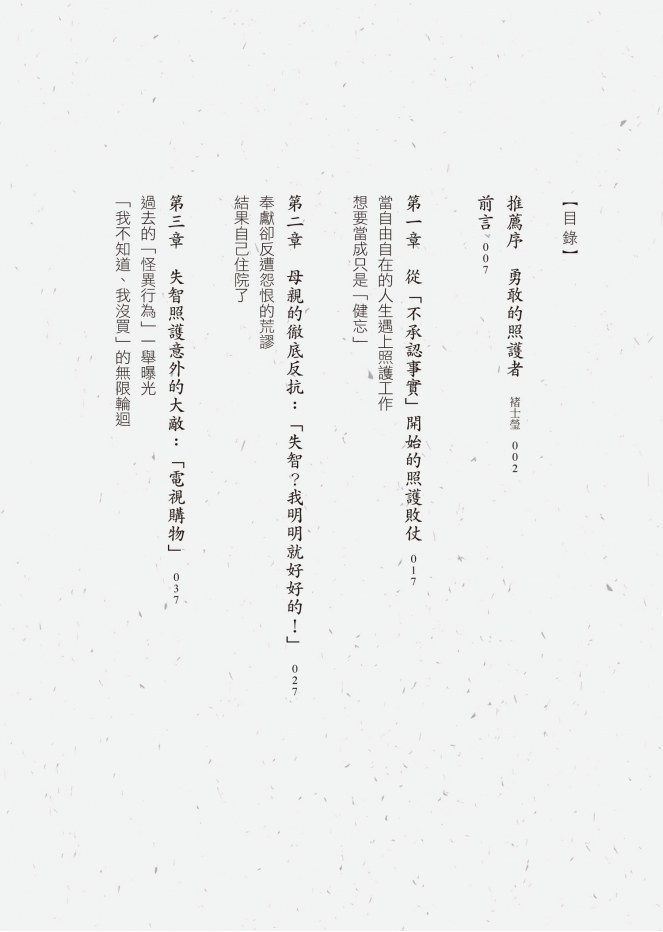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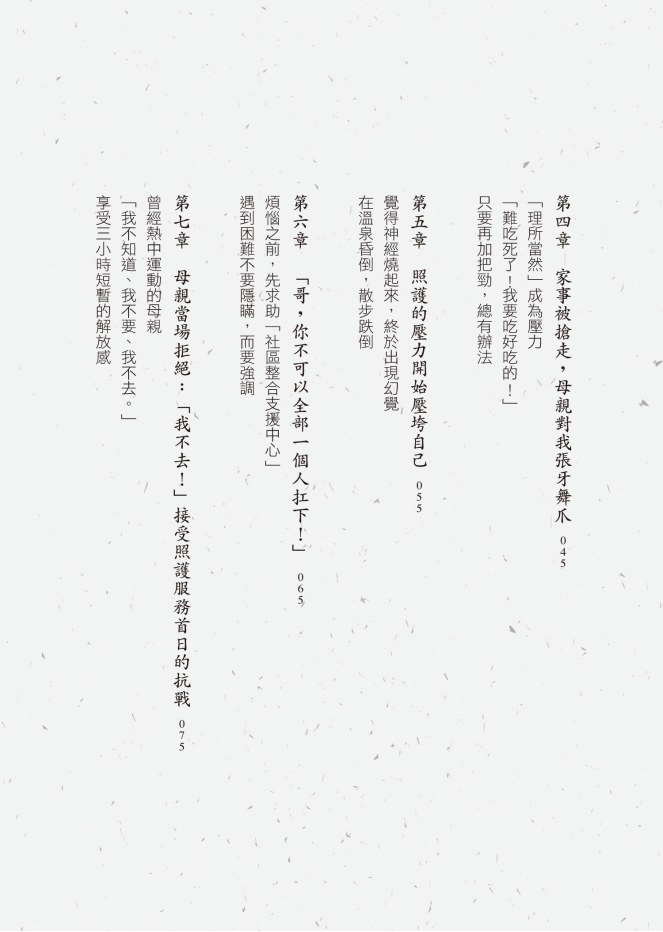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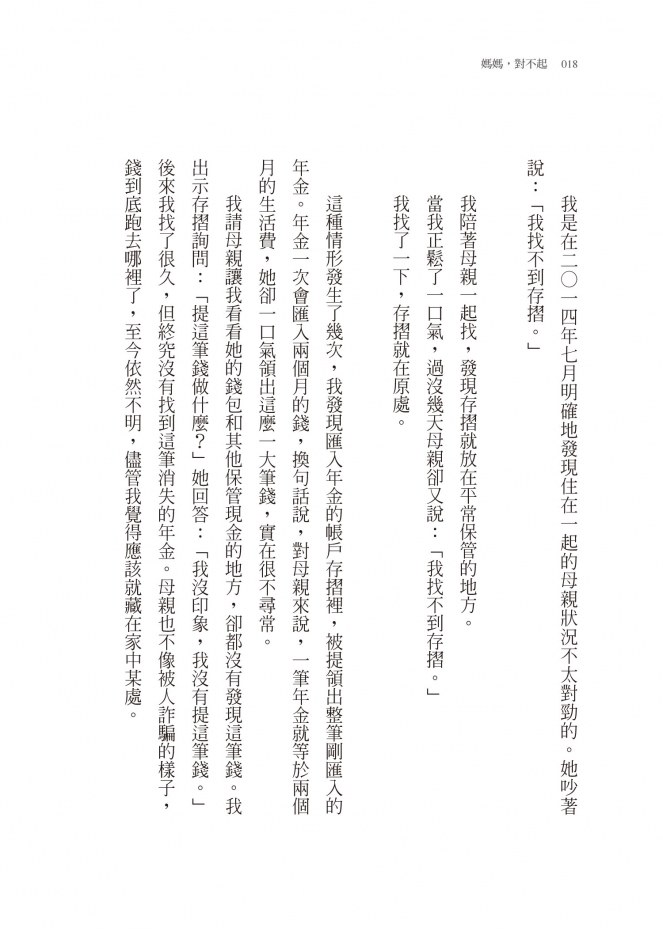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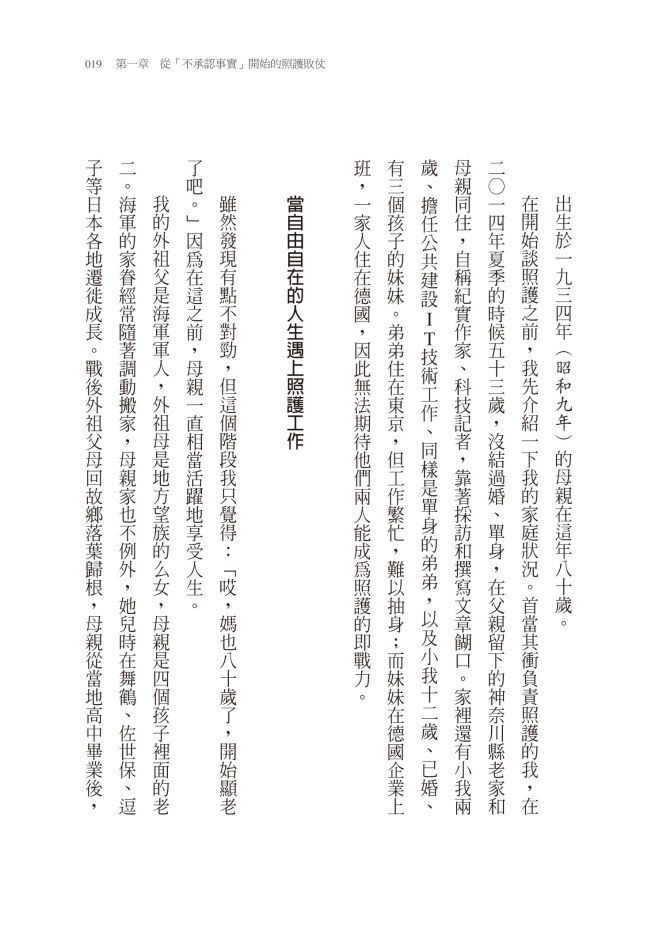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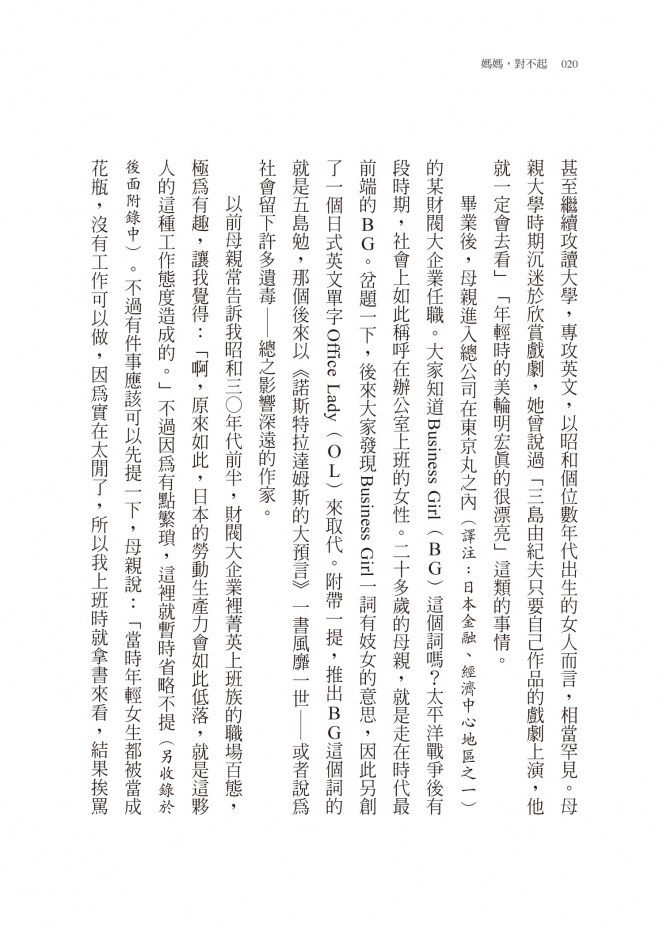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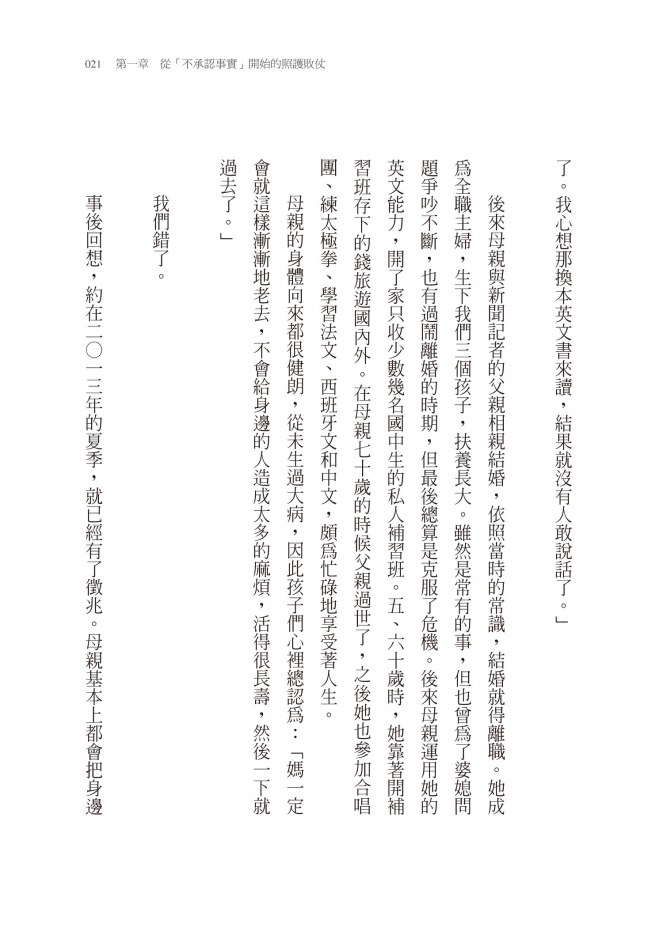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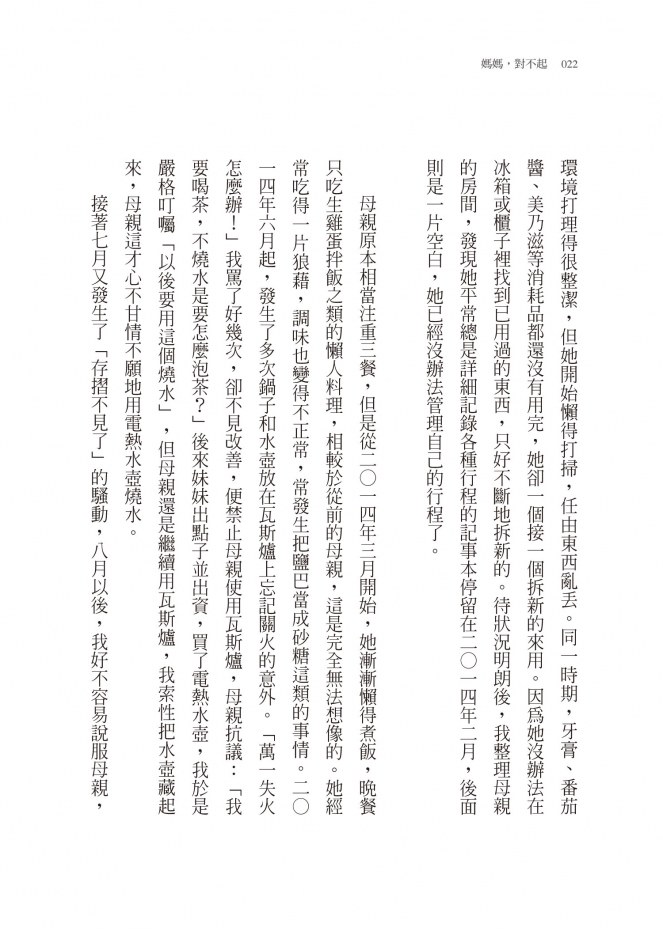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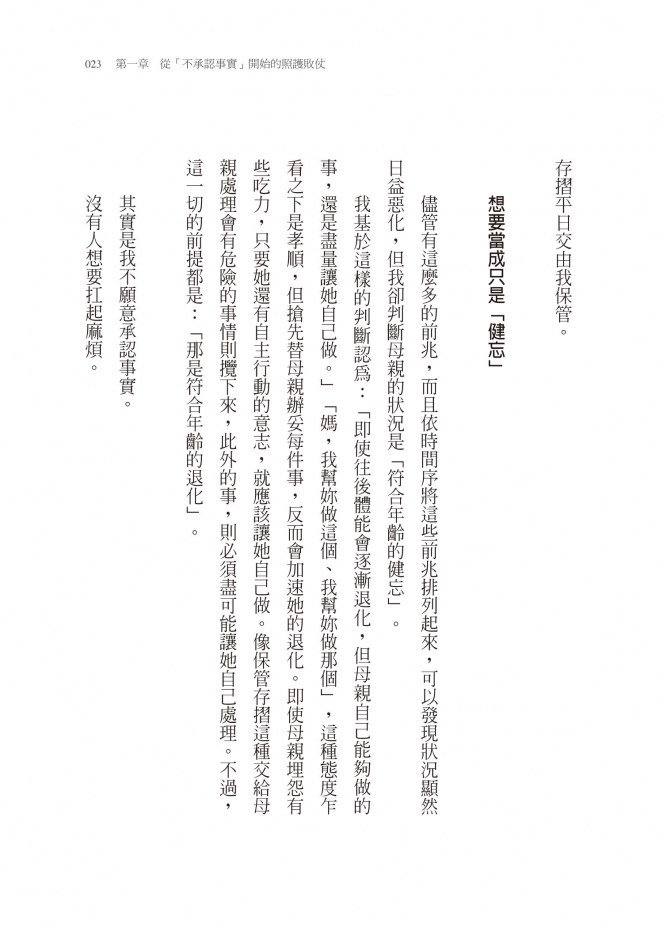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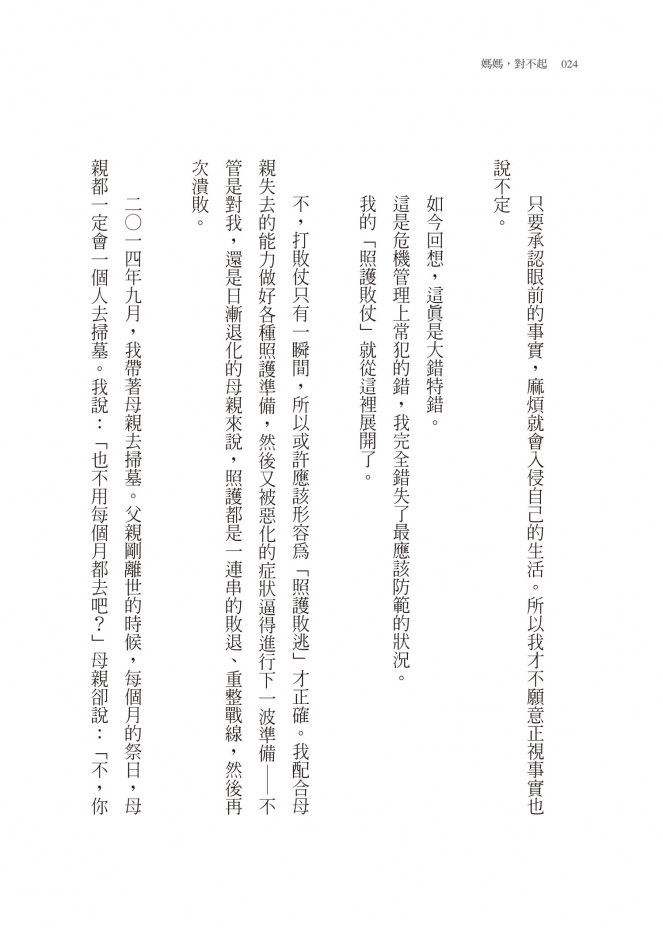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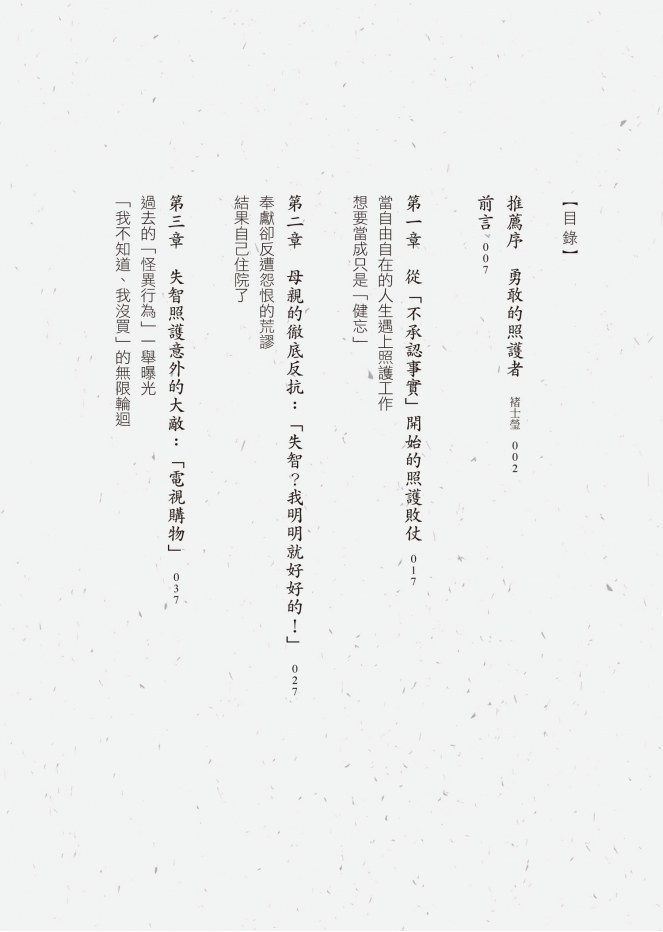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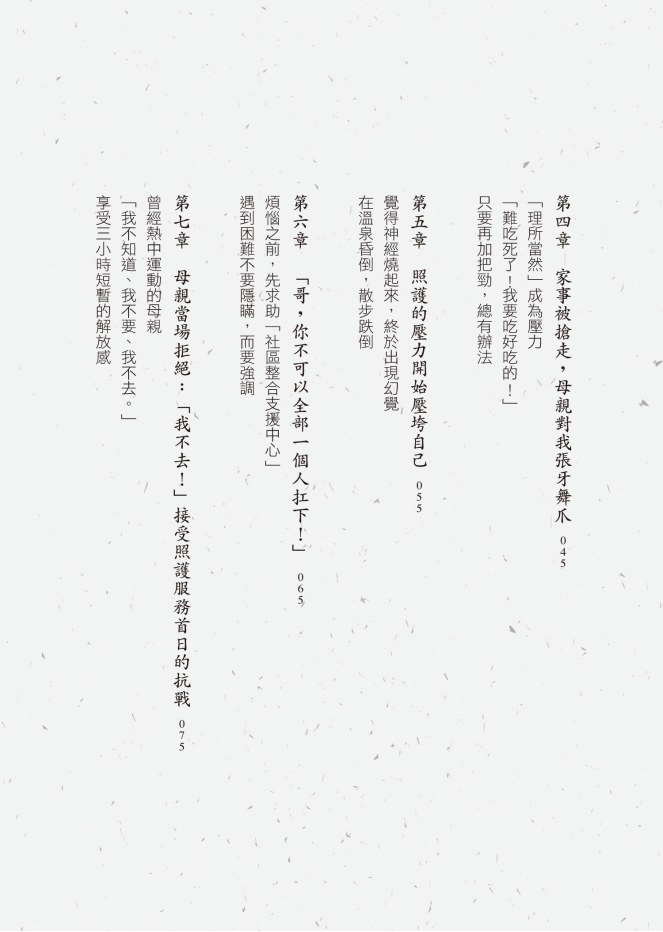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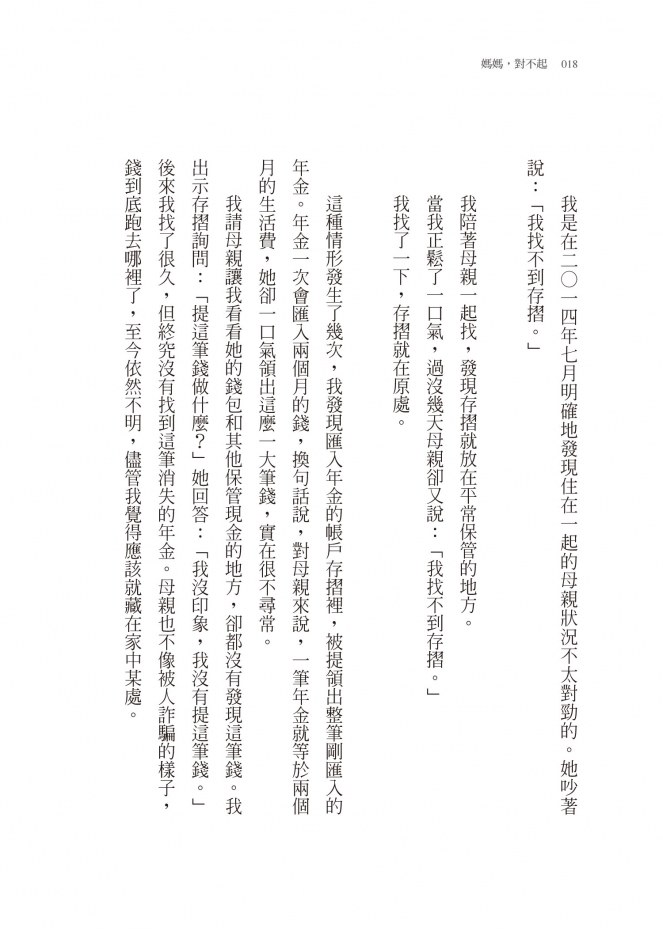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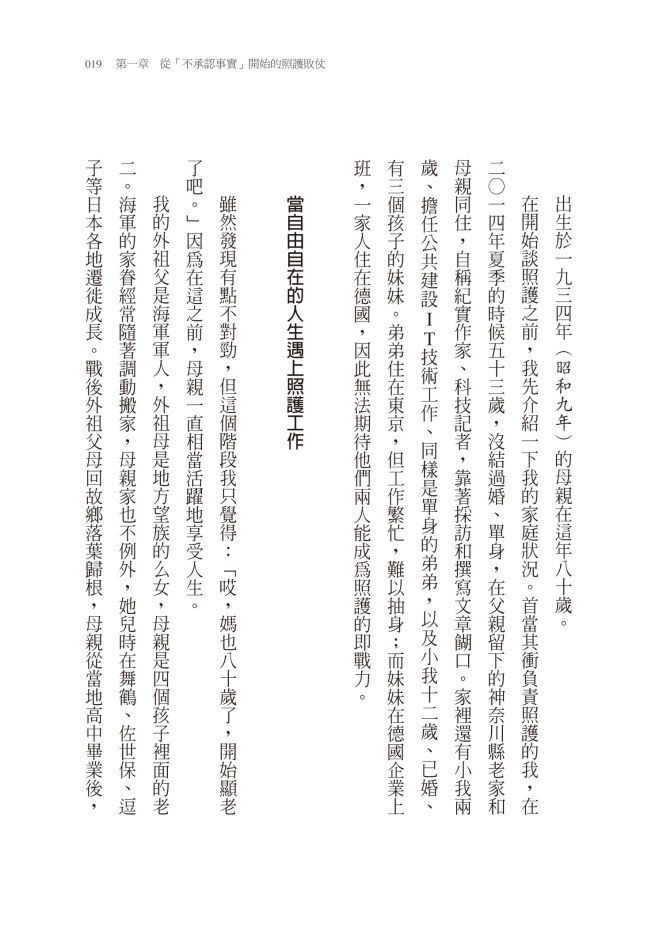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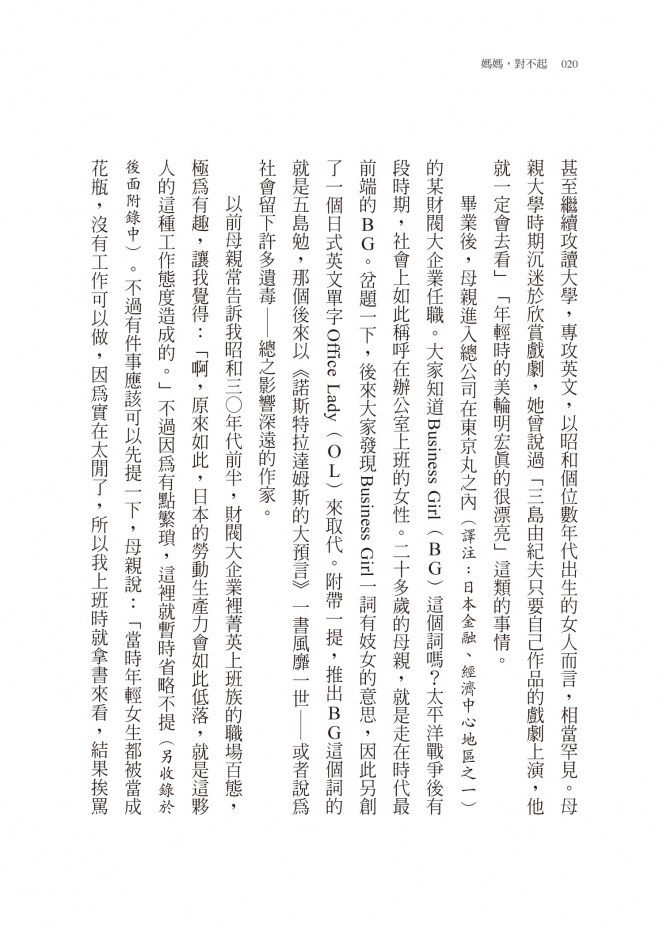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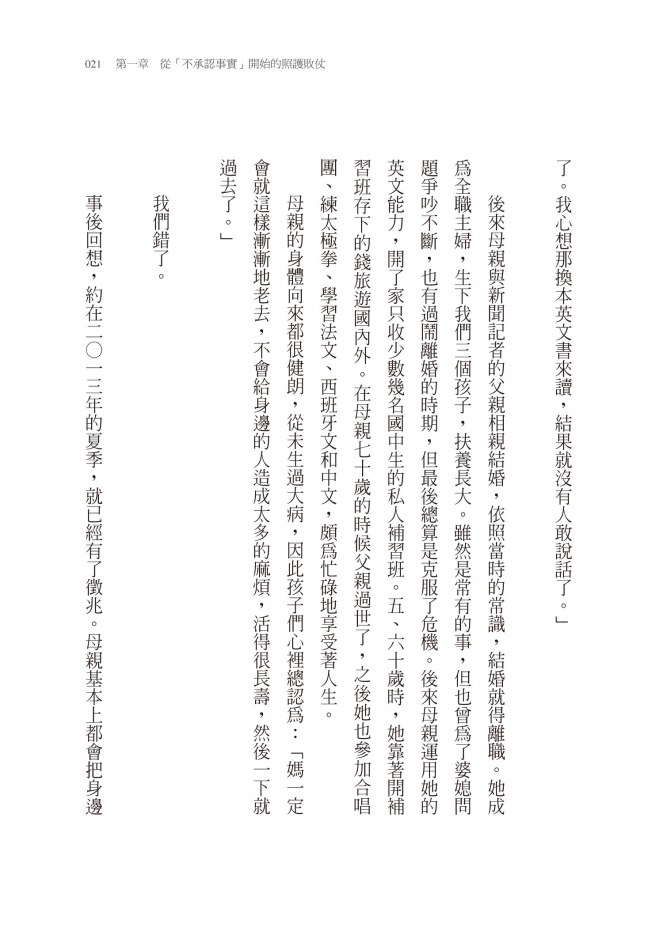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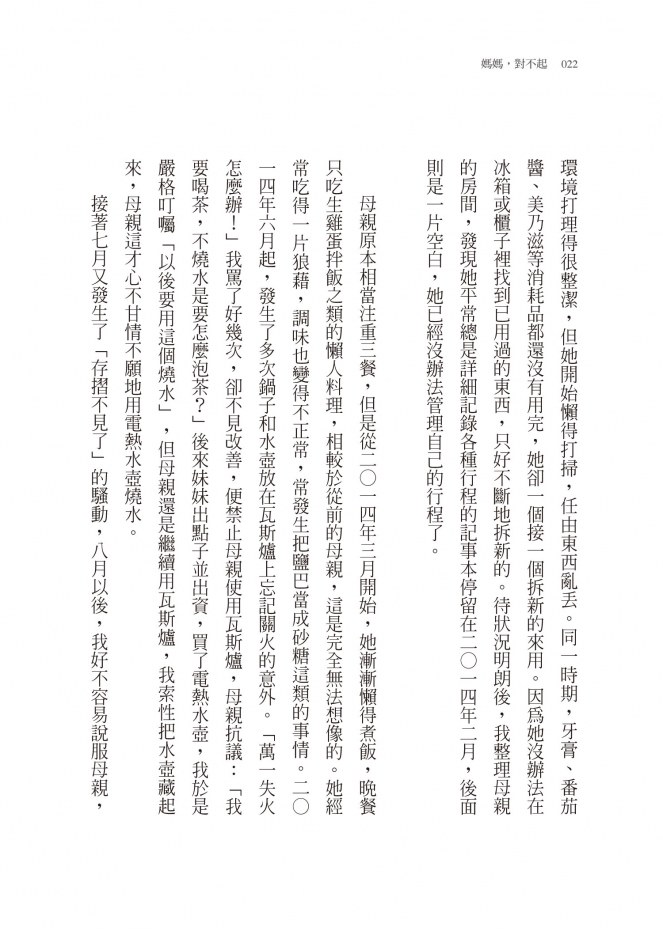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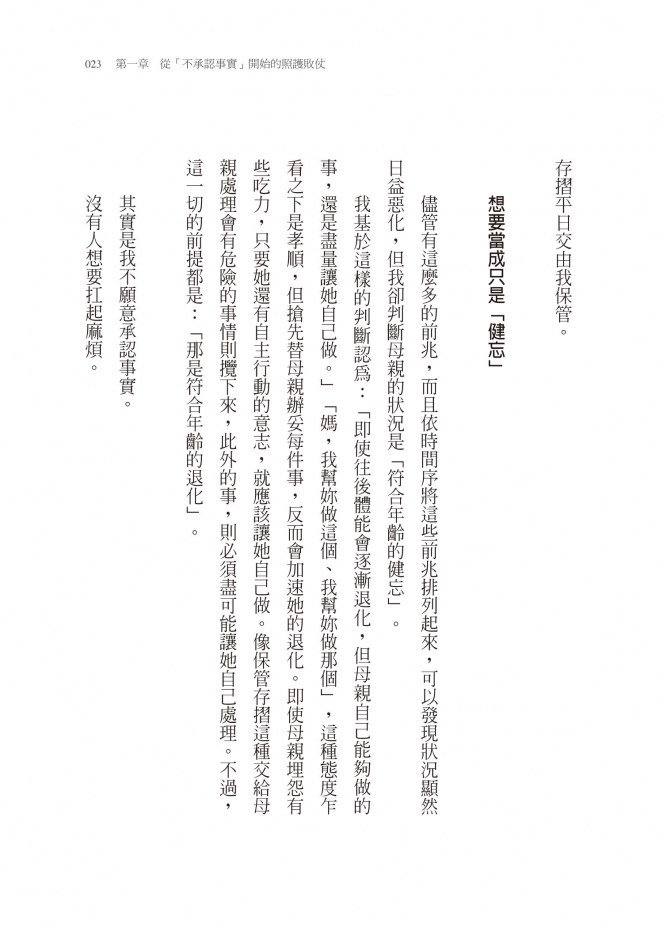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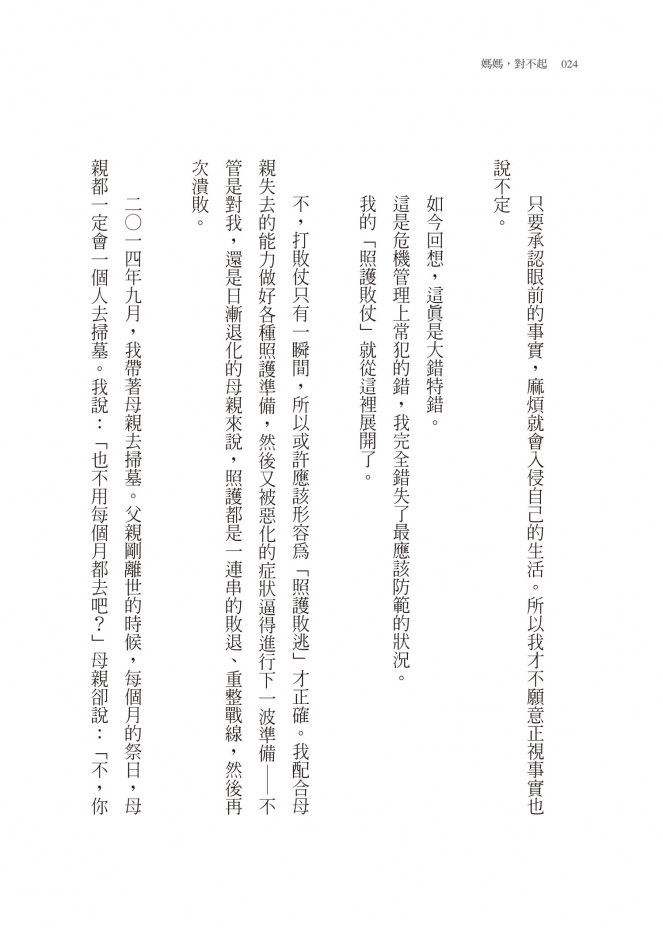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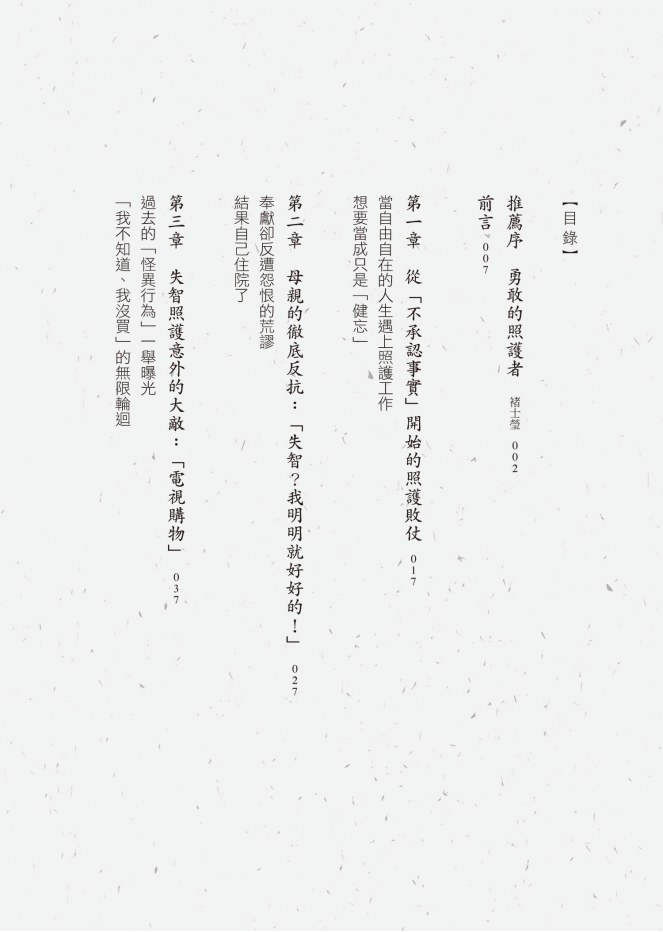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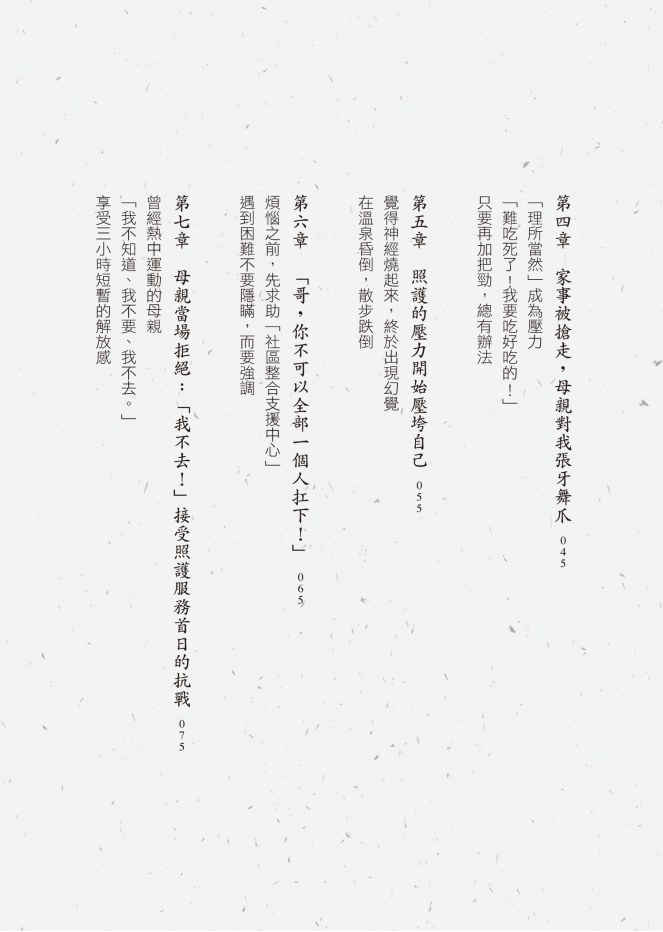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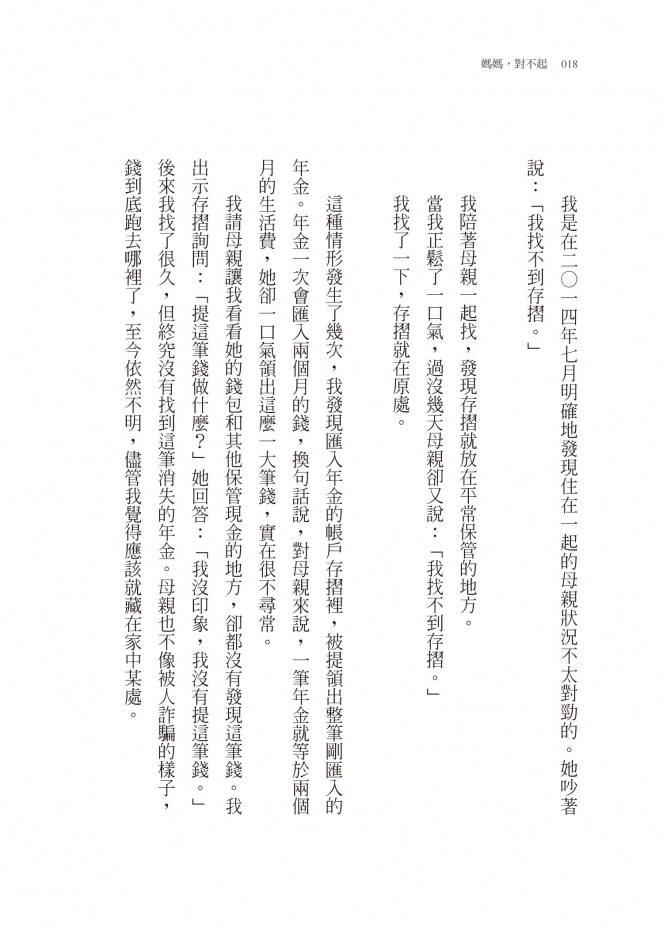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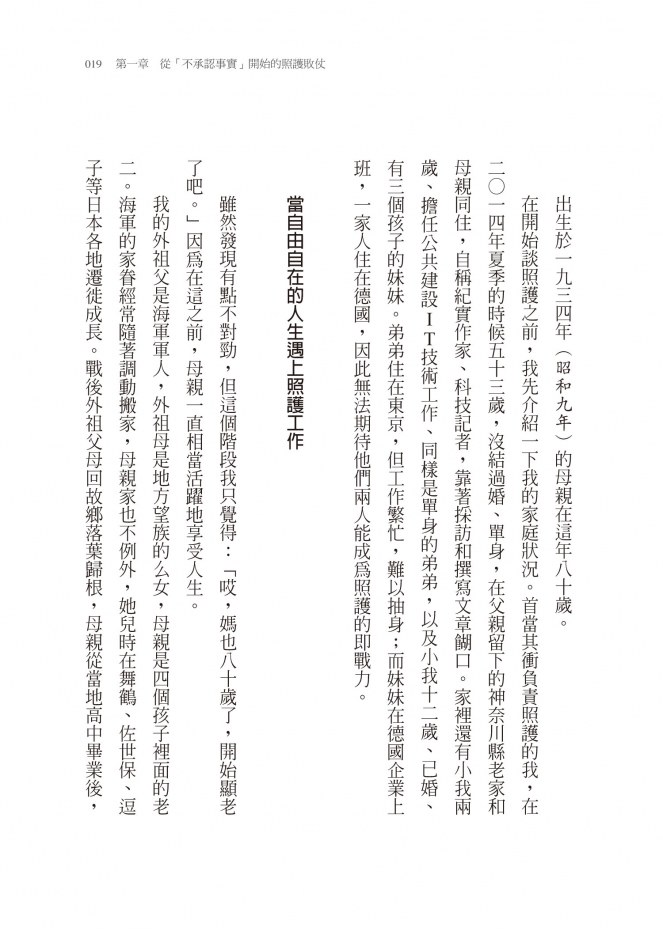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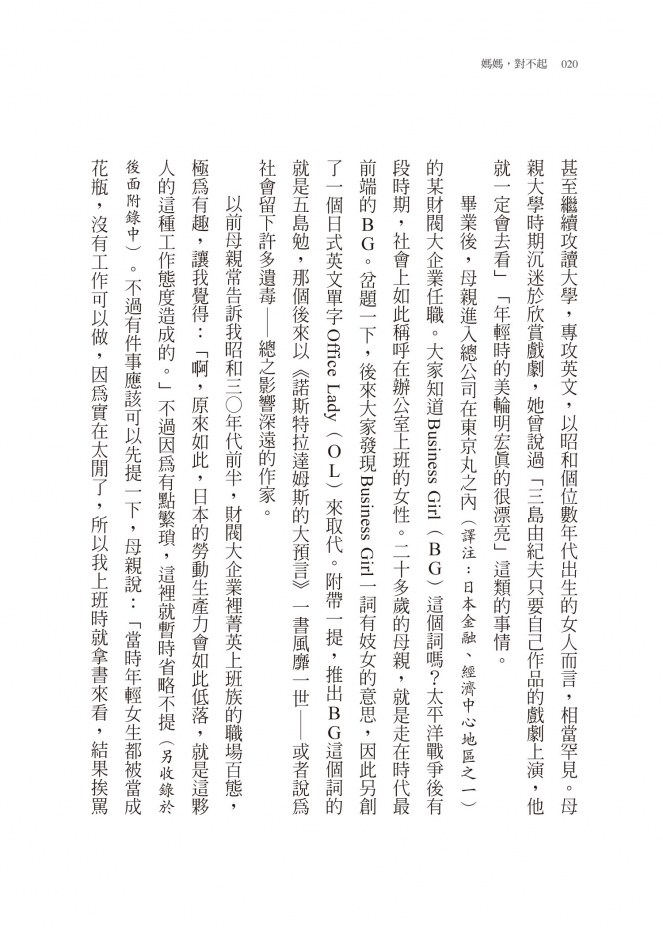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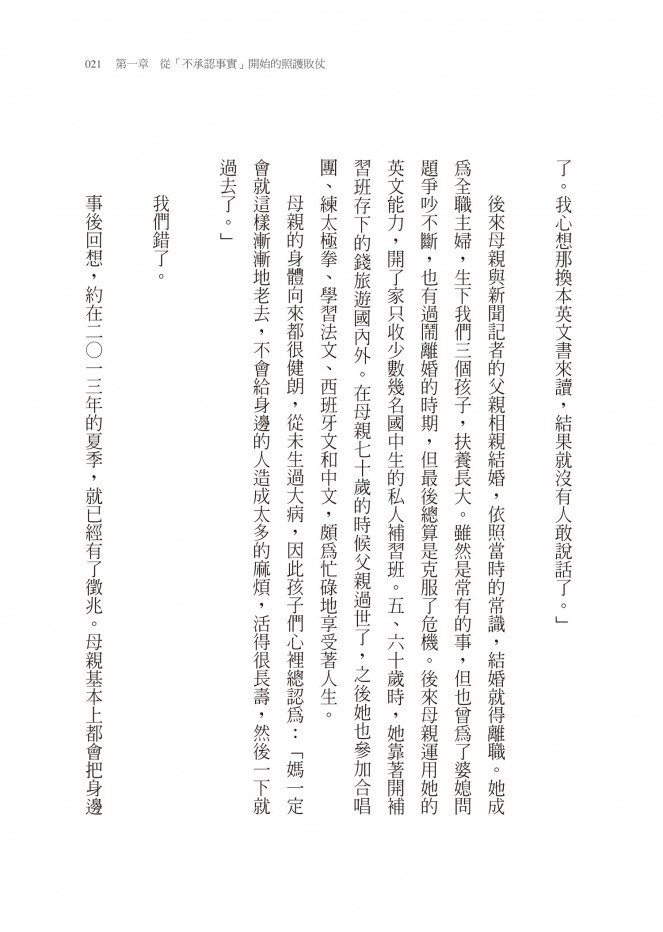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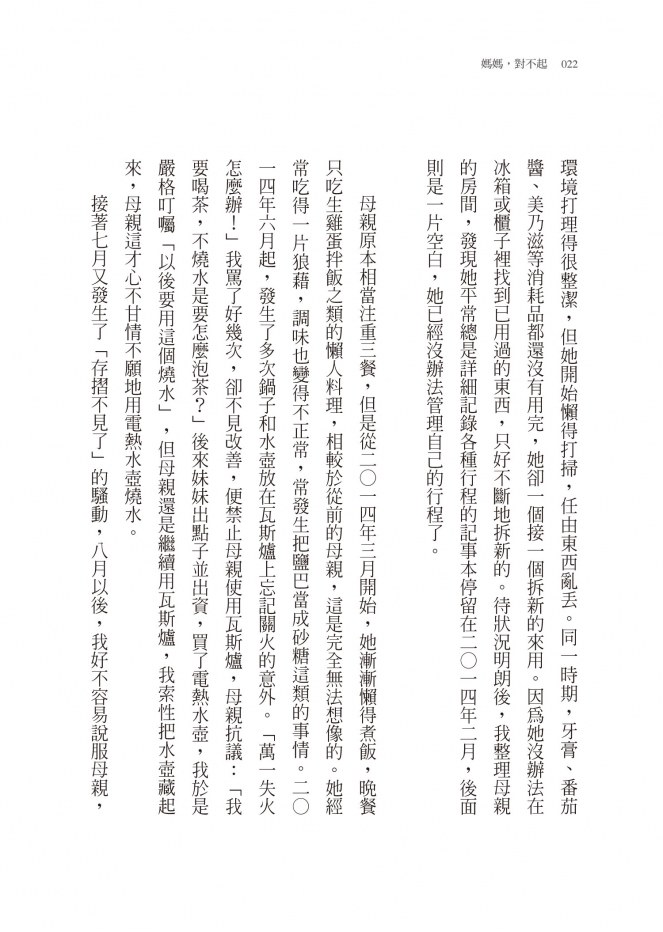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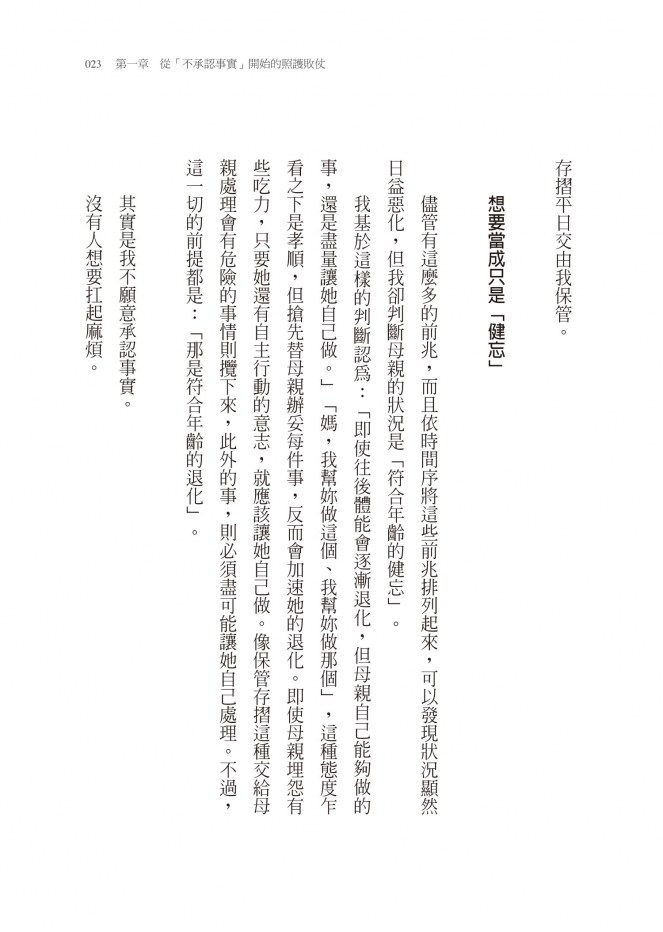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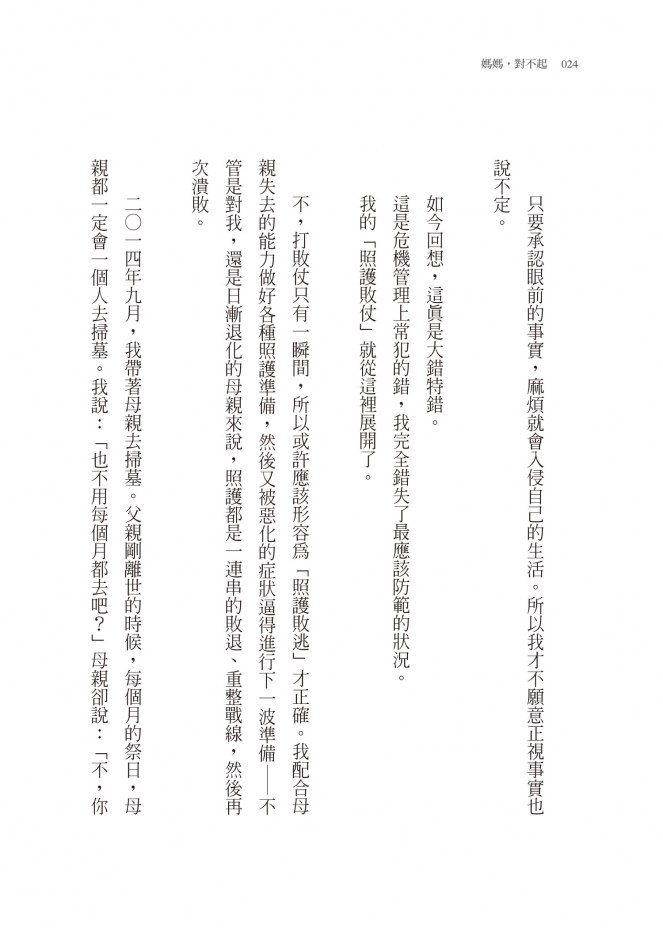
.jpg)


.pn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