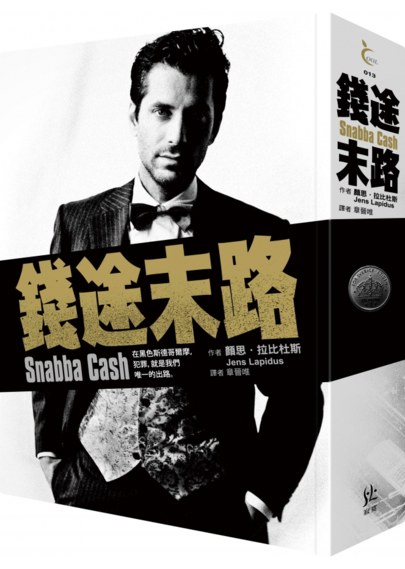日復一日,瑞秋固定搭乘早晚兩班倫敦通勤列車。
列車每天準時在同一站停靠,透過車窗外掠過的景象,她窺見了軌道旁15號住戶的生活片段。她想像那對陌生夫妻過得很幸福,還給兩人分別取了名字,在腦海中編造他們的人生。有時候,男主人的目光似乎盯著車廂裡的她……難道,在疾駛而過的瞬間,他也認出了她?
一天早上,瑞秋從新聞頭條得知,15號女主人竟已失蹤多日。她這才想起,車窗外的景象似乎曾透露不尋常的線索。但就在當晚,警方找上了瑞秋,要為失蹤案約談她。
這是怎麼回事?只在想像中互動的陌生人、隔絕於車窗之外的事件,為何開始與她有了交集?
這是所有通勤族的未知惡夢。《列車上的女孩》以列車移動觀點講述一個停不下來的故事,小說從女主角每天搭乘的早上08:04、傍晚05:56兩班通勤列車寫起,巧妙將車窗裡、外的陌生人兜在一起,交織出懸念強烈的情節。
新書消息一出,立刻在歐美文壇掀起一陣扼腕的哀嚎:
「以通勤列車作為敘事切入點?可惡,好創意被人捷足先登了!」
現在,請站好了。因為你即將踏入車廂了。7/30,你的通勤習慣即將改變。
.jpg)
◎瑞秋
2013年 7月5日 星期五
〔早上〕
鐵軌旁有一件衣服,淺藍色的,像是襯衫,跟髒髒的白色東西堆在一起。或許是垃圾,有些人會在旁邊的小樹林非法傾倒大量垃圾;或許是處理鐵軌的工程人員留下的,這一段經常施工;也有可能是別的。我媽常說我太愛幻想。我沒辦法。只要看見這些東西……髒T恤或單隻鞋子丟在路邊,我就忍不住要想到另一隻鞋,和那雙穿鞋的腳。
火車搖晃顛簸,發出尖銳的磨擦聲,再次起動。那一小堆衣服漸漸看不見了,我們輕快地朝倫敦開去,節奏像慢跑。坐在我後面的人煩躁無奈嘆了口氣,八點四分這班從艾胥伯里到尤斯頓的慢車對於耐性是種考驗,連最資深的通勤族都受不了。照理說車程應該是五十四分鐘,可是很少準時,這段鐵軌太破舊,號誌老出問題,老是在施工。
火車匍匐前進,劇烈震動,經過倉庫與水塔、橋樑與棚屋,經過簡樸的維多利亞式房屋。那些屋子都背對著鐵軌。
我頭靠在車窗上,看那些房子像電影推拉鏡頭掠過。我的角度與別人不同,就連屋主都不見得從這個角度看過自己的房子。我每天有兩次短暫的機會觀看那些人的生活。看陌生人安全在家待著,對我有撫慰的效果。
某人電話響了,鈴聲歡快,顯得有點突兀,好一會兒沒人接。我感覺其他乘客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動,我聽見他們的報紙沙沙響,我聽見他們在筆電上打字。火車搖搖晃晃轉了個彎,在紅燈前放慢速度。我努力不抬頭,努力閱讀走進火車站時拿到的免費報紙,但那些字在眼前變得模糊,沒半篇能引起我的興趣。我腦中依舊浮現躺在鐵軌旁的那件衣服,那一小堆遭人遺棄的衣服。
2013年 7月8日 星期一
〔早上〕
重新坐上八點四分這班火車,是種解脫。我並不是迫不及待想回倫敦展開新的一週……我沒特別想去倫敦。我只是想坐厚厚軟軟的絲絨椅,靠在椅背上,感受陽光照進窗來的溫暖,感受車廂在鐵軌上前後搖晃的節奏,那種節奏有撫慰的效果。坐在這裡看鐵道旁的房子,比去其他任何地方都好。
半路上某一處號誌出了錯。我想應該是出了錯,因為老是紅燈,我們常在同一處停下,有時候只停幾秒,有時候會停幾分鐘。如果我坐的是D車廂,而火車在這個號誌前停下,那麼我就有絕佳視野來看鐵路旁我最喜歡的房子:十五號。
十五號跟鐵路旁其他的房子並沒有太大不同,都是維多利亞式的連棟房屋,兩層樓,俯瞰狹窄的花園。那片花園照顧得很好,向前五、六公尺就是圍欄,和鐵道之間隔著幾公尺無主地。這房子我熟得很,我認得每一塊磚,知道浴室窗框上的漆剝落了,還知道右手邊的屋頂缺了四塊瓦。
我知道,住在這座房子裡的人,也就是傑森和潔絲,在溫暖的夏天傍晚偶爾會爬出大大的格子窗,坐在廚房延伸出去的屋頂上。他們是完美的金童玉女。他有一頭黑髮,身體強壯,性格和善,對她愛護備至,笑聲很好聽。她是小鳥依人型的美女,皮膚很白,金色頭髮剪得很短,臉型和髮型很合,輪廓分明,高聳的顴骨上雀斑點點,臉頰到下巴的角度很漂亮。
火車讓紅燈擋住的時候,我就尋找他們的蹤影。潔絲早上經常在外頭,尤其是夏天,她會在外頭喝咖啡。我覺得有時候她也在看我,與我遙遙相望,我好想揮手。但這不太可能,應該是我想太多。傑森就沒那麼常見,他多半時間在外工作。即使他們兩個都沒出現,我還是會想他們在做什麼。也許今天早上他倆都休假,她還在床上,他在做早餐;也許他倆一起去跑步了;也許他們都在浴室裡,她雙手抵著牆,他雙手在她腰上。
〔晚上〕
我稍微轉身面對車窗,背對車廂裡的其他人,打開一小瓶酒。這是剛在站內小店買的,不冰,可是還行。我在塑膠杯裡倒了些,蓋上蓋子,放回包裡。星期一在火車上喝酒人家比較不能接受,除非你有伴,但我沒有。
車上有許多熟面孔,我每星期都看著這些人往來倫敦,看久了臉就熟了。或許他們也認得我的臉孔,只是不曉得看得看不出我到底是怎樣的人。
這是個美好的黃昏,溫暖卻不悶熱,太陽懶懶西下,影子漸漸拉長,暮光為樹鍍上了金邊,火車輕快前行,掠過傑森和潔絲家,沒有暫停。有時候,只是有時候,假如對向鐵道沒車,我們的車又開得夠慢,我就能隔著鐵道瞥見他們在露台上。如果不能,例如今天,我也能想像,想像潔絲坐在露台上,腿蹺在桌上,手拿一杯葡萄酒;傑森站在她身後,手放在她肩上。我能想像他雙手的觸感、重量,那種讓人安心的感覺。有時候,我發覺自己試圖回想上一次與他人的身體接觸,像是擁抱或真心握手之類的,竟想不起,心就會揪起來。
.jpg)
2013年 7月9日 星期二
〔早上〕
上星期看見的那堆衣服到現在還在,看起來比之前更髒更慘。我在某處讀過一段文章,說火車撞人的時候能把衣服撞掉。火車撞人不常發生,據說一年兩、三百起,但兩天也至少有一次。不知道那裡面有多少是意外事件。火車經過時,我仔細地看,想看衣服上有沒有血。
沒看見。
2013年 7月10日 星期三
〔早上〕
氣溫持續攀升,才剛過八點,就悶熱起來,空氣又熱又濕。要是來場暴風雨多好,可天空硬是半點雲也沒有,就那麼一整片淺淺的水藍。我擦去嘴唇上方的汗水,後悔忘了買瓶水。
今天早上看不見潔絲和傑森,實在很失望。這樣很傻,我知道。我定睛搜索整棟房子,什麼也沒看見。樓下的窗簾拉開了,但落地窗關著,玻璃反射著陽光。樓上的格子窗也關著。傑森可能上班去了,他是醫生,我想,說不定還是為海外機構工作的,必須隨時待命。行李打包好了,放在衣櫃頂上,一旦伊朗地震或亞洲海嘯,他就會放下一切,抓起行李直奔希斯羅機場,飛往災區救死扶傷。
潔絲呢,她穿圖案大膽的衣服和Converse運動鞋,又有美貌和態度,應該是在時尚產業工作的,要不然就是在音樂界,或廣告界。她可能是設計師或攝影師,同時很會畫畫,很有藝術天分。我彷彿能看見她,在樓上多餘的房間裡,開著窗,拿著畫筆,音樂震天響,巨幅畫布靠在牆上。她會在那裡待到半夜,傑森不會去打擾她工作。
當然了,其實我並無法看見她。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畫畫,不知道傑森笑聲好不好聽,也不知道潔絲臉型漂不漂亮。我從來沒有近看過他們。我住那條路上的時候他們還不住那裡,是我兩年前離開後才搬來的,確切的時間我不曉得。大約一年以前,我注意到他們,然後漸漸地,對我來說,他們變成了重要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只好自己取。叫他傑森,是因為他帥得像電影明星,而且是英國明星,不是強尼戴普或布萊德彼特那種,而是柯林佛斯那種。叫她潔絲,是因為這名字跟傑森很配,跟她也配。像她這種長得漂亮又無憂無慮的人,很適合叫潔絲。他倆很相配,簡直就是天作之合,我看得出來他們很幸福。他們就跟我從前一樣。
2013年 7月13日 星期六
[早上]
不用抬頭看鐘也知道,現在是七點四十五分和八點十五分之間,因為陽光的亮度,因為窗外的聲音,因為室友凱西正在我房門外的走廊用吸塵器。
***
我整天待在房間裡,等凱西出門,好去買酒。可是她沒出門。她穩穩坐在客廳裡,說要加個小班,處理一點公司的事。我覺得自己好像在關禁閉,無聊得要命,不到中午就受不了了。我跟她說我要去散步,然後跑去大街上那家毫無特色的酒吧,喝了三大杯葡萄酒,外加兩杯傑克丹尼爾威士忌。又在火車站買了幾罐琴湯尼,上了火車。
我要去見傑森。
我不是要去拜訪,不是要去他家敲門,不是那樣的,我沒打算做那麼瘋狂的事。就只是想坐在火車上,遠遠看那房子而已。我沒別的事好做,也不想回家,我想見他,看見就好。
這不是個好主意,我知道這不是個好主意。
但也不會有什麼害處吧?
我會坐到尤斯頓,再坐回來。(我愛火車,這有什麼不對?火車很棒的。)
啊,快要經過他們家了。
陽光太強,我看不太清楚。(東西都出現疊影,我閉上眼再睜開,好多了。)
看見他們了!那是他嗎?他們站在露台上,對吧?那是傑森嗎?是潔絲嗎?
我看不清楚,好想靠近一點,好想靠他們近一點。
我要在惠特尼下車。
這不是好主意。
***
車廂另一邊有個男的,頭髮顏色沙金偏紅,對著我笑。我想對他說點什麼,可是話老是還沒出口就蒸發不見,我彷彿嚐得到那些字句的味道,卻嚐不出是酸是甜。
他的笑是不是嘲笑呢?我也分辨不出。
2013年 7月14日 星期天
[早上]
我的心臟好像在喉嚨底下跳,跳得好大聲,好不舒服。我翻身側臥,臉轉向窗。窗簾關著,但透進來的光還是刺痛眼睛。我伸手按住眼皮,想揉掉痛楚。我的指甲好髒。
不對勁。有那麼一秒,我覺得床消失了,我的身體失去了支撐,一直往下沉。昨天晚上出事了。空氣猛然吸進肺裡,我坐起來的動作太急,心跳好快,頭好痛。
我等了一會兒,等記憶恢復。有時候要花點時間,有時候它幾秒鐘就會出現眼前,有時候永遠不會出現。
昨晚發生了某些事,很糟糕的事。吵架,大小聲,有動手嗎?我不知道。我去了酒吧,上了火車,到了車站,出了大街,布倫海姆路,我去了布倫海姆路。
黑色的恐懼像海浪向我襲來。
昨晚出事了,我知道,雖然想不清楚,但感覺得到。我嘴裡有傷,好像是自己咬的,舌頭嚐得出血的味道。我噁心想吐,頭暈目眩。我摸摸頭髮和頭皮,痛得縮手,頭右邊腫了一塊,軟軟的,很痛。凝結的血讓頭髮糾結在一起。
我跌倒了,在惠特尼車站的階梯上跌倒了。有沒有撞到頭呢?我記得火車上的事,可是在那之後有一大段空白。我深呼吸,想放慢心跳,平息胸中升起的焦慮感。好好想想,做了什麼?我去了酒吧,上了火車,有個男的……我想起來了,他髮色偏紅,對我笑。我想他對我說了什麼,內容我記不得了。應該不只這樣,還有別的,可是我腦子一片空白,想不起來。
我很害怕,而且不知道自己在怕什麼,這就更可怕了。我甚至不確定是否真有值得害怕的東西。環顧四周,手機不在床頭櫃上;包包不在地板上,也不在平常掛的椅背上,但它一定沒丟,因為我在屋子裡,表示有鑰匙開門。
我爬下床,發覺自己一絲不掛。往衣櫃的全身鏡望一眼,我的手在抖,睫毛膏抹髒了臉,下唇破了,雙腿多處瘀青。我想吐。我坐回床邊,把頭埋進雙膝之間,等噁心的感覺過去,然後起身抓起睡袍,把門打開一個小縫,聽外面的動靜。
到了樓梯邊,頭又暈了,只好緊緊抓住欄杆,滾下樓梯摔斷脖子是我最大的恐懼之一(另一個是肝壞掉,內出血),想到這裡我又想吐了。我想躺下,可是得先把包包找到,檢查手機。至少得先確認信用卡還在,搞清楚我在什麼時間給什麼人打過電話。我的包包丟在一進大門的地上,牛仔褲和內褲脫在旁邊。一下樓梯就聞到尿味。我抓起包包找手機……還在,感謝主。包裡除了手機還有幾張皺皺的二十元紙鈔,以及染了血的面紙。噁心感又來了,這次更猛,酸水湧上喉嚨,我趕緊朝廁所跑,可惜半路就吐在樓梯地毯上。
我得躺下。如果不躺下,就要昏倒摔下去了。這些東西我待會兒再清理。
到了樓上,我先把手機插上充電器,再躺上床,小心翼翼檢查四肢。雙腿瘀青,位置在膝蓋上方,那是醉後的標準傷,走路東撞西撞造成的。手臂上的傷就比較令人擔心了,那些橢圓形的瘀傷像是指印,有可能是犯罪痕跡,但也可能是我跌倒之後,有人幫忙拉我起來。
這種事情從前發生過。
.延伸閱讀:連破出版史多項紀錄的小說,竟是她寫作夢想的最後一搏
.下一站直接駛入:《列車上的女孩》







.jpg)








.jpg)
.jpg)